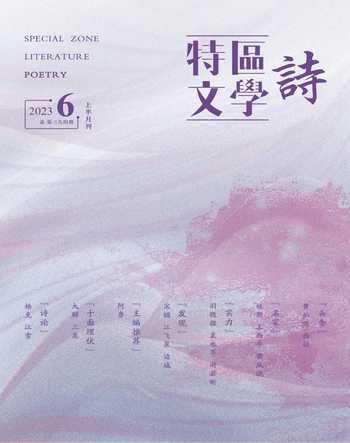隐秘与沉默:灵魂不朽的不确定性
第一次结识青年诗人阿鲁,是在广东中山。当时受邀参加由诗人、企业家倮倮和乡党诗人、小说家马拉一起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诗歌音乐节。第二次见到阿鲁,是在诗人余丛居住的崖口公社荔枝园。第三次见到阿鲁,则是在广州倮倮诗歌创作研讨会上。有一次,马拉在青年作家蒲荔子于广州创办的民宿里对我郑重地谈及阿鲁。马拉告诉我,阿鲁是一个极具才华却又十分低调的80后诗人,国内没有多少读者和朋友关注到他的诗歌写作,更没有多少杂志愿意发表阿鲁优秀的诗作。时间转眼过去了两年,尽管大家都很忙,但是我一直记着马拉跟我说过的话,我也一直记着阿鲁年轻、纯朴而腼腆的微笑。他话不多,总是面带笑容,热情而细心。几次去中山和广州,总会与他相遇,忘不了他一路对我的照顾,更是忘不了心里一直存着的念想:一定要读到阿鲁的诗。2018年的冬天,应我邀约,阿鲁给我发来了他近年的一批诗作,并且和我进行了一个访谈。我对诗人阿鲁诗歌写作的了解,可以说,是从这个冬天开始的。读完阿鲁所有的诗作,我陷入寂静而沉默的忧伤之中,我被他的诗感染,也被他的访谈感动。阿鲁虽然年轻,但是通过他的诗歌写作可以读出他对这个世界的隐秘表达与理想眺望。阿鲁是一位既优雅又忧郁、既炽烈又寂静的诗人,他的诗歌表达出来自乡村的八零后所经历的疼痛的变革时代,包括故乡与异乡,和诗人眼中所洞察的一切:诗意,纯粹,孤独与绝望。
阿鲁出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15岁以前还没有接触到诗歌,而接触到的所谓的文学,除了语文书上的课文,再就是在成年人中传阅的武侠小说。直到有一天,阿鲁上了高中,因为作文写得好被推荐当上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并且从此时开始知道,台湾著名诗人洛夫就是从衡阳走出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阿鲁就是受到地方大诗人洛夫的影响,而走上诗歌之路的,并且从16岁时起,便开始了有意识的诗歌写作。阿鲁的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叫《瘦死的树》,发表在1998年第12期的《星星》诗刊。阿鲁自己认可的诗歌写作,则始于2014年。他原以为走出学校之后,整个世界都会为诗人敞开,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为了谋生,他几乎要完全放弃自我。彭燕郊主编的一本《国际诗坛》陪伴了阿鲁将近十年,阿鲁才慢慢融入城市生活圈,开始与更多外地诗人交流,也慢慢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想藏书。阿鲁说,因为那本《国际诗坛》,他被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深深打动,后来通过对布罗茨基的阅读,又逐渐接触到外国重要诗人奥登、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爾施塔姆、米沃什、策兰、阿米亥。如今,阿鲁依然热爱着这些伟大的诗人,并且热爱的诗人还在不断增加。为此,阿鲁说:“从他们的作品里,我对诗歌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看见,或者说见证,在我看来,是诗歌的意义所在。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诗,‘借助语言的/放大镜,他释放了被囚禁的审判,语言对于诗人而言,就是一面‘放大镜。当然,‘放大镜的功能并不是为了鼓吹,而是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或许我们也可以稍稍修改一下布罗茨基的一个比喻,诗歌不但是一只朝向未来的望远镜,也是一只朝向过去的望远镜。米沃什、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的诗性随笔,每次重读都能给我启示。与其说是关于诗歌的启示,我更觉得是关于生命的启示,关于理解的启示。当然,他们的诗歌,给我的影响更深远。”
说了那么多,我们需要安静地阅读阿鲁的诗:
她的脸就像这片辽阔的树林
一小片灯光
让我从她的黑暗中脱身
事实上,并没有一盏灯
可以照亮她。在黑暗中,不被看见
比看见更真实,更令人绝望
就像她要开口说话
一只鸟从太阳底下飞过
而整片树林都在等候着,默不作声
—《火车上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阿鲁的这首《火车上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深深地打动了我,或者说,自读了这首诗,我已意识到阿鲁是一个不简单的80后诗人,他的诗性早熟以及对诗的敏感性得到了证实。从此诗的叙事语调、抒情背景与诗人的审美趣味以及诗人对他时代的记忆、历史的关怀与畅想,已经可以看出,在创作一首诗时所需要的冷静、成熟与思考,以及与时代性叙事关联的想象力,他全部具有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一份俄罗斯“历史的证词”,更是俄罗斯20世纪文学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阿鲁仅仅摄取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中的一个黑暗而诗意的场景,这种巧妙的摄取诗歌意境,然后再营造出一种“阿鲁式”的诗歌语境。它是迷人的,是幽暗的,也是让人悲伤的。诗人从黑暗中的树林写到黑暗中的灯,写到太阳底下的一只鸟,诗人在最后一节象征性道出了人类“追求光明、驱除黑暗”的终极理想,而这只鸟正隐喻了诗人心中的诗人,它也可以是曼德施塔姆夫人传承下来的自由精神的化身。人们常说,一首好诗足以让它的读者永远地记住它的作者。希望未来有人读到《火车上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就会想起诗人阿鲁。
从阿鲁近十年的诗歌作品中,可以感知到他的诗歌学养的现代性源头,主要来自现代西方诗歌,因而又可以感觉到他的诗歌起点不低。有一些诗作是他在阅读欧美诗人时留下的诗意思考,除前面提到一首之外,还有《中秋节祷告》《旋梯》《读普拉斯的<爹地>》《“别埋掉我”》《悼特朗斯特罗姆》《保罗,你应该去维也纳》等。这些诗歌有着鲜活而沉郁的现代诗学气息,诗人试图通过自己的阅读感悟与时代叙事之间建立一种隐秘的个人话语方式,我甚至能从阿鲁的部分诗歌中读出诗人策兰对他的精神性影响,包括策兰诗歌中的修辞方式。这种现代性的诗歌修辞的学习与创作是可行的。更为可贵的是阿鲁从这些杰出诗人的诗歌中汲取了普世思想的精神源泉:
小男孩法理德·舒基无力地
躺在病床上,苦苦哀求。
他曾眼看着家人和朋友不幸去世,
他害怕地下的黑暗和冰冷。
是谁召唤了脾气暴躁的怪兽,
他来不及跑回房间,拿上他的电光剑。
法理德·舒基的头,被一整个地球击中,
他的恳求,就是他最后的抵抗。
他等着父亲过来,
合上他流着血的双眼。
—《“别埋掉我” 》
2015年10月,一个名叫法理德·舒基的6岁也门男孩,在玩耍时被导弹爆炸产生的碎石击中,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他曾哀求“别埋掉我”。阿鲁看到这个国际社会新闻之后,便写下了这首诗,并且在标题下面加了一个题引,引注了波兰诗人米沃什《桌子》中的一句名诗:“我相信我的恳求会带给时间一个停顿。”从而为读者创设了一个解读此诗的通道,这种题引的修辞手法,阿鲁在诗歌中多次使用过。引注如果使用得恰当、得体而深刻,无形中会给诗歌作品带来解读的密钥,也会给诗歌生发出更多的诗意与张力,甚至可以阅见诗人的精神向度。《“别埋掉我”》《没有一块墓碑能容纳你的爱》《坦克诗》等,则显现出诗人正在自觉地承受来自现代性的人文精神与道义。这种诗学正义的表达,不禁让我想起曼德施塔姆1922年在《词的本质》一文中所言:“对于俄罗斯,脱离历史、背离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远离自由和目的论,这一切就等同于脱离语言。两三代人的‘失语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来说,脱离语言等同于脱离历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俄罗斯历史走在边缘上,走在岸边,走在悬崖上,它随时可能跌进虚无主义,即脱离语言。”而从阿鲁的诗歌作品中,我看到了新一代中国诗人在汉语诗歌独立精神上的探求,这也是阿鲁诗学品质中极为重要的精神光亮,同时,也是一种同时代人的精神表达。一个成熟的诗人,正是应该探求到属于自己的独立诗学面貌,哪怕它是艰难的,曲折的,遮蔽化的,只要他努力坚守人性的、自由的诗学源头,必然会让自己成长为一棵大树。我很高兴,作为阿鲁的朋友,我从他的诗歌写作中,看到了一种不凡的诗歌气象,不凡的个体诗学格局。
春天隔着一扇门
抚摸死者体内的花朵—
他毕生追求的
这些花朵,现在开得多么鲜艳
而孤独
—《清明述怀》
阿鲁在诗歌中多次抒写到“死”与“死亡”。除了《清明述怀》,再比如:“是的:沉默,即意味着获救/ 从死亡这粒善良而慷慨的种子”(摘自《后田园诗》);“它还在呼吸//守夜的人们/在星光下沉睡”(摘自《墓石》);“忍冬花的清香/更像一次死亡练习:/言辞不过是时间投下的阴影,/谁也无法从中/完好无损地逃离”(摘自《梦见一头牛对我说话》);“诗歌/从死亡/带回节奏/喋喋不休的/争论/加深了夜色”(摘自《旋梯》)等,占有较大的篇幅。“死亡诗学”是当今中外诗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诗学主题,学者、批评家江弱水在《诗的八堂课》中独辟一章谈论“死亡”,一针见血地指出:“20世紀中国新诗,对死亡书写同样表现出超常的兴趣,一位诗人如果没有写过死亡,简直都不配称之为诗人。看上去是对西方横的移植的结果,但是,死亡并非中国人的异己体验,它也是我们的切身之事,萦心之念,是我们形而上学和美学的最高命题。”阿鲁在诗歌中叙述或论及的“死亡”,包含了多重的意象与语义,既有现实的,亦有虚幻的;既有形而上的,亦有历史与记忆的。当我们在谈论死亡时,其实我们是在谈论灵魂。笛卡尔说:“我们的灵魂不死,它们在我们的身体消亡后依旧完好无损。”柏拉图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对话录《斐多篇》中即谈到“灵魂不朽”。柏拉图说,“最好给灵魂不朽穿上一件传奇色彩的外衣。”“死亡诗学”的本质,一方面呈现的是生命的“悲剧意识”,另一方面是诗人自觉于诗思中探求“灵魂不朽”的后遗症状:“死后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乌纳穆诺语)阿鲁诗歌中的隐秘与沉默,让我看到了“灵魂不朽”的不确定性。
阿鲁在诗歌中呈现出的死亡意识,在我看来是有迹可循的。阿鲁从小就生活在湖南乡下,生活在贫穷的小山村里。阿鲁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父亲的一生很平凡,也很悲凉。他说,他父亲每年都会在腊八节的时候在家门口贴上大大的“福”字,但直到父亲去世,家中依然一贫如洗。但少年阿鲁那时候对贫穷没有任何概念,相反他感觉自己过得很开心。阿鲁说,他的父亲在艺术上并没有怎么影响过他。但是,在阿鲁15岁那年中考时,他用父亲给他的零花钱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文学书《红楼梦》。拿回家后,他的父亲先拿去看了。后来他还书给阿鲁时说:“这本书没那么容易读懂,如果你真读懂了,生死也就参透了。”阿鲁说,这是父亲对他说过唯一的一句关于生死的话题,关于文学的话题。大概一个月后,父亲便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工地上罹难了。阿鲁说,父亲的死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他对父亲的思念里。阿鲁在《饮酒诗,献给父亲》(2014)中写过如此沉痛的诗句:“你不曾告诉我的/ 如今都密谋着向我扑来……”正是这种父爱的缺位,成为阿鲁的父亲带给阿鲁的另一种影响。
在父亲去世前,阿鲁并没有这种感觉。在父亲去世的前半年时间里,阿鲁也没感觉到很沉痛的悲伤。当然,阿鲁跟父亲的感情并没有出问题,是很传统的父子感情,不善于表达,但是都默默地爱着彼此。直到父亲去世半年后,阿鲁才慢慢发现,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久失去了,诗人再也无法抵达那种生命与情感的圆满状态。
长诗《十月悲歌》是阿鲁诗歌创作中的一首重要作品,也是诗人沉痛怀念和哀悼父亲的长诗,要想了解阿鲁的诗歌创作全貌,绕不过这首长诗。《十月悲歌》写得朴素而深挚,读来催人泪下,此诗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父子情,以及诗人从“父亲之死”中所参悟的生死之痛;或者,从诗学的层面而言,此诗饱满而深情地反映出诗人的身心困境,包括诗人所遭遇的与怀想的哀悼与乡愁:“我向着父亲奔跑/就像那年冬天一样/在雨里奔跑,在雪地里奔跑”“而那扇关着你的门/已经发黑,黑得再也关不住任何事物/黑得再也无法把它打开//你的离去,让这个村庄/荒废了这么多年/它一直都是你的,从来没有属于我”
相对于长诗而言,阿鲁的短诗写得更为出色,并且他的短诗占有更大的篇幅。无论是关注一个诗人,还是评述一个诗人,作为批评者,我十分重视诗人的精神素质与诗歌学养。从阿鲁的短诗创作的观念与现状来看,已经整体趋向于成熟与独立。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却又有着城市生存背景的诗人,阿鲁有着真实而敏感的诗性自觉与语言沉默,这些在命运共同体与诗意体验中生发出的诗歌品质十分可贵。阿鲁说过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诗歌最无法忍受的,除了布罗茨基所说的‘同义反复以外,还有‘谎言,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强加给我们的,一方面是从我们思想的内部滋生的。外部强加给我们的谎言,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扫雷一样的清除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新的雷区在我们周围不断生成。从我们内部滋生的‘谎言也是当前很多诗人惯用甚至自以为聪明的手段。通过这两种手段创作的作品,都不可能描绘出真实的、能瞬间俘获读者心灵的诗歌。而要对抗这种强加给诗歌的暴力,那就需要诗人保持诚实、敏锐的品质。”
人群散去,怀着各自的心事。
满地落叶,废弃的纸屑,随手扔掉的空瓶子。
耸立的雕像之上,是落日。
广场仿佛冥想的僧侣。
这个黄昏,“我”无处可逃
在这两者之间,只剩下孤独的影子徘徊。
—《人群散去》
《人群散去》,是一首想象之诗,一首介入之诗。我喜欢阿鲁如此风格的短诗,这些短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诗人擅长把自己的心绪与思考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与语境之中,它们可以是过去的记忆,也可以是未来的眺望,或者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征象。阿鲁善于营造一种策兰式的叙事停顿与米沃什式的现实拷问,抑或流露出叶塞宁的忧郁与灵光,从而让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歌时,会感受出一种整体性的诗歌气息,阿鲁式的纯净,阿鲁式的气息与意境。他的诗歌总会洋溢着忧郁而动荡的爱,真挚而敏锐的情感。他的诗既关乎个体的命运与情感,也关乎人类普遍的美德与孤独:“一只鸟,在黑暗中醒着/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包容//沉睡的天空,橡树之上的星宿/只有它能唤醒//特别是在风雨平息的夜晚/当它收拢翅膀时”(阿鲁:《悼特朗斯特罗姆》),“仿佛从一片松树林吹来/带着山谷微微升起的寒意// 身体逐渐敞开,在秋日清晨/如一只打着响鼻的牛牯奔向田野/呵,这片刻的欢娱稍纵即逝”(阿鲁:《回乡偶书》)阿鲁曾经迷恋过绘画和音乐,但最终阿鲁选择了诗歌,他意识到“只有诗歌能够让我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因而,诗歌成了阿鲁精神成人的自我启蒙之物。阿鲁切身感受到的人类所有的情感与美德,善的、恶的,均已被他匿藏于诗意之中。阿鲁在与我进行访谈时,说过一段深刻的话,我十分激赏,这段话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阿鲁的诗歌。就让他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吧:
在我的观念里,诗歌不是一门艺术,诗歌也不是用来回应或者诠释哲学的,而是从生活中、从现实中发现“哲学”的,如果非要提及哲学这个词的话。哲学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存在”的状态、关系与秩序,哲学不是用来指导现实的,而是用来理解现实的,是用来“擦拭生活的潮湿与迷茫”的。正如诗人阿米亥所言,“诗人总得在外面,在世界里—诗人不能把自己關在书房里”。
江雪,当代诗人、批评家、艺术家。原名江山,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著有诗集《汉族的果园》《江雪诗选》《牧羊者说》《幼年与历史》,评论集《后来者的命运》《理想与棱镜》,摄影集《饥饿艺术家》,编著《保罗·策兰年谱》等。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国内诗歌节、艺术节及学术交流活动,部分诗文被译为英文、德文、韩文发表,并入展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顾问,“Acquired·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创始人,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后天》杂志主编,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黄石书画院)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