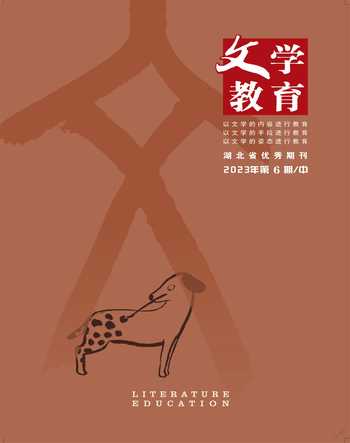论《现实一种》中的暴力叙事
邱心怡
内容摘要:暴力叙事作为一个复杂的审美范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醒目特质。从晚清到中国现代乃至当代,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社会现象的呼唤,作家们常倾向于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暴力叙事这一手段,在发挥启蒙作用的同时对社会进行重新审视。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凭借“暴力”的叙事特点,颠覆了对传统道德理念的理解,体现出先锋小说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余华 《现实一种》 暴力 刑罚 荒诞 意象
《现实一种》是余华早期的作品。本该和乐的一家子最后互相残杀,上演了一场人性的闹剧。皮皮的错误看似是整个悲剧的开始。在我看来,悲剧早已开始。皮皮无心的杀害比山岗处心积虑的杀害更为残酷,一个孩童在心里种下的不是友爱不是纯洁,而是从虐待堂弟的暴力中得到安慰和快乐。在我们为之惊叹的时候不禁要问,这所有荒诞的一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于是我们看到了,母亲只关心自己日渐干枯的身体而不顾皮皮需要关怀的感受,我们看到了夫妻之间的暴力给皮皮留下的阴影,看到兄弟媳妇之间近乎病态的连环报复,所有的一切也就清晰起来,所有的暴力和扭曲也都可以理解。暴力叙事是本作品的一大特色。
一.暴力叙事的主题——复仇与刑法
“暴力叙事”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以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思想启蒙的一种文学创作倾向。70年代末,中国涌现出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家,但由于其创作手法的刻板,故随着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后,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作家接过形式实验的大旗,挑战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在以往暴力叙事的创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创作意识。通过表层文字的“暴力”表现,反映出深层的时代与社会问题,实现了文学“回归自身”的创作。
余华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发表于《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作者采用零度叙事的手法讲述了山岗、山峰一家人以复仇为主题,不断挑战伦理秩序的底线的故事,整个文本都笼罩着暴力的阴影。“那天早晨和别的早晨没有两样,那天早晨正下着小雨。”[1]作者以饱含深意的一句话开始对文章的叙述,但是随即就将读者拉入一个陌生化世界,去审视那个异化的早晨。自山岗的儿子皮皮无意中杀死了山峰的儿子始,血腥与死亡就成为稀松平常的存在。从扇耳光的冲击声到掐喉管的爆破声,最后到摔下致死的清脆声,儿童皮皮都在用不同的声音去证明生的象征,然而这一切却是以暴力和死亡为代价,复仇的戏剧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当山峰回到家发现儿子死亡已成为事实时,便要皮皮为儿子偿命。随后,山岗一家也发疯似的重复上演复仇的戏码。“兄弟相残已不再是一个道德事件,确切地说,这也不是一个历史理性规范下的伦理事件,而仅仅是一次现代性叙事中的伦理事件,它彻底颠覆了‘亲亲、‘爱仁等历史理性认可的传统伦理。”[2]在山峰因山岗丧命后,山岗又受到山峰妻子的控告接受了枪毙。故事到此并未完结,在文章结尾山岗的遗体被捐赠后,留下的睾丸却移植成功了。不久后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十分壮实的婴儿,下一个皮皮的出世,使山岗后继有人了。文本从皮皮的暴力行为始,经过一个叙事过程又回到皮皮本身而终,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线性叙事描写,构成了一种圆形叙事的结构模式。在一个圆形复仇叙事结束的同时,意味着新一轮复仇的开始。暴力、复仇成为文本世界永恒的存在,而亲情则荡然无存。
刑罚作为暴力手段的特殊表演常常被作家们所青睐,如莫言的《檀香刑》、王小波的《似水流年》、阿来的《行刑人尔依》,等等。当代作家渴望通过对刑罚的叙述进而挖掘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寓意。在作品《现实一种》中刑罚表演也上升到了极致,一家人仿佛“杀人机器”般共存在一个空间下,不断从施刑者到受刑者身份转换,从而完成一出血淋淋的“闹剧”。皮皮以舔血迹的方式来消解山峰的怨恨,却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岗为了给儿子皮皮复仇,让狗舔舐山峰让他活活笑死。作为文本中一个唯一不流血的刑罚,在笑声嘹亮节奏鲜明中的死亡却存在着诡异的残酷。受到惩罚的山岗被拉去行刑,“想起先前他常来这里。几乎每一次枪毙犯人他都挤在前排观瞧。可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倒是第一次。”[3]此时,在这里“看”与“被看”的角色进行了互换。现代许多作家为达到国民性批判这一要求,刑罚与示众常常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行刑的刻画,在《药》中对夏瑜砍头的刻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余华承袭了鲁迅小说的特点,在刻画看客的麻木愚昧的同时,余华对被看者进行新的审视。例如山岗在行刑前寻找自己曾经观看的位置,以一个“被看”的主体去寻找“看客”的新角度,这是麻木到了极致还是想用灵魂观摩自己的死亡?
二.暴力叙事的手法——荒诞叙事
荒诞(absurd)一词由拉丁文(sardus)演变而来,最初的含义是“音乐不和谐”,而后在哲学上指个人与生存环境脱节。荒诞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具有强烈的讽刺功能。在《现实一种》中作者就利用了这种陌生化效果,构筑了一个荒诞的世界。
在余华的诸多作品中,儿童这一身份常常用来讽刺和反映现实。作品中的皮皮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兴趣,他将成人世界的暴力行为复刻在心里,同时又作用于无法反抗的堂弟身上。如同余华所述,“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4]充满暴力血腥的环境所带来的阴影,遏制了儿童的天性在试图打破孤寂氛围的情况下,皮皮的无意识行为展现了在荒诞的时空中儿童的情感缺失与本能选择,暴力在这里成为他的本质存在属性。在皮皮被逼迫舔存留在地上的堂弟的血时,他“伸出舌头试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种崭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放心去舔了。”[5]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6]在这里鲁迅所描述的吃人并非真的吃人,而余华所描述的却带有一丝真的吃人意味。但是两者都是对社会进行控诉,凸显时代与人性的冷漠,以此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文本中荒诞叙事还表现在亲情关系的疏离上。祖母看见孙子倒地而亡,却是吓了一跳,赶紧回自己的卧室。本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却展现出难以透视的淡薄,在这荒诞行为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无知还是对死亡的恐惧?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孩子的母亲身上,“走到近旁她试探性地叫了几声儿子的名字,儿子没有反应。这时她似乎略有些放心,仿佛躺着的并不是她的儿子。”[7]在这里,作者展现出两个层面上的荒诞含义。首先,当她否定倒地而亡的不是她的孩子后,她迅速转为看客的角色,做出了与祖母一样的举动,走向屋内。在讽刺和荒诞的背后展现的是家庭浓烈的分裂感。其次,面对孩子死亡的另一荒诞表现是母亲的侥幸心理和自我欺骗,在极其夸张的自我催眠背后透露出人民深深的麻木。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在她的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把死亡过程分成五个心理阶段,即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在文本中这位母亲所做出的反应就是第一个心理阶段——拒绝。在这里“否认”成为她的缓冲器,但是所激起出的心理防御机制却强大到辨认出是自己的孩子后依然毫不犹豫离开,在荒诞中让人唏嘘不已。
此外,死亡在文章也是作为一个荒诞的存在。在被行刑后的山岗只剩下半个脑袋,本该死亡的他并没有在刑场倒下。作者突破了现实世界的羁绊,让意识清醒的山岗在他笔下大刀阔斧地跨步前行,并且构成与妻子进行正常交流的荒诞情节。随后,山峰的妻子为了复仇以山岗妻子的名义将山岗的遗体捐赠了。作为牙医的余华从解剖学角度展示了死亡。但是对挽救生命为业的医生,余华所用的词却是“瓜分”。在异化的世界里,医生的神圣存在被抹杀,拿着手术刀的他们从救人转向“杀人”。“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8]在手术室外排队等待的医生,正如在等待着施暴的狂欢一般。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商品经济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改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追求物质丰裕的同时,所带来的精神空虚让人们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余华在作品中将思考投射在山岗这个虚拟人物身上,一个高等生物的价值到最后却是从物品的“实用性”角度去考虑,生命本身乃至精神的价值及内涵却被丢弃,在这里价值也被赋予另一种解释。同时,在医生们的解剖狂欢中也暗示了一种社会的暴力风气,当众人都在享受暴力带来的刺激时他们真正想享受的是什么?
三.暴力叙事中的意象
意象是具备美学意义的文学符号,作为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相统一的艺术形象,它不仅饱含作者的创作意图,更是具有独立的象征意义。在作品《现实一种》中,余华也创造了一系列意象,赋予文章多重意蕴。
小说开篇就对文章背景进行渲染:“因为这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星期,所以在山岗和山峰兄弟俩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遥远,仿佛远在他们的童年里。”[9]通过对阴冷萧瑟的环境勾勒,传达出一家人的灰暗生活。但同时,余华又给富有美学意义的“雨”的意象赋予暴力含义。皮皮把雨的声音比作是父亲用手指敲打他脑袋的声音,到最后他逐渐数出四场富有不同含义的雨,在这里也象征着文本将发生四场杀人事件。当雨停了即暗示着第一场杀人戏剧即将上演,阳光照在皮皮身上,一双带有屠杀意味的手伸向表弟,“你想去看太阳吗……我知道了,你是要我抱你”[10]随即,一个生命就此消亡。
此外,由于井的阴森意味,所以作家们常常会选择“井”作为小说的意象来传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中“井”的意象等。在小说《现实一种》中“井”也具有丰富的隐喻内涵性。“他只觉得眼前杂草丛生,除此之外还有一口绿得发亮的井。”[11]这里的井象征着人性的幽暗之处,同时也象征着麻木腐烂的世界,暗示了山岗下一轮的血腥报复。余华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敏感,在描述扑面而来的血腥的红色后作者马上转向“绿得发亮”的描写,这种鲜明的颜色对比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给文本渲染出阴冷、可怖的氛围。
小说中阳光与血的意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伴随存在的。阳光像是一位在场的隐形人物,观看着这一轮血淋淋的屠杀过程。当祖母打开房门,她看见的是涌进来的阳光与地上的一滩血,此时阳光是作为强有力的压迫象征以及审视人性的工具存在,亲情的淡薄在这种压迫下促使祖母马上走回自己的卧室。但同时在小说中又体现出阳光在文学传统中作为光明和正义的象征,“他记得自己一路骂骂咧咧,但骂的都是阳光,那阳光都快使他站不住了。”[12]对于阳光的谩骂,突显出麻木腐朽的人们对于鲜活的恐惧。而后用同样的笔法描写山峰在面对阳光时的天旋地转,这种重复的手法更是显现在光明的照射下人性难以掩盖的腐烂。小说中每一场死亡事件都是在阳光下发生的,“血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耀眼。他發现那一摊血在发出光亮,像阳光一样的光亮。”[13]阳光下的罪行比夜晚更富有恐怖意味,赤裸裸的人性在阳光下沐浴,与正常的现实秩序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一种特殊的超现实韵味。此外,小说对血的意象有着较大笔墨的描写。“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时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14]余华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去书写暴力,给予小说诗意的光晕,在暴力与诗意的互相转换中充满着恐怖美学的韵味。同时,血在小说中也不仅仅是作为自然物质的存在,也象征着血缘关系。“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宗法血缘关系非但未被冲破,相反,还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15]然而在小说中作者赋予“血”戏剧化的含义,象征亲情的血缘在惩罚中被享用了,在突出血的诡异美感同时,作者同样表达了小说中血亲之间的恐怖本质。
余华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原则,以纯粹暴力的叙述方式展现了“现实一种”。在作品中不仅以细致入微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暴力场景,同时,在暴力场景之外,他还发出了对当下社会、人性、情感等问题的全面思考的呼唤。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J].文艺争鸣,2000,(01):68-70.
[2]丁帆,傅元峰.余华的暴力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13,(06):126-129.
[3]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J].名作欣赏,2002(02).
[4]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5]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J].当代作家评论,1991(05-01):1002-1809.
[6]周艳秋.余华:暴力书写及其回归[J].美与时代,2008(01).
注 释
[1]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叶立文.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小说评论,2002,(04):40-45.
[3]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05.
[5]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鲁迅.狂人日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第14页.
[7]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8]陈晓明.“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J].社会科学,2010(5):159.
[9]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0]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1]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2]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3]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4]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5]马新.中国远古社会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