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流变:来华传教士“中国园林”话语体系的构建与解构
周宏俊 郭真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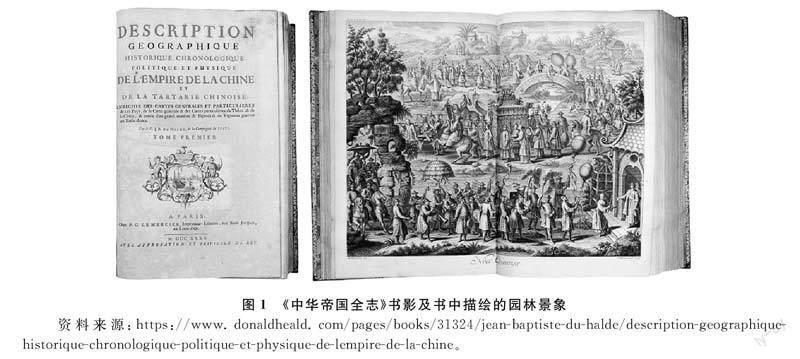


摘要:自16世纪起,欧洲传教士团体带着传教使命来华,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广泛接触。以传教士为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至18世纪末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邪轿会士对园林的记录与评述逐步构建了关于中国园林的独特话语体系,浸润了17—18世纪“中国风”热潮下西方人关于“中国园林”的集体想象。基于互为“异域”的文化背景,传教士对中国园林的呈现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对景观要素的描述发展到对园林艺术的审美认知。其中始终伴随着对中国园林“他者”身份的觉察以及中西对比的叙述方式,并构建了以假山要素、“自然的”特征、“乡村的”氛围为表征的话语体系。至18世纪末,传教士之外的西方话语对植物要素的关注以及有关“自然”评述的负面转向预示着该话语体系的解构。中国园林的想象流变过程交织着不同情境的影响,在园林风格层面,除了欧洲园林风格演变的主观因素之外,中国本土园林风格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关键词:中国园林;来华传教士;话语体系;跨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TU 0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3060(2023)03 0098 13
一、引言
16—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团体创造了丰富的文本体系 , 其在华期间写给欧洲上层人士的书信、记录在华工作与生活的日记、总结见闻所撰写的回忆录与专著等 , 见证了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评价 , 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 , 中国园林成为传教士了解与记录中国风物的重要主体与特殊对象 , 传教士的文本也促进了“中国风”(chinoiserie)热潮下中国园林形象在西方的传播。
目前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类。其一是对传教士群体相关著述文本的译介与汇编 , 以及从中西学术交流的视角切入对传教士著作进行的研究 , 其中部分著作聚焦中国园林并附有相关评述。其二是集中关注较知名的几位传教士 , 对其图像作品或论著进行的分析 , 例如对马国贤《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的视觉分析及其引发的中国园林热潮的研究 , 又如聚焦王致诚的书信探索圆明园对法国英中式园林影响的研究。其三是在探索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园林特征或在研究中国园林对欧洲园林风格发展的影响等议题时述及相关传教士的著述。综上来看,目前学界虽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关注的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尚未有研究从话语体系的角度剖析传教士群体对“中国园林”的意象塑造。
17—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园林的著作层出不穷,但这些论述大多来自对中国园林的间接观察与理解。而欧洲人所获取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与观念大多来自郁酥会士的著述,即便是使臣的记载,也多参考了传教士的论著。传教士根据亲身游历园林的经歷所创作的文本可被视为关于中国园林的重要一手资料。基于此,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 以里纳尔过(Bianca Maria Rinaldi)主编的《中国园林的观念:1300—1860年的西方记述》(Ideas of chinese Gardens:westernAccounts,1300—1860)一书中所摘录的传教士对中国园林的描述为主要研究材料,并以其他相关资料为补充,探究传教士文本中所呈现的中国园林。除了一手资料的摘录,该书亦从西方人的视角概述了西方世界在1300—1860年对于中国园林在观念接受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传教士的中国园林话语体系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中国园林形象在欧洲的传播特征,并反思中国园林本体的历史状态在其中所产生的客观影响。
二、话语体系产生的背景
(一)中国园林的观看者与记录者
早在13世纪,意大利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 Marco polo)便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园林的片段,并铺垫了关于“天朝”园林的想象之源。 17世纪“中国热”兴起之后,中国园林在欧洲逐渐崭露头角。从历史资料的角度来看,中国园林传入欧洲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由郁酥会士创造的宗教路径;其二则是以商人、外交官和旅游作家为代表的世俗路径,这条路径也可视为对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经历的延续。尽管世俗路径在外销商品的助力下通过图像的形式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力,但传教士群体有其特殊优势—在皇城供职与停留的机会以及对中国文化与语言的了解,促使他们对中国园林有更多的直接观察与实地感受,并因此有机会产生更深的理解与认识。
16世纪晚期,郎酥会传教士跟随葡萄牙人由海路到达中国,开启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广泛接触。除了传教之外,他们在中国传播数学、天文、地理、水力、历法以及铸炮技术等西方知识,同时将中国的思想介绍到欧洲。天主教的在华活动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从1582—1644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开始,1644—1722年进入繁盛阶段,最后在1723—1795年日趋衰落。中国礼仪之争后,瘫正皇帝开始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导致各地传教士被陆续驱逐出境,日趋衰落的文化交流也转向了满足皇帝个人对西洋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的兴趣 , 因此一批郎酥会士得以担任御前学者和艺术家。
作为文化表征,园林是传教士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1688年于北京成立的法国郎酥会为传教士提供了一份他们应调查的主题清单,其中便包括了中国的“花园……小巷、喷泉、花坛……的形式”。这些传教士被路易十四授予“国王数学家”( Mathematiciens du RoY)的头衔,通常具备多种才能。以法国人为主体的传教士团体从17世纪起陆续将中国园林呈现于文本乃至图像中。尽管在华传教活动在18世纪初期已开始进入衰落期,但由于清代园林营造活动的兴盛,以及论著出版的滞后性,其文本材料的问世时间多集中于18世纪(见表1)。1702—1776年在巴黎陆续出版的共34卷的《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et curieuses)以及由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Halde)在1735年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 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见图1)等著作,为欧洲读者了解中国园林与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被观看的中国园林
由于朝廷对传教士旅行路径及活动范围的严格管理 , 郎酥会士的园林游览体验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主要亲历的园林包括畅春园、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皇家宫宛。随着清朝对外政策的限制 , 从1757年到1842年 , 仅广州一个港口城市开放对外贸易 , 传教士观察与描述的对象也逐渐转变为当地官员或“行商”的私人园林。还有部分传教士从广州至北京途中游览了南京、扬州、苏州等处的园林及城市风景 , 而個别传教士仅在参与特殊庆典活动时得以窥见园林。综合来看 , 被描述的园林以北方皇家园林为主体 , 同时包含部分位于广州、南京等处的南方私家园林(见表2)。
虽然部分传教士具有进入皇家园林的特权 , 但是这种游览体验受到了较大的约束。不少传教士都提到了皇家宫宛的不可随意进入性。例如 , 王致诚在信件中写道:“做这种工作(指绘画), 我必须有充分的自由得以进入花园各处并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在这里这完全不可行。由于我对绘画有一点了解 , 因此已算幸运 , 否则我就会像遇到的其他几个欧洲人那样—他们已来此很久 , 却从来未踏足过这片令人愉悦的土地。”他还描述了在皇宫中活动所受到的限制:在不得已需要走出宫殿范围时 ,“他们就派一大群太监护送我们。……我们挤成一团 , 悄悄地走着 , 好像正在搞什么恶作剧。我就是这样走过这个美丽的花园的”。由于这样的限制 , 传教士通常会在描述中略加补充 , 以让自己的“在场”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马国贤在描述畅春园时写道:“我每天都去这个庄园 , 但我只有两次看到了全部 , 那是受皇帝之命去为使节梅扎巴尔巴阁下和莫斯科沙皇彼得的大使伊斯梅洛夫阁下当翻译的时候。”他在描述了避暑山庄的景致以及皇帝与缤纪在其间的活动后补充道:“在1721年和1722年,我目睹了这一切。”
三、“中国园林”话语体系的构建
基于互为异域的文化背景,传教士对异国花园的认识与描述通常从中西对比的视角展开,并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传教士在观看中国园林时尚未具备整体的空间感或明确的审美意识。从摘取回忆片段对印象最深刻的要素进行介绍,到基于空间顺序展开叙述,按游览路径描述眼前所见,再到后期逐渐关注园林艺术,其对中国园林的评述逐渐丰富,并在话语的传播与延续中构建出关于“中国园林”的话语体系。
(一)“他者”的园林:对景观要素的观察与呈现
在法国郎酥会士之前,意大利与葡萄牙传教士首先奠定了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显著不同且令人新奇的园林基调。曾昭德呈现了丰富的皇家宫宛园林景象:“(宫殿的)后院非常整洁宽敞。另外还有众多宜人的花园,在宫殿间迂回流淌的河流使人们极为欢愉。此外还有许多栖有奇珍异兽的人造山。很多花园都被精心建造并充满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后续卫匪国与安文思则强化了这种意象。这些描述尽管十分简单,但向欧洲人呈现了前所未见的以蜕蜒多变的水体以及人造山为中心的异国园林,既令人感到新奇,也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园林丰富多彩的变化。
其中,假山作为中西园林最大相径庭的造园要素尤为引人注目。早在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便有关于人造山的描述—“有一座山是用从湖中挖来的土以艺术(的方式)建造的”,马可.波罗强调,这座山上种满了皇帝收集来的世上最美的常绿树,埋下了关于东方园林中“青山”(the green mount)形象的伏笔。从利玛霎起,假山便频繁出现在传教士的文本中。利玛霎于1599年到访了位于南京的“魏国公徐孔基的花园”,描绘道:“一座由各种粗糙的石头建造成的人工假山被巧妙地挖掘成洞穴,里面有房间、楼梯、鱼塘、树木和许多其他兼具艺术性与娱乐功能的事物。”利马霎解释假山的功能是“为了在凉爽的洞穴里躲避夏天的炎热”,从而将假山比喻为“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穿过”的“迷宫形式”(labyrinthine form)。“迷宫”集中体现了游览于假山之中给人带来的错综复杂之感。关于“迷宫”的意象常常被后续的传教士引用,以强化对假山的描述。
传教士早期常关注水景的实际功能,例如养鱼、灌溉,后期则逐渐注意到水的艺术特色。其对假山石的关注也延续到对水体的观察。在相关文本中,传教士对水体驳岸重点着墨,常常论及山水的环绕关系。马国贤将畅春园中的河流和小溪描述为“由艺术引来的水”,形容避暑山庄中“大量的水涌出,并在艺术的指引下像河流一样围绕着这些山丘流动”。王致诚提到“水域的河岸变化无穷,没有两个部分是相同的”,并区分了中西园林在驳岸设计方面的明显差异—圆明园中“运河或小溪流的两岸,不像我们的花园那样用光滑的石头来设计,也不排成一条水道,而是用一块块岩石向内外交错(地堆叠),看上去粗糙而土气”。O11其后,蒋友仁在对圆明园的介绍中同样强化了这样的差异性:“这些水体不规则的河岸上装饰着护墙;但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的石头是基于艺术雕琢而成,自然已经被消除;而这些护墙是由岩石制成的 , 这些岩石毫无(人工)痕迹。”基于与法国古典主义园林风格中规则式水体驳岸的比较 , 传教士逐渐开始强调中国园林在水体设计方面所具有的自然性。
中西对比的视角在传教士对其他景观要素的描述与介绍中亦显而易见。在对建筑的描述中 , 传教士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建筑的差异性。曾昭德认为中国人居住的房子不如他们的“豪华和耐久”, 而房子建得不高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认为这样更适合居住”, 并提到了以清漆和绘画装饰建筑 , 虽不豪华但十分精致整洁。后续张诚则强化了中国园林建筑朴素与雅洁的特征。在描述皇帝在南海与畅春园的居所时 , 他频繁用到了“整洁”一词 , 称其呈现出“没有任何富丽堂皇的东西”“既不富裕 , 也不宏伟”的特征。而这种感受所参照的原型则是欧洲以大理石为常用材料的高大建筑 , 以及当时法国宫廷园林中宏伟壮丽的宫殿。李明对园林植物的评述也凸显了对比的视角。他对中国人的园艺水平流露出不屑的态度:“在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树木 , 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树木 , 这将成为花园的一大点缀。”他以法国园林为参照提出:“如果把它们和橘子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混在一起 , 做成小径 , 那将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其中折射出“中国人不擅长维护与设计植物景观”的观点。这恰恰是将注重自然种植形式的中国园林与极度重视规则式植物修剪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对比之后的直观感受 , 而他所提到的橘子树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便开始流行的植物品种。这种中西园林并置的叙述方式 , 让西方读者更易于理解异国园林 , 同时也强化了中国园林的“他者”身份。
(二)无序的自然:关于园林艺术的解读与审美感知
随着传教士对中国园林的了解逐步增多 , 以及部分传教士因绘画或造园技能而得以更频繁地停留于园林中 , 他们对造园艺术的解读愈加详细 , 对中国园林的审美感知也愈发深入。基于让西方读者更易想象的目的 , 马国贤选用极具西方特色但似乎与园林毫无关联的“郎酥诞生场景”(the Neapolitan cr?che)来形容中国园林:“若用三言两语来形容这个综合体(complex), 可以说它很有那不勒斯美好育婴堂场景的味道 , 该场景是为了自然地表现我们主的诞生而创作的。”以“郎酥诞生场景”类比中国园林 , 十分典型地呈现了传教士话语体系下“不规则的”“无序的”“多样的”中国园林场景特征。王致诚的论述集中体现了这种特征:“但在游乐场 , 他们宁愿选择一种美丽的无序 , 一种尽可能远离一切艺术规则的游离。……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 , 你会倾向于认为这样的作品非常荒谬 , ……但如果你亲眼看到 , 你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你会赞叹这种不规则的艺术手法的实施。一切都很有品位;经过这样的布置 , 它的美逐一呈现。”这段经典表述明确指向了中国园林的“无序性”“多样性”, 以及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好奇的感受。
与此同时 ,“自然的”在传教士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解读中成为核心词汇 , 并经历了持续深化的过程。在传教士的描述中 ,“自然的”一方面用于形容园林环境 , 例如畅春园与避暑山庄等园林确实建造于自然山水环境之中;另一方面 ,“自然的”是對不规则的以及因此看似“随机散落”的景观特征的概括 , 例如假山与水岸的不规则形式。最初 ,“自然的”标签主要用于表述在不规则风格之下的“貌似自然”。在描述畅春园的假山时 , 安文思写道:“这些岩石大部分都充满了孔洞和凹陷 , 这是由于水波的不断冲击造成的。中国人在欣赏这些未经打磨的自然作品时获得极大的愉悦。他们非常喜欢模仿那些高耸、陡峭而崎岖的岩石悬崖。因此 , 从中等距离看 , 整座山犹如崎岖的野山 , 这是大自然的第一个杰作。”马国贤认为 ,“其中一些(假山)由粗糙的石头构造连接起来 , 放置得看起来很自然” , 从而描述了假山给人带来的视觉印象。后续又出现了中国人是在有意“模仿自然”的看法。李明在形容假山石时说道:“他们把石头一块块地堆起来 ,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设计 , 只是为了模仿自然。”假山的设计来源于模仿自然的观点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固定印象。钱德明在描述崇庆皇太后庆寿场景时亦提及:“这些辉煌的建筑间穿插着很多假山,这些山和山谷是模仿自然而建造的。”(见图2)更进一步地,蒋友仁提出了中国人在设计形式上用艺术手法来模仿自然的观点:“中国人在布置他们的园林时,用艺术(原则)来改善自然,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艺术家赢得的赞扬体现为,他在模仿自然但不着艺术(手法的)痕迹。”及至韩国英,他对“自然的”描述则深入到设计手法的层次。此时“自然的”一方面指的是园林所呈现的风格特征,是“它们所呈现出的自然而令人愉悦的形态”;另一方面则被用以表示园林中的山水组合形式,例如他引导读者将“山冈、溪谷、活水、静水都融合在一起,想象这一切都是按照一个模仿自然的计划组织和安排的……”在此,“模仿自然”的对象被具体化为山水交融的布置形式。
中西园林并置的手法在此同样显而易见。马国贤关于自然的表述凸显了中西对比的视角。在他看来:“这座庄园和我所看到的其他贵族气派的庄园都是同样的品味,完全与我们欧洲人相反,因为我们在庄园中巧妙地试图与自然保持距离,把山峦变成平原,排干湖泊的死水,连根拔起原有的树木,矫直道路,大力建造喷泉,井然有序地种植花并。”马国贤以此强调了欧洲造园与自然相恃的关系。与此相反,中国园林所具有的一致的“品味”在于“用艺术手法模仿自然,将地形改造成小山丘,路径在一些地方宽阔笔直,在另外一些地方曲折……穿过山脉,穿过山谷”。马国贤通过对待自然的态度区分了他所理解的中西园林之间的最大差异。当然,这与他对避暑山庄的熟悉以及避暑山庄“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的环境不无关系。马国贤曾记录了他在热河爬上高山之后所看到的景象:“这幅全景图确实是最令人感到稀奇的,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山顶上可以很好地观看大自然令人惊讶的技巧(nature,sportentous tricks)。”这谊染了由自然环境带来的震撼感受。
因此,在园林艺术与审美感知层面,“自然的”成为话语体系的核心观念。尽管论述与认识程度不一,传教士们常自发地将本民族的园林风格与眼前所见之异域园林景象进行对比。作为传教士的主体,法国传教士们自然而然地采用与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完全相反的词汇来形容中国园林。因而,此处的“自然的”以及“通过艺术手法模仿自然”等评述并非触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特色,也并非表示传教士感悟到了中国人在园林中所寄寓的对自然的向往,而是在强调中国园林与古典主义风格极度理性化、规则化、人工化形成的巨大反差。尽管与其民族风格大相径庭,传教士团体仍以赞美为主的态度向西方呈现了中国人的造园艺术。
(三)锚固的形象:话语的传播与集体意象的强化
传教士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园林”意象在话语传播、意象沿用以及论述引用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的过程。部分传教士的论述在话语体系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并在反复引用中被锚固。例如,蒋友仁在描述圆明园时说道:“一些作家以才华横溢的想象力已经对这些迷人的花园进行了如此吸引人的描述,它们在皇帝的花园中成为现实。”在此,“一些作家”中便暗含了王致诚。而关于中国园林的种种意象在传教士群体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在利玛霎创造了“迷宫”的意象之后,纽霍夫将中国的花园和迷宫联系在一起,并引用了利玛霎的描述。卫匪国在文本中提及“有人在花园里见到过非常奇特的假山” , 并复述了关于假山的描述。郁酥会士阿尔德(Jean-Baptiste DuHalde)从未访问过中国,他对中国园林的评述明显参考了利玛霎的描述:“中国花园的主要特征是有大量岩石,其间有错综复杂的路径。”美国卫理公会信徒泰勒(charles Taylor)则描述了苏州狮子林中“巨大的人造假山”:“在各个方向都有最复杂和最令人迷惑的小径,这些小径引导你在石窟和洞穴中蜕蜒前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迷宫。”
意象的延续之外也有误读与偏见的存在,形成了诸如“中国人不喜欢走路”的刻板印象。李明在写给布永公爵夫人(Duchess of Bouillon)的信中提到,“看到中国人很少走路,小径对他们来说就不合适了” , 由此形成了由于中国人不爱走路而导致园林中没有散步道的印象。这个观点在钱伯斯的论述中得到了重复,他写道:“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散步,我们很少遇到像欧洲种植园那样的大道或宽敞的散步大道。”清朝大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的论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中国人,特别是商人以及大多数官吏,很少了解或者践行散步的乐趣。”若换位思考,欧洲园林中普遍存在的林葫道与散步道可以解释这种刻板印象的由来。相似地,西方园林中常见的大理石雕塑等要素在中国园林的缺失也在文本中被频繁提及。例如,张诚认为,中国人会为“怪诞而不同寻常”的古老石头花钱,而不是大理石雕像。约翰.贝尔游览了畅春园后也评述道:“他们有许多采石场,有不同颜色的精细大理石;但在皇帝的花园里连一尊雕像都看不到。”类似的观点也折射出西方人对“他者”与自身差异性的敏感关注。
除此之外,中国园林的形象也在传教士文本中逐渐锚固。在“自然的”标签之后,“乡村”则凝练了传教士关于“中国园林”的集体意象,并在“无序的”与“自然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了对“中国园林”的意象建构。张诚最早开始将皇家园林描述为具有“乡村”氛围。在描述畅春园时他写道:“這里有四条水质极好的小河,河岸上种满了树。园中有三幢很大、很漂亮的别墅;还有池塘,饲养雄鹿、野山羊和骡子以及其他各种动物的牧场,牛栏,池塘花园,草地,果园和一些耕地。总而言之,乡村生活令人愉快的地方(这里)样样都有。在此,前任皇帝们卸下了公务的重担,并暂时摆脱威严神态的禁铜,得以享受私人生活的乐趣。”O11通过详细的描述,张诚为西方人展示了皇家园林所具有的宁静风景,以及极为疏旷而令人愉悦的氛围。其后王致诚在描述圆明园时总结道:“总而言之,他们在这里模仿乡村的一切;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尽可能地表现出乡村生活的朴素和质朴”,“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愉悦的了:它们(指园林)有一种乡村的气息,令人陶醉”。这强化了由乡村带来的愉悦氛围。
“乡村”的标签实则是对“无序的”与“自然的”的进一步升华,并带有某种指向性的引导。蒋友仁在描述驳岸时表示,“增加不规则性”的结果是“使它们看起来更像乡村”。而韩国英则通过司马光的《独乐园记》将乡村和自然的氛围与人在其中的联想和感受联系在一起。他引导读者想象“在他们的园林中,人们只寻求复制美丽的自然,并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空间里汇集她(指自然)在无数景象和乡村景色中四处散布的元素”。从传教士的在华经历来看,他们并未有机会深刻感受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差异。而18世纪正值英国自然风景园兴起,其传播至法国产生了混合着英国的如画式(picturesque)园林与中国园林风格的“英中式园林”(Jardins anglo-chinois)。因此,“乡村”的描述很可能是一种想象的反向浸润与回响—中国园林在欧洲传播并一定程度上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发展相交融,在两种风格同时传播至法国之后,法国人无法清晰地进行区分,因此产生了杂标的印象,反之用“乡村”来描述中国园林。
传教士的描述塑造了关于“中国园林”的集体想象,这种想象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花园意象在欧洲成为被追捧或者批判的对象。企图利用理想化的花园意象的学者对其进行正向宣扬,反向滋养并丰富了想象,如钱伯斯的《东方造园论》(A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而在这种想象中察觉出民族风格发端之源受到动摇的学者,则通过贬斥中国园林来捍卫自身民族风格的地位,例如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此话语体系中,中国园林的品味从不规则的形式与多样化的场景到对自然的模仿与还原,再到对宁静的乡村氛围的呈现,为西方观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来源。西方观者常常基于自己的直接经历与主观认知来看待中国园林,但民族背景、职责与任务、逗留的时间、文本所面向的读者甚至其曾阅读的相关中国园林文本都可能影响到最终文本中所呈现的中国园林意象特征。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在于,集体想象中存在的观点分化或转变也受到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传教士到达中国的时间、游览的园林类型以及园林在彼时的状态。
四、“中国园林”话语体系的解构
1793年,派往中国的马嗅尔尼使团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为中英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此时正值传教活动的衰落阶段,因此来华的西方人群体从以法国郎酥会士为主体的传教士团体转变成以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主体的西方旅行者,并涵盖了外交官、植物学家、东方学家以及军官等多种身份。这些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描述开始出现态度与话语转向,逐渐打破了传教士所构建的“中国园林”话语体系。
马鳴尔尼勋爵及其随从巴罗的论述将中国园林与此前仅在文本中若隐若现的英国自然风景园直接进行了比较。在对避暑山庄的描述中,马鳴尔尼承认清朝御园与英格兰一些最好的园林“完全相似”,将其所具有的“如画般美丽”和“起伏的土地”的特征与英国最早的自然风景园如斯附园(park of stowe)、沃本农场(woburn Farm)和潘西尔公园(painshill park)联系在一起(见图3)。在论述中,马鳴尔尼回应了西方关于英中园林的争论并说道:“我们的园艺风格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人那里复制来的,还是源于我们自己……(我认为)即使是最遥远的国家,也同样可以在不相互借鉴的情况下,通过理智和反思而发现新事物。我们的园艺与中国人的园艺固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我们的杰出之处似乎更在于改善自然,而他们的则是征服自然 , 并产生了同样的效果。”马鳴尔尼在对热河避暑山庄的描述中写道:“但从我所能了解到的每一件事来看 , 它与王致诚神父和威廉.钱伯斯爵士作为现实情况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虚幻的描述相去甚远。”这预示着以传教士为主体建构的中国园林话语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走向解构。
当“中国热”趋于冷却之时 , 18世纪末的西方萌生了一种观点—郎酥会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是被理想化的观念所扭曲的结果。传教士团体的中国园林话语体系有两个明显的解构表征。其一 , 西方人对园林要素的关注点明显地从假山转移到了植物。许多植物学家带着寻找种质资源的目的来到中国进行植物考察。其中 , 苏格兰园丁梅因(James Main)的论述集中体现了趣味的转向。他认为 ,“构成中国园林之美的幼稚与怪诞之处如此之多 , 令人惊讶的是 , 如此聪明和文明的人民竟能满足于这种不自然品味的低级努力。然而 , 就他们收集的用以装饰花园的开花植物而言 , 这种组合令人着迷。……事实上 , 中国人最优秀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对花的喜爱”。梅因的描述表明 , 从18世纪末期起 , 在西方人对园林的空间构成与审美感知的好奇心减弱后 , 科学探索开始盛行 , 西方旅行者逐渐将中国园林视为园艺学的缩影。同时 , 对植物的关注也聚焦到“矮树”上 , 折射出话语的负面转向。泰勒写道:“你有时会看到一棵被训练得像一座几层楼高的宝塔的微型树。(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热情 , 喜欢把所有能接受这种做法的灌木品种都矮化和扭曲。”而英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则使类似的描述成为新标签。在参观广州红顶商人豪夸(Howqua)的花园时 , 他观察到“大量的矮树 , 没有它们 , 中国的花园就不会被认为是完整的”。此时 , 在形态上高度人工化与扭曲化的盆景以“矮树”的形式成为新的意象。
其二 , 关于“自然的”特征评述的负面转向也预示着话语体系的解构。除了马鳴尔尼之外 , 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将中国园林描绘成一种野蛮的畸变 , 并将他所感受到的“对自然的做作模仿”与缠足所造成的变形进行了比较。他写道:“大量的人造岩石要么露出水面 , 要么散布在地面上 , 假装模仿自然 , 在这些岩石上通常种植着矮小的树木。威廉.钱伯斯爵士对中国园艺的描述仅仅是充满想象力的散文作品 , 没有现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 , 他们的品味确实是极其有缺陷和恶毒的 , ……与他们女人的裹脚不相上下。”戴维斯以“假装模仿自然”以及“女人的裹脚”直白地对中国园林进行批判 , 并挑战了钱伯斯曾塑造的想象。钱伯斯所塑造的中国园林意象本质上与传教士话语是趋同并相长的关系 , 因此戴维斯的论述也间接预示了以“自然的”为正向形象的话语体系的解构。
中西关系的转变固然是诱发上述态度与话语转向的重要原因 , 但中国园林主体本身的变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一方面,此时皇家园林的进入权限较之前更为严苛。例如,戴维斯实际上从未参观过圆明园。他加入的韌见嘉庆皇帝的阿默斯特使团(Amherst embassy,1796—1820)在抵达北京后不久就被解散了。而使团成员们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圆明园的大门时,最终却没能进入园林,这让他们感到失望。博物学家克拉克对此描述道:“我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园林(圆明园)天堂般美妙的描述都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但只有在想象中,我才得以享受它们。”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或许也激化了负面情绪。另一方面,西方人主要到访的园林类型也从皇家园林逐渐转向广州的私人园林。被西方人称为“pon-tinqua”的清朝官员和商人潘什成的海山仙馆,是西方游客在19世纪中期最频繁游览的广州私人花园。此时,南方的私家园林规模相较于皇家园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传统园林的造园要素与手法也在晚清愈发呈现出繁复的特征。以海山仙馆为例,其独揽台谢水石胜概,有“南粤之冠”之称。园中花木繁多,“堤上红荔,水里白荷,庭中丹桂,苍松翠棕,竹影桐阴,奇花异草等则相互衬托,并形成为绿化体系”。这也是造成植物要素在18世纪末期受到西方人重点关注所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此外,福琼在描述慈溪市一所城市住宅的花园时写道:“为了理解中国园林的风格,有必要从脑海中消除所有关于草坪好、步道宽、视野开阔的想法,并用小尺度来代替它们……简而言之,(中国人)努力使小的东西看起来大,大的东西看起来小,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的特征。”关于中国园林的论述从强调自然氛围向“微缩”尺度变化,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观者接触的园林类型与尺度有直接的关联。若以传教士所塑造的话语体系对照自己眼前所见的尺度相异的小型私人园林,很容易进一步强化原本就负面的目光。
五、结语
1860年之后,更多西方人得以进入中国,同时也有更多的渠道记录与传播信息。传教士所构建的关于中国园林的话语体系与想象也逐渐在摄影术的发展以及理性研究的开启之下凝固为17—18世纪的特殊意象。在传教士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园林呈现出“多样化的”“自然的”以及具有“乡村”气息的特点,充满着与欧洲园林所不同的“不规则”与“无序”。传教士透过各式透镜去观看中国园林,互为异域的文化背景是其主观基底,中西方园林风格的发展与演变也是暗含其中的重要客观因素。一方面,17—18世纪欧洲园林风格从意大利台地园发展到17世纪中叶起占据主流的法国勒诺特尔园林,继而转变为以18世纪初开始兴起的英国自然风景园为主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传教士评述中国园林的参照体系。传教士的描述视角也从注重园林实用性的功能介绍发展为或直接或含蓄地与法国古典主义风格进行对比,再到充满了对英国自然风景园风格的观照。另一方面,中国园林本体也并非一成不变。传教士所亲临的皇家园林从清初至清中叶也经历了不断发展成熟的历程:从康熙时期的畅春园那般追求自然与疏朗氛围的自然山水园风格,逐渐演变为乾隆至晚清时愈发繁琐与猎奇的趋势。这样的情境在传教士对园林建筑的描述中彰明较著。
因此,17—18世纪传教士所构建的中国园林话语体系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在以传教士为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西方人缺乏亲历园林的机会,加之材料传播途径的局限性,使得传教士团体“近水楼台先得月”,先行建立了關于中国园林的话语体系,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反响。但这种影响力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较于以商品和图像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商业路径,传教士的文本在出版时间上具有滞后性,同时具有语言和受众的限制。因此,与外销瓷上的园林图案在大众中引起的热潮相比,传教士的文本更多的是为未能亲临中国园林的西方学者提供推崇个人观念与理论的重要素材。而“中国园林”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去语境化,愈发脱离本体而成为某种意象。18世纪末,尽管身份各异的西方人以普遍较为负面的态度解构了传教士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但个别观者对“借景”等手法的无意识描述 , 以及对园林美学的进一步认识 , 都为20世纪初期西方学界对中国园林的理性探索铺垫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西方语境下中国园林的文本与图像资料对于认识中国园林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接受机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需警醒的是,材料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由于语境的差异、信息的缺失以及主观目标导向,可能存在对原始材料进行删减、修改表述甚至添加信息的行为,这都影响了对材料的完整解读,甚至可能造成误读。本研究所参考的主要著作的编者对此也持审慎态度,并对可能的情况做了相关说明。来华传教士数量众多,著述丰富,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材料仅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在未来可做进一步的材料补充与探究,以期更客观、完整地还原异域视角下由传教士团体所构建的中国园林意象,并对当下中国园林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有所启发。
Imagination inFlux: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the“chinese Garden”Discourse system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ZHOU Hongjun , GUO Zhenzhen
(college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since the16th century,European missionary groups came to china with missionary missions,thus starting the first extensiv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with missionaries as the link,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by the end of the18th century. During this process,the Jesuits,records and commentaries gradually built a unique discourse on chinese gardens,infusing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westerners about the“ chinese garden” under the“chinoiserie”craze in the17th and18th centuries. Based on the reciprocal“ foreign land”cultural background ,the missionaries,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gardens had undergone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eepening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elements to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garden art. This wa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n awarenes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of the chinese garden and a contrastive narrative mo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us a discourse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elements of rockery,“natural”features,and“rural ”atmosphere was constructed. By the end of the18th century,the focus on plants and the negative shift in the comments on“ nature ” in western discourse outside the missionary group heralde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chinese garden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is imagination process was interwoven with different contexts. Besid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garden style,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hinese garden styles was an objective factor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keywords:chinese garden; missionaries to china; discourse syste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責任编辑:王晨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