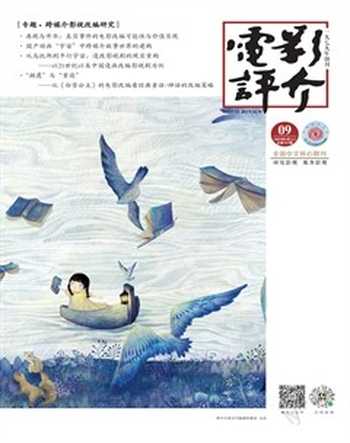《长沙夜生活》
徐辉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优秀影视作品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对于打造城市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老炮儿》(2015)、《火锅英雄》(2016)、《爱情神话》(2021)、《人生大事》(2022)等为代表的作品以强烈的地域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域电影百花齐放的当下,以长沙为背景的《长沙夜生活》(2023)应运而生。长沙丰富的夜生活曾通过《守护解放西》(2019)中“坡子街派出所”繁忙的夜间出警故事而广为人知,其一上映便火遍全网,并乘胜追击连拍三季的纪录片,用令人啼笑皆非又温情脉脉的真实故事把长沙这座城市鲜活地推到中国观众面前。一座城市的氛围与品格是由长久积淀孕育而生的,夜色笼罩下的长沙有着不同于白日的喧嚣与暗流涌动,人群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夜色掩映下的人性也更加的纯粹、柔软、坦诚,甚至显得脆弱。《长沙夜生活》把长沙这座城市华灯初上后的繁华与孤寂,海纳百川式的包容与多元淋漓尽致地铺陈出来,通过一个夜晚发生的故事,串联起这座城市中的人生百态,在展现长沙独特的人文景观与文化症候的同时,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漫游者一词来源于法语Flaneur,意为游手好闲者、闲逛者、漫游者等。城市漫游者意象最早出现在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诗作中,他把19世纪流连于商业拱廊,与城市和人群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者当作研究对象。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针对波德莱尔的创作提炼出城市漫游者的概念。本雅明概念中的城市漫游者主要指那些城市中没有固定工作且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无所事事,整日穿梭在大街小巷,却始终游离于社会之外,与外界保持着审慎、客观的距离,透过表象体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带来法国宫廷的解体,曾被奉为座上宾的文人沦为城市的游荡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审美体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不愿放下“抒情诗人”的高贵气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却无奈被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所物化和商品化。本雅明对漫游者的描述暗指一种景观消费主体性的构建。这种主体性是将城市景观作为“他者”并对其进行视觉消费而建构的。[1]城市漫游者的意象被后来的很多人应用于相关研究中,比如根据库哈斯对纽约城市空间的解读而写就的《癫狂的纽约》;李欧梵亦赋予了20世纪中国上海社会游手好闲的人物以城市漫游者的意象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不同的地域和时空都相继出现城市漫游者的形象,并具有相应的在地化特征与属性。《长沙夜生活》作为一部城市电影,塑造了一系列城市漫游者的群像,并通过想象性地重塑赋予城市漫游者更加宽阔的外延。
一、多线性叙事结构与多元化空间打造城市漫游者群像
对一部城市电影来说,人物是城市的灵魂所在,有了人物的流动和存在,城市才富有生命力。长沙作为开放性大都市,其海纳百川式的包容使生活于其中的人群构成十分复杂,群像设置使影片的内容表达更加丰富多元,其广泛性使观影的大多数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共鸣。为了打造丰富多元的人物群像,《长沙夜生活》采用多线性、收束式叙事结构。四条主线分头并进,适时穿插小的叙事段落,与几条主线形成呼应。随着故事进程的推进,人物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彼此交错又巧妙重合,形散而神不散,最终在丽姐大排档完成了汇合。多线性的叙事方式看似眼花缭乱,实则乱中有序,为多组人物故事的展开提供了足够开阔的空间,适用于打造人物群像。
19世纪的巴黎,拱廊的出现模糊了黑夜与白天的界限。21世纪的中国长沙,午夜的书店灯火通明,书香满溢;午夜的街头熙熙攘攘,人潮如织;午夜的大排檔,人声鼎沸、门庭若市,城市高速发展催生出的越来越多的城市景观消弥了昼夜的交错,打造出现代性的“夜消费文化”。漫游者群体成为这座“夜之王国”的鉴赏者与观察者,他们散点式地游走于大街小巷,打造城市的流动感,多线性地呈现出这座城市夜晚的全貌。作为一部都市题材电影,影片中的城市空间并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的复现,而是“一种想象和建构”[2]。城市景观作为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表现,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街道,是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室外空间与室内空间联系起来的中介。穿越街道的路径,是一些城市电影展现“回家”之途的场景。[3]何岸与父亲和解后,用小摩托载着父亲穿过滚滚车流,最终回到母亲的大排档;景为为与何西西用脚步丈量了长沙的大街小巷后,也回到了何西西继母丽姐的大排档;外来务工人员小东北、小西北和一直沉浸于失去亲人伤痛的维修工也相约来到大排档这座散发着“家”味道的“深夜食堂”。如果说波德莱尔时代“拱廊街的存在使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得以短暂成立”[4],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现代都市长沙,丽姐大排档便是这个无阶层差别的乌托邦,是一个供城市旅人喘息和栖息的避风港。在这里,热气腾腾的食物成为建立社会联系的中介,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治愈,甚至超越血亲关系,形成想象性的家人,感受到“家”的温暖。长沙人的一天,从一碗粉开始,也从一碗粉结束,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可以助力人们迎接新的一天。这种城市景观的拟人化不单单体现在大排档里,城市中的任一景观都可以被赋予主体性的感情色彩。如果把丽姐大排档作为一种有温度的消费景观,脱口秀剧场就带有工业社会的冷漠气息。脱口秀剧场居于城市高空,高傲地俯看芸芸众生,这个由玻璃环绕的球形建筑是新兴的城市景观,它彰显了技术的进步,代表了现代与流行,年轻的灵魂在这里汇集与狂欢,然而此处的景观消费是有冰冷的准入门槛。当何岸的父亲第一次身处这个空间时,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和无所适从,他被排除这座盛宴在外。何岸作为唯一一个专职脱口秀演员,用尽全力准备却由于不肯投其所好而被无情地拒绝,颜面尽失。工业社会的文明只看结果不问过程。当何岸终于自残式地将个人创伤剖给观众,而观众发出事不关己的笑声时,我们终究窥见一丝生活的残酷本质。[5]
二、城市漫游者群像的想象性重构
(一)精神困境的打破-城市漫游者的想象性成长
《长沙夜生活》中演员尹昉所饰演的景为为即是波德莱尔笔下典型的“城市漫游者”形象,作为“见证着现代性新状况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对极速变化着的社会和生活有自己的洞见。“现代性导引下的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经济模式让他们不适应了”[6],这种不适与抗拒使他们不肯随波逐流,自觉承担起观察者的角色,在美轮美奂的城市景观中保持着敏锐的思考,清醒的认知。
现代社会更迭迅速,流动性强,身处其中的普罗大众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迷失于光怪陆离的乱象中。城市漫游者则冷静地审视着当下发生的一切,这种观察不同于承载着权力体系的“凝视”,而是一种散点式的观望,不具有强目的性,但其游离性可以使观察者自身从现代社会洪流的裹挟中抽离出来,冷静客观地思考。《长沙夜生活》原名《群星闪耀的夜晚》,灵感来源于茨威格的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可见该片骨子里的文艺气质,也不难理解开场便以一场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辩论展开影片的叙事时空。景为为喜欢在夜间安静地研读与思考哲学,开口闭口萨特、尼采、维特根斯坦,他离群索居,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与群体性的聚集行为使他不适,夜间书店的一只板凳和一排书架筑起了他的安全堡垒,与何西西的偶遇像无波的水面被投入了一颗石子,使他被迫开始与他人进行交流。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打破了艺术永恒性的传统认知,把短暂性和偶然性看作艺术的一部分,何西西临时起意的恶作剧使景为为被迫在公众面前朗诵诗歌,正是这次被动的公开使何西西看到了景为为纯粹且真挚的内心世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这次“震惊体验”也使何西西萌生了与景为为继续交流的想法,不似波德莱尔在《给一位失之交臂的妇女》中为惊鸿一瞥却转瞬即逝的美丽女性而扼腕叹息,何西西把握住了主动权。从十二时辰书店、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头、五一广场到湘江一桥,景为为与何西西彻夜长谈,边走边聊,交流着对哲学、艺术、生活及人生理想的众多思考,长沙的城市景观随着他们的脚步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毫无疑问,此种情节安排明显带着《爱在黎明拂晓时》等三部曲的影子,也充斥着伍迪·艾伦式滔滔不绝的哲学输出。当一个所谓的知识精英对一脸崇拜的女学生夸夸其谈其引以为豪的男权文化,并试图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诱她时,景为为与何西西冲出来直白且恶作剧式地揭露了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伍迪·艾伦的名作《安妮·霍尔》中,当艾维无法忍受某教授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断章取义和大放厥词时,索性直接将麦克卢汉本人请出来当场对质的经典段落,两段情节形成了互文,是穿过遥远时空对伍迪·艾伦致敬。何西西与景为为这条线旨在揭示长沙烟火气中被遮蔽的另一面,诗和远方同样是当下长沙年轻人追求的生存状态与人生体验。与此同时,如影随形的精神困境也时时困扰和缠绕着他们,进退维谷的挣扎中,满溢的文艺气息丰富了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景观。随着聊天的深入,思想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对彼此的认知也逐渐清晰与深刻。何西西对景为为从针对到防备,再到接纳和爱慕,一步步卸下心防,甚至用跳江来弥补他没能救回前女友的遗憾。而景为为的纵身一跃也使他从长久的自责与封闭中解脱了出来,完成精神上的成长和蜕变,从旁观与游离中回归生活,开始接纳另一段感情。
(二)身份认同的获取——边缘漫游者的想象性融入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就已经开始关注酗酒者、拾荒者等社会边缘群体。在现代都市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这些被忽略和遮蔽的人群作为特殊的漫游者群体,赋予了城市多元的文化景观。随着时代的演进,漫游者形象不再局限于19世纪的巴黎,不同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现具有地域和时代特点的本土“城市漫游者”形象,比如中国特色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离开“由亲属构成的熟人社会”,只身前往承载梦想的大都市,并“在城市秩序下开始规训之旅”[7]。小东北和小西北作为城市流动人群,都市的外来者、边缘人,是这个城市万千外来务工人员的缩影,他们从乡村小镇来到繁华的现代大都市,在孤独与思乡中相互取暖。
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现代城市结构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指在规划者统一的设计下生产出整洁有序的现代化空间;[8]“后台”则相反,指向城市阴影中隐秘的不为人知的空间。微薄的收入使外来务工人员丧失了融入“前台”的能力,被动地成为隐身于“后台”的城市观察者,“只能对近在咫尺却无法进入的‘前台进行张望”。[9]摩天轮和烟花是现代都市典型的消费景观,小西北与小东北每天仰望着摩天轮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俯瞰这座城市,与摩天轮一起见证了很多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却从未有机会亲历。他们在绽放的烟花中麻痹自己,暂时忘却自己“城市弃儿”的身份,在与商品的相互消费中获得稍纵即逝的解脱。如果说坐在摩天轮里享受烟花浪漫服务的情侣们是这座城市的“前台”景观,那么蜗居于小小的控制室,为他人做嫁衣的小西北与小东北便是被遮蔽的“后台”景观。不仅工作环境狭小拥挤,寄居的出租屋亦窄小、杂乱,二人只能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呈现了城市中的“贫民窟”景观。“空间意义的生产与主体的精神感受有密切关联”,[10]物理环境的逼仄,折射了精神空间的游荡与无根性,无论哪一种环境都无法为他们提供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与“这里一切都太熟悉了”,想要逃离长沙去找寻陌生感的何西西相反,他们渴望认同,又无法停止回望故乡,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与进度。在被完全接纳前,他们只能互相依靠、互为支撑。对边缘漫游者的底层书写,对他们孤独无助又渴望建立联系的心理描摹,使这个群体被看见,体现了《长沙夜生活》的人文关怀,它化身为人生酸甜苦辣的万花筒,折射出很难被看到的市井小民的悲喜人生。而安排两位外乡人被接纳,则是一种想象性的身份认同与理想化的书写。在漫天绚烂的烟花和丽姐大排档热气腾腾的食物中,两位外乡青年得到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慰藉。
丽姐的人物形象设定也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但她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身份认同,不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还成为行业翘楚,把本地美食文化做到了极致。她的成功与她的本地人前夫并无任何关系,全是凭自己打拼获取的,她可以说是小东北与小西北的榜样与未来,是外来者融入的成功案例。她从边缘漫游者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流,而她的儿子也已经成长为本土文化的守护者。丽姐的成功经历是边缘漫游者对主流社会的想象性融入,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上升的可能和空间。丽姐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过创业初期的低潮和沮丧,是陌生人的温暖给了她继续前行的勇气。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麗姐慷慨地对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漂泊无依的人施予援手,她提供的不仅是一份食物,更是一份心灵慰藉。丽姐大排档作为“想象共同体”,是边缘漫游者们在陌生城市中的归属和依靠。
(三)代际和解的实现——来自主流社会的想象性接纳
何岸虽然是城市户口,不算外来务工人员,但他没有传统意义上正式稳定的工作,而是以脱口秀这种亚文化边缘化的职业谋生,不被以父母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所认可。成长过程中原生家庭的分裂,父亲角色的缺失,是束缚何岸的桎梏和枷锁,他不肯放下过去,不敢直面自己,这使他与所追求的脱口秀事业产生了较大的矛盾,无论付出多少努力,总是适得其反。脱口秀表演出师未捷使他遭受重创,与父亲的关系也降至冰点。心灰意冷后,他放下了所有的矜持与偏执,勇敢地剖析自己,当他以轻松的口吻调侃起过去的伤疤时,不仅演出获得了成功,父亲也看到了他的能力和决心,二人冰释前嫌。脱口秀表演虽然是一份较为冷门的职业,但何岸为此付出了很多别人看不见的努力,这份工作本身也被赋予了更多正面价值与意义。苦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再讲方言,何岸坚持用长沙话演出,立志要守护好这一地域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担当。然而,他的坚守渠道是父母所不理解的流行文化,亚文化与主流认知的矛盾构成悖论,他的离经叛道一度使母子关系剑拔弩张。影片花费了大量的篇幅铺垫陈丽姐的坚强与强势,从白手起家到成为20年老店的老板,她含辛茹苦地独自带大儿子。当疾病缠身、力不从心时,子承母业是她由衷的期望,但当她看到儿子对职业的热爱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时,她释然了,尊重了儿子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意味着亲子关系的和解,也意味着主流或优秀传统文化对新兴文化的接纳。多元文化的共存,传递出创作者对即将消失的地域特征的焦虑并强力挽回的努力。河岸“让长沙话走向世界”的梦想在电影时空中得到延续。
结语
城市的飞速发展使人与自然几乎彻底分离,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堆砌而出的现代都市丛林。日复一日麻木的工作和生活,使人们逐渐丧失了追求情感体验的主动性,冷漠疏离似乎成为现代城市居民的保护色,家庭的核心地位与价值归属也正面临着瓦解。不同于当下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品在描摹现代都市人际关系时的冰冷与悲观,《长沙夜生活》坚守中国“家”文化的传统和底蕴,对于当下社会中人与人的情感联系,仍旧抱以温暖的守望。或许大团圆式的美满书写略显老套与刻意,但在经历疫情的洗礼后,中国人需要这种诗意与烟火气并存的人间温情,来抚慰内心深处的创伤并展望美好愿景。正如该片在电影首映特别企划中提到的:致敬电影、致敬生活、致敬不易、致敬前行。
参考文献:
[1]严亚,董小玉,谢峰.从漫游者到媒介漫游者——城市的观看之道[ J ].城市规划,2014(04):79.
[2][3]陈晓云.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1990-2007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30,47.
[4]夏金鸽,徐磊青.并视本雅明与库哈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癫狂的纽约》的城市空间文本解读[ J ].建筑与文化,2020(09):199.
[5]尹一伊.《长沙夜生活》:被符号化的城市和“货不对板”的夜生活[N].文汇报,2023-5-17(11).
[6]魏建亮.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及其“漫游”[ J ].文史天地,2014(01):79.
[7][8][9]魏晓琳.是枝裕和的影像空间:都市漫游者、乡愁乌托邦与“想象共同体”[ J ].美与时代(下旬刊),2020(09):83-84.
[10]张益伟.日本電影《小偷家族》的社会视角观照与都市文明反思[ J ].电影评介,2019(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