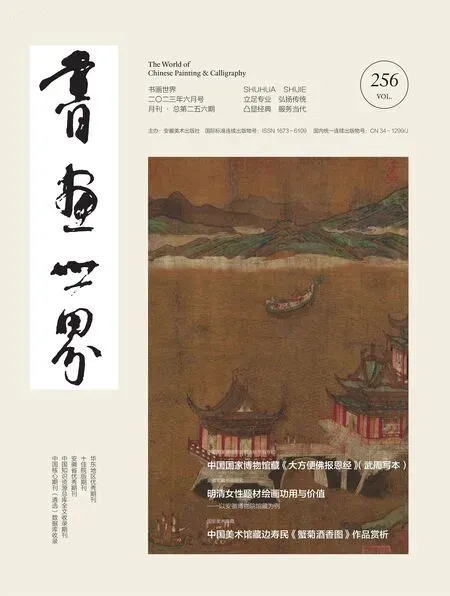从宋元时期的用笔看人物画的意象造型
文_凌晨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
内容提要:自张彦远提出“书画用笔同法”的观点后,在文人画理论的主张下,宋代出现了书画的“合流”,画家们探索出了各种的皴法、点法、擦法和染法,并将用笔进一步规范。这些对笔法的探索与完善共同造就了人物画用笔的丰富,为人物画造型的创造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与唐代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不同,宋代的文化观念转向了反省人生和对心灵探求的心理特征,进入了“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皇家画院的建立与对人才的重视使得人们对书画家的评价标准不再仅是“天然”与“功夫”,“学识”成了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可贵的“书卷气”和以“写性”“写心”为目的、表现人格精神的文人画,整体呈现出以文雅和怡情悦性为重的谦柔情韵。从这一时期开始,书画笔墨方法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从唐末之前山水的“勾线填色”到五代宋初的“三家山水”,从整体到局部,从人文到气象,画家们在将描法变成程式化的用笔后,对原本不太规整的皴法进行条理化和规范化,遂将皴法变成了独立的笔墨语言,使得原来以勾染为主的人物画法融入了更多的用笔特征:院体的法度与工谨,文人的简淡与幽远,禅宗思想影响下的率意与雄逸,等等。士大夫与文人们也无不在“治身”与“治心”中锤炼心性,向着书写万物心意的方向发展下去。
一、用笔的形势
宋代“重文”的风气和理学的发展使得士大夫和文人更关注“笔墨之外”的妙处,从苏轼对“常形”与“常理”的辩证①[1],可以看出宋代绘画审美观念的继承和转变。自中唐张彦远提出“书画用笔同法”的观点,将“连绵不断”“一笔画”的笔“势”与“一笔书”的“气脉”建立了联系后,画家们都非常强调书画用笔一致的观点。五代至宋,随着士大夫和文人自觉意识的增强,文人画重意趣与重主观世界表现的审美观念促使书法化意识进一步加强,以笔写形,以形求“横变纵化”之动势,进而求得内在精神的“意足”,成了宋代士大夫和文人共同追求的“理”。人物画发展至宋代,一方面,在前朝完备的风格样式、法度规则下,顾恺之、吴道子、周昉等人建立了完备的审美体系,使宋初人物画出现了“风斯在下”的瓶颈;另一方面,在山水画、花鸟画迅猛发展的压力下,人物画的审美语境逐渐被放置在“山水”中展开,郭若虚的“近不及古”、韩拙的“观古之山水中人物”等表述都说明了当时人物画理论视角的转变。但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不管是宫廷画家还是文人画家,他们在作画时都没有舍弃“常形”,而是向着不止于形似和法度之外那更丰富、深刻的“常理”和意趣探求。
院体画以“曲尽其形”为径,通过“高简写工”的笔韵和细畅精妙的笔墨,追求严谨、逼真的“自然”之态,以求谨守法度和气韵生动的统一。从《图画见闻志》中记载的帝王“威福严重之仪”、道家“修真度世之范”、赵佶“孔雀登高,必先举左”的论述,以及《朝元仙仗图》《听琴图》等画作,可以看出院画家以吴道子为艺术“骨格”的样板,继承了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客观物象描绘力求逼真、生动的审美原则。例如武宗元的白画②[2]《朝元仙仗图》(图1),场面壮观,人物宽袍大袖,裙带飞扬,有迎风飘举之势,属“重大而调畅”的艺术处理手法。璎珞配饰则呈现出“缜细而劲健”的用笔特征,与袍袖的飘举形成了明显对比,加之对背景中华盖旌旗、荷花、祥云和人物整体仙姿的烘托,营造了似如“吴带当风”的“壮气”。同时,武宗元在用笔上能取长补短,学吴道子而得新意,以动中寓静的方式追求画面整体气势的优雅与从容,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程式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对比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可以看出,武宗元画中的线条劲利飘逸,紧若铁线,状若游丝,环环相扣,细密而劲韧,相比吴道子“壮气”“劲怒”“莼菜条”状的衣纹用笔多了些许婉约之意。此外,武宗元对吴道子道释画的列仗阵势和人物造型也有了新的突破。从武宗元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初院画通过精准的人物造型与严谨的法度来实现形象与气韵的统一,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

图1 北宋 武宗元 朝元仙仗图(局部)王季迁旧藏
文人以“寓意于物”的观照方式,通过书画的兼融和笔法的统一,进一步使画面追求超越形似和法度的新意,探索平淡、萧散、简远的理趣。这一时期的画家更重视文思与体悟,将能否通晓画理与人的文采、文气联系了起来。例如文同、王诜、米芾父子、李公麟、晁补之等等,他们将文人情思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融入自己的作品。例如李公麟的《五马图》(图2),画中的人物与马主要用“白描”的手法描绘而成,不同种族的人物有不同的精神状态,造型精准,头部、身体及腿部的相互关系严谨、准确,刻画精妙入微,而且人物的神态生动自然,衣服褶皱与人物的姿态丝丝入扣,形貌生动逼真。从其对线条的塑造来看,可谓简练、精妙而又概括:有的似铁线,有的似兰叶,有的仿若游丝,疏密得当,交相呼应。《宣和画谱》中说李公麟“创意处如吴生,潇洒处如王维”[3],苏轼说李公麟“笔势隽妙”。李公麟既“阴法其要”又“不蹈袭前人”画法的转变,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画家们文化境界和审美趣味的提升,即由“壮气”至“冲淡平和”的境界之变。

图2 北宋 李公麟 五马图(局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院画家与文人画家对于“常形”与“常理”的共同追求也推动了这一时期人物造型和绘画画法、用笔的发展。从顾恺之描法用笔体系的建立,画人物“写自颈以上,宁迟而不隽。不使远而有失”[4],到唐代“书画用笔同法”理论的发展以及风格样式的建立,五代荆浩在“六要”中对笔与墨的重视,以及以“势”论笔,使绘画用笔到达了一种自觉的审美层次,到了宋代,笔墨技法更是在“诗画一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元代笔墨建立起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用笔的意趣
宋代理学之风甚为流行,同时受到禅宗尤其是南禅宗的广泛影响。南禅宗“不立文字”,大开方便之门,其对心性的修养方法与儒家的思想相互渗透,进而形成了文人士大夫这种集体的文化心理。当时的文人谈禅成风,对禅宗的广泛接受自然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即重视直觉的观照和领悟,并将绘画主体潜意识中的文化积淀以“墨戏”或“逸笔”的形式表现在画面中,从而使绘画主体的情感在绘画创作中释放出来,进一步将外物的“难画之意”与哲理自由地表达在绘画作品中,通过外物的神韵与意境表现画家的品格与境界。
在宋代,禅宗对心性的修养与解放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也引起了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士大夫通过谈禅、参禅修炼心性,追求生命的自觉。梁楷是宋代受禅宗影响、在绘画用笔转变上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艺术家。他师承贾师古,远承李公麟,其前期的绘画,如《黄庭经神像图》,有类似李公麟的细笔风格,但其后期绘画语言与审美旨趣则在禅宗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在《六祖斫竹图》中,“折芦描”的线条如斧劈般劲利、爽快,衣纹已不再是中锋行笔,而是侧锋直入,提按顿挫,所画出的线条已没有了“描”的痕迹,变成了起落分明的“写”。《布袋和尚图》在用笔上则较前期更为简率,也将智融的“两笔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尤重人物面部的刻画,以细笔勾勒,寥寥数笔就将人物面部憨态可掬的神情表现了出来,而衣纹装饰则多用简洁的粗笔勾画,配以墨色挥扫、晕染,塑造了一种简洁明快的人物形象。到了《泼墨仙人图》(图3),画中仙人的面部已不再是细笔勾画,而是具备更明显的写意特征,衣袍中那不经意间的笔墨挥洒体现了梁楷对笔墨关系与人物造型的把握。从以梁楷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探索可以看出,他们将院体画严谨和文人禅心的纵逸之气很好地统一了起来,为艺术创作和审美表现开辟了新的路径。

图3 南宋 梁楷 泼墨仙人图48.7cm×27.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禅宗思想,强调“心”对外物的观照以及所起的决定作用,激发了画家们创作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画家对用笔的自觉探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画家如李唐,他虽为画院画工,但也受文人画思想的影响,能够“以情入画”,将自己对现实的切身感受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作品中。以《采薇图》(图4)为例,画中用笔刚硬、方折,线条本身出现了明显的顿挫和粗细变化,这种用笔被称为折芦描。在梁楷的《六祖斫竹图》和《六祖撕经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线条,结合前面对梁楷心性与笔性的分析,可见这种线条的用笔心境必然与顾恺之那“春蚕吐丝”“循环飘忽”的用笔心境不同,与吴道子那壮气豪纵的用笔心境也大不相同。画中李唐以浓重的背景衬托两位着淡色衣服的人物(伯夷、叔齐),两人对坐,周围的树木、山石笔法各异,山石崖壁以飞白之笔侧锋直下,前后藤条缠绕的老松枝干以浓墨擦染,更显伯夷、叔齐二人在荒无人烟处“不食周粟”的决心和气节。邹迪光在题《采薇图》中说:“二人对话,酷有生态,一树离奇偃蹇,一树叶欲脱不脱,信腕挥运,自生妙理。”[5]可见图中所有的景与物都成了讲述作者心境的必要“语言”。

图4 南宋 李唐 采薇图 (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此,宋代的禅宗思想成了文人士大夫艺术创作生命力的源泉,画家们在对禅心与意境的追求中也得到了精神与创作的自由,使得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创了品格、性情的另一番天地。
三、 用笔的韵致
南宋末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了审美思想的变化。备受冷落的元代书画家在惆怅的心境中期望借复古求创新,在追求“古法”的同时,更重视对“古意”的寻求,以求形神兼备的韵致与意趣。赵孟提出“复古”的论调,讲到“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6],主张变革南宋院体“用笔纤细,敷色浓艳”的画风,强调“以书入画”,并以文人画高古、雅致的精神及艺术手法直追唐人的意境和韵致。赵孟所推崇的“古意”和所希望向唐人学习的是:通过形神兼备、六法俱全的唐人的“法度”来追求唐人的意境和品格,在追求摹写形似的同时思考怎样从唐人的境界中汲取营养,从而创造新的“韵致”。然而,在宋代的理学之风下,画家们更强调“师造化”,讲究从物性的自然处“究物之微妙”[7]158的“理”,再加之受统治者那精谨工致的审美旨趣影响,因此想追求韵致是困难的。到了元代,在文人自我调节、独善其身的过程中,画家们更强调“法心源”与“寄兴写意”[7]36,才在笔情墨韵中找到了“韵致”与主观意兴、情绪的发展方向。

图5 元 赵孟红衣罗汉图26cm×52cm辽宁省博物馆藏
在复古的主张与“以书入画”的笔墨要求下,元代人物画一方面上追以阎立本、韩幹等人为代表的唐人古意,另一方面在李公麟的文人格调下开启了多样题材的探索之路。元代人物画有刘贯道、任仁发的“高逸之笔”,也有颜辉的“狂怪之笔”,除此还有王绎和赵雍的肖像写真之作,可见种类之丰富。例如任仁发《出圉图》(图6)中的用笔既有篆书的遒劲与圆润,画中的人物与马匹笔法又严谨、工细、圆劲,描法介乎铁线描与游丝描之间,均以中锋单线勾勒;在衣纹的处理上又有书法中行草书用笔的变化与穿插,马的鬃毛用笔也是虚实结合,富有很强的韵律感,实现了引书入画的完美结合。再如王绎的肖像画《杨竹西小像》,画中的杨竹西手握竹杖,呈欲行之状,人物形象生动、神态自若,人物面部及须眉以细笔勾画,并略施淡墨,通过笔墨的晕染衬托出其凹凸有致的生动形象。在人物衣纹的处理上,仅以白描手法勾勒,用笔简练,并未晕染,寥寥数笔就描绘出了杨竹西时常穿戴的文人衣物,袖口、下摆与鞋尖处施以较重墨色平涂。与同期其他肖像画家相比,王绎完成了从“写像”到表达“本真性情”的转变,也表现出了元人特有的审美韵致。

图6 元 任仁发 出圉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所述,不管是宋代的画家们开始追求自我实现与更高层次的品格,进而探求更新更高的绘画表现方法,开启了以提高人性为目的的“文人画”新时代,还是元代的复古求新,画家们无不在“治身”与“治心”中锤炼心性,从画中求意,于意中求生,形成中国书画追求“意气”或“思致”的永恒品格。
注释
①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还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说明了这一时期人们在形似和神似上与前朝有不同看法。
②饶宗颐在《敦煌白画之特色》一文中讲,白画或白描为不敷彩之画,原只是画稿,仅具简单轮廓,与后期发展完善的水墨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