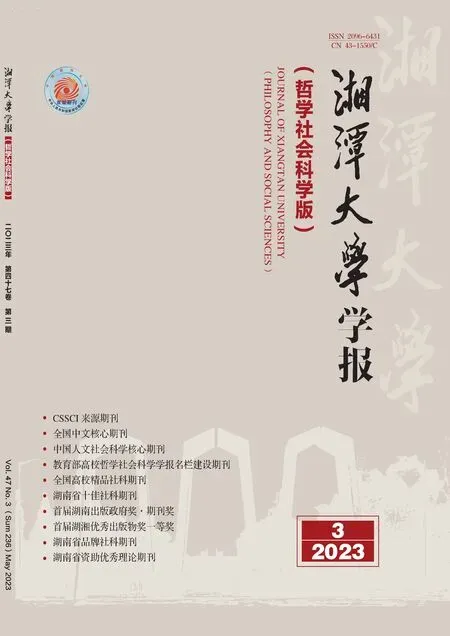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
赵树勤,杨杰蛟
(1.广州华商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399;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长期以来,学界在探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与域外文学的关联时,或是从女性文化批评的视角切入以阐明当代女作家普遍存在的性别意识的自觉中所包含的世界性因素,或是重视发现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哲学观念、艺术技巧等方面对当代女作家所具有的“实用性”价值,而西方传统文学资源的滋养作用却在无意中被遮蔽起来,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即是一例。在这一时期的欧美各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中国当代女作家接受影响最为明显的正是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法国作家的创作,这种广泛阅读后的主动选择是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所具有的独特思想倾向与艺术价值分不开的。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当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吸收、借鉴以及转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更能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与域外文化的双向对话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共鸣与接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特质的凸显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欧洲的出现与法国大革命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联,个人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开始被人们真正重视起来。随着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宣传与标榜,“人对于独立自由有了比启蒙主义时期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发展的个性主义趋势。”[1]5由此,文学世界里人的地位得到了全面的提升,过往固有的对于文化体系的认识开始出现变化。诚然,文化与文明体系的建构在根源上来自人的主观精神创造,也正因为此,它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于人的生命观与价值观的肯定,然而,随着文化与文明体系的日趋成熟,它也必然呈现出鲜明的理性化特征,这就与人的自然天性和感性体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说到底是作家用文字再现了这样一个观念急剧更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热情又敏感的内心,一切外在观念并非牢不可破的,人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欲望才具有主宰世界的作用。
尽管如此,欧洲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区别。华兹华斯眼里的大自然有花丛、嫩枝、清风、鸟雀,这些都是共存于世的伙伴,但人却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伤害着自己的同类(《写于早春的诗句》),雪莱的诗作里无论是宁静祥和的田园美景还是汹涌澎湃的自然伟力均成为他热爱与拥抱的对象,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等英国作家的笔下,他们均力图用对大自然的歌颂来抵抗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成为创作的重心。德国作家则沉湎于对人内心意识中神秘化的主观世界的描绘,诺瓦利斯在《夜的颂歌》中思考生存与死亡的界限,最后在对黑夜的赞美中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安宁,霍夫曼执着于对人内心矛盾的反思与探寻,人在物质世界中无法实现自身灵魂的安放。与之相较而言我们可以发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有着更为明显的现实介入意识,重视通过刻画人物的美好心灵世界以实现对于丑恶现实的超越,善于在颇具传奇性的故事中对理想人格形象加以营造,主观情感的抒发格外明显,同时,为了突出现实环境与人物性格,作家还广泛使用对照手法以营造审美上的差异性。
中国当代女作家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王安忆坦言,“我非常喜欢《巴黎圣母院》,尤其是站在塔楼上看巴黎那一段”[2]206,而《悲惨世界》则是她阅读世界中的一座高峰[2]345。迟子建则赞赏乔治·桑、杜拉斯、尤瑟纳尔等人作品中“浪漫的遐想,毁灭的恐惧,以及忧郁的宁静”[3]198。陈染在提到早期的阅读经历时说:“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那本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4]3除此之外,如铁凝、虹影、海男、赵玫等作家也均提到过自己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正因为此,她们在自己的创作中积极继承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有益成分并加以革新,我们将综合采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手段,试图揭示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当代女性小说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
二、理想人格:激愤倾诉与温情书写
对于“人”的重视成为自19世纪以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主流,艺术家们普遍致力于用主观色彩浓郁的笔触描绘人物的美好心灵,在苦难人生中煎熬却从未放弃人生信条的芸芸众生成了法国艺术走廊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对理想人格的诗意建构很自然地被当作基本的主题话语模式加以表现。这些艺术作品或以爱情故事的外壳细致勾画出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国青年从迷惘到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挣扎(《英迪亚娜》《娜侬》),或以散文诗式的笔调叙说人的精神世界里善的光辉逐步破除社会偏见对人的伤害(《魔沼》《小法岱特》)。
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一方面重视对其美好品质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更强调对其战斗意志的描摹。“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5]276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人物所表现出的与传统社会观念、等级差别乃至历史理性主义的对抗皆是为了反映出个体在当下的主观情感需求,人物的选择既不是为了从自然中实现心灵的解脱,也不会从颇具神秘性的灵魂斗争中走向颓丧,而是完全依凭自我的主观选择行事。乔治·桑的作品被称作“理想小说”,这主要就反映在其对于雷尔夫、娜侬、比埃等理想人格美好品质孜孜不倦的刻画之中。而在雨果与大仲马的作品里,人物与现实环境之间的搏杀有了更为直接的体现,《九三年》里的郭文在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放走了曾经的敌人,人道主义的精神在这时战胜了历史理性主义,《基督山伯爵》中唐泰斯先后面临朋友与妻子的背叛,但仍在历经苦难后回到故乡完成复仇。“自由与意志相关,自由产生于意志决断和行为。”[6]11人的价值的最终确认必然是通过其在一次次的主动选择中实现对过往自我的扬弃,进而实现“我”的个人主体性的张扬。
不过,在理想人物塑造的同时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也体现出一种观念上的复杂性,这就是既注重对人物主体自由精神的褒扬又反映出对传统宗教精神的回归。 “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具有排斥巫术和情感因素的倾向,它借助知性思考把这些因素升华为宗教救赎论,并在教义中描绘出世界的图象,进而力求理性地探讨世界的‘意义’”[7]102,这实质上便指明了知识分子恰是以宗教信仰为途径最终试图用奉献、博爱、良知等重新建立起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当我们看到冉·阿让在危难之时从神父那里感受到生命的救赎,小法岱特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以期待西尔维奈的痊愈时,其所反映出的正是艺术家们凭借自身浑厚的宗教情感来回应现世的痛苦与灵魂的挣扎。
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相较而言,中国当代女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一大批被现实环境所伤害的理想人物形象。这种伤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源于世俗规约对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哦,香雪》《小城之恋》),有的是由于历史风云变幻中个人的存在不再受到重视(《绿袖子》《北极村童话》),还有的则是被他人基于利益的需要直接当作了牺牲品(《回廊之椅》《偿还》),尽管如此,这些人物仍然与冉·阿让、格温普兰一样从未放弃过对于善与美的信念。中国当代女作家同样致力于利用作品实现对人物主观心灵世界的表现,王安忆认为,优秀的作家理应“富有浪漫气质”[8]213,但在她们的那些作品中,女作家们更多的是在故事叙述中将外部社会给人造成的伤痛当作潜藏的背景,在表现人物心灵世界的过程中使其逐渐得到消解。
而且,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对于宗教的认识不同,中国当代女作家常常是将宗教在慰藉人心上的积极作用同自身作为女性天然所具有的悲悯情怀融为一体。在迟子建看来,“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9]45徐小斌在谈到宗教的价值时则更直接地指出,“严格说来应当是‘宗教精神’而非宗教本身。”[10]204正因为此,尽管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作品中全力塑造了尼都萨满、妮浩萨满这样的宗教人物,但作者最终还是将笔墨收回到了对于爱与奉献这类普世情怀的歌咏之上。徐小斌的创作与宗教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她并非要通过对人物生命历程的探寻来为那些形而上的宗教观念给出答案。《羽蛇》中羽选择到金阕寺用刺青的方式实现解脱,《敦煌遗梦》里向无晔则以耶稣背负十字架式的精神力量带着肖星星脱离险境而自己却走向死亡,正是他们这些以毁伤自身肌体为代价的行为才使得原本神秘而不可把握的世界拥有了世俗人性的光辉。
正如勃兰兑斯所言,乔治·桑“经常屈服于女性的倾向,总是让心灵最先发言,而且说得最响”[11]138。情绪的节制在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这里表现得相对较弱,整体而言,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在塑造理想人格之时更重视激愤之情的抒发,这一艺术风格在其进行死亡书写时尤为明显,作者往往着重强调死亡仪式化的特征,借人物的言语、行为与最终遭遇呼唤着美好人世的到来。《九三年》里郭文被处以极刑的同时西穆尔登果断地饮弹自尽,《瓦朗蒂娜》里贝内蒂克特冲破等级的阻碍赢得爱情时却被情敌残忍杀死,所有的这些死亡现场都是以悲惨而强烈的方式进入读者的视野的。
中国当代女作家尽管也重视塑造人物时主观情感与思想的抒发,但在表现程度上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是有所不同的,她们注意表达的分寸感,避免因情绪或观点的过于直露造成审美上的缺失。王安忆说:“我从来不是像张爱玲那样地看世界的,我要比她温情。”[2]254迟子建则提出“我表达悲痛和感情并不想带有十分张扬的爱憎分明的情怀, 好作家用平静的语言叙述故事”[12]29。由此可见,这种创作风格上的同一性正是中国当代女作家在形成自身独立文艺观念后的自觉产物。例如在迟子建的《亲亲土豆》中,李爱杰尽全力也没能挽回丈夫的生命,在埋葬丈夫的遗体后,她只是用一句“还跟我的脚呀?”来表达出自己失去亲人的苦楚。对于中国当代女作家而言,其笔下的人物最终实现自身心境的安宁常常是通过爱与善的发现,于是,明确的温情意识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中便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传奇故事:神秘氛围与田园牧歌
受笛卡尔唯理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古典主义在创作观念上坚持理性原则,如布瓦洛便强调文学创作须模仿自然,故事情节应该合乎常情常理,避免荒诞离奇,而这样僵化的文艺思想在格外重视“自我”发现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眼中则成了发挥文学创作力的羁绊。“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13]92,在雨果看来,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书写本质上是其主观选择后的产物,也正因为此,由其所描述的历史本身就是杂乱无章的,作家的任务就是“用富有时代色彩的想象填补他们的漏洞,把他们任其散乱的东西收集起来”。[13]62乔治·桑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使人喜爱他关怀的对象,必要的话,我不责备艺术家稍稍美化这些对象”[14]113。通观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们均特别重视对于故事传奇性的把控,凭借想象、虚构与夸张的艺术手法来对自然真实加以重构,由此建立一个理想化的主观世界。
在情节安排上,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通常是将许多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所有事件尽管繁复,却是完全统一在主要情节周围,因此并不显得杂乱无章,而且,作者极为重视情节衔接上的合情合理,通过有效的安排与调度以避免空洞的想象。《笑面人》中的格温普兰原本为贵族出身,可惜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卖给儿童贩子,当他的存在可以为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服务之时,他又成了议员,而他之所以能够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正是由于当年记录有格温普兰身世的漂流瓶被儿童贩子丢到海中并在多年之后被宫廷得到。又如《基督山伯爵》里唐泰斯在出海途中曾受老船长之请给被囚禁中的拿破仑送信,这一行为的出现看似难以置信,但却在之后成为唐泰斯被人陷害的源头。此后,他又与素不相识的神父建立了友谊,而这一情节的设置则为他复仇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然状态中的非常态环境在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并不鲜见,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仍继承了18世纪后期兴起的哥特式文学的部分审美特征,对于自然环境的刻画着力渲染其给人带来的神秘、恐怖的心理体验;另一方面,他们则进一步从自然的野性、灵性、神秘性出发来发掘其迥异于社会性空间的荒野本色,重视其对于人发现自身、再造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由此,人便从对自然环境最初的心理性恐惧中解脱出来,实现主体精神与客观自然的有机融合。如在乔治·桑的《莫普拉》《魔沼》《水晶旅行记》《泰坦的风琴》《巨人岩》等作品里,她都在书写自己对于自然界中神秘力量的感受,故事初始的氛围完全是阴暗、奇诡的,她也正是利用了哥特式小说中的这类环境描写手法来烘托出小说的传奇性色彩。不过,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可以注意到,她并没有一味地承袭哥特式小说中血腥、黑暗的元素,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摆脱了对自然的仇恨或疑惧,反而是从自然惊人的伟力中汲取了前行的勇气。正因为此,勃兰兑斯在点评乔治·桑的《魔沼》时才会提出,这部作品“是她向巴尔扎克宣称她所乐意写作的——十八世纪的牧歌”[11]185。
王安忆曾提出,“写小说就是这样无中生有、无事生非。”[15]46这一表述本身即是对中国当代女性小说中存在的传奇性色彩的最好证明,尽管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叙事中,那些奇诡、超验的部分所占的比重相对要少许多,她们更多的还是通过对乡村或都市中凡人俗事的描绘来倾注个人的情感表达,但这并不影响其采用传奇性的书写手法创造出充满想象与虚构的艺术世界。
事实上,传奇在中国古已有之,由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出现开始,随着城市经济的日渐繁荣,“说话”艺术逐渐得到了从民间到皇家的全社会性的关注,这便为唐代以来传奇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基础,到了明清之际,文人传奇小说则进一步发展为“史、诗、思并存的‘复调’文体”。[16]79在中西双重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中国当代女作家很明显是重视小说的故事性与可读性的。虹影曾说:“我对故事的着迷如同对待美食。我永远想让我的人物多遇上点惊奇、多撞上点危险,读起来几乎像惊险小说”[17]17,这种对于讲故事的执着直接表现为她们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传奇性因素。例如,从情节结构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当代女作家注重因文生事、幻设情节,故事的发生看似有明确的时空背景,但后续展开则往往并不受其拘泥,以虹影为例,她的“重写海上花”系列即是对每段各不相同的传奇故事的精彩演绎。
但是,在向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传奇性书写特征学习的同时,中国当代女作家格外注意到的则是其部分作品中在传奇性外衣的包裹下透露出的牧歌情调,并在自身的创作中将这一倾向尽可能地发扬开来。如果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更多的还是用传奇故事来抵抗平庸、拒绝世俗,那么,中国当代女作家则在营造传奇氛围的同时还试图通过重构神话与回归自然的手段,力图在现代的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外开垦出一块灵魂的栖居地。对于中国当代女作家而言,重构神话是在非理性观念的支配下书写传奇并进而重新定义自身的文化过程,回归自然则是在肯定自然神秘性的基础上发现浪漫风景、保留生命原始激情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重构神话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一种普遍性行为,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重塑神话本身即反映出其强烈的存在焦虑。在陈染看来,“现代人的神话故事或神话式的小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原始向往或什么简单的永劫回归,它是以一种超自然的魔力,寓言式的哲理以及神奇的象征性来探索宇宙的源起、生命、意识和人性等等重大的前沿问题,它面对着的是永恒境界。”[4]164在她的“小镇神话”系列作品中,她笔下的罗古镇、乱流镇、老屋镇等都被笼罩在神秘、蛮荒的氛围之下,但陈染并非真正希望去探讨小镇特殊景象的形成缘由或个人与小镇之间的纠葛,其作为现代神话出现的意义在于将社会空间化的小镇视作人类文明历史的承载体,人物更为关注的是自身在摆脱与其具有的现实关联之后实现的心灵自由。
“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无比钟情, 而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 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18]80-81迟子建始终抱持着“万物有灵”的观念来书写自然,比如《逝川》中会流着眼泪进入人们视野的泪鱼、《候鸟的勇敢》里慰藉张黑脸与德秀师傅内心的东方白鹳,所有这些自然风物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世界。这种观念的出现与迟子建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漠河北极村的特殊风土人情使得自然环境与人类主体的浑然交融成为一种极富普遍性的现象,人类因其生命的有限性对永恒且神秘的自然充满了敬畏与崇拜,而当迟子建离开北极村步入城市之后,现代都市中的人情冷漠与拥挤喧嚣使她感到无所适从,此时她便希冀从大自然身上汲取养分,从而摆脱生命困境。因此,迟子建小说中对传奇性的自然风情的描绘最终是归于她期望中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情愫的,这类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则是她为自己创造出的童年天堂。
四、对照手法:极致表现与技巧革新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重视对照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灵活运用,其中取得最大成就的当推雨果。对于雨果而言,对照手法之所以在其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肯定。在基督教的文化体系中,世界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两个部分,即可以被把握的物质世界与抽象的、不具有实体性的精神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也便由此被概括为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易于毁灭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精神的”。[13]44正是受这种灵肉对立统一观念的影响,雨果坚定地认为文学同样应该表现出对立统一观念,理应反映出光明与黑暗的不同,重视美与丑各自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雨果极力提倡作家应摆脱过往狭隘的艺术认知观念,发现事物不同于过往的、被遮蔽的特征,“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3]30世界的真实面貌原本就是美丑并存的,作家的职责应该是向读者表现出世界的真实形态,而不是人为地以所谓纯粹的理性认知去否定人的感觉世界,将客观真实与秩序、条理、规则等普泛化的概念强行捆绑在一起。于是,雨果坚定地将美丑对照观念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这里主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雨果及中国当代女性小说的关联加以分析。
雨果对于人物的塑造是丰富而立体的,这使得其使用对照手法表现人物时并不单单拘泥于不同人物之间的两两对照,同时也可反映在同一人物的外部形象与内心品格的对照之中。《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埃斯梅拉达、广场上的乞丐与孩童等尽管未曾拥有显赫的外在身份,但却或天真烂漫、或嫉恶如仇,而克洛德、腓比斯等人纵然身处于上层社会,却均囿于一己私利。《悲惨世界》里的福来主教、冉·阿让、芳汀等人在看似悲惨的生命遭际中尽可能地为他人释放自己的渺渺微光,与之相对,如泰纳迪埃夫妇这类人物则成为恶棍的化身。雨果通过两两对应的人物群像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残酷与暴虐,让人们看到一个悲惨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而在同一人物外部形象与内心品格的对照上最为成功的则是卡西莫多与格温普兰,卡西莫多一出场即以其四方形的鼻子、马蹄铁状的嘴巴、眼睛上方硕大的肉瘤、隆起的驼背为丑怪树立下最高标准,格温普兰则是因儿童贩子的手术而有着一张看上去永远都在怪笑的丑脸,但正是这两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却拥有着远远超于常人的善良与纯洁。
中国当代女作家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对照艺术的继承首先也是反映在其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极限律的时候,必然地会选择处于两极的人作为他的主人公”[19]263,中国当代女作家在设置小说人物时就常常将其描写为具有不同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的两类人,由此营造一种明显的戏剧性冲突来形成对照性,例如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我”、父母、老师与妹妹安然之间在生活观念上的区分,王安忆的《富萍》里李天华与富萍面对生活变动时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但与雨果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美丑、善恶的极致表现不同,中国当代女作家尽管也表现恶与丑,但整体的表现程度上则明显被有意弱化,至于雨果作品中人物夸张的外部形象与臻于至善的内心品格之间的对照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笔下则更为少见,她们更多的是从现实文化环境的层面上对人物的不同选择加以注解。
同时,中国当代女作家借鉴对照手法时在运用范围上则有了进一步的革新,如在作品内部通过动与静、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来形成文本张力,在叙事视角与逻辑上借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不同形成一种复调式的言说,通过思考个体浪漫与集体浪漫的相互关系来表达其创作上的个人化立场,这些新变既是由中国当代女作家所面对的创作对象的丰富性所决定,也与其居于女性身份而习惯从细微处探究世界的认识方式有着紧密关联。
海男的《女人传》《乡村传》《身体传》等作品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叙述范式,这些作品没有主角人物,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故事,有的只是单纯的叙述和诗化的语言,而海男在这种自身独有的跨文体写作中创造性地通过动与静、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照性来结构文本,从而使作品内部拥有潜在的对话性空间。《乡村传》中一再出现的迟暮老人的照片以及作者从历史典籍上摘录的农具图或劳作图都在印证着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乡村行进的缓慢步伐,但作者在叙述中则借助“上百只滚动在尘埃和阳光之下的土豆”“一只兔子在广阔田野之间奔跑的速度”等处于活动状态中的事物来向读者低诉着乡村的活力与希望。《身体传》中“身体”的存在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物质实体,它自身的意义必须通过少时的数字、色彩和成人后他或她的抚摸等等对象来逐步得到实现。
成人通常是以理性与合乎逻辑的思维模式来展开思考,这使得成人得以对世界有更本质化的认知,但往往却忽略了对世界的情绪感知,而儿童对于世界的把握则更重视自身的即时感觉和想象力的释放,因此,从儿童视角出发能够在与成人视角的对照中进一步丰富作家对于外部世界的书写,而且,以儿童视角展开的文本还具有极强的乌托邦伦理叙事特征,故事主题的深重在童心的映照之下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解。迟子建的《清水洗尘》中,天灶第一次坚持着用刚烧开的清水洗了澡,感觉自己与夜色中的星光融为一体,天灶的成长也正是在与成人世界观念的对照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在《花瓣饭》里,儿童视角则直接成为摆脱现实境遇的有效手段,父母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眼神难免是“愁苦”的,但仨姐弟却在日常的斗嘴中排遣掉了家中紧张的空气。
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过程中,个体浪漫与集体浪漫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忽视的。在丁玲、杨沫等女作家的笔下,林道静这一类人物的出现是合乎时代话语要求的,当个体自觉自愿地投入集体的怀抱后,个体的浪漫渴求便与集体的浪漫事业和凝为一。然而,进入新时期以后,作家看取个人与集体的目光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一出场就站在个人的立场,这是我们的发源地”[20]34,显然,重视个体的独立价值成为这一批作家自觉的选择。例如虹影的《我们互相消失》中的尹修竹与徐小斌的《羽蛇》里的杨碧城,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她们未曾如旁人一样被虚幻的政治话语所左右,而是更珍惜作为个人和女性的自己,以浪漫的遁逃与狂欢中的集体划清界限。
“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是处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13]45以雨果为代表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对照手法的使用来呈现自身的美学主张乃至现实关怀,中国当代女作家在学习这一艺术技巧之后则根据创作的需求对其进行了灵活的运用,服务于自身对于主观化的理想世界的构建,使得对照手法在中国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了全新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