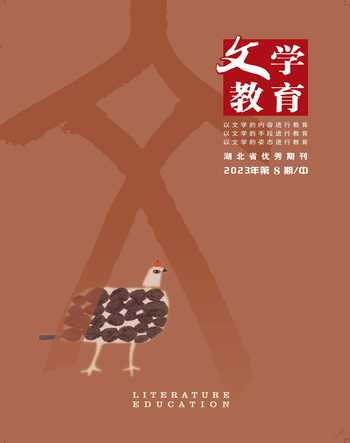从审美到空间:论《源氏物语》的中国文化源流
胡梦天
内容摘要:当代的空间价值评判体系深受西方话语的制约,追求技术至上是这一话语的重要特征。中国的空间文化有着数千年的传承,以天人合一为主的空间理念对东亚诸国的空间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源氏物语》的空间书写正是这一影响的体现。随着文学审美的提出,以民族主义导向的经典生成,近代《源氏物语》研究体系也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了探索其空间价值的倾向。本文所关注的正是《源氏物语》空间价值发现背后的话语,基于此探讨当代“源学”在“跨学科”趋势下的可能。
关键词:《源氏物语》 文学审美 空间价值 “跨学科”
正如川端康成所认为,“在《源氏物语》之后延续几百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都是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1]。《源氏物语》作为经典巨作,对后世日本的民族文化形成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近代以后《源氏物语》批评的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使得《源氏物语》经典的确立蕴含着将审美概念工具化的政治导向。但从器物层面看,《源氏物语》创作时期的日本上层阶级形成的是“国际元素至为丰富的文化”,建筑空间正是该文化下的一种表象体现,否定了汉意“缺席”[2]的可能。笔者所关注的正是中国文化下《源氏物语》的审美意识的确立到空间价值发现的联系[3]。
本文试图通过《源氏物语》审美确立下的表象空间构建入手,进而分析近代话语下文学经典确立与表象空间的关系,最后阐释近代以来物语空间价值的生成缘由。
一.《源氏物语》审美确立与表象空间构建
平安时代女性文学中的感性元素发达,“あはれ”一词备受推崇,也是《源氏物语》主要的审美观念。其本质是人的情感因外界的感动真实且自然地流露,“通过人情的纯粹化表现,使文学脱俗、雅化”[4]。据学者的统计,《源氏物语》中大部分情况下仅出现“あはれ”。这一审美情趣排除了“政治、道德、说教”这类无法引发“哀”的内容。这种“哀”则是自然而然地“与对象无限贴近,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直至与对象融为一体”,具有“人情主义”的倾向。后世将这一审美定义为“物哀”,其中“物”是能引发哀感“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这与陆机《赠弟士龙诗序》的“感物兴哀”与之较为接近,但在“物”的外延与“哀”的表现上仍有所区别。尽管如此“物哀”的源头依然与中国有关。道家主张的性情论正是生成其内涵的一大要素。性情论主张不被社会道德规范所干扰的自然天性,是“道法自然”在人之性情方面的诠释。从道家思想对平安时期文化的影响情况来看,性情论具有较大的可能性被紫式部内化进而形成“物哀”的审美观。由于“物语中主要人物生存环境的描写,都不是纯景物的静态铺陈,而是与人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相联系”[5],因此,空间作为叙事的舞台是人物生存环境的直接体现,且其本身就具备诱发哀感的条件。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贯穿全文的“物哀”审美,现实中的空间要素才得以被选择性地汲取,在化用中国文学的同时,构建出物语中的空间。
《源氏物语》中空间往往呈现“幽玄”的审美,在文学上这一审美观念起源于平安王朝。在中世后,武士与僧侣阶级对王朝文学的模仿并集中于“个人内在的精神涵养”,“幽玄”的审美因此得以兴起。与侧重男女情感的“物哀”相比,“幽玄”很早形成概念化成为中世审美的尺度。早在平安时期的文学中普遍具有“幽玄”的审美色彩,《源氏物语》也不例外,在空间书写上也是尤其显著。由于该时期佛教对上层贵族的影响主要是在“生活风俗与行为层面”[6],这使得空间中的“幽玄”审美尤为明显。笔者以为“幽玄”的书写还与中国道教存在着联系,早期道教的“静室”又被称为“幽室”或“幽房”,讲究清静、幽深、养阴,认为只有在这种特定的居室内斋戒,才能做到与神灵交通。[7]“幽玄”正是建立在信奉超自然的神灵基础上,由“氣”形成的“怪物”[8]才具有出现在空间的可能。《庄子·杂篇·庚桑楚》中云,“有生,黬也”。这里的“黬”是“幽暗”,林希逸说“喻气之凝聚”,也就是“有生命,乃是气的凝聚”[9]。“道家哲学把整个宇宙看作气化流行的大生命秩序,人是其中的小生命”[10],因此“幽暗”的空间则是具有连接人与宇宙的可能。不同于儒、佛这类显学,道家思想正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促成了平安时期的审美情趣,成为日本文化生成的养分。同时,“物哀”“幽玄”作为审美观念的确立与《源氏物语》经典化的过程密不可分。
二.《源氏物语》经典生成下的民族意识与表象空间
“国风文化”鼓吹的“和魂”意识,其去除“汉意”的观念与日本文化生成的客观历史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在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中,尤其能够体现。成书于11世纪初的《源氏物语》,尽管使物语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也“仅仅是女性的娱乐读物”[11]。江户时代以来,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武士集团的日益强悍[12],日本社会逐渐对该时期的中国产生了蔑视心理。本居宣长(1730—1801)通过“国风文化”中形成的《源氏物语》提出了“物哀论”,意图“彻底清除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影响”,“从确认日本民族的独特精神世界开始,确立日本民族的根本精神,即寄托于所谓‘古道中的‘大和魂”[13]。早在平安时代中期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专属男性,女性则需要远离“汉才”[14]。正是紫式部面对“汉才”的回避态度,才为后世的国粹主义者提供了发挥余地。笔者以为,这种“和魂”意识自形成以来就与中日交流的客观历史之间存在着矛盾。首先,“国风文化”发展阶段并没有任何一种极端的文化运动彻底摧毁“唐风”时期积累的文化财富,“国风文化”中所谓的文化自立不过是建立在长久以来的中日交流基础之上,并没有彻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意识提出显然与客观历史形成悖论;其次,“国风文化”发展以来文人普遍存在“和魂”意识的倾向,同时流露出对中国无限向往的矛盾心理,该时期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的中国书写便可证明这一点。
这种“和魂”的提出是建立在唯意识论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忽视表象的形成。中日官方停止交往的一段期间内,两国在民間仍有贸易上的往来,并且贵族也热衷于“唐物”[15],这点在该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物质世界书写尤其能够体现,在器物层面上否定了“国风文化”单一性的可能。河添房江认为,“国风文化”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催生出来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与藤原文化一样,是对10世纪到11世纪的文化的某一侧面的过度强调”。其“过度强调”的背后正是将文学中的情感语言作为政治工具。笔者认同《源氏物语》创作期间的文化环境是处于多元交融状态的说法,这种多元融合的文化集中体现在表象空间上,由此成为后世客观评价的重要依据。在河添看来“国风文化就是在消费唐物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洗练的都市文化”[16]。正是“唐物”构成的表象空间客观存在,主张去除“汉意”的观点才更显得不切实际。
三.《源氏物语》从“器”至“道”的空间价值发现
自日本近代以来,《源氏物语》的空间书写常被用于以“器”为中心的建筑研究[17]。赤泽真理认为,平安时期的居室是模仿中国的三合院,这形成了《源氏物语》中的居住空间书写。伴随着物语文本在中世的接受,对于读者的空间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物语绘卷可以认识中世、近世空间观的变迁[18]。安原盛彦试图通过《源氏物语》中包含了出场人物在空间中的所见、所思、所感,并且以语言的形式作为表现,因此透过这些书写可以了解到作者紫式部的空间观,进而得以考察居室的空间性质[19]。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五行思想和四合院的构造。笔者以为,这类观点无非是把居室作为具体之物看待,因此这类视角往往忽视文学中的空间想象与象征的成分。尽管若山滋认为空间是女性身体的延伸,空间顺序为“肉体、衣服、帷屏、帘子、纸隔扇、格子窗”[20],试图使空间与人物情感之间产生关联,但这种联系依旧属于物质层面,其研究的对象不过是表象上的空间。值得肯定的是,文化研究需要以“器”的层面作为起点,进而触及其“道”的实质。尽管如此,以情感语言为主的《源氏物语》反映的是人情,空间仅是作为人情的外在表现,因此空间中审美和文化仪式同样也是空间价值体现的一部分。
“道”是空间精神性的层面,《源氏物语》空间构建中的“道”主要集中在审美与文化仪式上。结合上文,物语中“物哀”的主要审美对象是人情,空间书写的存在正是为了反映人情,因此通过物语中表象空间的书写可以发现内在人情的影响来源。在中西进的《源氏物语与白乐天》一书中通过空间构建的相似性,反映白诗对《源氏物语》中人物情感的影响,例如书中通过《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和《草堂记》对“须磨卷”中源氏公子居处空间构建的影响提出,物语中“石阶桂柱竹编墙”的中国房屋样式与室内器物,正是紫式部“想要強调退居是多么的寂寥”[21],由此才“按照白乐天流谪江州、忠州”相等同的思路,构建出“源氏退居须磨”的居住空间。也就是说,空间作为情感的表象,紫式部通过相似的空间书写是为了化用情感。其次,《源氏物语》中存在大量以“幽玄”审美为引导的表象空间书写,包括可视空间与不可视空间。可视空间是以结构、光线和色彩为表现,以“幽暗”为主是平安时期空间的共通反映,在后世的空间构建中也有所体现。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提到,傍晩乡村茅草屋顶“幽幽亮起如今被视为落伍的那种浅碟型灯罩的灯泡时,甚至觉得别有风雅之趣”[22],这里的“风雅”即是“幽玄”所营造的居室之美。与视觉要素共同构建空间“幽玄”之美的还有香气和声音。由香气构成的空间主要包含室内焚香、居室沉香器物、庭院花草等,它反映的不止是居室结构,还是空间中人类的文化活动。在日本香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源氏香”[23],正是《源氏物语》表象空间价值的体现之一。在听觉要素中,由室外的自然之声、人之细语以及演奏乐器等构建起的审美意境,同样是介于可视与不可视之间的表象空间。正如“男女初次约会大都隔帘而坐,只听对方的声音”[24]所表现的“幽玄”之境,只有在感官要素融合的前提下,空间中的“境”才得以体现。
作为女性视角下的古典文学,《源氏物语》正是拥有大量的表象书写,才为物质层面的研究提供可能。近代以来空间的研究价值,依靠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发现与认可,《源氏物语》的空间研究也存在这一倾向,但其本身是以情感语言为主,加之涉及部分儒释道的启发性语言。因此,技术至上的话语必然破坏其中的审美因素。尽管若山滋将《源氏物语》的空间元素进行统计,就此提出物语中的空间是“行为的舞台”“行为的对象”“审美的对象”,但却忽视了背后文学经典化确立的缘由等精神层面因素。另一方面,以意识作为第一性形成的观点容易走向唯心主义的误区。单从“物哀”审美的确立来看,其词经过“单一性——丰富性——概念化——工具化”这四个阶段,正是物语研究本身存在过分注重形成下所形成的弊端。因此,“跨学科”视域下的空间研究需要避免这两种极端,这是本文探讨《源氏物语》空间的价值所在。
注 释
[1]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叶渭渠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2]详见本文第二节江户时期“物哀”提出的背景与意图.
[3]至今为止中日学界几乎未见对《源氏物语》居室空间价值的研究。本文引用的外文资料,除明确标注外,均由笔者所译.
[4]王向远《中日“美辞”关联考论——比较语义学试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63、179、181、185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作简称“美辞”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张楠《谈“源”论“道”》,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15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作名称“谈‘源论‘道”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6]详见:美辞,第161页.
[7]王承文《漢晉道經所見“静室”各種名稱及其與齋戒制度的關係》,载《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6年第三十四輯,第140页.
[8]原为“物の氣”,多数场合下写作“物の怪”.
[9]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08-711页.
[10]详见:谈“源”论“道”,第130页.
[11]刘金举《作为“国家认同”工具而被经典化的<源氏物语>与“物哀”》,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三期,第128页.
[12]张楠《从“物纷”到“物哀”——论<源氏物语>批评在日本近代的变迁》,载《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二期,第24页.
[13]本居宣长《日本物哀》,王向远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14页.
[14]详见池田龟鉴《平安朝的生活与文学》,玖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
[15]“唐物”一词本文中指中国各历史朝代出口到日本的货品,并非仅限于唐朝.
[16]详见河添房江《源氏风物集》,丁国旗、丁依若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6、7、283页.
[17]如《易经·系辞下》所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东亚建筑空间具有功能性和精神性统一的特征。详见李百进《唐风建筑营造(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75页.
[18]赤澤真理:『建築史の中の「源氏物語」――同時代の住宅像と考証学のあいだ』,载『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部門研究年報』2018年第14号,第55页.
[19]安原盛彦:『「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寝殿造住宅の空間的性質に関する研究』,東北大学博士卒論,2000年,第1页.
[20]若山滋:『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建築空間,载『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報告集』1990年第408号,第95-98页.
[21]中西进《源氏物语与白乐天》,马兴国、孙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90-92页.
[22]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刘子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23]尾崎左永子:『源氏の香り』,東京:朝日新聞社,1992年,第9页.
[24]详见:美辞,第169页.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本文为项目名称“中国美学思想与《源氏物语》建筑空间观念的形成”,项目编号IF2022064的结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