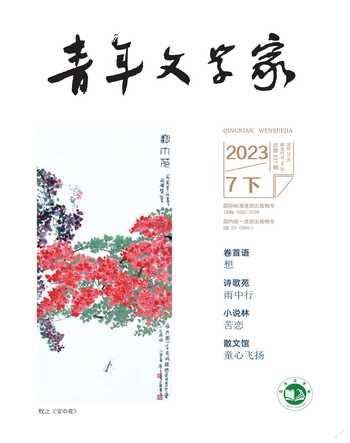漫将诗笔借花题
覃卫媛


王拯(1815—1876),马平县(今柳州市)人,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是清代广西籍著名文人。其散文师承桐城派后期领军人物梅曾亮,为文“淬厉精洁,雄直有气”(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七),与吕璜、龙启瑞、朱琦、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大家”。此外,他亦善书画,工诗词。其词多怀古伤今之调,风格情调近宋、元之交的张炎,与龚自珍、张惠言等并称“清代词坛后十家”;其诗歌“意深而词粹,‘兼有苏、黄二家之长”(刘汉忠《王拯年谱》),称得上是“广西历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王德明《广西古代诗词史》)。王拯诗歌主要收录在其诗集《龙壁山房诗草》中,有一千一百余首。其诗题材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山水行旅、赠别酬唱、悼亡、悼友、题画、咏物等方面。其中,咏物题材以咏花最为突出。据统计,王拯诗歌题目中与花相关的有七十余首,创作时间贯穿其青年至老年的大半人生,尤其是其辞官归居桂林后的咏花作品最多,计有四十六首,占总量的三分之二。纵观其咏花诗,所写之花卉约二十种,诸如牡丹、菊花、海棠、梅花、丁香、兰花、杏花、鸡冠花、凤尾蕉、山茶花、荷花、楸花、芍药、桃花、野凤仙、龙船花、那悉茗花等。从王拯的咏花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审美取向,也可以看出他对人生进退行藏的抉择与价值体认。目前,学界对王拯诗歌的研究还比较少,相关研究成果有对其诗歌思想内容的整体概述和艺术成就的评述等,此外也有对其写景诗与题画诗的研究,而对其咏花诗还未有相关探讨。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王拯的咏花诗进行分析,从其审美活动、进取仕途及退居乡里三个方面探究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
一、赏色与品香:嫣红姹紫密或疏,浥露浓香绝点埃
赏花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可以怡目娱心,也能陶冶性情。“对于各式花木,中国古代有着普遍、持久和强烈的审美热情。”(薛富兴《中国古代花卉审美概观—以〈花史左编〉为中心》)可见,这种审美意识的形成由来已久,且在不断发展中演化成某种群体的审美自觉。古人在赏花时,注重赏花之形、色、香。王拯赏花,尤以浓艳的花色、花香最能引起他的审美享受。1841年冬,进士及第后新任户部主事的王拯和朋友一同前往城南赏暖窖中的花卉,便被花儿鲜艳夺目的色彩吸引。其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同姚子箴大令(辉弟)翰臣蓱矼遍看城南窖花归饮酒肆》一诗中写道:“纷纷瓷玉堆盆盂,嫣红姹紫密或疏……凌波仙子黄玉肤,翠衣珊珊来藐姑……虬枝蟠天粉雪铺,鹤顶烂若腥红涂。”(王拯《龙壁山房诗草》,以下所引王拯诗例均引自该文献)暖窖中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争妍斗奇。密处绚丽浓艳,疏处娇美烂漫。水仙花朵如黄玉般润泽细腻,衬以绿色的叶子显得那么轻盈柔美,仿佛藐姑射山上的神女一样飘逸出尘。白梅如雪铺满枝头,鹤顶红花朵灿烂夺目的艳红仿佛是鲜血涂染的效果。这首诗中王拯对花卉颜色的鲜明感受可能还受到其新科登第正式进入仕途的愉悅心情所影响。但十年过去后,他在咏花诗中依然热衷于享受色彩带来的愉悦之感,如作于1854年的《同人过十刹海看荷花遂游高庙四首》,他感受到的是“水花红尽汇通祠”,扑面而来的是荷花那热烈缤纷的红色。1857年,他到极乐寺看海棠时依然对花有“露苞万蕾真珠红”(《伯涵老兄以出游城西看极乐寺海棠、万寿寺松长句见示次韵万寿寺余犹未到也》)的感受。由此可知,王拯赏花时侧重视觉感受,所描写的花色多呈现鲜艳明亮的特点,让人印象深刻。有时,他会将盛开的繁花想象成一道道美丽的锦帐,如他在极乐寺观赏海棠时,远远望去,只见“瞢腾锦幄千丝幛,的历金珠百琲排”(《极乐寺看海棠时花蕊甫齐也用壁间韵》),盛开的海棠花朦朦胧胧,像华美的锦缎和丝绸制成的帐幕,又像是将无数鲜亮的珍珠串在一起。另外,他还喜欢写花量之多,如“园池浇屋万荷花”(《与琴西步荷池上作》),也喜欢强调花色之浓,如“浥露浓香绝点埃”(《嘉甫兄庭中牡丹大开招饮》)等,足见花卉给他以密丽繁茂的深刻印象。
王拯咏花不但将色彩渲染得极为浓郁,甚至花的气味也十分醇烈,如他在《寓居时花数种盛开》中写道:“海乡春事早,花气满精庐……却忆城南陌,浓芳定几株。”这首诗约作于他在广州探望刘氏姐时,他欣喜于南方春天来得早,寓居的庐舍中充满了花的香气,同时又不由得想到京城城南常去看花的寺庙中,不知道这时候有几株花树能有如此馥郁的芬芳。而“城南诸寺门芳辰,岁岁香红走玉轮”(《次和润臣楸花诗意》),在他的记忆深处,城南寺庙中的花树每年都开得又香又艳,令人赏心悦目。
当然,王拯所咏之花也有清疏淡雅的色调,如他咏梅花“梦回欹枕沁香闻,胆瓶一枝助清警”(《瓶梅次子穆韵》),梅花枝条稀疏,香气清寒,沁人心脾。诗人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梅花的神韵。总体而言,王拯更偏爱描写鲜艳浓郁的色彩和香气,即使如兰花这种素来被视为清幽高雅的花卉,诗人也别开生面,描写群兰盛开的风姿与芬芳,如“百琲瑉珰掩黛裙,盈盈碧玉也超群”和“岭外曾传桂作州,簟瓢能使一山幽”(《赛兰作花其香殊甚褒之以二绝句》)等句,大片大片的兰花像珍珠美玉般,盈盈风姿,拔萃出群,它们散发的香气弥散在山野间或花田里。又如,清淡素洁的菊花,诗人也先看到它“紫红作意绚秋光,欲与春花斗晓妆”(《容庵同年春农太守各赠丛菊》)的奇趣,还有那“篱东花满夕阳西”(《庭中野菊正开松孙又送白者一种叠前韵》)的繁盛景象,更遑论牡丹那“灌水有秾芳”“艳植讵所当”(《粤花三咏》)的雍容华美。
狄德罗说:“在五官感觉之中,视觉最肤浅,听觉最傲慢,嗅觉最易给人快感。”正因为色彩最容易让人形成直观感受,而气味对感官的刺激最易调动人的情绪,所以花卉的色彩与芳香频频激起王拯的审美热情。有诗为证:“丁香淡白海棠红,摇毫掷简几不供。”(《琴西寓庐花事颇饶再叠颖叔大树庵韵余苑庐及舫斋海棠丁香近亦作花因复和之》)显然,鲜艳的色彩作用于王拯的视觉神经,唤起他的审美愉悦,调动了他的审美情感,让他情不自禁用文字复现这种审美感受;但他也感叹,无论写下多少溢美之词也难以言尽花朵的美丽与芬芳。
二、忧国与伤老:探花烂漫曲江曲,凄迷香色送青春
古人咏物注重“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这种传统的借物兴感的表现手法最能将诗人“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沈起龙《论词随笔》)。王拯常因赏花而兴发感动,遂借诗或表达爱赏,或抒发对国事的忧虑,或表达对老去无成的失意。诗人生于桂林,幼年时父母双亡,遂到柳州与寡姐相依为命。其姐课弟甚勤,因此王拯学业颇为上进: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后又屡有升迁,曾任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寻迁通政使。他在《示内》诗中说自己从小便立下壮志,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因此格外关心政治时局。
王拯一生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个时期,彼时内忧外患困扰着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也牵动着王拯的忧国之心。为了挽救危亡的清政府,王拯积极条陈时政、出谋划策,为朝廷荐举人才。他还用诗歌反映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对家国命运的忧患之情。他在1852年写的长诗《书愤》中真实记录了一场战争,诗中抒发了诗人对集团内部因政治矛盾而相互倾轧的不满和愤怒。当时的大学士祁隽藻给予这首诗高度的评价,认为这首诗在思想内容上与杜甫的《北征》一样具有诗史的性质,并说王拯是“壮岁忧时未解颜”(《题王定甫〈龙壁山房诗稿〉二首》)。这说明,该诗的创作动因是诗人对时局的担忧。这种担忧在其咏花诗中多有呈现,如1853年,王拯在《残菊》中写有“故园经乱取相思”之句,表达了他对家乡政治时局的关切;1854年,在京城南郊赏花时,他写了《次和润臣楸花诗意》一诗,诗中耿耿于“霜蹄蹴踏风如扫”的动荡局面。1857年,他所作的《月夜杏花下作》最能体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黄昏晚饭深檐坐,新月林梢一痕破。栖鸟林间时有声,花枝蒙蒙月微堕。去年种花春事稀,今年看花春又迟。两株红白自能好,正是江村菖叶时。连畿到处愁蝻子,吴楚东南兵未已。削榆为粥冰作糜,重说流亡起淮氾。探花烂漫曲江曲,暖日和风浑不足。明年花发定如何,日坐花前转愁独。”诗歌前八句写看花的时间环境与感受,渲染了清冷的氛围与兴致之缺,以“两株红白自能好”聊作一赏。接下来的四句则表明了无心赏花的原因,“连畿到处愁蝻子,吴楚东南兵未已,削榆为粥冰作糜,重说流亡起淮氾”。据《清史稿》记载,咸丰七年(1857)春,长江流域至黄河流域地区蝗灾严重,“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虸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邢台有小蝗,名曰蠕,食五谷茎俱尽;武昌飞蝗蔽天;枣阳、房县、郧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除了天灾,又有人祸。起于1851年的兵变对清朝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故王拯有句“吴楚东南兵未已”。因为天灾人祸造成了百姓游离失所,无以充饥,过着艰难的生活。诗人也由此关注到历史上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关注。最后四句表现出一种对时局发展的担忧,其中“探花烂漫曲江曲”用了杜甫的典故。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有诗《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甫被困长安,春日潜游曲江,面对家国的残破内心里压抑沉痛,眼中的烂漫美景却生发无限的伤感与凄凉。显然,王拯借此表达自己面对混乱时局,心中愁肠百结,忧思惶恐。
王拯所任官职多为闲职,这使得他无法实现政治理想与抱负,其诗多有蹉跎岁月的人生慨叹,如《慧福寺看牡丹》:“苑墙东与梵宫邻,花事来看百感新。绝代有人伤暮景,仙云何事落凡尘。江湖莽荡风埃剧,簪珥栖迟岁月频。只合僧窗闲啜茗,凄迷香色送青春。”此诗约作于1860年夏初牡丹渐衰之时,是年王拯四十五岁,在京任军机章京一职。彼时,清王朝政治环境动荡不安,王拯到慧福寺看牡丹时显得心情极为复杂,所以他在首联第二句写“花事来看百感新”。颔联写“绝代有人伤暮景,仙云何事落凡尘”,他从风华绝代的牡丹花临近衰萎时期而兴发流年易逝的感伤之情,接着又用仙凡进行对比,牡丹这种美好的花卉只应天上有,却不幸落入凡尘,暗示自己人生境遇的乖违。颈联“江湖莽荡风埃剧,簪珥栖迟岁月频”,写凡尘俗世如今是战乱不断,动荡不定,而牡丹花栖迟在这安静的寺庙当中空度岁月。诗人继而联想到自己正当壮年却闲差散冗无所事事,只能到寺庙中喝茶赏花,他借着眼前花色凄迷的牡丹为自己徒然流逝的青春送行。整首诗借牡丹起兴,表达诗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自己失意于仕途理想、虚度年华的隐曲之意。即便王拯辞官归老后,也常在赏花时发出“堪嗟雄剑气,都化野夫材”(《咏黄鸡冠》)的喟然长叹。
从王拯的咏花诗中可以看到,其诗中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仕途生涯的挫败与无奈。因此,他对自己的政治人生是充满失意与遗憾的,这也是他晚年厌宦思归日愈加深的原因之一。
三、思归与慕陶:传驿春花四牡归,黄香晚节共谁提
因为幼年时的经历,王拯对家乡和亲人有着无限的眷恋。他虽祖籍山阴,但生于桂林,自父母双亡后,又到柳州依其姐(刘氏姐)生活读书。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达他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当然,王拯的思归情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其姐的深厚亲情。他在好友陈鑅为己所绘的《媭砧课诵图》上作序,讲述了幼年时姐姐对他严格督课的细节,感恩之心溢于言表。但他二十岁后,因为求学在外,难与姐姐团聚;待进士及第做官后,他一度想迎姐姐到京城养老,却因姐姐老病无法成行,让他对姐姐充满愧疚之情。多年的羁宦京师,又屡屢让他生出去官还乡的想法。1864年,他因上疏弹劾侍郎董恂、薛焕等人“佥壬”(巧言谄媚,行为卑鄙),反被降三级调用。之后,他便自觉无用于世,告老还乡之意愈迫,在其咏花诗中也可见到这种愿望的流露。他的《子穆归平南再叠瓶梅诗韵》一诗表达了对彭昱尧归乡的羡慕之情:“春风有脚知何处,明日归帆天际青。”他想象友人得以归乡的轻快愉悦之感。王拯也曾遥想过自己归乡后的闲逸生活,如“何当归去海南春,与子褰裳访仙客”(《苏虚谷同年汝谦属题屠墉画山茶便面歌》)。虽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留有遗憾,但他最终达成了归乡隐居的愿望,赏花活动变得很频繁,咏花诗的创作也达到了高峰。他在《花朝后日王友苕纲招同子实及家芷庭恩祥春农栋朱蓉庵辂陈莘香鉴壶山看桃花遂集七星岩年来山下李花方盛桃花已不多矣》一诗中写到了归乡后的心情:“海岱归来信曲肱,玉壶招客买春行。”在王拯看来,以前从政的生涯就像是登上高山,会感到疲累,如今解职归老,可以乘兴而往,玉壶买春,赏花观景,身心得到了放松。可以说,家乡的风景疗愈了他多年客宦的疲惫和忧伤。
王拯辞官归乡后,所咏之花以菊花为最多。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十四首咏菊诗有十二首作于此期,且又有多首与陶渊明相关,可见他和许多文人士子一样,都希冀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隐逸范式中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为此,他思接千载,“穿越”时空,想象着自己在“庐山真见陶元亮,又索新诗带月题”(《庭中野菊花正开松孙又送白者一种叠前韵》)。诗中提到的“柴荆”“柴桑”“栗里”等地名,都与陶渊明的隐居相关。在王拯看来,只要自己也像陶渊明那样不被功名利禄所困,始终保持安贫乐道的精神,那么到处都是可隐居之所。
王拯的慕陶情结还体现于他在咏菊诗中充分诠释了由陶渊明建构的菊花文化之内蕴。一是他咏菊时会联想到“东篱”意象。陶渊明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使“东篱菊”或“篱菊”成为其回归田园的化身。王拯在其咏菊诗中,既赞叹友人“自有东篱伴”(《容庵同年春农太守各赠丛菊》)的生活风致,也表达自己归乡后“犹得东篱对樽酒”(《咏万寿菊即佛顶黄》)的乐陶情怀。二是王拯于咏菊诗中呈露自己对隐逸生活的追求。“隐逸者总是与远离世俗社会的形象相关,被视作是高洁傲世的化身。”(陈冬根《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陶渊明历来被视为隐逸之士的代表,而菊的某些品性契合了他那种隐逸品格。又因陶渊明之故,周敦颐明确指出菊是“花之隐逸者也”,因此许多文人在仕途生涯中萌生倦意想要退隐时,总会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引。三是在王拯的咏菊诗中屡次提到“晚节”一词,如“要留晚节看冰霰,问有芳心结暮迟”(《残菊》),“我已惨枝判寥落,黄香晚节共谁题”(《松孙见示黄泥塘看晚菊诗次韵》)等句。王拯借咏菊表露自己虽处于人生的暮年阶段,始终如陶渊明一样追求高尚的生命品质。此外,王拯在其咏菊诗中,也抒写一种超逸绝俗、旷达疏放的生命情怀,如“孤踪也复辞彭蠡”(《松孙邀同过丁秀才韬书院看菊次韵奉和》)表达了一种追求超然世外的生命境界,这是对陶渊明淡泊清静、悠然恬适的人生真趣的追步,也是王拯受到陶渊明名士风度的感染,在仿陶中表达对陶渊明高逸襟怀的崇尚之情。
王拯童年痛失双亲,为其刘氏姐抚养长大。在他的心目中,其姐替代了父母的角色,成为他亲情寄托的对象。因此,他長有所成,便时刻思报亲恩。但世事乖违,加之客宦京城,妻子早亡,使他陷入孤凄的处境中。亲情与归属感的需要引发他归乡的渴望,只有家乡能带给他安定与满足,让他直抒热爱家乡山水的胸臆。虽然暮年看花于明艳与浓郁的表达中,又多了几分寥落与萧瑟,但他以陶渊明作为追慕的对象,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内心的郁结,重新发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其咏花诗中反复出现的咏陶意象,便是他在爱陶与慕陶的过程中,不断确认着自己的志趣与品格。
清代学者叶燮说:“古今有才人之诗,有志士之诗。”(《密游集序》)他认为,才人之诗在于诗人通过“谐声状物”来传达自己的审美体验,而志士之诗则重在诗人“深古今身世之怀”。王拯的咏花诗便是将才人之诗与志士之诗合而为一。他在赏花的审美愉悦中,生出“人意傲如残岁菊,诗情浓似暮天霞”(《时将长至庭菊犹花松孙叠“叉”字韵》)的创作冲动,遂在这种“妍远诗情”中寄寓自己人生易逝的感慨、对国家的担忧,以及归乡隐逸的情怀。这无疑是王拯对传统咏物题材的创作继承,同时也是他心路历程的呈现与自我价值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