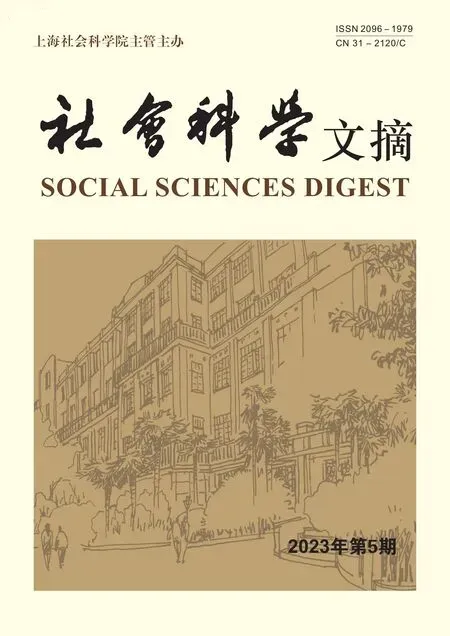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
——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文/高瑞泉
“直觉”是现代中国哲学家普遍关注的课题,20世纪出现过各种直觉论,乃至有西方汉学家认为,是否肯认直觉成为中西“思想规矩”的分野之一。如墨子刻曾经如此划分:中国哲学家认为“具有形上智慧者会以默然的直觉超过名言之域。这个看法与西方形上学的主流迥然不同。除了像Plotinus(205—270)或者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较例外的思想家以外,西方形上学很强调在名言之域中以‘理性’与‘观念的分析’去建立一些能经过批判而不受反驳的预设,而以为在超名言之域中以直觉或情感来追寻智慧是不可能的”。像许多哲学新兴趣是西方哲学的译介所触发的一样,现代直觉论的兴起多半与柏格森等欧洲哲学思想影响有关。然而,今天我们检视20世纪中国哲学直觉论的演化史,会发现体系建构的中国哲学家,对柏格森大多不再接引而是扬弃,他们主要承接儒释道传统,尤其是以对禅宗的“顿悟”之发挥为根据。而中国的实证主义者倾向否认禅宗“顿悟”说的方法论意义。如胡适说:“禅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顿悟,决不是多数人‘自悟悟他’的方法。”这说明现代直觉论与禅宗“顿悟”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作一番考察。
一
率先把“直觉”作为中国哲学主要特征和范畴来讨论并引发广泛注意的是梁漱溟。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糅合了王学、唯识论和柏格森思想等,又借助对儒学和佛典的诠释,对西方现代性展开批判。他强调直觉和工具理性的对立,即东西方文化的对立;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凸显直觉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何谓“直觉”?首先,梁漱溟断定:“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换言之,“仁”并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内在的德性;甚至就是本能、情感和直觉。不过“直觉”是无私的情感,其发生有自发性和直接性。其次,直觉是玄学的方法,本体是不可分析的,所以玄学不能如科学那样用分析方法进入,只能采用直观的方法。即人仅能借助直觉和实在直接同一。因为此故,直觉所得需要用中国哲学擅长之流动的概念来表达,而不能使用抽象概念或分析方法。再次,直觉所得并非知识,是连接主客体的纯粹经验。它虽非知识却有意蕴,涉及价值领域,因而有内生动力性。
梁漱溟的贡献是提示儒家经典包含丰富的直觉论资源,对中国哲学重直觉的特点,作出了有洞察力的发现。但是他对“直觉”的界定是含混和游移的,又把“直觉”等同于本能、冲动,且可以支配人生,离开了儒家理性主义传统。所以,他后来多次反省,改用“理性”来指称直觉。这一在“本能”“冲动”“非量”和“理性”之间徘徊的现象后面,可能有一些未曾明言的背景。他赞赏王门后学,而王学近禅,王门后学甚至被视为“狂禅”。1984年,笔者曾有机缘当面向梁漱溟先生请益。梁先生对前人视泰州学派中人为“狂禅”的评价颇不以为然。在笔者问到“直觉”的真意时,梁先生用“神悟”一词来回答;而且他坚持“人并不是一死就完的”,相信禅宗高僧确有《五灯会元》记录的种种“神通”。他晚年自称:“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所以,笔者以为,梁先生的直觉的“底子”是禅宗的“顿悟”。而“顿悟”又很难明言,因为进入了“心行路绝,言语道断”的境界。正如牟宗三所说,“假定照康德所了解的神秘主义讲,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中,有些是肯定我们对超绝世界可以有直觉”,神秘主义以为不能用分析方式说,但可以改换言诠方式,“此即是辩证的非分别说,这就好比禅宗所表示的方式一样”。
二
与梁漱溟类似,熊十力也是直觉论者。其力作《新唯识论》就是要证明,认识真实的存在只有依靠“反观自照的直觉”。其直觉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从形上学而言是心本论,从方法论而言是对分析和常识思维的批判。后者和他区分科学与玄学、理智与性智、俗谛与真谛、表诠与遮诠是相应的。“表诠”是用名言来表达的知识,而玄学乃“求表超物之理”,故需用“遮诠”,为玄学所倚重。由此熊氏赞美空宗的“破”,破而后立,“遮诠”可以为获得“悟”铺平道路。
如梁漱溟一般,熊十力也把直觉称作“神悟”:人们认识过程中存有创造性直觉,即在极短时间内洞见真理,它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仿佛不期而至的灵感。不过熊十力既拒绝神化它,也未曾将直觉与本能相联系,而是坚持只有通过深入反观才能获得直觉,属于理性思维形态,人类高级精神活动的结果。熊十力还仔细地辨别了“悟”之“顿”与“渐”,讨论了直觉与逻辑分析以及思辨的关系。在此问题上,熊十力对禅宗的“顿悟”既有吸收又有所保留:“后来宗门喜言顿悟,不独大小乘空有二派罕言之,即就《阿含》考察释迦氏的思想,便可见他注意解析与修养的工夫,那可轻言顿悟。如果要说‘顿’,除非一顿以前,经过许多渐悟。譬如春雨轰然一声,阳气之积以渐故也。”换言之,既有解析前的“悟”,又有解析后的“悟”,解析活动既与“悟”有所不同,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简言之,熊十力的“直觉/顿悟”本质上并不排斥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已经初步涉及“思辨后的直觉”和“直觉所得如何理智化”等问题。
围绕直觉之界定,为了区别玄学与科学,熊十力使用了一连串哲学概念,包括“明智”“证量”“证解”“神悟”等,用得更多的是“默识”和“体认”。就其反求本心而言,这两者既相通,又各有侧重:“默识”指非分析、非名言的途径所达到的形上境界,实际上就是本体自身的呈现;“体认”则强调其直接性和实践性。其实,“默识”和“体认”——善的直觉——更多地凸现为实践哲学的概念,由此使其直觉论超出了认知领域,表现为实践智慧,指向德性主体。由此我们可以说,熊十力的直觉理论是一种“良心论”。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ly)曾经分析过“良心论”的三种直觉论:理性的、感情的或知觉的直觉论者。按此分类,梁漱溟属于感情的直觉论者,而熊十力接近于理性的直觉论。但是,熊十力同时强调德性的实现需要经过修养,它随着主体的能动过程而发展。良知是呈现,“默识”与“实证”也就是良知呈现的过程。这开启了牟宗三关于“智的直觉”的讨论,是第一代新儒家留给后学的遗产。
三
梁、熊属于心学,心学近禅,重视禅宗是其来有自;冯友兰则属于理学,理学近道,道家另有直觉论传统。朱熹强调格物致知到最后可以到达“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莫不明”的境界,提示了向形上学飞跃的途径。但就其学思而言,冯友兰对“直觉”或“顿悟”,有一个从批评到袭用之过程。
冯友兰早年曾表示“不敢赞成”直觉说,认为“直觉”和“顿悟”并非哲学方法,后来发生了明显转变。在构筑其“新理学”体系时,冯友兰用逻辑分析(“正的方法”),从分析经验或事实命题中抽取出构造“新理学”的基本范畴,同时又强调“负的方法”,即道禅“破”之重要,认为完全的形上学必须是“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甚至认为“负的方法”是达到哲学顶点的保证。
“新理学”的骨干是以四组命题表示的观念(理、气、道体、大全),它们“完全是只拟对于经验作形式的释义”;但是冯友兰发现“严格地说,大全、宇宙,或大一,是不可言说底”,甚至是“不可思议底”。“形上学的正底方法,从讲形上学讲起,到结尾亦需承认,形上学可以说是不能讲。”这就引发出所谓“负的方法”。冯友兰以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运用这一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家和禅宗。道家求得道,其方法在“去知”。禅宗则认为第一义不可说,凡有所说,即非最“第一义”。但既然承认有第一义,就要寻找表达的方法,“所以知第一义所拟说者之知,不是普通所谓知识之知,而是禅宗所谓悟”。进一步考察表明,冯友兰在“悟”的解释上有深浅不同。他并不强调悟之瞬时性,而是详细分析禅宗为了教人明白不能以日常求知的方法去追求最高的真理,通过显示以理智分析的方式追求智慧必然失败,来引导人们如何反身向后,改变认识的方向,“禅宗人常形容悟‘如桶底子脱’。桶底子脱,则桶中所有之物,均一时脱出。 ……所以悟后所得底道,为‘不疑之道’”。
人们运用“负的方法”获得“无知之知”,又为“不疑之道”,表明推动人们改变求知方式的不是认识本身,而是对第一义的信仰和追求。因此,在冯友兰看来,获得“无知之知”,有助于人们走向“义境”,在“天地境界”中与万物浑然同体。换言之,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志向在于成圣,而“负的方法”断绝名言之路,自然会将人引向圣人的境界。
四
冯友兰说讲形上学要从“正的方法”开始,终于“负的方法”,缘起于禅宗之“第一义不可说”。这与金岳霖先生认为治形上学会遇到“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说”相似。20世纪中叶,在与金先生论学中,冯契认为欲回答“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说”,也须问“说不得的东西怎么‘得’”?转接冯友兰的问题:“第一义不可说”,即要追问“第一义如何得”?这成为冯契“智慧说”的中心问题。
何谓“智慧”?“中国古代讲‘圣智’,以‘智慧’译佛家的‘般若’,以及希腊人以哲学为‘爱智’等所含的意思,‘智慧’一语指一种哲理,即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所谓智慧,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insight),它与人性的自由发展内在联系着,所以这种洞见仿佛是人的理性本身所固有的。”当以对道的洞见insight解“智慧”时,insight本就有内在地考察、突然醒悟(顿悟)的意思,已蕴含着通达智慧需要思维过程的飞跃。对“智慧”的两种释义,表明冯契广义认识论所探索的,必定包含“顿悟”,又不停留于“悟”,而要将其系统地表达出来。这种基本的哲学风格,决定了冯契对禅宗的“顿悟”说的双重态度。
“顿悟”源自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冯契以为,禅宗的贡献是集中地突出了“顿悟”,且有强调主观能动性、承认认识过程中有飞跃、获得全面贯通性认识等三点优长。冯契对禅宗“顿悟”以及“顿悟”与“渐悟”关系论述的重视,还突出表现在“理性的直觉”概念中,因为它是“转识成智”的重要环节。哲学要求“穷通”,即要追求那个大全和究竟之道,就要从分别的知识经验,向会通天人、物我迈进,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实现认识的飞跃,冯契称之为“转识成智的飞跃”。冯契的“转识成智”由“辩证的综合”“理性的直觉”及“德性的亲证”三环节绾合而成,其中之关键是“理性的直觉”。因为“德性的亲证”依靠“体证”,而“辩证的综合”最后用一套哲学范畴(达名)来表达囊括万有、超越对待,类似大全、天道、第一义等“总名”,其实是“强为之名”,它非单纯“遮诠”,也非纯逻辑推演之所得;既是德性的表现,还要在生活中自证。在冯契看来,“直觉”普遍存在于认识活动中;是原始思维的孑遗;不仅禅宗,庄子和王夫之对之也颇有贡献。因此不主张对“顿悟”作神秘主义的解释,这是冯契区别于上述三家的重要之点。
五
禅宗之“顿悟”是以“成佛”的信仰为前提的,现代哲学家吸收禅宗的“顿悟”,是将其视为到达形上智慧的方法。这一点使得中西哲学的主潮形成方向性的差别。前文所述四位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分析哲学那样单纯地“拒斥形而上学”,这应该是他们对禅宗的“顿悟”有所取的原因之一。不过其间也有区别:梁漱溟自称是“佛家”;熊十力对灵魂不灭问题“其唯虚怀而默于不可知”,且对儒学教旨持有的信仰与宗教无异;冯友兰相信有“天地境界”,此境界中人自觉“是超生灭、超死生底”;与上述三位持有儒佛信仰不同,冯契是实践唯物论者。在其理论活动的起点就肯定“智慧的对象,我们称为‘道’”。“理性的直觉”之所得,即是直接把握大化洪流的客观实在感。在学缘上与冯契相近的是李泽厚。虽然李泽厚对其学说有“吃饭哲学”“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乃至“情本体”等概括,但依然可归入实践唯物论谱系。
李泽厚对禅宗的注意首在“不立语言文字”,而后引到“顿悟”和“由美启真”的“心灵哲学”和美学。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他对传统哲学的直觉包括禅宗的“顿悟”即有所论列。他将庄禅并举:“它们讲求的是创造的直观,亦即在感受中领悟到某种宇宙的规律。这种思维认识方式具有审美的特征,它是非概念非逻辑的启示。”李泽厚也注意到禅宗“顿悟”说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他们强调“顿悟”的个体性,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禅宗之“顿悟”是信仰的“悟”,而非一般的求知的“悟”。作为哲学方法的“直觉”,虽必有一终极的信念,但未必如宗教般一定是出世的信仰。禅宗的悟道——直觉,是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在感性世界中无所住心,即为超越。
李泽厚既没有讨论“顿悟”如何导向形上智慧,也没有讨论它如何与道德修持相结合,而是把“顿悟”引向审美。其“由美启真”路数,固然走向对感性世界的肯定;其直觉论更多地服从美学理论构建,因而在美学的领域颇有开展。这对人们领会传统的诗书画艺术和山水的“禅意”大有裨益,禅宗的“顿悟”说也因李泽厚的阐发而在现代中国美学中呈现出更为丰满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