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向以鲜:为什么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
邓苗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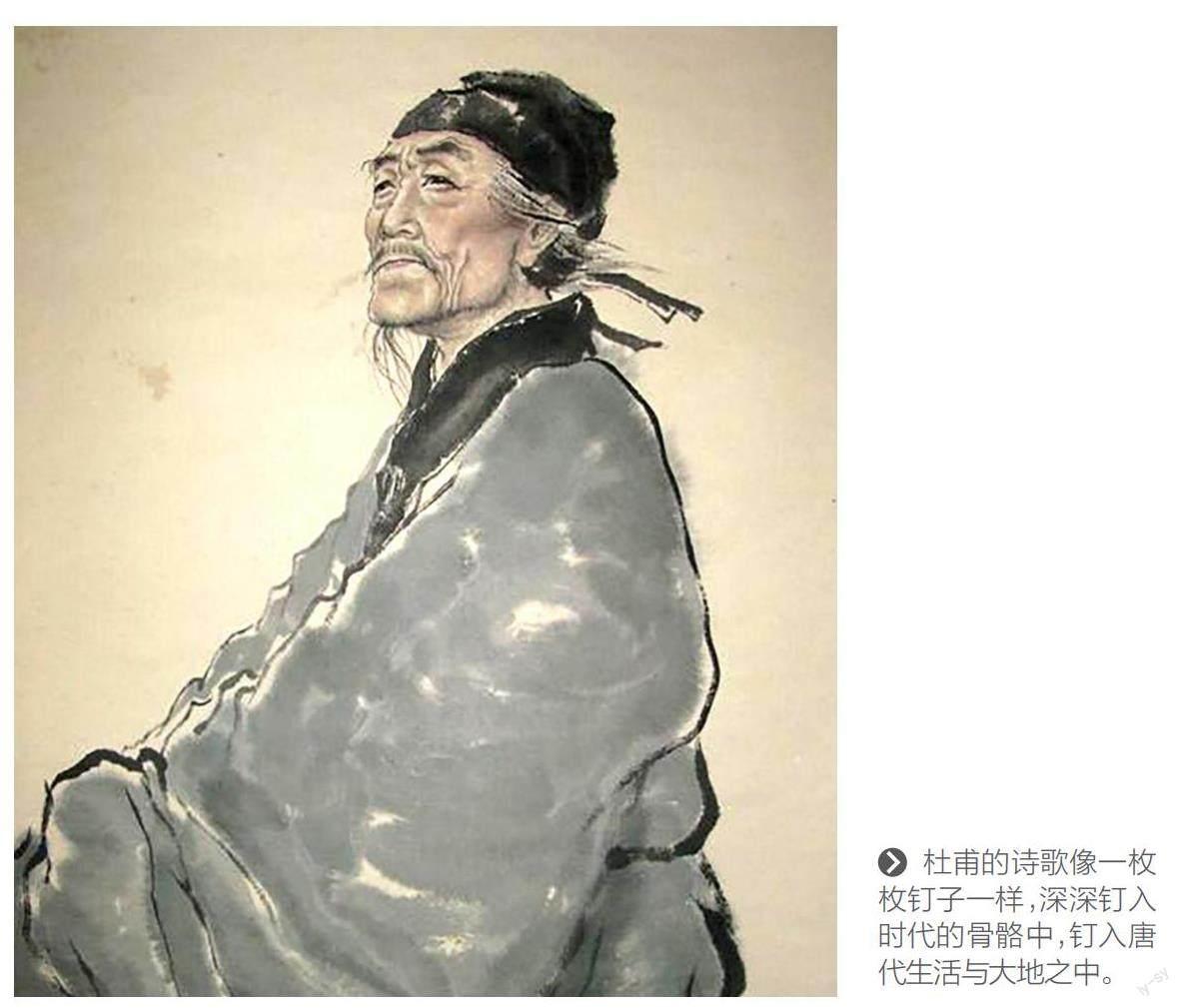
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在热映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诗人高适曾说:“只要诗在,长安就在。”盛唐风采在一首首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笔墨之间尽显山河壮阔、人间百态。诗歌为何在唐代达到顶峰?唐诗塑造了怎样的中国?群星闪耀的诗人之间有何联系?带着这些疑问,廉政瞭望·官察室专访诗人、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一窥唐诗风貌。
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
廉政瞭望·官察室:诗歌在唐代时达到了顶峰,创作规模和创作质量都可以说是无可比拟。您认为唐诗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方面?
向以鲜:唐诗繁荣原因,古往今来讨论的人很多,也找到了很多原因,比如唐代政治生态的开放与包容性,唐代与世界文化尤其是中亚、西亚乃至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唐代科考,在明经、进士之外,专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对于促进唐诗的繁荣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代统治者,尤其是盛唐时代的唐玄宗十分热爱诗歌,大诗人李白得以成为翰林供奉,即缘于其卓越的诗歌才华。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记载:“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严羽的意思是,宋诗之所以无法超越唐诗,原因在于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相对比较稳定,而宋代科考中的诗赋并不固定,时而考诗赋时而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这样一来,就不太利于刺激诗人的诗歌才华。
当然事物总是两面的:一方面,官方的支持大大刺激了人们诗歌的激情;另一方面,官方所支持的诗歌风格,产生出大量迎合时代口味的应试之作、颂圣之作、矫情之作。这样的诗风,对于真正的诗歌创作又是极其有害的。当然,礼部省试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两首佳作,比如大家熟知的祖咏《终南望余雪》就是一首省试之作:“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廉政瞭望·官察室:唐代的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对唐诗繁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除了这些外部原因,您认为还有哪些原因需要我们关注?
向以鲜:唐诗繁荣还有一个原因需要强调,即诗歌發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中国诗歌的历史,如果从有记载的第一首“南音”诗歌算起来,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那首诗歌,还和咱们巴蜀文化有着至深的关联。百余年前,也就是民国二年(1913年),蜀学巨擘谢无量写出惊世骇俗的《蜀学原始论》。谢无量在该文导言中断言“蜀有学先于中国”,并从儒学、道学、佛学、文艺等诸方面力证其是。论及文学时,谢无量指出:“文章惟蜀士独盛。有四始:一、南音,涂山氏创离骚所出。二、赋或曰赋始荀卿,然汉志录赋实首屈原,原所生即今巫山地。三、古文陈子昂复兴。四、词曲李白创。”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谢无量的说法或有可商量之处,但有些认识确有其合理性。谢无量所说的“南音,涂山氏创离骚所出”,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的理解,南音即南方的声音或音乐,还应包括南方的气息和温度、南方的节奏和韵律、南方的风土和腔调、南方的忧郁和抒情本质,这声音或音乐是南方诗歌早期代表《离骚》的源头。谢无量的说法,当出自南朝梁代文艺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的论说。刘勰曾提及好几段重要的远古诗歌,如葛天氏的牛尾八阕歌、黄帝的咸池歌、帝喾的六英歌、涂山氏的候人歌、夏王孔的破斧歌等。这些远古诗歌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唯一流传下来的是“南音”——最早见载于战国秦吕不韦《吕氏春秋》:“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它不仅是中国南方诗歌的初啼,是《离骚》的源头,也是《诗经》的源头。
有趣的是,这首中国最早的诗歌“南音”正好来自于巴蜀大地,而且还是由一位巴蜀大地的深情女子涂山氏所唱出来的:“候人兮猗!”用今天的话说:我在等我的人啊,唉!这四个字,带着原生的、永不向命运和时空屈服的勇气。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首诗歌仅有四个字,形式简单,让人想起了《诗经》。
向以鲜:是的,从这首“南音”诗也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诗歌,甚至还没有文字时代的口语诗歌,其基本形式就是四言诗,这是由汉语单音节的独特形式所决定的,后来在《诗经》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和固化。《诗经》基本上属于中原北方文化系统,以整饬的四言为主流。然后到了南方的《楚辞》,形式开始变得丰富复杂起来,尤其是独具南方气质的语助词“兮”的大量使用——我们还记得,这个字早在“南音”中就已出现——完全突破了四言的格局,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式汹涌而至。
但是,《楚辞》毕竟是地域文化极其强烈的一种诗歌形式,并不完全被辽阔的各地诗人所普遍接受。延续《诗经》传统的中原北方四言诗歌,到了汉代,由四言变成了五言,典型的代表就是《古诗十九首》和汉乐府。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汉魏时期热爱四言诗的大有人在,比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四言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写四言诗的人越来越少,诗歌的主流也开始由五言诗拓展至七言诗。
此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人们开始注重严格的音韵约束。以周颙、沈约等人为代表的诗人,提出了诗歌写作中的“四声八病”学说。柏梁体、宫体诗、乐府诗的花朵竞相绽放。可以说,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到了南北朝和隋朝,已为一个即将到来的诗歌巅峰时代做足了准备。建安风骨,魏晋风度,一大批诗人成为唐代偶像,如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庾信等。
可以说,唐诗的繁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目空一切的李白才会如此倾慕地写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也才会对庾信彻底服气:“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将灵魂安放于唐诗中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认为唐诗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对当时的人们、现在的人们乃至将来的人们有何意义?
向以鲜:唐诗中国的序幕刚一拉开,就展现了夺目的光彩。“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这是郑振铎先生当年写给“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一句颂词。为了表达由衷的赞美,郑西谛先生忽略了王勃的性别,称我们的诗人王勃为唐代东方的黎明女神。他或她的光芒虽然没有太阳神那么耀眼,却为一片不可方物的玫瑰色,那是只有天才才能享有的颜色。可能还有几分羞怯,掩不住的美与力量,已然展露出来。那景象,让我们想起王勃的另一位同时代诗人宋之问的诗句:“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一个新兴国家的诞生和强大,光靠些老成持重的文武大臣当然不行,如果只有这样一些人支撑着,那么,这个国家的天空将是暮气沉沉,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最终,必将走向衰落和灰暗。是的,要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国家,一定得有一群天才,一群才高八斗、目空天下的天才出现,这个国家才会是生机勃勃,充满想象力、创造力和吸引力的。
那么我们来看唐诗塑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唐诗中的中国,唐诗中的唐朝,正是在这样一群才华多得怎么用都用不完的天才手中,不断缔造、不断纵横出来的。由隋入唐,时代的车轮滚滚碾过,大唐的版图越扩越辽阔,天纵奇才的人也越来越多。你看看,好多的天才,那些灿烂的群星啊!王绩是天才,骆宾王是天才,卢照邻是天才,杨炯是天才。后来的李白、杜甫就不用说了。我们的王勃更是天才,就连他的两个哥哥王勔和王勮也都是天才。我们翻检一下初唐时代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会发现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全都是些早慧的天才。这些天才不约而同地出现和到来,似乎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要让他们的时代和国家,成为东方最夺目的圣地。
这样的诗中中国,这样的诗中唐朝,对于唐代,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当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我们文化自信的渊薮在哪儿?毫无疑问,必定来自以璀璨唐诗为代表的悠久文化传统。我曾在差不多十年前的一部赞美唐诗的诗集《唐诗弥撒曲》扉页上写下这样的题记:我们的灵魂无处安放,就让它安放于唐诗中吧!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也曾研究过宋代文学,有一种观点是“会通唐宋”,认为唐、宋两代的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唐诗对宋代的文学有怎样的影响?
向以鲜:宋代文学尤其是宋代诗(包括宋词),其实是唐诗发展的一种延续和变革。文学传统就是一条斩不断的河流。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孔子站在河畔,看见宁静的流水而发出感叹:生命如逝水,一刻也不停留。孔子要说的,不仅是生命,当然也包括历史、艺术和一切存在之物。
宋代诗人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比如人们经常谈及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以才学为诗”等等,都是宋人在诗歌方面的精进探索。我个人认为宋人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很多时候体现于词作的创作方面。宋词这种起源于唐代民间的诗歌新形式,到了宋代,长短句(词)成为宋代诗人抵抗唐代强悍诗歌波涛的有力武器。
总体上来说,宋代诗人在自我诗歌价值判断上,认为唐诗是无法超越的。南宋诗歌理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反倒是后来的一部分人们,觉得唐宋诗各有千秋,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指出:“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这个看法直接影响了钱钟书。他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唐诗天空群星闪耀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之前出了一本书《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您认可“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一观点吗?除了杜甫以外,您还推崇哪些诗人?
向以鲜:“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一观点,最早是由著名学者洪业先生提出来的,我认可这句话。杜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其使命的,他的使命就是要来为汉语诗歌写作制定标准。杜甫的标准,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形式上的苛求者。人们说,诗体至唐代始大备。这句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诗体至杜甫始大备。尤其是在排律和七律方面,杜甫就是古典汉语诗歌的天花板。杜甫是一个视诗歌形式如生命的诗人,一个诗歌形式的苛求者。杜甫对于诗歌形式近乎偏执的熱爱与追求,对于今天或未来汉语诗人的启示在于:自由诗无论多么自由,现代诗无论多么现代,诗人们都绝不能放弃诗歌在形式上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胎记”,那“胎记”就是节奏。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节奏,节奏,在任何时候都是要命的。
鲜活的创造力。杜甫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的就是一种鲜活的创造力,别人甚至包括自己,写过的绝对不写。众所周知,唐代诗人深受汉魏乐府影响,李白写了大量乐府诗题材,如《将进酒》《长干行》等。但是,在杜甫留下来的1400多首诗歌中,却没有一首旧题乐府诗作,反而是写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即事名篇”之作,如“三吏三别”等,从而开启了中唐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鲜活的品质对于诗歌来说太重要了!鲜活,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思想的鲜活,二是指语言的鲜活。杜甫善于从日常语言中提取诗歌的黄金,从古典传统中获取富有生命力的表达。
勇敢的批判精神。杜甫的诗歌像一枚枚钉子一样,深深钉入时代的骨骼中,钉入唐代生活与大地之中。杜甫始终是唐朝的批判者,比如,对待战争的态度,杜甫总的来说是反战的,尤其是对一些穷兵黩武的战争行为,杜甫持坚定的批判态度。我们从“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诗句中,能够明确听到杜甫批判的心声。即使是面对他十分热爱的唐玄宗,诗人也是勇于批判的——批判是诗人的权利,也是诗人的武器。
拓展母语的宽度和深度。杜甫对人世和大自然微妙变化的敏感性,如“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如“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和对汉语音乐之美的挚爱,如“思飘云物外,律中惊鬼神”,以及杜甫词语之丰赡,在唐代诗人中绝无仅有。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杜甫的诗歌,汉语的表达力将为之大大减色。
相形之下,现代汉语诗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还没有为丰富和提纯汉语的表达做出太多的贡献。
唐代大诗人太多,杜甫之外,我还喜欢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王之涣、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太多了,理由也多。唐诗的天空太耀眼了,随便指认一颗星辰,都可能让世人眼前一亮。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曾提到“一个诗人在他一生中,一定会和另一个诗人,尤其是历史上的某个诗人发生神秘的联系”,这是您的个人感悟。那么您认为在唐代诗人群体之间,互相发生联系、产生某种奇特效应的诗人有哪些?
向以鲜: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李白和杜甫了,两人年龄相差11岁却情同手足,同吃同睡,“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诗人闻一多是这样来表达两人相见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紧逼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此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有过相互的交往和影响,从旗亭画壁的故事中我们也知道,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等人交谊甚深,相互游赏和砥砺。
杜甫说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千秋也好万岁也罢,都太久了,生命多么短暂啊!还是读唐诗读杜诗吧,唐诗绝对可以抵消部分生命的幻灭感。我读得多了,便会对杜诗的口吻越来越熟悉。有时候,仅凭直觉我就可以对杜诗异文做出判断。比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部分版本将“白日”写作“白首”,我熟悉杜甫的口吻,我知道他会怎么说。杜甫在这儿绝对不会以“白首”去对“青春”,一定会以“白日放歌”去对“青春作伴”。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诗人杜甫,他有他的腔调,他有他特别喜欢的词语。“白日”和“青春”这四个字就是杜甫所喜欢的,与年龄没有关系,他的口吻具有顽强的生命感召力。或者可以说,新诗或现代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并没有鸿沟,不仅没有鸿沟,很多时候,古典诗歌本身就是现代诗歌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