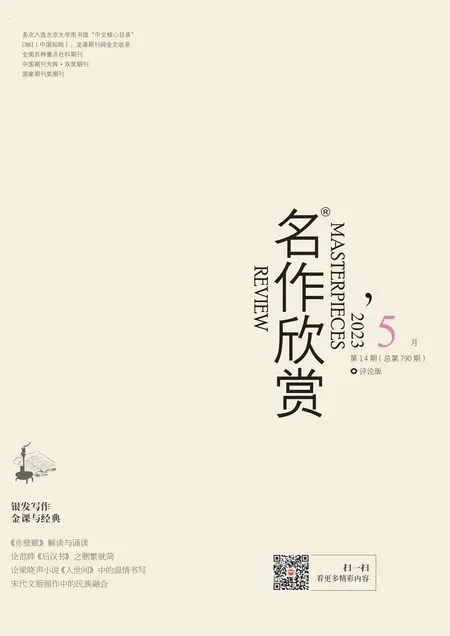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
⊙张伊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1189]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是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是波兰第五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同时,作家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在题为《温柔的讲述者》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托卡尔丘克揭露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冲击,并表示了担忧,此外,作家还称自己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对动物甚至是生活物件的热切关心与尊重,继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观:“我们周遭的景观也有生命,太阳、月亮和所有天体也有生命。整个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都有生命。”①基于此,作家决心为动物发声,为自然发声,由此,《糜骨之壤》应运而生。
《糜骨之壤》曾入选2019 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以及2020 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是一部披着保护动物的外衣探寻生命权利的佳作。作品讲述了一位奉行生物中心主义的老妇人为给动物复仇而接二连三杀人的犯罪悬疑故事。如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表面上看该作品探讨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的主题,实际上隐藏在这之下的还有作者对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探求,更确切地说,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命运的思考。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托卡尔丘克
单从“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的构词便可以明确了解到该理论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其所指涉的批评范围包含了生态主义批评及女性主义批评,具备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鲜明特点。早在1974 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coise d’ Eaobonne)便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首次使用“生态女性主义”(ecoféminisme)一词,将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并阐明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贬低女性与贬低土地之间的关系。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逐渐兴起并形成一股强势潮流,众多文学批评家及学者对这一批评理论进行了阐明与补充,如生态女性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女性主义理论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美国学者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无论各个批评家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有何种定义、观点如何,我们都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是建立在父权制社会的世界观之上的,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便是从人类对自然的奴役开始的,换言之,父权制社会的世界观使得女性处于社会中被统治、被虐待的边缘地位变得有理可循。
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对理论内容进行了扩展,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之一保利·默里(Pauli Murray)提出了“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概念,将“女性”的定义充分延展,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概念。加德对该理论的定义进行了如下表述:“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女性主义伦理,致力于研究相互关联的概念结构,这些结构认可了对一系列群体的压迫:女性、有色人种、动物、GLBT 等非异性恋人群以及自然界”②。换言之,“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女性”已然“成为一种文化隐喻,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或尚处于边缘地位,饱受男性/人类/资产阶级/西方/白人等占统治地位的压迫者欺辱的弱势群体”③,这种理论的扩展使得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糜骨之壤》成为可能。
托卡尔丘克与生态女性主义更是有着不解之缘,作者不仅关注自然周围的一切生命,还在作品中刻画动物与女性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在文学领域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的创新性表达。在题为《温柔的讲述者》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托卡尔丘克认为:“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问题、感情,甚至与人类一 样的社会生活”,“动物是神秘、智慧和有自我意识的生物,精神的联系和深刻的相似性一直将我们与它们联结在一起”④,作家要做的就是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事物,并在作品中有所映射。托卡尔丘克本人个性鲜明,读大学时她没有遵从父母的意愿选择文学专业,而是就读心理学专业,她认为女性应该具备一定的反叛精神,要勇于挑战传统与强权压迫。作家笔下的女性是独立有主见的,可以掌握自己命运走向,“特别是,她让默默无闻的女人成为活生生的个体”⑤。
托卡尔丘克虽不是旗帜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却在文学世界中为自然发声,为女性助威。《糜骨之壤》更是深刻体现托卡尔丘克关于自然和女性生存等思想的力作。作品中出现的系列人物形象是托卡尔丘克的有意安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家的灵魂寄居在老妇人杜舍依科身上,她是素食主义者,她与迪迦从不吃肉;她资助基金会维护动物权利,她展开一场精心策划的动物复仇行动;托卡尔丘克生活在波兰的西南部,与捷克接壤,她的目之所及,便是杜舍依科女士的向往之地。
二、《糜骨之壤》形象塑造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治理既需要男性的理性掌控,又需要女性的感性参与,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存在,而是要和平共生。《糜骨之壤》中的女性形象鲜活感性而又勇敢独立,托卡尔丘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杜舍依科女士、女作家“灰女士”,甚至是出现篇幅仅一章的董事长妻子的形象也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与观点,部分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男性也与女性一样,命途多舛,美好却脆弱。而与此相对的警察局局长、富商福南特沙克、董事长,则是在人类社会中扮演酷爱猎杀动物、漠视弱势群体的男性“肉食者”形象。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看,托卡尔丘克希望通过人物间的观念冲突与命运走向,揭露男性对动物的残忍杀害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与剥削,表达女性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文明的向往。
(一)身为“肉食者”的男性形象
“肉食者”一词来自于《左传·庄公十年》,原意为吃肉的人,后引申为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接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强调将人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尺度。“肉食者”不仅掠夺自然、大肆猎杀动物,而且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视为“动物”,毫无顾忌地对其进行压榨与剥削,而“肉食者”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批评的父权制社会下的产物。
《糜骨之壤》中与杜舍依科女士处于对立面的男性形象多为“肉食者”,他们热爱打猎,从野兔、野鸡、野猪到鹿,都是他们的战利品,并且面对杜舍依科的阻拦与驱赶,这些猎人嬉笑着表示:“我们这完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⑥。这无疑是对猎杀动物这一行为的曲解与美化。
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德娜·席瓦(Vandana Shiva)把父权家长制式的开发视为“畸形开发”(maldevelopment):“基于性别的从属和父权家长制虽然是最古老的压迫,但是通过开发,它们带上了新的甚至更具暴力的形式”⑦。《糜骨之壤》中村镇里代代传承的狩猎传统,实际上隐喻了父权制文化,更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对自然的掠夺。作为打猎队伍的领队人物,沙沙将狩猎看作人类与大自然亲近的一种方式,并且怒斥不遵守狩猎规则的偷猎之人,宣称我们是“守护自然之美,守护秩序与和谐的人”⑧。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社会框架下的狩猎行为是遵循一定道德信仰的有选择性的活动,并不是对动物的肆意捕杀与残害,而是在守护自然的平衡,维护自然秩序与万物和谐。按照这个理论逻辑,猎人便是自然的守护者,狩猎塔也被称为“讲道坛”,甚至道貌岸然的猎人们还时常在这个猎人之家讨论狩猎文化、道德、纪律与安全等问题。然而他们不会思考他们单方面制定的狩猎规则是否有正义可言,不会考虑动物将如何在人类迫害中艰难求生,更不会关注到动物其实也有生存的权利。
“肉食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的掠夺上,除此之外,生态女性主义者还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弱势人群的贬抑与掌控。“肉食者”的一贯思维定式是将自然界的所有生物视作他们的所有物,他们以一种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姿态拥有对自己所有物的处置权,而所有物的生存状况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小说中的“肉食者”们通过对居民的控制,全方位控制这片土地,使得这些“肉食者”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游刃有余,并且对野生动物的猎杀行为变得更加猖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加肆意。普瓦斯科维什的花岗岩资源丰富,富商福南特沙克计划重启采石场,进一步开发石料资源,对此同为“肉食者”的董事长认为人们应该心怀敬意,这无疑是在为这一不符合自然规律行为的背书,要知道采石场的重新启动是建立在对资源的肆意掠夺以及居民居住环境的占用基础之上。“肉食者”丝毫不尊重自然规律,威胁到了村镇的自然生态环境。无形的等级制度使得底层民众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对自然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与剥削,而这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心的问题。
伪善的“肉食者”站在狩猎塔上,就仿佛站在了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的道德制高点,尽揽对其他生物的生杀大权,将自然完全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社会弱势群体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些弱小无力的“动物”。而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人类社会中的男性与女性均处于自然环境之中,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达到生态平衡,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才会出现。
(二)“任人鱼肉”的弱势群体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常用以比喻生杀大权掌握在别人手里,自己处在被宰割的地位,可简化为“任人鱼肉”。生态女性主义者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Adams)提出缺席指涉理论,将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视为“肉”,并揭示出“肉食者”的食肉行为与欺压弱势群体之间的联系。《糜骨之壤》中的自然、动物、女性人物及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中的“肉”,即处于“任人鱼肉”的状态。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且女性比男性更加接近自然。杜舍依科女士是真正热爱自然的人,她常年居住在波兰与捷克交界处的一片山林中,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幽静而又偏僻。杜舍依科每天都会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进行日常散步巡视,像一只孤独的母狼一样巡察着自己的领地。她对森林中动物的习性甚至数量尤为熟悉,她为小动物起名字,为不幸死去的动物们修建墓地。她聆听大地深处的秘密,与森林低声私语,亦是在与林间精灵进行对话沟通。她认为人类与动物都是这片家园上的主人,大家生而平等,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正如托卡尔丘克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与大自然联系会让人感悟到最深刻的生命本质,自然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我,我们都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女作家卡罗尔·亚当斯认为,食肉行为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⑨“肉”的原本指涉是活体动物,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下,“肉”的指涉通常被加工处理过的肉质食品所替代,被宰杀、分尸的活体动物被替换为食物,此时的动物就变成了缺席指涉。⑩《糜骨之壤》中董事长的妻子亲眼看到丈夫将猎杀的鹿分尸放入冰箱,鹿血洇染了整个桌板,此时指涉在场,她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作为食物的鹿肉,而是每次走到冰箱附近就会想到里面有动物尸块,甚至因此推断是自己冷酷无情的丈夫杀了富商福南特沙克,这实际上揭露了猎杀、屠宰动物的残忍。“肉食者”食肉的暴行是对动物的压榨与杀戮,是对动物生存权利的野蛮剥夺,当指涉暴露于阳光之下,放到读者面前,在指涉在场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无法抑制住对“任人鱼肉”的动物生命消亡的深切怜悯与同情。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不仅是动物被“肉”化,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肉”化了,二者均处于相似的被支配地位,均在男权社会中受到了不公对待。而除了肉体暴力外,女性往往还会受到其他来自精神方面的暴力,包括年龄、道德、习俗等。杜舍依科是一位社会边缘人物,是可以瞬间隐入人群的存在感极低的老妇人,是外人眼中有些神经质的“疯老太婆”,她的名字经常会被人错喊成“杜申科”,就连作案工具都是十分符合世人眼中老妇人形象的塑料袋。杜舍依科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然而校方与教育委员会却不合理地迫使她提前退休;当她亲自到警察局报案时,接待人满脸不耐烦与鄙夷,甚至有时恶语相向,最终不了了之。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与动物的遭遇是相似的,动物的命运是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而女性所遭受的往往还有一些无形的暴力。
卡罗尔·亚当斯认为,缺席指涉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动物与女性,这一理论适用于一切受到这种压迫的弱势群体。当邻居大脚被鹿骨卡住喉咙意外身亡后,大脚的伐木工朋友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葬礼,朋友们站在门口迎接沙沙,但后者“没有看任何人,而是快速地走进了屋”⑪。当警察到访时,所有人都站在外面迎接,而警察却显示出了傲慢与形式化,他们“一句话没说就走进屋里消失了”⑫。底层民众的低眉顺眼与权贵阶层的傲慢无礼形成了鲜明对比。富商福南特沙克想要重启采石场,可是他并没有考虑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该何去何从。牙医就住在采石场附近,对此他借用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讽刺了权贵阶层:“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⑬父权制社会下的权贵阶级把人分为“有用之人”与“无用之人”,像牙医这样“无用”的底层民众就应该被果断抛弃,因为他们并不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与效益的增加,而这一点也是被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
三、《糜骨之壤》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创新表达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均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衍生而来,这两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需要采用“雌雄同体”和“两性对话”两种方式。所谓“雌雄同体”,并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的雌性与雄性共用一个个体,而是指男性与女性气质的一种融合,即同一个个体中的男性力量与女性力量能够和谐共生,平等合作,达到融洽。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为,任何一个拥有纯粹男性力量或者纯粹女性力量的个体都不能进行创作。⑭所谓“两性对话”就是指在两性共存的条件下探讨女性价值的实现与发展,彻底解放女性,实现男女完全平等,创建一个平等互助、关系融洽的共同体。
从实践层面来看,“雌雄同体”的模式无疑更加抽象,仿佛无法实现,然而《糜骨之壤》却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大胆尝试。杜舍依科女士有一位名为迪迦的忘年交,迪迦很瘦弱,虽然身为男性,却拥有如女性般小小的手掌、软软的头发,像一朵娇小的雪钟花,杜舍依科眼中的迪迦“一直是个小男孩,甚至像一个小女孩”⑮。迪迦的到来于杜舍依科而言便是找到了救赎,二者的命运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一,两人的身体都很虚弱:迪迦有很严重的过敏症,能吃的东西很少,而杜舍依科女士的状况更差,她饱受病痛折磨。其二,两人都是社会边缘人物:迪迦被周围人排挤,在警察局裁员的第一批名单中迪迦的名字赫然在列,杜舍依科女士因年龄的增长而被学校无情辞退,被迫提前退休,教育委员会也对她的诉求无动于衷,正如她一次次被警察忽视一样。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迪迦与杜舍依科女士都位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之列,而托卡尔丘克将一位男性刻画得如此善良聪慧、感性敏感而又脆弱,便是对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统治者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于生态女性主义“雌雄同体”模式的一次创新性的大胆尝试。
托卡尔丘克还吸收了生态主义理论的部分观点,并在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了创新性的表达。生态批评家布依尔(Lawrence Buell)提出了“环境启示录”(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ism)的概念,指出启示录是对未来生态环境的一种灾难预警,也是一种报复性话语:“那些特殊要素——天空、空气、土地、风和水——将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⑯。杜舍依科女士十分热爱占星术,时常计算星盘运势,认为星象与人的品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她推测出警察局局长权势滔天、以权谋私,是一个混迹于阴暗、邪恶交易中的神秘莫测的人。将土星与富商福南特沙克联系起来,因为土星的星变会造就卑鄙下流、阴郁无耻之人。除此之外,她还热衷于利用占星学来预测生命的消亡,警察局局长“上升星座的主宰星在白羊座,白羊座是负责管理头部的,因此暴力(火星)与他的头部有着直接的关系”⑰。果然,调查结果显示局长坠井而亡,死于头部撞击。作为“反派”的杜舍依科女士希望人类能够警惕自然的报复,希望权贵阶级能够认识到弱势群体对不公的反抗,她自称是动物复仇的工具,人为地制造了几起符合星象学规律的凶杀案,在她看来,这是她代表动物向人类发出的警告,也是自然向现代文明社会发出的灾难预警。
杜舍依科自称是“无用的人”,像这样“无用的人”在社会中绝不是个例,他们无权无势,偏安一隅,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做着于别人而言无足轻重的工作,是社会中的小透明,不被社会所承认。这样的群体该何去何从?对此杜舍依科女士提出了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难道飞鸟就没有活着的权利?在仓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呢?还有黄蜂、雄蜂、野草和玫瑰,它们都没有权利活着吗?谁有这样的智慧去评判孰优孰劣?”⑱最终她感叹:“人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①9
四、结语
《糜骨之壤》中杜舍依科女士无疑是一位孤勇者,她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公,在求助无门后,她坚决而勇敢地拿起利刃刺向了权贵阶层。这不仅是动物向人类的复仇,也是自然向人类社会的复仇,更是一切处于压迫状态的弱小他者对父权制社会做出的宣战与反抗。
众所周知,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要改变男权制社会下的二元对立关系,不能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大融合,最终实现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糜骨之壤》中的杜舍依科一次次无言的疼痛与哭泣,一次次高声的呐喊与争执,都是在向持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社会发起挑战,想要冲破迂腐的父权社会所制定的一切条条框框,然而她所信奉的生物中心主义无疑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她关心动物比关心人还多,甚至为了动物变成了一名加害之人,这样的选择是令人悲哀的,也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①④⑤⑥⑧⑪⑫⑬⑮⑰⑱⑲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何娟、孙伟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版,第321 页,第321 页,第303 页,第71 页,第265 页,第43 页,第44 页,第154 页,第75 页,第75 页,第273 页,第273 页。
② 〔美〕格里塔·加德,韦清琦:《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探讨梅卡人捕鲸诉求中的伦理语境及内容》,《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第128页。
③⑨⑩ 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页,第76页,第72—73页。
⑦ 〔印〕范德娜·席瓦:《作为西方父权家长制的新工程的开发》,铃木昭彦译,《环境思想的谱系2环境思想和社会》,小原秀雄监修,转引自〔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冯雷、李欣荣、尤维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⑭ 〔英〕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第二卷)》,王义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版,第578页。
⑯ 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