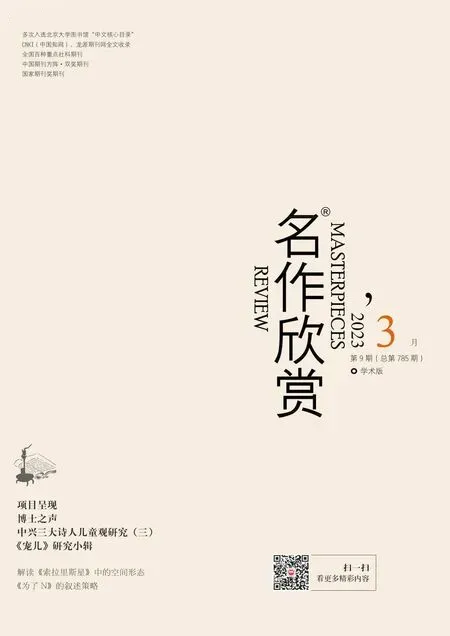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及变异
⊙饶梦琪[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 330008]
现代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西方文学发展演变中出现的具有前卫特征的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与传统文学和艺术相背离。意识流文学由现代主义衍生而出,是现代主义文学一条重要的分支线。严格意义上说,意识流小说并不能称为是文学流派,而是一种创作手法,即以自由联想等为线索直接且自然地展现人物意识流的叙事手法。作为一种叙事技巧,意识流的特点是叙述者不参与感知和意识的交集。意识流以主观感受为现实的中心,把意识看作是变化无常、殊难预测、杂乱无序的,只能由叙事人来照实记录的东西。
一、意识流小说的特点
意识流小说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根据情节的次序和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来构成连贯的线性结构,而是根据与人类思想意识运作的联系构造和交织故事。情节之间的安排和联系一般不受时间、空间、逻辑或因果关系的限制,可以随意跳跃、变化和穿插和重叠。意识流小说主要采用 “内心分析”“内心独白”“时空蒙太奇”“诗化和音乐化”等手法进行文本创作。例如美国意识流文学代表作家福克纳,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对意识流的运用驾轻就熟,显示出极大的文学艺术创作技巧。在第二章大儿子昆丁的自述中,可窥见其对“内心独白”和“时空蒙太奇”的灵活运用。昆丁作为家中长子,父母亲对其期望极高,最终昆丁也不负众望,考上了哈佛大学。但昆丁时常感到孤独,身处校园内却经常回忆童年家里的事情,即使是在和别人的对话中也能联想到过去,不断地进行时空转换,因时因地更换回忆的对象。在对昆丁的描写中,很大部分是他自说自话的内心独白,就连准备自杀的前几个小时,昆丁都还在自言自语地准备自己的后事。这些细节都充分展示出意识流塑造人物的特点和魅力,把读者引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发展
意识流最早是由日本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催生了私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和郁达夫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狂人日记》中对狂人意识的描述是一种精确而现实的方法,与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理论十分吻合。它没有从传统小说的人物感受出发,将内心情感外化为生动的意象,而是看作是“疯子”的内心独白。在意识流中时间的逻辑秩序被弄散打乱,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片混沌,全都杂糅交织在一起,相互渗透,不依靠情节而完全由“疯子”的自我联想来构造整个作品。“‘狂人’所联想到的内容互相纠缠,却又毫无边际,这些自由联想就像放射出去的一条条射线,这种结构小说的方法在意识流小说中是一个常见的特征。”虽然不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但其叙事视角逐渐从外部转向对内部心理活动的描述,这对中国传统小说来说已经是一大突破。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刘呐鸥和施蛰存结合传统现实主义和新兴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创作出一系列具有现代气息的中国本土小说。刘呐鸥的《都市风景》采用蒙太奇、人物心理分析等写作手法,以中国本土城市上海为背景,将大都市的丰富多彩和光怪陆离展现在读者面前,体现了上海这一城市的“现代性”和写作方式的“现代性”。
意识流小说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求新变异之风,而中国文学迎来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转换。在这次转换中,意识流首先“流”到中国,成功并且合时宜地实践于当代文学艺术之中。
王蒙是第一个在其作品中广泛使用意识流技巧的人。他的小说被称作是“集束手榴弹”,《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是王蒙从1979年到1980年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而成,且质量尚优。他在作品中采用了时间和空间相互交错切换的手法,将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错位,形成一种意识的随机流动,将西方意识流手法和文学结合使用起来。
《春之声》是王蒙对“意识流”技法的一种典型运用。这部小说描述了岳之峰在1980年的春节前夜回家探亲时,在一辆密闭的罐车里待了两个多小时的精神历程。故事的开头,主角岳之峰在车上随着车不断“颤抖”和“摇摆”时,脑子里对家乡的美好记忆油然而生;然后是车轮的声音,从这引发了一系列的联想:雪、手工打铁、三角风铃等。岳之峰的思维不断穿梭在画面和情感中,穿梭在事物和人之间,穿梭在潜意识和自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这部作品出版之后,许多读者觉得这种无聊的东西不值得阅读,不可称为书籍,更罔论去尝试了解和接受它。但实际上,王蒙《春之声》在精神空间中意识流的运用极其优秀。所谓的“时空”观念,其实是一种崭新的、混乱的、倒置的时空观念。他的空间和时间构成是错位、颠倒的,而他的精神空间和空间状态即是他的创作空间及状态: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漫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80年春节前夕我们主人公的心灵。①
时空错乱、错综复杂,这都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混乱”。身体和心理上的时间是互相冲突的,角色的理性和荒谬的行为是严重分离和解构的。时代的矛盾、体制的冲突、角色的冲突、心理的冲突,使得整部小说在矛盾的旋涡里摇摆。
岳之峰在闷罐车中两个钟头的精神历程,他的联想、时间和空间的倒置,有别于一般的时空观念,将空间时间化,使闷罐车这个小小的时空实体,成为一个“过去——未来、国内——国外”的大时空体。王蒙善于观察时空,善于把握时空,善于将不同的时空相结合,使其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节点。因此《春之声》的内容,尽管是岳之峰在列车上的两个小时,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从上到下,跨越了五千年,跨越了数千公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融合了丰富的人生场景、社会经验和历史变迁。在时空的倒置与交错中,彼此渗透,使得人物的视觉、记忆、向往等三种形象互相交错、重叠,呈现了人物的奇异人生和多元的社会现象。《春之声》开辟了人类心灵的认知领域,也突破了以往以一条主线为线索、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展故事的传统叙事方式。
在后来的意识流大讨论中,宗璞、李陀、王安忆、莫言等一大批作者,都对意识流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意识流的研究上。他们从“心理时间”这一新的观念出发,把人们的内心世界纳入小说的框架之中。如宗璞的长篇小说《我是谁》,更为注重人物的精神活动,描写人们的情感、心理,折射出当时人们的复杂心理和不断变化的精神状况。空间与时间的跳跃与意识的流动,既是对新鲜感的追求,也是对作品具体表现的加深。他们的努力与创新,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也改变了小说的整体观念。“西方的意识流文学以‘心理时间’来描绘人类的心灵世界,而新时代的作者则逐步将创作的视野转向人类的主观世界,以‘内心视角’去探寻人物的意识。”
此后,意识流小说逐步向寻找民族文化心理的方向发展,即“寻根文学”。李陀的《七奶奶》中的七奶奶本质上看好似继承了鲁迅《风波》中九斤老太的衣钵,她对旧事物的怀念和新事物的恐惧支配着她的整个内心世界,这正是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大惰性。莫言的《欢乐》描写,一位多次高考失利的乡村青年齐文栋在自杀之前的几小时里,他的意识流表现出个人与社会、个人意识与文化意识的剧烈碰撞,以及传统与社会习俗对人类造成的巨大、无形的恐怖压力。王蒙后期创作的《活动变人形》是一部以封建思想、伦理为基础的都市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经历,它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为背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心态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抨击。王蒙曾指出:“意识流小说从自我意识的挖掘发展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根,无疑是走向深入和成熟的重要一步。”②
三、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变异
意识流小说是在西方世界诞生的,因此它代入的是西方的文化与环境。然而,在传入中国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却可以说是对西方意识流的一种异化与扬弃。作家们在借鉴、吸收西方意识流的文学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既不放弃传统,又将意识流引入作品中。
首先是其内容与主题思想的体现。西方意识流主要通过描写人们的精神空虚、沮丧、偏执的病态与歇斯底里来刻画人物、抨击时弊。而中国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在表达对现实和历史的不满和批判时却显得十分理想主义,力图表达内在的乐观与豁达。比如,莫言的《欢乐》以审美的眼光放大所有的丑陋,读者看到的是欢乐中的痛苦;然而,从审丑的角度来看,读者所能看到的,却是一种滑稽的欢乐。视角的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莫言在批判传统社会恶习的同时,也关注对希望和理想的憧憬和热切盼望。
其次,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以潜意识为核心,具有“泛性欲”的特征。而中国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则往往在探究人类的心理活动的同时,又展现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体现了对现实和人生际遇的热切关注。在“意识”这一方面中国作家们就显得更理性。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多头叙事的视角,立体地描写了淮北小村庄几个家庭的命运和生存状况,特别是对人物涝渣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这一线索,对我们民族以“仁义”为核心代代相传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儒家的“仁义”精神包涵了善良、忠厚、团结、反抗等优良品质,但也包涵了顺从命运、愚昧、封建迷信等文化弊端。
最后,西方的意识流文学注重将人物主观感受到的“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主张淡化对情节的描写,反对如介绍人物的身世、背景、环境,抑或是评头论足的传统小说写法,要求作者“退出小说”。而中国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则更能观察到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内心活动,但又没有完全抛弃情节,在作品中展开小说的发展脉络时总是相应地埋伏着线索,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依旧鲜活,使人的精神与现实相结合。比如王蒙的《春之声》,看似平淡的故事,晦涩枯燥的情节,其实也有迹可循。在岳子峰乘一辆闷罐车这条明线索里,也内含着暖春到来、冬天已去的暗线索在其中。因此,尽管《春之声》的读者会感觉部分情节十分模糊,但通篇看下来最终对整个故事还是能了解清楚。就像王蒙所说:
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而是一种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
四、结语
美国批评家罗伯特·汉弗莱在20世纪50年代总结西方意识流小说时说:“意识流小说已经汇入小说的主流之中。”这一结论用来描绘我国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发展走势也十分贴切。现如今我国的意识流小说潮流已经衰落,并逐渐汇入其他类型小说的主流之中。那意识流小说在今后有没有重卷浪、重涌潮的可能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学流派都不会永久占据文坛,它都有一个从兴起到高潮到衰落的过程,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来得快,涨得猛,落得也快,是否能重掀浪潮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意识流作为一种技巧表现世界和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否具有永久的价值和生命力。令人欣慰的是在国内,意识流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描写和挖掘人的心灵世界的艺术手段已经被归入了“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阶段。
意识流的实验并广泛应用,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达内涵,增强了其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拓宽了文学的美学理念和发展之路,使得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为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王蒙:《夜的眼及其他》,上海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② 王蒙:《王蒙选集(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