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宇澄《繁花》的“双线”叙事策略
尹晓琳 张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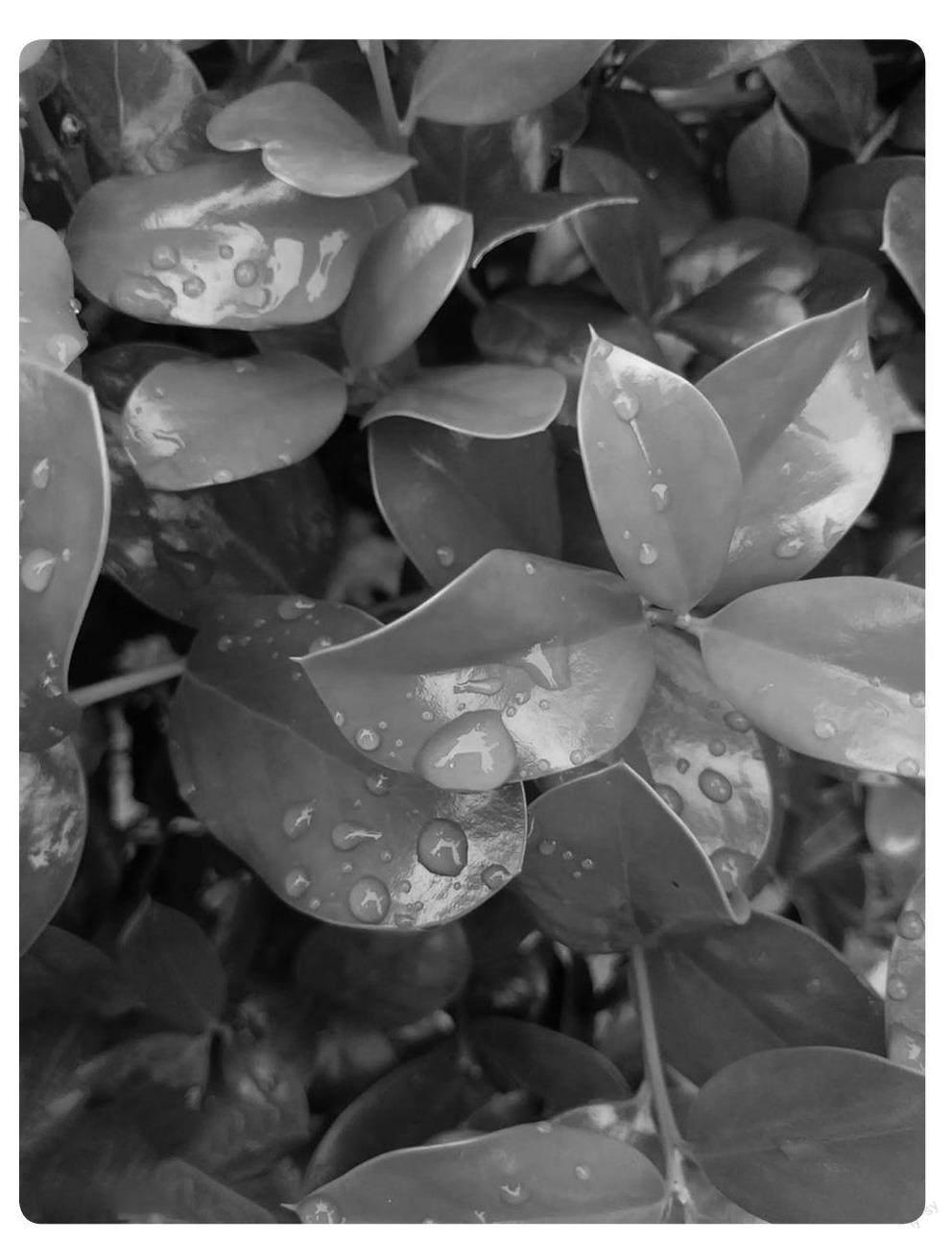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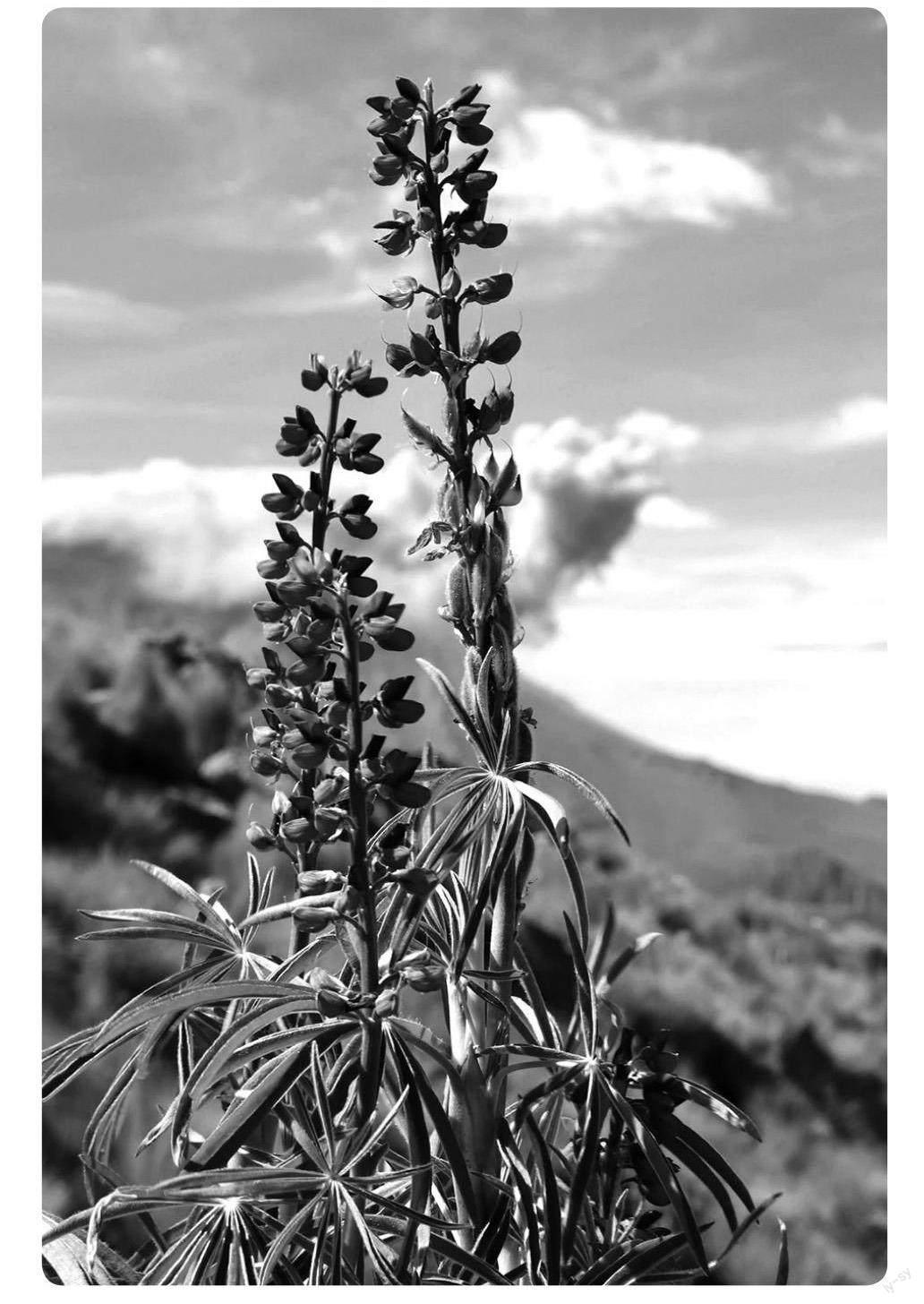
上海作家金宇澄在其小说《繁花》中以和缓平实的叙述展现了上海城市风情,营造出馥郁的市井气息。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双线并置的叙事结构,记录跨越四十年的沪上市井生活,将繁杂的日常片段穿针引线般串联起来,看似琐碎,但又相互勾连、遥相呼应。《繁花》采用了文本与图像互动的形式,不仅充斥着具体可感的地标书写,还在相应章节插入作者亲手绘制的地图作补充说明,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小说继承了《海上花列传》以来吴语写作、聚焦小人物的市井叙事的海派文学传统,使整个故事中既有大量的沪方言,同时也兼顾了非上海读者的阅读习惯,且经作者的多次修改文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良沪语。另外,小说还承传古代话本小说的语言特色,将沪方言与雅致的文言结合,使古朴典雅的话本语言成为小说的叙述语言。
一、叙事时间:“过去”与“现在”的双线并置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认为:“作品的价值依赖于作品的结构。”《繁花》存在两条清晰可见的时间线,小说的单数章节表现的叙事时间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呈现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样态;偶数章节的叙事时间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展现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上海市民的生活琐细。读者通过对单、偶章节的交错跳跃式阅读,产生一种别具一格的阅读体验。
“过去的故事”还保留着老上海的繁华与雅致。作者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在《繁花》中,作者细致地描写了上海的城市建筑、街道地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真实地名和标志性建筑,如霞飞路、淮海路、“华外”集邮店、大自鸣钟、国泰电影院等,使读者在阅读时被深深带入。记忆中老上海的弄堂景观、洋房景致、工人新村、本埠版图……这些城市建筑与地标记录着上海人珍贵而质朴的旧时生活日常,已成为上海街头一种独特的文化,对上海人性格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厚影响。即使是在物质贫瘠的年代,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爱好的追求。少年时期的阿宝和蓓蒂喜欢收集邮票,哥伦比亚美女票、法国皇后丝网印刷票是蓓蒂的心头好,阿宝则喜爱植物、花卉两类主题的常规票。淑婉是电影迷,召集男男女女一同到自己家跳舞、听唱片,男生模仿劳伦斯·奥利佛、钱拉·菲利浦,女生则烫奥黛丽·赫本头,修和她一样的眉毛,一同相约到国泰影院看时兴的电影;姝华则热爱读诗、抄诗。他们用独有的小市民智慧研究出时髦的衣着打扮,用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从贫瘠的土壤中吸收养分。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世俗生活里常见的日常风物,体现出他对物质的写实追求以及对过往生活情调与韵味的怀念。而“现在的故事”描写重心转移至无穷无尽的饭局,室内的“宴饮”场面成为日常。例如,李李的“至真园”饭店、“夜东京”饭店、“绿云”茶坊、“唐韵”二楼等,曾经的里弄、教堂、电影院渐渐淡出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范畴,相反酒吧、迪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沪上传统文化受到西方经济的冲击消散不再。饭局似乎成为反映世间百态的名利场和都市男女钩心斗角的角斗场。
王晓明认为,“一切形式的背后都有非形式的原因,作家建构艺术结构的基本图型,往往正是来自他感知人生的独特方式”(《“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通览整部作品,作者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市民的生活的描绘主要聚焦在家庭变故、个人情感、生活追求等方面,使读者跟随人物的脚步穿过城市的街头巷尾尽览整个上海的景观,在对历史的回顾中透露出对过往的怀恋与感叹;而在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中则更多地表现出情欲权力交织的空洞的生活状态,无穷无尽的饭局传达出人物生存的焦虑。曾经的精神家园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物质工厂,两幅鲜明的时代城市生活图景隐含着作者对城市精神的担忧。
二、叙事空间:文本与图像的双线互动
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要认识一个城市,人们必须在他的街道上行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值得关注的是,真实的地标书写在《繁花》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与张爱玲、王安忆对一个突出的地标进行大篇幅描写的方式不同,金宇澄主要通过人物的行动轨迹使电影院、商店等各种各样的地点蔓延开来,逐渐形成一幅立体化的地图。
细致入微的地图书写主要体现在《繁花》的单数章节,具体来看,《壹章》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以方位名词为主导交代出茂名路沪生家、皋兰路阿宝家和沪西大自鸣钟小毛家的情况,第四部分还延伸至阿宝祖父所在的思南路洋房。后面的單数章节以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位主人公家的地点构成上海地图的三个核心坐标,叙述内容也通过三位主人公的往来活动展开。作品以文字的形式将空间和方位精细化和准确化,唤醒了读者对上海的记忆,儿时生活的街道、历史的变迁、过去的时代重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这种精确的地图描写对于非上海本地读者来说,上海的建筑和自然风貌、人物所生活的日常区域在想象中生发,描写的细节越生动则越亲切可感,使读者离作品描述的故事和人物更近一步。
同时,作者绘制了二十张插图,按内容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是作者手绘的行政区划示意图,分别为二十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的卢湾区地图、南京西路以北地图、沪西地图和上海中心城区简图。第二类是老上海地标建筑图,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院、锦江饭店的街廊、长乐路与瑞金路街角,记录着四十年的变迁。第三类是老上海人的居住空间示意图,小毛、银凤所住的大自鸣钟理发店属于上海典型的老式弄堂,还有因其实际户数被上海人称为“两万户”的工人新村。第四类是对书中出现的物品描摹,有放在旧货商店寄售的钢琴,小毛自己加工的开瓶器,曹杨工人新村的马桶板等。第五类是人物速写,有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码头边穿着华服的日本女人。这些插图有力地展现了文字难以表达的内容,让每一位读者通过图像直观认识和体察上海的人情风物,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性。
三、叙事语言:改良沪语与话本语言的双线运用
从清末的《海上花列传》开始,沪语小说由来已久;然而,随着文学风向的变化和普通话的普及推广,沪语小说逐渐式微。许多上海评论家担忧,沪语小说的消失不单是文学体式的消失,更是上海传统文化的消失。金宇澄自觉接续吴语写作与话本写作的传统,秉持着“保留地域韵味,谋求非上海读者”的创作理念,用心打磨小说语言,使小说中人物对话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改良沪语,而叙述语言则呈现为古朴典雅的话本语言形态,体现出作家创作在语言表达上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上海话作为上海市区的方言有着七百多年的历史,自开埠以来,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让上海话影响越来越大。《繁花》最开始是在“弄堂网”上完成的,最初的版本为地道的上海方言。为了扩大非本土读者的阅读接受范围,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繁花》单行本并未采用纯正沪语,金宇澄多次修改文稿,删减修改沪语用词,甚至专门用普通话改写一稿。“《繁花》借鉴说书人的叙述方式,糅合沪语与普通话,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以语感的地域书写呈现出新异的叙述空间。这种书写聚焦于市井,既体现食与色的本性,又暗含抓取人生体验的欲求,更成为建构的镜像,实现共情与审美的多重阐述空间。”(高博涵《语感、市井与碎片化传奇—〈繁花〉的三重阅读空间》)《繁花》中的沪语改良,不是浮于表面的形式技巧,而意在表现上海城市的精神内核与上海市民的性格气质。
最初的网络版本中充斥着相当多味道浓郁的上海方言,如“好伐”“阿拉”“侬”等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市民口语,如果不是本地的读者,就很容易造成阅读的滞留和误解。金宇澄在保留上海话的基本韵味上,去掉了一些不好理解的口头语,如将“弗响”“勿响”改为“不响”,将许多地道的沪语语调浓缩为具有方言意味的词语“事体”。方言小说的创作历来有之,但能自成一体创造出独特文学语言的作品凤毛麟角。小说中改良沪语的运用,让习惯了普通话表达的读者在阅读时感到别有一番风味,同时有助于外部读者了解上海文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宛在目前,展现出上海魅力独具的市井风情。“沪语与普通话的对照写作使作者金宇澄获得了双语双方言的多重文化语言视角。”(刘进才《俗话雅说、沪语改良与声音呈现—金宇澄〈繁花〉的文本阅读与语言考察》)
除了小说中人物对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良沪语,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别具一格。金宇澄并没有拘泥于现代汉语中主谓宾的句式结构,而是承传古代话本小说的语言特色,融合古代散文游记的独特风味,将沪语方言与雅致的文言结合,形成了古朴典雅的话本语言。例如,书中第二章描写自然景色的语句:“江南晓寒,迷蒙细雨,湿云四集……小舸载酒,一水皆香,水路宽狭变幻,波粼茫茫……”這些描写,形式整齐,韵味别致,颇有古代散文游记的神韵。同时,小说在描写生活风物时,也常使用四字文言句式,如“呢绒旗袍,闪面花缎,四开纺绸,平头罗纺,竖点纀绸,颜色素静”。这些四字句式不仅能够将事物描写得当,生动可感,同时也有助于地方文化和市井风情的展现,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上海市民精明干练、含蓄委婉的性格。
金宇澄在叙事时间上采用“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双线并置,叙事空间上运用文本与图像双线互动的形式书写上海市民生活的本来面貌,展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社会历史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变迁,建构了一部鲜活的“当代上海生活图景”。《繁花》以沪语写作、半白半文的话本形式继承了海派文学的传统,文白夹杂,雅俗共赏,颇具复古性和先锋性。可以说,《繁花》运用出色的叙事策略,凭借其独特的文学性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性,成为海派文学中一部不可跨越的作品,为今后海派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