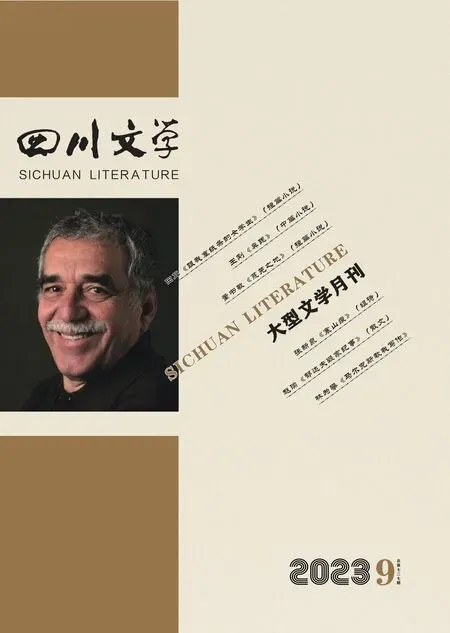长翅膀的树
□文/巴文燕
天麻麻亮,衮草寺就摸索着起来,穿上藏青色薄棉袄,取过挂在床头的烟杆,斜插进后腰,挪着步子往外走。屋里的家什只见大致轮廓,衮草寺的动作缓慢,生怕碰到什么,发出动静。拉开木栓,打开门,晨光闪耀,温润翠绿的气息,似整夜都待在门外,此刻见着人,争先恐后将他包围。
任何一个窄小的缝隙都填满了。
如过去的每一天,衮草寺停下脚,闭上眼睛,尽量拉直身子,关节处发出欢快的嘎吱声,像溪水撞击着卵石。他站在门口,体会清风、田野、稻穗溢出的混合气息;清新的空气滑过脸颊、指间,凉凉的,软软的。每一个出门的清晨,都是衮草寺最舒适的时光,屋子里有火塘、有家人,还有他的重孙衮月亮,但他还是喜欢走出屋去,在寨子里转转,在田间地头走走,跟早起的乡邻扯几句闲话,然后,无一例外,抬脚往后山走。
好几年了,只要没什么事儿(确实没什么事儿),滚草寺每天早上都要去那儿待上一阵子。
天还没大亮,路边高耸的晒谷架上,挂满黄灿灿的稻穗,一蓬蓬,一堆堆,像扁而平的黄金屋,蜿蜒在小路两旁,挨过每家每户的门扉、瓦檐。衮草寺嗅着浓浓的稻香,感觉那坚实有力的味道,此刻有了光照的作用,嘟嘟囊囊的,洒他身上,又悉数滚落地上。
他反剪双手,走在石头和泥土混杂的小径上。
乌隧特有的晒谷架上,修剪整齐的稻穗,像漫溢的金光,垂挂在衮草寺行走的半空。
他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哪儿都行,何时回来并不重要。
曲曲弯弯,上上下下,哪里有块撅起的鱼鳞石、鹅卵石,哪里有根歪斜的青杠枝、花椒树,哪里的马兰草、毛蕨、苜蓿长得最茂盛,哪段台阶有几级,有一块青石有些松动,衮草寺清楚得很,闭着眼都能走。不过,他还是微眯眼睛,盯着脚下的路面。九月收谷子前,他非要和春生去看打谷斗放哪里,不小心在田坎上摔了一跤,幸好没有摔断骨头,要不然就不是躺一个星期了。想想都后怕,衮草寺想起秋妹,硬是在床上躺了三年,他不嫌麻烦不嫌脏,为了安慰她,天天给她说,几十年了都是你照抚我,还不能伺候伺候你?
秋妹一辈子是个勤快人,咋受得了天天躺在床上嘛,苦哦。
想到秋妹,衮草寺的鼻子有点痒有点堵,他伸出硬邦的手指擤了擤,一点点清鼻涕,顺手擦在路边的柴胡叶上。路边的柴胡,茂盛得很,一堆一堆,从脚边延展到远处,长得高的都快齐腰了。饿饭那几年,他经常和秋妹一起打柴胡,和韭菜一起煮,放几滴猪油,再加上热气腾腾的红薯,日子照样过。只要有人,有手,哪里不是人间的滋味。最近些年,城里人好东西吃亮了,又开始寻摸着吃起这些野菜来,饭店里价格昂贵。大孙子衮秋生在县城工作,少回,每次来,都让春生媳妇帮忙,采上几大把带回去,说是送人情,比送烟送酒还稀罕。
乌隧在娘娘山的半山腰上,有公路在山下绕行,远远望去,寨上连绵的木屋若隐若现,高大茂盛的树木密布其间,仿佛乌隧寨是它们的孩子,精心围拢、呵护着。如果注意看,会发现寨子后面,略显平缓的斜坡上,有一大片愈加密集、浓重的林子,那就是衮草寺每天要去的地方。
他的爷爷,爷爷的爷爷,以及他的爹妈,还有秋妹,都在那里。
衮草寺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他就要和他们团聚了。每每想起,还有几分雀跃。
衮草寺九十二岁了。以前,是一年比一年脚步迟缓,自从摔了那一跤,他感觉是身子骨一天比一天沉。夜里,他常常梦见秋妹,有一回,秋妹就站在他的床头,和他说了好久的话,还打趣他“你耐烦心好得很,硬是舍不得走”。言语间是他熟悉的嗔笑。年轻的时候,秋妹就是那样跟他说话的。在梦里他还问秋妹,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走快点。秋妹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一大袋刚刚收下来的粮食,狠狠砸在他身上,一惊,从梦中醒来,重孙衮月亮正不管不顾地趴他身上,“祖爷祖爷,起床了,起床了。”
他纸片下的薄骨都要散了,皱巴巴地收紧,幸好春生及时把月亮抱起,否则真够他呛的。衮春生抬起巴掌就要打儿子的屁股,嘴里训斥,“给你说好多遍了,不要去闹祖爷,硬是不听硬是不听。”衮草寺半撑起腰杆,伸手阻拦,说:“月亮崽还小,没得事。”春生赶忙过来扶他,一边说:“您老别惯着他,都上一年级了。”
祖爷让重孙把他的烟杆拿过来,月亮崽聪明得很,答应得脆生生的,人已经像猎枪打出的子弹,射到床尾,祖爷两尺长的烟杆挂在床头。见儿子还是不知轻重,春生又作势要打,衮草寺的手在空中划拉一下,月亮崽赶紧把烟杆递给祖爷,说:“我去给你拿烟叶。”说着跳开往柜子那边去。衮草寺伸手到枕头下面,说:“不用不用,这里还有。”
衮草寺一想到他的重孙衮月亮,脸上就会像平静的江面,扔进一块光滑的玉石,荡起的肉纹久久不散。他去后山,不仅是要看自己那棵树,还要看月亮崽的那棵树。其实,月亮崽的那棵树和月亮崽一样,五岁了,比他的小腿还要粗壮,不用管它,也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很快,就会长得像秋生、春生的树一样壮实、笔直。春生虽然不爱说话,当初在外面找了媳妇也不吭声,月亮崽也是在外省生的,但还好,没忘祖,生的那天就给家里打了电话,当天,他这个祖爷就种下了一棵树。
什么事都不是事,都可以忽略,可这树,却是万万不能不种的。
走到林中,衮草寺转了两圈儿,摸摸这棵,看看那棵,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最后,走到自己那棵树下,弯身坐下。衮草寺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掏出烟丝,装满银制的烟锅。那拇指大小的烟锅,已经发黑,亮铮铮的,在林间的灰光下像蛰伏的天牛。林子就是林子,和别处是不一样的,再没有比待在这里,更让衮草寺踏实的了。
稻穗黏稠的味道远去,此刻尽是蓊郁青翠的绿色,长长短短,硬硬软软,排着队往老人的鼻孔里钻。除了时远时近的虫鸣、风过,衮草寺最喜欢的就是听鸟叫,它们跟树一样,挥动羽翅,发出各种声响,有脆生生的,有瓮声瓮气的,有唱一声歇半天的,还有斜斜地刺破空气的;嗓音有银针那般细,也有蒲团一样圆润。
鸟的声音很高,但始终在天空之下。
衮草寺眯缝着山峦般的眼睑,咬着白瓷的烟嘴,看着眼前茂密的林子,十几棵树后,就看不清楚了,远处隐喻在灰色的薄雾里。他侧过头来,伸手摸索树干遒劲的树皮,龟壳般坚硬、粗糙,如同深海大鱼的巨大鳞片。时间停滞下来,它们匍匐在这棵比腰还粗的杉树上,任它笔直地冲上天空。这是它们的杰作,由此,它们可以和这位老人一起,在静谧中体会这时间的魔幻。
也就是半袋烟的工夫,秋妹就出现了。
她清清爽爽的模样,坐在衮草寺对面,中间隔着一小段缓坡,他们的脚如果伸直,脚尖就能碰到。不过,衮草寺的脚伸直有点难度,而秋妹也不会那样坐,她都是蜷着腿坐,双腿往一边倾,十指交叉,护在膝上。秋妹身后是棵银杏,叶子黄透了,落下了大半,在周围铺成一张褐黄色的鳞状软垫,秋妹坐在上面,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跟他初见时一模一样。他忍不住问:“秋妹,你咋活回去了。”秋妹就答:“就是活回去了。”脸上似乎还有得意的神情。
“给你说个事儿。”
“啥事你说嘛。”
“昨天,秋生回家了。”
“哎哟这小子,难得回一次家。”
“就是喽。”
“他回家你该高兴。”
“我是高兴。”衮草寺嗫嚅道。
“什么事儿你说嘛。”
衮草寺下定决心似的,说:“他给我说,县里搞什么改革,领导干部要带头,说以后我们乌隧不能直接把人埋在山上了。”
“我们没有埋,我们只是种了一棵树,你看。”秋妹还没理解到他的心情,抬头仰望娑婆如汪洋的枝叶,继续说:“你看这林子多漂亮啊!没有这些树哪里来的乌隧嘛。这不还是我刚嫁到乌隧时,你给我说的么?”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不行,他说必须遭火烧。还说什么以前那一套都是迷信。哼,我当时就想捶他。”
秋妹担忧起来:“那烧了是不是你回不来了?”
“乌隧以前有个人,哦,就是衮火旺家舅,在外面做活路出意外,被烧死的,骨头都找不到,他们家人还是种了一棵树。那棵树就一直长不好,一直长不好,没几年就死了。”
“那怎么办?”秋妹紧张起来。又说:“这个衮秋生哦,早晓得不让他读那么多书了,读个大学出来进了政府,就不晓得自己姓哪样了。”
“他也是没办法。”
衮秋生是在“嗞嗞——”的电器打磨声中醒来的,拿过手机看,七点半,起来洗漱,做了面条,发现爷爷床上没人,问春生,爷呢?春生关掉锯木电器,也不抬头,手指灵活地扒拉开锯木面,渐渐显出一个凹槽,嘴里说:“后山。”衮小树疑惑:“上后山干什么?”脑子里浮现出爷弯成半弧的单薄,“他能行吗?到后山得走上些时间。”
“以前嘛,一个星期上去一次,自他腿摔了好了后,就天天去,没什么能拦得住他。”
不用问,秋生也知道爷为什么要去后山,想起昨天晚饭给爷说的话,心再次揪起。衮秋生把面碗放在堆满工具的桌上,“你吃了吧,我去看看。”
衮春生抬起头来,问:“你晓得路吗?”
衮秋生瞪他一眼,转身走了。
乌隧距县城八十余公里,虽然绕山绕水,柏油路却修得齐整,中间还有一段高速路,驾车回来也就一个多小时,但秋生却很少回,不是他不想,是他工作太忙。这次,要不是这件事儿,他寻得个充分的理由,算是出差,顺道还要走走附近几个村镇,摸摸底,他还是回不来。昨天下午到,原本打算早上起来就走,可没看到爷,加上春生说他去了后山,他心里很不踏实,无论如何也要跟爷告个别,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大学毕业后,衮秋生埋头考了三年,考上县上的公务员,当时在乌隧他是第一个,乡邻敲锣打鼓来祝贺,可算是光耀门楣。十几年来,他凭着谦逊、温良的性格,暗自发力,在没有什么关系和臂膀的情况下,走到今天,成为县里的一名副科级干部——民政局副局长,其中的苦涩和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比春生大七岁,春生大学毕业时,当哥的让弟也考公务员,说有他的帮助,春生会轻松许多。但春生不愿意,一个人跑广东打工。三年前,父亲去世,春生回来,还带回老婆儿子。办完丧事,衮家紧接着给春生办婚事,才算踏实了。
秋生也不是没有争取过,乌隧寨的丧葬风俗,按现在的理念来说,其实很环保。乌隧人自古爱树崇拜树,树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祖先。最能体现这一观念的,就是将生死与树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从多久以前传下来的规矩,乌隧人出生时,父母会为其种下一棵树;待到离开,便以此树为材料,制棺深埋,不堆坟,不立碑,再在其上种下一棵树。如此循环往复,在乌隧,活着的和死去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树,属于自己的树。国家禁止砍伐林木后,扼制了乱砍滥伐,但是除了乌隧,其他不是树葬的乡镇村寨,家人去世也去砍一棵树,出现了浑水摸鱼的乱伐现象,长此以往,会形成管理漏洞。而且,各地都火化,如果乌隧例外,别的村寨估计也就找到了借口,工作不好开展。在讨论的过程中,衮秋生是乌隧人,不好过多提出自己的异议,按他的理解,丧葬改革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虽然最后争取到允许树葬,也允许砍树,但必须火化,秋生的心里还是不好受,他知道这对乌隧意味着什么,对他的爷意味着什么。
“我倒不怕烧,死了嘛,早晚一团气,就怕成了一堆灰,还要哪样棺材嘛,直接洒在娘娘山上得了。”
“那不行,还得埋,不然我去哪里找你。”秋妹说。
衮草寺吐出一口烟说,“不砍树,慢慢地也不用种树了,咱们乌隧千百年来的规矩,怕是要破喽。”
秋妹伸出手来拉衮草寺。自从秋妹走后,这还是从未有过的。衮草寺经常梦见秋妹,经常在后山和秋妹聊天,但两个人总是隔着一定的距离。好多次,衮草寺想去抱秋妹,一抱一个空,秋妹就笑他。此刻见秋妹主动伸手来,衮草寺赶紧回应,噫,还真抓住了,实实在在,暖暖和和,就是感觉手变大了,虽然秋妹是一双劳作的手,但摸起来总还是秀气的。
“爷,你咋睡着了。”
衮草寺的耳边突然响起孙子秋生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哪有秋妹的影子,孙子勾着腰,拉着他的手。老人意识到什么,有点羞赧,大声说:“呀,我咋个睡着了。”说着欲起身,可身子坐久了,不听使唤,衰草和落叶窸窸窣窣地叫唤,竭力拽住老人瘦削的屁股。秋生赶紧伸手搂住爷的腰际,将爷整个抱起来,老人这才把身子站直。
“爷,这都要入冬了,你坐在这里湿气重得很,你咋睡得着。”孙子搀着爷风一样扁平的身子,“我们回家吧。”
“嗯,回家,回家。”衮草寺侧过头去看了一眼枫树,又扫了几眼周围静默、林立的树,树叶像鸟的翅膀,在空中挥动。衮秋生顺着他的目光,也游走了一遍。一老一少,一高一低,这才缓步往林子外走去。
爷孙俩到家时,春生媳妇在厨房洗刚刚摘下来的青菜,衮月亮坐在门槛上,一边咬一根辣条,一边冲着一辆电动玩具车,呜呜叫唤。两条人形影子,盖住他上半身,孩子立即跳起来,嘴里嚷嚷:“祖爷你去哪儿了,都不叫上我。”祖爷枯枝般细长的五指,摩挲月亮崽的头,三角形的脸上,露出海绵似的笑容,缺了一半的牙床溜出来,算是回答。
大伯问:“作业写完了?”
月亮崽大声答:“早就写完了,昨天我在教室就写完了。”
“不错不错。”衮秋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侄子,“收起。”正好春生媳妇出来,湿漉漉的手赶忙在围裙上乱抹一气,把钱挡回去,“谢谢伯伯,我们钱够用。”
“一点心意,给月亮崽买件羽绒服,天气跟到就要冷了。”
春生媳妇说:“他有羽绒服,还有棉衣,您快收起。”
“那给爷买营养品。”
“您昨天那一车还不晓得要吃好久呢。”
昨天衮秋生回来,吃的喝的穿的装了一后备箱,春生还怪他,说他做古琴挣不少,根本用不着他买这么些,还掏出五千块钱给兄长,说是侄子上高三辛苦,拿去买些好吃的,被衮秋生坚辞。春生三年前从广东回来,不仅带回媳妇和儿子,还带回一门制作古琴的技艺,这让衮秋生很是意外,如果不是春生,他根本不知道穷乡僻壤的乌隧,还有制作古琴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爷衮草寺还说,这下好了,都有了去处。
虽然是深秋,南方的阳光仍旧很充足,白光从云层后面溢出来,照得乌隧亮晃晃的,家门口的坝子蒸腾着热气。
衮草寺坐在门口晒太阳。
不大一会儿工夫,春生媳妇就给老人端来一碗面,汤多面少,一枚白花花金灿灿的鸡蛋,侧卧碗边,绿油油的碎葱花点缀其上,香油拉扯出几道润泽,看着都流口水。春生媳妇想得周到,摆个小方桌在爷面前。秋生叹春生媳妇手巧,主动去厨房取了自己那一碗。堆尖了,两个鸡蛋,油辣椒必不可少。衮秋生说我咋吃得了这么多?春生媳妇说你等下要走,路上别饿着,多吃点。
衮秋生只能一边吃一边点头。
春生呢?衮秋生趁着嘴巴的间隙问。
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旁边有个寨子有个老房子要拆,上百年了,他骑起摩托车就去了。
哦,那我就不等他了,吃完面我就得回了。
别等了,收老木花时间,不晓得哪时能回。
制作古琴需要老木。
乌隧地处西南腹地,林木茂盛,祖祖辈辈用木建房,如今,好多地方搞移民搬迁,老房要拆;不搬迁的,再建房基本改用泥砖。在乌隧,时不时地下会冒出几截木头来,有些成了阴沉木,而有些,则是制作古琴上好的老木材料。秋生问过他兄弟,他是跟谁学的这门手艺?春生没细说,只说他师傅传奇,做的琴卖价极高,却没有固定的住所,四海为家的那种。秋生就说,那把你师傅叫来住,咱们这里适合养老,春生也没言语。
秋生在爷枕下,塞了两千块钱。
那时临近中午,衮草寺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子蜷成三折,阳光见缝插针,灌满全身,窸窸窣窣地滚动,像在给他做按摩。老人感觉弓起的背脊,像一块春天的稻田,支棱起细碎的翅膀。
衮草寺掏出烟丝,往烟锅里放。
秋生过来坐他旁边,帮他放烟丝,又给他点燃。
衮草寺将山峦收拢,双肘撑膝盖处,烟杆架在他窝成椭圆形的五指上,感觉到热气快到嘴巴处,就深深啄一口,两颊凹进牙床。
衮月亮站在旁边呆呆看着,问祖爷:“祖爷,好吃吗?”
衮草寺懒得睁开眼睛,说:“好吃,你要不要咂一口。”说着把烟杆作势递过去,把月亮崽逗得咯咯笑,像有人挠他的痒痒肉似的。
秋生看时间差不多了,说:“爷,我该走了。”
衮草寺点点头说:“嗯。”
“爷,你莫怪我。”秋生突然有点想哭。
衮草寺侧过头来,说:“我怪你啥子哦,没事没事,我会考虑的。”想想又说,“不过,你得让乌隧人都同意才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晓得的。”
“我晓得的,爷。”
“嗯。”衮草寺继续眯起眼睛,咂他的烟,晒他的太阳。
衮月亮拿根树枝,举在嘴边,学祖爷的样子,夸张地咂巴嘴。
春生媳妇过来一把扯过去,作势要打月亮崽。月亮崽瞬间就跑一边去了。春生媳妇也是吓吓他,回头对大伯说,“要不吃了午饭再走,我已经在做了。”秋生说:“跟镇上约好还有事情要谈,走了。”春生媳妇想起昨天摘的一堆野菜,转身拿了追过去。
接近中午,衮秋生刚开完一个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县委办电话,让他过去一下。秋生放下手中的工作,也就五分钟,就到了隔壁楼县委办。还没进办公室,就看见爷坐在靠门的沙发上,他一惊,快走两步,奔到爷面前,“呀,爷,你咋在这儿,好久来的?咋不给我说一声。”转过头,发现局长也在,还有县委办的一位副主任。局长说他爷到了一个多小时了,衮秋生有会所以这会儿才通知他。县委办副主任接着告诉衮副局长,说他爷是来反映树葬的事,说树葬是乌隧千百年来的习俗,虽然火化不影响树葬,但牵一动十,有可能会让子孙后代不再有种树的习惯,那就可惜了。
“我给你爷说了,”办公室副主任戴着眼镜,脸上堆着笑说,“种树的事情国家会管,让他不要担心,可是你爷就是想不明白。”
衮草寺窝成一团坐在沙发上,眼神虚挂,茶几上白色纸杯里的茶水,早已冰凉。一向隐忍的衮秋生,面朝那个主任说:“是你想不明白还是我爷想不明白?”对方一愣,往上堆起的肉纹松弛下来。“对于乌隧人来说,一堆灰,洒哪儿都一样,即便埋在地下,也不必浪费要去砍一棵树,长此以往,乌隧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文化,有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说着往局长方向看过去,“我专门就这个情况写了报告递交给局里、县里,不瞒您说,我还递交到了州里,但是,至今我没收到任何答复。”局长摸摸鼻子,又抻了抻衣襟。“你们可能觉得我偏袒自己的家乡,但我是就事论事,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局长是快退休的年纪了,说:“小衮,这个我们是知道的、知道的。”办公室副主任点点头,表示对局长的认同和对衮副局长的理解。衮秋生还想说什么,衮草寺从沙发上直起身子来,秋生赶紧伸手搀扶,那如蓑篷般的身子骨,在他掌间晃来晃去,衮秋生的眼眶瞬间发胀。
老人的声音很轻:“回吧。”
衮秋生也没打招呼,搀着爷往外走。
局长站起来,冲着两个人的背影说:“小衮,你先扶老人家回去,这个事回头局里给县里打个报告,我们再争取下。”衮秋生回头点下头,和爷相携着往外走去。走出大门,正下楼梯,迎面撞见春生。这才知道爷是一早自己个儿坐班车到县里,也没给春生两口子说,把春生给急得,火烧火燎地跟了过来。春生几乎是抱着衮草寺说:“爷,以后您去哪儿能给我说一声行不,我都同意,我送您还不成吗。”激动之下,又加一句:“您上天入地我都跟着,我都同意。”衮草寺抬起烟杆,敲下春生的头,“乱讲话。”春生噘了下嘴,然后笑了。秋生心里虽然还有些后怕,也挤了挤嘴角。
以前多少次,衮秋生想把爷接到县城来,横说竖说爷都不答应,找理由说县城太硬、太窄、太高,他住不惯。后来年龄越来越老,更不愿意了,说是怕死在外头——这是衮草寺的原话。这次来了,秋生自然想抓住机会,无论如何也要让爷在家里住些日子,自己也尽尽孝。可爷还是不愿意,本来让春生立马带他回的,拗不过秋生求半天,终于答应吃个午饭。
看着爷上了春生的车,秋生心里难受,那一直酸胀起的眼眶,终于掉下泪来。
衮草寺和春生到家时,才下午四点,春生让媳妇赶紧做饭,说县城的饭菜太油腻,爷没吃好。衮草寺阻止,但没用。做好饭,月亮崽下学回来,先吃了,乖乖到房间去写作业。衮草寺坐下来,喝了一碗酸汤,吃了一小碗米饭,就进了屋,说累了、倦了。春生想陪他进屋,被爷拦住。想到媳妇每天都会把爷的床铺好,也就罢了。衮草寺衣服也没脱,就躺进被窝里,刚眯着,秋妹就出现了,和前几次一样,笑吟吟地站在床边。这回,秋妹主动伸出手去牵他,衮草寺突然有了力气,不但牵了秋妹的手,还紧紧地抱住了她。
抱着秋妹,衮草寺久久不愿放手,生怕一松手,秋妹又不见了。
秋妹身上的味道比以前还要好闻,身体比以前还要柔软。衮草寺在秋妹的耳边呢喃,我的秋妹哟,我咋觉得回到年轻时候了呢。秋妹的下巴搁在衮草寺的肩膀上,“就是啊,你还不知道吗?”衮草寺使劲儿点头,“知道知道,这回是真的晓得了,你咋不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你,你能咋的。”秋妹嗔笑。
“就是就是。”
天麻麻亮的时候,衮月亮背上书包,出门上学,刚走出门,又折转回来,摸索着走到祖爷房门前,想看看祖爷在不在床上,如果在的话,可以讨要两块钱。每回,祖爷都会给他十块、二十块,从来不会只给两块。推开门,月亮崽一阵欣喜,被子拱成半弧——祖爷静静地躺在床上。孩子走近,被子盖住祖爷的大半个身子,一条裹着薄棉裤的腿露在外面,稀疏的白须支楞着,凝固在半空。即便是个孩子,也感觉不太对劲儿,怯生生地唤:“祖爷……”然后,月亮崽看见祖爷的脸,像被什么光照着,比月亮还要白,比玻璃弹珠还要透明。
衮草寺就葬在秋妹旁边。
按老人的遗愿,秋生春生给种下一棵枫树。
烧纸的时候,有着神秘花纹的黄色纸钱,不停翻卷,一半灰烬一半纸,像长相奇异的蝴蝶,在秋生春生的指臂间,在林间,穿来梭去。秋生说,他收到州里面的回复了,要求县政府特事特办,乌隧还是沿袭原有的丧葬习俗,树葬,也不火化,让爷安心上路。一只乌雀从天边飞来,在枫树上鸣叫,灰蓝色的眼睛凝视不远的乌隧。一会儿,它飞到树梢,穿过山腰,回到它曾经祈祷过的地方。
风慢下来,瑟瑟的,洒进月亮崽细小的脖颈,孩子打了个寒战,说,“祖爷的树长了翅膀。”
春生让月亮崽叩了头,然后指着十几米开外的一棵杉树说:“那是你的树。”月亮崽望过去,像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充满好奇,走过去,看见祖爷站在树荫处,还未来得及叫爹妈,祖爷就示意他不要说话。
“祖爷,你不是变成树飞走了吗?”
“是啊,我回家了。”
“你家不是在乌隧吗?”
“乌隧也是家。”
“我想去你家玩。”想想又说,“我也想飞。”
衮草寺指着旁边一棵大榕树说:“等你的树长到这么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找我了。”
月亮崽噘嘴,“那要等好久好久,祖爷。”
“快得很,一眨眼。”
“那我可以飞吗?”
“当然可以,到那时,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月亮崽别提有多高兴了,仰着脖子,拍起巴掌。孩子的眼里,所有的树杈都长出翅膀来,它们变成鸟,或是云朵,在乌隧的上空,在遥远的天边。
回来的路上,月亮崽不停地眨眼睛。春生媳妇问他是不是眼睛痒,月亮崽说,不痒。
快到家时,他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立在院中,像是等了许久的样子。老人脚边搁着个黑白相间的编织袋,背着一把用麻布包裹的古琴,灰白的头发稀疏、蓬乱,冷风贴着它们,遮蔽住半张脸。春生呆了会儿,抬腿就跑过去,嘴里喊着师傅。衮月亮眨巴眨巴眼睛,对娘说,那个爷爷也想变成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