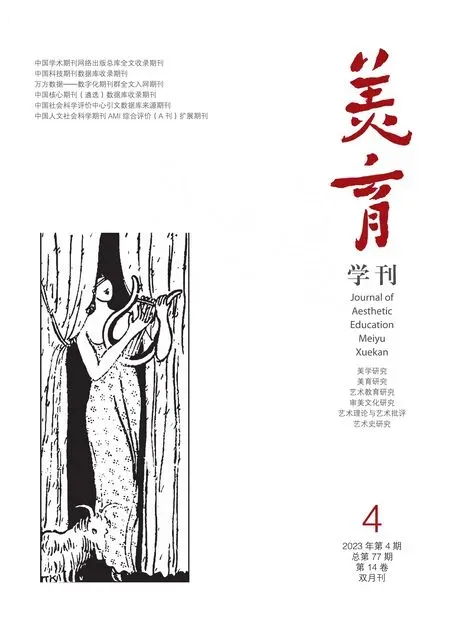诗艺、诗人与诗教
——重回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语境
吴明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诗人贺拉斯生活在古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早期,亲历了共和国末期的内战和帝国初期的强盛。《诗艺》写于公元前20—公元前10年前后,罗马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战迎来和平。维吉尔大约在同时期完成了史诗《埃涅阿斯纪》,讲述罗马城邦从童年到罗马的辉煌故事,用神话为新的罗马帝国奠定基础。贺拉斯的《颂歌》同样致力于塑造罗马的民族性,他也是古罗马的“民族诗人”。除了创作诗歌,贺拉斯还写作了《诗艺》,讨论“诗人”和“诗艺”,思考诗人在新的国家形态下的身份和作用。贺拉斯面对奥古斯都时期形成的文学秩序,在国家、恩主、朋友、公众等各种权力关系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1]
贺拉斯作品主要分为三类,诗歌(包括《颂歌》与《长短句集》等)、闲谈(sermon)与书信,其中《诗艺》通常被归入书信作品。学者主要关注《诗艺》中提出的“合式”(decorum)、诗画关系以及“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因为它与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批评有密切关系,主要被看作文艺批评作品。[2]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容易忽略它作为书信的形式以及文本特征,且脱离当时的政治背景、古罗马的修辞实践和贺拉斯自身的关切。《诗艺》是贺拉斯应皮索之请而写作的回信,有具体的教学意图。本文尝试结合《诗艺》的形式对文本做些梳理,重新回到贺拉斯《诗艺》作品本身、古罗马的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古典修辞学语境下来理解“寓教于乐”这一说法,并将其置于西方的诗教传统当中加以审视。《诗艺》曾经引起很多的论争,尤其是《诗艺》的形式结构以及主旨聚讼纷纭。[3]15-40大体可以确定的是,贺拉斯讨论了“诗人”和“诗艺”的问题,在他看来,“诗人”问题是讨论“诗艺”的前提和基础。当诗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承认,讨论“诗艺”才可能而且必要。
一、“诗人”与《诗艺》
《诗艺》又名《致皮索父子的信》,以诗体写作,全文共476行。在贺拉斯之后大约一百年的昆体良在他的《修辞术原理》(8.3.60)中以“论诗艺之书”(liber de arte poetica)来称呼这封信,这个名称延续至今。从昆体良开始,它就从论诗的书信变成了文艺批评作品。到了中世纪,又有学者将它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放在一起,认为这部作品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由此形成“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解释系列,这一理解方式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4]
因为它曾被看作是严格的批评作品,以及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亲缘关系,所以多数学者以理解《诗学》的方式来理解《诗艺》。他们认为《诗艺》应该有严谨的结构。但是,《诗艺》表面结构的松散、随意和跳跃,与严谨的文艺批评作品严重不符。《诗艺》的结构引起相当多学者的争论,学者们想尽各种办法对它进行划分,但是仍然没有公认的划分方式。[5]170-174因为对《诗艺》结构的分歧较大,我们也仅能作大体的划分。《诗艺》大体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讨论诗艺(ars),一部分讨论诗人(artifex)。对于“诗艺”部分的具体划分,历来分歧很大,但“诗人”部分则比较统一,基本认可从第295-476行为专门讨论“诗人”的部分。[5]154-157(1)有人将“诗艺”再分,变成三部分,也即“诗艺”(1-152)、“悲喜剧”(153-294)、“诗人”(295-476)。王焕生也持两分法,即分为“诗艺”和“诗人”。还有一种划分方式,将之分成“诗的样式”“诗的内容”“诗人”。
如果我们不把《诗艺》当作《诗学》这类严谨的哲学作品看待,而将它还原为与友人论诗的文学书信,或许更容易接受它结构的松散和随意,以及多处的跳跃。[3]244-272《诗艺》是贺拉斯写给皮索父子三人的回信。大概是皮索的儿子想从事诗歌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就向他请教,贺拉斯作了回信。有关皮索父子的身份,历来争议较多,没有固定的结论,但我们知道他们是罗马贵族,爱好诗歌。贺拉斯是奥古斯都时期的“桂冠诗人”,处于古罗马由赞助体制和流通机制支配的文学秩序当中。[1]《诗艺》这封回信也表明,当时古罗马的贵族圈子中,诗歌作为一种贵族间的交际手段,深嵌在古罗马的政治生活当中。作为一封书信,它有明确的针对性,有具体的对象和内容。但是,它又有公开性,它的读者不仅仅是收信人,还包括其他读者。贺拉斯的直接读者是皮索父子三人,潜在的读者则更加广泛。皮索父子三人的身份,恰好符合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贺拉斯可能借这封回信,向这类读者——对诗歌和诗艺有了解和爱好的人,来全面谈论他对诗艺和诗人的看法。因此,《诗艺》文本具有明显的“对话式”特征。[3]3-14
《诗艺》虽然结构相对松散,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基本的思路和线索。《诗艺》始于讨论“诗艺”,贺拉斯却在后面用很多笔墨来讨论“诗人”。将《诗艺》回归其教育的意图才能理解两者关系:“诗人”问题是讨论诗艺的前提。当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得到确定之后,谈论具体的诗艺才有价值。在《诗艺》中,“诗艺”部分附着于“诗人”,从属于该文的教育目的。在“诗艺”与“诗人”衔接部分,贺拉斯明言,自己虽然不再从事写作,但想到“磨刀石”的作用,要告诉他们,“诗人的职责和义务,从何处汲取材料,如何培养和塑造诗人,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如何走向美德,避免错误”(306—308)。(2)本文《诗艺》的翻译主要参考杨周翰中译本,并据Niall Rudd的拉丁文本对部分词语作了修改。[6]153,[7]这既是贺拉斯《诗艺》文本从“诗艺”向“诗人”的转折,也是写作《诗艺》的意图之一,他由此开始讨论有关“诗人”的问题。贺拉斯以谈论诗人的“职责和义务”(munus et officium)开始讨论“诗人”。“义务”(officium)是典型的古罗马用词,突出个人对共同体的道德责任。西塞罗曾经写作了论“义务”的长信《论义务》(De officiis),告诫自己的儿子如何认识高尚(honestum)与益处(utilitas)的关系。[8]贺拉斯提到的美德与错误,同样指涉道德哲学。以此来看,《诗艺》处理的问题,除了诗艺,也与道德教育密切相关。贺拉斯讨论“诗人”,以期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诗人”。
二、“理想诗人”与公共教育
贺拉斯提到他教导诗人的“职责和义务”,但他没有直接谈论“职责和义务”,而是从批评两位希腊诗人开始,在论“诗人”的中间位置讨论了“古代诗人”。不管是被批评还是被赞扬的诗人,贺拉斯所举的例子主要是希腊的古代诗人,在希腊的两种诗歌传统中有抉择,在继承和扬弃希腊传统之时塑造古罗马的“理想诗人”形象。“诗人”部分内容丰富,结构错综复杂,结合贺拉斯有关“职责和义务”的论述以及教育的意图,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一是从何处学习作诗,二是塑造和培养诗人,三是诗人的作用。在具体文本中的主要线索则是首先处理天资与技艺的关系,其次是强调“睿智”作为写作的开端和源泉,最后处理诗歌的娱乐和教育功能。[9]325-328
首先是讨论天资与技艺的关系,摈弃只认天资以及“迷狂”的诗人。贺拉斯论“诗人”部分从批评德谟克利特开始,以批评另一位诗人恩培多克勒结束。贺拉斯论“理想诗人”部分恰好处于批评两位诗人的中间。德谟克利特主张天资重要,排斥头脑健全的诗人,并远离人群(295—304)。恩培多克勒希望人们把他看作天神而跳入火山口(465—476)。贺拉斯将他对“理想诗人”的论述置于这两位诗人中间,基于天资与技艺这两者的关系批评这两位诗人,为他的“理想诗人”设定了边界。这里的说法也指向了该书的主题——技艺(ars)。[9]330贺拉斯教人如何写诗,自然要给技艺留下足够的空间。如果立足于诗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贺拉斯此处的论述就会更清楚。贺拉斯的“理想诗人”关注“职责和义务”,必然排斥“迷狂”的诗人。此外,这两位诗人是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人,不关注道德哲学。按西塞罗的说法,苏格拉底与前苏格拉底哲人最大的差别在于,“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唤下,并将其安置于城邦之中,甚至还把它导向家舍,又迫使它追问生活、各种习俗以及诸多善和恶的事情。”[10]《诗艺》教人作诗,诗人又与共同体密切相关,尤其推崇道德哲学,必然肯定和重视技艺、贬斥“迷狂”,并且批评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人。这部作品又是应皮索父子需求而作,直接的教育目的更胜于其诗学意图。贺拉斯对天资与技艺的处理,既是回应古希腊以来的诗学问题,更是出于古罗马的现实语境及其作品的教育意图。
其次是确立“睿智”作为诗歌写作的开端和源泉。贺拉斯批评了前面这两类诗人,摆正了诗人的位置后,他才开始强调“睿智”的重要性,认为“睿智”是写作的开端和源泉。这里的“睿智”(sapere),应该从贺拉斯的意义上来认识它。(3)在贺拉斯的意义上,“sapere”这个词有非常强的伦理意味,也有实践的意味。英译一般译为“wisdom”,杨周翰翻译成“判断力”,李永毅翻译成“智慧”,本文将其翻译成“睿智”。它有很强的伦理意味,偏重道德哲学。贺拉斯说这种“睿智”可以从“苏格拉底的文章”那里获得。“苏格拉底的文章”,指的是柏拉图、色诺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苏格拉底生活和言论的记述。贺拉斯的“睿智”呼应了前面提到的“职责和义务”,从对国家和朋友的职责开始,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包括爱父兄、爱宾客、元老和法官的职务、将领的作用,等等(312—315)。这也再次将《诗艺》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联系起来。诗歌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也应在具体的政治生活当中承担政治教育功能。在另外一封《致弗洛鲁》的书信中,贺拉斯还认为,荷马和维吉尔等诗人,比起道德哲学家来说更懂得“高贵和低贱,有用和无用”(《书信》1.2.3-4)。[11]589由此来看,诗人应该是“高贵和低贱,有用和无用”方面的专家。由此,贺拉斯才将具有伦理意味的“睿智”置于诗中最重要的位置,将其当成诗歌写作的开端和源泉。贺拉斯批评两位希腊诗人,强调“睿智”的首要性,突出“理想诗人”与公共教育之间的关系。
最后是突出快乐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贺拉斯那里,诗人通过“诗教”与政治共同体相关联,他在第333-334行提到:“诗人想要的是,要么有益人,要么取悦人,要么他所写的同时带来快乐和有益于生活。”[6]155贺拉斯随后进一步解释了前面提到的概念:这种人能够结合快乐与益处(miscere utile dulci),既取悦,又规劝(343-344),赢得所有人的赞扬[6]155。“结合快乐与益处”也即我们所说的“寓教于乐”。贺拉斯在这里列举的三种方式是并列关系。这里指的可能是三种类型的诗人,或者是三种类型的诗歌。一种教育人,一种取悦人,而另一种既让人愉悦,又有益生活,也可以说是结合了前面两种。这句话表明,在当时的普通诗人那里,教育人和取悦人是分离的。或者理解为,针对不同对象,诗人创作不同类型的诗歌。贺拉斯特别看重的是第三种,他的“理想诗人”既能取悦人又能教育人。贺拉斯提到要结合这两种功能不仅仅是教育方法,也有政治上的功能,涉及政治阶层的融合。因为长老的“百人连”喜欢带有益处的戏剧,他们看重诗歌的教育意义;青年骑士团更喜欢有趣味的戏剧,排斥无趣的戏剧(342-344)。[6]155那么,贺拉斯提出结合快乐与益处的说法,也有弥合政治阶层和年龄分歧的考虑。首先,这是古罗马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中的问题。贺拉斯在古罗马戏剧演出的语境下谈论这个原则:诗人身处城邦,承担城邦教育的职责,教育观众和邦民,弥合政治分歧,获得观众的喜爱。其次,结合快乐与益处,是古希腊罗马诗学与修辞学的主题。贺拉斯在这里的用词,有益(prodesse)、取悦(delectare)、规劝(monendo)等,都深深浸淫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实践中。它既指向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相关说法,又与古罗马的修辞术直接相关。[9]353-354,[12-13]除此之外,这里有关快乐与益处、取悦与规劝的说法,必然关涉人的灵魂类型与性情,又与古典诗教关联。我们借助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诗歌的两次批评来理解诗与城邦的关系。在《理想国》第二卷和第三卷,诗只是承担着城邦教育的功能,以城邦之是为是,以城邦之非为非,不符合城邦标准的诗人就要被驱逐。[14]69-94但是在第十卷,诗被赋予更高的地位,它与认识人的灵魂和性情相关,诗超越了具体的城邦。[14]356-395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诗关注人的性情,旨在教化,归属于政治学。[15]贺拉斯的《诗艺》结合快乐与益处,同样有这方面的考虑。贺拉斯与古典诗教的关系,在他有关“古之诗人”的说法中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结合贺拉斯前面的论述来看,其“理想诗人”既要学又要教。他从“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学习个人对于共同体的职责,也即“睿智”,而他教的内容能带来快乐且有益于生活,结合了快乐与益处。这种结合也能够用另一种方式理解。贺拉斯的“结合快乐与益处”既是对诗人创作而言的,也就是针对读者的接受而言的。对诗人来说,写作的时候要兼顾两者,也就是兼顾两种读者(观众)的需求。对读者而言,在阅读和欣赏的时候,能够发现诗人教的内容。这必然涉及两个层次的读者:一种是普通读者,他们在阅读或者欣赏诗作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种读者则从诗歌认识到诗人背后的“教”,获得对灵魂的某种认识。接着,贺拉斯揭示了俄耳甫斯、安菲昂与共同体的关系,进一步推进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贺拉斯的这些内容都是针对皮索父子以及类似的读者来谈论“理想诗人”的。
三、“古之诗人”与诗教传统
贺拉斯的“理想诗人”的核心部分插入了一段追溯古代诗人的内容,这是“诗人”部分的重点。诗人之所以承担教育的角色,不只在于他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角色,而是超出政治共同体。贺拉斯确立诗人的地位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批评两位希腊诗人开始,另外一条从延续古代诗人的地位来讨论诗的起源。
贺拉斯谈论古代诗人,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诗学观念以及他的“理想诗人”:
当人类尚在草昧之时,神的通译——圣明的俄耳甫斯——就阻止人类不再屠杀,放弃野蛮的生活,因此传说他能驯服老虎和狮子。同样,忒拜城的建造者安菲昂,据传说,演奏竖琴,琴声甜美,如在恳求,感动了顽石,听凭他摆布。(391—396)[6]157-158
在贺拉斯笔下,最早的诗人既是启蒙者,也是立法者。诗人和诗歌都被看作是神圣的,享受荣誉和美名。贺拉斯在这里提及的古代诗人,都属于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功绩也限于传说。最早提到的俄耳甫斯是神的通译,沟通神和人,传达神的旨意。他阻止了人类的屠杀,使人类放弃了野蛮的生活。传说中诗人驯服了老虎和狮子,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实际上是他用音乐改变了人类凶残的习性。被驯服的老虎和狮子只是人类野性的代表。贺拉斯扮演了通译者的角色,沟通古代和现代、传说与现实。其次提到忒拜城的建造者安菲昂,他的诗艺能够感动顽石。这里又涉及一个传说,安菲昂和他的兄弟一起建造城墙,他兄弟以手来搬石头,而他通过奏乐,让石头自己动起来。贺拉斯提到安菲昂的音乐感动顽石,也暗示出诗歌对城邦和民众的教化意义,以及诗人与安邦定国的关系。此处出现的人物,要么是神的通译,要么是城邦的建造者,都停留在传说当中。贺拉斯总结出古代诗人的智慧:“划分公私和敬渎,禁止淫乱,制定婚姻礼法,建立邦国,铭法于木。”(397—399)[6]158
古代诗人为人类生活划分公共和私人的领域,划定神圣和世俗的领域,同时引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建立城邦,制定法律。他们主要扮演了建城者和立法者的角色。除了与政治生活直接相关,此处还暗示了诗人与引导和训诫人的灵魂相关,与教化相关。古代诗人与公共生活的关联主要通过教化达成,从而形成“诗人—诗歌—灵魂—城邦”的模式。在此之后,贺拉斯提到了希腊的荷马和提尔泰奥斯。荷马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称为所有希腊人的导师,而提尔泰奥斯以写哀歌著称。他们的诗句曾经激起战士的士气,最终取得战争胜利。贺拉斯此处没有提到传说,只提到诗人的功绩是刺激将士追求荣誉。从神的通译和建城者,到士气的激励者,在贺拉斯的历史叙述中,从传说转变到现实,诗人的地位在下降,但诗人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变化,诗人通过诗歌影响个人的灵魂,进而影响到共同体。这里也看出诗教的不同层次。贺拉斯这个时候再次总结诗人的地位和作用:“传达神的旨意,指示生活道路,求得帝王恩宠,在劳作之后给人带来欢乐。”(403—407)。[6]158
贺拉斯在此追溯古代诗人,确立诗人与政治共同体的本然关联,诗人不仅能表达城邦或者国家的意见,也可以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越古罗马的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快乐与益处,则不仅是功利的教育目的,而且涉及诗人对灵魂的认识与思考。诗人只有深刻认识不同的灵魂类型,才可能结合快乐与益处。贺拉斯谈论古代诗人,解释他的诗学原则,突出诗人通过创作诗歌影响人的灵魂,与公共生活建立联系,在城邦教育而非文艺理论这个维度继承了《诗学》。贺拉斯主要讨论的诗歌形式是悲喜剧(153—294),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公共教育手段。[11]671-693(4)贺拉斯在《致屋大维》的书信中也主要讨论戏剧,可作为《诗艺》的补充。贺拉斯写作的《诗艺》针对作为公共教育者的“理想诗人”,讨论如何写作以及通过写作进行教育,而非泛论诗艺。
我们将贺拉斯的诗学观点置于其产生的语境,可以清楚地看到《诗艺》作为公共教育的文本性质。它以书信的体裁提供一种对话的开放性。它不仅讨论了具体的诗歌技艺问题,更是通过讨论诗人联结了诗歌、诗人与城邦。诗人也通过创作诗歌进入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秩序当中,通过创作诗歌影响读者,教育公民。我们至少有三条线索来理解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和《诗艺》。第一条也是最常见的,即《诗艺》是“诗艺之书”,从诗艺以及西方文艺批评史来认识《诗艺》,我们在此基础上补充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第二条线索是“罗马之书”,它深嵌在古罗马的政治语境当中以及由古罗马的国家、恩主、朋友、公众组成的文学秩序中,不管是它的具体语境还是它的用词,都具有典型的罗马特色。第三条线索,《诗艺》是“教育之书”,它是古典诗教的一部分,突出诗歌在城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诗不仅表达城邦意见,不只是传声筒,诗人还类似立法者,是灵魂的导师。贺拉斯追溯“古之诗人”也抬高了诗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在这条线索上,贺拉斯的《诗艺》既与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育相关联,又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柏拉图的《理想国》、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荷马史诗》这条诗教传统联系起来。《诗艺》既是文艺批评作品,也是现实政治教育之作,更是超出具体时代和城邦的诗教之作。从这三条线索认识《诗艺》,贺拉斯的“结合快乐与益处”(也即“寓教于乐”)能在更高的层面得以理解。此外,西方的古典诗教又可以跟中国的古典诗学批评以及礼乐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的古典诗学同样有“兴、观、群、怨”的传统,中西诗学可以在诗教层面互相发明。
《诗艺》被当成文艺批评作品,读者对“寓教于乐”的理解就脱离了其具体的语境,往往强调其诗学原则和文艺思想,注意其形式和技艺因素,而淡化了它在古罗马语境中的作用尤其是公共教育的意图以及价值,更是忽略了贺拉斯对诗人的期望。这是大多数古典作品后来的命运,其诗教的意义被弱化,而突出其审美和艺术的因素。重新审视其最初的语境,恢复诗艺、诗人与诗教的视野,仍然有现实意义。
四、结语
贺拉斯的《诗艺》是一部复杂的文本,有多个面向。把“寓教于乐”之说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到《诗艺》与诗教密切关联,《诗艺》的核心是诗教。古典的教育主要以诗教的形式进行,盖因诗歌有打动人心的能力,能帮助认识人的灵魂。贺拉斯在《诗艺》中塑造了“理想诗人”的形象,在此基础上讨论具体的诗艺。“诗人”部分是整部《诗艺》的前提和基础。贺拉斯追慕古代诗人,把诗人提升到“立法者”“通译者”的地位,突出了诗歌与灵魂的关系。“理想诗人”处在古罗马具体的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当中,也深嵌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传统当中。此外,贺拉斯又超出了具体的政治语境,“寓教于乐”必须立足于对人的灵魂的洞察和对人的性情的把握。
贺拉斯的诗学观念在古典主义时期受到推崇,并与戏剧实践相结合,成为文艺批评的经典文本。在贺拉斯的作品、古罗马的现实处境以及古希腊罗马修辞学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贺拉斯的诗教观,进而认识古典诗学的政治维度。就此而言,回到语境中重新认识贺拉斯的诗学观念,思考古典的诗教传统,也对我们当今的美育有所启发。
——亚里士多德《诗艺学》第4章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