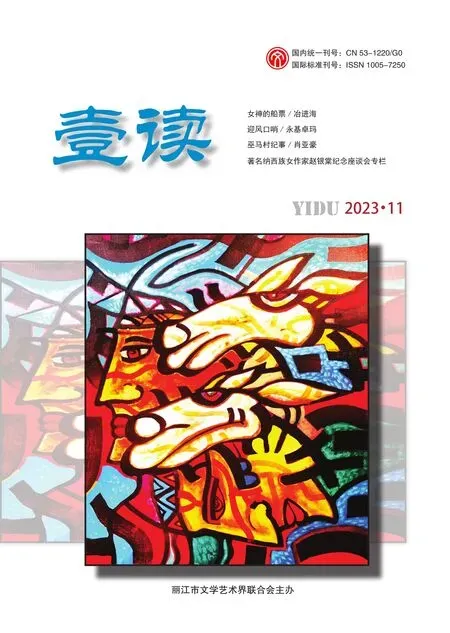迎风口哨
◆永基卓玛
1
“你相信什么,什么就会进入你的生活。”
朗杰在我耳边冷不丁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话。
“以前我也相信世界是我的,但留给我们大器晚成的励志故事从来都不会实现。”我忍不住嘲弄朗杰的深沉,自顾自地端起手里的酒杯喝着。
我们坐在一个老乡开的弦子吧,舞池里,不同年纪的人随着音乐的节奏与灯光的跳跃舞动着身体。
舞池里有个女孩很特别,高昂着下巴,却低垂着目光,眼睛不看人,小腿像鹿一样灵活,自己转着圈。
“你要有力量去吸引你心里相信的。”
此时此刻,我的耳膜被音乐震得隆隆作疼,朗杰还断断续续地把他的哲学挤进我的耳边。我并不想与他讨论什么,虽然我满眼都是舞池里的那个姑娘,但连同这个女孩开始一段友谊的力量都没有。
这是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但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此时此刻,我知道我需要睡眠,或者一碗热茶。虽然我可以回家,回到床上,但我害怕一个人,一个人在房间的寂静慢慢坠入心里的黑洞。
黑洞是什么,我不知道,每次我凝视那个黑洞的时候,只感觉自己的力量在被吸收,而全身的神经会慢慢紧紧地绷紧起来,一个对生活无能为力的自己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相对于那种寂静,我更愿意坐在这嘈杂的地方喝酒。有时,嘈杂的周围也能按摩紧张的神经。
“当你完全信任,力量就会充满你的内心。”说完这话,朗杰把头转向一边,眼睛空洞地看着正在聚光灯下跳舞的人群。
“我要把甲巴放入你的心里。”
“甲巴?甲瓜?”
“甲巴!”朗杰重重地把两个字说了一遍。
这个快接近五十的男人,营养不良的头发被他扎成个小马尾拴在脑后,使得朗杰头发稀少的大脑门显得更夺目,他依然目光空洞地看着舞台。
“甲巴说,解决了吃饭穿衣这些物质基础以后,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自己出发的路,屋顶太厚,会压到自己飞翔的翅膀。我们应该做出一些选择,只要是向着美、向着自由,都应该放手去折腾。”
“甲瓜。”我不无恶意地说道。心里忍不住地想骂,你自己穿得土不拉叽的,快五十岁的人,还在脑后拴个小辫子,虽然你有那么多道理,干嘛不把力量装入你的心里。
但我没把这些话说出口,昏暗的灯光下,我和朗杰,两个不修边幅的老男人,目光空洞地看着舞台喝着啤酒。
我已经十天没洗澡也没换衣服,我知道自己的状态并不比朗杰好多少,在这个小城里,除了朗杰,没有人会在我旁边呆坐上一个晚上或者一整天,用一些胡言乱语来打发时间。
2
当我在自己房间醒来时,时间已是下午一点。
我慢腾腾地起床,在房间里不停地咳嗽。最近两年来,每天我吃很少的食物,在小城里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每天走很远的路,常驻的还是老乡开的弦子吧,那里可以吃简单的炒饭,有时老乡会给我送上一壶酥油茶。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朗杰,他经常一个人,我们两个坐到了一起,听他说那些没头没脑的话语。
头一个晚上朗杰说的话此时却在我脑海显现出来,“甲巴说,解决了吃饭穿衣这些物质基础以后,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自己出发的路,屋顶太厚,会压到自己飞翔的翅膀。我们应该做出一些选择,只要是向着美、向着自由,都应该放手去折腾。”
美,自由……空荡荡的自由。最近的几年里,我很少与人接触,更别说发生过深层交流或者建立某种固定的亲密联接关系。没人管束我,但我也与这个世界毫无联系。
我讨厌朗杰的故弄玄虚,但他跳跃的思维时不时冒出些让我无语的话语。
但我喜欢听他说起甲巴,有时对我的反驳或者无动于衷,他就开始讲甲巴的故事,或者“甲巴说……”,朗杰说的甲巴,总有些道理,我怀疑过,朗杰是不是因为感觉自己的话没人听,所以想出一个“甲巴说”,就好像我们习惯引用某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诗人的话语。
我还是心里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向着美,向着自由。
甲巴,什么鬼。
带着空荡荡的自由,我游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在这个土黄色的小镇,满街都是人,带着土黄脸色,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他们忙碌地折腾着世界,每个人也充满欲望地让世界折腾着自己。我只是他们其中忙碌的一员。
我出生在这个土黄色的小镇,在这个小镇里度过童年、小学、中学、大学,而后工作。小镇的每个角落我都熟悉,几十年来,它的变化越来越大,曾经我出生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改为一个公园。
我经常感觉自己平凡,渺小甚至无力,如今的我,经常在夜里两点抽着劣质的烟喝着呛鼻的酒,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就会这样的死去,没人纪念我,没人提起我。
3
“过马路时小心点,你听到了吗?”
“哦,妈妈,我听到了。”
过马路时,母亲的声音在我心底响起来,我乖乖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着绿灯。
35 岁的我,从来没对母亲说过“不”字,虽然这样,母亲每次和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加上一句:“听到了吗?”
影子跟着我的脚步慢慢悠悠地走着,我还是想向前走,虽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刚才在心底响起母亲的那句话,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把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点力气又吸走了。走在太阳下的我,感觉一点力量都没有。
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就是一块大石下的小虫。
“宅男,游戏里的英雄,现实里的废物。”而我呢,现实世界里是废物,游戏世界里也不是英雄,我离开WOW 已经两年了。我曾经用了20 天的时间,完成从1 级到70级的历练,完成与女友从陌路到牵手又分手到陌路,直到在游戏里的最后一丝力气用完的时候,游戏里,我的号傻傻地看着别人的号,而我坐在电脑前傻傻地看着自己的号。
我曾是小镇的高考状元,读书并不是我的乐趣,我读书只是为了母亲。
这些,都是我与世界的对抗,但所有的对抗,都抵不过一句话,我对抗不了。
“我过得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你听到了吗?”
“喔,妈妈,我听到了。”
母亲是被我领大的,虽然生活中的吃穿用都靠母亲,从父亲跟“野猫子”跑了后,我开始领着母亲长大。对我来说,课本里那些名词解释、三角函数、英语或者物理给出来的难题,都比母亲给我的难题要简单而且好应付。
我不能让母亲开心。所有的教科书都没给我一个答案。
父亲是小镇的本地人,母亲当初是被父亲的很多情书诱拐到这个小镇,但最后,父亲跑了。和一个外来的汉族女人跑到汉地去了,离开了这个小镇。
母亲和我留在了这个小镇里,成为小镇的人。
父亲离开后,家里经常都是寂静的,空气凝固成一团,我与母亲谁先说话,那团凝固的空气就会被打扰。一直以来,我的成绩都很好,可这些让母亲开心几分钟后,她又开始沉默,有时,她愤愤然把正在切皮的洋芋哐哐啷啷丢进铁锅,嘴里骂骂咧咧:“这对狗男女,吃肉喝酒,好日子都让你们过了,死没良心的。”
配着母亲的抱怨吃下的洋芋总是酸的。在睡着的时候,我有时竟然梦见父亲和那个女人,他们惬意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笑着。
而我,居然很羡慕地在旁边看着。
醒来后,我总为梦中自己的背叛感到羞耻。
但这样的梦越来越多。
4
待我再去弦子吧的时候,才知道朗杰去世的消息。
三天前,早上起来后,朗杰一直盯着路口的柿子树,熟透的柿子在阳光下显得透明而发出黄色的光芒。朗杰不和任何人说话,楼梯也没搬就往树上爬。中午的时候,路口正是人来人往,满街的眼睛眼睁睁看着朗杰像片羽毛从树尖滑落下来,直到地面发出“砰”的一声,所有人才反应过来,朗杰从树上摔下来了。
跌落在地上的朗杰摆着一个夸张的大字,已经没有了呼吸。
也就是这一天,朗杰成了被所有人谈论的重点。大家回忆起他的点点滴滴。也在大家拼凑回忆的时候,大家又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么多年,朗杰一直是个不被人看见的人,甚至他的年纪,点点滴滴都回忆不出来。
朗杰有个能干强壮的老婆,在家里,朗杰说话根本没分量,他总有种本领让事情都搞砸。朗杰坐到火塘旁,火炉上的油锅就会被莫名其妙地打翻;炒青稞时,落在地上的青稞籽比锅里的还多;打酥油的时候,酥油还没出,木桶里的牛奶大半已经洒到朗杰的衣服和地上。
朗杰做过酿酒,学过拖拉机,也开过小卖部,所有的事情无一例外地都被搞砸,最后,每天家里人忙忙碌碌,朗杰在家里这头坐到那头。听着这话,我想象着拴着辫子的朗杰像个影子一样,在媳妇的数落声中,从火塘边飘到门口,又从门口飘到弦子吧。
5
以下是我听到的故事。
朗杰的生母与养母并不是同一个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正是中国大建设时期,边疆的农村周围也建设起各种工厂营房,一部分外来的干部拖儿携女来到边疆做贡献。
当时雪山下的小镇,正是木头经济的时代,一大批说着普通话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到小镇的伐木场,那个世界与周边的农村偶尔有交集,但从来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一边是半牧半农说着当地方言的村民,一边是操着普通话来自五湖四海用着先进机器的外地人。
在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里,朗杰出世了。朗杰的父亲母亲都有各自的家庭。
朗杰的生母属于半牧半农说着当地方言的村民,生父是操着普通话来自五湖四海用着先进机器的外地人中的一员。他们家有三个女儿,朗杰出生后被抱到生父家抚养,朗杰总向往农村的生母家,一有时间就往生母家跑。
“有一次,他一个人抱在村口的石头上抱了十个小时,但没人来留他,也没人劝他,最后,他回到自己在伐木场的另外一个家。”
伐木场关闭后,朗杰父亲的家人也随搬迁大军又回五湖四海去了,但朗杰却没有跟随搬迁大军,他离开了家人,与小镇上一户人家的女儿结了婚。
6
只要我不去弦子吧,我与朗杰的友谊也就消失了,我们两个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坐到一起,结成伙伴。
但是,朗杰死了。
朗杰和我说话的时候,断断续续地说不连贯,而我只是因为有个人这样在旁边说些无意义的废话时,空气也显得有几分轻松。我甚至猜想,朗杰的小辫子是不是为了引人注意才那么留起来,可这造型反让他成了被嘲弄的对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认真专注地听过朗杰说话,有时他断断续续在我旁边说着,我心里想着其他事,眼神凝视着他的脸庞时,他就会显得很开心,和他50 岁的外表并不相称的开心。
想到这里,我有点疑惑,朗杰是50 岁吗?在大家的回忆中,朗杰的年纪也是模糊的。
那天,他给我说的神秘莫测的话语,有种绝望的空洞在他的脸上。
“他一个人抱在村口的石头上抱了十个小时,但没人来留他在村里,也没人劝他回到伐木场,最后,他自个儿回到自己在伐木场的那个家。”
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或者是晴天,或者是雨天,或者有风,有雪,一个七、八岁或者十岁的孩子,渴望与母亲一起在村里生活,当他抱住石头时,渴望被看见,也许,除了这样,他找不到更好的对抗方式。
所有人都知道有个孩子抱住了一块石头,但所有人都装作没看见,连他生母也没去劝阻。
朗杰是怎么回到伐木场家里的呢。
甲巴说:“去他妈的传统吧,放个羊人累得要死,牧羊的事情应该用直升飞机来干,声响和螺旋桨刮的风足以让羊慌忙逃窜!几分钟就干完一天的事,这才是科学、效率。”
我忽然想到朗杰的两个故事,在大家喝酒起哄开玩笑时,正在打赌谁敢吃苍蝇,一声不吭的朗杰拿起桌上的两只苍蝇就放到口里咽了下去。事后,“连苍蝇都吃”成了朗杰被嘲弄的话题。
我问过他:“你真的吃了苍蝇吗?”
“是的。就那样吃了。”他同我说话时,眼神浑浊而温顺,我猜想,在喧闹声中,他脸上绝对带着一种英雄般的豪情,他在表演。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他在舞台上脱了裤子,在热闹的表演舞台上,他为什么脱裤子呢?
每个人都在心里解构着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美都各自不同,当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心里的真诚时却以另外一种意外的方式出现,不知道是迎接荒诞还是嘲笑幽默。
老乡为我端来酥油茶,配着炒饭还有一碗泡椒。平时我从来不吃辣椒,这会儿,我盯住碗里黑乎乎的辣椒拿了一个就放在嘴里。
一阵痛感顿时从舌尖烧到心口,又从胸膛烧向头脑,我的耳朵被烧得嗡嗡作响,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胸膛被辣椒烧裂的瞬间,我感觉到心里有块石头,先是细微得让我没觉察的一声崩裂,石头已经在逐渐裂开。随着依然让我没觉察的崩裂声,石头那些坚硬的棱角随着裂痕慢慢脱落,一块一块石头碎裂开来,最后,那块石头如同风化石一样,哗哗啦啦坍塌成一地尘埃。我脸上的眼泪,一下无声地哗啦啦从眼眶中奔涌而出。
7
第二天,我在怀中装上哈达,来到路口的柿子树——朗杰跌落的地方。
那颗让朗杰付出生命的柿子还黄灿灿地结在树梢上。
“像片羽毛从树尖滑落下来。”
树梢的那颗柿子,至少有108 种方式可以把它取下来,而朗杰为什么用了最笨拙的一种。至少,朗杰为了心里的愿望,专注地做了一件事,哪怕只是一颗柿子。
那么,甲巴呢。甲巴会选择怎么样的方式。
我忽然想到那个甲巴。
我念着《度母经》把哈达挂在树上。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寻找甲巴。
我来到朗杰生长的地方。
伐木场已经没人居住了,整齐联排的老式青瓦砖房安安静静,好多房子的木头窗户及门已经坏了。茅草从水泥路的缝隙长到屋顶的青瓦上,曾经几千人驻扎过的集市,现在如同一个弃儿,让人看不出曾经的辉煌。但只要仔细找寻,还是能找到那个年代的痕迹,房子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已经剥落的黑板,有人的地方就有思考,有人的地方就有宣传,石灰刷过的标语还模糊可以辨识“团结、人民”几个字。
村子与伐木场之间隔着一个山坡,我慢慢向村子走去,心里有种莫名的期盼,不管甲巴年纪有多大,不管她是什么模样,不管她美丽或者丑陋,我都想见见她。
8
村子已经不是一个村子,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大部分牧民已经搬到生活条件更为便利的地方去了。当我问起朗杰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只有几位老人稍微记得一点伐木场的故事。
“那个时候,伐木场有好多汽车,那里的人生活可幸福了,他们经常吃罐头。”
没人记得朗杰。我试着说了那次朗杰在村口抱着石头不肯走的事后,有个老人想起了他。
“那个小孩,他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建国还是建军,天天往村里跑,放着拿工资的幸福日子不过。”
朗杰的家人也搬家了。
“小孩子家嘛,谁有空一天去哄,别理他,他就不折腾了。听说,他也没把书读好,不然可以当上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呢。”
“甲巴,村里没有叫甲巴的人哦,当时,我们对伐木场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都叫甲巴。”
没有朗杰,没有甲巴,这里有个王建国。
朗杰说:“你信任什么,什么就会进入你的世界。”
母亲说:“你听到了吗。”
从村里出来,我的步伐变得更沉重,每走一步都感觉到骨骼的疼痛。此时此刻,我感觉我前所未有的劳累。
我不知道我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我与母亲,我与朗杰,那些相处过的场面,还有他们说过的话语,像蒙太奇一样,在我脑海中轮放着,一会儿是母亲,一会儿是朗杰,偶尔,甲巴的话又会在我脑子里蹦出来。
甲巴说:“每个人都会自己与自己对抗,与世界有对抗,在这些对抗中,灵活地面对世界,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坐姿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权利。”
对抗?
母亲总用一堆抱怨的语言,对抗着洋芋,对抗着我。
朗杰在对抗吗?
那么,我呢,我曾经想证明自己去对抗,对抗那酸了的洋芋,可就算我是小镇的高考状元,洋芋还是酸的。
9
我混混沌沌地走着,不知道走向何方,有时上坡,有时下坡,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有个马蹄声,我不知道是梦中的马蹄声还是真实的马蹄声引导我,我还是向前走着。马作为臆想经常穿行在我一个又一个陈旧的梦境之中。
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可能我已经这样走了一天一夜或者两天两夜,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此时天地在一片暗黑之中,我什么都看不清楚,看不到我从什么地方走来,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在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时,遥远的地方正慢慢出现一抹金黄。我凝视着远方,那抹金黄在黑暗中把口子撕得越来越大,那金黄色越来越红也越来越亮,在这些颜色的撕扯中,太阳一下蹦出来了,挂在山头上,整个黑暗被全部拉开,天地镀上了一层梦幻的鎏金。
我走到山顶了。
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有什么不同。与我每天在小镇看到的景色虽然不同,只不过是一天又来了。
“太阳啊,你使大地复苏万物生长。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刻,可对于一个我这样从来未被看见的人来说,每一天也没有不同,现在,我的身体又疼又冷。没有朗杰,没有甲巴。”
“没有朗杰,没有甲巴,那你就自己创造。”
“哼,创造?创造什么,我又不是神。”
“创造!拿出你那活泼泼的生命力,向着你热爱的去战斗。创造出你所相信的,创造出众神。”
“你是太阳,不是枯草,也不是树叶。更不是朗杰,更不是我,也不是甲巴。”
“你看过我炽热的外表,但你知道我背面吗?你看到此刻大地光芒一片,没被阳光照射之前,大地又是怎样的黑暗?我是太阳,我是甲巴,我是朗杰,我也是另外一个你,我是大地,我是枯草,我是落叶,我是大自然。”
太阳照得暖暖的,我被晒出一层微微的汗。不知道那段对话是怎么来到我脑子中,是我打盹了吗。
甲巴?
“甲巴给头羊的头蒙上塑料袋,披着塑料袋的头羊像个魔鬼在山上奔跑起来,整个山坡的羊跟着头羊像疯了一般飞奔起来。甲巴惬意地躺在山坡上吹起引风口哨……”
甲巴……引风口哨……
10
悠扬的口哨若隐若现地在我耳边出现。
甲巴?
清脆的马铃铛越来越近了,是个牧场归来回家的牧人,牵着马,自在地吹着口哨。
见到我,牧人也在旁边坐了下来。在当地,牧人一般进牧场都会呆好几个月,牧人是往家里送酥油并准备带些必需品再返回牧场。
他好奇的目光盯着我,几次谈话后,感知我的冷淡,牧人皱着眉头,眼睛眨巴着,坐在我对面,好像研究一个新鲜东西一样瞪着我。
我也毫不客气地瞪着他。
这样瞪了半天,他自嘲地挤眉弄眼了一下,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从随身的褡裢里掏着什么。
朗杰曾经给我说过,甲巴一吹引风口哨,丝丝凉风就会在口哨的召唤下来到身边。我曾经无数次在弦子吧里请求朗杰吹一次引风口哨都遭到拒绝,他说:“人在屋子里时,不能吹口哨,即使是风来到屋子里,对人会不好,会召唤来鬼神。”
在牧人断断续续的口哨中,好像有丝丝凉风从远方吹来,吹到我的面颊上。
真的有风。
“您吹的引风口哨吗?”
“是啊,是啊。”他瞪了我一眼,悠扬的口哨继续响起来,我的问题对他来说显得很奇怪。乡下的老乡都会吹引风口哨,给谷物去皮的时候,劳作累了的时候,旅途休息的空档……
牧人的口哨并不是一段完整的旋律,而是类似于鸟叫,更类似一种召唤。他一边掏着褡裢的什么东西,又用手拍拍裤腿上的灰尘。
我迟疑地跟着前面这个陌生的牧人,吹着口哨。他更奇怪地瞪着我,随后,他拍拍屁股,骑着马,沿着下山的方向走了。
我的口哨声刚开始还很迟疑并断断续续,慢慢地,我能把口哨吹响亮并流畅了,在我响亮而流畅的口哨中,大风来了。
风吹动我的发尖,吹过我的手背,吹过我的耳旁,吹过我的鼻尖。
我站起身来,张开双臂,迎接着被我呼唤而来的风。我被什么看见了,我看见了什么。我呆呆凝视着眼前的一切。
风继续从山谷吹来,白色的流云顺着山顶飘动。一群冬鸟扑腾着翅膀,呼啦啦飞起来,又呼啦啦落下。雪山的顶峰随着太阳的升起慢慢变幻着颜色。山下,青色的薄雾轻盈地盖住了村子、田地。
此时此刻,我呆呆看着眼前的一切,万物的各种颜色在风里流动起来,真美。云是白的,山是青的,雪是蓝色的,树是绿的。
我是多久没感受到美了。
风继续吹着,我想起一些很久远的事。
“朗杰……”被大风吹远了。
“你听到了吗?”母亲的话在大风中被撕裂了。
“石头下的小虫。”石头被大风揉碎了。
大风继续吹着,从一棵树到另外一棵树之间,从枝干到树梢,到每一片叶子,千万种不一样的绿色在风里流动着。
11
为什么大风中流动的颜色这样美?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我是谁,那块在我身上的石头又是些什么?
这些对美的感知一直存在于我的身体内吗?当我第一次看到彩霞漫天并感受到炫目时,当我第一次看到蓝色冰川并感受到震撼时,当我第一次在火塘边吃父亲给我用灶灰烤的洋芋时,洋芋是那么的软糯又香甜,可为什么后来我吃的洋芋都是酸的?那些我第一次看到并感受到的美好,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在我心里,在脑海里不停地转换着。
流动的风把在生命之河中曾经滋养过我的那些支流一条一条汇集而来涌向我。
原来的我是什么样的呢?
洋芋是酸的,还是软糯香甜的。世界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我是谁?好多陈旧的梦也跟随来了。
回归?
一个词蹦到我到脑子中。
回归你热爱的一切,你向往的美,而不是框架中那个僵硬的你。
“甲巴说,最美的事发自人类内心最质朴的对自然的热爱,自然的美丽和苍茫会触动了最柔软的心弦,精神性的东西会在瞬间迸发。”
我好像看到一位姑娘,赤足走过山岗的草地,穿行在城市中。她有着明亮的眼睛,一头乌黑的长发像是生长得茂密的柳树,被大风吹起,朗杰同好多人一样,在她的身后慢慢透明,融入空气。
我忽然明白了,朗杰心中有个甲巴。甲巴的世界就是朗杰描述的,朗杰一直在构建自己的世界,也在心里构建着一个故乡,但那个故乡未曾在朗杰的生命中燃烧起来。朗杰自己也不敢相信,如果有人认同,朗杰会变得大胆,但他一直走在寻找认同的路上。
此时此刻,我相信世界上有个甲巴,以后我将会继续讲述这个故事:“甲巴说……”
我相信,甲巴生活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或者是洛杉矶,或者是非洲,痛快地生活着,淋漓尽致地去爱去恨,感受着她与世界的连接。她对着所有的伤痛与快乐做着鬼脸,燃烧着自己的世界,真诚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