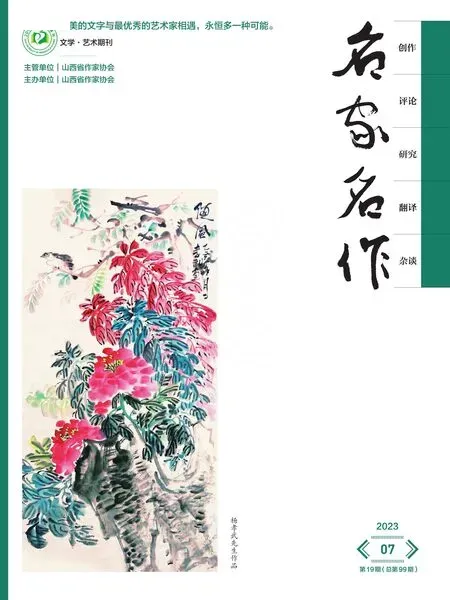浅析庾信的赋作对初唐七言歌行的影响
徐立昕 王 熠
“赋”和“诗”虽是两类文学体裁,但它们在文体特征上体现出众多的相似之处,具有紧密的历史渊源,汉魏时期多诗赋并称。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有“诗赋略”一栏,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也曾提出过“诗赋欲丽”。汉代和唐代可分别称得上这两类文学体裁最繁盛的时期,而处于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成为文学史上“诗”“赋”这两大文体盛衰相转的过渡期。 “诗赋互渗”“诗赋一体”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及至初唐,七言歌行体兴起,虽然是诗歌,却表现出某些赋的特征,这正是魏晋以来“诗赋互渗”的演变成果之一。庾信作为南北朝时期重要的诗赋作家,其诗赋作品正好体现了这种亲缘关系,其赋作尤其对初唐七言歌行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一、题材的沿用和承袭
纵观庾信赋作,其题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援史入赋”“咏物写景”以及“荡子思妇”。其中“援史入赋”最具个人特点,即在创作时借用“历史题材”,以历史描写为基础展开议论和抒情,代表作如《哀江南赋》。《哀江南赋》全篇大量的史实描写以及由史而来的直抒情怀开创了赋题材表现的新大门。初唐七言歌行中,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风格题材都与庾信的《哀江南赋》极为相似,极具“史论”之风。除了这类“赋史”,庾信的咏物赋占据了他赋作的绝大部分,前期的《春赋》《象戏赋》《灯赋》《镜赋》,后期的《小园赋》《枯树赋》都是,但无论是写景还是状物,其咏物赋最终都会落到抒情或者表达哲理的最终目的上来。在初唐七言歌行中,王勃的《落花落》、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是借落花描写春景,表达诗人对春光易逝的慨叹,抒发对生命的感悟,都有庾信《春赋》这类题材的影子。庾信也偏爱荡子思妇题材,带有宫体余韵,如《荡子赋》《鸳鸯赋》《七夕赋》等,这一类作品在初唐七言歌行的作品中非常多,如王勃的《秋夜长》《采莲曲》,都是借景抒发思妇、征夫不得相见的思念之情,《江南弄》则几乎全篇都是对男女相悦而不得见的描写。足见这一内容和选材对初唐诗歌的深远影响。
二、创作手法的影响
创作手法上,庾信赋对初唐七言歌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具象体物的铺陈手法
“铺”作为一种赋的手法,在“以赋为诗”“诗赋互渗”特点的呈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庾信赋法中所用的“铺”与汉大赋那种大开大合的铺陈不同,不是面面俱到,一味求全,而是选取适合的不同角度,具象地描绘某一事物,这种特点被初唐七言歌行所吸收。庾信的赋在状物和写景上非常注重对具体形象的刻画、描写,如《春赋》主要描写宫苑春景和贵族们游宴的场景,在描写春景时,并不是“前后左右广而言”,而是选择典型的场景:园林中的春色景物、宫室中美人的春游图景、宫苑中春季时分的骑射歌舞以及三月三的曲水流觞,从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视角对春景盛况进行铺写,以点成面,用特殊表现一般,完整而生动地呈现了一幅春景图。在这一特点上,初唐七言歌行与庾信的赋是一脉相承的。卢照邻《长安古意》开头从“长安大道连狭斜”写到“凤吐流苏带晚霞”运用连续的六句写“车”,由大道到小巷,引出来来往往的“车”,再由一般的“车”写到“玉辇纵横过主第”[1]81的王公贵族的“车”,接着又从宏观转到细节,开始描绘马车的外物装饰“龙衔宝盖”“凤吐流苏”。短短六句,从车的出现,写到车的流动场面,再转至车子本身华美的造型描写。这种观察入微,层层递进的细腻刻画,给人以真实生动的画面感,使人身临其境。这种“以赋为诗”的铺陈手法,与庾信的具象体物的赋法有高度的相似性。
(二)独特的“史论”手法
庾信的《哀江南赋》以史入赋,有“赋史”之称。其独特的“史论”写法主要凸显在三个方面:“对社会历史的铺陈描写”“对个人身世经历的思索和感叹”和“对荣华难久世事无常的怀古反思”。
庾信的《哀江南赋》篇幅巨大,在具体的历史叙写上包含了诸多方面:对侯景之乱前夕梁朝奢靡混乱的宫廷生活的描写;对梁武帝等身处侯景之乱大局中各种相关人物的描写;对自己辗转半生,凄凉身世的描写;通过反思揭示梁亡真相等等,基于大量的史实描写,展开议论、反思和抒情,表达了对南朝梁覆灭的伤悼以及个人身世的哀叹,使它成为一幅规模空前的历史画卷,作品有意识地从多个方面去总结梁朝灭亡的反思和教训,这种写史、悟史,自觉地把历史环境和个人身世相结合的方式,是极具独创性且意义深远的。在初唐七言歌行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长篇歌行体”作品在主题的选择和内容的表达上都倾向于“登高怀古”“凭高吊古”,并且大量地铺排史实和昔日京都宫宇巍峨和市井的繁华用以抒情、悟理或讽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勃的《临高台》、骆宾王的《帝京篇》都是如此。这些作品或多或少继承并深化了以上三个方面。
王勃的《临高台》,全篇以登高远观为起点,前文极力渲染帝都的繁华,借长安的景貌展示了唐朝建国以来的繁盛。但这种描写并不是正面的,而是带着浓厚的讽刺和批判意味,实质上表现了统治者的奢侈豪华、荒淫无度,暗含了对王朝衰亡的预测和担忧,在文章末尾“银鞍绣毂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少妇不须颦,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2]75表明繁华难久的主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托古意而写今情,以浩浩汤汤的铺陈手法描绘了京都长安的现实盛况,一方面流露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另一方面写贵族阶层骄奢淫逸而同时内部又互相倾轧的真实状态,寄寓了深刻的讽刺意味。另外也能从中看出作者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悲戚和愤懑,以及对世事无常、荣华难以长久的感悟。骆宾王的《帝京篇》与《长安古意》相似,在着力描绘京都长安繁华的同时也显露了“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3]13这样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在主题思想上,《临高台》《长安古意》《帝京篇》都很相似,且与庾信《哀江南赋》“史论”手法一脉相承。
(三)用典特点
虽然说文学创作中皆可以用典,但庾信的赋和初唐七言歌行,在用典密度以及风格偏好上更具有相似性。首先从用典密度看,庾信赋作可以算得上辞赋之冠。仅仅《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4]94的这一段叙写,短短的二十二句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就有11 个。初唐四杰的七言歌行中也大量用历史人物的典故,如卢照邻《长安古意》中“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1]82“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1]82“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1]82四处皆用典;骆宾王《帝京篇》中的“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2]12句句接连用典。
除了用典密集,庾信赋与初唐七言歌行在用典上的选取和处理上也有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借古人自比,用以抒发“同病相怜”“同仇敌忾”的情感共鸣。庾信的《小园赋》 “崔骃以不乐损年, 吴质以长愁养病”[4]19、《竹杖赋》 “伯玉何嗟, 丘明唯耻”[4]34,其用典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由南入北后被迫身仕魏朝的耻痛心情;而悼念梁王朝的覆灭以及自己逃亡时的艰难境遇时,则说道:“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三日哭于都亭, 三年囚于别馆”[4]94(《哀江南赋序》)。初唐七言歌行中,卢照邻《长安古意》: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运用扬雄的典故,以著书的扬雄比喻自己,与长安的显贵人物形成对比,有借扬雄的遭遇自伤自怜的意图,抒发自己时运不济的寂寥愤慨并自我宽慰。骆宾王的《帝京篇》:“马卿辞赋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3]14,列举汉代著名的贤能人士,表明他们虽才华冠世,但升迁滞涩,令人悲叹;后两句谈到张释之十年一直担任骑郞事,也是以张释之自比,叹息自己十年皆毫无升迁的境遇。这两处用典都是结合诗人自身“时运不济”的人生境遇,以典论事,以典共情,在这一点上,庾信赋与初唐七言歌行的处理是相似的。
三、句式特点和遣词风格
句式以七言为主,五、七、杂言错综使用,富于变化。庾信的赋作中,全篇皆是七言句式的,几乎是没有,多为五、七、杂言相混的,如《春赋》《对烛赋》《荡子赋》《哀江南赋》《枯树赋》等。庾信的大多数赋作和杂言歌行作品都是以五、七言为主干,其他句式相辅的体式来完成的。初唐的七言歌行不像庾信赋夹杂四、六言,而是三、五、七言相杂。以王勃《秋夜长》为例,全诗共17 句,三言的有3 句,五言的有6 句,七言的有8 句,三言、五言、七言交错使用,句法错落有致,富于变化,营造出了声情摇曳的美感。再如骆宾王《帝京篇》,开头和结尾都是五言,中间主体部分大多采用七言,夹杂有五言,长短句交错出现,错落有致。
华美的遣词风格。庾信前期作品是典型的宫体文学,“风格秾丽轻靡,辞藻华丽”[5]7,即便后来因人生境遇改变作品风格逐渐走向苍劲沉郁,也没有完全脱去宫体文学的影子,这一风格延续至初唐。初唐七言歌行作品虽然大体摆脱了齐梁的绮靡之风,但在绘物、用词方面仍然保留了华美的风格,主要体现在“炼词以求工对”、善用“颜色词”、常用“连绵词、叠音词”以增强音韵和谐等。
如庾信《春赋》:“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金鞍始被,柘弓新张”[4]74;《七夕赋》:“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嫌朝妆之半故,怜晚饰之全新”[4]79;《灯赋》:“舒屈膝之屏风,卷芙蓉之行障”[4]80,都达到了对仗精工,文辞妍丽的效果。初唐七言歌行中,如“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1]73(王勃《采莲曲》),“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1]74(王勃《临高台》)都凝词工对,且文辞、意象都表现出华美秾丽的风格。除了“对仗”上的用词特点,庾信赋和初唐七言歌行也都爱用“颜色词”,且尤其偏爱“红”“绿”“青”“紫”这类对比强烈的颜色词。如 “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苔始绿”“麦才青”“绿简既开,丹局直正”“白凤遥临,黄云高映”“辉辉朱烬,焰焰红荣”“青袍”“白马”“秦中水黑,关上泥青”……初唐七言歌行如“绿水芙蓉衣”“叶翠”“花红”“紫阁”“丹楼”“赤城”“绿树”“朱轮”“翠盖”“掩翠”“窥红”……用大量颜色词营造出色彩浓烈的画面感,呈现出作品的遣词风格。另外,华美之风也体现为“音韵和谐”的形式美,表现为善用连绵词和叠音词。其中连绵词常分为“双声”和“叠韵”,庾信赋作中常出现“酦醅”“婆娑”“辉辉”“焰焰”“琉璃”“鸳鸯”“溃溃”“茫茫”“昧昧”“苍苍”等;初唐七言歌行也表现了这一特点,如“徘徊”“崔嵬”“萋萋”“苍苍”“葱葱”“玲珑”“漠漠”等,它们的运用都使得音韵更加缠绵和谐,营造出婉转动人的艺术美感,体现了雕琢华美之风。
魏晋以来的“诗赋互渗”现象,正是当时文学观念开始转变,文学思想进步的写照。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道:“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荡摇。”[6]680这种观点表现出人们对文学本身审美特征的重视,也标志着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赵国公集序》中的“含吐性灵,抑扬词气,曲变《阳春》,光回白日。”[4]656是庾信提出的观点,可见受到时风的浸染,庾信的文学观念明显与萧绎等人是一致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大环境下进入自觉的时代,即“人的自觉”“文的自觉”,这种转变浸透至文学创作中,主要呈现出了两种趋势:一是求真,注重体物和抒情;二是求美,注重形式美。因此,同为文学样式,诗除了抒情,也应该注重形象的刻画,赋除了描写也应该注重情感的表达,由此,诗与赋的界限便不再那么明确,诗的赋化、赋的诗化渐趋自然且顺理成章。及至庾信,使这些特点更加融会贯通,其作品的手法运用更为成熟,对初唐七言歌行的影响力也更为强劲。
四、结语
从赋和七言歌行两者的表现特点来看,一方面,西汉的盛世造就了“赋”,“赋”也是描写和反映盛世颇为适合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想要表现出长安的繁华,比之其他诗体,具有赋性质的七言歌行更具优势和感染力,正所谓“长歌骋情”(钟嵘《诗品序》),带有“赋体基因”的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出现和兴盛是必然的,而在汉唐文学的嬗变中,庾信的作品刚好发挥了这么一个关键的过渡作用。
可见,庾信不仅在南北朝文学成就巨大,以其赋作对初唐七言歌行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他也担得起“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7]815(杨慎《升庵诗话》卷九)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