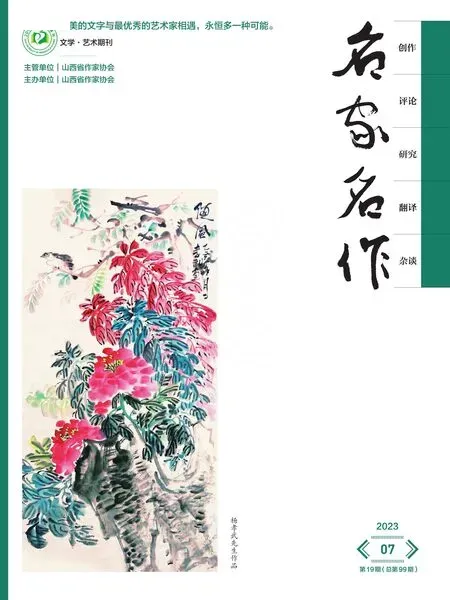论鲁迅与余华小说中看客的“异化”
王 雪
近现代以来,看客作为一个人物形象而出现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417看客不仅作为人物形象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社会文化而存在。在现当代文学中,看客形象自鲁迅开创之后就一直生生不息,其中现当代作家笔下的看客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延续与继承了鲁迅笔下看客形象的内蕴。其中最能表现鲁迅风格的当属当代作家余华,因为两位作家笔下的看客都是在特殊时代下产生和发展的,他们小说中的看客形象都呈现出人格缺失的“异化”。
一、外在行为的“异化”
看客赖以生存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无论是鲁迅笔下无知地“看”,像鲁迅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假使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2];还是余华小说中有意识有目的地“看”,其“看”的行为和所看之事都不约而同地打上了其所在时代的烙印,呈现出异样的生存状态。
(一)鲁迅笔下的看客:麻木愚昧的灰色群体
通览鲁迅的作品,不难发现他笔下的看客几乎贯穿他全部文体的创作之中,除了专门描述看客的《示众》《复仇》外,鲁迅对看客的描写都是寥寥数笔,或以主要事件的环境、或以中心人物的背景而存在。因此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是群众性的边缘化的符号形象。最典型的就是《示众》这篇小说,一群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人你推我挤地争着抢着看马路边被“示众”的“白背心”,作者有意识地放大这群无名、无姓、无思想、无主见的看客“看犯人”的行为,将看客那种凑热闹找乐子打发无聊的精神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阿Q 正传》中阿Q 杀头的名场面,杀头这种血腥恐怖的大事,在看客的眼里就像演了一出大戏,“两旁都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1]525,临近高潮之时,还兴奋地“发出豺狼嗥叫一般的声音来”[1]526,边看边点评——认为“枪毙无杀头这般好看”[1]527。作者鲁迅以白描的手法戏谑地描摹出看客那冷漠的死一般的无可救药的麻木。
鲁迅笔下的看客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有着无形力量的群体,他们常常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并助力中心人物悲剧命运的走向,成为封建统治势力的“帮凶”。例如《狂人日记》中想方设法要吃掉“狂人”的看客们,正是“‘狂人’的清醒成了对他存在的诅咒,注定他要处于一种被疏远的状态”[3],注定被秉持着所谓正统理念的看客所拒绝,他们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监视着狂人,并构建起强大的舆论力量,逐渐将“狂人”抹杀。还有《祝福》里的祥林嫂,导致这个充满悲剧性的中国传统妇女最终死亡的原因除了封建专制“三权”的奴役外,还有鲁镇的镇民和“我”这一群看客的推波助澜。所以鲁迅笔下的看客就是“几乎无事的悲剧”[4]的制造者。
(二)余华小说中的看客:凶残恶毒的黑色个体
余华继承鲁迅的国民批判性,在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麻木的看客。《一九八六年》里的看客要捆绑一次次用古代刑法自残的疯子,只是为了不再去听疯子那毛骨悚然的嚎叫声,与鲁迅的小说《长明灯》里的村民为了制止疯子熄灭长明灯而想办法将疯子送上绝路,这两篇小说中对看客行为的描写较为相似。还有《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在临刑前看到的场面,不禁联想到鲁迅《示众》中那些争先恐后看犯人的看客们。《兄弟》中一些关于看客冷血漠视的细节,例如当李光头因偷看美女屁股而被抓住游行时;当孙伟母亲变疯而裸奔时;当宋凡平为迎接自己的妻子在车站被活活打死时,这些时刻发生的惊人事件,看客每每都在第一现场“看戏”,或哈哈大笑,或全程静默。在他们眼里,无所谓悲喜,不过都是一场滑稽的戏剧罢了。恰如鲁迅激愤的表达,“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163。
余华在继承鲁迅的同时又超越了鲁迅。余华小说中的个体看客,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偏执的思想、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除了鲁迅笔下爱“看戏”的特点,看客还给自己“加戏”,即创造机会使自己参与到“戏”中,使自己观看他人的同时也被其他观众赏鉴。《朋友》中作者设置了一个独特的看客视角——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从这个孩子的视角出发,旁观那充满暴力、欲望与交易的成人世界,从而更深刻地反衬出看客行为的“异化”。《难逃劫数》中的看客在看了彩蝶变美失败的表演之后,还密切关注着彩蝶接下来的举动,甚至在幸灾乐祸的等待中还发挥艺术想象,创造出彩蝶寻死觅活的“好戏”。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看客的“看”更是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荒诞和滑稽,特别是一种类似于丑角人物的出现。“以《 在细雨中呼喊 》为分界点,‘看客’所指的重点发生了悄然变化——不再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余华将它演化为一种狂欢节气氛中‘观众’与‘小丑’(巴赫金语)之间看与被看的模式”[5]。之后“三部曲”中的《兄弟》,在宋凡平与李兰的婚宴上,宾客们竟“东找西找拿出来了两只白瓷杯盖,让李光头和宋钢叼住杯盖上像奶头一样的圆钮”,“在他们看来就像叼着李兰的两个奶头”[6]49,看客这种自己组织戏本,还要求中心人物表演,以此满足他们内心压抑的性欲望。“三部曲”中的《许三观卖血记》,林芬芳的丈夫大肆向许三观的邻居们宣扬许三观在强奸自己的妻子之后给妻子买补品,作者有目的地给林芬芳的丈夫充分的表演空间,使这个个体看客在自己看的同时还呼唤其他观众一起欣赏点评,以彰显这个本是边缘化个体的存在感,传达了生存环境造成的人的异化。
余华小说中的看客的旁观行为还充斥着凶残嗜血暴力般的狠毒。《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出门远行,热心帮助汽车司机的苹果被偷事件,反观汽车司机回馈给“我”的是冷漠的旁观和忘恩负义地偷窃,将刚涉世怀着美好理想的“我”瞬间打入黑暗的谷底。还有《兄弟》中窥视他人隐私或个人私密的看客,就是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7]的表现。像刘镇上的男性都意图偷看镇花林红的屁股,以昂贵鲜美的“三鲜面”来比喻林红的屁股,以此达到邪恶的意淫。在偷看异性肉体的基础上,还参与观看他人的思想意志。小说立足于时代背景,展现了人物的一切——从身到心,从家庭到周边,所有相关的人和事都被拿到太阳下揭露。由于宋凡平出身地主,总被要求交代自己的罪行。从私自抄家到歪曲话语再到强加思想,这一系列看客参与和制造的行为都以强大的力量虐杀着中心人物的肉体和灵魂。毫不夸张地说,宋凡平最后的惨死与看客的凶残恶毒脱不了干系,甚至是直接凶手。
二、内在心理的“异化”
无论是鲁迅笔下灰色符号般的看客,还是余华小说中黑色利器般的看客,其看的行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根据心理学原理,没有无缘无故的作为,背后必定有相应的心灵驱使。鲁迅和余华小说中看客的外在行为的“异化”表明其内在心理也一定是病态的。
(一)鲁迅笔下的看客:可悲的空虚
鲁迅笔下的看客在喜欢看戏起哄的非正常的行为之下,表现出看客内在心理的极度不正常。《药》里茶客看夏瑜被杀时的状态——“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1]440;《祝福》中的祥林嫂变成了鲁镇看客们闲来聊天打趣嘲讽的“玩物”,“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8]18;《风波》里七斤的剪辫子风波,村民们迎合着赵七爷的恐吓威胁,等待着七斤犯法被杀头等一系列看的行为、看的状态,除了表现出看客无情冷漠的心灵和麻木不仁的精神,其真正驱使的是他们那烦闷空虚的只剩一副躯壳的内部灵魂。在经历了长期的儒家思想的教化之后,在日复一日的机械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早已对生活没了热情。所以当有人因奇怪的言论被杀头,有人生活困苦磨难重重,有人要犯事时,但凡是有点新奇的闻所未闻的人和事,都能激起看客强烈的兴趣,以此在这无比寂静的一洼死水中激起一点求之不得的涟漪。鲁迅正是愤怒于看客这可悲的空虚,对其复仇,在散文诗《复仇》中“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8]172来看一男一女或杀戮或相爱,为报复看客的好奇心理,始终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使他们无聊空虚至死。
(二)余华小说中的看客:可恨的反叛
余华小说中的看客如此邪恶的行为表征彰显出了其内心的扭曲和极端,是一种变相的挣扎,是一种压抑的发泄,是一种绝望的呼喊。《黄昏里的男孩》中的小贩撞上男孩偷苹果,借此机会残忍地痛打处罚,通过对别人施虐来发泄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兄弟》中对欲望放纵的放大描写,例如刘镇上从一个少年李光头偷窥女性上厕所发展到全镇的男性都去间接偷窥,其看客群体分布广泛:李光头、刘作家、赵诗人、民警、其他刘镇男人,这种荒唐可笑的行为,各个阶层的参与和偷看,都深刻地讽刺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因性压抑而以这种另类的方式来获得短暂的性满足。还有全镇的人对于性的敏锐关注和联想,当大汗淋漓的宋凡平在篮球场上抱着心爱的李兰时,看客们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大笑、微笑、尖笑、细笑、淫笑、奸笑、傻笑、干笑、湿笑和皮笑肉不笑”[6]43。对于性的幻想性的满足,在《细雨中呼喊》也有涉及。在曹丽和音乐老师之间的恋情信件被要求上交之后,学校里的老师们争相传看,还大肆讨论,一时间这一盛事成为大家百无聊赖闲暇时的谈资。余华小说中的看客对于身边一切有关男女之间的事总是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好奇,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行哪业,都急迫地想旁观想谈论,作者以这种戏谑、荒诞的笔法传达出所处时期的看客既可恨又可悲的挣扎、叛逆、变态的心理动态。
三、看客“异化”的时代原因
鲁迅笔下的看客和余华小说中看客形象的行为与心理的“异化”,表明了看客的精神与思想的非理性释放,尤其是“在极端状态下人的兽性展露无遗”,而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作家记忆深处的那个极端时代。
(一)鲁迅所处时代的“失语”
鲁迅作品中展现的是百年未有之的皇权崩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大变革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乱时代。历经辛亥革命和两次复辟等接二连三的变局,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国民物质贫困、精神困苦,甚至可以说人的生命连牲畜都不如。就是这样国将不国的年代,整个民族乃至全体国民就是鲁迅所指的铁屋子里尚在呼吸的死人。人民群众在几千年传统封建的统治下被摧残、压榨、奴役,成为没有个体灵魂、没有自我生命的“空心人”。这个时代下的国民“活着便只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任由社会以及生活将灵魂从身体中抽离出去,只剩下一个空壳”[10]。所以他们无比的空虚寂寞,滋生了看客文化。同样因为他们的空虚,而盲目从众地旁观,导致抹杀个体的判断和话语表达。鲁迅笔下的看客完全丧失了自由表达的欲望和权利,因此他们的生存方式由此仅有一个——浑浑噩噩地看。
(二)余华所处时代的“狂语”
余华的小说营造了一个迷狂的、疯魔的、邪恶的世界,有死亡、鲜血、斗争、伤残、欺骗、背叛、暴力、欲望、金钱等,似“鲜血如阳光般四射”[11]。余华极尽笔墨挥洒出特殊年代下的死亡和苦难,竭力全面揭示现实中人性的丑恶。可以说,在余华的小说中,看客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人民群众每时每刻每处每地都处于完全裸露的看与被看之中,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癔病。
四、结语
结合跨时代的两个作家的作品中的看客形象,从行为表征到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追溯到看客精神压抑思想“异化”的深层原因——时代环境的造就。无论是余华小说中黑白颠倒的没有情感、没有人性的革命时期,还是鲁迅笔下的家国危在旦夕新旧断裂的混乱年代,都揭示了巨变时代之下的人民群众精神压抑与道德失常的“异化”之态。看客的“异化”是自我人格的缺失,是社会使命的失责。勒维纳斯说过,“从我到我自己终极的内在,在于时时刻刻都为所有的他人负责,我是所有他人的人”[12]。所以对自我与他人负责,是完成人格健全的两个主要因素,看客的人格缺失直接反映出时代信仰与时代精神的批判和理性的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