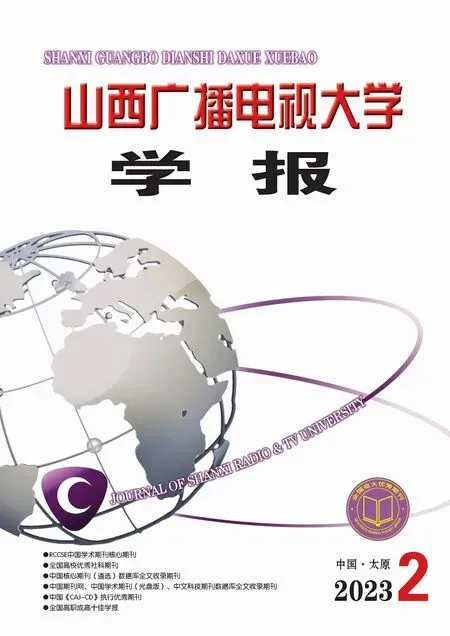论小说《雪城》的意象使用
郭腾雁
(晋城开放大学,山西 晋城 048000)
小说《雪城》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家梁晓声以真实动人的笔触展示北大荒知青的苦乐经历,满怀激情地礼赞逆境中迸发出的人性光芒,几度掀起强烈的阅读和评介热潮。2019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典藏的价值植根于深刻的现实主义,集中表现为悲壮的色调和诗的品格,这一独特艺术美的形成无疑得益于意象的合理使用。
一、用整体意象烘托背景
意象即“寓意之象”,是渗透着主观情感的客观事物,既是我国古典诗词的核心审美要素,也是现代派象征主义等流派的重要表现手段。对小说《雪城》整体意象的使用分析,第一步是全面准确地理解“雪城”的象征意蕴。“雪”的意象和“城”的意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雪给人的感受是多重的,洁白无瑕、晶莹剔透的外观,飘飘洒洒、层层叠叠的状态,冷峻肃穆、寒意森森的特性,让“雪”的意象呈现出多样化的美学风格,严寒与温暖、冷静与激越,多元交织。城从篱笆发展而来,从起初的防范野兽侵扰逐渐成为防御敌人的屏障,从物质方面的居住地演变为精神的栖息地,代表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人文风景。“雪城”这一意象组合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和美学价值,不能简单地对应为东北地区的某座城市,就算小说中有“苏联红军纪念碑”“防洪纪念塔”等地标,也不能用原型来削弱“雪城”这一象与意的有机结合体的典型意义。在期盼返城的知青脑海里,皑皑白雪笼罩下的城市,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家乡,雪城是温馨的,那里有他们的亲人和年少时的青葱岁月。然而当“上山下乡”宣告结束,他们真实地返城了,才真正体会到雪城的冷酷,城市并不欢迎他们,他们成了城市的累赘。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他们忧郁、迷茫、惆怅、失落,他们倔强地捍卫人格,拒绝特权,接受卑微,忍辱负重,挺起脊梁,重新在城市扎根立足,重新找回城市烟火中的温情。从梦幻的温馨到现实的冷酷再到奋斗中的冷暖自知,“雪城”这一整体意象在温度、明暗和色彩上不断变换,显得斑驳陆离,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这样的解读还是过于笼统和表面化,接下来我们尝试与《雪国》《围城》《城堡》等中外典型意象进行对比触发,更为深入地挖掘“雪城”整体意象的独特价值。“穿过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简洁的文字把读者带入虚幻的唯美境界。“好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个白天,仍在下”“天气格外寒冷,零下三十一度”[1]。白描直截展示严酷的冰天雪地场景。不同的雪景之“象”,服务于相应的思想之“意”。“雪国”意象所呈现出的洁净之美、悲哀之美、虚无之美,营造出寂静清冷、空灵悠远的氛围,用极致的美景反衬人物,把美与悲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弥漫着的失意感伤情绪给人深刻的“物哀”感受。“雪城”意象则采用正向烘托的方式,用恶劣极端的天气渲染凝重的悲剧气氛,通过生存环境与个性精神的映衬赞扬“悲壮”之美。“雪国”意象所表现的“往昔徒然空消逝”的颓废情绪与“雪城”意象所表现的“英雄追崇”式的挑战精神反映出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迹。
钱钟书先生以“庸常人”方鸿渐的爱情为主线,“围城”直指婚姻,城外的想冲进去,城里的想逃出来;由婚姻延伸到职业和其他,人生处处是“围城”,得到后的厌倦与得不到的憧憬,这一永恒的困惑带有普遍意义。“雪城”中,北大荒姑娘小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姚玉慧对“最后停泊地”的温馨回忆,刘大文对过往幸福爱情的固执和对好女人的不舍等诸多迷失、绝望、崩溃的情形,都从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生存困境,揭示出更为新鲜的“围城”内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城堡”在雾霭和夜色的笼罩下模糊不清,城堡就在主人公面前,但他费尽心思、终日奔波,至死都未能进入城堡工作。这一“可望不可即”的人生情形是对个人抗争和寻求和解的彻底否定,是悲观厌世情绪的集中表达。“雪城”里返城知青迷惘但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孤独但始终坚守人格的尊严,虽然生活窘迫、生计困难,但他们不屈膝、不卑躬,坚定而执著地守着心灵的自尊这最后一道精神防线[2]。姚玉慧自觉放弃家庭的庇护,顽强地面对世俗的压力,不接受任何同情和施舍,坚守自己的城堡负隅战斗,保卫高贵的灵魂。严晓东在享受金钱物质、贪恋情感欲望、沉溺艺术虚荣的同时,总是缅怀自己固守的人格与道德堡垒。这种自尊与道义的城堡虽然也饱含着挣扎和妥协,但与海市蜃楼般的徒劳追求相比较却是非常积极的。从以上比较不难看出,独特鲜明、内涵丰富的“意象”对文章风骨的确立是多么重要。《雪城》的动人之处正是通过“意象”使用,生动地再现了一代返城知青艰难地回归城市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不甘沉沦的决心[3]。
二、用系列意象构建情节
整体意象为作品中的人物生活渲染出或明或暗的背景底色,同样与人物生活相关的一系列意象也让故事情节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姚玉慧是小说中最先出场的主要人物,也是作者倾注心血和笔力剖析得最为深刻的人物形象。她的六次情感故事让人唏嘘不已,她的本我和超我处在紧张的对峙与斗争之中,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不得不在被时代与政治所异化了的思想观念和本能的生命情感冲动之间徘徊[4]。我们试分析一下意象使用在叙述描绘姚玉慧爱情经历和内心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前三个情感故事采用回忆的方式,姑且概括为“最亲密的女友”“柞树林中的头巾”“雪夜送毛衣”。冬日午后,姚玉慧半醒半睡,枕边的书籍《简·爱》陪伴着她,从中学时代到后来成长为兵团教导员,“简”一直是她最亲密的女友,她在心里与“简”进行严肃的讨论,用日记的形式给“简”写信,她和“简”都不漂亮,她们同病相怜,她对“简”的依恋是她与自我封闭心灵的沟通,“简”就是她自己。《简·爱》这一物象饱含着强烈的独立自尊与倔强抗争意味,这种意味赋予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色,渗透在人物的一切思想和生活中。
作为原兵团的一名营级教导员,作为全兵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标兵,政治职务和荣誉光环遮盖了她的女人味,再加上市长女儿身份造成的高傲和孤僻,使她的情感长期处在压抑之中,对自己的虚伪和空虚感到恐惧,深深地忍受着堂皇的虐待。这种政治无意识毁灭了她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段美好爱情。“柞树林中的头巾”,青春的悸动,对教导员来说是不应该有的情况,面对王亚军火热的目光和亲昵的举动,她言不由衷,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表面说教变成了冷酷的拒绝。“柞树林”“头巾”,还有那长途步行取来的“麦乳精”都化为淡淡的惆怅、缠绵的柔情和尘封的温馨。
六年后,姚玉慧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有了自己的房子,她仍然是孑然一身,顽强地坚守着内心的独立王国,生活仿佛抛弃了她,两室一厅的房子就是她的“城堡”。妹妹的态度,使她的价值准绳松动了,激发她主动求变来拯救自己。心底浮躁的渴望驱使她召来了未婚夫田非,以满足她长期压抑的需要。在迷乱的欲望中,多年前在营长家的相同体验从尘封的意识中渐渐苏醒,她觉着欲火燃烧的自己是多么丑陋,羞耻心在欲望的边缘痛苦地挣扎。孤独的女王不再享受孤独,她买来一只纯种波斯猫作为朋友,猫的高贵执著深得姚玉慧的怜爱和信赖。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猫也招引异性,猫被劁了,姚玉慧连连顿足,继而心生厌恶,失手把它从窗口抛了出去,但这只命大的猫居然回来了,搅得女主人心神不宁。“猫”在这里成了欲望的象征,劁猫的行为实质上是对欲望的人为控制和约束。对于心灵上不能接受的电脑选择的未婚夫就和对这只被劁的猫一样,不能完全没有但又时常厌恶,让她恼恨和无奈。
城市压迫着寻觅不到真爱的老姑娘,每每感到失望、沮丧、困惑、疲惫的时候,她便禁不住缅怀为之付出青春的北大荒,北大荒成为她心灵“最后的停泊地”。兵团管理员的女儿小俊来了,这姑娘浑身焕着勃勃的生命力,为她带来了回忆中的点滴温馨,她对自己还能够喜爱一个人感到惊讶,给小俊无微不至的关心,引导小俊“阅读”城市、领略城市的风情。在与小俊交谈中,姚玉慧听到了营长的可悲结局,知道了“上山下乡”给北大荒人的伤害,感受到了北大荒对知青的不欢迎。更为荒诞的是小俊竟然夺走了她的未婚夫,而且这个管理员的女儿也是冒牌货,可把她给骗惨了。仲夏之夜,姚玉慧周身寒冷,她的“最后的停泊地”飘浮远去。梦碎后的大失落转化成了姚玉慧笔下的“鲑鱼图”,形状古怪的黑鱼,四壁墙上、地上、沙发上到处都是,这是大而黑的绝望。猫和鱼都代替不了一位丈夫,她最终把自己嫁给了一位双目失明、装着一条假肢的战斗英雄,这或许就是她心中景仰的最终的“罗切斯特”吧。
三、用典型意象揭示主旨
意象的典型性可理解为客观之“象”与主观之“意”的约定关系。由于长期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积淀,生活中的万千物象一般固定地指向某种寓意,但伴随着文化的演进和语境的变化,单一固定的寓意逐渐被赋予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单一固定的寓意越来越深邃,多意发散的寓意愈来愈广阔,两种趋向使意象的典型性在深度和广度上均得到有益的拓展。
“桥”这一意象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连接沟通的寓意浓烈。从思想情感的寄寓来看,古往今来,无数作品都凭借“桥”以描绘刻画不同彼岸、不同世界、不同理念、不同心灵之间的联络与分割。宋词中“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鹊桥,千古悲欢离合温暖了桥的灵魂,当代文学汲取传统文学的养分,不断将其引向大众化。路遥在《人生》中巧妙地运用“大马河桥”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把现实与理想联系起来,把屈服与抗争联系起来,在平淡的叙述中再一次彰显“桥”的魅力,给同时代的创作者以有益启示和无声鼓励。
在小说《雪城》中,作家梁晓声也借助“江桥”意象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哀婉曲折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小饭馆邂逅,如今的晚报记者吴茵激动地紧紧握住了当年校冰球队长的手,久别的重逢弥漫着惆怅。吴茵把因打架被拘留的王志松哥们仨解救了出来,他没理由不陪她走走作为报答,一路无言来到江畔边江桥下,江桥把他们带回尘封的过往。江桥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他和她曾一块儿从它身上走过,那是她第一次过江桥,他像大哥哥一样哄她长大后爱她。十一年了,对于这份纯真的情愫他亏欠得太多,江桥在夜色中沉默,他挽起了她的手臂再次同步踏上了江桥,走进它沉睡的梦境。冰封的江面像睡美人,江桥像巨人的手臂拥着美人入睡。她渴望他的救赎,但得到的却是彻底的绝望。月光下的江桥震颤了,伤感的梦境破碎了,在命运的摆布下她太想自由自在地飞翔,太想回到少女的时代。
真爱像一束光感召着男女主人公,他终于省悟亏欠她的太多,她的囚禁在幽暗冰冷命运牢笼中的灵魂终于看到了光明,两只被抚乱的棋子冲破舆论的压力,不惜失去工作,义无反顾地跨越“意念束缚之桥”和“拥抱真爱之桥”。婚后的生活并不是向往的新生活,朦朦胧胧的糊涂一团,庸常地累人。对于丈夫的圈子和信仰的种种改变,她有过怀疑和不满,对于生活本身和爱情本身的残缺不全的深切体会,让一切的抱怨变得释然。然而他的一篇沽名钓誉文章、他的凭借出卖亲情往上爬的行为最终成为压倒爱情与婚姻的最后砝码。温柔的雨夜,她再一次来到江桥,她想走到对岸的黑夜中,去破解人性之谜。她紧紧抓牢水淋淋的铁栏杆,在死亡冲动和生活继续中作着艰难的选择。江桥同样见证了爱的裂痕和婚姻的名存实亡。
典型意象的多义性在小说《雪城》中集中表现在“孩子”这一意象上。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末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深切呼吁,孩子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救救孩子”体现出了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雪城》传承了“五四”以来“为人生”的文学价值追求,赋予“孩子”这一典型意象更为特别和丰富的内涵。
小说《雪城》中的孩子是一个弃婴,是北大荒知青的后代,这样一个孩子首先象征着“错误”和“问题”,反映了知识青年中存在的不成熟和责任心缺失现象,同时也象征着“良知”和“担当”,北大荒知青的后代不能没有爸爸和妈妈,正直的知青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高度的思想一致和行为默契,在相互帮助抚养、教育、保护孩子的艰辛过程中,对知识青年闪亮美好的人性给予了热情的讴歌。
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扩大了“孩子”意象的内涵。“孩子”造成了误解,郭立强误把宁宁当成了王志松与徐淑芳爱情的结晶,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才有了“婚礼上燃烧的花圈”,所以误解发生后,他坚持与徐淑芳保持距离,迟迟不能再次接纳她。通过对误解描述和处理,使小说的故事情节陡生波澜,也折射出每个涉事知青高尚的伦理观念,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孩子”是吴茵与王志松夫妻爱情天平上的砝码,她满怀热忱想做一位爱别人孩子的好母亲,但孩子只把她当作“姨妈妈”,她必须从内心克服丈夫、徐淑芳,还有宁宁生父生母所造成的心理干扰,培养起母亲对于孩子的特权,从而保持夫妻情感的浓度。“孩子”是知青联盟的盟主,他将一干返城后的知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谁胆敢违背道义和责任,他们将投以鄙视甚至一顿痛揙,哪个若企图认领孩子,他们将团结一致、出钱出力,想尽办法把孩子保护好。
意象就像一把开启寓意之门的钥匙。小说《雪城》中除了“江桥”“孩子”,还有许多思想蕴含深刻的典型意象。林凡临死托付战友送给妹妹的“白桦树皮帆船”模型,闫晓东新房里摆设的“维纳斯”雕像、“波琪儿”油画、猫头鹰标本,姚守义手里又红又大的山楂,徐淑芳背上沉重的木箱,刘大文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爱人照片,还有兵团服、羊剪绒帽子等。这些事物无不浸染着作家的情感,铭刻着时代的烙印,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