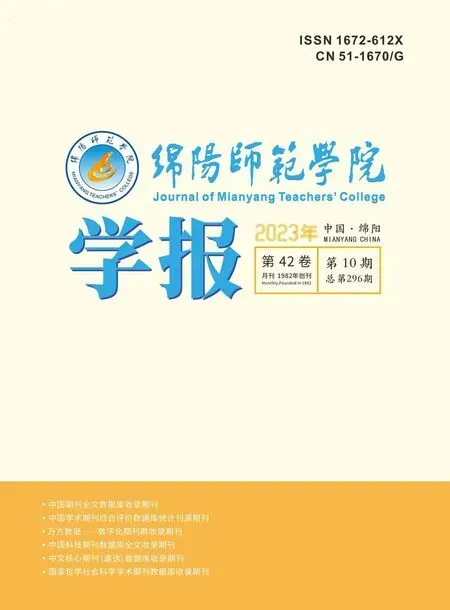从加拿大土著语言政策变迁看土著文学的发展
左丽芬,杨建国,孙芳丹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加拿大土著民族,包括第一民族(以前称为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及梅蒂斯人,是加拿大的原住民群体,一直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其文学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记录着历史的变化,值得人们关注和探究。无论什么文学都需要以语言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语言是文学表达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文学实现的载体。因此,语言的发展变迁或多或少会展现以该种语言文字传递的文学发展变迁史。
一、加拿大土著语言的发展变迁
加拿大土著语言的发展经历了建邦前与外来语言的自然碰撞与融合,联邦政府成立后殖民统治时期的强制同化政策下的压制与清除,土著民自我觉醒后多元趋势下的有限自治,与现在的多元文化下的尊重、保护与自我发展。加拿大土著语言拥有这一发展历史进程实属不易。
(一)建邦前的融合与伙伴关系:语言的自然碰撞与融合
“大多数土著人是自愿而不是被迫把食物与知识分享给那些白人……直到19世纪下半叶,白人移民开始大量涌入,土著人才明显感受到来自白人的威胁。”[1]11由此可见,外来的欧洲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最开始的关系是和谐的,加拿大土著语与英语、法语在白人到来的早期是自然地碰撞从而相互融合。
当然,早期的欧洲人与土著人能够进行和谐的贸易,其中不乏联姻为自由贸易铺平了道路,也为加拿大土著语与外来语言的自然融合提供了平台。其中,毛皮贸易商娶土著女人为妻,生下儿女,最为常见。如西海岸第一个发表土著文化作品的女作家玛莎·道格拉斯·哈里斯,她本身是皮货商和土著民结合的后代[2]3。《温哥华传奇》的作者埃米莉·保利娜·约翰逊,也是白人与土著民的后裔。回忆录《从冬季赠礼节到讲道坛:威廉·亨利·皮尔斯自传》的主人公威廉·亨利·皮尔斯,其父亲是苏格兰毛皮商,母亲是钦西安人(属印第安人)。然而作为北美印第安人和白人结合的后代,他们的身份模糊、尴尬而糟糕,没法融入白人社会,又受印第安人排斥,他们一直遭受歧视,没有归属感,这一点从莫林·达夫的作品《混血儿科吉维》和亨利·彭尼尔的回忆录《印第安人》中的描写可以体现。
由于早期很多土著语言只有口语,没有文字,他们也惧怕书写。在这一时期,外界对土著人的了解是通过一些所谓的“媒介人”“中间人”。如作为文化相对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弗朗兹·博厄斯曾经把加拿大的土著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加拿大中部的因纽特人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北沿海的群体人群进行人种学研究。在此期间,作为“中间人”的乔治·亨特一直为他工作,帮助其收集资料。沃尔特·赖特曾作为中间人为威尔·鲁滨孙(Will Robinson)提供资料,才有了后来的《梅迪克人》(1962)。像这样的“中间人”还有查尔斯·埃登肖、詹姆斯·贝农、查尔斯·诺埃尔等。
这些土著人与白人一起合作实现有关土著文化方面的研究或进行土著文化方面的文学创作。他们对土著人形象、土著文化的塑造更多地倾向于满足白人读者的需求,因此,大多关于土著人的形象不够真实或者是被扭曲了的。可以说,这一时期加拿大作家对土著文化进行了妖魔化叙事,通过丑化土著文化,扭曲掩盖殖民历史。
随着大批欧洲人的涌入及欧洲市场对皮草只增不减的需求,毛皮贸易彻底改变了加拿大的经济,与之一同改变的还有土著语言的生存环境,这让土著人感受到一种外来的威胁。
(二)联邦政府对土著语言政策:鄙视—压制—清除—反弹—尊重
加拿大政府对加拿大土著语言的态度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从早期的鄙视,企图通过英、法两种主流语言的强势入侵,强行同化,对其压制、清除,使得部分土著语言濒临灭绝,到土著人民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获得教育自治权,使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语言教育,再到采取保护措施,开展社区语言教育项目及计划,逐步尊重土著语言,加拿大土著语言发展经历了“鄙视—压制—清除—反弹—尊重”的发展过程。
1.殖民统治时期的土著语言政策:家长式的教化和强制同化。在白人的眼中,土著民既无知又迷信,既野蛮又残忍。为了迫使土著民尽快走出所谓的“野蛮”社区,进入“更高的文明”,从而融入欧洲主流文化,在加拿大政府的推动下,特别是1876年由加拿大议会通过的《印第安法》加持下,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应运而生。“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和教会共开办了130多所基督教寄宿制学校,15万土著儿童被迫进入寄宿制学校就读。”[3]为了强制同化土著民,政府剥夺了他们接受土著语言教育的权利。在寄宿学校,土著语被禁用,一并被禁的还有所有的土著文化习俗。违反规定使用土著语的学生将被隔离、处罚。在寄宿学校,土著民的孩子被强行灌输基督教文化。这一时期,土著文化遭受严重摧残,有些土著语言一度濒临灭绝。土著孩子被迫与家庭分开,经历各种不平等的对待,包括长期营养不良,遭受身体、精神甚至性虐待。寄宿学校强行切断土著儿童与土著语的联系,试图抹去土著人对自己语言、身份、文化的认同感。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对土著语言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土著孩子在成长中自信心的建立及自我身份认同感的确立。由于土著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被剥夺,他们被强制要求学习并使用英语,随之改变的还有土著民运用英语进行自我创作的能力,同时,印第安人寄宿学校也为后面的土著文学创作提供了创作主题,后来产生了不少有关这一时期该主题的土著文学作品。
第一个获得艾戈夫奖的土著作家雪莉·斯特林把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坎卢普斯寄宿学校的经历写成小说《我的名字叫西皮扎》。类似描述寄宿学校对土著民孩子不公平对待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厄尼·克雷在《从我们的怀抱偷走的:诱拐土著民孩子和重建土著民社区》中分析了加拿大主流社会大规模同化土著民带来的灾难;玛丽·劳伦斯在自传《我和我的民族》中回忆了自己在寄宿学校的经历;维拉·曼纽尔的《印第安女人的力量》也有涉及到关于寄宿学校时期被关禁闭的秘闻;罗兰·克里斯约翰、雪莉·扬和迈克尔·莫兰合著的《围猎》(2002)记载了寄宿学校对土著儿童极其非人的惩戒方式。
2.自我觉醒下的抗争:多元趋势下的有限自治。20世纪6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逐步觉醒。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69年颁布《官方语言法》(OfficialLanguageAct)。在该法案中,英、法两种语言一同被确立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并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该语言政策的影响下,其他各民族的移民因为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或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强烈要求政府保障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与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联邦政府为寻求新的策略以满足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强烈要求,最终于1971年10月8日推出了“在英法双语框架内主张各民族文化平等共存的多元文化政策”[4]。这一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与推进也为加拿大土著语言后期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土著民族自主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文化自由理念”开始萌生,争取平等语言教育权利的诉求也愈发强烈。由于对西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土著人希望自己创办或掌控属于自己的学校,并在学校开展一些土著语言项目。在加拿大土著人的不断抗争下,他们享有了保护和发展本族语言的教育权利,土著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逐步合法化。“1970年9月1日,布鲁奎尔斯学校正式成为加拿大第一所由土著人掌控的学校。”[3]加拿大联邦政府最终于1973年通过了土著民教育自治的建议,土著民终于获得了教育自治权,摆脱了只能使用英语或法语教学的殖民语言政策,逐步走上有权管理自己民族语言的教育之路。通过加拿大土著民族语言教育管理权的调整,土著人开启了保护和发展本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发展进程。198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问题,并指出少数民族儿童有权利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5]。政府也意识到尊重土著民族语言、保护其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校开设土著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方面的课程,专门为土著民族语言学习培养师资。为了提升土著儿童的教育,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如直接聘用土著民族教师或聘用懂得两种语言的教辅人员参与协助教学。在语言教育资源开发方面,也采用相关保护政策,如开展祖裔语言(heritage language)教育,进行相关的土著语教材、课程体系开发,在社区开展语言教育项目。198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重新修订了《官方语言法》,强调除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并“规定各学校有责任和义务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多种语言教育或双语教育”[5]。
为了保护、复兴土著语言,进一步提升土著语言的地位,加拿大政府在土著民族社区和各大院校开展各种土著语言复兴的项目。例如:菲利斯·切尔西在各大院校复苏舒斯瓦普语,并编著了《学习舒斯瓦普语》;1974年第一部卡里尔语(Dakelh)词典《内卡里尔双语词典》出版;1988年致力于保护、发展因卡·迪恩语言文化的因卡·迪恩语言学校成立。在这些语言运动中,加拿大土著语言获得尊重,受到了保护,随之一并得到保护的还有土著文化。在提倡多元文化政策的土壤之上,土著文学得以生根发芽并迅速成长。土著人逐步掌握了发展变化的英语,也有能力用英语进行创作,他们不再需要媒介,自己直接与白人进行对话。198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土著人拥有了自己控制经营的出版公司。对土著人而言,他们需要自己出版书籍,因为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在出版过程中可能会遭到误解或被拒绝。
二、语言政策发展变化下的土著文学
文学从另一个层面记录着加拿大土著语言的发展历史,加拿大土著文学作品不乏土著人与白人抗争的烙印。赛克韦佩姆诗人戈特弗里德松曾指出,土著人大多数情况是在与语言斗争,通过掌握英语来完成写作这一文学活动,然而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充满挣扎。那些土著作家,从通过口述、替白人收集资料、与白人合作撰写文学作品、到自己学习英语,逐步自我掌控出版文学著作,这一历史进程也折射了加拿大对土著语言采取的相关政策。从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土著语与外来语言的融合过程,看到土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极强的忍耐力,看到土著人都市化自信心的崛起以及土著文化的重生与在土著社区内部的自我传承。
(一)最初的荒原之声时期
早期的加拿大土著文学启蒙于土著民族传统的口述故事以及各部落的宗教活动。作为皮货商与土著民的后裔,或称之为梅蒂斯人的后代,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土著文化影响,他们混血的身份为其接触土著文化提供了便捷,有的把从老一辈听来的土著故事翻译出版,有的通过由土著民口述与白人合作撰写得以发表,这些最初的荒原之声有关于神话传说、民族故事传奇及记录历史事件的小说、自传及诗歌题材。埃米莉·保利娜·约翰逊的诗歌集《白色贝壳》(1895)中的土著文化主题内容不多,但在早期算得上是突显了土著文化的文学作品。《考伊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民间传说》(1901)就是拥有混血身份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女作家玛莎·道格拉斯·哈里斯把原本口述的土著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比埃米莉·保利娜·约翰逊的《温哥华传奇》早了十年,其中不少故事就是“她从拥有一半克里族血统的妈妈那里听来的”[2]3。书中的民族故事记录着人类对超自然事件及神秘世界中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这些传奇故事通过文字记录下来或多或少失去了由老人讲述时的精彩,但其为土著文学后期的发展提供了萌芽的土壤。乔治·亨特为德国人类学家法兰兹·博厄斯收集的土著人讲述的故事就出现在博厄斯的《杰瑟普北太平洋探险》中。正是因为有夸扣特尔族长查尔斯·诺埃尔与耶鲁大学的克莱伦·福特的合作,才有《烟源于火:夸扣特尔族长的一生》(1941)的诞生。威尔·鲁滨孙的作品《梅迪克人》(1962)也是从土著人沃尔特·赖特讲述的部落历史改编而来。这一时期的土著文学作品的出版权不在土著民的手中,出于迎合白人读者的需求或由于故事收集者的个人喜好,有的作品被篡改,许多怪诞的土著故事被排除在外,例如莫琳·达夫的《草原狼的故事》(1933)是在麦克沃特的帮助下才得以出版,其中“莫琳·达夫大多数作品被编辑过度美化而改得面目全非”[2]21。
(二)伴随殖民历史和不断抗争的文字书写时期
随着英、法两种语言的强势入侵和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系列殖民政策的加持,土著民族自身的意识形态遭受冲击,原生态的土著语言文化遭到强制破坏,这一时期的土著文学作品因土著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这种被迫与土著文化、民族语言及传统生活方式的分裂与隔绝,从某种程度来说加速了土著文学的成长与崛起,刺激并丰富了土著文学的创作。
加拿大土著文人把自传与小说融合、通过口述与人合作写回忆录、自传等。他们通过这种自我书写为加拿大土著文化发声,企图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身份,其中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当属拥有萨利什和克里血统的土著作家李·玛拉克尔的自传体小说《博比·李,印第安人的反叛》(1975),书中讲述的是反抗正统文化团体的故事。她劝诫加拿大人应该“了解殖民掠夺的含义,弄清怎样才能让殖民掠夺完全消失”[2]50,这是土著民对抗殖民历史的文字书写。这类以个人经历或家族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回忆录还有:有关族长丹·乔治的《你称我为族长丹·乔治的生平》(1981)、彼得·韦伯斯特口述的自传《我所知道的一个阿霍塞特长者的回忆》(1983)、因卡·代内语言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玛丽·约翰与奇特·莫兰合著的《斯托尼·克里克女人:玛丽·约翰的故事》(1989)、理查德·玛洛威口述的《故事讲述:理查德·玛洛威族长的一生》(1994)、柯克尼斯和西蒙·贝克合著的《热拉·查:西蒙·贝克族长的自传》(1994)、海达族最富盛名影响力的女性弗洛伦斯·埃登肖·戴维森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弗·布莱克合著的《我的时代:海达族女人弗洛伦斯·埃登肖·戴维森》等等。
记录土著民族不断抗争书写的另一主题是土著民口述的部落历史事件。他们用英语记载和整理这些带有民族、部落特色的口述故事,追忆民族历史与特色,同时记录部落的信仰、风俗。例如,黛西·塞韦德·史密斯的《起诉还是破害》(1979)记录了禁止冬季赠礼节法令执行后夸扣特尔族财产被充公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类似的还有记录吉特克桑和威特素威特恩族提出的土地诉讼案件的《审判中的殖民主义:土著土地权和吉特克桑及威特素威特恩人的领土案》(1991)、由哈里·鲁滨孙讲述、威克怀尔编撰的《用心铸成:史诗世界的奥卡诺根语故事讲述者》(1989)、《自然的力量:奥卡诺根语故事讲述者的精神》(1992)等。他们企图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唤起人们了解真正土著民的文化、生活及信仰,唤起民众对加拿大土著民的倾听。
在诗歌方面用文字书写来反抗殖民统治的土著作品也不少:格雷戈里·斯科菲尔德在《聚集》(1994)中有对梅蒂斯人的深刻见解;格雷格·扬·英在《血流成河与花》(1996)中展现了殖民主义、梅蒂斯人的尴尬地位及遭受种族歧视等相关主题;诗集《反抗有色人种》(1994)的作者康妮·法伊夫在《母亲的儿子》中控诉雅各布斯因拒绝把孩子交给社会福利院而遭加拿大骑警枪杀事件,她在诗中抗议到:“如正义的人们一样我凝望着/指责他们对你的谋杀、指责他们袭击你的血肉......”[2]89
(三)为自己发声的土著文学时期
在加拿大开始走向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土著文学也逐步走上了为自我发声之路。代表北美土著民文学的期刊《集会》的出现,格雷格·扬·英参与编辑的《土著批评:土著人的视角看土著文化》(2001)的出版,都象征着土著民的觉醒与土著文化的复兴。《我们就是历史:海斯拉族遗产赞歌》(2005)的出版则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一历史进程,展现了土著作家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定位,以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肯定与认同。例如,《回归的羽毛:五个吉克桑族的故事》(2004)的作者M.简·史密斯从一开始怀疑传统故事的真实性,不愿意承担记录传统吉克桑族故事的责任,到发自内心接受并相信这些故事,对“这些故事像族长的徽章一样需要珍惜和保存”[2]137表示尊重。再如,努恰纳尔什族世袭族长E.查理德·阿莱特奥在《察沃克:努恰纳尔什族人的世界观》(2004)中向人们介绍了努恰纳尔什族故事中的本体论及努恰纳尔什族人对宇宙的自我理解。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土著民族文化自信心崛起的表现。
还有大量土著文学作品通过对部落族长的个人经历的记录来追忆自己民族部落的发展历史与传统文化,以此重建土著民的精神家园,找回自己的民族归属感。例如,第一本描述瓦卡瓦卡族女族长的传记《划向我站的地方:贵妇阿格尼斯·艾尔弗雷德》(2004)、西蒙·贝克与韦尔娜·寇克妮斯合著的《科特拉恰:西蒙·贝克族长的自传》、查尔斯·琼斯与人合著的回忆录《帕切纳特的世袭族长:奎斯托》等。其中《帕切纳特的世袭族长:奎斯托》,因其出版时查尔斯·琼斯尚健在,书中记录的大量温哥华土著民生活及习俗作为更真实的一手资料被保存下来,而更具价值。
另外,不少土著作品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探讨城市生活中的困惑与迷茫,并开始思考现实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土著民族问题。例如,克里斯·博斯的小说《地狱》(2004)讲述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在面对现实存在问题及文化适应困扰时的挣扎。伊登·鲁滨孙的小说《血腥的户外运动》(2006)便是以温哥华市为故事背景创作的。新生代比较有影响的土著民首领杰拉尔德·泰艾阿克·艾尔弗雷德在《和平、权利和正义:土著民宣言》(1999)和《瓦萨塞:土著民的行动之路与自由之路》(2005)中就有对现在的土著民族问题的思考。玛丽·克莱门茨的剧本《愤怒的真相》(2003)揭露了西北地区土著矿工被骗去挖生产原子弹材料的矿石,却告知挖的是一种用于治疗癌症矿石。该剧本揭露了旷工死于癌症的真相与高辐射矿及联邦政府无作为脱不了关系。
无论是最初的没有自主权的荒原之声,还是伴随殖民历史和不断抗争的文字书写,或是后来为自己发声的土著文学,这些作品以不同体裁、不同主题,向世人展示了土著文学从萌芽、成长到逐步呈现于人前的自由蓬勃发展,这一路充满了荆棘与不易,并落下了联邦政府对土著民语言政策的痕迹。
三、小结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土著语言从一开始的鄙视,试图清除、压制,到土著民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反抗与争取,到最后获得尊重,其语言与文化得到保护,使其在土著民社区得以内部继承。加拿大土著文学也由最初迎合白人口味的荒原之声,到伴有殖民历史和不断抗争的文字书写,再到重获自主权,精神上的去殖民化,为自己发声,重新构建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似乎是其文化抗争及语言政策下的发展规律。加拿大土著文学的发展之路或多或少展现了加拿大政府对土著语言的政策。然而,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其民族文学的生存将得益于其民族文化的存在而发展。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当是民族语言多元并存与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加拿大对土著民族管理自己的语言教育给予的极大自主权,特别是土著语言教育权利保护与语言教育资源开发方面对促进加拿大土著文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