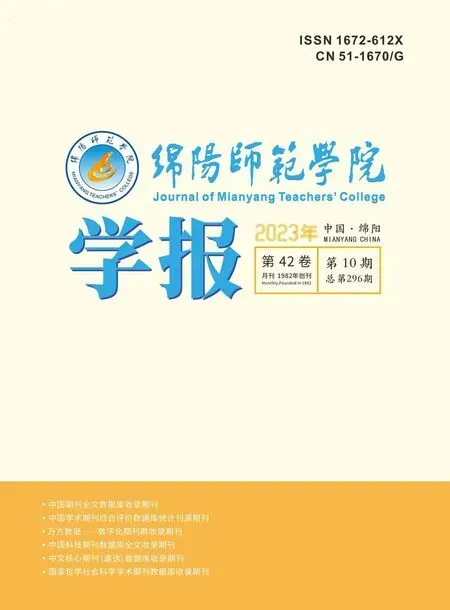论古尔纳《赞美沉默》的讽刺艺术
陈虹霏,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赞美沉默》是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于1996年创作的一部英语小说,小说中的叙述者既向英国家庭编造过去在桑给巴尔的经历,也含混地向原生家庭透露自己在英国的生活,在社会裂缝中的挣扎使他最终与两方家庭关系断裂,小说以此展现了文化夹心人的现实处境。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小说中展现的后殖民图景、身份焦虑主题受到了较多关注,这些研究为理解本部小说的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而从艺术形式角度分析讽刺话语仍有较大探讨空间。相较于古尔纳大部分作品悲怆沉重的风格,这部小说将反讽、戏仿、悖谬三种技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含蓄而戏谑的讽刺风格,形成了古尔纳这本小说独特的风格统一体。因此,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讽刺艺术也值得关注。通过以讽刺性语言的呈现为切口对小说进行解读,能够分析讽刺性语言的呈现方式及文本意义,进而有助于明晰这部小说独特的创作风格,并将其纳入对古尔纳总体创作风格的关照之中。
按照黑格尔在《美学》中的定义,讽刺是指“以描绘这种有限的主体与腐化堕落的外在世界之间矛盾为任务的艺术形式”[1]267。《赞美沉默》中的讽刺可以被理解为叙述者与言说对象的矛盾,正因为叙述者独特的文化身份,他在对话与讲述中常常表达对异己的批评。小说中的讽刺是通过不同的技巧呈现出来的,按照艺术形式可以大致将这些技巧分为三类:反讽,戏仿,悖谬。这三种技巧在交叠与融合中运用,它们一并构成风格总体,其共同特点都是以讽刺作为核心意义与主要目的。
一、反讽:展现身份的隔阂疏离
反讽(irony)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2]333,即在特定的语境中,语言的实际意义潜藏在文本下,并与字面意义对立,通过此类反语对对象进行讽刺。小说的叙述者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在英国,由于文化的差异,他难以真正接纳并融入英国的社会文明。叙述者既讲述在自己所处的英国家庭中难以与女友爱玛、自己的女儿以及爱玛的父母融洽地相处,也袒露了自己重返故乡桑给巴尔时的失望。在从桑给巴尔返回英国后,他与爱玛的关系完全破裂,以沉默的方式面对自己破碎而断裂的文化身份。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叙述者受制于这种身份为他带来的社会关系,他只能在言语表层认同英国社会所渗透的文明,并通过反讽的方式,委婉地向读者传达他实际上的抵牾情绪。
(一)对英国文明的反讽
在游历了作为后殖民地的故乡桑给巴尔并与爱玛关系破裂后,叙述者曾在英国参与水暖课程的学习。在讲述水暖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对于储水湾马桶这一源自英国的发明创造抱有嘲讽与不认同的态度,通过言语反讽,叙述者嘲讽了英国的学术发明和传统。他追溯了水暖系统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篇在道德层面讨论有关我们水暖行业所谓水体废物的产生和处理的学术论文,这是一种丝毫也不可笑的智慧,但你依然不能剥夺此人的赞誉,因为他是继古罗马人之后,第一个系统思考这个问题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的人。”[3]248从文本表层含义上来看,叙述者似乎在赞扬约翰·哈林顿爵士的学术研究价值,他的学术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从未被研究过,具有空前的创新性。但文本深层却传递出相悖的一套信号:道德层面的讨论对于处理废水排放问题毫无用处,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真问题。结合本章节开头的引文,可以更好地理解哈林顿爵士其人。本章开头引用了哈林顿爵士的《戏剧论》一文:“我们衣着光鲜亮丽,想要被当作更好的绅士看待,我们使用很多垫条和村里,以显得体型更匀称、肩膀更宽阔、腰身更苗条、大腿更结实,我们经常刮胡须,以显得更年轻;我们里外都喷上香水,让自己更好闻;我们穿上木跟鞋,以显得更高大;我们礼貌地行礼,以显得更友好;我们低贱地顺从,以显得更谦卑;有时我们在交谈时庄严肃穆,以显得更睿智也更虔诚。”[3]203此处的引用暗含着对他的讽刺。首先,引文内容和引文标题并无关联。根据题目的命名,文章本应讨论与戏剧相关的话题,但引文却满是对英国人外在衣着与气质的描写。其次,引文的行文逻辑表明了哈林顿爵士的思维逻辑。这七个并列的句子都采用了相同的句式,即“我们如何做,以达成某个目的”的基本格式。在前半句,哈林顿爵士都提出了对于外在行为的建议,注重人在表面的包装;后半句的目的则指向内在的、抽象的品质。从这段引文的逻辑可以窥见哈林顿爵士的思维逻辑,即外在物质是先决条件,由此就能拥有内在的精神,他以象征的方式来对众多事物做出抽象化的阐释,反而体现出他内心的虚伪。根据小说中的引文,并结合实际语境对这一段看似赞扬的话进行思考,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反语。“丝毫也不可笑”表面在说这篇论文具有令人敬畏的智慧,而道德与工业技术的耦合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第一个”看似在强调爵士的开创性地位,但正是因为这篇论文探讨的问题没有实际价值和效用,前人才不会对此进行研究,这个词语由此沾染了一层贬低的含义。从文本深层含义来看,既否定了哈林顿爵士的学术水平,也消解了他的学术创新性。由后文可知,这个问题在英国人使用了两百年夜壶之后,被钟表匠詹金斯真正解决。从身份上来看,爵士与钟表匠的对比十分强烈,哈林顿爵士是一位正经的绅士,曾于剑桥大学学习,并翻译了众多文人的文学作品,却写了一篇毫无价值的论文,还能够赢得赞誉;而钟表匠则在英国的一片郊区中实现了带储水湾马桶的真正运用。通过点明身份的差异与悬殊,足以彰显叙述者对于前者的讥讽。
(二)对爱玛的话语进行反讽
叙述者也通过情境反讽和戏剧反讽,对女友爱玛身上的学究气质进行揶揄。爱玛是专攻叙事学的英语博士,在日常对话中经常融入学术式的言说,她会反复打磨词汇以让叙述者折服于她的睿智。
首先,爱玛的话语产生了功能障碍(malfunction)。叙述者详细地向爱玛编撰了“舅舅”哈希姆促成叙述者父母的婚事一事,而在结婚后,由于“舅舅”哈希姆、叙述者的姑姑不断介入这段关系,叙述者父母的关系陷入了僵持的境地,最终父亲离家出走。在听闻叙述者的父亲从成婚到离家的故事后,爱玛以学者的姿态对父亲婚后痛苦与压抑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她认为一是对更多女性欲望的压制,二是恋母情结的不及时解决。可见,爱玛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以人的欲望为核心,对一个陌生的、被转述出来的事件进行套用。而实际上,父亲的忧郁与出走是叙述者一直无法理解的事情,在他返回故乡后,经过与家人的谈话、对现状的观察,他发现父亲是为了逃离毫无希望的家庭、摆脱衰败零落的桑给巴尔岛。叙述者将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延迟揭露,读者在阅读到小说末尾时,会发现爱玛的推测完全与事实相悖。反观此前爱玛的姿态,叙述者看到的是“她朝我猛地点头以示胜利”[3]61,“胜利”体现的是两方之间的关系,一方的胜利必然带来另一方的失败,这个词语表明爱玛的推测胜过了叙述者在当时的不解,而联系后文可知,这个词实则体现了强烈的反讽意味,看似合理的精神分析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阐释,爱玛的分析其实是失败的。
除此之外,叙述者以戏剧反讽的方式揭露了爱玛认知的疏漏。他曾向爱玛讲述了他从桑给巴尔来到英国的起因及过程。在家人为他寻找在英国的联络人时,母亲提到她找到了叙述者的生父阿巴斯的地址。此时,爱玛曾激动地打断他,并说出自己的发现,叙述者却做出如下举动:“但我挥手示意让她住口。你要知道,我告诉她,一则叙事必须有延后。”[3]91延迟是叙事学中的成规之一,通过对爱玛插话的阻止,他暴露了讲述故事时遵循的叙事技巧,不仅使得被嵌套的故事具有了文本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暗示了现实对话中爱玛的疏漏。作为研究叙事学的博士,爱玛对于叙述者采用的叙述惯例反而无法察觉,此处叙述者和读者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共谋,对爱玛的疏忽进行反讽。但叙述者对叙事学成规的使用意图仍然值得深思,他讽刺爱玛并未意识到叙事技巧仅是表象,其实际意图是对她在生活中的学术式言说的反感,她常以学究式的眼光将两人阻隔开来,以显示她自己的话语权是强于叙述者的。这一行为虽然充满戏谑与嘲讽,但其背后隐藏的是由爱玛制造的阻隔而带来的不适感。
二、戏仿:反抗潜藏的宏大叙事
戏仿(parody)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概念,琳达·哈琴将其定义为:“带着批判距离的重复,允许在有相似性的核心部分发出差异的讽刺信号。”[4]26戏仿最重要的特征是模仿,它的生成一定是基于一个前文本,并通过表达与之相反的含义,使得当下的文本与前文本产生对照,以讽刺前文本。
通过观察小说中几位英国人的话语,可以发现其中潜藏着宏大叙事,叙述者在面对这些话语时,为了能在社会中继续维持自己与英国人的关系,没有直接进行反驳,而是夸张地重复这套话语,以戏仿的方式体现自己因为话语与英国人的疏离。宏大叙事是指“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5]4。具体到这本小说中,宏大叙事是由英国作为发话者,向受话者非洲确立的一套话语规则。英国所构建的“自我-他者”这一话语体系,既包含英国对非洲的想象,也是对两者权力强弱的隐喻。一方面,叙述者的戏仿行为以历史中确乎存在的这套话语作为前文本。根据《未存在过的非洲:四百年来英国人是如何描述非洲的》(TheAfricaThatNeverWas:FourCenturiesofBritishWritingAboutAfrica)中的研究,在16—20世纪,英国人眼中的非洲一直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野蛮自然、原始落后,又宛如空白的噩梦,需要英国人的殖民与驯化[6]。在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传记中,他常用“贫穷”一词对当地人民进行刻画,并记录了他们野蛮的生活方式。在1869年他与儿子的通信中,他写下在非洲探险时与非洲部落的人对话:“他们给他看了一个最近被吃掉的头骨……那是一个大猩猩的头骨,在这里被称为‘索科’(soko),他们确实吃这个。”[7]394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电影中,英国人也以“蛮荒”来想象非洲人,“从来没有非洲人参与烹饪、工作、吃饭或睡觉等‘正常’行为的形象……非洲自然人被构造成一种野蛮、嗜血、吃人的野兽”[8]。此外,英国殖民者认为,他们的各种行为是为了将非洲居民“引入人类更高级阶段”[9]489。黑人克劳瑟在英国受训后也接受了这一套话语规则,公开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辩解:“非洲既无知识,又无技术……去开发其巨大的资源以改善自身状况。因此,主张非洲仅为非洲人所有,实际上是让非洲继续受到忽视……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一个民族永远也无法超越现在的状态。”[10]323另一方面,文中众多英国人的话语都是对宏大叙事的生动演绎,例如医生由心脏病推测出叙述者的族裔、爱玛屡次在争吵时认为是她给叙述者带来了神圣的婚姻。叙述者通过模拟发声的方式对此类宏大叙事进行了模仿与颠覆。
(一)对刻板印象的嘲讽
叙述者对刻板印象进行了嘲讽。在小说开篇,叙述者便讲述了自己因为身体不适前去诊所就医。在面对英国医生简单暴力的问诊方式时,叙述者以戏谑的态度模拟了英国人对非洲人妖魔化的认知,重言刻板印象。他向医生讲述他“早餐喜欢青香蕉和熏猴子”[3]10,“青香蕉”即还未成熟的香蕉,“猴子”也并不属于文明社会的食物,将上述两类食物作为早餐,意味着野蛮与血腥,这是在表面上忠实于英国人对非洲的想象。而在后文,叙述者内心的独白中,他陈述自己突发奇想,本想讲述更加古怪而原始的故事:他们会通过手淫改善猴子的肉质。“突发奇想”即叙述者即兴生成的想法,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描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在这些荒谬怪诞的虚构中他是在戏耍英国医生,对于刻板印象的模仿实则是在嘲讽这些话语。这就可以理解此前与医生的对话中,叙述者以错位解读的方式,对多类刻板印象进行幽默的讽刺。医生听闻早餐的内容后十分惊讶,他没有将其理解为是对他早餐的奇异血腥而做出的反应,而是理解为“毫无疑问对我居然没有食品供应不足问题而感到惊讶”[3]10。叙述者非常肯定地认为,医生眼中的非洲是贫穷的,因此他惊讶于非洲竟然可以供给充足的早餐。早餐中的青香蕉与熏猴子,在此处不再指向人与食物的关系,而是转向数量上的考量,从野蛮与血腥的意义转向了食物供应充足的意义。通过对医生想法的语义转换,他将原本戏仿“非洲人很野蛮”的刻板印象,转向了“非洲人很贫穷”这一语义上来。无论是以何种意图对叙述者的戏仿进行理解,医生竟在短暂的惊讶后,选择相信叙述者的话语,可见在医生潜藏的思想中,此类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对于这件事情的描写,不仅表现了话语的力量:这位英国医生愿意相信未经证实的言语,从而构成他对非洲的想象,也对刻板印象的加固过程进行了一次即兴演绎。
(二)揭示帝国故事的虚假
叙述者也揭示了帝国故事的虚假。从故乡桑给巴尔来到英国之后,叙述者与女友爱玛的父母有过多次交流,他讲述了自己与爱玛的父亲威洛比先生在用餐期间的对话,在此过程中,他向威洛比先生虚构了无数动听的帝国故事,但这些帝国故事实则与现实相去甚远。叙述者对酒吧进餐过程的叙述可被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就餐的现实状况,另一条则是回忆以前在桑给巴尔上学的故事。第二条叙事线索中,叙述者坦言自己在向威洛比先生讲述帝国故事,他明白他在编织伪造的故事,模仿由英国掌控的话语机制。对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发放的食物,叙述者从材料的珍奇和种类的丰富两方面来建构梦幻般的学校生活,他们喝的牛奶并不同于普通牛奶,而是加了三种香料,水果不仅种类多样,并且是当季供应。他对这样的生活进行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升华,在表面上认同大英帝国在帮助殖民地摆脱黑暗,看似在表露对英国殖民者的感激之情,实则对这套由英国确立的宏大叙事进行颠覆,反对帝国故事背后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选择当季水果时,叙述者说“当然还有香蕉”[3]31,他将“香蕉”单列于前文提到的菠萝蜜、荔枝、橙子之外,其区别在于进食的对象与背后可能潜藏的隐喻。在此前叙述者向医生讲述他早餐的内容时便提到了香蕉,香蕉不仅是人的食物,也是猿猴的食物,而前列的水果则单属于人类社会。18世纪,一位荷兰的医生曾提出“非洲人的面部角更接近于猿而不接近于欧洲人”[11]65,正因为两者的相似性,以香蕉作为食物的非洲人获得了一个野蛮的隐喻意义。“当然”体现的是叙述者以自嘲的姿态,将香蕉视为一个熟悉的对象,而非作为水果的客体,叙述者通过强调关系的亲密进行嘲解:欧洲对吞食香蕉的非洲人充满种族主义的歧视,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也会供予学生香蕉。可以看出,英国通过各种事件要素建立的“文明-野蛮”的对立,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宏大叙事中英国象征的文明与进步、非洲象征的落后,都是由于英国的叙事方式扭曲了部分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叙述者还通过场景的交错,以对比的方式揭露帝国故事的虚假。在酒吧就餐时,无论是饮品还是食物,都不尽如人意。对于啤酒的糟糕评价,是从英国人威洛比先生的口中说出的,因此从言说的主体来看,食物的难以下咽并不带有叙述者的偏见,他也对端上餐桌的食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比喻肉丸像屎一样,躺在棕色的汤汁中。将两条叙事线索进行对比可知,随着场景的倒错与置换,对食物的勾勒也呈现出相反的样貌。就连当下所处的英国餐厅的食物都既不美观也不美味,而帝国故事里英国给殖民地供应的食物竟充足、珍奇,因此“就餐”这一条叙事线索的作用是对帝国故事进行拆台,叙述者在模仿的同时解构了帝国故事。
三、悖谬:质疑文本与历史话语
布鲁克斯将悖谬(paradox)理解为语言的“各种平面在不断地倾倒,必然会有重叠、差异、矛盾”[12]313,悖谬即有对立、差异的内容同时出现在文本中,在表达真理的同时它会产生讽刺、惊奇等效果。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悖谬也获得了历史、政治维度的意义,它将历史问题化,“它既利用又滥用、既设立又颠覆它自己所挑战的那些概念”[4]3。
小说既在文本中将相悖的语言并置,也体现了更为广泛的悖谬特征。无论是反讽、戏仿还是悖谬,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不尽相同,但就其本质而言都体现了两种话语的对立,隐藏着叙述者因为英国社会的束缚,而被迫选用委婉而非直接的抵抗方式。究其根本,是因为移民而造成的历史断裂给叙述者带来了身份困惑,在历史书写的维度中,他对官方历史、个人历史的质疑与呈现,对两种历史的矛盾态度,皆展现了他特殊文化身份下的悖谬态度。
(一)文本层面的悖谬
通过文本中悖论式的言说方式,叙述者造成了讽刺的文本效果。在讲述自己去英国诊所就医一事时,叙述者以离题的方式,回溯他所知的英国医疗体系,其中不乏大量的批驳。他追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移民给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带来重荷,描写涌进诊所的移民们伤口的丑陋肿胀。此处的讽刺本指向这些移民,但叙述者随即却将讽刺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他展示出医生医治行为的野蛮与医疗过程的潦草,讽刺其不专业的医者姿态,认为这里的医生无法按照正规的程序进行治疗。对于叙述者胸腔的不适,医生反而希望胸腔能够自主释放出某些信号,随即开始揉捏他的肉体,连掐带挤,并草率地告诉叙述者他有心脏问题。与前文医疗环境的开阔舒适相比,医疗的实质过程如此不堪入目。叙述者以“外部-内部”两种不同角度的目光,从正反两面讲述对于英国文明的不同解读,将情感态度的波折隐藏在讽刺的陡转之中,将赞美与消解并置,以“倒顶点”的方式达到更加强烈的讽刺效果。
此外,叙述者在小说末尾讲述自己打算报个夜班学习水暖课程,研究马桶的疏通问题。在叙述过程中,他既评价了英国人的马桶疏通研究过程,也追忆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在回想自己的亲生父亲时有这样一段感慨:“水是献给死者的礼物。死者的灵魂渴望生命,希望饮下记忆河的水,却只能喝到遗忘之水。这是一个俄耳甫斯教的奇喻(Orphic conceit)。然而,重要的并不是死亡。这是关于管道维修另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13]237在语段开头,叙述者对“水”进行了宗教式的阐明。在俄耳甫斯教中,水与人的生死轮回关系重大,人必须饮下记忆之水以保留对自身神圣起源的认知,而饮下遗忘之水则意味着继续转世以面对苦难[14]85-87。奇喻是玄学派诗歌常用的手法之一,永生与记忆、转世与遗忘这两组不具有相似性的事物,通过宗教而产生了关联,形成奇喻。而在最后一句话,叙述者突然将话题转向了管道维修,除开水会存在于管道中,话语前后两个部分并无太大的逻辑联系,这种言说方式看起来高深莫测,实则与前文提及的管道维修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呼应,讽刺其中语言与意义的贬值。从语言风格来看,语段前面部分是“高级的”文学式语言,而最后一句话则纯粹是不相关的论证式语言,通过将宗教的神秘言说与世俗而现实的话题进行畸形拼凑,这段话实现了文体的混合,造成读者在阅读时的惊奇,以获得令人发笑的嘲讽。
(二)历史维度的悖谬
在小说中,除开文本语言层面上的悖论,作者也拓宽到历史书写的维度以表现悖谬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官方正史问题化,叙述者在揭露历史写作模式的同时,也指涉了文本外部的世界;二是在讽刺官方历史编撰的同时,叙述者也在伪造个人历史,以悖谬的方式展现了个人记忆。
首先,叙述者揭露了历史的文本性。在讨论英国与外来移民的关系时,叙述者引出了一段关于波卡洪塔斯的历史叙述,以揭露历史文本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叙述者在此处呈现的历史文本是为英国人所熟知的版本,在1629年英国军官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个人编撰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夏令岛通史,连同真正的旅行,冒险和观察,以及海洋语法》(TheGeneralHistoriesofVirginia,NewEngland,andtheSummerIsles,togetherwiththeTrueTravels,AdventuresandObservations,andASeaGrammar)中有所记载[15]101,162,217-220,235-240。在英国人的历史认知中,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对英国殖民者表现出了亲善的态度,不仅拯救了史密斯,还在来到英国之后接受洗礼、嫁给另一位殖民者,她如同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一位和平使者。但在引入的故事中,叙述者在讲述的同时不断进行插话与评论,对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叙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首先点明了英国殖民历史故事中的叙述成规:“当地的美丽公主迷恋上欧洲骑士,为了爱情可以全然不顾一切。”[3]7可见,英国人所讲述的历史正是按照这种浪漫式的情节编排模式进行选择与剪裁,以构建符合英国利益的历史,因为“用这样的情节结构给事件编码是某一文化理解其个别及公共历史的方法之一”[16]178。其次,他不动声色地对波卡洪塔斯的年龄与行为间的差异提出异议。根据史密斯的历史版本,波卡洪塔斯在挽救他的性命时,年仅十一岁,这显然与她的行为有着不正常的落差。最后,在去往英国后,她被称为高贵的土著奇人,从这一个称呼之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对她隐含的歧视,“高贵”作为尊称,是由于她嫁入英国、改换名字和宗教信仰;“土著”则是由于她的印第安身份,含有歧视意味。而在整个故事中,波卡洪塔斯竟没有任何抱怨,可以推知叙述者实则在隐晦地暗示她的境遇并不同于史密斯所写的历史。正如海登·怀特所言:“绝大多数地历史事件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编码方式,结果就有关于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16]177波卡洪塔斯在英国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如同一个沉默的附属品,她的个人意识没有得到彰显,且表现为一位甘愿臣服于英国人的附庸。由此可知,是英国历史的编码方式压抑了她的话语。由特定主体书写的历史总会为了主体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排斥差异化的叙述。回到如今的情境中,当殖民历史造就的这一批移民涌入英国时,呈现出了与历来的历史叙述相异的状况,他们不再是以沉默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是不断地为了少数群体的权益而抗议。叙述者揭露了历史文本的虚构性,提出对官方正史的质疑,而这些质疑本身也展现了真实的历史现实。
其次,虽然叙述者讽刺了历史编排中的选择性,这使得历史无法反映全面的事实,但他自己在讲述过程中,也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如果说他在讽刺历史的失真,那么他在用言语向英国、故乡的家庭杜撰他个人的历史时,讽刺也指向了他自身,发掘出对前者讽刺中潜藏的对于叙述者自身的讽刺,有助于文本张力的生成。在思考是否将医嘱告知爱玛时,他陈述道:“我讨厌欺骗。”[3]13而后文爱玛向他问起他故乡的家庭情况时,他坦言自己对个人经历进行了粉饰,并编造了诸多细节。在向隐含读者陈述另一个版本的个人“真实经历”时,他做出这样的总结:“这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其中大部分都是真事。”[3]97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可以发现,叙述者前后的思想规范是不一致、矛盾的,他在文中随时可能说谎,这些冲突都让叙述者的言语不再可靠。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的许多故事都是捏造的,在与故乡的家庭交往时,他隐瞒在英国生活的状况,使父母误认为他在英国的生活落魄;在面对英国的家庭时,他杜撰个人经历,美化在故乡的生活,以便维护自己的面子。叙述者在对官方正史的书写进行抨击与抗议时,也在以言语伪造个人历史,读者可以发现他是如何操纵事件要素,以合成一个新的个人历史,而叙述者在文中袒露的所有经历也反映了他真实的个人记忆,他悖谬地重访了个人的历史。
四、结语
纵观全文,古尔纳使用的讽刺手法不局限于直接的明讽,小说中有大量的讽刺通过反讽、戏仿、悖谬进行表达,这些技巧从本质上来看可以被归入后现代的范畴之中,因此能使小说在书写主人公个人记忆与境遇的同时,又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上述的三种讽刺技巧通常悄然隐藏在叙述者的陈述与回忆中,不动声色但又充满幽默。然而,这部小说中的讽刺艺术也不能简单地被纳入一些已有的范畴,它既不是对社会的严肃谴责与批评,也区别于含泪的微笑中诙谐背后的坎坷悲剧,更不同于黑色幽默中怪诞滑稽里蕴含的荒谬与苦痛。《赞美沉默》中的讽刺性语言虽然充满戏谑与自嘲,但又含蓄克制,在表意上更加委婉。讽刺的背后是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他对移民一代的现实处境进行了再现,正如文中的叙述者,他既不愿回到落寞腐朽的故乡,也难以被英国社会接纳,作者的讽刺都聚焦于他无奈而失望的际遇。异于古尔纳其他作品显露出的悲怆与厚重感,这本小说以其独特的讽刺艺术,丰富了我们对于古尔纳创作风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