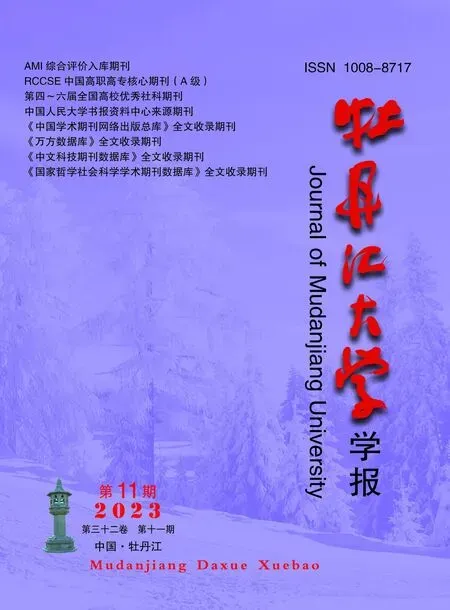元代乐府诗内部的分化与礼乐建设的现实需要
刘星雁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元代时“乐府”已有众多含义,如国家音乐机构,乐府诗、词、曲等,乐府诗的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这在乐章与乐府歌行的区别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拟在元人汇编典籍基础上,结合元人诗论和礼乐制度,从文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元人将祭祀乐章和乐府歌行分列的原因及对乐章的认知,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乐章”而轻“乐府”:乐府诗体内部的分化
(一)元代乐章与乐府歌行的分置
元代出现了乐章与乐府歌行分列的现象。苏天爵《元文类》“所录诸作自元初迄于延祐,正元文极盛之时”[1],主要涉及元代前期的作品。《元文类》将诗类列于赋类之后,诗又依次分为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等,乐章与乐府歌行被四言诗和五言古诗分隔开来,“乐章”收录有《郊祀乐章》《太庙乐章》《社稷乐章》《先农乐章》《释奠乐章》几首诗作,且未标注作者姓名。“乐府歌行”则收有33首标有作者的诗作,其中既有乐府旧题,也有即事名篇的乐府新题。虽然元人并未对乐章和乐府歌行下明确的定义,但从所收诗作可以看出乐章与乐府歌行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正如方回所言:“上之化以此达乎下,先王设官采诗,祭祀宾享,有郊庙朝廷之作,而邦国闾里所赋之风,亦取以为房中燕闲之乐,下之情以此达乎上。”[2]乐章是“郊庙朝廷之作”,与国家礼乐制度相结合;乐府歌行是“邦国闾里所赋之风”,更偏向私人的创作。
历代典籍,乐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被视作乐府内部的诗体。例如,曹勋《松隐集》乐章被收入乐府并置于卷首,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并未被列于乐府之外,吕祖谦《宋文鉴》没有单列乐章一类,明人吴讷所编《文章辨体》也未将乐章单列于乐府之外,徐师曾《文体明辨》也说:“今采汉以下诸辞,分为九品而列之:一曰祭祀,二曰王礼,三曰鼓吹,……其题不袭古而声调近似者,亦取附焉,名曰新曲,使作者有考焉。”[3]乐章也没有被分离出去。二是在没有乐府一类时将乐章单列。例如,柳宗元《柳河东集》、张孝祥《于湖集》,又如谢翱《晞发集》将宋铙歌鼓吹曲、宋骑吹曲列于诗体最前,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将乐章列入文体并与制、祭文同置于一卷。与上述情况不同,《元文类》是在有乐府歌行一类的情况下又在诗体内部将二者区分。宋初姚铉所编的《唐文粹》与之相似,诗体分为古今乐章(附琴操)、楚骚体、效古诗、乐府辞、古调歌等,古今乐章和乐府辞被分列开来。但《元文类》的体例与《唐文粹》也不完全相同,并非全部沿袭前人。总体而言,将乐章与乐府歌行分列的情况并不多见。
虽然元代大部分文人都鲜有乐章创作流传后世,乐章在别集编纂中也少有体现,但苏天爵《元文类》的观点并非独有。左克明《古乐府》中并无用于郊庙祭祀的乐章。郝经《原古录·序》也说:“骚、赋、诗、联句、乐府(乐章)、歌、行、吟、谣、篇引、词、曲、长句、杂言、律诗(绝句),十有五类,皆篇什之文,《诗》之余也,故为《诗》部。”[4]乐章与绝句皆以小字写于乐府、律诗之后。用小字写于后,是因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如律诗与绝句都是有格律的近体诗。单列出来,是因为二者之间有所不同。乐章与乐府歌行的分列也在此体现出来。
(二)元人对待乐章与乐府歌行的态度
乐章与乐府歌行在诞生之初便紧密相关。《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5]汉武帝是因郊祀而立乐府,司马相如等人的诗赋是用于祭祀的乐章,采于民间的乐府诗则是乐府歌行的重要来源。元人也延续了《汉书》的说法,如马端临《乐考》:“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6]乐府在汉代的兴盛离不开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用于祭祀的乐章和采于民间的乐府诗也和“乐府”之名联系在一起。
但元人重视乐章远多于乐府歌行。首先,出于对乐章礼乐象征意义和政治色彩的追求,元人常常梦想自己的作品能用于国家礼乐场合。吴澄《戴子容诗词序》:“使今之词人真能由香奁、花间而反诸乐府,以上达于三百篇,可用之乡人,可用之邦国,可歌之朝廷而荐之郊庙,则汉、魏、晋、唐以来之诗人有不敢望者矣,尚何嘐嘐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哉!”[7]文人在夸赞他人作品时,也会说:“……谓其所作,可以被管弦,荐郊庙。”[8](陈旅《马中丞文集序》)可以如乐章一般“荐之郊庙”是对作品莫大的肯定和赞誉。其次,元人会格外重视乐章的政治功用。袁桷《书程君贞诗后》说:“雅之体,汉乐府诸诗近之。……雅也者,朝廷宗庙之所宜用。”[9]但并非所有乐府诗都用于朝廷宗庙。戴良《淮南纪行诗后序》也说:“而汉之鼓吹铙歌,亦皆军中之乐也。后世音乐废缺,乃独歌以诗,而乐府诸作,见于军旅者为多。”[10]但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看,郊庙歌词和鼓吹铙歌都并非汉乐府的主体。罗根泽说:“其实《清商》《相和》诸歌,占乐府主要部分,文学价值极高,史家以其无关国家典制而轻视之,实为大谬。”[11]元人也未能免俗,总是关注郊庙乐章、鼓吹铙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占乐府重要部分的里巷歌谣,这些正是乐府歌行的重要源头,这种忽视也是一种态度。在“古乐府运动”兴起之前,元人普遍表现出对乐章的重视和对乐府歌行的轻视。
(三)《元文类》的存史意识
苏天爵具有一定的存史意识和实录精神,其在《元文类》中将乐章与乐府歌行分列的安排不会是偶然为之。纵观苏天爵的履历,他有十年的时间都从事修史的相关工作。《元史》说:“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记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12]苏天爵修史注重真实和客观,他在《三史质疑》中说:“南宋自宁宗、金自章宗已与国家相接,欲尽书之,则有当回护者;欲尽削之,则没其实矣。”[13]在修史时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维护真实客观的历史真相,是苏天爵身为史官的基本素养。同时,苏天爵受到了元好问的影响,追求全面地保留史实,他说:“元好问为《中州集》,小传多庶官及文学隐逸之士,所以补史之缺遗,惜其尚多疏略。又所述野史《名臣言行录》,未及刊行,当求访于其家。”[4]《中州集》因所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而受到一些文人的批评,苏天爵则对元好问《中州集》所体现出的存史意识表达了肯定。
这些史学精神在苏天爵编《元文类》时也表现出来,陈旅《国朝文类·序》说:
监察御史镇阳苏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以国朝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佚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
然所取者必有其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15]
苏天爵编修《元文类》的目的就是存一代之文,所选文章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在编选上,《元文类》有着“足以辅翼史氏”的标准,且“不以微而远者,遂泯其实;不以显而崇者,辄襮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16](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元文类》的存史意识也在此体现出来。同时,苏天爵在编修《元文类》时受到了《文选》《唐文粹》《宋文鉴》的影响,这几部总集的体例虽不尽相同,但都足以代表一定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苏天爵编《元文类》时也有意以此反映一代文学,因此,《元文类》对乐章和乐府歌行的安排不会是他随意而为。
二、“非礼”“不辞”:元人将二者分列的原因
(一)政治功能的变化:乐章的保留与乐府歌行的消减
政治功能的变化是元人将二者分列的重要原因。在元代,乐章依旧在政治功用上同礼乐制度紧密结合,礼乐承载着维护治理、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胡祇遹《礼乐刑政论》说:“圣人代天理物,身之以道德,下观而化,无为而治,尚恐身教之而不能齐一,礼乐刑政,由是而举焉。自人之始生,至于终身,匹夫之贱,天子之贵,一动一静,莫不有礼。”[17]礼乐贯穿人的一生,涵盖所有阶层、群体,在国家治理层面可同刑政相提并论。柳贯《御诗一首》也说:“然而仁义彰施,恩德和洽,则本之教化,成之礼乐,其效固亦可睹已。”[18]但是,乐府歌行已不能再承载如先前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9]《艺文志》中对汉乐府的描述偏重于采自地方的乐府诗的政治功用,即观风俗。但在元代,这一功能没有得到发挥。胡祇遹《斡哩监司诗卷·序》说:
民俗之于吏政,缄默而无诗也久矣。不惟无诗,虽一歌一谣一咏无有也。……至于为士者,是非义理之不知,好善恶恶之不公,而清议亦废。其见于诗什者,例皆庆官、践行、生朝,不情过誉,虚美之浮辞俚语,实无足取。[20]
这是一个时期内诗歌创作的共同问题:有关吏政的诗歌太少,虚美浮辞太多,无法起到“观风俗”的作用。同时,采诗之官缺失已久。吴澄《诗珠照乘序》说:“古之诗或出于幽闺妇女、山野小人,一为采诗之官所采,以之陈于天子、隶于乐官,至今与雅颂合编,人尊之以为经。采者岂惟无功于诗哉!后世不复有是官,则民间有诗,谁其采之?”[21]他在《鳌溪群贤诗选序》中也说:“采诗无官,编诗无人,其诗浸浸湮没。”[22]采诗之官的缺失使得民间即使有可以观风俗、补时政的诗歌也于事无补。由此,乐府歌行的政治功能逐渐消减,与其他诗体无异。
但采诗早在元代之前就已不再纯粹。刘辰翁在《赠采诗生·序》:“古巷歌故俚,采而删之为风,楚非无诗,计其所遗,若《祈招》者众矣,此骚辨之所不能平也。唐时采诗盛而童谣绝,猿啼鬼泣,里无歌声。今宋又如唐矣。尝疑李杜以来所不泯没者,非其自致于人,人岂复有喧众口诵百寮上者哉?”[23]刘辰翁怀疑前人采诗的真实性和纯粹性,也揭露了采诗存在的一些问题。元人乐府观念上的改变,还有更多的原因。
(二)文人的自矜:对“贱工野人”的轻视
乐府歌行被轻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文人对乐府歌行创作主体的轻视。在一些元人看来,古时候乐章之外的乐府诗格调不高。如吴澄《题李伯时九歌图后并歌诗一篇》:
三闾大夫不获于上,去国而南,睹淫祀之非礼,聆巫歌之不辞,愤闷中托以抒情,拟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嫚之言,又借以寄吾忠爱缱绻之意。后世文人拟琴操、拟乐府肇于此。琴操、乐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辞,而其辞鄙浅,初盖出于贱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韩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诸人作乐府诸篇,皆承袭旧名,撰造新语,犹屈原之《九歌》也。[24]
吴澄将后世文人乐府与屈原《九歌》相提并论,将早期乐府、琴操与屈原之前的祭祀巫歌类比。早期巫歌“非礼”“不辞”,早期乐府也是如此。吴澄认识到早期乐府诗出自民间,却又认为早期乐府诗因创作者出身卑贱,为“君子不道”。吴莱也曾批评过乐府的“不辞”:“故今或观乐府之诗者,一切指为古辞。虽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残讹缺漏,不能附益。”[25]通俗的诗歌并不受元人欢迎,元稹、白居易便遭到方回的批评:“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26]又说:“诗必摆俗好、弃少作而备众体,则立言不朽。”[27]早期乐府诗大多采自民间,创作者没有受过太多教育,言辞上以质俚通俗为主,这也是乐府歌行被轻视的原因。
这些观点是受元代社会影响的。元代科举不兴,文人缺少上升途径,尤其是元初文人,巨变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些转变。如舒岳祥《陈仪仲诗序》:“方宋承平无事时,士有不得志于科举,则收心于学问,放情于吟咏,自是天下乐事,君生没得其时也。今予亲值乱亡,有先人之菜田在,沦为民伍,遂执里役。晨起开卷未数行,悍吏操棍曳索,隳突灶奥,败思挠怀,呻吟执事,夜分尤未甘匕饭,城舆绛老,曷日免泥途之辱耶?”[28]赵文说:“自世变来,士贱傭贵,一切所需,直百倍他日。”[29]落差使文人越发看重读书人的身份,并迫切地另寻他路。舒岳祥《跋王矩孙诗》:“唯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矣!”[30]刘辰翁《程楚翁诗序》:“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31]牟巘《唐月心诗序》:“场屋既废,为诗者乃更加多。”[32]
科举之路不通,文人便转投诗歌创作,这是文人相比于普通人的“特权”。文人会有意或无意地维护这一“特权”,比如强调作诗的家族传承:“诗有谱,而家谱尤亲。歆、向家于文,谈、迁家于史。故诗不可以无家。”[33](何梦桂《胡柳塘诗序》)在采诗之时忽视普通百姓:“……求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数年,得诗六百余篇,归庐陵,将刻而传之。”[34](虞集《葛生新采蜀诗序》)甚至有人对《诗经》产生了疑问,如苏天爵《江西佥宪张侯分司杂诗·序》:“读《国风》之诗,有以考俗尚之美恶,知政治之得失,然皆民俗歌谣,非公卿大夫雅颂之音也。”[35]言语中流露出更加崇尚“雅颂之音”的意味。苏天爵《读诗疑问》:“《诗》三百篇,夫人女子作者居十之三。夫以淫邪妇人而能为此,岂圣人润色之欤?不然,后世老师宿儒反有不能及者,何也?”[36]这也是文人自矜的一种体现。元好问也有类似的态度:“……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37](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虽然元好问未对这些诗表达否定态度,但一个“虽”字,隐含了对“小夫贱妇”的否定。
(三)性情之正:雅与俗的对立
但元人并未轻视同样有大量民间作品的《诗经》,因为《诗经》符合“性情之正”。赵文说:“古之为诗者,率其性情之所欲言,惟先王之泽在人,斯人性情一出于正,是则古之诗已。”[38]卢挚说:“夫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斯得性情之正,古人于此观风焉。”[39]元好问也说:“盖秦以前,民风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适足以污简牍,尚可辱采诗官之求取耶?”[40]《诗经》的创作时代离先王之时未远,创作主体仍能有先王时民风的“性情之正”,这个高度是后世难以企及的。
乐章也倡导“性情之正”。乐章是礼乐系统的重要部分,礼乐具有教化功能。统治者借礼乐倡导“性情之正”。如郝经《五经论·礼乐》:
喜怒哀乐之未发,性也;其既发,情也。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乐而乐,则情之所以率乎性也。喜怒哀乐,不当其可而发,则非性、情之正,而人欲之私也。
故《礼》《乐》者,王政之大纲也,得则治,否则乱,圣人致治之功,必于此乎取之,而不敢易也。以性、情治天下,以天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故礼乐之治,王者之极治也。[41]
郝经称《礼》《乐》为“朝政之大纲”,认为礼乐可以节制人欲、宣畅人情。礼乐所涵养的性情不仅是个人的性情,也是社会整体的性情。礼乐倡导的性情中正平和,胡祇遹说:“礼乐者,中和而已。中则有伦有序,有序则不乖戾,不乖戾则和中和存养乎内,又假外物玉帛钟鼓存养乎外,此圣人制礼作乐之情也。”[42]学诗也是为了涵养性情,如胡炳文:“孔门学诗,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后世学诗,艺焉而已矣!”[43]
乐府歌行则被置于“性情之正”的对立面。文人认为乐府歌行“淫靡”,如陈栎:“高祖《大风》之歌,孝武《秋风》之辞,悲壮慷慨,视古诗已有愧,况房中之楚声,乐府之淫靡?”[44]南朝也是乐府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作也受到了文人的批评:“诗一降而为楚为汉,再降而为魏为晋,宋下至陈、隋,则气象萎薾,辞语靡丽,风雅之变,于是乎极矣!”[45](贡师泰《重刊石屏先生诗序》)“淫靡”已成为文人对乐府诗的刻板印象。白居易《长恨歌》也遭到了批评:“《长恨》一歌,亵语诲淫,岂可兴、可观者?”[46](胡炳文《程草庭学稿序》)也有文人批评李贺的诗作,李贺正是以乐府歌行闻名:“近人宗长吉怪诞,绮靡刻画则过之,故优柔之味减,正大之情遂失,论大家数者少之。”[47](唐元《梅庭弊帚诗序》)“正大之情”的缺失,也是乐府歌行遭到轻视的原因之一。
三、“大乐氏失职”:元人对乐章的认知
(一)“礼乐之殷”:元人对本朝礼乐建设的自豪
元人对本朝礼乐建设充满了自豪。元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并未放弃礼乐建设。《元史》说:“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48]彼时南宋尚未灭亡,元代礼乐建设起步并不晚。吴莱《张氏大乐玄机赋论后题》也说:“……闻太常所用乐,本大晟之遗法也。自东都不守,大乐氏奉其乐器,北移燕都。燕都丧乱,又徙汴蔡。汴蔡陷没,而东平严侯独得其故乐部人。国初有旨,征乐东平。太常徐公遂典乐,向日月山奏观乞增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49]《元史》中也说:“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地于日月山。……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50]元代礼乐制度是在宋、金、西夏几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元代礼乐建设兴盛,《元史》说:“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51]元人对本朝礼乐建设充满自豪,虞集说:“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兴,列圣继作,至于世祖皇帝一统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万方。郊庙社稷之祀享,朝廷之会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节,以奉于天地神祗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邻百官及四方之来宾者,骎骎乎礼乐之殷也!”[52]这自豪之情是大一统王朝带来的底气。但元代的礼乐建设是一段漫长的过程。虞集又说:“往年东平王拜住典奉常,予忝博士,尝为言制礼作乐,将在此时。及东平相至治,予退在荒野,后召对京师。时方大作宗庙,欲以前说与大夫君子议之,而事有不及者矣。”[53]从虞集有心“制礼作乐”到“大作宗庙”,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元初的礼乐建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沉寂时期,直到成宗时期,“有元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雅乐仪制才算逐步纳入正轨。”[54]
沉寂过后,文人更加迫切地想要投身于礼乐建设。有积极为礼乐制度建言献策的,如袁桷《进郊祀十议状》:“国家车书混同之后,声文昭明,典章纯备。议礼考文,实惟圣明之大本。观会通以行典礼,今维其时。然因循有待,几三十年,得非睹历代仪文之繁缛,费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举也。……谨献所为《郊祀十议》以补缺佚。备皇朝之礼,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55]这无疑是袁桷上奏的出发点,虽然其中也有些夸赞之语,但三十年间礼乐之未兴也是主要原因。也有梳理礼乐建设情况的,如《太常集礼稿》,李好文在序中说:“与其具于临时,孰若求之载集?与其习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征?此裒集之有编而不敢后者也。曰稿者,固将有所待焉。他日鸿儒硕笔,承诏讨论,成一代之大典,则亦未必无取。”[56]《太常集礼稿》是文人自主编撰的,这是元人有意识地、自发地投入到礼乐建设中的表现。
(二)崇古尚雅:元人所尚的乐章风格
元人在乐章上特别崇古、尚雅。首先,元人所崇之“古”是更早的上古时期,如王惟贤:“三代之隆,礼乐达于天下。”[57]夏商周三代礼乐兴盛,尊崇礼乐也应以夏商周三代为标杆。三代之后的礼乐建设都有不足,郝经曾批评汉代的礼乐建设:“而汉制皆因秦敝,不为之革。……使汉之礼乐不兴,不能比隆三代,杂而不纯者,留侯误之也。”[58]吴澄说:“周之经制,破坏于秦。汉定朝仪,杂采秦制。鲁两生谓礼乐百年而后可兴,故文帝谦让未遑。至于武帝,而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然古制不复,君子不无憾焉。”[59]赵天麟也说:“(汉武之朝)乃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然帝徒能好名而不复察实,故当时之体,断不能肩上世帝王之治也。”[60]他们都批评了秦朝对于礼乐制度的破坏,而汉承秦制,其礼乐制度也有缺陷。同时,元人将乐章的传统上溯至上古时代,又将乐章同乐府的概念剥离开来,如赵德:“古乐章之名,见于载籍者,由伏羲、神农、少昊氏以来皆有之。……然逮汉元狩,乃有乐府之名,以定郊祀礼。立乐府采诗及民俗歌谣,以知政教得失。”[61]汉代乐章的创作也并不受元人青睐,如吴莱:“自秦变古,诗乐失官。至汉而始欲修之,燕代荆楚稍协律吕,街衢巷陌,交相唱和。当世学者,司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虫篆刻之辞,而欲立汉家一代之乐府。”[62]
元人在乐章上主张的“尚雅”更多是从现实角度出发。元朝的礼乐是“雅俗兼用”,《元史》中对此并无太多非议,但并非所有元人都接纳礼乐中的“俗”。袁桷说:“切以阳春白雪之唱,和者固希;清庙朱弦之音,知之尤寡。……俚歌日烦,古调几废。”[63]《清庙》是《诗经·周颂》的篇目,为乐章范本,然而却面临着曲高和寡的情况。这更多是因为当时俗乐的兴起。刘辰翁也说:
余尝与祭太学,见太常乐工,类市井倩人,被以朱衣,及其歌也,前者呼,后者哦,群雁而起,竟亦莫识何曲,而音节又极俚,有何律度?而俗儒按之以为曲,曰乐章。姜尧章至取编钟、朱瑟,铁较而字定之,然语言无味,曾不及其自度《香》《影》诸曲之妙,乃知柳子厚《铙歌》、尹师鲁《皇雅》,皆蔽于声,质于貌。呜呼,吾读文王《清庙》,何其往来反覆,愈简而愈有余地,虽不能知其声,而洋洋者如倡而复叹之不足也,故可歌也。故知依声铸字,出于述者之过,中无所见,则如市人滥吹,闻而从之者也。[64]
刘辰翁生活在宋元之交,“与祭太学”也是发生在南宋时,可见当时俗乐已“侵入”雅乐体系,且俗儒难以辨别。南宋著名音乐家姜夔所作乐章更注重乐器之雅,言辞上则有所缺憾,柳宗元《铙歌》和尹师鲁《皇雅》也有短处。面临这样的情况,元人更加迫切地想要复兴雅乐,而《清庙》之雅就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三)“但颂国家功德”:元人眼中乐章的缺陷
政治因素是元人批评诗歌的重要标准。郝经说:“故三代之际,于以察安危,观治乱,知人情之好恶,风俗之美恶,以为王政之本也。”[65]这是发扬了“兴观群怨”之“观”的功能。何梦桂也说:“诗者,所以载民风,系世变也。”[66]诗歌承载着民风世变,这是对诗歌反映政治功能的强调。姚燧说:“今之诗虽不得方三百篇,可考以知国风与王政之小大,要亦繇于吟咏性情,有关美恶风刺而发,非徒作也。”[67]诗歌不仅可以反映政治、社会,也可以通过讽喻来批判政治现象。
乐章也是如此。元人意识到了乐章创作的一些问题,由此提出了一些直接的批评。如吴莱《宋铙歌骑吹曲序》:
初《汉曲》二十二篇,魏晋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颂国家功德,不言别事,大乐氏失职。唐柳宗元崎岖龙城山谷之间,亦拟魏晋,未及肄乐府。今朝又拟夫宗元者也。[68]
在吴莱看来,汉与魏晋的铙歌只为国家歌功颂德,这是当时乐官的失职。后世之人所称赞的柳宗元的《唐鼓吹铙歌》也是向汉魏乐章学习,“唐鼓吹铙歌十二曲,柳宗元作以纪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劳之事。”[69]柳宗元自己也在所作铙歌的序中直言歌功颂德的目的:“……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70]柳宗元的作品也只是歌功颂德而已,何况那些学习柳宗元的文人?吴莱明确地对那些只是歌功颂德的乐章表达出了反感之意。不仅吴莱如此,在元人眼中,只是歌功颂德的乐章并不能算是优秀的作品。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也说:“而国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谣,诗人之讽咏,至于后世,遂无《雅》《颂》之音。虽用之郊庙朝廷,被之乡人邦国者,犹夫世俗之乐耳。独何欤?盖诗之为用,犹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无隐。诗系一代之政,婉而微章。”[71]后世乐章即使用于郊庙朝廷,也是俗乐,是因为这些乐章没有起到“史”的作用,即直而无隐。大部分只歌功颂德的乐章也是这一范畴。乐章同礼乐制度紧密相关,元人有此看法也是出于建设礼乐制度的目的,“大乐氏失职”不仅是对从前乐章创作的批评,也是对礼乐建设的警示。
四、余论
总而言之,在元代,乐章与乐府歌行在雅俗上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也是有些元人将二者分列为二体的原因。同时,元人对礼乐制度建设充满了热情,特别重视乐章的政治因素,除了秉持崇古尚雅的乐章创作主张,元人还直接批评了乐章创作中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但是,元人并非一直对乐府歌行持轻视的态度,元末“古乐府运动”的兴起,使得不少文人再次重视这一诗体。同时,《元文类》中乐府歌行列于五言古诗之后的现象也值得学者注意。元代文学观念多样多变,乐府观也是如此。本文所探讨的元人对待乐府歌行的态度,只是“古乐府运动”兴起之前文人所持有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有元一代所有文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