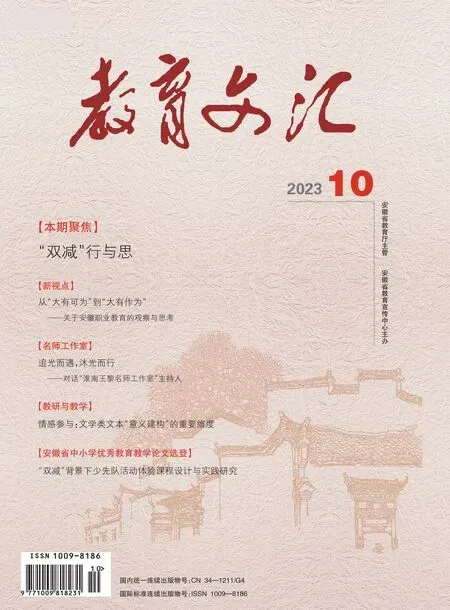情感参与:文学类文本“意义建构”的重要维度
——以“文本阅读的整合式认知模型”为出发点
广东省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郭跃辉
龚鹏程先生在《文学散步》中认为:“所谓意义,是作品的灵魂。文学作品的价值,即在于它本身就是人类探索意义、发掘意义、建构意义的主要典范。”[1]表达意义,是文学类文本的灵魂,这种意义并非客观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需要阅读者的参与和创造。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最好不要把文学作品看作固定的文本,而是能够源源不断衍生出各种意义的母体。与其说它持有意义,不如说它产生意义。”[2]这也说明,意义是被不断建构的。阅读文学类文本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构意义,阅读教学的目的则在于教会学生建构意义的方法与策略。
一、文学类文本教学的问题透视
笔者在听一些教师执教文学类文本时,发现其容易出现三大误区。一是误将提取文本表层信息等同于读懂文本。例如,教师在执教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时,习惯要求学生从文本中找到昆明雨季的特点,通过圈画出文本写景、写物、写人的句子来把握其特点。学生很容易从文本中找到昆明雨季的特点是“明亮丰满”,仙人掌的特点是“多且肥大”,昆明菌子的特点是“多且美味”,卖杨梅的女孩子声音的特点是“娇娇的”,缅桂花的特点是“香”,房东的特点是“善良”,等等。在教师看来,学生掌握了准确定位这些词句的能力并概括出景、物、人的特征,就意味着读懂了文本。二是误将识别静态的语文知识等同于读懂文本。这些知识包括修辞手法、描写手法以及文体知识。教师在阅读文本时,头脑中已经先在地识别出了“需要”教的各种知识,于是在教学时,就不断地引导学生在知识点之间“滑来滑去”。例如,执教《白杨礼赞》,教师指导学生概括出白杨树的特点,并且对应白杨树所象征的精神,然后就将教学重点放在“托物言志”的知识上,其中还穿插着直接抒情以及比喻、拟人、对比、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的知识。实际上,教师课堂上不断指导学生“找”句子、“找”信息、“找”知识的行为,远远达不到建构意义的阅读目的,自然也不能帮助学生完全读懂文本。三是误将读懂“这一篇”文本等同于读懂“这一类”文本。阅读教学就是指导学生读懂教材的一篇篇课文,忽视了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的训练。学生只有在读懂“这一篇”的基础之上,不断总结阅读经验与方法,才能够继续阅读“这一类”文本。
代顺丽博士在《文本阅读的整合式认知》一文中区别了文本阅读的两种思维方法,一种以文本要素分析为中心,认为阅读效果取决于对阅读材料的文本要素分析;一种以认知策略为中心,认为阅读效果取决于对文本信息的精加工程度。这种精加工主要包括“访问和检索”“统整和解释”“反思和评价”等深度加工策略。作者对这两种思维方法进行整合,构建出“文本阅读的整合认知模型”,将阅读目的、认知条件(先备图式)和认知过程(认知策略)整合成新的系统。具体来说,就是阅读前要根据文本特征厘清认知条件,生成初始发现;尔后让认知过程持续运行(使用一系列认知策略),产生持续的阅读发现。阅读发现经过积累形成对于文本的终极观念:文本的深层意义[3]。
该模型对于文学类文本的“意义建构”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既强调了以文本要素分析为中心的解读“这一篇”文本的维度,又强调了以认知过程为核心的培养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的维度,便于进行“这一类”文本的阅读,同时能够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不过该模型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行为,具体到文学类文本阅读,还应该在模型中加入“情感参与”的维度和内容。
二、“先备图式”中的情感要素
对于一般意义的文本而言,“先备图式是过去阅读活动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关于阅读材料的某种结构,存储在读者的长时记忆中,这种结构代表了文本的类型、特征,预示了文本的潜在意义走向”[4]。也就是说,对于每一次阅读行为而言,读者并不是带着“空白”进入文本,而是在头脑中已经存在着一种“先行结构”。这种“先行结构”正是乔纳森·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阅读诗歌是由一定规律制约而产生意义的过程;诗提供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必须由读者自己去填补,因此,读者便按照他读诗经验中产生的一系列形式规则去进行创造,而这些规则既是他创造的条件,又对他的创造加以约束。”[5]代顺丽博士和卡勒所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以文本的文体特征为核心的系统性知识。而卡勒所说的“文学能力”,指的就是“阅读文学文本的一套程式”。例如,在阅读写景抒情散文时,读者已经在过去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一套“阅读程式”,包括阅读时要着重把握作者在文中抒发的情感、景物描写与作者情感之间存在着某种照应,等等。
不过对于文学类文本而言,“先备图式”中不仅有客观意义上的阅读材料的结构,包括文本类型、特征、规律等,还包含过去阅读经历中的情感参与成分。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我们所谓理想的融通方式,应是紧扣文学的特质,并同时发展与此特质相呼应的一般性知识和逻辑性知识,而以此类知识切入生命存在的感受中,去做思虑的体会和涵泳的辨析,达到严羽所说‘多读书多穷理以极其至’的境界。”[6]这也说明,文学类文本阅读的“先备图式”除了知识外,还包括了“生命存在的感受”等情感内容。这在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时,表现得尤为强烈。例如,学生阅读鲁迅的《藤野先生》,自然离不开阅读同类文本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时的情感经历;阅读史铁生《我与地坛》时,也离不开阅读《秋天的怀念》时的情感经历。
当然,“先备图式”中的情感因素不只是存在于阅读同类文本、同作者文本的过程中,还存在于与文本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中。因此,在阅读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前,可以启发学生调动过去的阅读经历、生活经历。这一点在统编教材的“预习”提示中多有体现。例如,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中《春》的“预习”提示是:“春天展现美丽的世界,春天带来崭新的希望。历来文人墨客都喜欢描绘春天,赞美春天。你读过哪些描写春天的诗文?这些诗文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回忆一下,准备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这实际上是调动学生过去的知识积累与阅读经验。《济南的冬天》的“预习”提示是:“朗读课文,看看作者笔下的济南的冬天与你印象中的冬天有什么不同”;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背影》的“预习”提示是:“默读课文,设身处地地体会文中描写的情景,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文中的父子深情”。上述两篇课文的“预习”都指向了学生的生活经历。这都是“先备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图式”中的知识内容,同时也要关注“图式”中的情感要素。
三、“认知过程”中的情感参与
从认知的角度看,阅读就是读者试图主动地理解文章、努力探寻意义的过程。梅耶认为,该过程需要三类知识:“①内容知识:是指文章中所涉及的学科内容领域的有关信息。②策略知识:是指学习者为了更有效地学习而采用的各种程序。③元认知知识:是指阅读者对自己的认知过程以及对自己是否成功地达到任务要求的意识。”[7]其中,“内容知识”隐含在“先备图式”中,而“策略知识”和“元认知知识”显然都与认知过程有关。代顺丽博士的“整合式认知模型”也是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构建的,尤其强调“访问和检索”“统整和解释”“反思和评价”等精加工策略。实际上,“访问和检索”“统整和解释”“反思和评价”更适用于PISA 考试中的非文学类文本阅读,而对于文学类文本而言,除了认知层面的因素,还应该考虑情感层面的因素。在认知过程中,情感参与的主要路径有:
(一)共情:基于情感相似性的角度
文学类文本的“意义建构”不仅仅表现在理解和把握文本的主题,更在于把读者自己“摆进去”,能够和文本的形象、主题、情感、语言甚至细节实现“共情”。正如伊瑟尔所说:“艺术作品的意味不在于被密封在本文之中的意义,而在于下列事实,即本文的意义揭示了以前一直被密封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的东西。”[8]在阅读教学中,如果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过远,无法实现与文本的共情,教师的任何讲解都无异于“灌输”,而情感恰恰是最无法“灌输”的。肖培东老师在备《湖心亭看雪》一课时曾这样反问:“生于繁华,终于沦落,饱经国破家亡、升降浮沉的张岱,他那种有意追求的凄清、恬淡、孤独的审美境界,孤高耿介、高洁自守的文化人格,中国传统文人普遍的文化心理,以及空灵冰雪之文气,哪里会是初二学生能读能品的呢?”[9]学生感悟不到、理解不了这些境界与心理时,文本就是外在于学生的“无生命之物”。不少教师在执教此文时,要么会补充背景材料,引导学生感受作者的“亡国之悲”,要么会抓住文中的描写性语句,从炼字、修辞等知识角度加以赏析,这些手段都无助于学生的意义建构。肖老师在教学时,没有知人论世,没有探讨文化心理,没有补充背景资料,就是抓住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句,引导学生用心读、反复读,学生读“与”,读“一”,不知不觉走进了作者张岱那孤独而又痴迷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类文本的“意义建构”。
同理,在执教余光中的《乡愁》时,尽管学生没有和作者相似的经历,但也要能够围绕“邮票”“船票”“坟墓”等意象,引导学生实现与文本的共情,而不仅仅是讲解有关意象的知识;执教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就是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精彩的句子如“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在反复朗读中咂摸作者的情感,而不只是给学生讲“托物言志”的创作手法。王元骧教授认为:“文学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不是以认识的心理形式,而是以情感的心理形式来反映生活的。”[10]对于学生而言,只有把握到文学类文本内部“情感的心理形式”,才能真正读懂文本,而不是上完一节阅读课后只会说出学到了那些静态的知识点。
(二)体验:基于经验相似性的角度
伊瑟尔认为:“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是通过他在本文中的存在与他的习惯性经验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现在,他的习惯性经验是一种过去倾向。因此,读者领会文学文本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种生产性的响应过程。”[11]也就是说,文本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读者过去经验的参与。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将文本内容与自己的人生经历相联系,从而在对文本理解的基础上,创造文本之于个体的意义。刘基在《项伯高诗序》也说:“予少时读杜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疑冰矣。”[12]《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一个片段就揭示了这个道理。香菱读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很有感触,她说:“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13]如果仅仅读出了“余”和“上”的妙处,还不能算完全领会了诗歌的意义。香菱正是将这两句诗和过去的相似经历联系起来,在诗歌中读出了过去的经历,又用过去的经历体验本诗,从而获得了属于个人的意义。
在解读郑振铎的《猫》时,如果能够联系到自己曾经有过的被冤枉的经历,就更能深刻地体会到文中的张妈和第三只小猫一样,同样也是被冤枉的对象。但是“我”在获知芙蓉鸟并非被第三只小猫咬死之后,内心发出了最沉痛的忏悔:“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这种忏悔之情固然能够引发读者的“共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对受冤枉的小猫满怀歉疚和懊悔,而对于张妈则只字未提,这说明“我”的忏悔是不彻底的。笔者在成年以后阅读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时,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家庭曾经有过的贫困,于是对若瑟夫的父母有了一些同情,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与批判,进而也能体会到若瑟夫在叙述父母行为时的调侃心理,而这种心理是建立在对家庭拮据生活的无奈和对父母的包容基础之上的。同理,在阅读史铁生《秋天的怀念》、莫怀戚的《散步》、李森祥的《台阶》、朱自清的《背影》等,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联系与自己父母相处的经历,进而切身体验文本内容。
当然,在阅读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革命传统作品时,学生未必会有相似的经验,甚至这些作品的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经历距离过远,从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语境差”。教师要善于还原文本产生的语境,尤其是还原写作素材和创作情境,并在教学中设计真实的情境任务,从而链接真实生活[14],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产生“相似的经验”,从而缩短读者与文本的距离。
(三)反省:基于审美相似性的角度
在意义建构时,通过情感相似性和经验相似性实现与文本的“共情”以及对文本内容进行体验,并不意味着读者建构的意义是绝对个人化的,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个性化的解读都符合文本的内在规定性。伊格尔顿认为:“文学作品不可能只对我一个人具有某种意义。虽然我也许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从原则上说,我所看到的必须是可以和别人分享的,这样方可称为‘意义’。”[15]这一观点和康德提出的“审美共通感”是相通的,正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着相似的审美感觉和经验。实际上,“审美”中的“审”字意味着对美的感觉和体验,需要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即在直面审美对象时,要不断地思考:我为什么会感觉到对象之美?他人是否和我有着相似的感觉?同样道理,在阅读文学类文本时,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与经历,而是要不断反思,建立与他人相似的感想与理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本意义的建构。
例如,阅读梁衡的《壶口瀑布》,读者能够从语言和形象入手,想象作者描绘的黄河和壶口瀑布的雄伟壮观的画面,甚至能够结合个人的“相似经历”,对文本进行“身临其境”式的体验。个人情感状态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对于黄河水和瀑布的感悟与理解自然也会有差异。但如果要实现意义的建构,就要在共情和体验的基础之上进行反思,要能够结合作者所说的“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挟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来把握黄河的“伟大性格”。这一点龚鹏程先生在《文学散步》一书中也曾论及:“在文学欣赏活动中,读者不但要建立自我的美感价值观,也要设法去体察作者通过作品所显示的美感观念、所呈现的艺术意志,探索每一历史文化群体的美感价值模式,并藉着比较的研究来丰富、来反省自己的美感观念。”[16]也就是说,文学阅读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其中既要有个人层面的情感参与和审美体验,但又不能只局限于“自我的美感价值观”,而是在文本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之上,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且将“这一篇”文本置于历史文化传统中进行观照。换句话说,文学类文本的意义建构,要在个人情感、个人体验、自我反省与把握原初意图、文化传统的互动与融通中实现。
总之,文学类文本的解读与教学是初中语文教育的重点与难点。针对文学类文本教学过程中的误区与偏差,教师可以借鉴代顺丽博士提出来的“文本阅读的整合认知模型”,并在“先备图式”和“认知过程”中加入情感参与的成分,既关注知识的讲解与训练,又重点训练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同时指导学生善于将自己融入文本,进而达成阅读的最终目的: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