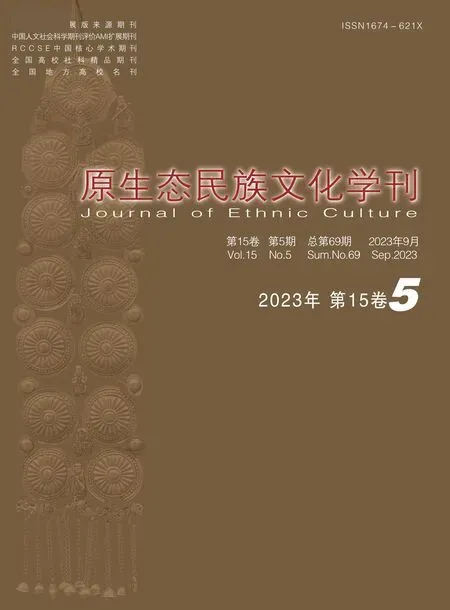元明之际的国家道教治理转型
——以明初玄教院的兴革为中心
朱宇超
元明之际是中国古代道教发展的又一巨变时期,日本学者窪徳忠论及元明之际的道教时谈到:“在元代,世俗性的各道教教团取得了辉煌发展,然而到了明代,其活跃的势头急行消失,元代教团的面貌已荡然无存。”①窪徳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要牵动相应制度安排,影响国家道教治理模式的更易。明代是中国古代道教治理的成熟完善时期,其创立的匹配国家行政层级的道官制度,以“两京道录司——地方道纪、道正、道会司”的垂直体系为核心,名山宫观提点、两京神乐观为辅弼,沿袭两代不废。但这一模式的建立也并非一蹴而就,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仿元制设玄教院,十四年废,次年置道录司,兴革损益,逐步形成了明代的道教治理模式。目前,学界对道录司的研究较为成熟②其要者如赵轶峰:《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何孝荣:《明朝宗教》,南京出版社,2013 年;刘康乐:《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金城出版社,2018 年;贺晏然:《官僚、科举与道派:明代道官考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较为集中分析了洪武十五年后道录司体系的制度与职官问题,但均未对玄教院做出足够的探讨。,已揭示出道录司体系的“集权”与“官僚化”特点,然而,一个久被忽视的问题是,从元代各道团内部治理的“教团自治”,到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以后道录司体系的“集权管治”,二者在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有若云泥,这种转变何由成立?易言之,道录司体制建立的历史合理性在何处?由此,则必须将视野转向于洪武前十四年间这“失落”的玄教院时期。同时,先承袭旧制度再建立新制度乃是制度演进的必然过程,明初玄教院毫无疑问是仿元制设立,因而明确“元制”,明确元人的治理逻辑如何成立是首要的,玄教院作为“元制”与“明制”的转换阶段,它的演变脉络洽能体现元明之际的连续与断裂。故而本文将以明初玄教院为切口,探讨元明之际的国家道教治理转型。
一、道派制衡与教团自治:元代的道教及其治理
有元先是与金、南宋鼎立,其后大兵南下,重新缔造了中华的统一,而治道教史者往往也将南宋、金、元连称,这不仅仅是出于此期政治形势上的连贯,更是由于道教发展形势由分散到整合的基本脉络。
宋金对峙时期,新道派层现错出,其大者如陈垣所称“南宋初三大新道教”,即河北的太一道、大道教、全真道,以及活跃于南方的净明道、金丹派南宗、清微派等。但多则多矣,分散的诸道派却有着一些共同特征,即儒道合一与下层化发展①黄小石:《略论宋元新道教的主要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84页。,这一特征除了与唐宋以来的三教融合趋势有关外,也与金元时代的复杂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元人虞集言:“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藏外道书》第35 册,巴蜀书社,1992 年,第423页。,王恽则称其时隐逸清洁之士“翕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相启牖,自名其家……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敦纯朴素,有古逸民之遗风焉”③陈垣:《道家金石略》,《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陈智超,曾庆瑛补校,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94页。,全真道尤为其典型,王重阳之后的掌教马丹阳,其不少弟子在金朝的乡试中获取功名,元人称之为“玄门十解元”④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中,《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5页。,陈垣亦曾探讨全真道士与士流接纳的关系,指出变乱时期全真道对汉族士人的庇护作用,直称“以逸民名初期之全真,诚得全真之真相。”⑤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5页。
更进一步地,道教教团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相当的社会组织与教化功能,如金贞祐二年(1214 年),山东杨安儿起义,金遣驸马都尉仆散安贞往平,丘处机应仆散安贞请求,抚谕登州、宁海,“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⑥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道藏》第19册,第734页。,元人陈绎赞之:“在金之季,中原版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时则有若东平严公,以文绥鲁,益都李公,以武训齐。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真主,而为天下式焉”①陈垣:《道家金石略》,《增修集仙宫记》,第783页。,乃将丘处机之全真道与北方两大割据势力李全、严实并提,同为纲维北方之柱。同期的太一道之“密毗治化,潜卫家邸”②陈垣:《道家金石略》,《太一广福万寿宫令旨碑》,第841页。亦为忽必烈所盛称。
基于道派教团在乱世发挥的这种社会整合作用,金元时代的统治者们都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以更好地治理道教为其统治服务。金人统治华北时,即曾以封号赐额拉拢诸道派,如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 年)太一教主萧抱珍之被召、大定七年(1167 年)大道教主刘德仁之觐见皆属此类,而若结合其时政治形势来看,这种笼络手段正是自金熙宗自皇统年间推行的“汉法”的重要一环,也是在熙宗朝,金仿效唐宋制度③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六《道教》,中华书局,1986年,第518页。,逐步建立其道教治理体系。但随着十三世纪初蒙古南下,这一进程被打断,金贞祐南迁后,黄河以北地区出现了政治权力的真空期,蒙古人虽然在军事上控制了这一区域,但尚未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丘处机执掌的全真道此时已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号召力,于是二者合流,全真道成为蒙古在汉地的代理人,被授予免役和管理道门特权,教团势力因而急速发展,在社会变乱期,“承担起一种重建社会秩序、重组广大民众精神社会生活的关键角色”④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中华书局,2015年,第166页。,到尹志平掌教时期,全真道更短暂地扮演了北方“临时政府”⑤张广保:《尹志平学案》,齐鲁书社,2010年,第22页。的角色,如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 年),尹志平招抚陕西抗蒙的金遗民,“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⑥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三《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第743页。
金元之际道教的这种佐治之效,深刻影响了元代道教治理模式的形成,但元人的道教治理策略并非简单承袭金人。蒙古人的借重使全真道在丘处机、尹志平、李志常三代(1203年-1256 年)掌教时期发展到了顶峰⑦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而随着其统治日益稳固,元廷对全真道团以及道教的态度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其政策从拉拢借重转变为了利用与限制,与其对待汉人世侯如出一辙,逐步确立起兼容并包、分而治之的宗教政策。
通过调停佛道之间在元宪宗五年(1255 年)、元宪宗八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年)的三次辩论,蒙哥及其继任者忽必烈扶植了佛教势力来平衡道教的盛势。而在道教内部,至元五年,元世祖以孙德福辖诸路真大道,孙德福因而被称为真大道六祖。至元十三年,元世祖赐太一道掌教萧居寿掌教宗师印,正式认可太一道的大派地位,元廷以对二者的扶持,钳制全真道在北方的发展势头。同年,元灭南宋,南方的龙虎山天师张宗演应召赴阙下,即于次年被授江南诸路道教,通过将南方划分为正一道的势力范围,元廷既达到了利用正一道稳固南方统治的目的,又进一步限制了全真道的扩张。同时,随张天师入朝的龙虎山道士张留孙被诏留京师,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为玄教宗师,正式开宗立派,如此,正一道的驻大都机构在皇权的直接介入下发展为一个新宗派,传播于华中、华北地区,分化了正一道、全真道的势力,至此,道教内部各派并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与道派并立局面的形成相同时,元廷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到忽必烈时代基本形成了道教治理上的“元制”,这一治理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教团自治”。宏观而言,元廷以全真道、正一道、玄教、真大道、太一道为五大宗,加封给绶,“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第423页。,各自统领自上而下的各级道官,与官府埒。具体来说,这种“教团自治”实践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
在中央,元廷以集贤院总管道教事务,以礼部兼管。集贤院初与翰林兼国史院同署办公,到元世祖统一后的至元二十二年,玄教宗师张留孙议,“分集贤、翰林为两院,以道教隶集贤,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702页。,“集贤院,秩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③《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192页。职官包括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待制、经历、都事等等。然自职能和职官设置可以发现,集贤院兼及儒、道,并非纯然的道教管理机构。按诸典章,集贤院之介入道教事务,是通过“知集贤院道教事”“同知集贤院道教事”诸头衔来实现,通常以此衔加诸各派领袖,以收监视、顾问之效,其制度逻辑在于,道派领袖首先因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得以宗教身份领受世俗权力与职官,然后这世俗权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宗教权威的合法性,教权与政权由此合一。其处理道教事务的通常流程为:掌教遇事呈文集贤院,院奏皇帝,中书议后下院,院给劄付予掌教,掌教发下予道观④刘晓:《元代道教公文初探——以〈承天观公据〉与〈灵应观甲乙住持札付碑〉为中心》,《法律文化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在地方,元廷实行按宗派和按区域的双重管理路径。元廷将治理的具体权限委托于各派领袖,诸掌教有“诸路都提点”、“都道录”之类为副手,负责管理本门地方具体事务,如至元十八年,龙虎山道士李庭晰授“张天师下道教都道录”⑤《龙虎山志》,《诸高士·李庭晰》,王卡,汪桂平:《三洞拾遗》第13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57页。,未几,陈士囦授“张天师下道教都提举兼提点太上清正一宫事”⑥《龙虎山志》,《宫门·陈士囦主持》,第55页。,这二者即是领在正一道张天师下,授其管理本门诸路道官之权。“诸路都提点”之下则路设提举,至元年间集贤院从翰林院中独立出来后,又郡设道官,以府设道录,州设道正,县设威仪等衙门,形成一种教团内部自掌教以下的垂直管理系统。地方各宫观住持则有“提点某宫、某观”之名,各教团各任以道士,由道派领袖具文,集贤院备案而已。
在管理区域上的划分主要是指玄教、正一道、全真道三派的区域分割。在北方,授全真掌教领“诸路道教所”,最早领受者为张志仙①张志仙掌教始于至元二十二年,《祁公道行之碑》末尾题刻时间为大德三年,张志仙领诸路道教所的时间当在此二者之间,见《道家金石略》,第700页。。在南方,至元十四年(1277 年),元世祖赐天师张宗演,“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为道士”②《龙虎山志》,《人物上·张宗演》,第18页。,设立“江南诸路道教所”。次年,元世祖又命新授的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等路新附州城道众”③《龙虎山志》,《大元制诰·领荆淮道教》,第38页。,后升格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所”,故元代的道教地图呈现一种三分而治的情况。这一区域的划分既有道派固有势力范围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玄教作为元朝皇帝以皇权强力扶植的一个道派,玄教所属的总摄所及其管辖范围正是对南北两道教所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一举措事实上同时钳制了全真道与正一道的扩张。
同时,与本区域所属不同的道派亦属本区域掌教管理。易州正一道观龙兴观建自唐景龙中,与本地的全真道实属两派,但以其地处北方,其“政权”归属全真道掌教,其住持缑公“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法旨,令充本宗门下提点”④陈垣:《道家金石略》,《龙兴观提点缑公功行记》,第980 页。,掌教大真人即全真道掌教完颜德明,在这样的跨道派调动、管辖案例中,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结合,宗教权力的执行以完颜德明领受的世俗权力为保证,清晰地体现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二者的关系。此外,据虞集所言,真大道也得“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与全真、正一之流叁立矣”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第423页。,而这一点也更加表明,地方道教的管理与地方道官的设置,是以各道派平行、各教团各自为政的形式进行的,这同样也是道派制衡的一种体现。从地方道司的运作来看,也确乎与官府无异,“一如有司,每日公署莅政施刑……道官出入驺从甚都,前诃后殿,行人辟易,视部刺史、郡太守无辨”⑥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七《抚州玄都观藏室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491页。,而其“为僧录、道录者……与三品正官平牒往来”⑦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元代奏议集录》(下册),邱树森、何兆吉辑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文书制度上也使用了与元代官府一致的呈文与劄付体,这绝少见于前代。
综上所述,虽然道团对本门道士管理的合法性来源于皇帝对该派领袖的承认,但道派与中央分别对地方道官有一定的掌控力,在事务具体开展层面,各道派对各自地方道官的掌控程度还要大于中央。可以认为,元代的道派组织是以一种半官僚半自治化的方式完成自我治理,此处的“半”,乃是强调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的先后关系,首先有皇帝对道派领袖的绝对权威地位,其次才是治理权限的下放。“教团自治”更多的是描述教团组织获得了行政管理权限,得以独立地“治其众、理其事”这一情形,因为归根到底,这种“教团自治”治理模式成为可能,离不开对峙时期道团组织的“佐治”功效,离不开佛道共存、道教内部分化所达成的派系制衡局面,因而是在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与道教发展的客观形势合力下,形成了这一“教团自治”治理模式。
二、元制的失效与礼部的归复:明初玄教院时期的道教治理
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明太祖仿元制设中央道教管理机构,“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明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2016年,第499页。,但其治理实效如何仍待考察。
(一)玄教院时期的地方道官
在明代官方记载中,类似元代道教治理体系中的路道录司、州道正司、县威仪司的地方道司记载首次出现于洪武十五年,“置僧道二司,在京曰僧录司、道录司,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②《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洪武十五年四月辛巳,《明实录》第5册,第2261页。,即先有道录司之设,才有各地分支机构,因此学界往往将洪武十五年道录司体系的建立与地方道司的建立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观点似乎将地方道司视为一夜之间建立的,事实上,道录司体系中的地方道司早在玄教院时期就已出现,道录司体系实际是继承了这些机构。按诸方志,在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间存在不少关于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的记录,恰可补官方文献之不足,试举几例。
开封府密县。“天宝观,在县治西,泰定三年建,国朝洪武三年修,置道会司于内。”③万历《开封府志》卷十五《祠祀·密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6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638页。
西安府耀州。“僧正司在山寿寺,道正司在州治后新街太白观,俱建自洪武三年。”④嘉靖《耀州志》卷三《建置》,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93页。
长沙府茶陵州。“青霞观,在州城内,梁大同建,曰洞真,元延佑为青霞万尽宫,元火。洪武五年,道会尹性安、袁德升、刘从性相継复修之。”⑤嘉靖《长沙府志》,梁小进等点校,卷六《方外纪·寺观·茶陵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2页。
开封府。“延庆观,在城内汴河之北,浚仪桥之西,旧为朝元万寿宫斋堂。……国朝洪武初,为宝泉局铸钱之所,后移局于蔡河湾,而斋堂悉已颓毁。洪武六年,设道纪司于内,十年,都纪邵惟真、副都纪郑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及东西两庑。”⑥李濂:《汴京遗迹志》,周宝珠等点校,卷十《寺观·观》,中华书局,1999年,第163-164页。
承天府潜江县。“通明观在县治东,元时建,后兵燹,洪武初重建,十二年设道会司,弘治二年毁,八年重修,正德十四年改建。”⑦万历《承天府志》卷十七,寺观志·潜江县》,《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24页。
保定府定兴县。“道会司在聚仙观,洪武十二年道会刘得全建,万历间移于城隍庙左。”⑧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建置志·官廨》,《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214页。
广西全州。“玄妙观在州治西,本朝洪武十四年开设道正司于内。”⑨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十七《外志八·全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1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673页。
以上诸例包括了华北、江淮荆襄两大区域(下文另将引用到江南区域的一例),启自玄教院建立次年的洪武二年(1369年),晚至洪武十四年,在时、空分布上基本可以普遍地反映玄教院时期的地方道司较为广泛的存在情形,但这些道司又与元代的级别又有所不同,基本是以府级设道纪或道正、县设道会的形式建立,与其后道录司体系的安排一致。若再深入比较,其建置过程和设置原则也是相似的,如南安府,“道纪司,洪武十五年开设于玄妙观。玄妙观在县西一里,……历宋及元,修废无考。洪武初,知府于润珪重建”①嘉靖《南安府志》卷十八《建置志四·属廨·南安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第769页。。又杭州府,“佑圣观,在兴礼坊内,宋孝宗潜邸也。……元季兵火,此观独存。皇明洪武十五年,置道纪司于观中”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陈志明编校,卷十七《南城分脉城内胜迹·道院》,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16-217页。。凤阳府临淮县,“通真观,在升仙坊,元至治二年道士王永模创建,壬辰年毁于兵火,洪武六年道士王兰谷复建,洪武十五年开设道纪司”③成化《中都志》卷四《宫观·临淮县》,《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第350页。。可见其基本都是在宋、元旧有道观的基础上,或修或建,沿用旧观,设官署事。
同时,地方道司的位置随道官变动而在道观间改易、轮署的现象在洪武十五年道录司体系铺开后并不少见,但以方志所见,玄教院时期的道官衙门其实也存在着相同的改设现象,这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如嘉兴府海盐县,于洪武十五年前即有道会,“栖真观,在治西北一百步,旧真武庙,宋乾道二年,道士郭宗谅移请废额为之。洪武初,道会沈廷芝附籍住持”,至洪武十五年,随着道录司体系的建立,道会司改置于紫虚道院,“紫虚道院,在治西南二百步,元至正间,道士沈廷芝增置武安祠,十五年设道会司。”④万历《嘉兴府志》卷四《寺观·海盐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9页。第二种情况是,旧衙门并未在洪武十五年当年改设,而是沿用几朝后再改,如前引保定府定兴县道会司,正德以前设于他处道观,洪武十二年道会刘得全建聚仙观,正德间,道会谷道全改道会司于聚仙观,万历年间又移于城隍庙左,“聚仙观,古城隍庙址,元碑泐,明正德中设道会司,以谷道全为道会,始定观名”⑤光绪《定兴县志》卷十四《古迹志·寺观》,第374页。。以上这些方志记载都表明,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的玄教院时期,地方上已经存在着较为完备的道官衙门,掌管地方道士管理与祈祷事务,而依据相似的建置原则和跨阶段的改设情况两点判断,道录司体系应当是接收了玄教院时期的地方道司,二者在地方层面具有相似的基层组织。
(二)玄教院与地方道官
玄教院与其时存在的地方道司是否有统属关系,玄教院是否有深入地方的分支机构?这个问题关涉玄教院的职能及其治理实效。明人文集中记载了一个两道士争住持的案件,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梁道士贞者,字松间,处州丽水人,……十二投紫阳观为道士。时玄妙观有髙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杨景云,以道化远近,贞居紫阳六年,不见道,乃入玄妙事希玄,讫传其道。……安期生之徒、特进于大宗师,一见器之,留居蓬莱宫十余年,乃与集贤大学士六十四荐于朝,得处州路玄妙观住持,提点领本路道敎事。贞南归领职未一年,今天子命越国胡公取处州。……及参军胡深归镇处州,俾建醮三日夜,……贞即尽心殚力支欹,危补罅漏,既迄功,……辞去,参军与知府程孔昭不听,会嗣天师亦强起之,乃复为强起。……建州两道士争住持,相与愬于中书,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择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属贞。贞至建州,折以片言,两道士委服,乃奉币物为贞寿,贞即骂曰:‘若等出家者,乃争至烦我远来,市人不若也,何复以市人处我,趣反而币物无以点我也。’两道士惭而退。”①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四《传·梁道士传》,《四部丛刊初编》第251册,上海书店,1989年,页11-b。
处州府道士梁贞于元末入府玄妙观,后入玄教大宗师于有兴门下,授职处州路道教提点,可称之为地方高道。入明后积极投身道观的恢复,复为地方军民长官及张天师所器。按,仿元制,玄教院由中书省直属,李善长正式任职中书左丞相的时间为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四年正月二日,此时玄教院已立三年,若有职官建置当已完备。而本案中两道士争执不下,乃直接诉至中书省,而非总领道教事务的玄教院,反观梁贞在元时得授处州路玄妙观住持及道教提点,俱得自大宗师及集贤院举荐,考虑到大宗师必然也领集贤院衔,梁贞的授职可以认为完全出自集贤院名义的举荐任命,而仿元制建立的玄教院却无法独立处理,可知在明初与元代类似的制度框架下,玄教院在道观住持任命上权限已较低,同时这也表明,在其时道士心中,似乎并没有一个统领天下道教事务的衙门存在,这是其一。
其二,事既上,流程为先至中书省,中书再下文玄教院,由该院在建州周边选派高道前往处理。按,本案中梁贞并未身具任何官职头衔,差遣时也并无强调或加封,从处州府至邻省建宁府处理此事,其所恃惟有“高行”而已,可知玄教院在处理地方道教事务上采用的是临时性差遣使者的形式,而非逐级移文地方道司。这首先表明,玄教院之“领道教事”,并非以掌握地方道司来实现;其次,它对于地方道司应当并没有管辖、统属关系。尽管本案仅仅是明初南方的一例,但若将之与元制进行比较,则也可发见玄教院与地方道司的关系。在元制下,集贤院虽不直接掌握地方道司,但藉由领集贤院衔的掌教,包括住持任免在内的地方道官事务完全可以道派通过文书行政方式解决,若发生道派间冲突,则由二者协商处理,如正一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与玄教掌教大宗师吴全节曾就抚州路崇仁县保安观的住持任命发生冲突,双方各有人选,协调之下将该观住持改为甲乙相传②《虞集全集》,《抚州路相山重修保安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68页。,又如延祐六年(1319 年)的《承天观公据》③陈垣:《道家金石略》,《承天观公据碑》,第875-878页。所载太平路当涂县承天观争住持案,同样是正一门下的道士与玄教所属道士相争,最终由掌管江南诸路道教所的张嗣成作出裁决。两相比较之下,玄教院的“领道教事”在运行上似乎并不顺畅。
(三)玄教院与度牒授予
度牒制度是王朝国家控制道士人口、进行道教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明初制度如何尚不清晰,但立国时所设的玄教院似乎并未掌握相关权力,管理上的缺失使道众一仍旧态,元末以来的失序私度、不守戒律等情往往有之,因此在洪武五年五月,乃有太祖“礼教之训”,厉言“僧道之教以清净无为为本,往往斋荐之际男女溷杂,饮酒食肉自恣,已令有司严加禁约”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洪武五年五月戊辰,《明实录》第4册,第1353页。,自此开始,明廷的宗教政策日趋严格。
由于玄教院“领道教事”的运作不畅和道教治理的实际需求,礼部相关权力被提升以填补空白。礼部初设于洪武元年八月(1368 年),略晚于玄教院,其职掌变化正与道教治理的收紧相同步。在“礼教之训”的次月,即定礼部职掌,以其祠部“掌祭祀、医药、丧葬、僧道度牒”,这一事件不能不说与玄教院对道士戒律管理不严没有关联②刘康乐直接认为不受戒律导致了道教自治权的废除,见《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第41页。,明确了将相关权力归于礼部祠部,到同年十二月,始给僧道度牒,“时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礼部言:前代度牒之给,皆计名鬻钱以资国用,号免丁钱,诏罢之,著为令”③《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明实录》第4册,第1415页。,并由礼部主管,玄教院在道教事务上的法理权限被初步削弱。
洪武六年八月,“礼部奏,度天下僧尼道士凡九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人。”④《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四,第1501页。既由礼部奏报,则礼部显然为该责任者,这表明度牒由礼部主管作为制度趋向固定。
同年十二月,同样出于前元之弊,“时上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又以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⑤《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第1537页。通过限制道观数量,控制僧道人口,以考试定度牒三条规令,礼部在道教管理的权限与内容更加细化。
洪武十一年,“礼部郞中袁子文建言度僧,诏许之”⑥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上)》,何孝荣点校,卷二《钦录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郎中当指祠部主官郎中,专掌僧道度牒,这表明礼部已经能够主动因应情况提出发放度牒的申请,介入道教治理中。
以品级论,自洪武元年玄教院、礼部二者建制以来,礼部与玄教院二者品级竟一直是以玄教院为尊,其秩从二品,而礼部自洪武元年定制,秩才正三品,但管理权限尤其是度牒管理的权限,从诏令来看一直是以礼部为主,礼部一直处于一种以小临大的状态。直到洪武十三年,以中枢改制为契机,“升礼部官品秩。先,洪武元年始设礼部,定官秩,属中书省。至是罢中书省,升六部官秩,仿古六卿之制,分领中书之政,升尚书为正二品,侍郎正三品……。”⑦俞汝辑等编:《礼部志稿》卷七《国初礼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7页。礼部品级始高于玄教院,与此同时,礼部职掌又稍稍有变,“定六部官制……礼部尚书、侍郎各一人,总掌制诰、天下礼仪、祠祭、宴享、贡举之政令,其属有四部焉……;曰祠部,掌祠祀、享祭,及乐律、祭器、牺牲、医学、释道优给之属”⑧《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第2069-2070页。,从仅限度牒扩大到了包含僧道优免、给度的一切事务,道教管理权力的转移更加彻底。此时玄教院的原上司部门中书省已革,新制也未明确玄教院的归属,这就造成了在洪武十三年同时存在两个二品上的衙门管理道教事务,既不符合此时道教治理需求,也容易导致两者之间互相推诿,二者自然要留一废一,玄教院的废置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综上所述,洪武元年(1368年)定制“领道教事”并直属中书省的玄教院,虽然参与道教管理,但职权非常有限,对道士的管束力度也十分不足,对这一阶段已经存在于北方、江淮荆襄、江南各版块的地方道司亦无组织上的统属关系,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中央总领机构与地方道司的脱节,地方的道官衙门及其所属道众实际处于一种松散乃至放任的自治状态,可以说,所谓玄教院“领道教事”,其实并不成立,它的存在对国家道教治理实际并未起积极作用,甚至反而影响了道教事务的有效开展,因此在其存续的中后期,道教治理的权限已经开始转移。
三、权势转移:废院改司的历史逻辑
洪武十四年二月,“甲戌,革善世、玄教二院”①《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明实录》第5册,第2214页。,次年,诏设道录司,附礼部,地方以府州县普设道司衙门,明代的道教治理模式初具规模,而从元明之际的道教发展形势来看,这一废院改司进程的推进实际有其必然。
玄教院于立国当月与其他中央机构一并建置,其时明太祖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统一战争上,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何孝荣曾综合前人研究指出明初佛教最高机构善世院的此种阶段特点②何孝荣:《明初善世院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而并设的玄教院亦可为一典型。从品级上看,洪武元年所设善世、玄教二院俱从二品,明显是仿自元制宣政、集贤两院,而从中枢权力结构来看,玄教院又是明显的“得形忘意”。
元代集贤院体制在实际运作上皆以诸派掌教署集贤院同知衔,以此实现兼管道教,这个制度的顺利运行建立在元代道派制衡并立的格局上,道教管理的权力操于各道派领袖,并经由集贤院这一松散的组织形式汇总于中书省与皇帝,进而实现国家对道教的治理。然而,自元中期至于明初,由于各派依附元廷而日渐奉行上层路线,加之社会环境的基本和平,其教义发展停滞,新旧各派间日渐合流,道教的发展形势又有一大变局。
五大道派中,太一道在河北三新道派中一直属于弱势一方,主要活动于两京太一广福万寿宫,在七祖掌教萧天祐死后,其教团归并于正一道③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连太一道士专职负责的六丁祭祀都变成了由正一道士住持。真大道祖山为大都天宝宫,主要活动于华北、淮北,十二祖张清志死后,到泰定中,其道众逐渐归并于全真道④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三卷),第264页。。全真道历代掌教均陪侍帝侧,深度参与元廷政治,于大都大长春宫住持,末代掌教完颜德明在至正年间仍可见活动踪迹,但其后却无人能号令教团,全真教团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教团组织陷入一盘散沙⑤高丽杨:《全真教制初探》,巴蜀书社,2018年,第211-212页。。玄教与全真道类似,作为一个由皇权强力扶植的道派,教义发展有限,在第五代掌教于有兴死后十余年,元亡,其教复归于正一。正一道历代天师都受元廷宠遇,加师号、真人号,并且官方承认的天师号也是自元代始,其“主江南道教”的地位也成为一种定制,大德中加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后,更是使南方新旧符箓道派在思想、组织两方面日渐合并为一个大宗派,但与其他掌教不同的是,历代天师一是兼任集贤院职务者不多,二是常驻龙虎山而非大都,因此与元廷上层统治者日渐疏远。要言之,元末时作为“教团自治”基础的道派并立与制衡状态已难以维系。
到明初,一是由于政治上的关联一时难以转向,二是由于地理位置,惟有张天师早在西吴时期即与朱元璋保持密切联系,太祖甫一称帝,即正式加封其真人号,承认其领导权,“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改天师印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赞教,曰掌书。制曰:……尔四十二代孙正常,……远绍祖传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赐以名号,尔其益振宗风,永扬玄教,可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天下道教事”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甲戌,《明实录》第2册,第601页。,正一道因此稍得尊崇。但虽有此形势之巨变,明初制度架构却仍套用元制,以中书省直属玄教院为总领,然其院内并未设置类似元代的“同知”衔,更不必说作为这一模式运作基础的道派领袖了,玄教院无从实现其道教治理的职能,梁道士一案正可窥其端倪。同时,唯一尚存的道派领袖张天师与玄教院首领同样号为真人,但并不处院内,而其品级乃至高于玄教院首领的从二品,其僚佐的设置与玄教院真人基本一致,又同样“领道教事”,这样一来,法定的国家最高道教管理机关,和一个道教内部的宗教领袖,二者职权相同,级别类似,却同时独立存在,这只会造成二者职权的冲突,而张天师的威望又未曾稍坠,如此,玄教院在道教内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权力。这种制度安排上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了明初道教治理中一时的空白。
从明初道教形势来看,亦迫切需要一种有力的治理模式。元末道教内部的混乱和奢靡之风自不待言,入明后这种失序情形并未好转,玄纲日益不振,滋生了生活作风、敲诈勒索与派系纷争等等腐败现象②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明太祖有鉴于元,加之其本人经历,对元明之际的僧道问题有深刻认识,因而对宗教的态度非常清晰。早在洪武三年(1370 年),明太祖即有申明:“上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亵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为令典,俾世守之。……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禳告星斗之类其禁尤严”③《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洪武三年五月乙未,《明实录》第3册,第1017页。,次月又有“禁淫祠制”④《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第1037页。,下达宗教戒律与祭祀的禁令,并由此开始了延续到洪武晚期的“清理道教”运动,“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以尽废。惟严行禁约,毋使滋蔓,令甲具在,最为详密。”⑤《礼部志稿》卷三十四,《释道》,第637页。禁令范围不仅在于管理制度,更涉及斋醮科仪与行持、宫观组织与器物,对道教事务进行整体性的规范,洪武七年,明太祖御注《道德经》,诏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钦蒙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上下经,立成道门上范,清理道教,崇奖备至”⑥张宇初:《道门十规》,《道藏》第32册,第146页。。而道教内对此也有积极响应,洪武十年(1377 年)嗣教的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作为其时道教内部的最高领袖,著《道门十规》,作为道教内部清理的纲领性文件,内称“三箓之设……不可僣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①张宇初:《道门十规》,第149页。种种制度、禁令都需要实体来执行,有名无实的玄教院自然是无力的,而交由道门内部完成更是不能,因而创设一种以更严格的以行政权力“集权管治”为要的治理模式自是必然。
更为重要的是,玄教院所因袭的元制中,治理权限分散于诸领袖而非专于中枢,这与明太祖所秉持的权集中央、权集皇帝的统治理念背道而驰,更与其宗教政策相悖。对于僧道二教,明太祖向来主以利用,要求宗教为统治、为教化服务,“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②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黄山书社,1991年,第215页。,“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哉”③朱元璋:《御制玄教成立斋醮仪文·序》,《道藏》第9册,第1页。,但从制度设计和治理实效上看,玄教院都难以符合,太祖对玄教院有意无意地不畀以事权,根本目的就是虚化玄教院“领道教事”的职权,而仅作为尊道的笼络手段,玄教院真人也就成为一个荣衔,玄教院也因此权极小却能长期保持从二品高位。另一方面,在洪武年间的制度建设上,以洪武十三年为标志,之前明廷制度基本以沿袭元制为主,而在洪武十三年废丞相开启中枢改制后,从地方收权且更加集权于皇帝的“明制”逐渐确立,废院改司实际也是这一进程的一环,通过“清理道教”对道教组织与教众的整顿,到洪武十三年,皇帝直接控制下的礼部就已实际攫取了道教治理的绝大多数权力,而在中枢改制之后,作为直属上级的中书省既去,玄教院所根植的元制已不存在,明朝国家统治也已稳固,玄教院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新的“集权管治”治理模式浮现而出。
若就历代道教治理的一般趋势而言,玄教院所仿效的元制本身即是异数。一般认为,道官制度的形成、道士进入官僚体系开始于隋唐时期④周德全:《道教与封建王权政治交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按隋制有崇玄署,设令、丞管理释道,后改玄坛监,唐复设崇玄署,隶鸿胪寺⑤《唐六典》卷十六《宗正寺·崇玄署》,中华书局,2014年,第467页。,贞元中分左右街设功德使。北宋有道录院,隶鸿胪寺,院分为左右街道录司,自神宗起改院为司,沿用至南宋,徽宗朝短暂复司为院以重其事。由此可见,隋、唐、宋以来,中央道官衙门均为司、署级别,在官制序列中属于中下级衙署,其人也多为文官,以其上级衙门负责政策的制定,道教治理初步进入了“官僚化”和“科层化”的路径。但元代则不然,由于蒙古人对待宗教的开放态度,其宗教职官皆“高其品秩”,中央集贤院从二品,地方路一级掌管民政的总管府对兼集贤院衔的掌教真人甚至需要使用呈文申送,地方路道录则与地方三品官使用平行公文,这种体制虽然表明上实行以院统司,但事实上集贤院对地方道官并无科层制的直接控制,地方的道教治理掌握在教团手中,只是有了国家权力的授权而已,其道教治理,实际乃是道教的半自治,在“官僚化”的路上反而后退了,明初的玄教院仿设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设道录司的圣旨中言:“照得释道二教流传已久,历代以来皆设官以领之,天下寺观僧道数多,未有总属,爰稽宋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①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上)》,何孝荣点校,卷二《钦录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50-51页。新设道录司渊源自宋人旧制,其称“未有总属”可以理解成作为过渡阶段的玄教院并无治理实效,或理解为礼部未有专门的僧道事务管理机构,但最终目标无疑是将僧道管理最高权力收归礼部,废蒙元之高品“院制”而恢复唐宋之“司制”,将道官制度和道教治理模式重新拉回到唐宋以来的官僚化路径上来,将宗教组织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中,而非赋予宗教组织行政管理权限。道录司体系以礼部辖道录司,道录辖府道纪,府辖州道正、县道会,从道录司到最低的道会司,最高正六品,最低不入流,各级道官归属于本级民政长官管辖,是一种有别于齐民,但与之平行的道教“编户”型治理方式,明人称其“犹令率其民以听于守,守率其民以听于中朝之大臣也。”②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二《赠觉义祖庭上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这已然是一种彻底国家化的“集权管治”治理手段,而其程度较唐宋制度无疑更深。
四、结语
明初所设玄教院的权力极为有限,虽有从二品高位与“领道教事”之名而无其实,对当时已存在的地方道司也缺少掌握能力,可称为权不配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玄教院简单套用自元制之集贤院,但集贤院仅仅是元代“教团自治”治理模式中的最表面的一环,其道教治理的实现根本上依靠于道派领袖和教团的力量,但在元明之际的政治变动中,道教发展出现了又一变局,道派组织与教团面貌已然翻覆,“教团自治”治理模式已无法成立,这样建立的玄教院在制度上成为了无根之水。此后,由于玄教院导致的治理空白,加之明的统治日渐稳固,明太祖的宗教政策亦逐渐确立,道教事务的权限逐渐向礼部转移,道教治理回到了唐宋以来的官僚化路径上并以中央集权加以强化,洪武十三年基本完成,到洪武十五年以礼部领导的道录司体系的建立而完善,最高道教事务衙门由从二品玄教院变为了礼部下属的正六品道录司,“集权管治”的治理模式最终确立并沿用至清代,从结果来看,道教自此后再无深度参与政治的情形,这一演变脉络既是元明之际制度演进的生动呈现,同时又是道教在元明时代的发展形势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