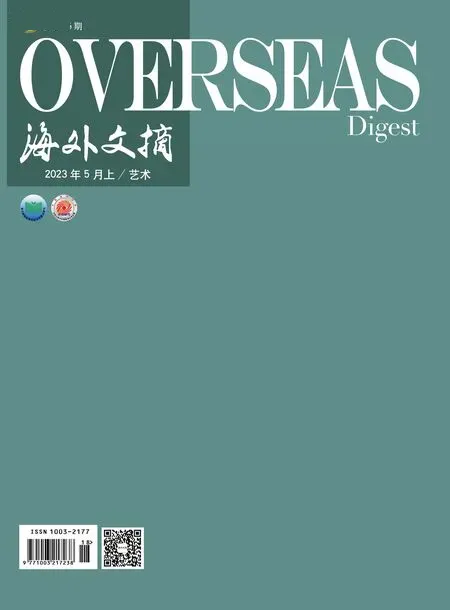从海德格尔“此在”视域下探究《大瑟尔》的信仰书写
□郑清荷/文
《大瑟尔》是“垮掉的一代”核心成员杰克·凯鲁亚克后期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相比他壮年巅峰的作品《在路上》,这部小说风格迥异,是他创作后期人生心态和信仰的巨大转变在作品中的突出体现。“《大瑟尔》这部小说主要记录了1960年的夏天,凯鲁亚克在加州海岸大瑟尔的六周经历,小说弥漫着孤独和死亡气息,却又同时充满了对永恒的向往。[1]”凯鲁亚克如是说,这是他最“诚实”的作品。同时,恰特兹评论说,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部重要作品”[2]。凯鲁亚克用其一贯擅长的自发式写作方式,凭借准确的记忆,仅仅用时十个晚上即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于1963年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盛行。“存在主义”又称生存主义,由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创立,后经法国哲学家萨特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海德格尔宣扬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3]”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存在主义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观念。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其本质就是追问存在、追问存在的意义,而此在的存在又是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追问往往从此在的存在论建构着手。本文从海德格尔此在视域出发,探究《大瑟尔》的信仰书写。
1 “此在”本质的追问:凯鲁亚克“在世之在”中的挣扎与逃离
杰克·凯鲁亚克被当时美国年轻人追捧为“垮掉之王”,他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都引来年轻人疯狂的效仿。而创作《大瑟尔》时的凯鲁亚克的心态和人生状态与之前正值盛年满是雄心壮志的自己相比已是大相径庭。20世纪60年代的凯鲁亚克对人世喧嚣感到疲倦,对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到无力。在此阶段,他的追求并不像年轻时候那样轰轰烈烈,总是反叛到底,而是只想求得精神的平静和心灵的平和。这一阶段,凯鲁亚克对于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本质以及人最终的生命意义归属有了新的体验和精神领悟。这种体验与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的阐释有着相似之处。对于“存在”这一本质问题的追问一直深受哲学和文学界的关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他强调,回到事物的本身,体验生命的真实历程,回归生命最纯粹的状态,以最终探求到“存在”的本质。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对立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超越了主客之对立的传统认识方式。要想把握存在,就要把握存在者自身意识到自身本质存在以及其背后生成的过程。当存在者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此在”的本质就得以显露。而“此在”的本质就是“去存在”的过程,“去存在”意味着不被自身定义所束缚,人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探求存在的过程和意义。归根结底,“此在”是人的一种生命状态或是具体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说,“世界”是“此在”本身的一种性质。因此,在研究“此在”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此在”与“世界”的概念和思索。在后来的理论阐明中,海德格尔也明确了“在世之在”的概念内涵。“此在”具体包括了“此在”与“此-在”的内在联系以及“此在”与“世界”的关系。这交织的关系中就涉及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所感知的“烦”“牵心”“操劳”等感受。而这些世俗感受正一步步折磨着这一时期的凯鲁亚克,他备感煎熬,也逐渐在“在世之在”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2 “此在”信仰的探寻:凯鲁亚克“向死而生”中的本真存在
“在世之在”的现代化世界一步步煎熬着凯鲁亚克的内心,人的“此在”意义与“世界”开始不协调,种种精神矛盾也接踵而至。这致使凯鲁亚克辗转在“烦”“牵心”“操劳”等一系列“在世之在”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中,这也促使他加快了逃向大瑟尔的决定,决心逃离这一切。凯鲁亚克在《大瑟尔》的第一章就点明了成名后的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和精神饱受惊扰。他在书中写道:“大家都嚷着那个酷极了‘垮掉之王’回到城里来请大家喝酒啦然后大家又乱哄哄地跑到所有有名的酒吧去喝酒。”成群的效仿者只是沉迷于模仿明星般的垮掉之王的行为,却鲜有人尝试深入地了解和探寻凯鲁亚克的理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垮掉的一代”的运动高潮正值凯鲁亚克等人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年岁,他们愤怒地呐喊,执拗地叛逆到底,无视社会规则,漠视主流社会的评判甚至道德原则,用行动坚决反抗现实美国社会的条条框框。但这一切过后,“垮掉的一代”发现自身无法给出明确的未来蓝图,引导理想社会的创建。“垮掉的一代”“以打碎所有既定规范为手段,却从未思索将一切打碎后如何建构的问题。[4]”这也是其追随者只能停留在简单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采取最外在的反抗手段的关键原因。没有明确和容易把握的具体目标纲领就难以触及垮掉派分子对社会和整个世界的核心精神观念。垮掉派分子的三位核心人物(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对于社会蓝图的创想和具体的社会观念也各有分歧,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理想价值。“垮掉的一代”的社会蓝图也只是各自零散的“乌托邦之城”。
同时,逐渐规范化秩序化的现代生活使得凯鲁亚克试图融入社会的努力显得十分被动,他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逐步艰难的境地,这也是“此在”与“世界”难以协调的另一个原因。“搭便车”旅行和出发是凯鲁亚克《在路上》时期主要的场景之一,垮掉派分子“通过这种随意而放纵的方式来展示内心的真诚以及对抗社会既定规范的勇气。[5]”但在往返于城市和大瑟尔的路上,他试图再次搭便车,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也只能乘坐火车并被迫接受它成为新的出行方式,而这也是垮掉派后期妥协与接纳社会规范的明证。他在书中写道:“根本就搭不到车了”,“那天下午有五千辆或者是三千辆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没有一辆动过停下来的念头。”凯鲁亚克将其解释为,因为“美国的世风已变”。“世风已变”准确有力地呐喊出了新的时代下凯鲁亚克格格不入的艰难和绝望。社会存在方式快速发展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垮掉的一代”的精神不再有赖以生存的空间和一丝被继续传递的可能。垮掉派的初衷原本是力求打破束缚人和制约人的条条框框,主张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社会规则上,都要回归人的本真面貌,但垮掉派终究也没有凭一己之力而力挽狂澜,最终被淹没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浪潮之中。
事实上,大瑟尔也没能给凯鲁亚克带来理想中的精神平和,两进两出大瑟尔表现了他精神上极度地挣扎和痛苦。后期朋友们的善意造访,给凯鲁亚克带来新的精神焦虑和困扰,“此在”与“此-在”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再度显现,这种矛盾具体蕴含在垮掉派分子内部之间在观念和信仰上的分歧。对“性”持开放态度是“垮掉的一代”鲜明的旗帜和风格。“把性与身体从受压抑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是‘垮掉的一代’反抗传统思想束缚、追求人性自由的一种表现。[6]”这一评价和描述对于《在路上》时期的“垮掉的一代”来说是客观的而准确的,但对于《大瑟尔》时期的凯鲁亚克而言,对于“性”的态度方面已经和其他垮掉派分子出现严重甚至本质上的分歧。凯鲁亚克在《大瑟尔》中迷醉又清醒地记述了他所面对的一切畏惧、烦躁、死亡、操劳、良知等情绪和生命体验。在自我精神的不断思索中,凯鲁亚克也从“垮掉的一代”群体的盲目中逐渐解放出来,慢慢从非本真状态发展到本真状态。海德格尔所指的非本真状态和本真状态构成了“此在”状态的全部。非本真状态具体指人呈现出一种盲目状态,跟随某种潮流和趋势人云亦云,沉沦在世而不自知。这种非本真状态使人给自己附上某一种具体的标签,将自己融于外界和外物,从而丧失掉一定的主观自我可能性。凯鲁亚克在《在路上》时期的状态就是一种非本真状态,他常年浸润在酒精等的麻醉之下,虽然酒精带来的麻木感能抵消他的迷茫与痛苦,但也使得他原本敏感的感知神经和作家与生俱来的清醒和犀利变得钝化,他反而因此煎熬辗转于清醒与迷幻之中。于是,凯鲁亚克决心逃出城市,逃离人们的追捧,逃离喧嚣的闹市,奔向大瑟尔,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和港湾,以为心灵求得最后一片荫蔽。他试图挣开烦扰,解掉“在世之在”所带来的“此在”情绪的枷锁,遵循自我,挣脱束缚定义自我的一切干扰,进入生命的本真状态。
3“此在”与“本真”的融汇:希望出口的再探寻
“此在”的本真状态下也包含着良知的呼声、召唤意在唤起此在。“此在”世界是把握存在的必要前提,而死亡也是整体存在的必然构成部分。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派分子对待死亡的态度与海德格尔生存论中所提到的“向死而生”意义有相似之处。“海德格尔认为面对死亡,人类应当‘向死而生’地做出生存论筹划。”人们对于死亡有着又觊觎又畏惧的本能态度。“出生”和“死亡”是通往永恒的两条必然途径。海德格尔谈及自己死亡观时指出,常人沉沦在日常之中回避死亡,死亡又本能地勾连起人类畏惧的情绪,而这种“畏”的本质就是恐惧死亡。凯鲁亚克在《大瑟尔》中这样写道,“于是我立刻就醒了,彻底清醒了,又回到恐惧中,当一切都说过做过,那种恐惧就是对世界的恐惧。”在对生命意义进行不断探寻和拷问的过程中,禅宗为凯鲁亚克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行的救赎之路。行至中年,天主教出身的凯鲁亚克找到了禅宗的参悟之道,也许上帝死了,但哲学和佛经为不知所措的人们开辟了新的生命意义。“向死而生”的死亡观和禅宗的“立文字,见性成佛”的超越思想给凯鲁亚克和没落中的“垮掉的一代”以新的生命指向。《大瑟尔》的结尾也给所有读者和世界一个生命的答案,“在温柔的春天的夜晚,我会站在院子里的星空下——美好良善将从万物中显露成长——并会闪耀金光直至永恒——无须再讲了。”也就是说,最终我们都会被拯救。
4 结语
对城市喧嚣感到疲惫至极的凯鲁亚克在逃去大瑟尔的过程中,试图探索新的生命本真。这种本真状态的找寻就是海德格尔生存论中“此在”的深刻内涵。事实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成为真正能给凯鲁亚克带来宁静的心灵栖息之地,清幽隔绝的大瑟尔也不能。此时的大瑟尔对深感焦灼的凯鲁亚克来说也只是片刻停留的“心灵乌托邦”。“在世之在”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生命负担,但人“此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死亡和永恒持“向死而生”的积极生命观和死亡观也有助其找寻生命的本真状态。在《大瑟尔》的结尾,凯鲁亚克向我们描述了生命意义新的永恒。“带着对万物永恒的祝福,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世界一切如初;杜洛兹会在鲜花盛开的日子里告别,坐上返家见妈妈的列车,穿过美利坚的秋日;海边的卡罗琳魅力依旧,小男孩会长大成为了不起的人物;院子一角埋葬的‘小淘气’的泥土地会成为一块崭新而芬芳的圣地,让我的家变得更温馨。”凯鲁亚克最终在生命的希冀和禅宗的智慧里找到生命本真状态的回归,这种意义不同于以往酒精等带给感官的片刻欢愉,而是给日落中的生命以新的领悟和生命真谛,也给后世留下新的希望和生命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