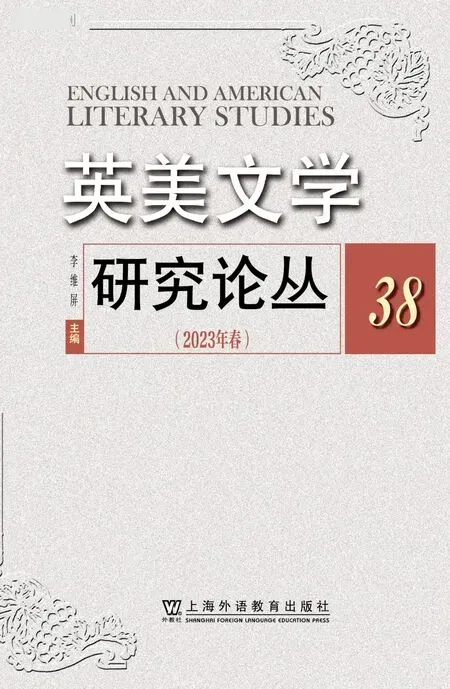论乔伊斯对阿奎那思想的借鉴和发展*
申富英
内容提要: 阿奎那对乔伊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乔伊斯并未囿于阿奎那的思想,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借鉴阿奎那的美学思想,乔伊斯发展出自己的审美三阶段和“颖悟”说;借鉴阿奎那的宗教“三位一体”说,乔伊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人物群塑造艺术;乔伊斯小说中的“容纳、平和”主题和“超越”艺术观也与阿奎那的生活观与艺术观具有密切联系。需要注意的是,阿奎那的思想不等于乔伊斯的思想,它的作用仅限于三点: 一是有助于说明乔伊斯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充当了乔伊斯美学思想的促发剂,三是被乔伊斯融入自己的思想。这些作用被斯蒂芬比作了一盏灯的作用,它只是被乔伊斯自己借用,为他自己指路,借着它的点化,他能自己有所成就。
在《青年艺术家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下文简称《画像》)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借斯蒂芬之口,用了大量篇幅畅谈自己的美学观,其中多次借用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美学理论,并称自己的美学观为“应用型阿奎那思想”(乔伊斯2011:262)。通观乔伊斯的著作,不难发现,乔伊斯与阿奎那在对待艺术和生活的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阿奎那的基督教神学、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肖像》和《尤利西斯》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李维屏55)。
虽然乔伊斯或许仅仅“在私底下对阿奎那的文本做了一些非正式的研究”,而且是出于想要“检验和阐释他某些观点来源的好奇心”(Noon 20),但阿奎那学说对乔伊斯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普拉日记》(The Pola Notebook,1904)中有两篇文章是专门探讨阿奎那学说的,《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画像》的初稿)中的美学理论乍看似乎也是在阿奎那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雅克·奥伯特(Jacques Aubert)认为《斯蒂芬英雄》的整个立论都是建立在阿奎那学说之上:“《斯蒂芬英雄》更像是一个外在的证据,证明了乔伊斯的整个论点都来源于对第三个无声的作者①即阿奎那,笔者注。的引用”(Aubert 100)。但如果对乔伊斯的思想详加研究的话,可以发现虽然乔伊斯在美学思想、灵魂观和诗学思想上对阿奎那的思想都有所继承,但他亦在这三个方面均对阿奎那的思想进行了革新,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乔伊斯对阿奎那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美学思想虽在阿奎那学说中并未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却对乔伊斯早期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阿奎那认为,“中悦视觉者为美”(转引自刘素民124),也就是说,在视觉上给人以美感的即为美,由此将美与视觉直接联系起来。而视觉之美可通过两种方式被人们感知,一是出于感官的本能反应,二是通过理智的判断。阿奎那将判断区分为“肉欲意义上的判断”和“理性的喜悦”,但主张“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将这种属于肉欲的材料去除”(刘素民125)。由此可见,阿奎那所谓的“美”虽可能是一种感觉到的美,但这种美必须是在理性判断之下得出的。乔伊斯继承并革新了这一理念,将直觉与理智的和谐、平衡和结合看作美的基础,并发展出自己的“颖悟”(epiphany)①本文遵循朱世达译本译为“颖悟”,国内学术界还有“顿悟”“灵悟”“显现”“昭显”“生显”等译法。美学思想。他指出,“美是具有审美意识的人所渴望的,这种渴望能在可感觉的事物的最佳关系中得到满足”(Joyce 1959:147)。在《画像》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斯蒂芬又借阿奎那之口,发展出“静态平衡”说:“阿奎那说,斯蒂芬讲道,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就是美”(乔伊斯2011:260)。他进一步阐释说,阿奎那所谓的“审美颖悟力”,“无论是通过视觉或听觉还是通过其他的理解的手段[……]相当明晰地排除激发欲望与厌恶感的一切善的与恶的东西”,是一种“静态的平衡”(同上)。在这里,乔伊斯强调的是在审美过程中要排除的是由肉体的动物本能所激发的欲望和厌恶感,而不是基于肉体功能的直觉。与阿奎那的观点不同的是,斯蒂芬[此处也是乔伊斯]垂青于直觉,也就是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令人愉悦的东西”其实是人类直觉可以感知的、符合人性需求的东西。基于理性和直觉的长期磨合和争斗而达到的平衡,基于在这种平衡之中长期的思考和感悟,人类可以通过肉体的视觉或听觉或者其他感官,体味到这种东西带给自己的愉悦感。而人类这种在理性和直觉达到最佳平衡的瞬间突然体会到的最微妙、最深刻、最美妙的感觉就是颖悟。
乔伊斯在关于“颖悟”方面,也体现出自己对阿奎那学说的创造性继承。“颖悟”原是基督教术语,指一些东方教堂的信众于每年6月1日庆祝东方三博士来到圣城耶路撒冷,“看到”基督向世人显灵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在初版于1944年的《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中,乔伊斯通过斯蒂芬之口,对该词的内涵进行了拓展,指出“颖悟”“就是在思索中突然的精神感悟”,“不管是通俗的言辞,还是平常的手势,或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心境,都可以引发”(Joyce 1977:188)。在乔伊斯看来,即便是最微小最普通不过的事物,如办公室里的钟表,也能够激发“颖悟”。随意一瞥之下,这座钟表不过是众多寻常物件当中的一个,然而,当“灵魂之眼”对它聚焦的一瞬间,“那座钟的意义会被突然颖悟”(同上188)。可见“颖悟”的获得往往会在一瞬间,而这种精神颖悟虽然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却是经历了“灵魂之眼”的探寻与思想的苦苦静思之后获得的。乔伊斯对“颖悟”的阐释摆脱了宗教的桎梏,也不囿于阿奎那学说,既将这一术语形象化地运用到了生活和艺术之中,拓展了这一术语的范畴,又强调直觉和理性在颖悟过程中的作用,避免了阿奎那学说中对所谓“肉欲”的排斥。
乔伊斯将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解释成审美的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阿奎那的美的三个要素包括:“首先,完整或完美,因为凡是残缺不全的东西都是丑的;其次,应该具有适当的比例或者和谐;第三,鲜明,所有鲜明的东西被公认为是美的”(刘素民128)。阿奎那所谓的“完整”,指的是事物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事物的存在状态,可以通过本能的反应和理智的判断获得。“和谐”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关系,“阿奎那将理性视为观赏者与被观赏者之间的关联——理性为比例和谐之物而着迷[……]对称就是美”(Bosanquet 147—148),只有和谐的、有序的、对称的存在才能产生美。“鲜明”则指涉事物存在带给人的精神状态,真切、明晰的事物总会令人愉悦。在阿奎那看来,只有具备了这三个要素的事物才是美好的事物,只有这样的美才具有普遍性。
在《画像》中,斯蒂芬(乔伊斯)把对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的再思考与自己关于“颖悟”的思考结合起来,提出了关于“审美三阶段”的理论,丰富了关于“颖悟”的理念。“斯蒂芬说,可觉察事物之间的最完美的关系因此必须与艺术颖悟的各个必然的阶段相吻合。当你发现这些时,你便发现了普遍美的特征”(乔伊斯2011:265—266)。他引用了阿奎那的一句话,将之译为:“美需要三样特性: 完整性(integritas)、和谐(consonantia)和光彩(claritas)”(同上),并创造性地指出这三个特征正是呼应着“颖悟”的三个阶段。斯蒂芬(乔伊斯)把阿奎那关于审美事物首先应当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观点,创造性地阐释为感知美或者颖悟的具体步骤。斯蒂芬认为感知事物的第一步就是感知事物的“完整性”。斯蒂芬将颖悟的过程比作感知篮子的美的过程,“首先将篮子与它周围可见的空间分离开来”(同上266),这便完成了“颖悟”的第一阶段,即通过事物在空间或时间中与背景的关系来感知审美对象,从而“颖悟”“它的完整性”。在从整体上界定了审美对象之后,在篮子形状的引导之下,“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来感悟“它的相对于它极限之内的部分而言的均衡的部分”,这便构成了对事物的进一步分析,从而“颖悟到它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可分割的,可分离的,是由各部分、各部分的结果和它们的总和所组成,是和谐的”(同上266—267),这就是斯蒂芬所谓的“颖悟”的第二个阶段,与阿奎那所倡导的“美”应当“具有适当的比例或者和谐”的观点有许多共通之处。关于“颖悟”的第三阶段,斯蒂芬认为阿奎那所用的术语“光彩”“看来不太精确”。为了让这一术语更加清楚、明白,他继续用篮子作比喻来加以阐述,指出在对篮子进行整体感知并加以分析之后,审美者“完成了逻辑上和美学上允许的唯一事情——综合”,便明白了篮子的存在并“感知了最高的特性”(同上267)。斯蒂芬(乔伊斯)将阿奎那所谓的“光彩”创造性地解释为事物的精神和艺术性的一面,指出正是这一面使审美对象本身更加光彩灿烂:“被审美形象的完整性所攫住、被审美形象的和谐所着迷的心明白地颖悟美的最高特性和审美形象的明晰的光彩的那一瞬间便是审美愉悦的辉煌无声的静态平衡”(同上268)。这三步都完成之后,篮子的“完整”和“和谐”的特征开始绽放“光彩”,使得篮子这件寻常之物变得无比奇妙,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美学形象,不但令人愉悦,更能使人“颖悟”。
不难看出,在乔伊斯(斯蒂芬)的审美三个阶段中,第一步和第二步更多与理性相关,最后一步更多与直觉相关,但每一步基本都是理性和直觉相协作而完成的。第一步强调事物的完整性以及相对于其他事物的独立性;第二步强调事物的特点,特别是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强调各部分之间的和谐,或者它的独特性;第三步强调事物在人的理智和直觉中所引起的精神反应,强调事物美的特性和效果,它令人愉悦,使人“颖悟”。在斯蒂芬的审美三阶段中,阿奎那学说中失衡的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得到了平衡。
乔伊斯在其小说创作中不断践行他由阿奎那美学思想发展出的“颖悟”理念,捕捉了无数的意义非凡的颖悟瞬间。奥伯特指出,“在《斯蒂芬英雄》中和最后在其修订版《画像》中,乔伊斯把[‘颖悟’美学]理念应用于他的美学体验中”(Aubert 105)。在《画像》中,少年斯蒂芬在向神父忏悔之后,非但没有得到心灵的宽释和解脱,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疑惑和痛苦之中。他孤身一人来到海边,意外地看到“有一位少女伫立在他面前的激流之中,孤独而凝静不动,远望着大海。她看上去像魔术幻变成的一头奇异而美丽的海鸟”(乔伊斯2011:210)。此时,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先是一幅全景图,对于少女这一审美对象的感知通过空间直接地展示出来,而少女也如上文提到的篮子一般从背景中被分离出来加以整体观照。在进行了审美聚焦之后,审美对象以其自身的存在和形态引导着斯蒂芬进行了点对点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从“她那颀长、纤细而赤裸的双肢”到“圆润可爱”的大腿到“酥软而纤细”的胸脯再到秀发和脸庞,少女展现的是一种神奇、和谐、极致的美。少女这一审美形象无论从整体还是细节都是完美的,而她“孤独而凝静不动,远望着大海”这样一种存在又使她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融。“海鸟”这一意象更彰显了她与大海互相联系、互为存在的共处关系。完整之美、和谐之美使得海边的少女这一形象光彩夺目,在一瞬间触发了审美主体斯蒂芬的“颖悟”,他突然醒悟到: 天主教的教条是反人性的,是压制肉体的,他要的是肉体与精神和谐的生活。他在少女身上获得的颖悟看似纯直觉的体验,但它是基于他自己长期的理性思考和精神挣扎,而且颖悟到的内容从实质上说也是理性与肉体的结合。“去活,去犯错误,去失败,去成功,去从生命中创造出生命来”(同上),就是去人性地生活,既要去过基于肉体的、直觉的、世俗的生活,又要在这种生活中提炼、汲取精神的、理性的精华,去创造艺术之美。
二、乔伊斯对阿奎那“三位一体”观的继承与创造性运用
阿奎那的著作中用了许多篇幅来阐释其灵魂观。阿奎那否定了将肉体视为灵魂的载体的灵魂观,强调只有肉体与灵魂两相结合,人“才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实体,一个有位格的人”(转引自江作舟、靳凤山84)。他承认灵魂具有非物质性,认为人的理智不仅能认识物质的存在,也能知晓非物质的存在,既“知道永恒的存在,也知道绝对的无限的存在”(同上84—85)。在阐述灵魂的力量时,阿奎那延续并扩展了宗教中的“三位一体”概念。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术语,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为同一本体,具有同一属性。这三个不同的位格由他们与天主的联系构成一体。在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圣父借由自我意识的联系产生圣子,而圣子又因为自己的神性而激发和巩固人类对天主的信仰,从而产生永恒的圣灵,圣灵拥有神授的爱戴天主、爱戴天父的本质。阿奎那关于肉体与灵魂相结合以及灵魂不死不灭的观点为“三位一体”说提供了依据。在分析天主的三位一体的本质时,阿奎那的关注点是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意志力,认为“人类的理解能力代表着圣子产生于圣父的过程,而意志代表着圣灵的过程”(英格利斯101)。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阿奎那的三位一体观并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学说,而更多是解释人的理解力和意志的学说。
奥伯特曾评价说,对“三位一体”的讨论其实是阿奎那学说最核心的部分,它之所以为后世所关注,主要由于它与艺术的类比关系:“永恒(aeternitas)既是父亲、个体或意象的属性,又是儿子的属性,而使用(usus)、喜悦或者享乐(jouissance)是圣灵的属性;儿子可以被视为个体,因为他与父亲完全相像,而这样一个完美的形象更是一种自然之美”;而且艺术所描摹的对象之美的体验就好比人类心中对圣灵的体验,“人类对艺术对象之美的体验是一种类比,是对这种超验之美的类比”(Aubert 106)。
乔伊斯对阿奎那的“三位一体”概念感兴趣,不是因为他笃信宗教(事实上他对宗教多有批判),而是他看中阿奎那关于“三位一体”论断中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的类比意义。他在阿奎那的“三位一体”概念中发掘出这种关系的“异位同质”(consubstantiality)特征,并将这种特征用于类比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所谓“异位同质”,就是指圣父、圣子和圣灵虽然以不同形态、不同位格存在,但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异位同质指的是在不同的平等事物之间的相同本质。圣父、圣子和圣灵虽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身份,但却具有平等的相同的神圣本质,即相同的神性”(Clarke 198)。
“三位一体”关系中的“异位同质”特质被乔伊斯极具独创性地运用到塑造小说人物间关系的创作实践中。例如,关于“三位一体”的“异位同质”理念被用在《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中的布鲁姆、斯蒂芬和莫莉的三位一体的关系上:布鲁姆是寓言着爱尔兰历史和平和、接纳之德的精神父亲,斯蒂芬寓言着爱尔兰当下处于诸种势力钳制争夺、不断寻求精神之父的艺术家,他也是布鲁姆的精神之子,而莫莉寓言着走向文化杂糅的未来的爱尔兰,是大地之母,也是“布鲁姆和斯蒂芬走向永恒的护照的会签”(Joyce 1975:278),他们三个人共同组成了由爱尔兰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构成的三位一体(申富英2004:26—30)。关于“三位一体”的“异位同质”理念也同样被应用到《尤利西斯》中的女性人物群的塑造上: 小说中卖牛奶的老妇人是贫穷愚昧的爱尔兰的化身,梅是饱受天主教之害的爱尔兰的化身,格蒂是饱受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美化和丑化的爱尔兰的化身,莫莉是走向文化杂糅的爱尔兰的化身,四位女性形象正如三位一体那样分别有不同的位格,但在寓言层面上又是同质的,都是爱尔兰的化身,分别寓言着爱尔兰不同的侧面(申富英2010:112—119)。
三、乔伊斯对阿奎那生活观与艺术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对待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上,乔伊斯虽在许多观点上与阿奎那学说具有一致性,但也有所不同。阿奎那对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和普通场景赋予了非凡的意义,认为它们是艺术美的素材。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指出,阿奎那“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正是街上的普通人说的话”(Ellmann 5),而乔伊斯作品中“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判断便是为普通事物辩护[……]乔伊斯发现[……]普通事物是非凡的”(同上),乔伊斯和阿奎那对普通事物的共同关注“将乔伊斯的作品置于了阿奎那的世系之下”(Hibbs 126)。正如阿奎那注重民众之言一样,乔伊斯笔下所描绘的也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乔伊斯所追求的,是要化腐朽为神奇,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艺术之美:“一个下巴,一个微笑,一杯茶,一首歌,一个回声,一个唤醒,都会产生一种洞察力,洞察之前隐藏的某种形式”(Santoro-Riuenza 148)。
更重要的是,在阿奎那学说的基础上,乔伊斯发现了普通与普遍性的关联。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关于普通与普遍性之关联性的看法带有阿奎那思想的影子:“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许多时日,一天接一天。我们从自我内部穿行,遇见强盗,鬼魂,巨人,老者,小伙子,妻子,遗孀,恋爱中的弟兄们,然而,我们遇见的总是我们自己”(乔伊斯1996:347)。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普通生活的每一天构成。尽管人们在表面上身份不同,或是强盗,甚或是鬼魂,或是巨人,或是老者,或是小伙子,或是妻子,或是遗孀,或是恋爱中的弟兄们,但是在普通生活中,在某些境况下,我们都曾经在现实中或在内心深处扮演着上面所说的角色。在日常普通生活层面,我们人类是相似的和相通的,我们是兄弟、妻子或丈夫、子女,我们年轻过,也会年老或年老过,我们伟大过也渺小过,我们是好人但也做过坏人或在内心涌动过作坏人的念头;这些角色既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也是我们全人类。
在阿奎那关于普通事物就是艺术的素材的观点的基础上,乔伊斯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观: 真正的艺术,就是书写人类的普遍性。借助对莎士比亚艺术创作的讨论,斯蒂芬提出艺术家要表达人类的普遍性的观点:“他什么都是,存在于我们一切人当中,既是马夫,又是屠夫,也是老鸨,并被戴上了绿头巾”(同上)。正是由于伟大的艺术家能够关注普通事物,但又能超越琐碎,超越个体情感,把握人类的普遍性,他才可以创作出永恒的作品。“由于失对他来说就是得,他就带着丝毫不曾减弱的人性步入永恒”(同上353—354)。
另外,阿奎那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观点与乔伊斯的反唯意志论和反个体主义思想有诸多关联。在论及人的生活时,阿奎那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转引自江作舟、靳凤山189),并“强调理解、言谈和意愿在交流中的统一性,强调友谊对人类社会的必要性”(Hibbs 133)。人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源,而只有通过参与社会生活,通过参与社会分工,人才能获得必要的知识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语言为人类的群体生活提供交流媒介,成为区分人与动物、彰显人类社会性的显著标志;人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表达情感,维系人类的群体生活。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只有协调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个人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阿奎那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观点“为斯蒂芬提供了理论上的和隐含的实践上的素材来克服现代哲学的唯意志论和个体主义”(同上)。也就是说,阿奎那的思想或许为乔伊斯的反唯意志论和反个体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乔伊斯并未囿于阿奎那学说,在关于人的社会性方面他与阿奎那的学说有所不同。阿奎那所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一种求同存异的社会生活。然而,乔伊斯在承认友谊以及人的社会生活的同时,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差异性。托马斯·S.希布斯(Thomas S.Hibbs)指出,“在说明众人之中存在的友谊对于社会的必要性时,斯蒂芬引用了阿奎那的话,[……]朋友可能被描述为另一个自我,但他是一个独特的自我,他与我的联系扩展了我的经验和知识。[……]斯蒂芬对人物和人物群的描述否定了所有的差异”(Hibbs 134)。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乔伊斯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塑造上。在主题上,他强调“容纳、和平、不抵抗”的特质,这一点可以从《尤利西斯》中一开始愤世嫉俗、信奉“二选一”(either...or)逻辑的斯蒂芬对容纳、和平、不抵抗的布鲁姆的认同上看出来,也体现在他们二人走向永恒的关键前提是以杂糅为特征的莫莉身上。在人物塑造上,乔伊斯大量使用模糊不同人物身份的手法,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差异。例如,在《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1939)中,HCE是酒馆里的老板,是父亲,是丈夫,也是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男性人物;ALP是HCE的妻子,也几乎是小说中所有的女性人物。通过模糊人物之间的身份,乔伊斯暗示了人物身份边界的不稳定性,从而达到彰显身份单一性的荒谬性。
总之,在乔伊斯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阿奎那的影响如同幽灵一样侵扰着斯蒂芬的思想,也如幽灵一样,侵扰着乔伊斯的小说创作。在《画像》的后半部分,阿奎那甚至似乎成了显性存在,被斯蒂芬奉为权威,以阐明自己的艺术理念。但即便如此,阿奎那依旧是一种幽灵存在,逐渐被斯蒂芬自己的艺术理念所替代。对于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E—322 BCE)的思想,斯蒂芬的思路是:“我需要那些思想,只是为自己所用,为自己指路,一直到后来借着它们的点化,我能自己有所成就。如果油灯有点儿烟,或是有点味儿,那我就修剪一下灯芯。如果那灯给的亮光不够了,那我就卖掉它,再买一盏”(乔伊斯2011:252)。也就是说,阿奎那之所以如幽灵般存在于《画像》中,是因为他有助于说明斯蒂芬艺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但阿奎那的思想不是斯蒂芬的思想,它只不过就是被斯蒂芬改造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就如被修改了灯芯的一盏灯,其光亮已经不是原来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