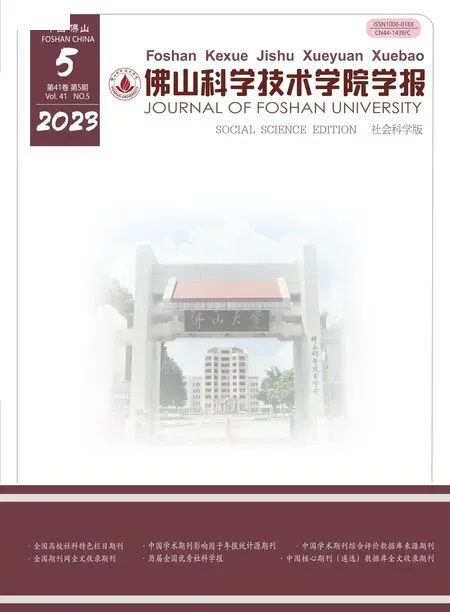“薛马争雄”再审视
——传统粤剧的现代转换
徐燕琳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从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到30 年代中期的10 年间,两位著名粤剧艺人薛觉先、马师曾分别在“觉先声班”和“大罗天剧团”“太平剧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们在艺术上切磋砥砺、并驾齐驱,推动粤剧艺术创新发展,开创了粤剧史上的新局面,这一时期被称为“薛马争雄”时期。[1]
“薛马争雄”是粤剧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转折点。它不仅仅是粤剧本身的变革,也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所进行的传统戏曲的改良。由于薛觉先、马师曾在理论上、实践上引领潮流,在中华文化及粤剧本身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其他剧种和其他艺术的精华,粤剧因此确立了“保持传统,求新求变”的特色,得以成熟和发展。以前学界对“薛马争雄”现象关注不多,本文深入分析其产生背景及薛觉先、马师曾的粤剧改革思想。
一、外界压力和粤剧困境
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戏剧的教育作用十分重视。1904 年在上海创刊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即呼吁戏曲要为民主革命服务;1905 年,陈独秀撰文称赞戏曲的作用,认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与此同时,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戏曲剧目创作发表,“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3]但随着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涌入,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学、传统戏曲鸣鼓而攻,力图建立更为“先进”的新文学、新戏剧。
新文化运动发动之初,传统戏曲即成为被批判的“旧文学”“旧文化”代表。1917 年3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3 卷第1 期刊发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认为“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但往往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4]。钱玄同的意见得到刘半农、胡适等人呼应,开启了批判旧戏的序幕。《新青年》继而开辟专栏讨论戏曲,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陈独秀等对传统戏曲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旧戏必须按照西方戏剧进行改造,并将戏曲编制概括为“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5]。其中改良戏曲的意见可以参考,但一些断语过于偏激,而要求中国戏曲全盘按照西方话剧的创作方式进行改造则更不可行。
粤剧的改革当时已经开始。辛亥革命时期及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形式,优天影、振天声等粤剧戏班还把戏棚官话(中原音韵,即桂林官话)改为“白话”(广府方言),其后一些“大老倌”如朱次伯、金山炳、白驹荣等在某些戏或某些唱段中用白话演唱。但经过二十多年,粤剧演出仍停留在“半官半白”的状态,同时,因为社会生活、文化潮流已经有了诸多新变,传统粤剧与时代发展和观众需求有了更大的距离:一是剧目和表演多陈陈相因,不乏恐怖迷信、低级趣味、博人眼球的内容;一是部分艺人德行有失,为人诟病;加上旧戏院环境嘈杂污浊,也令不少观众望而却步。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在美国有声电影的冲击下,粤剧严重不景气,很多戏班解散,艺人失业,戏院关门。据统计,从1930 年至1934 年,广州电影院已达21个,总座位20 000 个,还有3 家电影院在兴建中,各影院一般每天放映4 场,而粤剧仅10 个演出场地,一般每天只有2 场,且总座位只有影院的一半。进入20 世纪30 年代,戏院常因营业不佳而歇业,海珠、河南、太平戏院开始兼放电影[6]。此时“戏班衰落,为数十年来所未有,伶人失业者共四千余名之多,其中女优及未正式加入八和会者尚未计算在内。无职伶人为生活所驱,沦为乞丐盗窃者,报章常有记载。”[7]
粤剧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此际,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东的文化和教育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报刊、文艺团体不断出现,粤剧在南北交流、中西碰撞中也得到新的发展。部分艺人求新思变,从内容到形式对粤剧进行了一系列革新。领导这场改革的就是“大老倌”薛觉先和马师曾。
二、薛觉先“融汇南北,综合中西”
1927 年,薛觉先从上海回到广州,应广州协和公司总经理刘荫荪邀请,加入新组成的“天外天”班,从此开始进行从编剧到舞台艺术的改革。1929 年“觉先声”剧团成立后,薛觉先更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和创新。
薛觉先注重编剧,废弃“总纲戏”“提纲戏”,杜绝“爆肚”(即兴表演)、“吞生蛇”(不熟悉剧本台词,临时瞎编),要求排演忠于剧本,唱、做、念、打不得随意改动,极大地保证了演出质量,促进了粤剧思想性、艺术性的提高。他博采众长,向靓元亨、新珠学习粤剧传统的武戏和文戏艺术,同时吸收其他艺术形式服装、化妆、布景和音乐伴奏的优点,将京剧架子、排场、行头尽量移于粤剧;采用小提琴及中、低音乐器伴奏,引进京剧武打技艺。他开男女同班风气之先,破除“红船”陋习,收徒时废除“师约制”,又整顿台风,维持剧场秩序。[8-9]在唱腔上,薛觉先借鉴京剧唱腔,吸收江浙小调、流行曲轻快流畅的风格,创出字正腔圆、韵味十足的“薛腔”,同时融合京剧的武功、身段,结合电影表演艺术、现代舞美技术,开创了“北派”艺术新风,使观众耳目一新。薛觉先技艺精湛,文武、反串、生旦、丑戏都很擅长,荣膺“万能老馆”称号。
薛觉先的戏剧思想,集中体现在1930 年出版的《觉先集》自序。1936 年重新刊发,题为《南游旨趣》,表述了他的戏曲改革观点,包括对粤剧表演、剧目建设的主张和态度。
薛觉先首先阐明,戏剧的意义重大。他认为,戏剧有教育功能。“国家强盛之道,不在坚甲利兵而在教育普及;人类进化之机,不贵物质进步而贵风俗文明,此中外哲者之所公认也。戏剧虽云小道,实能易俗移风,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功莫大焉。”他提出,提高戏剧地位,首先要提升艺人的学识、修养、人格,提高艺人和戏剧的水平之后才能提升戏剧的地位、发挥教育作用:“觉先不敏,幼研乐歌,即欲改革戏剧,破除陋习,灌输剧员之学识,修养剧员之人格,提高剧员之地位,以兴起国人注重戏剧教育之观念。”[10]
薛觉先介绍了自己十余年的努力和改革实践:“年来融会南北剧之精华,综合中西音乐而制曲,凡演一剧必有一剧的宗旨,每饰一角必尽一角之个性。以言发抒革命真理,则《爱情非罪》颇能阐微;以言改革锣鼓喧呶,则《还花债》实称创作;《可怜秋后扇》儆自杀之颓风,《三五鲁难记》写国耻之痛史。凡此种种,聊尽寸心,用奋艺术之精神,敢负观众之期望哉。”[10]
薛觉先进而表明,传统戏曲改革的目的,是贡献于世界文化之林:“觉先之志,不独欲合南北剧为一家,尤欲综中西剧为全体,截长补短,去粕存精,使吾国戏剧成为世界公共之戏剧,使吾国艺术成为世界最高之艺术,国家因以富强,人类借以进化,斯为美矣。”[10]
《南游旨趣》既是薛觉先粤剧改革的理论宣言,也是实践总结。他重视剧目的思想性和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认为戏剧应表现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主题,进行社会教育。他“合南北剧为一家”“综中西剧为全体”的努力,推动了粤剧的创新和发展。
三、马师曾的“新派剧”主张
与薛觉先相似,马师曾粤剧改革的思想基础是“爱国”,是“自葆其国有之道德文化”。他自信地说,中国戏曲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可以“补教育之不逮”,可以“改造社会”[11]81。他力图纠正当时一些对传统道德文化全盘否定的倾向,批评他们“莫不唯欧美是效”,认为可以取长补短,但是不能将自身精华丢弃:“夫取他人之长,以补吾所短,此固谦受益之义也;奈何嗜新忘旧,至于糟粕道德,稗秕仁义……举我国数千年特有之道德文化,几于摧残净尽,不独不能化人,且将被化于人,此则有心人不胜为之浩叹者矣。”[11]77-78
马师曾同时认为,戏曲在道德文化内核上需要坚持,但在形式上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为观众了解和欣赏。1931 年出版的《千里壮游集》中有他对当时粤剧的弊端和危机的描述:“近年以来,中外的交通,多么利便,生活的变迁,多么剧烈,我们的伶人,依然死守着什么场口步武的成法,什么靶子演唱的老例,纯粹用图案做脊椎,决不能站起来自称艺术,在电影戏和舞台戏的激烈竞争当中,哪有不一败涂地的道理呢!”[11]79
马师曾有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亲自参与撰写的剧本达九十多个。他的上述论述,既有对戏曲的教化作用的认识,也继承了传统文学理论中“趋时”“参伍因革”“酌于新声”的“通变”观[12]。他提出的“艺术虽不是为人生,人生却正是为艺术”口号,是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文艺,包括“为人生”与“为艺术”论争的一个呼应。他更将粤剧作为艺术,认为粤剧创作需要深度的探索,需要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
马师曾明确说,自己的艺术改革是新文化影响下的“革命”,新的剧目是“新文化的簇新作品”:“师曾自从南洋归来,在大罗天剧团,眼见粤剧万分寂寞,感觉得艺术虽不是为人生,人生却正是为艺术,便本着革命的精神,努力奋斗,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放着胆子,打倒千百年的老例,先后编演《贼王子》《子母碑》《欲魔》《冷月孤坟》《飞将军》等新文化的簇新作品,差幸备受了社会热烈的欢迎;现在还不敢自满,又新编了一出《秘密之夜》,迸出一朵从来没有开放过的艺术鲜花;更给香港钟声慈善社剧部,饰阿露佛伯爵,拍演《璇宫艳史》,准备和有声影片,争一回胜利哩!”[11]79-80
马师曾1933 年在《伶星杂志两周年纪念专刊》中具体说明他变革粤剧的主张是“一方固须效他方之长,一方仍须保存粤剧之精华,从而发扬之”,“将舞台原有粤剧加以一度之变革”而成为“新派剧”。他阐明了对音乐、舞台、排场的改革要求,并提出:“一剧分幕,不宜过多,多则易使剧情流于松弛。每一本剧最高限度,由八幕至十幕足矣。剧情为戏剧之灵魂,表演为戏剧之骨干。剧情固属重要,而剧员表演之技巧,则尤须特别注重也。表演之技巧深刻老到,虽平凡之剧本,成绩仍有可观;若对技巧衍敷,则虽有名剧,上演后无有不失败者。”[11]85-86这其中凝聚了马师曾的编剧心得和舞台经验。
1925 年至1929 年,马师曾主持大罗天剧团时,即打破过去一个戏班只有一名“开戏师爷”(编剧)的惯例,特设“编剧部”,聘请多名编剧合作,大量推出新戏,新编词曲,使用广府方言,并大量吸收木鱼、龙舟等民间文艺形式。欧阳予倩在1929 年的《戏剧》第2 期发表《书〈粤剧论〉后》,对马师曾予以大力支持:“马师曾唱平喉,许多人骂他。平喉吐字容易清楚,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法子。再者,师曾用的词句,的确有很粗俗的地方,不过能运用俗语却是很好。”马师曾勇往直前,带动了许多人参与,莫汝城先生总结说,20 世纪30年代初,粤剧“广府班”除了传统戏中的某些专腔仍需用“官话”唱外,其余都可以用广府方言演唱,基本完成了从“官话”改唱“白话”的变革。[11]3
马师曾在《苦凤莺怜》一剧扮演义丐余侠魂时,吸收卖柠檬小贩声音沙哑而咬字清晰的特点,创造出独特的“柠檬腔”,又称乞儿喉,悠远动听,人称“马腔”。他将导演、排练制度引入粤剧,把背景、灯光等舞美技术用到粤剧舞台,设立男女同台演出的“男女班”,推出新编剧目、引进西洋乐器,极大地丰富了粤剧的舞台表现力。
四、“薛马争雄”的意义和影响
“薛马争雄”主要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到30 年代中期的十年间。薛觉先和马师曾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素养比较高,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热爱戏曲艺术;他们并非从小科班出身的“红裤仔”,但勤学苦练,粤剧素养扎实丰厚。高瞻远瞩的“文化自信”,是大刀阔斧“改革”的基础。他们善于学习其他剧种精华,借鉴外国戏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法,对粤剧进行了编剧、表演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薛觉先、马师曾在艺术上的良性竞争和创新实践,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戏曲思潮涌动和粤剧发展受困且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进行的。他们的改革也有明显的共同点:首先,确立“以我为主”的方针,在传统粤剧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发挥个性,大胆创新。其次,重视剧本,重视演出效果。粤剧编剧在这个时期得到空前的重视,薛觉先、马师曾都分别有四五个编剧人员组成的班子,负责编写新戏、策划演出;马师曾的太平剧团,大约一周左右就推出一套新戏。他们密切关注观众和市场反馈,随时修正编剧手法和经营方针。薛马二人都直接介入一线创作,创作出许多好戏,有宣传新思想、批评时弊的粤剧,如薛觉先编写的《爱情非罪》《可怜秋后扇》《毒玫瑰》和马师曾编写的《苦凤莺怜》《子母碑》;也有将外国作品改编而成的粤剧,如薛觉先的《白金龙》《胡不归》,马师曾的《贼王子》《蝴蝶夫人》。再次,结合时代特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在剧本和演出中结合时代新思想新形式,反映时代呼声。抗战期间,他们都以粤剧为武器,宣传抗日,奋起救国。薛觉先编演四大美人戏《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赋予她们强烈的爱国思想,马师曾以《爱国是侬夫》《还我汉河山》《洪承畴》等剧号召抗日救亡。他们多次领导参与抗日活动,抵制汉奸卖国,利用舞台宣传抗战。
在薛觉先、马师曾的带动下,粤剧界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使剧坛风貌大为改观,编剧、表演、舞台不断完善。许多优秀艺人努力探索,使各自的表演艺术趋于个性化,形成了粤剧五大唱腔艺术流派,即薛觉先的“薛腔”、马师曾的“马腔”、廖侠怀的“廖腔”、桂名扬的“桂腔”、白驹荣的“白腔”。他们的风格各有特点,极大地丰富了粤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此外还出现了白玉堂、陈非侬、靓少华、靓少凤、靓少佳、靓荣、新珠、曾三多、嫦娥英、谭兰卿等一大批著名艺人,可谓群星熠熠。
薛觉先、马师曾在艺术上的“争雄”,推动了粤剧的内容上和形式上的现代变革,促进了粤剧创作的繁荣、声腔流派的形成,带动了粤剧界的新风,这个时期因此成为粤剧发展史上最为生气蓬勃的年代,可谓新剧频出,异彩纷呈。虽然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光怪陆离的负面状况,但总的来说,粤剧艺术的提升和进步有目共睹。粤剧此际的“革命”,也是传统戏曲改革的重要内容。如同徐慕云《中国戏剧史》所言:“粤人富于革命思想,戏剧虽小道,但粤伶亦每能日新月异,力谋改进。二十年前苏州妹、李雪芳等所演之戏,即与近年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肖丽章诸人所表作者,大相悬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