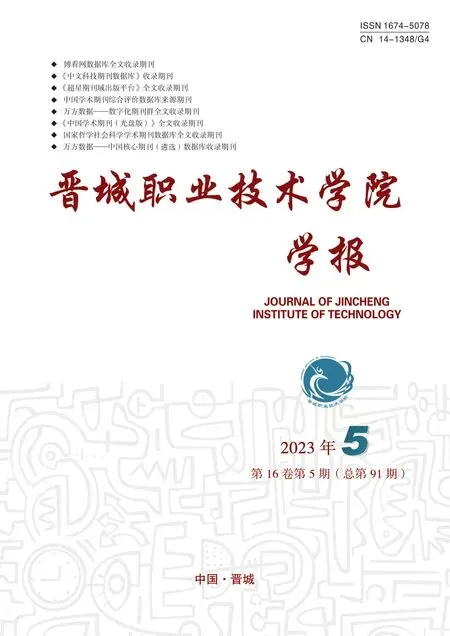基于马克思女性主义的拜占庭史家女性书写探究
——以安娜·科穆宁为例
杨起帆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太原 030006)
安娜·科穆宁(AnnaKomeneos,1083—1153)是一位具有卓越影响力的拜占庭女性历史学家,她出身皇室,系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统治者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IKomnenos,约1056—1118)膝下长公主,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可以直接接触宫廷事务的高贵出身为她日后的历史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她的代表性著作《阿莱克修斯传》高屋建瓴地述写了其父阿莱克修斯在位时期拜占庭帝国行政、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历史,由于作者笔触生动、史学素养优秀、史家操守坚纯,凡所记述务求客观中立、如实直书,加之其所记述史事又多为亲身经历,故安娜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她本人也被历史学者J.W.汤普森称为远超同侪的“最卓越的历史学家”“中世纪最杰出的妇女之一”。[2]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阐释了女性权利在阶级社会中受到的系统性剥夺。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以莉斯·沃格尔(Lise Vogel)、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女性问题,通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来研究妇女在阶级社会中所扮演角色受到的异化与禁锢,马克思女性主义应运而生。
若以马克思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安娜·科穆宁的著作,则不难发现,尽管安娜出身皇室,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食利阶级,但其作品中在女性视角下对女性历史人物的记述、女性扮演角色的思考与女性不公地位的抗议等诸多女性主义的书写使她突破了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成为引领一个时代女性觉醒的进步力量。
一、人身依附:安娜·科穆宁所揭示的女性困境
安娜的著作《阿莱克修斯传》虽以其父为名,但并非完全是阿莱克修斯皇帝的个人专传,其中亦以女性的视角记述了许多来自各个阶层的、血肉丰满的女性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也在书写中揭示了她们所面临困境的共同指向:封建社会下,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在书中,她通过记录身处政变两方的女性所遭受的不同苦难,揭露了造成双方苦难的共同根源。
一方,是科穆宁家族的女性家眷。阿莱克修斯·科穆宁虽贵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但其皇位却非以父死子继的正常程序获得,而是来自一场宫廷政变。根据安娜的记述,阿莱克修斯本是尼基弗鲁斯三世皇帝麾下的统兵将领,因与皇帝的两位宠臣政争落入下风而担忧被杀害,故决意同兄长伊萨克·科穆宁(IsaacKomnenos)合谋抢先发动政变撷取皇权,以防“皇帝听信二人的诋毁”。[3]49-55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压力下,阿莱克修斯与伊萨克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召集军队,宣告举事,但安娜此刻的叙述笔触却突然转向城内科穆宁家族和出身科穆宁家族的女性家眷,她们在这场政变中“被留在君士坦丁堡广场上”[4]56——由于科穆宁兄弟为保护自身生命亦为撷取权力的冒险举动,致使科穆宁兄弟的妻子、家族中的女性亲友陷入了比他们自身更加危险的境遇中。以马克思女性主义的视角观之,驱使科穆宁兄弟做出以牺牲家族女性为代价换取自身脱身的决定之根源,正是阶级社会财产私有制下,由封建家长制与封建包办婚姻所维系的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女性对财产支配与人身健康权利行使的不自由与不充分。作为封建家长的男性可以直接支配女性伴侣或亲属的一部分或全部的个人财产、情感生活乃至于人身自由,其缔结婚姻关系的本质目的亦是在封建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背景下确保权力与财产的继承,这种婚姻形式,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总结的“建立在丈夫统治之上的”专偶制婚姻。[5]66于是,以封建家长典型的“物权支配”观念看待家庭与婚姻的科穆宁兄弟,便视依附丈夫的妻女为用以博取更大利益的“私人财产”,作为筹码摆上了权力游戏的赌桌。
另一方,是尼基弗鲁斯三世的皇后玛利亚。她身为帝国皇后,却与科穆宁家族的女性一样在遭受苦难,且造成苦难的根源与后者完全相同。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6]87玛利亚皇后的经历亦在印证恩格斯的观点。玛利亚本是封建包办婚姻下前任皇帝米海尔七世的皇后,并与其育有一子,当米海尔七世被尼基弗鲁斯三世经由政变推翻后,为了保护自己与前朝皇帝的幼子,她又不得不委身于推翻丈夫的政变者。在阿莱克修斯起意发动政变时,又以让米海尔七世之子君士坦丁作为皇位继承人,并与自己的长女缔结姻亲关系为条件,换取了皇后玛利亚的信任与帮助,然而在已经登上皇位的阿莱克修斯的长子约翰出生后,这份约定又很快被废弃,君士坦丁的继承权被黜落,玛利亚也被迫进入修道院了却余生。在讲述这段史事时,安娜的文字对皇后玛利亚这位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女性倾注了许多感情,甚至可以说将自己移情其中——她亦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懵懂的婴儿状态下便被父亲作为谈判的筹码,以一种典型“买卖婚姻”的实质方式许配给了未曾谋面的玛利亚皇后之子君士坦丁,当阿莱克修斯毁约后她又在父命下与尼基弗鲁斯·布林努斯结婚,被迫开启了两段都很难称之以“美满”的婚姻。或许也正因如此,某种意义上身处受害者与被压迫者立场的安娜方能在书写中以女性更加细腻柔软的道德情感观念重新审视这场政变对女性也对无辜受到波及的百姓所造成的伤害,揭露着封建社会中被视为“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乃至于“物品”的女性在家庭生活和政治运动中被强制依附于男性生存所感知的恶意和敌意,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迷茫、不安与彷徨,就像在政变的刀兵交锋中身不由己的玛利亚皇后,既在等待并恐惧着宫殿外战斗止熄的信号,也在等待并恐惧着战斗胜利者对自己命运的宣判,如同海伦恐惧着那“浅色头发的墨涅拉俄斯”。[7]71
以莉斯·沃格尔为代表的一部分马克思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就女性在阶级社会受到的压迫问题而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女性同样处在由家庭和社会施加的系统性压迫中,换言之,在阶级属性上她们或许分处于食利者和劳动者两个阶级,但在另一个反抗封建家长人身支配的维度下她们又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8]玛利亚、安娜和其他科穆宁家族女性的命运与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沃格尔的观点,她们可能短时间内生活优渥,衣食无忧,但在封建家长制所维系的人身依附关系下,她们既无独立的经济来源又无脱离家庭背景可独立存在的社会地位,又如恩格斯所言,肩负着没有爱情支撑的、无偿的生育义务,这便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层面压制了封建社会的女性地位,安娜的撰著便将她所处时代拜占庭女性的困境揭示在读者面前。
二、反对异化:安娜·科穆宁所提出的女性诉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社会中劳动与劳动者被异化的根源在于分工,马克思女性主义学者在前人理论基础之上将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家务劳动自然分工引入了和真正的社会劳动分工等同的批判领域当中。[9]中世纪基督教道统伦理和拜占庭传统封建道德要求的双重桎梏下的拜占庭帝国,女性身为男权社会的它者被扭曲、被异化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更甚于后世。在基督教伦理下,她们和她们的子女是父权与夫权的附属物,需与丈夫一损俱损,女性被要求深居简出,与其说被拒绝参与劳动,毋宁说她们被排除在一切的公共事务之外,剥离了政治参与、经济支配、人格独立的权力,被家庭分工异化为操持家务和生育后代的生产工具,成为波伏娃笔下被封建强权塑造的“逐渐形成的妇女”[10]。尽管基于时代的局限,安娜对于妇女被异化根源的认知是朦胧的,但她亦在文字中表露了对有类于此现象的抗议,基于实践地提出了身处女性立场的诉求。
安娜对女性被封建社会家庭分工所异化之现象的抗议流于文字的部分是细微且隐晦的,她更倾向于有选择地花费大量笔墨书写倾注入如前皇后玛利亚这般能令“蛇发女妖戈尔贡为之惊奇”[11]74的、兼备美与善又命运多舛的女性,将她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容貌同她为求自保反复委身多个男人,又因阿莱克修斯的背约而最终软禁幽居修道院的悲惨命运相互映衬,以真实发生的一位女性从希望到幻灭的历史事实揭露于后世读者面前,继而试图去唤醒与玛利亚所共情者的觉醒与抗争。而安娜在书中为数不多的直抒对某些女性受到不公正对待现象质疑的文字在于阿莱克修斯政变成功登上皇位后,由于政变中他带领军队“全部进入城市为居民招致难以完全描述的灾难”[12]80致使他陷于良心的不安与自我谴责中,便不得不向大牧首与主教们寻求告解,希求通过得到惩罚而向上帝赎罪并告慰死难者。大牧首从善如流地执行了阿莱克修斯的请求,判处他应当接受相应的惩罚,但不仅要惩罚阿莱克修斯,“所有参与举事者都要受这样的惩罚,就连他们的妻子也无法摆脱接受同样的惩罚”[13]80。毫无疑问,这对举事者的妻子而言绝非受到忒弥斯祝福的裁断,她们身为被排除于绝大部分公共事务之外的女性此前可能从未听说丈夫将要参与谋划一场针对帝国最高统治者与最高权力机构的宫廷政变,更遑论承担其中伤害百姓、亵渎神明的罪责。且政变开始之时,她们被丈夫和父亲当作筹码与诱饵抛出,留在了城中最危险的地方,直面皇帝的雷霆震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她们更像是这场政变的受害者。安娜也就此在她仿照修昔底德客观冷峻的笔触,自诩“记叙每件事情时都力图保证记载的准确”的史家撰著中,第一次发出带有强烈情绪化的抗议:“这是为什么?仅仅是由于她们爱自己的丈夫?”[14]80
同表达抗议的方式一样,安娜也将她代表女性的诉求隐入字里行间的暗示中,以对女性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她们命运的述写徐徐表露。尽管科穆宁家族的家眷被留在城中,面临危险,但她们最终并未受到更多实质性的侵害,其中引导她们转危为安的契机,在于一位重要的女性,阿莱克修斯的母亲、安娜的祖母——安娜·达拉塞纳。当政变已为皇帝的人手所知晓,达拉塞纳当机立断带领家眷前往圣尼古拉教堂避难,并以急智与口才谎称自己是“花光盘缠来此休息的东方女子”[15]57,获取了教堂卫兵的同情和信任,得以使女眷托庇其中。在第二天她又和儿媳一道同皇帝的来使交涉,声称自己的儿子阿莱克修斯起兵非为谋逆,实为“铲除奸佞小人,维护皇帝的统治”,并果断以死相逼,换取了皇帝以宗教名义对她们人身安全的担保。当阿莱克修斯登上皇位,她又以太后的身份摄政,帮助其子处理了几乎全部的帝国政务,稳定了政变上位之初暗流涌动的政坛格局,使阿莱克修斯可以安心在前线征战,对抗趁帝国内乱借机入侵的外敌。值得强调的是,达拉塞纳所摄政辅佐的皇帝,并非年幼登基致使主少国疑者,而是在此之前就能领兵征战,参与帝国政治斗争,并策动一场政变成功登上皇位的,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换言之,她并非如某些参与摄政的太后那般仅仅作为稳定人心的花瓶,实际的国家治理皆交由男性廷臣,而是一位行政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得到皇帝认同乃至于依赖的强大女性,以至于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她的诏令与我的具有同等效力,任何人不得拒绝,应当视之为法令并且在未来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16]82可以说,达拉塞纳这名女性历史人物的存在本身以及安娜史笔下对她的大书特书本身就是安娜诉求最直接的表达——安娜·达拉塞纳身为女性对家族的挺身保护、对财政的自由支配、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和对国家的直接治理等诸多作为既是安娜对那个时代女性权利的期许,亦是对女性脱离被封建父权、夫权所强加的异化身份的渴求。她也在人生中践行着她的诉求,当第一任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丈夫君士坦丁英年早逝,第二任丈夫布林努斯竞争继承人失败,弟弟约翰二世最终荣登皇位,自幼受到祖母影响,梦想参与国家治理幻灭的她做出了和父亲同样的选择,以女性之身组织起一支军队发起了政变,这场政变尽管很快被镇压,身为发动者的安娜亦被软禁入修道院中了却余生,但究其意义,这便是那个时代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一次撼动封建父权、夫权的尝试。
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正是作者晚年政变失败幽居修道院中所作,撰著者的思想经历了从希望到破灭,从破灭到抗争,再到二次破灭的过程,从梦中的理想不得不回归现实的思考,由是作者阐发了基于女性立场对异化、压迫女性的宗教道统、传统道德和家庭分工系统性的抗议与改变现状的诉求,并经由笔下历史人物之口向读者表达,诉说了让“所有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务中”这一解放女性的必由之路。
三、填补缺位:安娜·科穆宁所代表的历史意义
长久以来,古代社会诸多文明以男性视角书写的文史作品层出不穷,在这些作品中女性的存在感以缺位居多,更有甚者,其中男性以女性的“物主”与“支使者”的形象出现,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揭露的:“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17]66“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18]72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中,女性亦被视为具有性别缺陷的,地位几近与奴隶等同的“不完全的人”。事实上,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封建时代下带有系统性歧视女性的古希腊文化底色之政治实体,在其相关史料中,几乎不存在为女性提供系统性公立教育的相关具体证据。[19]换言之,除了自学与接受家庭教师的私人教育外,女性被断绝了接受教育并成为知识分子的渠道,由是进一步构成了拜占庭帝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女性失声与缺位的局面。
在女性受教育权利被剥夺,女性发声渠道为人扼断的境况下,安娜以女性视角对女性历史人物的书写、对女性解放意识的表露,就显得弥足珍贵。她通过史笔的娓娓述说,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彰显女性主体意识,构建女性身份认同,真正意义上填补了这一时期拜占庭文史作品中,女性主义书写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