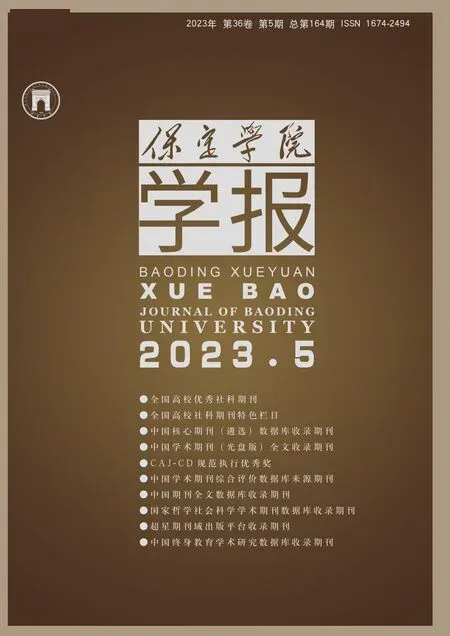中国古代戏剧中王安石形象的多维透视
张 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王安石作为宋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受到了后世剧作家的青睐。从宋代的滑稽戏到明清传奇,王安石的形象得到了多方面展示,这也关涉到了戏剧本身创作倾向的微妙演变。对历代荆公戏进行系统整理,不仅有利于拨开其形象的历史迷雾,也有利于还原剧作者的创作心态并剖析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学界对此已有所关注①如陈东的《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形象》(《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郭羽的《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四川戏剧》2006年第4期)以及王兴君的《论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形象》(《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对元杂剧中的王安石形象进行了论证剖析,另有邓乔彬、夏令伟的《宋代滑稽戏与宰相》(《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提及了王安石与宋代滑稽戏的关系。,但总体来说尚缺乏对古代荆公戏的综合分析。
本文据《明清传奇综录》[1]、《清代杂剧全目》[2]、《古典戏曲存目汇考》[3]和《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4]等书目,整理出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荆公戏共19部,其中宋代滑稽戏5部、元明清戏剧14部。宋杂剧文本简略,散佚严重,目前仅存条目和演出情况的相关记载,分别是:《跨驴上殿》[5]、《僧道献图》[6]、《甜采即溜》[7]、《救护丈人》[8]和《王安石改科举》[9],因其剧目原作者和呈现形态与元明清的成熟剧本相异,因此单独整理。元明清14部相关剧目的存佚情况如表1所示,后文所引皆据表1中版本,故不再赘述。其中元杂剧共有6部,在数量上位列第一,14部元明清戏剧中保存完整的有8部,其余6部已经亡佚。对剧本内容及其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可以从多个角度透视王安石的复杂形象,归纳出历代荆公戏的组织模式和艺术特点,并对“荆公入戏”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阐释。
一、荆公戏的编演模式
王安石政治地位高、名声大、性格执拗且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因此一些来源于史实的片段被反复利用和加工,剧作中王安石这一形象的建构也经过了主客观的双重改造。以下根据戏剧中的情节与王安石本事的关系,把编演模式大致分为因史演事、剪裁嫁接、戏谑编造三种不同的模式加以分析,这对于把握剧中的荆公形象有所助益。
(一)因史演事模式
戏剧本就有以史为源的传统,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推行新法,不仅牵动了北宋朝政,也影响了大批文人的命运,因此因史演事是荆公戏最常见的组织模式。这首先体现在剧作家对新旧党争的态度上,戏剧创作往往将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化为奸忠两派,只对重要的历史因素予以保留。剧中王安石和吕惠卿等新党人物被捆绑在一起构成了戏剧中的反派群像,正面角色则由旧党的司马光、苏轼、苏洵、郑侠等人担任。像清代乔莱的《耆英会记》就是因史演事的典型剧本,该剧讲述的是一批大臣因反对新法而被渐次贬谪、相聚在洛阳结社赋诗的故事。“耆英会”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事件,正源于史实记载,据《宋史》载:“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谓之耆英会,好事者莫不慕之。”[10]10263-10264由此可见,熙宁变法的相关史实是荆公戏的重要源泉。
宋代的滑稽戏虽然并不具备成熟的杂剧形态,但是相关的故事仍和史实紧密相关,譬如伶人不满王安石的新政,便通过表演逗趣的方式对皇上进行劝谏,其中比较著名的伶人就有北宋时期的丁现仙,熙宁时期有“台官不如伶官”的说法[11]。元代陆显之的《碎冬凌》也是根据变法衍生的剧本,此剧剧文虽已佚失,但是所述的核心情节是熙宁变法时期王安石捣碎冬凌的事件,相关内容可以参考宋代笔记小说《东轩笔录》:
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设巨碓捣流水而役夫苦寒,死者甚重。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去磨平浆水,今见碓捣冬凌。”[12]
可见《碎冬凌》这一剧目创作也发源于史实,是借戏文表现变法所导致的民生疾苦。此外,因史演事还体现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上,荆公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情节有“流民图”一事,这一情节在《金莲记》《眉山秀》《四元记》等剧本中都有出现,故事的呈现也较为接近。主要讲述郑侠作为监门,目睹百姓为新法所累的景象后,将流民的惨状绘成图上呈皇帝,说是王安石的新政导致了天下大旱,最终促使王安石罢相,历史上确有此事原型。郑侠作为王安石的门生,他对新法的反对也进一步突出了王安石“不得民心”,加上“天谴”“预言”所携带的传奇色彩,致使这一史实被众多剧本吸收,“流民图”成为戏剧中正派扳倒王安石的重要回目。而吕惠卿对新党人物的迫害,乃至于背叛王安石的情节也与历史现实相符。综上可知,史书甚少记载王安石的风流韵事和生活趣闻,故而剧作家大多聚焦于政治变法的相关史实,因史演事也就成了荆公戏最常见的组织模式。
(二)剪裁嫁接模式
剧作家出于演出效果的需要,会对王安石的相关本事进行移接,实现对现实的艺术建构。这种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时空进行压缩,删繁就简,去除与戏剧主题无关甚至相悖的部分,只保留历史的大致原貌,将重要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加强戏剧效果;二是采撷历史上的传闻,进行人物替换,将本不属于王安石本人的罪名或者事件加诸其身,进一步印证主题和推动情节发展。比如关于王安石的任相,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早在仁宗期间,王安石就多次上书改革,但并未被采纳,后又经历了宋英宗、宋神宗,直到他五十岁左右才得到重用。戏剧往往模糊了他仕途的具体时间线,省去了改革的背景和王安石的坎坷经历,直接以王安石入主朝堂为始。并且在变法后期,王安石曾经两度罢相,第一次退居江宁以后神宗依然召请他回朝,但几乎所有剧本都对这些经历只字不提,只简单地将变法失败浓缩为第一次罢相。也正因为这种时空上的压缩和剪裁导致了政治斗争的简单化,人物关系也进一步对立,出现了“一言不合就贬官”的戏剧模式。像明代汪廷讷的《三祝记》更是对整个北宋时空进行了剪裁和压缩,王安石和范仲淹本不属于同一批在朝为官的官员,作者却将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的时间提前,使得两人在朝堂上相遇,显示出部分戏剧在时间安置上已经脱离了史实本身。
除了时空,情节本身也被剧作家剪裁和嫁接,这主要体现在王安石和苏轼的“对手戏”上。在元杂剧中,除了已经佚传的《荆公遣妻》和《碎冬凌》两部,其余戏剧都褒扬苏轼为理想人格,贬低荆公为乱政贼子。当需要突出苏轼等旧党人物命运坎坷、形象高大时,便故意将王安石设计成反派角色。故而元杂剧中的王安石性格特征比较单一,相应的唱词宾白并不多,且常有雷同。《东坡梦》《贬黄州》《满庭芳》所述皆为苏轼因续写菊花诗和调戏王安石夫人被贬,这些作品大多进行了故事嫁接和细节夸张。如“续写菊花诗”一事本为王安石与欧阳修之事,然而在戏剧中却成了苏轼不知黄州菊花谢,贸然续写菊花诗,被王安石记恨而将其贬去黄州看菊花[13]。另如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并且还曾替苏轼求情,戏剧却将李定与苏轼的矛盾转移到王安石身上,把苏轼一生最大的坎坷归罪于王安石,加剧了两位名人的戏剧冲突。虽然元杂剧中的新旧党争为历史事实,但是剧作家在考量艺术效果时为了进一步强调矛盾冲突,选取了重要的情节进行一系列的嫁接和夸张,强化了戏剧冲突,使得情节更加紧凑和曲折,也导致了相关人物形象黑白分化。
(三)戏谑改造模式
戏剧作为舞台艺术,势必会通过趣味性的虚构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深入人心的艺术效果。加之王安石本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因此借他之名虚构出来的情节和人物也不少。戏剧家对于风情故事情有独钟,但因王安石从一而终,又一生醉心于政治改革,不像其他文人三妻四妾,所以流传下来的风流韵事极少,故很难生成风情戏。但这并不代表荆公戏的艺术虚构无处施展,剧作家对王安石形象仍然有不少编排改造的地方。以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本事为例,剧中的苏轼作《满庭芳》调戏王安石夫人从而触怒王安石的故事情节,既显示了苏轼的才学与潇洒,又符合观众消遣的审美趣味,因此被不少文人引入剧中,比如《贬黄州》《东坡梦》《满庭芳》等。这一本事于史无征,系剧作家根据苏王关系和词文内容主观编造而成的。
除此之外,清代四愿居士的《四元记》编写了王安石膝下只有一女,名为方雲。王安石却十分想要男孩,方雲为此女扮男装。但历史上王安石并没有这个女儿,而是三子三女,长子曰“雱”,方雲正是由此字拆演而来,一女夭折,另外两女分别嫁于吴安持和蔡卞[14]。《四元记》剧中的男主人宋再玉装扮成尼姑躲避王安石的招亲,王安石的女儿方雲却扮作男子去祈福,这种男女互换的戏谑情节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增强了戏剧的娱乐性。由此可见,戏剧家对于王安石的亲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编排改造,这样生发出来的情节与史实相去甚远。
另外,党争的相关情节也被改造得更具有戏剧风味。如李玉的《眉山秀》在党争之余增添了王安石之子王雱求娶苏小妹不得而怀恨在心,这显然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正反关系臆想出来的,显示了戏剧对现实的改写。还有苏洵写《辨奸论》批判王安石,这本是党争事实,这一本事被李玉改编为苏洵本来和王安石关系尚佳,苏洵在为被贬的富弼送行后,目睹了流民之苦,于是酒后对王安石破口大骂,特意写下《辨奸论》来批判王安石。苏洵的醉酒宣泄无疑是剧作家编造的艺术手笔,这样的安排使得剧情更加紧凑和颇具抒情效果。显然,荆公戏利用戏谑改编的手法,使得原本平缓的情节走向陡峭,增强了戏剧的起伏性。
这些趣味编排,一方面,正面人物的性格特点得到了更好的展示,也反映了剧作家对王安石形象的认识。另一方面,戏剧的冲突性和趣味性得到了提升,能够更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总而言之,这些趣味性的编排增加了戏剧的看点,增强了荆公戏的艺术魅力。
二、戏剧中荆公形象的多维透视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荆公戏的呈现是历史客观和剧作家主观意图双重作用的产物。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使他饱受争议,其形象评价历来呈现毁誉参半的状态,戏剧中的荆公形象同样复杂。以下从政治、生活和学术三个角度对其形象进行审视。
(一)性拗而专权:朝堂之荆公
作为北宋变法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在戏剧中呈现出的形象首先就是一位新法的坚定推行者。在荆公戏中,除了《荆公遣妻》这一元杂剧完全取材于轶闻趣事,其他尚存的8部戏剧都和变法有关。在这些戏中王安石主要是充当推动情节发展的“贬官者”,这一形象在苏轼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东坡梦》《满庭芳》《赤壁赋》《贬黄州》《秦苏夏赏》《金莲记》《眉山秀》等剧作都突出了苏轼被贬是因为他不满新法改革,又逢王安石掌政,故而多遭迫害,以元杂剧《贬黄州》为例:
(苏轼面圣前)下官前日具疏,论王安石之奸。不想李定党比王安石,劾奏下官赋诗毁谤朝廷。主上听信,将下于大理狱。要处以死。[15]214
(马正卿开场词)因王安石柄国,某在朝与他言论不合,致政来家,十分自在。近闻学士苏子瞻。上书发王安石之奸,反被言官论劾,贬他来黄州安置,有人传说将次来到。[15]217
在该剧中,王安石先是因为与苏轼政见不合,将他贬去黄州,又暗中命黄州杨太守拒绝周济落难的苏轼,企图将他迫害致死。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台词呈现,都突出了王安石的“奸邪”,剧中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一派把持朝政,对旧党人物多加排挤和迫害。其他荆公戏也大多利用“王安石斥贬忠良”这一设定来推动剧情发展。再如明代汪廷讷采用时空嫁接的模式,为了给主人公范仲淹设置挫折,将王安石在神宗期间所推行的改革事件提前,并由王安石这一“行动元”来实施贬官,从而推动后续剧情发展,利用中途的贬官挫折凸显《三祝记》结局“福、寿、男子俱全”的圆满。乔莱更是在《耆英会记》中指出贤相首推司马光,称他有万古高名,而这一剧目本身就是围绕大批官员反对新法因而渐次被贬展开的,因此王安石和吕惠卿被归为“奸邪”一类。可见,朝堂上的王安石形象被设定为权势滔天的奸臣和性格执拗的权相,这也可从多个剧中不同人物的评说中加以验证:
司马光:最忧王介甫执拗偏迂……吕惠卿奸国小人……党附安石。(《耆英会记》第一出)
苏老泉:忠良的尽斥逐,相汲引的总奸枭,把天焚地变,等鸿毛一任,你狠心肠、偏执拗。(《眉山秀》第八出)
宋之仁:如今当朝宰相王安石,执拗成性。……使见忤权奸,阻挠新法,我的门闾未必显耀。(《四元记》第四出)
再看部分戏剧对苏轼的描述,大多为远近钦慕的“大学士”,不仅才学过人而且性格洒脱、忠君爱国,是宋代文人的典范,如《赤壁赋》中:
苏轼(自云):我想为人半世清贫,十载苦志,学得胸中有物,为朝廷显官,治国平天下,当所为也。想俺秀才每学就文章,扶持圣主,方显大丈夫之志也。
苏轼:俺两个(指与王安石)十年旧,到今日一旦休,才得志便与我话不相投。则为他家有贤妻,送了俺交绝故友。我如今苦痛分妻子,他今日谈笑可便觅封侯。
【滚绣球】我也曾写珠玑一万联,判莺花三百篇,扫千军笔端鏖战,但行处天子三宣。结平生诗酒缘,掌中天风月权。不是将帝王埋怨,为甚把苏轼似贾谊南迁。[15]219
由此可见苏、王二人形象在剧目中的差异性,这不仅对应了戏剧创作者对忠、奸人物的艺术设计,也是文学史上“苏王相争”这一母题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戏剧中的荆公在朝堂上往往拥有滔天的权势,是斥贬忠良的“罪魁祸首”,这一总特征几乎贯穿了所有荆公戏。更具体地说,他性格执拗,固执己见,始终打压旧党人物,好与人争,利用自己的身份排除异己。神宗与司马光曾有对话曰:“上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16]戏剧和史书中的王安石都具有执拗的性格特征,但是历史评价较为全面,而戏剧中的王安石则被简单概括为奸诈专权的执拗宰相,在朝堂上充当着反面角色。
(二)勤俭而柔情:日常之荆公
朝堂上的王安石较为刻板,当剧中的荆公褪去朝服,回归到日常生活,其他形象特点也得以彰显。剧作家对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虽多有批判,但部分戏剧在改革动机上对他给予了肯定。无论是剧中还是剧外,王安石所求的都不是荣华富贵,纵使他身居高位,依然勤俭至极。他的勤俭之名并非空穴来风,《宋史·王安石传》中称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10]9370。邋遢于他人而言或许是缺点,于荆公来说却从侧面突出了其形象上的不拘小格与勤俭节约。除此之外,明清不少戏剧都参考了冯梦龙的话本小说,其中亦有“荆公为人至俭,肴不过四器,酒不过三杯,饭不过一箸”(《王安石三难苏学士》)[17]18的相关描述。戏剧中的王安石同样保留了“不重口腹之欲、不贪图享乐”的特征。以《耆英会记》第二十四出为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扪心自问道:“若说我是小人,天下做宰相的哪有粗衣恶食、一钱不爱的小人。”这一台词深刻地刻画出了王安石勤俭为民的形象,他身为宰相却选择粗衣恶食,如此坚志令人钦佩。
再看清代四愿居士的《四元记》一剧,王安石因女婿宋再玉逃婚而急火攻心,郁症难解,此时其女方雲与侍女伴云商议原因,有对话如下:
(小)莫不是饮食疏筋难舒失祇承?(旦)爹爹从来极其淡薄的。(小)莫不是服饰荒少安和欠娟婷?(旦)爹爹衣垢不瀚,面垢不洗,世人多称其贤。这服饰欠精之说,一发不是了。(第二十一出)
除勤俭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还是个专一柔情的人,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妻子的关爱上。宋代文人大多三妻四妾,王安石却择一而终,这给了剧作家施展才华的空间,敷衍出了《荆公遣妻》这一剧目,所述正是荆公拿钱遣返夫人所购小妾之事。除此之外,不少苏轼戏都设计了“苏轼作《满庭芳》调戏王安石夫人”这一戏剧冲突,述东坡于宴会中作词调戏王安石夫人进而被贬之事,东坡在剧中称安石“靠妻偎妇”,纵为批驳之语,也映衬出了王安石对夫人的尊敬。更何况剧作中王安石得知夫人仰慕苏轼后,还特意设宴请之,可见其对妻子的宠爱。
无独有偶,剧中的王安石对待其他亲人也颇显柔情,像《眉山秀》中他操心儿子王雱的婚事,赞赏儿子的才学,这时俨然是一位慈父形象。更加明显的是《四元记》,此剧写到王安石对女儿方雲颇为疼爱,因男主逃婚之举气急攻心、过度忧虑从而患上恶疾,这种不为朝堂病而为儿女病的呈现,将王安石的柔情之处刻画得十分生动。日常生活中的王安石身上显现出更多常人的柔情,有效地弥补了朝堂上形象过于死板、单一的缺憾。
(三)博学而谦虚:学术之荆公
相较于政治上的众说纷纭,王安石在文学上的口碑更为统一,其博学之才也为剧作家所公认,这主要体现在明代张大谌的《三难苏学士》中,这部剧的曲文虽然已经散佚,但其内容与冯梦龙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类同,因此大致情节依旧可考。苏轼被誉名为“宋代第一才子”,在学识上却比荆公稍逊一筹。这主要通过三件事来衬托王安石的才学:一是苏轼认为菊花不会凋谢,贸然续王安石之《菊花诗》,说菊花并不会落到“满地金”,殊不知天下菊花惟黄州不谢;二是王安石让苏轼取瞿峡水煎药,苏轼却以下峡水代之,不知二者区别;三是苏轼无法对出安石所给上联,得安石提点[17]16-22。这些题材大多来源于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和民间轶闻,最终逐渐被戏剧吸收,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荆公形象。以清初李玉的《眉山秀》为例:
〔净(王安石)〕也罢,就在楼上二十四橱内,取上一册,不拘前后,念上文一句,老夫答下句不来,就算老夫无学……〔小生(苏轼)〕老太师学问渊深,岂晚辈可及……〔三段子〕才高八斗,徹书囊驱驰汗牛,腹饱九丘,倒词源纵横玉虬……〔小生、丑合〕真个是事业文章堪不朽。(第十一出)
在苏轼考王安石这一情节中,王安石果然对答如流,苏轼对他心服口服。苏轼的父亲苏老泉亦在两人会谈时云:“一老蠢鱼而已,岂如老太师目徹十行,行穷五车二酉之藏哉”(《眉山秀》第二出)。剧中吕惠卿对王安石的评价为“那王丞相,名安石,字介甫,临川人氏,他胸藏万卷,笔扫千言”(《眉山秀》第二出),这都足证荆公学术能力之强,阅书之广。
同样是博学才高,剧中的苏轼往往恃才傲物,显现出轻薄之气,无论是菊花诗的贸然续写还是《满庭芳》词的调戏之用,都显示出苏轼轻薄放浪的一面。清代四愿居士《四元记》中王安石登场台词云:“下官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也,少好读书,一日终身不失”(第三出),更显低调谦和。面对他人对自己的称赞,他总是秉承着谦虚恭敬的态度。在苏轼错取下峡水以后,也没有过多责备,而是详陈原因,多以教传。在李玉《眉山秀》第二出中,安石之子王雱就显得目中无人,自认为学术高超,无需他人指教,王安石则批评其云:“吾儿过矣。”这一细节将王安石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饱满,他虽有才学,酷好读书,却不以此为傲,常有自谦之语。在戏剧的呈现中,学术之荆公才高博学又谦虚低调,不失为大家名流。
三、荆公入戏的历代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荆公入戏的历代演变不仅彰显了戏剧文化本身的历代演变,同时也折射出了各个朝代的时代背景和剧作家的情感倾向。荆公入戏在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彰显了王安石在通俗文学中的接受一隅。
(一)荆公戏的演变及原因
戏剧内部文本的演变与创作者的情感偏好存在着对应关系。宋代滑稽戏将王安石作为取材对象,主要是发挥滑稽戏的讽谏戏谑作用。如《甜采即溜》调笑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为“开溜”,《跨驴上殿》以“驴”讽刺其改科举征召人才之策。王安石在宋代剧作中主要是被嘲谑的对象,这种情况与其改革权相的身份有关[11]。王安石处于政治的漩涡,又是权倾朝野的宰相,自然成为伶人的讽谏对象。在政治的高压下,伶人选择通过戏剧的方式来讽谏和逗趣,在满足观众呼声的同时发挥戏剧的政治作用,因此王安石成为了宋代戏剧的重要选材。元代的戏剧曲词对王安石的批判更加狠厉,这主要和元代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创作心态有关。一方面,科举制在元代遭到了遏制,文人的地位下降得相当厉害,他们的理想遭遇了挫折。苏轼作为文人的理想化身,自身又命途多舛,故而在剧中成为了作者共情和赞扬的榜样,王安石则成为被唾弃和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元代民众饱受人间疾苦。元代官修《宋史》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颇有微词,不少人都认为是王安石固执地推行新法加速了宋代的灭亡。因此,元代的剧作家通过对文人故事的推演寄托自己的抱负理想,也借对王安石的批判之语来抒发心中愤懑。
到了明清时期,受个人主义和心学观念的影响,剧作中以史为鉴的情绪有所消减。个人思想更加开放和活跃,剧作家对“荆公入戏”的态度由主观宣泄向客观改写靠拢,对王安石也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这一现象同样和笔记小说的流传有很大关系,像冯梦龙在《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就有意淡化了政治背景,采取了更贴近生活的通俗视角,对日常故事进行了夸张和放大,以此来博取读者的注意。明清剧作家在引入“荆公”这一角色的时候,就不仅仅只关注政治上的新旧党争,而是辐射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增添了很多心理相关的描写。这和明清剧作家对王安石的认识更加客观有很大关系,也显示了群众审美趣味生活化的趋向。有的作家脱离了狭隘的批判视角,深入分析“好人办坏事”的原因,甚至对王安石流露出了同情之意;有的淡化了政治斗争的严肃感,取材于生活,加入女扮男装等戏谑情节,将戏剧作为娱乐之用。因此,荆公戏在主题呈现上走向了平民化和多元化。
(二)苏王褒贬的文化因循
在新旧党争中,苏轼与王安石因意见相左而不合。苏轼作为后代理想中的文人形象,无论是在知识分子还是民众之中,都颇受喜爱。虽然苏轼的贬谪与王安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两人私交尚可。苏轼曾向王安石举荐自己门人秦观,并得到了王安石的肯定,在王安石罢相以后,两人甚至同游而互相赞赏。所以两人的关系并非戏剧中所呈现的“非黑即白”。只是由宋伊始,不少野史记述了二者的纷争矛盾,两人的不合从朝堂演绎到了生活上,这为戏剧的情节冲突提供了发挥空间。宋代《邵氏闻见录》记载:
介甫与子瞻初无隙,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不悦。子瞻外补官。[18]
戏剧讲究人物冲突,因此两人不可避免地被置放进了对立关系中,也就预示出高下之争。苏王相争的文学命题在戏剧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王安石是权倾朝野、知识渊博的老相国,苏轼是天赋异禀、受人爱戴的全才,他们本人都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就赋予了戏剧更多传奇性。宋元剧作“褒苏贬王”基本已成定论。忠奸党争也对应着苏王相争,苏王相争在元杂剧中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苏轼贬官的起因皆是于公于私上得罪了王安石;二是苏轼性格的理想化和荆公形象的小人化。直到明代冯梦龙的视角创新,才给苏王相争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冯梦龙对王安石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他取材于平淡,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重心不再是朝堂争斗而在于人物塑造。故而在其话本小说中,荆公不仅才学更胜苏轼,而且品格更为谦逊。其贬苏褒王的态度显著:
宁可懞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懞懂。如今且说一个人,古来第一聪明的。他聪明了一世,懞懂在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才夸己的看样。[17]16
除此之外,冯梦龙在《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又写道:“此人目下十行,书穷万卷。名臣文彦博、欧阳修、曾巩、韩维等,无不奇其才而称之。”[17]24后面并述王安石变法所导致的民间疾苦,但摒弃了对他的极端批判,采用了让他自己幡然醒悟的方式,流露出了对王安石的同情之意。这无疑是一种形象的洗白和正名,冯梦龙的“褒王贬苏”对后代《三难苏学士》《金莲记》《眉山秀》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到了明清剧作里,“苏王相争”的文学命题不再是简单的两人争斗,两人的矛盾获得一定程度的消解,或者剧作家认为双方各有过错,安石执拗而东坡轻浮。并且明清传奇中的“苏王相争”和新旧党争之间的界限也更加明显,把纯粹的坏人这一角色设定由王安石转向吕惠卿,也增添了吕惠卿背叛王安石的情节,剧作家突出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民生,只是受到了小人的蒙骗,所以王安石也就获得了民众更多的同情和谅解。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苏王相争”从简单的意气之争演变为苏王平等、各有千秋,这种复杂多元的认识也就更加贴近史实,削减了两人的针对性,从而使王安石的形象走向清明。戏剧中苏轼和王安石的形象认知折射出苏王褒贬史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苏王相争”这一文学命题的特殊意义。
(三)荆公在通俗文学中接受的意义
戏剧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包含着创作者对王安石的认识,也反映和影响了王安石在民间的接受。显然,王安石一生都醉心于政治改革,不似其他文人多有风流韵事流传。因此他很难充当戏剧的主角,王安石本人的端庄与严肃也使他和戏剧的娱乐性产生了距离。但他的博学、执拗等性格特点又被后世附着上深刻的印记,因此荆公戏虽然名气不如东坡戏,但荆公入戏确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譬如王安石本为江西临川人氏,但是因为他常年在钟山附近游山玩水,久居金陵,并且写下了不少山水名篇,因此部分戏剧在介绍王安石时会采用“金陵人氏”的说法,这无疑是戏剧文学对于王安石生平经历的变形接受。
王安石的创作对于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供人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儿,我不愁富贵,但惜声名”(《四元记》第二十九出),他不好功名富贵,致力于读书治国,这样的精神与志向在通俗文学中得到了展现。清代梁启超曾为其重新作传,称赞王安石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19]。因此,对荆公入戏的全面挖掘和深入研究是王安石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宋元明清的戏剧作为娱乐和讽世的载体,为后世了解王安石的接受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首先,荆公入戏彰显了下层人民对权威的戏谑调侃之情,明清笑话中也有“嘲荆公”的相关记载。王安石的正襟危坐和权倾朝野使得他不如苏轼贴近百姓,无论是滑稽戏还是其他杂剧中的滑稽情节,都体现了下层百姓对他所代表的权威阶层发起了挑战。
其次,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朝堂之上关乎文人升迁,朝堂之下关乎民生民计,尤其是青苗法一说,几乎在每部戏剧中都有所体现,并且包含大段百姓自身的唱词,贴近民众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求,戏剧对于荆公的引入体现了为民声张的创作倾向。
再次,通过戏剧文学的创作,王安石一生的重要事件得以展示,突出的形象特征得到强化,“奸”“拗”“博学”等字眼和王安石一起建构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荆公的相关本事进行推演,加深和丰富了底层人民对他的认知。像笔记小说中描写民间寡妇在豢养家畜时也会直呼“啰,啰,啰,拗相公来”[17]29,虽为贬低之意,却也是民间接受的呈现。相较于吕惠卿这种纯粹的小人和奸佞,王安石在戏剧中的接受经历了“戏谑—憎恶—同情”三个情感阶段,形象的多面性也从方方面面得以透视。荆公入戏不仅展现了王安石这一人物在文人阶层和民众中的接受与认识,也反映了王安石在通俗文学中的接受,折射出了“荆公”这一文化符号的风采。
结语
由宋至清,荆公入戏是剧作界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早在戏剧尚未完全成熟的宋代,就已经有不少伶人对其进行戏剧编排,滑稽戏中对王安石故事的推演与当时的时政密切相关。到了元杂剧时期,苏轼戏风靡一时,“苏王相争”这一命题受到了剧作家的高度重视,苏轼人格的理想化也对应着王安石形象的“小人化”。到了明清,受《三言二拍》等小说和心学思想的影响,王安石的一些正面描写逐渐增多。剧作中关于新法及其所引党争有了更加系统和复杂的表现,王安石的形象更加多元和立体,在政治、生活和学术上折射出多面的性格特征,形象之争也由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