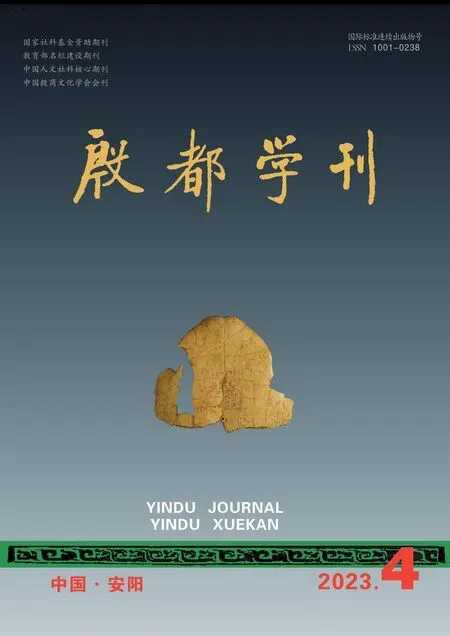赵元任语言学思想述要
汪维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语言学人,本人就是其信奉者和追随者之一。这种影响今后无疑仍将持续下去。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学派林立、异说纷起的时代,总结赵先生的语言学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有许多疑问需要通过阅读赵元任来寻求答案。
早在1916年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上的《中国语言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这是目前所知赵先生最早的语言学论文。吴宗济《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序》评价说:“他这学生时代初露头角的作品,居然能立论十分鲜明,举例详赡准确。他提出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语言学要用科学方法研究,二是文字必须改革,竟是一篇当年讨论中国语言学的最强音,可以说是吹响了本世纪语言学研究序幕的号角。”赵元任著,吴宗济、赵新那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页。第一篇《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Ⅰ.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Philology)(2)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赵世开译,吴宗济校,第668-712页。里,赵先生就明确提出了“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这一重要命题,可以说,“中国语言学要用科学方法研究”是赵先生语言学思想的一个核心,他终身都在致力于“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除此之外,赵先生似乎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语言学思想,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著作来间接地体会和总结。笔者读赵著不多,理解不深,学识也很有限,对他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难以有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只能就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粗浅的体会,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1)研究口语;(2)尊重事实;(3)系统思维;(4)经世致用;(5)重视科技;(6)金针度人。管窥蠡测,未必惬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研究口语
赵元任先生爱好广泛,文理兼擅,但是研究活的口语是贯穿他一生的主要学术兴趣,也是他最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平田昌司先生说:“赵元任应用语音、音乐、音乐(?sic)各领域的知识,为‘耳朵的文学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口语语法研究。在1926年发表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里有下面一段话:‘就是有好些是人人天天说话用的语助词或语助词的用法,都是作语法书的人不大提、写白话文的人不大用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很可以给写“话剧”剧本的人参考参考。’如果回顾一下汉语语法学史就可以看出,这篇论文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对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河。”(3)[日]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8页。
赵元任先生说:
我们的学者通常有把自己局限于研究语言正统部分的习惯,而且怕去涉及俗语。然而,如果科学的语言学家的职责是去收集、整理和解释语言事实,他就不该忽视他不同意的语言运用和用法,正如社会学家不能忽视犯罪的事实,只因为它是不好的一样。(4)《中国语言的问题》,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72页。
以赵先生早期的语言学论文《“俩”“仨”“四呃”“八阿”》(5)《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1927年。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240-246页。为例。这篇文章研究的是北京话里的“俩”“仨”这些口语词,还创造了“仨”字来记写这个活词并被大家接受。文中除了旗帜鲜明地“研究活的口语”之外,还有许多语言学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揣摩。
明确区分了“字”和“词”。虽然文章只用“字”而没有用“词”这个术语,但是作者说:“俩字本来读liǎng(6)原文用注音符号,这里改成汉语拼音。,是‘伎俩’的俩,与‘俩子儿’的俩(7)引者按:音liǎ,“两个”的合音。没有语根的关系。”说明虽然都写作同一个字形“俩”,但记录的是两个音义都不同的词/语素。
描写精细入微。文章先分析意义和用法,把“俩(liǎ)”的用法概括为五大“限制”,可谓条条精准。顺便把通用量词“个”也描写得入木三分。次分析语音。这是赵先生独擅的胜场,剖析精微,结论确当,因为懂的语言多,例子都似信手拈来。
揭示了这些词的语体特点--口语性。它们是“在语气很随便的时候用的”。
文章最后一段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末了,关于上述的种种变化的程序不过是一种就事实的分析与比较而推测出来的解释法,并不是根据史料而重建出来的俩、仨史。例如两个[liɑŋɡ]跟俩[liɑ]都是现在的活语,并不是两个死了然后产生出俩来的。不过照音理上看,我们可以看得出俩比两个是新一点,而且推想得出大概是经过甚么样的过渡式而成的罢了。(8)《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246页。
现代汉语语法学巨著AGrammarofSpokenChinese(9)有吕叔湘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和丁邦新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本文所依据的版本是: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编校者:胡明扬、王启龙,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更是赵先生这一语言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在《中国话的文法》的序里说:“书里的例句都尽量采用了日常生活中曾经说过的,或者能够说的句子。有时引用特别体裁的例子,像文言、白话文或者方言,都加以注明。”(1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4页。在这部书里,赵先生对“研究口语”这一根本旨趣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摘引一部分:
不过文法意义跟真实意义还是有关联,因为语言的种种语式到底是从日常生活应用中发展出来的。(11)《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22页。
中国话是什么?--所谓中国话,像本书的题目所用的,是指二十世纪中叶在不拘形式的场合里所说的北京话,有一点体裁随便的意味。(12)《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26页。
本书探讨的主要体裁是日常用语。
本书既然要对中文的一种重要体裁作切实的研究,就要尽可能地描写真正的口语。(13)《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28页。
在“1.2.2 引例的出处”里赵先生提到了下面几类:
(1)自创例--这些多半是我个人以语言学者跟发音人的双重身份所造出来的短例子。不过我只在一岁、十七岁、卅二到卅九岁,跟四十一岁几年在北京住过,九岁之前住在河北省其他地区。而且我以前念经书都是用常州音,所以不能像道地北京人的发音那么绝对可靠。因此对于我认为可疑的例子都请别的北京人查对过。
(2)“中国文法实例”--这些是我多年来听到而随时记下来的跟文法有关的对话。这一类资料大都是北京话以外甚至官话以外的方言。
(3)国语会话留声片跟录音带--……这些资料都是随说随录,没有经过预先练习,……真正随意的对话,是一面想,一面说,甚至常常只说而不想。(1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29-30页。
关于第一种材料,朱德熙先生说:(15)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第321-329页。
因为赵先生兼有语言学家的洞察力和作为“活材料”对北京话的敏感,再加上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中国话的文法》这部书里的例句确实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尽管如此,书里也还有个别的例子看得出是受了吴语的干扰。(16)例如所举XXY重叠式的例子里有“壁壁直”(吕译本109页),又“高兴不高兴出去野餐去?”“你什么事不高兴他了?”(吕译本326页),“大家吃饭的前头,你别吃点心。”(丁邦新译本64页)
研究口语自然要涉及语言的历史,这是不矛盾的,赵先生的汉语研究,通常都是以口语为对象,而溯及历史。
研究活的口语,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一语言学思想在今天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赵先生在《语言问题》里说:“向来研究语言的都是注重语史方面,这是晚近几十年来才注意直接描写一个时代、一处地方的语言。”(17)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依我的理解,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研究自然口语及其变化,因为其中蕴含了人类语言构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我们提倡“面向古代活语言的汉语史研究”(18)“面向古代活语言的汉语史研究”是刘丹青先生提出来的,见刘丹青:《语言学对汉语史研究的期待》,在“第五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2017年4月8-9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上的发言,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2017年4月24日推送。此文后刊于《上古汉语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页。,正是基于这一精神。
二、尊重事实
赵先生是公认的语言天才,被他的弟子王力先生赞为“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以他的颖悟和博识,他研究汉语语法完全可以用内省法自己编造例句,但是他绝不。大家知道,赵先生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小笔记本,西装表袋上别着四五支各种颜色的笔(19)参看陈原《我所景仰的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年谱〉代序》,载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页。,一听到或看到有意思的现象,就随手记下来。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正如沈家煊先生所说:“最为可贵的是,赵元任对语言现象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和兴趣。”(20)沈家煊:《大家来读赵元任》,在“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实验语言学”公众号2022年12月5日推送。1916年发表的《中国语言的问题》第一篇《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说:“不管是多细微的规律都应该仔细地研究。”(21)《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76页。仔细地研究规律,首先需要搜集丰富而又可靠的第一手语料。他的太太杨步伟女士也是他的语料来源之一,《中国话的文法》“绪论”部分提到过两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回我太太问我:“你花(22)她的话有下江官话的底子,所以“花”平常都不带词尾“ㄦ”。ㄐ-ㄠ的水够不够?”整句话中间没有一处停顿。我把“花ㄐ-ㄠ”听成“花椒”,所以莫名其妙。但她再说的时候,没有说“你”,而在主语跟谓语之间停了一下,说:“花,浇的水够不够?”由此可见,复合词各部分或主谓语的接合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跟不是、或断跟续的问题,而是有的是这样,有的却是两样都行。(1.1.3节)(23)《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26页。
又如我太太在检查给猫撞过的窗户时说:“它把玻璃(打破了)”,但话还没说完就发觉玻璃并没有破,所以就改口说成:“它把玻璃没打破”。要是早想好了那句话,就一定该是“它没把玻璃打破”。(详见2.14节“想好跟没想好的句子”。)(1.2.3节)(2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32页。
赵先生研究口语语法,就是这样从老老实实、一点一滴地搜集真实的语料开始的,真是聪明人下笨功夫。他的语言知识也是通过仔细观察、勤学苦练得来的。《我的语言自传》谈到他如何学习in:ing和en:eng的分别:
关于这一点连我母亲都分不大出来。到很迟很迟,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书,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十年过后才觉到有分辨的必要,然后再开始把所有那类的字一个个地重新学过一道。例如“斤、亲、心、痕”收ㄣ(n),“经、青、兴、恒”收ㄥ(ng)。这是在我会说了两三种吴语以后才注意到的事情。有时候从谐声上可以看出来一点儿,例如“亲”收ㄣ,“新”也收ㄣ,“青”收ㄥ,“清、情、静”也收ㄥ。不过也有些例外的,比方“经”收ㄥ,“劲旅”的“劲”虽然收ㄥ,可是“用劲”的“劲”收ㄣ。反正从不分到分是必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从分到合就只须记得一条规则就可以一律通用了。例如广东话分双唇跟舌尖鼻音的韵尾。学北方话只要记得凡是-m都改成-n一条规则就够了。我大概到十几二十几岁才把ㄣ、ㄥ的字分得出来,可是到今天说话说急了的时候有时还会把“因:英”或是“恩:鞥”说混了。(25)《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9-90页。
笔者读大学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把自己没有把握的普通话字音逐个学过一遍,我的母语(浙江宁波话)里不分的“in:ing”和“en:eng”自然是学习的重点,也是那时才知道“劲”有jìn和jìng两个读音,意思不同。所以读到这一段时感觉特别亲切。不过我当时有《新华字典》可以查,赵先生当年大概是没有工具书可查的。
《语言的描写和规范问题》一文说:
有时候我代表中央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差到各省调查方言,譬如我问:“这话你们这儿怎么说?”或“这音你们这儿怎么读?”那是调查方言。被问的人说什么,就是代表这地方的话。我把他的话纪录下来,不能批评是非。所以说这方言的人是最高最后的权威。(26)《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530页。
同样的意思他在别的地方也表达过,这是他调查方言所秉持的基本信条,理论基础就是尊重语言事实。作为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先生所掌握的语言事实之丰富和精深,恐怕是无人可与伦比的。
他对语言规范的问题抱持通达的态度,这也反映出他对语言事实的尊重。《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一文说:
从本文总的调子,读者会认为,我一定很同情这样的老师,他们怀念正误分明的美好的往昔,他们看到人们渐渐不再保持某些区分,纯正的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上变得愈来愈洋气,而哀叹着语言的退化。其实,尽管我对事物的感受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情绪,但是在对待语言的正确性问题上,不论是就一般语言而言,还是具体就汉语而言,我却肯定不是死硬的纯语派。我完全同意美国结构学派语言学家的主张:学者的任务是纪录用法,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这些用法;教员的任务则是教给学生,什么语言适合什么场合。人们用一种格调的发音吟唐诗,用另一种格调同家人闲谈。日常会话中说“今儿几儿了?”在讲台上或者课堂里就得去掉大多数“儿”尾,说“今天什么日子?”(27)除非我教美国人汉语的时候,是两种形式都举。遇到要注释《孟子》的语法的场合,你即使用纯正的文言写作,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但是如果需要我报道国际时事(我很难设想自己会去做那样的工作),我只有使用那些已为新闻界所经常使用的新的欧化词语。由此可见,什么是正确的语言,这要看什么场合适宜于说什么话和说话人(或写作者)是什么身分。如果你要在交际中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么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此说来,语言的正确似乎成了有条件的规定,而不是绝对的规定。但是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他的责任就是要进行有效的交际,他使用的语言应该始终切合相应的场合,因此,上面这句话在陈述前提的时候也就包含了结论。换句话说,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28)《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第59页。
三、系统思维
全面把握语言系统是赵先生语言学思想的精髓之一。李荣先生说:“写《多能性》这篇文章时,作者正在当年,那广博的知识,恰当的实例,深入的见解,妥帖的文字,充分证实‘名下无虚士’,议论不同凡响。以后的著作说明赵先生的语言学是全面的。”(29)李荣:《赵元任》,《方言》1982年第2期。又收入李荣:《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9页。
早在1916年发表的《中国语言的问题》第四篇《设想的改革》“1.发音的标准化”中,赵先生就强调了系统性。他列举了“对于标准化最重要的原则”,一共有五条,其中前两条是:“(1)符合历史发展的系统的一致和简单。(2)最大程度的区别。”(30)《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89页。《语言问题》更是集中体现了赵先生的系统思维,全书共十六讲,对语言和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广泛而系统的阐述,这只要看一看各讲的题目就不难知道: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语音学跟语音学的音标,音位论,词汇跟语法,四声,上加成素,方言跟标准语,何为正音,语史跟比较语言学,语言跟文字,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英语的音系跟派别,实验语音学,一般的信号学,各种信号的设计,从信号学的立场看中国语文(“一般的信号学”和“各种信号的设计”两讲是介绍当时尚属新兴的信号学)。第一讲对语言的定义是:“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31)《语言问题》,第3页。概括了语言的五个特征,其中最后一个特征是:
任何一个语言,是一个由比较少的音类所组织的有系统的结构。人的耳朵的辨声音的能力是以千、万计,可是任何一个语言所利用的必要的区别,只是以几十、乃至仅仅乎十几计的,这是平常人不大想到的语言上的事实。在一个语言范围之内,它的音类不但数目少,而且总是成一个相当有系统的结构。当然每一个语言的系统里有各别的特点,比方说:中国话有四声;英国话动词分现在、过去;德国话名词分阴、阳、中三性;不管系统是复杂还是简单,有系统总比没有系统有办法一点儿。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语音的系统性。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也贯穿着系统性思维,比如《“俩”“仨”“四呃”“八阿”》一文说:“……照这看法,无论是一呃、俩、仨、四呃、五呃、六呃、七呃、八呃、九呃、十呃,都是要当一回事看的。”(32)《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245页。把“俩”“仨”放到从“一个”到“十个”的系列中加以观察和分析,它们的来源就看得很清楚了。
四、经世致用
李荣先生说:“赵先生是理论跟实际并重的语言学家。”(33)李荣:《赵元任》,《方言》1982年第2期。又收入李荣:《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9页。的确,赵先生是一位现代学者,而不是旧式的学究,他研究语言既有学理的追求,也注重经世致用。他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核心作用,就是这一语言学思想的最好体现。
《我的语言自传》说:
那几年我在国语统一的运动上同时也相当地活动。先是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里头一部分的工作是大辞典编纂处,后来出的四册的国语辞典,就是从这里出版的。委员会里工作最多的最常见面的是汪一庵、钱玄同、黎锦熙、白涤洲、刘半农、林语堂等。我们谈谈谈到切韵序里有“吾辈数人定则定矣”一句,大家就说咱们干吗不组织一个会叫“数人会”来定各种提案,再送呈大会跟教育部决定。后来这里头工作最要紧的部分一样是国音的标准,从民国八年的“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人工式的国音,一改改成民国二十一年的完全用北平音的标准;第二样是拟了一套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民国十七年由大学院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的第二式。(34)《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第101页。
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有:
1.参加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数人会”,制定国音标准:1919年“老国音”,1932年“新国音”。灌制国音唱片,推广国语。
2.创制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缩写为G.R.)。
3.参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与钱玄同一起校订《国语辞典》(共四册)。
4.与杨联陞合作完成汉英口语字典《国语字典》(ConciseDictionaryofSpokenChinese)。
5.研制“中国通字方案”。
6.大规模调查汉语方言。
7.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编写教材和字典、读物,培养汉语人才。
这些成就充分反映了赵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
五、重视科技
众所周知,赵先生文理兼通,对先进的仪器设备和科技手段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动手能力很强。借助科技力量来更好地研究语言,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思想。赵先生早年写的《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35)《科学》第7卷第9期,1922年。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27-36页。是描述用他自制的仪器研究汉语声调(没有正式试过)的一篇论文,从中可以一窥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和能力。
吴宗济《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序》说:
赵先生的语言本领是天赋加力学,他的口耳审音之精,不但能运用好些方言作演讲而乱真,而且他的研究方法更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和刘复先生在二十年代同时都是用浪纹计、渐变音高管等仪器(这在当年是最先进的)来分析声调,但很快他在南京中研院史语所创建的语音实验室,其设计于建声规格和电声设备上,就前进了一大步。他在1959年的《语言问题》讲演中,就介绍了十几种研究语音的最新工具,并详述其声学原理和机电维护等问题,显出他在科技方面的功底。(36)《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3页。
《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跟着赵元任先生调查方言”一节对此也有具体的记述,比如:
记得我们那时用的录音设备是刚刚从美国进口的,叫唱片灌音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跟赵师在一起,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
事情发生在南京。当时我们从美国新进口了分析语音的仪器,花了不少钱。老师让我把它装起来,我按图纸都准备好了,以为没有问题了,没想到刚一通上电,闪了一下,就没有动静了。几位师兄弟都吓坏了,以为我把这么贵重的仪器弄坏了,闯了大祸了。可赵师一点儿责备我的意思都没有,他非常平静地看着我,脸上满是信任和鼓励。由于我心里没有压力,所以原因很快就找到了。原来这台仪器要求的电压是110伏,而我们国内的电压是220伏,因此,只要换一根保险丝,再配上一个变压器就解决问题了。(37)吴宗济口述,崔枢华记录、撰文,鲁国尧策划、作序:《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84、255-256页。
六、金针度人
赵先生写文章,从不故作高深,而是尽可能用大众化的口语和恰切的比喻把深奥的语言学道理说清楚。正如吴宗济先生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序》里所说:“赵先生对语言科学的造诣,对边缘学科的贯通,在他的著述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乃至枯燥难懂的情节,都能用自然口语,如话家常;对现象的比喻,也能信手拈来,都成妙谛。”(38)《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1页。赵先生不仅始终以活语言为研究对象,而且终身坚持用纯口语写作,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国语言的问题》第四篇《设想的改革》“5.书面词语的改革”主张:
引喻和引用不要多加,除非想要神秘化或者卖弄。像“梦蝶、杞忧,刻舟”这样一段表达过分的话反倒失去了思想的力量和纯真。也许人们喜欢它们因为这些人原本没有什么思想要表达。像“虽不中,不远矣”那样的引喻和引语,它们本身是明白的、比较少的矫揉造作。在外国文学里,这种表达比上面那段过分表达的话要更常见。
我们应当发展我们的幽默感。……
我们应该避免放弃自然和纯朴,追求机械的匀称和对偶。……
我们的信件应该避免“谦恭”的无聊而给真诚腾出点篇幅。(39)《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98页。
他的《语言问题》就是演讲的实录,是能看的“活语言”。此书“原序”说:
为保存原来讲堂空气起见,除了上述的删除重复跟整理句法以外,一切仍是照旧。关于这一点,台静农先生特别鼓励我这么样儿做,所以原来的“啊”呀,“么”呀,什么的,还有些似不相干而又相干的笑话,为了存真起见,也都照原来的样子留在里头了。(40)《语言问题》,第4页。
这种体例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笔者年轻时一看到它就觉得新奇得不得了,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
赵先生用国语罗马字写作的文章,尤其能反映这一思想,比如《“连书”什么“词类”》这篇文章(41)原文用国语罗马字写成,由温锡田先生译成汉字。:
反对拼音文字的人,他们顶爱问的问题就是同音字怎么分别的法子。这问题的顶容易答的答复就是“词类连书”:只要是成词的字都给它们拼在一块儿。每个词就有它各自各儿的“面孔”,就不会跟别的词混了。
这个法子当然是不错了。可是我觉得要是一个人单靠这个法子,他写起文章来还是会用些声音不干脆、字眼儿生冷的词类来唔兹唔兹的(ngtzyvxde)写了一大片,我怕结果还是不像从活语言里写出来的活文字,还怕像是一种汉字的文章,不过换个样儿罢了。
要把G.R.文字写得明白,好说,又好认,我觉得还得有几样儿事情应该格外留心的。
第一要紧的话是:别怕写白话。现在不是白话文已经通行的日子了吗?国语罗马字不是本来单为写白话文用的吗?还说什么怕不怕的话呢?我所以要说这种废话,是因为现在一般的白话文靠着有汉字的鬼脸儿,还可以不管说的明白不明白,只要汉字“写”的明白就算了。拿这种文字改拼成了罗马字,哪怕是里头的词类都没有跟别的词同音的,还是没有真正拼音文字的味儿。真正白话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们些人用了它这么些年代,凡是听了不容易明白的词,早就丢了不用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虽然用不着说非用顶白的白话不可,但是至少可以说,写拼音文字的时候儿,咱们得要拿顶白的白话来做个标准。
上头说的是咱们应该走的大概的方向。分开来说呐,就有底下的几样得留心的事情:
一,声音要响亮。凡是希虚希虚乌里乌里声音的字总是少用的好:juhyih(注意)不如lioushin(留心),yush(于是)不如ranhow(然后),iouliuh(忧虑)不如fachour(发愁),lihshyr(立时)不如maashanq(马上),lihje(立着)不如jannje(站着),buderyii(不得已)不如meifal(没法儿),shyyjong shiuyaw chiuh de(始终须要去的)不如tzaowoal deeiyaw tzoou de(早晚儿得要走的)。
二,多用同音字少的字:shiu(须)不如deei(得),tzyh(自)不如tsorng(从),ing(应)不如gai(该)或是inggai(应该),chyuan(全)不如dou(都),jyh(制)不如tzaw(造)。
三,在文法上“l”(儿)韵当名词的记号儿的,应该放开了胆儿多用用。wey有weysherme(为什么)的wey(为)、鼻子闻的wey(味),well就一定是闻的well(味儿)了。suey有pohsuey(破碎)的suey(碎)、niansuey(年岁)的suey(岁)、挂的sueytz(穗子)的suey(穗),suell就一定是挂的suell(穗儿)了。daw有dawluh(道路)的daw(道)、dawnall(到那儿)的daw(到),dawl就一定是tzooudawl(走道儿)的dawl(道儿)了。yi的意思多得简直让这个字音没法儿单用,yel就一定是母亲姐妹的那个yel(姨儿)了。wan有wanle(完了)的wan(完)、wanshoa(顽耍)的wan(顽)、yawwantz(药丸子)的wan(丸),wal(顽儿)就一定是小孩子wal的顽意儿的wal了。
四,一个字有几种读法,而意思没有分别的,就用跟别的字同音顶少的那个读法。she(色)不如shae,bor(白)不如bair,bor(薄)不如baur,jwo(着)不如jaur,jyue(嚼)不如jyau,luh(六)不如liow。
五,单字词够明白的就不用改成生冷的两三字的词,shiee(写)不必改shushiee(书写),wal(顽儿)不必改wanshoa(顽耍),benn(笨)不必改yubenn(愚笨),tzoong(总)不必用tzoongguei(总归),shiudeei(须得)也可以就用deei(得)。
六,要是用多音字词的时候儿,顶好里头的那些单字也都是声音响亮意思明白的字,因为中国的白话的词类虽然有慢慢儿变成两字词的神气,但是老实话说,到底还有一半儿是用单字词的;并且哪怕就是用多字词的时候儿,里头所用的单字的意思还是在说话人的脑子里头活着呐,并不像英法文的多字词里头的拉丁字的本来的意思都是半死半活的了。所以假如你用些很文的文言,同音字又很多的字,拼拼凑凑弄出一大些词来,像jifwu(羁缚)、jingbor(精博)、youluann(淆乱)、fuuwey(抚慰)、yuhniaan(欲念)、jigow(机构)、shyhtay(事态或世态)什么什么的,看的人假如看不出来是什么汉字,就很难看懂;假如“因为猜出了汉字来”才懂的,那还不是仍旧让汉字在背后跟G.R.唱双簧?我的G.R.朋友里头,有人对我说,那些词就是得那么硬学,不用管它本来是些什么汉字。这个“做”是当然没什么“做”不到,碰到了新思想用老“普罗”的白话没法儿说的时候儿,那也只好造点儿汉字的双簧词儿来用用,预备以后有唱“单簧”的日子,不过我现在要说明白的,就是万不可靠因为有汉字帮你造词,弄的你以后(换个比方说)断不了汉字的奶。所以要造多字词的时候儿,假如能用声音响亮、意思明白的单字作材料,那还是用这类的单字,哪怕你拼出来之后另外有新的讲法,可是给学的人可以容易学得很多,用它跟读它的人的嘴里也可以多尝到些滋味儿。他们老先生们喜欢咬文嚼字,可是关着嘴唇儿偷偷儿的咬人家的汉文,嚼人家的汉字,那就有点儿太寒碜了。
……我写这篇东西是一起头儿就拿G.R.打草稿的,这么写法写出来才是真正的G.R.的白话文。我敢说要是先写了汉字再翻成罗马字拼音,那结果恐怕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后你们写稿子的时候儿也这么来来看!(按:这篇原稿是用国语罗马字打的,这里是翻成汉字。)(4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5-78页。又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405-409页。
这篇文章里谈到的口语词的种种特点,十分值得玩味,都是很好的研究题目。赵先生所倡导的这种完全属于“我手写我口”的地道白话文虽然后来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以活的口语为基础来写白话文的精神却是逐步被大家接受了。
赵先生是觉得语言“好玩”,也想尽量带着大家一起玩。上文提到的《“俩”“仨”“四呃”“八阿”》,在写法上也示人矩矱:一是用纯口语写作,易读易懂;二是把思考过程也连带写出来,金针度人。
七、余论
最后应该指出一点,就是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思想是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标准国音”的问题。1916年发表的《中国语言的问题·ⅳ设想的改革》“1.发音的标准化”部分的基本观点是想要模仿德国的标准德语来制定一套汉语的“标准国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设计出来的“老国音”(1919)最后以失败告终。人为制定的“标准音”是不可能推行的,标准音只能以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为基础。这一点他后来有了清楚的认识,“新国音”(1932)就是如此确定的。《什么是正确的汉语?》(1961)说:
规定音位的(如果不是语音的)发音标准的最初尝试,其成果体现在1919年的官方字典《国音字典》里,它用当时新设计的注音字母拼出每个字的发音。人们正像《切韵》的编定者们在公元601年所做的那样,“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定下了官话发音的标准,叫做“国音”,要从此在所有的学校里都教这种发音。国音有第五调或入声,分尖团,有/o/(ㄛ)和/e/(ㄜ)两个中元音(多数北方方言只有一个),以及符合传统的其他各种特点。由于国音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教员的家乡音,于是一项任务落到我的头上:给这种标准语灌唱片,并在所有学校推行。1922年,哈佛大学在中断了四十年之后,重新开设汉语课,那时我在哈佛大学教的,实际上就是这套音。不管有没有唱片,教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总是难事。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到了1932年,未公布任何根本性的变动,《国音字典》悄悄地修订成了《国音常用字汇》,它实际上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这一下子就涌现出了一百万以上可能的师资来代替我这个孤家寡人。现在,不论在北京还是台北,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时候,首先总要问她是不是生在北京,或者至少是不是在北京上的学。(43)《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第56-57页。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1922年他写给黎锦熙先生的《讨论国音字母的两封信·其二》中就已经认识到了:
我近来研究研究言语的变迁,渐渐觉得天然趋向的势力比人为的有意识的主张厉害的多。所以我们自负为言语文字改革的“英雄”者,只能在“事势”当中ㄅ,ㄆ,ㄇ,ㄈ……几件有可能性的主张拣一个最好的,才有成功的希望。这话你看起来似乎是大家已经晓得的陈话,但是事实上很不容易照它行。我从前以为德国的标准国音是定好了就通行的,哪晓得有些地方和多数人的习惯不合的就改不过来。例如……这种现象在现在中国言语里一定也有许多例。我想声调的废除不废除恐怕也是要看现在全国言语里有没有声调消灭的趣向和可能性。不仅问假如废除了有甚么便利的地方。(44)《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24-25页。
二是1916年发表的《中国语言的问题》第一篇《中国语言学的科学研究》“3.词源学”部分,今天看来有不少观念是不对的,比如认为汉语跟印欧语言具有同源关系:
词源学中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部分是汉字的起源问题。有些西方语言学家曾经推测中国语言和印欧语言间的共同来源;尽管在相应的字中间有很多相似点是偶然的,特别是拟声字,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成百个字的单子,哪些字被认为跟印欧语的词是同源的,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是既成事实。举些例子如下:

英语汉语同源字古音 英语汉语同源字古音beat伐bat ring领burn 焚bunsad悴dzotchaste洁kitseek索sokcut割katset设shetelk鹿lokshine灼give 给small微 mihook钩koksmell味mihumble谦 k’imstrong壮kick脚kakthrough透king君(德语könig)throw投、丢mill磨(拉丁语mola)tongue尝dungpair 配turn转 tunpeel 皮yoke 约yokquiet 歇 kit
有人可能反对,认为其中很多汉字是现代的字。是的,不过这些字的本身的确存在过而且通过书法变化的各种演变在口头形式里给修饰过了。这个事实很多人应当欣赏,因为它解除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也就是把中国语言看成是由整个汉字组成的。(45)《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74-675页。
这样的所谓同源词证据显然是无法让人“不得不认为这是既成事实”的。类似的看法在赵先生后来的著作中似乎没有再见到过。
赵先生的语言学思想,大概到了65岁以后就基本定型了。他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的《语言问题》写的《新版序》说:“这本书从一九六八年再版以来又十多年了。现在又有再印的计划,总是还有点儿用处吧?……除此没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原书没有大毛病,还是因为我自己学问近年来没长进的缘故?请读者断定吧。”此序写于1979年2月14日,离开《语言问题》初版(1959年,赵先生67岁)已经二十年了。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赵先生神化,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并非“生而知之”者,只不过是天分过人,又极为勤奋,所以学东西比常人快,知识比常人渊博,最终成了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一代语言学大师。吴宗济先生说赵先生是“天赋加力学”,这是准确的概括。他早年的一些观念存在错误,不足为怪,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也无损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整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