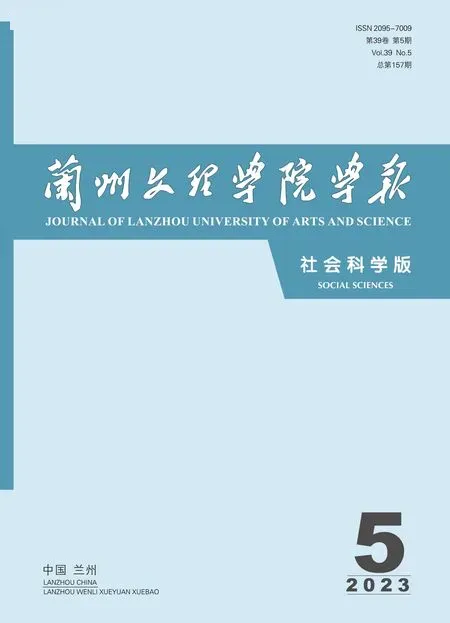明清以来天水伏羲祭祀的历史演进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
朱 姝 民,刘 全 波
(1.天水市博物馆,甘肃 天水 741000;2.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太昊伏羲氏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开中华文明先河。伏羲氏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创乐器,用文明之火引导人们走出了蒙昧混沌时代,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对中华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对伏羲礼赞有加,并逐步建立起伏羲祭祀体系。秦宣公四年(前672年),设密畤,祭青帝,如果西畤、鄜畤与伏羲无关,此密畤与伏羲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秦人利用畤祭,逐步建立了与诸天神沟通的桥梁,从西方到东方,从白帝到青帝,从少昊到太昊,源远流长的太昊伏羲祭祀就起源于此时。就算秦人心目中的青帝与后人眼中的太昊伏羲氏之间还有距离,但毋庸置疑,后世人眼中的太昊伏羲氏在很多时候继承了青帝的位置与功能。当然,伏羲被神化、被祭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应该是先秦开其端,秦汉仍其旧,汉代多强调伏羲之“行”,魏晋多强调伏羲之“德”,唐代诸学者最终构建起伏羲氏的“圣王”形象,伏羲祭祀也被明文定于史册。元代对于三皇(伏羲、神农、黄帝)的崇敬热情是最为高涨的,虽然三皇祭祀用历代名医配祀,但是全国各个郡县皆建立三皇庙的举措是影响深远的事情。在辽阔的元朝版图之内通祀三皇,首先完成了一个情感认同,天下四方皆是三皇之疆域,普天之下皆是三皇之子孙,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继承和利用、发扬,虽然不敢说此举对巩固元朝大一统的天下贡献巨大,但毫无疑问的是,天下一家、同祖同宗的理念渗入了更多人的头脑之中。
一、明代天水伏羲祭祀体系的重建
明代的伏羲祭祀,从国家层面的祭祀来说,在建立之初,先是延续了元朝的祭祀制度。《明史》载:“明初仍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洪武元年,令以太牢祀。二年,命以句芒、祝融、风后、力牧左右配,俞跗、桐君、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十大名医从祀。仪同释奠。”[1]在随后厘定祀典的过程中,明太祖朱元璋对全国通祀三皇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于是“四年,帝以天下郡邑通祀三皇为渎……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1]。禁令一出,除了国家祀典中对三皇和历代帝王的祭祀,地方上只允许陵寝地河南太昊陵祭祀伏羲,这无疑限制了甚至是中断了元朝发展起来的地方三皇祭祀。
《明史》又载:“嘉靖间,建三皇庙于太医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1]对伏羲祭祀身份的不同阐释,除了上文中的医家之祖外,还有以历代帝王身份的国家祭祀。在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又出现了以圣师、皇师身份的伏羲祭祀。“圣师之祭,始于世宗。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九圣南向。”[1]
在朱元璋厘正祀典的大背景下,禁毁淫祠也成为地方官“承流宣化”的一项使命[2]。《明史》记载了洪武末年,宁波知府王璡毁淫祠之事。“毁境内淫祠,三皇祠亦在毁中,或以为疑。璡曰:‘不当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渎。惟天子得祭三皇,于士庶人无预,毁之何疑。’”[1]4061这或许反映了三皇庙以及三皇祭祀的真实状况,也可以说,本来在洪武初年就要废止的三皇庙,有些其实并没有完全废止,宁波到了洪武末年还有三皇庙存在,可见,很多事情并不是一纸诏书就可以解决的。其实,明代祀典常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2],也就是说,国家祀典并非严格的固定体系,在禁与立之间是存在一定空间的,这为后来秦州官员申请立伏羲庙并祭祀提供了可能。
相传,甘肃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而在朱元璋废止三皇祭祀之后,秦州却没有资格祭祀伏羲,于是秦州地方与明中央朝廷之间,围绕伏羲祭祀之事展开了多番互动,到了明朝中期,情况逐渐明朗起来。《明史》载:“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成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雄奏也。”[1]参照伏羲庙碑刻及《畿辅通志》卷七十四《政事·河间府》中的记载,冯时雄应为冯时雍[3]。《直隶秦州新志》亦载:“太昊庙在小西关南向,明正德十一年从巡按冯时雍奏,立庙于州北三阳川卦台之上。”[4]天水西关伏羲庙创修之前,天水伏羲祭祀主要在三阳川卦台山伏羲庙举行。
卦台山伏羲庙的创建时间无明确记载,刘雁翔教授考证认为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约976)[5]。元至正七年(1347)普奕所撰《伏羲画卦台记》碑文载:“至正甲申,秦州同知周赟承直下车,既剔蠹出奸,民俗安静。一日方谒庙,周览方隅之盛,垦田迥辟,黍稷芃芃。询民之耆旧者,咸曰:乃古之赡庙地也。”[5]可见,在元至正年间,卦台山不仅有伏羲庙,还有赡庙田。明初,受到朱元璋废止全国通祀三皇的影响,卦台山伏羲庙官祭不继,但伏羲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着相当的信仰基础,因此民间祭祀或仍有保留。此时关于卦台山伏羲庙的各种记载甚少,祭祀情况亦不能详知。
天水伏羲祭祀中心自卦台山移至秦州小西关伏羲庙,首先是地方官员主导的结果。“(正德)十六年,巡按许凤翔以祭祀弗便,复请立庙于此。”[4]据《重建伏羲庙记》碑等校正,“许凤翔”应为“许翔凤”。事实上,根据伏羲庙所存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的《新修太昊宫门坊记》碑,早在弘治三年之前,已有秦州知州傅鼐所建伏羲行宫,秦州士绅还于弘治三年捐资建立了太昊宫门坊。“秦州西关一里许,有伏羲行宫焉,□前□□傅公天和之所建也。……弘治庚戌岁,郡之耆老刘克己辈各捐己资,□□□匠建立坊门,榜曰‘太昊宫’。”[5]128此时应只建成伏羲行宫,伏羲庙整体格局尚未形成,伏羲庙完全建成至早在嘉靖十年(1531)。
《太昊庙乐记》历述了秦州主政官员创修西关伏羲庙,并修缮卦台山伏羲庙的情况。“正德间侍御成都马溥然氏、瀛海冯时雍氏、平阳许翔凤氏先后建议焉,遂宁陈讲氏、云中卢问之氏次第创庙焉。嘉靖初,侍御新安方远宜氏广庙于台焉,钟离陈世辅氏、任邱郭圻氏饬庙于郡焉。”[5]131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秦州伏羲庙的建成,并非一蹴而就,二是三阳川卦台山伏羲庙在嘉靖初,仍由官方修葺维护。此外,嘉靖十年《秦州画卦台新建伏羲庙记》和嘉靖十二年《增修太昊庙记》二碑,分别记述了该时期卦台山伏羲庙的修缮情况,说明在嘉靖时卦台山伏羲庙仍是天水伏羲祭祀的重要场所,祭祀中心由卦台山转移至西关伏羲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天水西关伏羲庙建立以后的祭祀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伏羲庙现存明代碑刻大致勾勒。详考诸碑可见:自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秦州地方官员不仅积极推动了伏羲庙的创修,还对伏羲庙祭祀礼仪进行了完善。胡缵宗于嘉靖十三年(1534)所撰《太昊庙乐记》碑文对此有详细记述:“今岁春,侍御铜鞮张鹏氏按行至郡,既谒庙,遂及祀事。州守黄仕隆具以对……乃檄仕隆召公制器,按八音以为乐,准八佾以为舞。盖琴、瑟、笙、镛之属必调,籥、翟、冠、袍之属必緻,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持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5]131~132
伏羲祭祀的日期、费用、祭品、乐舞、祭文等情况,《直隶秦州新志·建置》有载。“秦安胡中丞(缵宗)《羲台志》志其籩豆牲牢乐舞之制一准孔庙,有礼部颁行祭文,祭品三十有六,牛一羊一……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之乐,乐器三十有六,乐生四十有四人,冠服一百四十有四,舞器百有三十,舞生六十有六人,冠服二百六十有四。岁以春秋丁祭,用官银办祭。”[4]碑刻资料和志书记载相互印证表明,明代天水伏羲祭祀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与国家层面的祭祀保持了一致,不止春、秋两祭,礼部颁行祭文,还有严谨的、合乎礼仪的乐舞告祭。
秦州地方官员如此积极地推动伏羲祭祀活动,除了与伏羲在天水的影响力有关外,还与明廷将祭祀纳入地方官员行政、政绩考核有关。明制,地方官受职到任时,首要活动即为“祀神”,对于祭祀不敬的地方官员,明太祖朱元璋还曾亲自撰文予以告诫[6]。地方官员积极推动天水伏羲祭祀体系的构建,既是地方官员与国家祭祀意志的联结,充分反映了明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祭祀功能,也意味着地方官员对国家祭祀政令的完成。《明史·职官四》记述知府的职责时说:“凡宾兴科贡,提调学校,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1]1849具体来说,地方官修明祀典的职责,包括修订地方祀典和相应祠庙的维修,以及具体的祀神活动。不论是出于教化民众,还是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国家对于地方祀典的重视,促使地方官员延续了当地的祭祀空间、信仰和祭祀风俗。因此,在地方祭祀活动中“地方官员作为国家政权派驻基层社会的代表,其行为举止映射出国家的政治诉求。官方祭祀活动作为王权意志在地方社会的体现,也就成为地方政府政治生活的一部分”[7]。
《直隶秦州新志》收录有明廷礼部颁行给秦州的祭祀伏羲的祝文。其内容为:“维年月日,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致祭于太昊伏羲氏。于惟圣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道启百王。顾兹成纪之乡,实惟毓圣之地。爰承明命,建此新祠。用妥在天之灵,并慰斯灵之望。时惟仲(春、秋),祀事式陈。神之格思,永言无斁。”[4]在祭文中,有“秦州某官某钦奉上命致祭”的表述,可以确认地方官员作为皇权的象征或代理人,参与了秦州的伏羲祭祀活动;“爰承明命,建此新祠”,则表明了此次祭祀时间应距秦州西关伏羲庙创建不久。至此可以明确地说,天水伏羲祭祀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是官方允许的合法祭祀。在此后的发展中,以秦州伏羲庙为中心的天水祭祀体系得以构建起来,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支持下祭祀空间的构建、祭祀中心向政治中心地的转移、祭祀仪式的完善等实现的。
二、清代天水伏羲祭祀的发展演变
延至清代,围绕着维护统治的现实诉求,清王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祭祀伏羲的礼仪制度。在祭祀时间、祭品、承祭官、祭祀仪式尤其是祭祀事由和祭文方面,清王朝继承和完善了明朝的相关制度,形成了集庙祀、陵祀、殿祀等于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祭祀格局[8]。清代各地设有专祀,伏羲致祭于河南太昊陵及甘肃秦州,清朝对陵祀伏羲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明朝,清廷每位皇帝都曾遣官致祭于太昊陵。可见,天水伏羲祭祀在此时并未能够达到与太昊陵并驾齐驱的高度,所幸者地方官员对于秦州伏羲庙的维修未有懈怠。
历史上对天水西关伏羲庙的维修共有11次[9],其中清代在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等朝,均有地方官员对伏羲庙进行维修,多记载于伏羲庙碑刻及方志文献中,其中不仅记述伏羲庙维修事宜,还强调了朝廷崇重秩祀,地方官员修明祀事之意。如建于顺治十年(1653)的《重修太昊宫碑记》载:“于顺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工,未及半载工已告成,庶可以副朝廷崇重秩祀之意,慰民庶仰□报答之诚矣。”[5]133乾隆五年(1740)《重建伏羲庙记》载:“崇垣甬道,碧瓦朱薨,秩然焕然,庶足以妥圣灵而明祀事欤!”[5]135
客观来讲,尽管清代将伏羲祭祀提升到“具有维持王朝统治社会功能”[8]的高度,但终清一朝,天水地区的伏羲祭祀活动,未有超过明代的创举,从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祭祀礼仪、祭祀费用两项即可窥见一斑。《直隶秦州新志》载:“未知何时祭品止羊豕等,乐舞俱略而银皆州官捐备。李守(李鋐)既修庙,曾申文藩司请动公项复旧仪,议未定而止。”[4]可见,清代天水伏羲祭祀费用,至少在此时期不由官方拨付,而多由州官捐备,这种情况持续到乾隆四十六年时才有了改观。《秦州直隶州新志》载:“乾隆四十六年,知州侯作吴请于大府,每岁藩库给银二十两有奇,复用太牢,灌献拜跪如他中祀礼。”由此可知,天水伏羲祭祀在此时才申请到官方银两支持,祭祀费用维持在二十两左右。又《秦州直隶州新志》有“额支伏羲庙祭祀银二十两,庙户工食银一十二两”[10]的记载,说明二十两祭银维持了较长的时间。研究者指出,清代物价增长明显经历的两个高峰时期,其中之一即在乾嘉道年间[11]。物价上涨而祭银未增,导致祭祀经费越来越紧张,应该也是清代天水官方祭祀伏羲活动逐渐衰落的诱因之一。而这种情况也并非秦州伏羲庙独有,其他地方祭祀经费也存在同样情况,这与清朝对地方祭祀经费的规定不无关系。“在清代,国家虽然以存留形式,给地方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祭祀经费。事实上国家提供的祭祀经费仅限于祀典所载之祭祀,且主要用于购置祭品,其余费用由州县官设法经营,甚至祀典所载之祭祀经费不足部分也须由州县自行解决。”[11]
由于清代州县祭祀费用依赖地方,由州县官捐备,而州县官又通过与地方绅士共同捐备等方式自行解决,无形中促使地方士绅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日后民间力量祭祀伏羲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地方绅士耆老参与到祭祀中的情况早已有之,明清时期官绅捐资修建伏羲庙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伏羲庙留存的维修碑刻中多有记述。如明“弘治庚戌岁,郡之耆老刘克己辈各捐己资,□□□匠建立坊门”[5]128。清《重修太昊宫碑记》载:“况闻肃王暨□卦台各有助施,但苦不足,余亦捐俸若干,命中军贾万钟、同乡耆王纪等督率工匠,勤力修理。”[5]134乾隆五年《重修伏羲庙记》载:“爰于四年六月,洁捐薄俸,鸠工庀材。嗣州人亦有助之者,委别驾吴三煜、参军郑重、阶州绅士乡耆数人敦其事。”[5]135嘉庆十二年《朝议大夫升任宁夏府知府直隶秦州知府王(公)重修伏羲庙碑》又载:“公自捐钱三百万、银六百两,并所积罚锾,共银一千一百两。又不足用,乃遇绅士石作环等老成练达者董其事,募之民间,复得二千余金。”[5]138
显然,地方绅士群体由于文化影响力、能够募集资金等因素,逐渐成为祭祀组织中的重要力量,在伏羲庙维修与伏羲祭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士绅”这一群体的定义、名称等,目前仍存在分歧,本文沿用伏羲庙碑刻中的耆老、绅士以称呼,概念界定不局限于“士大夫居乡者为绅”,还包括在当地商界等行业中颇负盛名的人士。当地耆老、绅士这一群体以其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或捐资,或举办祭祀活动,在清末伏羲庙维修、伏羲祭祀活动中贡献颇多。天水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同治帝钦赐“乡贤之巨”的秦州举人张登阶,同治三年(1864),三捐万金修伏羲城,故同治四年,得以获得奉旨领祭伏羲之殊荣[12]。光绪十三年(1887)《重修伏羲庙记》碑中,亦提到任其昌、苏统武董率绅耆为修伏羲庙而集资之事:“乙酉夏,始与州牧余君泽春协心营建。既各捐俸为倡,且延在籍主政任君其昌、苏君统武董率绅耆,分诣陇南各州县劝分集赀。”[5]139张登阶、任其昌、苏统武都是清末天水地方名士,在地方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登阶奉旨领祭伏羲,进一步说明,地方士绅耆老群体在地方祭祀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绅祭伏羲表明其时伏羲祭祀活动除由官方举办而外,也由地方士绅主办或襄助。士绅最初主要是襄助祭祀,与官方祭祀结成一体,但随着官方力量的不断衰微,士绅力量逐渐壮大,最终成为天水伏羲祭祀群体的领导者,以地方士绅为主的民间祭祀组织应运而生,应该就是今天的天水“上元会”的前身。关于上元会的具体成立时间,据说在清代,但是也不会很早,结合目前资料,多见上元会在清代中晚期的活动痕迹。“上元会”首任、次任会长,据说即是被誉为“陇南文宗”的任其昌及其子任承允[13]。在清后期官方祭祀无以为继时,祭祀活动即由上元会主持,成为民间祭祀伏羲的主要力量。但是在由清进入民国的一段时间内,上元会基本处于解散状态,有关于伏羲庙的记载基本也是空白。
整体而言,清代天水伏羲祭祀的一个重大现象是开绅祭伏羲先例,官祭和民祭并存的方式,预示了后来伏羲祭祀复兴之后,公祭与民祭并行的两种态势。除此之外,祭祀活动内容亦在清代有所扩充。伏羲庙西碑廊有一块题名为“伏羲庙设立灯会布施碑”的残碑,可辨识“道光七年(1827)正月十五日,伏羲庙创办灯会”[14]的记述。民间相传伏羲诞辰在正月十六,故清代伏羲祭祀日期在正月十六日,伏羲庙于正月十五创办灯会,定是为丰富祭祀仪式而增加的民俗活动。
三、当代伏羲祭祀的复兴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
1963年,伏羲庙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伏羲庙的维修又开始陆续进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文化复兴的社会浪潮下,传统文化纷纷复归,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也助推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许多信仰活动与地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进程相混合,逐渐成为综合性的市民文化活动的一部分。”[15]1988年6月26日,天水市政府立足文化和旅游发展,将带有“节庆”性质的公祭庆典活动和带有“会展”性质的经贸活动结合起来,恢复公祭伏羲活动。首届公祭伏羲的活动方案、参祭名单等文本都明确表现出发展旅游业为地方服务的动机,在“关于龙年伏羲祭典旅游活动方案”中,明确指出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扩大对外宣传,促进天水旅游业的发展,借此为振兴天水服务。祭祀目的的转化,同时意味着祭祀人群的变化,“应邀参加天水市伏羲祭典活动名单”显示,参祭人员主要以旅游行业从业者为主。组织者希望借助伏羲“始祖文化”的人文资源属性,通过举办伏羲祭祀活动,树立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达到扩大当地文化影响力和促进当地文旅产业的目的,进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转化性利用。对此,研究者指出“各地举行这些国家祭祀活动时,均隐含着经济指向的目的”[16]。
伏羲祭典恢复后,天水通过“伏羲出生地”“继承传统祭祀历史”等立论,争取对伏羲祭祀和伏羲文化发源地的话语资源。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祭祀规格不断升高,正是塑造和强化天水伏羲祭典同类文化资源话语权和权威的关键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艺术依据国家行政层级进行保护主体的划分,以此来对其官方性、合法性和重要性级别进行潜在背书……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意味着至高荣誉和绝对的文化权威。”[15]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同一祭典列入的,还有河南太昊陵。一庙一陵在明清两朝的庙祀、陵祀基础上,发展至当代依然是同类文化资源中拥有祭祀话语权的信仰中心地。在这一过程中,天水伏羲祭祀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扩充,开始以“同根同祖、中华共祭”为祭祀主题,将天水伏羲祭典构建成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象征符号。
在官方建立渠道与台湾省共祭伏羲之前,天水伏羲庙和台湾伏羲庙就已经存在伏羲文化相关的交流,2014年,天水与台湾省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后,天水伏羲祭祀的人文内涵又有了新的阐释。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伏羲,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共宗的文化象征,被赋予了民族认同的文化涵义和祖国统一的政治意义。诚如研究者所言,“伏羲有共祖的含义,临祭以及聚会也不失提供了一种不用地域念及共同记忆、乃至同根血缘的途径”[17]。
综上所述,当代天水伏羲祭祀虽说是继承历史传统的复兴,但并非承而不变的延续,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不断演进,并且,从祭祀主体的身份象征、祭祀形式、内涵到社会功能,在不同时期都有重新建构、阐释和利用的过程。
明代伏羲庙创修之后,成为官方专祀伏羲的场域。清代,在乾隆五年李鋐所撰《重修伏羲庙记》碑碑阴有“令主持道人宜处修香火,小心经守”,亦不能让闲人“任意出入游玩骚扰”,违反规定者,住持应予以制止,“立即扭禀以凭拿究”[5]160。自1963年伏羲庙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伏羲庙不仅作为专祀伏羲的场域存在,还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区对公众开放。对比明清时期不许闲人任意出入游玩骚扰的规定,当代天水祭祀空间已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也不再仅作为祭祀或信仰空间,而是成为集合了祭祀、旅游等多种功能的场域,并且根据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需要,还被赋予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等空间职能。
在祭祀场域性质和功能演变的同时,伏羲祭祀的形式和内涵也随之改变。组织者依据文献记载,参照现代社会祭祀风尚重塑了伏羲祭典,以公祭和民祭并行的形式,兼容了不同祭祀者的诉求,不失为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映射到仪式活动上,公祭表现出现代国家治理下的公共性,与同为祭祖类公祭典礼的轩辕黄帝祭典相比,在组织实施和仪式活动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同时,祭祀中大量运用的伏羲象征符号又显示出组织者对遵循古礼的强调,如以乐舞告祭形式出现的太牢之礼,再如祭坛两侧陈设的九鼎八簋,以祭器陈设的规格等方式,与伏羲的地位建立起对应关系。相较于公祭的现代性和公共性,民祭则以贴近民俗、与民同乐的原则表现出对明礼的沿袭,不但祭祀流程基本参照明代祭礼,在祭祀文本上,甚至出现直接搬用的情况,如民祭时最核心的三献礼流程中,主持人所吟诵的三献礼乐章,即为明胡缵宗所撰《太昊庙乐章》中的初献、亚献、终献乐章。祭文作为祭祀活动的主要文本,祭祀者、祭祀对象、祭祀原委、文化内涵都在祭文中有所呈现。前文所引明代祭文充分表达了地方官员代表皇权致祭、追颂圣祖功绩并祝祷之意,而当代天水伏羲祭祀祭文中,除了固定的颂赞伏羲功绩和表达祝祷外,还有对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成就的表述,反映出伏羲祭祀活动在不同社会时期,对不同群体祭祀需求变化的调适,亦体现出地方文化习俗对国家战略和人文精神的呼应。
在祭祀内涵不断重塑的同时,伏羲祭祀的功能也在当代不断重构。一般认为,传统伏羲祭祀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先祖祭祀、精神抚慰和凝聚人群方面,而当代伏羲祭祀除发挥原有的祭祀功能,信仰的神圣性开始转向世俗的实用性。比起传统伏羲祭祀,对文化资源价值利用的指向性更突出,强调通过对伏羲祭典这一人文资源的转化利用,实现地方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诉求,“艺术节庆活动利用开放与灵活的特点,为城市文化提供展示平台,增强城市文化底蕴,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18],而“城市文化品牌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承担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19]20。此外,原本以祭祀形态存在的民间乐舞,淡化了其原有的祭神、娱神的功能色彩,在当代以具有地域特色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活动的面貌加入进来,通过传统文化重构与展演的形式,使一些民俗特色和族群印记一定程度地从小范围的流行区域内走出来,进入到更广阔的现代文化视野,充分体现出伏羲祭祀的文化传承和整合功能。
四、结语
伏羲氏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与之对应的时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被尊称为“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刘雁翔教授《中国伏羲祠庙志》指出:“不论是在古史系统中还是在民众心目中,其地位非常崇高。可以说伏羲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和确立的民族文化的象征,伏羲信仰本身体现出一个民族血缘和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而为数众多的伏羲祠庙正是伏羲信仰民俗的物化和具体表现。”[20]追溯历史上对伏羲的祭祀,可谓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朝廷继承了历代王朝的伏羲祭祀传统,又从国家与王朝的视野,对伏羲祭祀做了规范与调整,这是伏羲祭祀在国家礼制中的适应与改造。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天水伏羲庙的庙祀伏羲和淮阳太昊陵的陵祀伏羲能够在同类信仰资源中脱颖而出应奠基于此时。在明代重建起了祭祀体系的天水伏羲祭典,经历了清代的发展和近代的延续之后,于当代实现复兴,建立起了一套官、民并行的祭祀体系,有机联系起传统与现代、继承和发展,使不同群体的祭祀和文化诉求都囊括在祭祀体系中。同时,又借助于太昊伏羲祭典这一人文资源,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不断阐发伏羲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使之与现代国家人文精神相呼应,体现出比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总之,研究伏羲文化,调查伏羲祭祀,不仅对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精神、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更是意义深远[21]。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