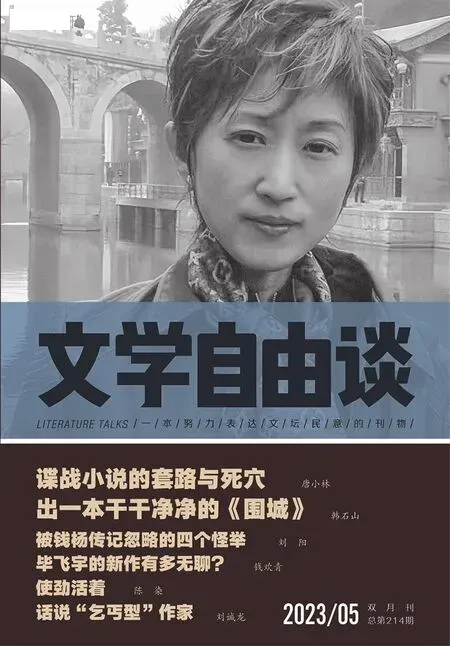听钟叔河先生谈“最好的死法”
□韩磊
今年五一假期,在北京见到任理先生,向他打听钟叔河先生近况。任理说,钟老头脑还很清楚,精神也不错,但是说话听起来吃力了,偏瘫的半边身体改善也不大。顿了顿,他接着说:“九十三岁的人了,要想恢复到中风前的状态,很难啦!”
我听了,心里一阵难过。
任理先生见状,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你也不要太难过,钟老自己一向豁达,对生死看得很开的。”
这话倒是不假,让我忽然想起两年前的那个电话来了。
2021年1月17日上午11点20分,我在办公室用座机给钟老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钟老本人。
钟老问:“请问哪一位?”我说我是韩磊,老人说:“噢,韩磊,你现在在深圳还是‘勃京’(北京)?”我说还在深圳。他说:“你发表在《天津文学》和《芳草地》的文章我都看到了。最近一期《芳草地》他们寄给我一本,看到了。你的文笔很不错。”
我问钟老:“沈昌文前不久去世了,您跟他有交往吗?”钟老说:“沈昌文我认得,比我大一点。他走得很突然。听说他死了,我的心情很不好。流沙河比我小一天,也死了。邵燕祥比我小两岁,也死了。我很难过。他们三个人死得都很突然,一觉睡过去没有再醒。但我认为,对死者却是最好的事。这是最好的死法,很好。”
钟老继续说:“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死法’,就是(指)人死的方式。还有吃法、写法,跟死法一样,一个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将来能这么死。这是最好的死法。人是生物,是生物都要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有个最低纲领,就是要看着某人死,这个纲领实现了;还有个最高纲领,就是要活得比某人长,这个也实现了,某人八十多岁就死了,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
我夸钟老:“您在这方面很豁达啊!”
钟老倒也不客气:“是呀,我是很豁达。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怕自己的事情做不完。我这个人事必躬亲,什么事都自己做。这一点我和朱正不同。朱正有个儿子,能帮他做一些事,至少他可以把有些事交代给儿子做。我不行,没有人帮我做。几个女儿都不做这方面的事,帮不上我的忙。”
钟老继续说:“我现在还在编我的文集,争取春节前后印刷。”他说,出版社以前老催他,想在他九十大寿的时候出来,后来也不催了。“我还在一遍一遍校改,总想让它少出点错。”
钟老说:“我的生日也从来不过。对于年龄大了的老人来说,过生日不是什么好事,过生日说明离死更近了一点,不值得庆祝。”他说:“我现在很怕有人来找我,占用精力和时间。以前的老编辑讲究礼数,来信必复,我现在做不到了。人家来了信,有的还写得很诚恳,不回不礼貌,但是让我每信必回,我做不到了。还有人寄来一大箱书,签名还可以,还要包装,给人家寄回去,这些事都要我来做,太麻烦了,再说我也搬不动了。”
我将电话听筒夹在左边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歪头听着,一边在纸上速记下重要内容。
11点35分的时候,我还想继续聊下去,钟老说:“保姆喊我吃饭了,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说没有了,不打扰您了。他说:“那我吃饭了,谢谢你的关心,再见!”随即挂了电话。
2019年12月之后,我没有再见过钟老,但我一直关注着老人,偶尔会打个电话。
钟叔河说,他并不是一个平和的人,只是老来才慢慢学着平和。我很认同,感觉晚年的他真的变成了一条大河,经历了高山峡谷、激流险滩,最后来到入海口,静静流淌,波澜不惊。
2021年年中,钟叔河因中风导致偏瘫,从此不能自主行动。住院半年后,回家继续做康复治疗。
“我已经被枷锁锁在这张床上了。”他说。虽然身体被困,但思想仍然自由。他面向的,仍然是整个世界。他始终乐观、豁达。
他甚至自嘲:“我这个人,现在已经死掉大半了。”
2021年3月,在《十三邀》第六季与许知远的对谈中,钟叔河说自己前半生历经坎坷,真正的人生从四十九岁才开始。但他说,跟其他人相比,自己“算是幸运的”。
跟年轻朋友谈到这次中风,他再次表示自己是幸运的:“我早就活到了生命的终点,(现在)还能坐起来跟你交流,我认为我已经很幸运了,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我已经占了很多便宜。”
2023年4月初,《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采访钟叔河时,问他“怕不怕死”,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有点怕痛。病榻边的人听到这句有些孩子气的“怕”,都笑了起来。
沈轶伦问:“冒昧问一下,您去世后想用哪句话作为墓志铭?”
钟叔河说:“朱纯(钟叔河妻子)的骨灰撒到岳麓山上一棵枫树下了。我以后也这么办吧,也撒在这棵枫树下。”
他转过脸来,鼻下插着氧气管,用能动的右手取下眼镜,双目炯炯地对病榻前的人说:“不需要墓志铭的啊,等风一吹,漫山遍野,皆可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