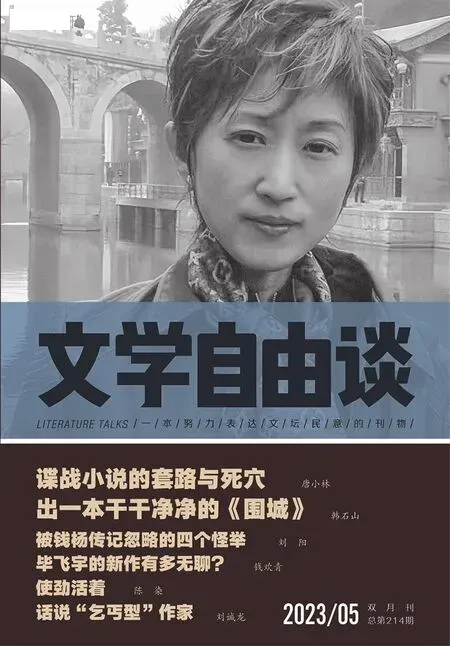“百年和解”背后的新诗难题
□李仪
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一说,最早见于2018年谢冕与《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的一次对话,谢冕在回答“新诗与旧诗共存,是融合还是和解、共舞”时明确说:“应该是和解,而且期待着共舞。”在此之后,谢冕在多种场合还进一步谈到这种说法,他在银川举办的一次关于中国新诗百年的活动中说:“一百年了,不能再把古典诗歌当作我们的对立面,更不能当作敌人,更不能随意地破坏它,我们作为后人要好好地向它学习,把那些好的东西用来丰富今天新诗的创作,要和解。”目前来看,这是对“百年和解”的较为具体的阐释。
如果仅就“和解”这句话来说,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新旧文体之间并不能构成对立关系。那么作为中国当代新诗的领航人和护航人,谢冕在新诗百年之际提出两种诗体“和解”一说,这自然是出于他对新诗形式问题的长期考虑和认识。本文拟就此谈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是新旧体诗的争议。
对中国诗界来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一个重要和敏感时期,其中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拉开了诗歌改革的帷幕。尽管黄、梁等人看到旧的诗体模式已走到尽头,但其举措并未改变古代汉语载体形式,没有突破格律诗学模式这一旧体诗学最坚固的堡垒,沦入改良主义的窠臼。“诗界革命”的贡献在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随后在胡适等人身体力行下,新诗横空出世,为新文化运动打了头阵,因此它的出现是激进的,是压抑许久爆发式的,是以一种语言和文体双重革命的姿态出现的,打破了文体衍变的渐进式规律。
对此,谢冕看得很清楚,他在《百年中国新诗史略》总序《论中国新诗》中详细分析了引起这一变革的前因后果,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这也是一次对于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反抗最为彻底的一次诗歌革命。”并且强调这一诗体的变革是划时代的,其成功在于用自由代替了格律,用白话代替了文言。
但是新诗的出现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当时习惯于古文言和旧体格律的诗人看不惯这种新诗体的出现,认为诗歌语言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白话入诗“没有形式”“缺乏韵律”,大骂这是“必死必朽”的“死文学”,甚至倾向于将新诗排挤出“诗”的行列。以胡适、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新诗开创者们高举“诗体大解放”的旗帜,在和保守派进行激烈交锋的同时,围绕形式、韵律和新诗出路问题,亦从自身写作经验出发,为新诗寻找新的理论依据,促进了后来新诗的发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极端,一是新诗作为文体变革的彻底性;二是倡导变革和反对变革的激烈性。正是由于这两点,才导致新诗一直处于被质疑的尴尬地位。
当然,新诗毕竟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保守派的反对和谩骂只能成为一时的喧嚣。问题在于,新诗的出现只是打破了对旧诗的迷信和崇拜,白话入诗抛弃了旧体格律的形式美感,以后的路怎么走就成为新的问题。直到现在,新诗的写作仍屡遭诟病,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没有“鞋子”穿的“问题少年”。
对此,谢冕认为,用自由代替格律,用白话代替文言,新诗在创立之初的这个追求,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他在探索新诗问题的时候,也指出了产生的根源:当年黄遵宪提倡的“我手写我口”,胡适说的“要使作诗如作文”,基本上混淆了诗和文的界限,对新诗的伤害非常大,可以说造成了新诗的内伤。毫无疑问,谢冕在谈到新诗问题的时候,也是与后来的“创格”派一样,是把形式问题摆在前头的,但是作为新诗的守护者,谢冕理想中的形式与“创格”派大力推崇的格律并不是一回事。
其次是格律对新诗的纠缠。
应该说,新诗之初确实散漫肤浅,诗文不分,并不符合谢冕关于诗要有“味”,更要“好听”,最重要的是要“精致”的美学要求。而谢冕所说的“内伤”,指向的是新诗的形式。但是在百年来中国诗界有一个奇怪现象,对新诗形式问题的介入,竟然是新诗早已摒弃的格律,也就是说,要给这个“问题少年”穿上格律的“鞋子”。
新月诗社成立之后,闻一多率先对新诗实践进行反拨,倡导新诗“创格”,当然闻一多的初衷并不是对新诗的釜底抽薪,而是针对当时新诗的浅薄和散文化现象,用格律纠正写诗比下棋、打球、打麻将还要容易的弊端。为此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建筑美(整齐),由此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唐代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由格律向自由体转化,而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月诗人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转化。两者都是逆向而行,给人们留下深深思考。
闻一多之后,格律理论对新诗形式的干预起起伏伏,尽管遭到戴望舒“诗不能依靠音乐”的阻击,但还是持续下来。最值得一说的是何其芳对新诗格律的重新阐释,他在1954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是他相关理论的集中展现。其中,何其芳对新诗创作需要格律“节制”的观点,强调诗歌的听觉效果,以及押大致相近的韵,对闻一多格律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随后“新民歌运动”兴起,“现代格律诗”理论很快陷入沉寂。
尽管何其芳对新诗格律的研究生不逢时,但客观来说,格律体与自由体的形式争论一直纠缠不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体的先锋和口语诗歌渐渐走火入魔,刺激了传统诗词重新崛起。在弘扬国粹的旗帜下,一批热心“创格”的诗人、评论家、学者摆出拯救新诗的架式,在深圳成立了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两年后,学会在北京召开雅园诗会,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新的格律诗派——雅园诗派正式建立,其宗旨为“重振新格律雄风”。学会和雅园诗派成立后,着手推动新格律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形成了继闻一多之后的又一场格律诗运动。
2004年9月,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其目的在于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和“三大重建”,其中就包括重建新格律诗体。
客观说,当今格律诗派尽管使用的是新诗初创期保守派的武器,即说新诗“没有形式”“缺乏韵律”,但与保守派不承认新诗不同,而是不得不承认新诗作为一个新诗体的存在。这些人不满新诗创作的过于自由,信心满满地表示“要改变新诗史上一腿长(自由诗)、一腿短(新格律诗)的畸形面貌”,为此还把诗分为自律、准格律、半格律、共律、格律几种基本形态,甚至有人“郑重地宣告:将来的诗坛必然主要是新格律诗的天下”。这和有人撰文高呼“真诗在歌词中”一样,都属于用情绪化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学术问题。
面对诗歌界如此混乱的局面,谢冕在对话中明确表示:新诗的灵魂是从内容到形式彻底的自由而摈弃格律的规范,近百年间不断有人想恢复或部分恢复传统诗词的格律形式,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为有悖于新诗的自由精神,很难被普遍认可。他在《论中国新诗》以及多个场合也确曾说过,“音乐性也是诗歌的一个底线”,认为“诗歌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很显然,这里的理论含义是,音乐性并不等同于格律。
再次是新诗的音乐性之辨。
所谓格律,即平仄、用韵、对仗以及顿歇等方面的要求,是诗歌创作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化形式。需要强调,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先有了格律才有了诗,而是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古代文人为了让诗更适宜吟唱,总结出的一套完整的格律框架,这套框架直到中唐以后才完全成熟。
由此看来,为了让诗在形式上更美,适宜吟唱,这才是制定和完善格律的唯一目的,因为违背了格律就会在吟唱时变得拗口。可以这么说,格律就是关于格式和声韵的游戏规则,并不涉及文本的内容,也不能概括文体形式的全部。
即使这样,也不能说格律就等同于音乐性;同理,音乐性也不等同于文学性,诗作为文体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因此,人们说的押韵只是为体现音乐性而非文学性,如果只谈音乐性,对新诗来说无异于缘木求鱼。先人是从敲击一块石头开始发现了音乐,人们说话有声有调还有韵也具有了音乐的形式质感,这才是谢冕把音乐性当作诗的底线的来由。
就文体意义而言,在探讨诗的形式和音乐性时,有一个首要问题需要考虑,就是诗到底是什么,而认识这个问题必然涉及诗从何来,它在艺术上呈现的特征是什么,以及作为诗体它应该被什么所左右等等。再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把诗称作文学中的文学,称作缪斯女神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定是有着一个能够统摄一切文学艺术的共性的东西,而这个统摄一切的“主宰”应该说就是“诗性”。诗性既然在所有艺术样式中都存在,那么作为诗就应该是诗性体现最活跃的地方而不是其他。换句话说,“诗性”就是诗的特性,是诗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对诗的认识,这个焦点不能缺失。
新时期以来,“诗性”一词在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界可以说频繁出现,但这个词至今无人能够说得透彻,甚至还常常把它和诗意混为一谈,以致有人慨叹“这也许是一个永远难以理清而无法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应该看到,“诗性”具有超验性,我们很难提供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争议的定义,但作为一种内心感应和诗性思维相互激发的本源,我们从学理角度将其内涵、特征、外显功能等搞清楚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比单纯强调语音声韵的研究更为重要。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有助于人们对诗的认知,消弭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其实诗性与否,最直接的判断就是要看诗的感发方式,诗是人性中一种内心隐藏着的冲动,这种难以持续的内心感受和意绪飞扬是写诗的动力,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其他文体完全不同。这也难怪有人说,“诗简直就不是文体”。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郭沫若在阐述“内在律”时提到的诗“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现情绪的)”,更能触摸到诗的本质。
心绪飞驰为诗,中国的古典诗歌遵从自然声韵和心动的节奏,乃为天籁。这才是谢冕所说的音乐性和诗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