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的诞生与13—14世纪的传记书写
邱江宁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13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崛起,旧世界的格局和秩序被全盘颠覆和彻底改变。杰克·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1](P282)确切地说,从成吉思汗结束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开始,对于草原上的游牧人而言,他们有了共同的君主,对于13世纪的世界而言,“这是蒙古帝国建国的开始,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2](P1)“世界史的诞生”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所著《世界史的诞生》。实际上拉施特主持《史集》编撰之际,伊利汗国完者都汗就朦胧地意识到,蒙古人的形成历史实际纳入了不同区域的文明史,具有世界史的特征。而西方学者亦往往以世界史的视角和格局,来观照和研究蒙古人的世界征略及其对于此后世界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诚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指出的,“蒙古人,虽然是残忍的,但是还有一种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并且对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3](P29-30)他概括得很精当。尽管历史领域的研究向来直面蒙古人的世界性影响,但中国传统传记研究领域对13—14世纪的传记似乎颇有忽略,既不关心这个时代的传记书写本身,对其在世界性和民族性书写方面的独特贡献也鲜有置喙。事实上,这样一种忽略,可能是方法论的问题,而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13—14世纪以来包括传记写作在内的所有书写的研究。
一、蒙古人的百年征略与13—14世纪世界格局的形成
蒙古人的崛起和世界征略,“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1](P282)与之前的所有时代相比,蒙古人所建立的帝国,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黑海沿岸,南到南海、印度、阿富汗,北到北冰洋,蒙古大汗国重组了世界版图,统一了原来相互隔绝的国家,为世界建立了新的秩序。[4](P440)追踪蒙古人的发迹和崛起历程,可以知道,蒙古人的百年征略史,打破了旧世界的秩序板块,破坏了之前由许多政权割据而形成的各种阃域藩篱,使得“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5](P318)可以说,在13—14世纪间,蒙古人成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主体,并推动了13—14世纪世界格局的形成。
1、成吉思汗时代的征略与世界秩序之变
从时间上看,13世纪是蒙古人崛起的时代。1206年,铁木真统一漠北高原,建立大蒙古汗国。1205—1227年,蒙古对西夏发动(1205、1207、1209、1217、1224、1226)六次大的战役,直至灭夏。西夏东界与金国接壤,北界与蒙古相邻,控扼着连结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的主要交通线。1211—1334年,蒙古对金朝发动了1211—1217、1217—1223、1230—1334三个阶段的灭亡战。鼎盛时期的金朝疆域,包括东北、华北、关中、中原和黄淮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金朝灭亡,使位处漠北的蒙古汗国势力直接延伸到南宋。
在征战乃蛮族之际,蒙古人注意到在中亚建立的西辽国。西辽国在其势力最盛之际,高昌回鹘、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和花剌子模国都对其臣服,基本控制着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段线。1218年,蒙古攻打西辽,不仅拉开了蒙古第一次西征的序幕,也是对陆上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进一步开拓。1219年,成吉思汗以“讹答剌事件”为由,(1)1218年,成吉思汗派由450人组成的蒙古商队,前往中亚花剌子模国从事商贸活动。在途经讹答剌城时,守将亦纳勒赤黑诬陷他们是奸细,并将蒙古商人全部处死,只有一名驼夫逃回。成吉思汗派使者要求赔偿,遭到拒绝,于是发动攻打花剌子模国的第一次西征。发动对花剌子模国的大规模征略。花剌子模国的疆域西越里海、乌拉尔、咸海,北至伏尔加河,南抵申河、波斯湾,东至帕米尔高原,控制着商人到伏尔加河、乌拉尔、大波斯、近东及东罗马帝国的必经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占领花剌子模国的重要文化中心不花剌城时,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将士毫不客气地宣示了他们对世界新秩序的主导权。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这样记述道:
……他们又把装古兰经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兰经左右乱扔,拿箱子当马槽用……当代的伊祃木、沙亦黑、赛夷(sayyids)、博士、学者,在总管的监督下,替他们看守马厩中的马匹,执行总管的命令……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自己的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6](P113)
不花剌的语源为“不花儿”(bukhar)一词,在祆教徒的语言中意为“学术中心”,“自古以来,它在各个时代都是各教大学者的汇集地”,[6](P109)但是,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将士在占领不花剌后,却让学者们为他们看马,把装古兰经的箱子作为马槽,把古兰经踩成烂泥。之所以如此践踏不花剌的文明秩序,是因为成吉思汗要以不花剌为范例向世人宣谕:“我是上帝之鞭”“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在成吉思汗看来,所谓的“不必说出你们在地面上的财物;把埋在地里的东西告诉我”,[6](P114)也就意味着地上所有的人与物,所有的地上秩序都将由蒙古人确立和掌控,以往的秩序和规矩亦将由此改变。
2、窝阔台汗时代的征略与世界驿站之建设
1227年,西夏被灭之前,成吉思汗去世,其第三子窝阔台接续大汗位。1231年,窝阔台汗灭亡花剌子模国;1234年,灭亡金朝。之后,1235年,窝阔台汗发动第二次西征,继续成吉思汗的开藩建汗事业。第二次西征后,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到维也纳,都承认蒙古帝国的权威。
相比于成吉思汗的业绩,窝阔台汗对于当时的世界秩序而言,是在帝国统辖范围内遍设站赤,确立驿站制度。“站赤”是蒙古语“jamci”的音译,“站赤”本指管理驿站之人,另有“向导”之意。[7]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汗国境内普遍设立站赤,配备人员和牲畜,而窝阔台汗确立驿站制度,无论铺设范围、密度还是供给,都远胜于成吉思汗时代。从《元史》的记载来看,驿路有水路和陆路之分,故驿站供有走陆路的马、牛、驴、狗等牲畜以及车;使用站赤资源要凭官府颁发的符信为证;而供给站赤的民户以时签补;站赤在关会之地配有办事机构和官员,若有纠纷官司,由通政院、中书兵部处理。《元史》写道,窝阔台即位当年(1229年)十一月,敕:“诸牛铺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一十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四年(1332年)五月,谕随路官员并站赤人等:“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段匹、鹰隼,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8](P2584)由于窝阔台汗在当时蒙古人所统辖之地遍设驿站,并确立了较为细致的建设制度,“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8](2583)窝阔台汗设立的驿站制度被后来的大汗所继承。
窝阔台汗曾评价自己的功绩云:“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9](P619-620)金朝与蒙古是历代世仇,成吉思汗也是以掀起蒙、金的民族仇恨而打开蒙古征略世界的局面,但蒙古灭金的事业是由窝阔台领导完成的,而窝阔台将平定金国与设立驿站等同并举,足见窝阔台汗在驿站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成吉思汗的意义在于奠定蒙古人开藩建汗的事业,并向世界宣告蒙古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到来的话,那么窝阔台在蒙古人统辖的世界范围内建设驿站的意义在于,它令13—14世纪的世界,梯航往来、“海宇会同”。[8](P2583)
3、蒙哥汗、忽必烈时代的征略与13世纪世界格局的确立
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之后,大蒙古汗国经过政权的动荡更迭,于1251年共推蒙哥为大汗。新当选的大汗立即发动以对西亚为主的第三次西征。1252年旭烈兀奉诏率军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10](P144-145)1256年灭木剌夷国,1258年攻陷报达,灭阿拔斯朝,1259年侵入叙利亚。1260年,以蒙古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艾因·贾鲁战役中的失败为标志,第三次西征结束。
蒙古的三次西征,建立了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除在漠北草原建立驿站外,四大汗国境内也遍设驿站,将蒙古草原与四大汗国的驿站交通网连接起来,使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原至草原,再到西域、中亚、钦察草原,[11]形成由蒙古“黄金家族”所统领的世界性大帝国,也正因如此,旧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不再被各个割据政权的国界所隔离。
在西征的同时,蒙哥汗还在东亚的高丽和南宋拉开战局,最终因1259年蒙哥汗在南宋战场去世,蒙古帝国分裂为一些区域政权。1265年,元朝发动全面攻打南宋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元朝与四大汗国时常爆发边界冲突。这使元朝的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为此,元朝对于控制着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南宋志在必得。1276年,元朝一统南宋。此后,元朝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先是于1274、1281年对日本发动了两次战役;1282年攻打占城;1277—1287年发动对缅甸的战争;又于1284—1285年、1287—1288年对安南发动了两次战争;1292年还远征爪哇,等等。这些东亚、东南亚国家,虽属蕞尔小国,却往往控制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路段。尽管元朝没有将这些王朝变成自己的附属国,但从《岛夷志略》写作的情形来看,作者汪大渊在1330年、1337年两次乘桴浮海,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远达东非,这也可以侧见元朝海上丝绸之路拓展的情形。
由于蒙古人对海、陆丝路的大力开拓,13—14世纪人们的世界格局意识引人注目。人们发现,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在1402年被朝鲜合成了一幅颇为“完整”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而这幅东亚现存最早的单幅世界地图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包括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特别是,正西竟然绘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包括欧亚非三大洲。[12]这些落实于地图上的地理名称和标画位置,以及所隐含的地理观念等,不仅集合了13—14世纪中国、伊斯兰世界和朝鲜半岛的地理知识,更让人无法忽略由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而带来的13—14世纪人们所具有的世界格局意识、世界性书写动向。这其中,关于蒙古人的传记非常具有代表性。
二、13—14世纪世界作者对蒙古人的传记书写
在蒙古人依靠武力改变13世纪的世界秩序之际,那些被各个割据政权管辖的交通要道、文明中心、人口聚集地被统一到以成吉思汗为领袖的“黄金家族”的管领之下。在13—14世纪间,对蒙古人的书写不仅有蒙古语,还有波斯语、阿拉伯语、拉丁语、亚美尼亚语以及汉语等诸多语言,并产生了类如《史集》那样极富世界性书写倾向的标志性著作。
1、蒙古语系列
蒙古语系列主要有《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两部著作。《蒙古秘史》(2)《蒙古秘史》或称《元朝秘史》,原名《脱卜赤颜》,因为是蒙元时秘藏内廷的蒙古史书,明洪武时,翰林译员们把它题作蒙古语《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并把其中每个蒙古词逐一用汉字音写下来,再加上旁译(每个蒙古词旁所注汉文意思)和总译(每节蒙文大致内容的汉译),作为培养通蒙古语的大批译员们的蒙语教材,汉文书名为《元朝秘史》。(Mongqol-unNihuchaTobchiyan)是成书于鼠儿年(3)关于鼠儿年所指的具体时间,学界有多种不同的意见,主要有戊子年(1228年)、庚子年(1240年)、壬子年(1252年)和甲子年(1264年)诸说。的用畏兀儿体蒙古语撰写的《脱卜赤颜》的汉语表述,它从成吉思汗先祖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开始写起,叙及成吉思汗系谱、传说、事迹,一直写到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为止。余大钧先生根据中外史料认为,“《秘史》成书于1252年壬子鼠年秋七月”,[13]钱大昕认为“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唯《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俚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鲜,良可惜也”。[14](P456)
《圣武亲征录》中的“圣武”由成吉思汗的尊号“圣武皇帝”而来。“圣武亲征录”这一书名,是元世祖至元年间史臣编撰完稿时所用的名称,所以《圣武亲征录》是有关蒙古历史的用汉语译写的著作。全书共一卷,其内容稍稍带过铁木真出生的端起,然后便从壬戌年(1202年)开始叙述,直到辛丑(1241年)冬十一月初八日,窝阔台汗五十六岁时在月忒哥忽兰之地驾崩,记录其间所发生的成吉思汗一些早年事迹、统一蒙古各部,西征、攻金以及窝阔台汗灭金等事件。[15]
2、波斯语系列
波斯语系列主要有《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萨甫史》《纳昔儿史话》等著作。关于《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y-iJuvaini)的写作与作者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1226—1283年)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志费尼曾担任蒙古派驻乌浒(今阿姆河以西)诸省长官阿儿浑的秘书,于1247年、1249年、1251年跟随阿儿浑赴蒙古朝见大汗,在哈剌和林停留一年五个月;又曾跟随旭烈兀参加征服阿剌模忒堡,灭掉亦思马因派王国的战争。在哈剌和林停留期间(1252—1253年),志费尼应友人之请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此后又断续写了七八年。《世界征服者史》所记述的内容共分三卷:第一卷,记述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三汗时期历史,以及畏兀儿、哈剌契丹后期的历史;第二卷,主要是花剌子模王朝史,以及花剌子模灭亡后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等的统治;第三卷,从拖雷、蒙哥到旭烈兀的历史,以及亦思马因派王朝史。[16]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征略花剌子模的过程,志费尼是第一个对其详尽书写的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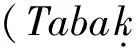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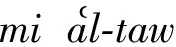
3、阿拉伯语系列
阿拉伯语系列主要有《历史大全》《札兰丁传》《眼历诸国行纪》等著作。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艾西尔(Ali ibn al-Athir)的《历史大全》(Al-Kamilfial-Tarikh),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创世时代,下迄1231年。伊本·艾西尔一生经历了两次外来侵略,一次是西方十字军东侵,一次是蒙古人西征。伊本·艾西尔年轻时正值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晚年时亲历蒙古人西征,所以该书根据作者亲见亲闻,特别对十字军东侵和蒙古人西征,作详尽记载。[18]
奈撒维(Shihab al—Din Muhammad al—Nasawi)的《札兰丁传》(Siratal-SultanJalalad-DinMangubirti),写于1241年,内容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在位后期一直写到札兰丁之死。札兰丁是花剌子模国的最后一任君主,作者奈撒维是呼罗珊(Khurasan)之奈撒人,1223年蒙古军班师东还后,花剌子模末代算端札兰丁从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复兴破败之故国,奈撒维被任命为书记,自此追随札兰丁直到他败亡(1231年)。因为书记之便,奈撒维不仅与花剌子模高官有交往,熟知其国事,且目睹了蒙古人和札兰丁的军事活动,所以传记在详述蒙古攻灭花剌子模国过程之际,尤其对札兰丁的活动轨迹以及呼罗珊一带的情况加以详述。[19](P94-95)

4、亚美尼亚、拉丁语等
亚美尼亚修士乞剌可斯·刚扎克茨(Kirakos Ganjakets’i)于1241—1265年撰写《亚美尼亚史》,该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关于蒙古人征服亚美尼亚的记录。乞剌可斯1203年生于阿塞拜疆的Gandzak(今阿塞拜疆的甘贾)。1236年,乞剌可斯与老师瓦纳堪(Vanakan)被蒙古人俘虏,并担任可汗的秘书,与西方通信。乞剌可斯因此学会了蒙古语。1236年,人们为瓦纳堪支付了赎金,乞剌可斯也成功逃脱。所以,在《亚美尼亚史》中,乞剌可斯编制了第一个在欧洲语言中有等价物的蒙古语单词表。另外,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于1254年奉拔都之命入朝觐见蒙哥汗,乞剌可斯作为随员陪同在旁。他们此行的行程及见闻被乞剌可斯记录下来,收入《亚美尼亚史》中。(6)Kirakos Ganjakets′i,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ans.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1975,1986),Section58:"Concerning the trip of the pious king of the Armenians,Het′um,to Bate and Mongke-Khan",Online at: http://www.documentacatholicaomnia.eu/03d/1240- 1250,_Kirakos_Ganjakets′i,_History_of_Armenia,_EN.pdf.Berosian′s website has been mirrored online at:http://www.attalus.org/armenian/kgtoc.html. (Some theological sections omitted.)
用拉丁语写作的《蒙古史》(L′YstoriaMongalorum,又名《出使蒙古记》)是意大利方济各主教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ean de Plan Carpin)出使蒙古的亲身经历记录。1245年4月,加宾尼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从法国里昂出发,前往蒙古汗国,希望一方面侦查蒙古征伐的动向,一方面阻止蒙古对欧洲的征伐。1246年的8月,他们到达哈剌和林,参加了贵由大汗的登基大典。当年11月,他们踏上归途。1247年,加宾尼一行回到里昂,向教皇递交了他的奉使报告——关于鞑靼人的见闻记录,这就是后来在欧洲影响深远的《蒙古史》。全书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见闻的情况,是欧洲人最早对蒙古人的观察和记录。[23](P1-175)
鲁布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的《东行纪》也是用拉丁语写作的。1253年,鲁布鲁乞受法国路易九世派遣,从君士坦丁堡启程前往蒙古汗国。他先到达钦察汗国拜会了拔都,并跟随其一道前往哈剌和林,于1254年觐见蒙哥汗。1254年7月,鲁布鲁乞带着蒙哥汗答复路易九世的国书,于1255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他将沿途各族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写成出使报告递交路易九世,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情况。[22](P177-327)
5、日语系列
日语系列主要有《蒙古袭来绘词》《八幡愚童训》等。《蒙古袭来绘词》是日本竹崎季长根据其亲身经历所绘制的长卷画册,完成于1293年2月9日。它以图像的形式记录1274、1281年蒙古与日本发生的两次战争。一般认为,“绘词”是竹崎季长命令画师所作,绘图之外还有解释战况的词,故又称《竹崎季长绘词》。
《八幡愚童训》中的“八幡”指八幡神。日语中的八幡神(はちまん),也被称作八幡大菩萨,自古以来被日本人作为弓箭之神广泛信仰。“八幡愚童训”的意思,就是让儿童都能懂得八幡神在这场战争中显灵的一部解说书。作为最早将“元日战争”场面纳入视野的叙事作品,该著如实描写了双方的作战方法,对日本武士的活动、日期记载也相对准确,是现今留存了“文永之役”对马、壹岐岛作战过程的唯一资料。[24]
6、汉语系列
汉语系列包括金人、南宋人、高丽人、元人的书写,是关于蒙古人历史的主要载录来源,主要体现为行记、碑铭、传记、行状等形式。金人的著述以《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汝南遗事》等为代表。《北使记》是吾古孙仲端口授、刘祁笔录而成的行记作品,记述了兴定四年(1220年)七月,金宣宗派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出使蒙古,向成吉思汗请和之事。其时,成吉思汗正远征花剌子模和印度,驻扎于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一带。吾古孙仲端一行经西夏,涉流沙,逾葱岭,行程万里,到达成吉思汗驻跸处。完成使命后,于次年十二月归国,历时一年半。记述了蒙古人活动轨迹里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地理气候、民族历史、物产状况、人物风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内容。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至十六年(1221年)丘处机及一班弟子西行见成吉思汗始末,“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24](序,P1)
王鹗《汝南遗事》是记录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至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金亡之前,作者追随金哀宗在蔡州被宋蒙联军所围的历史,随日编载,有纲有目,皆作者亲见亲闻之事,记载详细确切,极为真实。
南宋人的叙录以赵珙《蒙鞑备录》,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等著为代表。《蒙鞑备录》乃嘉定十四年(1221年),赵珙被遣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见木华黎之行的叙录。内容仅十四则,未为全书,但留存了蒙古开国事迹的记载。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彭大雅跟随使者邹伸之出使蒙古。彭大雅作为书状官记录使北见闻。端平元年(1234年)十二月,宋廷再次派遣邹伸之等出使蒙古,徐霆随使,作《北征日记》。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徐霆将彭大雅使北所记稿本与自己所作《北征日记》相互参照,编成《黑鞑事略》。《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
元人的叙录以《西游录》《岭北纪行》《西使记》为代表。《西游录》记录1219年耶律楚材随蒙古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并在西域停留近十年的经历。著作记录了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时的强大,同时反映了蒙古人对西域文化的吸收情形。《西使记》由常德口授、刘郁笔录。元宪宗九年(1259年),常德奉命西觐旭烈兀,自和林出发,经天山北麓西进,到达今撒马尔罕等地,往返共十四个月。《西使记》记述了常德西行的见闻,尤其详述蒙哥汗之皇弟旭烈兀奉命西征,征服阿拔斯王朝、木剌夷政权的事迹。《岭北纪行》作于1248年,记述了1247年张德辉应诏北上觐见忽必烈的见闻,对蒙古人所居住的草原地形、气候、饮食、驿站、关山、河流、习俗等皆有记述,也是汉语文献中最早专讲蒙古可汗驻帐和林情形的报告。再如程钜夫《世祖平云南碑》、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记录忽必烈亲统中路军远征云南的历程。王恽《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记录速不台随蒙古黄金家族征略世界的一生事迹。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记录钦察人土土哈家族归入元朝,为蒙古统治者征战、平定内乱的历程,等等,汉语文献中有大量的碑铭、行状、传记记录蒙古人的事迹,是蒙古人历史最丰富的史料来源之一。
如上所述,包括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拉丁语、汉语在内的多语文献对于以蒙古人为主体的13世纪历史的记述,很真切地反映出13—14世纪间世界史家共同参与和书写蒙古人的历史与传记的事实。莫里斯认为,“蒙古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连接起了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蒙古时代见证了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第一次直接接触,这些交流为现代早期乃至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舞台”。[26]所谓的蒙古时代,其最核心的意思在于,蒙古人是那个时代的主导者和被关注的焦点,13—14世纪各种语言对蒙古人行迹的传记书写也强有力地呈现和印证了这个说法。
三、13—14世纪传记书写典型特征:世界性和民族性
如前所述,13世纪是蒙古人的时代,因为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和暴力外交,旧世界的秩序和藩篱都被打破,因追随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而带来世界范围的作者、世界范围的观察视域。共同的观照对象被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作者们追踪观察和切实书写,这使得13—14世纪以蒙古人为传记主体的书写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世界性特征,另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意味。蒙古人的世界征略行为,在打破13世纪世界本来封闭且相对单一、此疆彼界森然的秩序的同时,还给文明社会带来“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26](一册,P178)的毁灭性破坏。人们在关注蒙古人的行踪之际,基于一个被打开的世界背景进行书写,往往从族群的起源、分布、特征、称谓、信仰等方面来认知和区分部族和人群或者个体,具有很明显的民族性特征。
就13—14世纪传记书写的世界性一面而言,它体现为地理空间的打开、时间表述的差异和价值观的去中心化等情形。以1211年发生的蒙古攻金事件为例,作为一个极为典型的区域性事件,由于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以及北非各地被连成一个整体。这个事件成为世界诸多区域作者围绕蒙古人的发迹史而进行书写的共同对象。
《蒙古秘史》:
成吉思汗于羊儿年出征金国,先取了抚州,越过了野狐岭,又取了宣德府,……派遣者别、古亦古捏克·把阿秃儿二人为先锋,到达居庸关。居庸关山岭有金军守御,者别说:“咱们试着把他们引诱出来再战吧!”于是,率军退走。金军见者别率军退走,便下令追击,满山遍野地追来。追到宣德府的山嘴时,者别掉过头来迎战……杀得敌军积尸如烂木堆。[9](P415)
《纳昔儿史话》:
当我们来到桃花石的疆域之内、接近阿勒坛汗政府的所在地,从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就在视野中出现了一座高高的白色高地。我们和那个高地之间相隔颇远,有二到三程甚至更远的距离。我们这些花剌子模沙政府派遣的人员猜测那个白色的高地可能是一座雪山。我们就询问向导和当地人,他们的回答是:“它全是被杀者的骨骼。”我们又向前走了一程,土地由于人的脂肪而变成油乎乎的,颜色发暗,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了另外三程,直到我们重新踏上干燥的土地。由于来自土地的侵染,使团的一些成员生病,有人病死。[27](P183-184)
《圣武亲征录》:
(辛未)秋,上始誓众南征……金人惧,弃西京。又遣哲伯率众取东京。哲伯知其中坚,以众压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谓我军已还,不复设备。哲伯戒军中一骑牵一马,一昼夜驰还,急攻,大掠之以归。”[28](P212、216)
《史集》:
成吉思汗纪[五]
从始自伊斯兰教历607年8月的豁你亦勒,即羊年[1211年],也就是他出征乞台、同乞台君主阿勒坛汗作战之年初起……现在还让我们来[记述]成吉思汗远征乞台的历史吧。成吉思汗发兵出征后,首先来到了塔勒湖,占领了大水泺……蒙古军尽管人数不多,却很快地击溃了乞台、哈剌契丹和女真军队。[蒙古人]杀了许多人,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17](一卷,二分册,P225、228、231)
1211年发生的蒙古攻金事件,对蒙古人而言是一个证明其武力值的重要事件,他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往最强大的仇敌遭到了几近灭顶的打击。对于13世纪的世界而言,南下攻金意味着蒙古人开始以原有的高原地盘为起点,陆续对世界展开征伐,宣告“蒙古时代”的到来。在上述书写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书写的世界性范围。作为蒙古人传记书写的一部分,对蒙古攻金这一事件的书写,从13世纪大蒙古国汗廷所在地和林,拓展到中亚的德里苏丹国,又跨越到元朝的大都以及西亚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在相当大程度上覆盖了13世纪蒙古征略的世界范围;书写者有畏兀儿人、波斯人和汉人等,当时的主要书写语种都囊括其中。
其次,世界范围内的书写中,关于时间的表述。上述所引材料的写作时间,都距1211年蒙古攻金事件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更重要的是,写作时间都在蒙古人已发动世界性征略之后。蒙古人已然令13世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区域和政权臣服于自己。所以,对蒙古人传记进行书写中的时间表述就意味深长。作为草原游牧部落族群,蒙古人据其游牧生活特点而以草青为一岁,新月初升为一月,《蒙鞑备录》云:“其俗每以青草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为一月,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29](P266)蒙古人以动物纪年,《蒙古秘史》的纪年即完全按照动物生肖表述法,但在与汉人、女真、契丹人的接触中,蒙古人学会了以干支纪年。《蒙鞑备录》谈到蒙古纪历时说:“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改曰庚辰年。”[29](P267)所以,至元年间编撰的《圣武亲征录》的纪年表述即为干支纪年。有意思的是,拉施特用伊斯兰教历来表述时间,但很注意指出蒙古纪年时间。而综合这些世界范围内蒙古人传记书写,在时间表述细节上的体现,可以看出作为世界征服者的蒙古人与世界之间的双向奔赴。1265年,忽必烈在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期望创造一种可以“译写一切文字”的书写符号体系。[8](P4518)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创制出堪称古代“世界语”的方形竖写拼音字母——八思巴字,期望作为书写表达工具,能从中原中州一直到“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26](14册,P100)八思巴字的创制反映出蒙古人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动性。《圣武亲征录》《史集》等的书写未尝不隐隐表现出蒙古人立足世界,对自身历史书写的积极擘划态度。
另外,上引材料虽是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但价值观和立场并不一致。在描述蒙古攻金的残虐程度时,《蒙古秘史》以蒙古人的口吻写对方“积尸如烂木堆”,《圣武亲征录》以冷静的笔致描述蒙古军对金人“大掠之以归”,《史集》则写道,“[蒙古人]杀了许多人,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气”,虽冷静,却有力量,一如志费尼对于蒙古人毁灭与杀戮景象的表述“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6](P116)他们对蒙古人的书写都态度隐忍,立场有些倾向于蒙古人。在上引材料中,唯有《纳昔儿史话》的作者术兹札尼是以被征服者立场和第三者的视角来描述蒙古攻金之后的惨烈情景。他描述战争之后,金朝繁荣的京城变成白骨堆积的“雪山”,而人的脂肪致使土地“变成油乎乎的,颜色发暗”,甚至使得走过的人被侵染生病,乃至病死。这种细节描述,即便是想象和编造都难以企及,而作者也指出,他的写作灵感来自花剌子模君主穆罕默德算端派遣出使蒙古的使节赛典赤·宝合丁·拉齐。此人是“一位有高贵品格的赛夷,具有显赫的出身”(7)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算端听到了成吉思汗崛起的消息,“他迫切地想通过自己信赖的人员,调查消息的真实性,带回关于蒙古军队状况、数量、武器、军事器械等的确切情报”,于是,派遣赛典赤·宝合丁·拉齐等人出使蒙古,见党宝海:《外交使节所述早期蒙金战争》,《清华元史》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所以描述没有虚构,这也深刻地还原了《蒙古秘史》所表述的“积尸如烂木堆”的现场情景。正是借助术兹札尼的描述,人们才真切地体会到蒙古人征服世界、改变世界旧秩序给世界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而不同价值立场主导下的书写,使蒙古人作为世界征服者这一传记主体形象被展示得复杂而多面。
就13—14世纪传记书写的民族性一面而言,它可以称得上世界性的根本内核,诚如合赞汗在组织编撰《史集》之前所发出的“灵魂追问”一样: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在“伊朗之地”生活,我们与东方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以及其他汗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怎样的血脉联系?[30](序,P2)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不仅打破了旧世界的藩篱,而且建设了完善的驿站系统,并在军队过去之后,将驿站系统开放给全世界的商人、传教士以及旅行者等。基于这样一个被打开的世界背景进行传记书写,包含着族群的标识性内容成为人们记住自己,并将自己区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基因。对于起初弱小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特别知道,记住自己的族源和民族历史,才不至于在被不断驱赶和不断迁徙的历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使自己陷入被人奴役和定义的危险。所以,13—14世纪间,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传记书写,关于传主民族起源和民族特性的书写是其突破和区别于以往传记书写的重要内容。
例如《蒙古秘史》中对成吉思汗的书写:
……等到篾儿乞惕人远离之后,帖木真才从不儿罕山下来,捶着胸说道:“多亏豁阿黑臣大妈,/像黄鼠狼一样耳敏,/像银鼠一样眼明,/才使我得以躲避。/我骑着缰绳绊蹄的马,/踏着鹿走的小径,/登上不儿罕山,/用柳条搭起棚屋居住。/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上,/躲避了我微如虱子的性命!/爱惜我仅有的性命,/骑着我仅有的马,/循着驯鹿走的小径,/登上合勒敦山,/用破开的柳条搭起棚屋居住。/合勒敦·不儿罕山,/庇护了我蝼蚁之命,/我惊惧惶恐已极!/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天早晨要祭祀,/每天都要祝祷!/我的子子孙孙,/都要铭记不忘!”说罢,面向太阳,把腰带挂在颈上,把帽子托在手里,以(另一)手捶胸,面对太阳跪拜了九次,洒奠而祝祷。[9](P111-112)
作为首部以蒙古语写成的史诗式著作,《蒙古秘史》记述了蒙古祖先起源及大蒙古汗国初期的历史,充分反映出蒙古人的世界观、文化观、自然观与认知方式。引文中,未曾发迹的铁木真代表蒙古人的形象,被形容成微如虱子、弱如蝼蚁,惊惶不可终日,既形象生动,又体现出蒙古人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风格特征。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成吉思汗活动的怯绿连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位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侧),这里充满淤泥,到处是险林,但它的原始地貌护佑了蒙古人。蒙古人在这里逐渐成长,逐渐强大,所以它成为蒙古人的神圣之山和精神归依。他们不停地从战场回到不儿罕山来祭祀,举行忽里台,向不儿罕山寻求精神护佑。有关蒙古人在不儿罕山生活的风俗、从不儿罕山走出去和从外面走回来的路线、不儿罕山周边的地理环境以及沿途的风物等内容,在《蒙古秘史》中有着非常多生动而真切的记录。[31]这些内容可以说是蒙古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民族性文化内容,对它们的详述也正是13—14世纪传记书写非常值得注意的民族性特征体现。
再比如阎复给钦察人土土哈作传,也是从族群的起源和族群分布开始说起:
公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産宜马,富者有马至万计。俗衽金革,勇猛刚烈,盖风土使然。……岁丁酉,宪宗在潜邸,奉命薄伐,兵已扣境,公之父班都察,举族迎降,从征麦怯思国。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种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蒭牧,俾掌尚方马畜。岁时撞马湩以进,其色清彻,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剌赤,盖华言黑也。[26](9册,P265)
阎复这篇《枢密句容武毅王碑》是一篇民族性特征非常突出的传记,钦察人因为蒙古人的世界征略,从距离中国三万余里的地方浩浩荡荡地迁徙进入中国。这一现象展示的是历史的世界性的一面,而中国本土作者阎复在书写土土哈时,从其族群的起源、分布及其迥异于中原民众的特征写起,关注的是其民族性特征。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关注和表述的内容。作为钦察人,阎复对土土哈的个体书写是从其所属的族群开始书写的,书写的内容包括:他到底来自哪个族群,这个族群本来分布的区域、族群的性格特征、他的族群系谱是怎样的,这个族群如何与为何迁徙到此,这个族群怎样立身于蒙古朝廷,其立身之道与立身之本是什么,他们怎么被称谓,等等。拉施特在《史集》中称赞合赞汗对民族历史的关注态度时写道:
非常详细地了解很受蒙古人尊重的蒙古族历史,非常详细地知道父辈、祖辈和男女亲族们的名字,古今各地蒙古异密(王公大臣)们的名字,并且详细知道[其中]每个人系谱的大部分。
他知道古代以迄于今的算端,篾力们的一切癖性、习惯、规距,即每个人在作战、宴饮、愉悦或不快时的习惯,衣、食、骑马的习惯,也知道他们的其他情况以及他们的现状。他曾把这一切详细地讲给各民族的代表们听,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32](三卷,P354)
合赞汗的民族历史修养集中且典型地反映出13—14世纪间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关注和表达态度,而这种对自身出处、来历的关注也深刻地影响了13—14世纪间传记书写的民族性特征。基于这样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理念,拉施特在《史集》中写道:
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因为他们的外貌、形状、称号、语言、风俗习惯和举止彼此相近……所有这些民族,都认为自称蒙古人,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17](一卷,一分册,P166-167)
作为蒙古帝国史又是最早的“世界史”,《史集》全书原分为四部分:第一编为《蒙古史》,第二编为《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为《世系谱》,第四编为《地理志》,就其编排来说,体现出从民族到世界的书写序列特征,而具体到最主体的部分《蒙古史》的撰写,拉施特对蒙古人传记书写的确在努力回答合赞汗提出的首要问题:“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力求通过撰述这一民族起源、民族的族群构成以及该族群的各种特征等问题来构建这个民族的独特性。
《史集》的产生具有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它用波斯语写成,其中含有大量突厥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的用词和术语,不仅极具世界性,而且是对蒙古人发迹与征略世界历史叙述的集大成者。而《史集》在其序言中,站在世界历史书写的立场很郑重地表述传记写作的民族性特征时写道:
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将各民族的记载传闻,按照他们在书籍中所载和口头所述的原意,从该民族通行的书籍和[该民族]显贵人物的言词中采取出来,加以转述。[所述正确与否,正如阿拉伯语所说],责任“在于转述者”。[17](一卷,一分册,P93)
《史集》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其指导思想所根据的是这样一条原则:伊斯兰教各族人民——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历史,只不过是注入全世界历史海洋的一条河流;世界史应当是全世界的历史,包括当时已知的各族人民”。[17](一卷,一分册,P60)所以,《史集》撰修过程中,有作为蒙古人的合赞汗亲自参与和建构;参考了当时波斯语、阿拉伯语有关著作,参阅了伊儿汗宫廷所藏蒙古人的传说和古老记录、世系谱等口传、记述内容以及蒙古人从世界征略区域所搜集来的关于科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的手稿;还动用了从蒙古统治范围内各文明圈招来的不同人种、不同语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等等。杉山正明认为《史集》的完成,“确切地证明了蒙古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时代,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30](序,P7)如果说《史集》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史”的诞生的话,那么,《史集》撰修者们认为其意义即在于它只不过是对各民族传记进行真实转述,这可能意味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特征的交融并存既是13—14世纪传记书写的重要特征,又是代表这个时期所有书写所贡献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