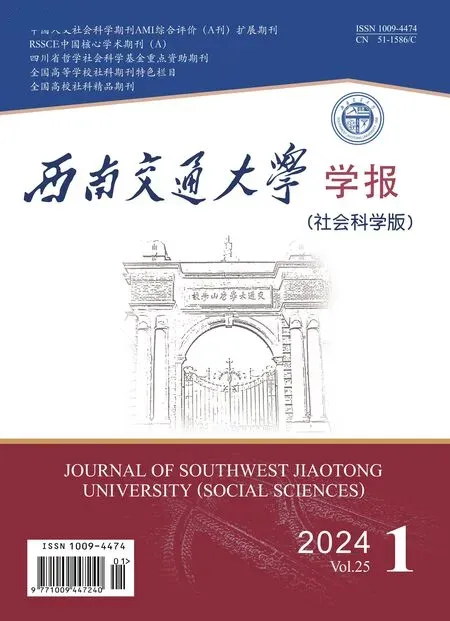简谈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
徐子黎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字典,作者东汉许慎将汉字按照部首编排,同一偏旁的文字置于一个部首之下,这种编排方式对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了将汉字按部首编排之外,许慎对汉字构形分析亦很有建树。传统文字学者在讲汉字构造的时候,一般会遵循“六书”的说法。“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云:“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六艺”是周代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技艺。《周礼》并没有说明“六书”的具体内容,汉代学者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郑众注《周礼·地官·保氏》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1〕许慎《说文·叙》还给“六书”分别下了定义,后人多袭用许慎的“六书”名称,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本文所引《说文》内容出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引《说文》中的例字均出此书,不另注。。班固、郑众、许慎对“六书”分别有不同的解释,其说大同小异,同出一源,其中许慎的说法最具体,不仅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等字分别举了例字,还对汉字构造做了一些说明,这也是汉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说文》中,许慎首先提出形声字的省形和省声理论,省形如《说文》云:“曐,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生声。一曰:象形。星,曐或省。”“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关于省形和省声,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说:“造字或用字的人,为求字形的整齐匀称和书写的方便,把某些形声字的声旁或形旁的字形省去了一部分。这种现象文字学上称为省声、省形”〔3〕。对于形声字的省声,裘先生在书中将其大体分为三类:(1)把字形繁复或占面积太大的声旁省去一部分;(2)省去声旁的一部分,空出的位置就用来安置形旁;(3)声旁和形旁合用部分笔画或一个偏旁(2)形声字省声的三种类型具体使用情况可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7页。。
以上所说的省形和省声,是比较常见的。本文讨论的是古文字中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此处所说的古文字指的是秦以前的文字,包括秦代小篆。下文试从形声字的省略和表意字(3)本文没有采用许慎“六书”中“会意字”的说法,而倾向于裘锡圭先生“三书说”中的“表意字”这一意见。的省略两方面加以讨论。
一、形声字完全省略声旁
对于形声字来说,由于声旁在形声字中是关键性的主导构形要素,如果完全省略了,就成了一个不认识的字或者是错字,对于文义的理解也造成障碍。然而在古文字中,有些形声字是完全省略声旁的。下面通过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


《集成》11295号著录的章子国铜戈是1981年湖北省文物商店在枝江县收购的,其上铸有铭文。黄锡全先生曾撰《湖北出土两件铜戈跋》一文,对此戈的铭文、国别和年代提出了一些见解。据《集成》所印拓本,章子国戈铭文位于胡部,一行十一字,学者对其作出考释,铭文“尾其元金”中的“尾”字比较令人费解,《集成》增补本隶作“尾”。黄锡全先生读其为《说文》中从“火”“尾”声之“”,“”即“燬”字,并引《说文》“,火也。从火,尾声。《诗》曰:‘王室如。’”今本《诗·周南·汝坟》作燬。“燬其元金”意为用火化其好铜,犹如金文习见之“用其吉金”“择其吉金”等义〔5〕。李家浩先生不同意黄锡全先生读“尾”为“燬”的意见,认为“燬”作为名词指“火”,如《诗·周南·汝坟》“王室如燬”;作为动词是“火烧”的意思,如《晋书·温峤传》“峤遂燬犀角而照之”;但是似无火化或熔化之义。他也不同意黄锡全先生认为“尾其元金”犹如金文习见之“用其吉金”“择其吉金”等义,认为纵观两周铜器铭文,凡是讲到用“吉金”铸作器物,一般都是先说“择”或“用”“其吉金”,然后说铸作某器,并将邾公孙班镈铭“邾公孙班择其吉金,为其龢镈”和章子国戈铭相比较,认为章子国戈铭“尾”当读为“选”,“尾”省略了“少”字。字本应为从“尾”从“少”,“少”“小”古本一字,甲骨文作三小点或四小点,像细小的沙粒之形,所以“少”古有“沙”音,章子国戈“尾”可看作从“尾”“沙”省声。上古音“沙”是生母字,“选”是心母字,都属于齿音。“沙”是歌部字,“选”是元部字,歌、元阴阳对转,“沙”可以读为“选”〔6〕,李家浩先生认为“尾”省略了“少”,是基于古文字中本来存在从“尾”“少”声之字。章子国戈“尾”旁右侧模糊不清,李守奎先生认为从残存笔画和构形上说,可能是“攴”〔7〕,黄德宽先生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亦疑右边是“攴”,并读其为“选”〔8〕。

二、表意字的形体省略
在形声字完全省略声旁之外,表意字中还存在特殊的形体省略现象,裘锡圭先生就曾说表意字有省略偏旁字形的现象,并且举了几个例子,如“尘”字繁体“塵”的篆文从三“鹿”从“土”,籀文“塵”中之“鹿”则省为鹿头形。《说文》把“尘”字篆文分析为“从麤从土”,“塵”所从的“鹿”可以看作“麤”的省形。另如“尿”字篆文从“尾”从“水”会意,隶、楷省“尾”为“尸”,也可看作省形〔3〕。裘先生所举的这些例子是一般意义上的省形,省略前后还有明显的字形联系。


我们以天亡簋(《集成4237》)为例,天亡簋是西周重要的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国家博物馆,又称大丰簋、朕簋。器内底有铭文8行77字,铭云:“乙亥,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饎上帝……丕克讫衣王祀,丁丑,王饗大宜。”《逸周书·度邑》记述了周武王克商后至东土洛邑相宅时对周公讲的话,云:“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14〕。
天亡簋铭和武王至东土相宅有关,其中“衣祀于王”的“衣”或解释为祭祀名,与殷通用。《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郑玄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公羊传·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殷,盛也。”“丕克讫衣王祀”,“衣”读为“殷”,“丕克讫殷王祀”即终止殷王之天命祭祀,亦即灭亡了殷。《尚书·多士》:“殷命终于帝。”〔15〕李学勤先生云:“‘衣’字前人多读为‘殷’,但‘殷’有合义,祀文王一人为什么称合祭?‘衣’字读作‘卒’,训为既,似更允当”,并且说“总之,‘衣’‘卒’二字在卜辞金文中往往混淆不分,需要我们细心区分,才能正确读释。这和我们讨论过的‘氏’‘氐’两字在金文中相混淆,情形正是类似的。这为古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一种新的事例,值得今后进一步讨论”〔13〕。裘锡圭先生云:“簋铭‘衣祀’和‘衣王祀’的‘衣’,很有可能也应该释读为‘卒’。‘王卒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可能是说王举行完对文王的祭祀,然后‘事喜上帝’。‘丕克气衣王祀’疑当读为‘丕克讫卒王祀’,簋铭是有可能以‘丕克讫卒王祀’来赞美周王的。”〔12〕在已经发表的殷墟卜辞中的所谓“衣”字,除去一些辞义不可解的,都应该释读为“卒”。
至于甲骨、金文为什么用“衣”字表示“卒”,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如果仅通过类比就认为这种情况与“氏”“氐”相混淆类似,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氏”“氐”本是同一个字,后世才逐渐分化的。由于氏、氐音稍变,故在“氏”下加“一”以别之。与之不同,“衣”和“卒”本来就不同字,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人常用“衣”表“卒”的原因还有待商榷〔12〕。对于“衣”“卒”之间的联系,其他学者亦有论述,如田炜先生认为“衣”“卒”相混用,与二者古音相近有关。他说:“把‘卒’字简化而与‘衣’字同形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商末的黄组卜辞,西周甲骨文和金文承袭了这种用字习惯。上古音‘衣’字属影母微部,‘卒’字属精母物部,微、物二部是严格的阴入对转关系,而声母则似相隔。不过有学者认为‘衣’、‘卒’二字的读音是有关联的。有研究音韵的学者指出,后代读为影母的字在上古有时候是可以和其他声母字相谐的。”〔16〕



我们再谈一些可能的情况,金文中有“夨”字,其字如可通读为“吴”,很多疑难便可迎刃而解。《说文》:“夨,倾头也。从大,象形。”甲骨文“夨”字像倾头之形,而不必倾左倾右。《说文》以左倾者为“夨”,右倾者为“夭”,非其本义。《说文》:“吴,姓也。亦郡也。一曰:吴,大言也。从夨口。”大言即大声说话,或许就是歪理邪说的意思。从文字构形来说,“吴”字毫无疑问是一个表意字,与夨、口相关,二者作为意符会合而表意。“夨”在金文中作为国名、人名出现。如相传出土于陕西凤翔的散氏盘(《集成》10176),现藏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内底有铭文19行356字,又名散盘、夨人盘,记“夨”“散”二国土地纠纷事,铭文云:“用夨践散邑,乃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夨人有司履田”。可是,问题在于我国历史上的古书从未记载过夨国,铭文内容和典籍不符。如将“夨”读作“吴”,就有可能是《国语·齐语》的“西吴”,铭文就好讲通了。《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即位数年,“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韦昭注:“流沙、西吴,雍州之地”〔18〕,和散氏盘出土地相合。2001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叔夨方鼎,铭在腹内壁,8行48字,铭文云:“王呼殷厥士,爵(劳?)(14)此字铭文当为“爵”,王辉先生《商周金文》读其为“劳”,暂存疑。叔夨以常、衣、车、马、贝三十朋。敢对王休,用作宝尊彝。”此方鼎出土于114号晋侯墓中,如将“夨”看作“吴”,叔夨即为叔吴,“吴”“虞”可通,叔夨即为晋开国之君唐叔虞。《史记·晋世家》云:“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与武王曰:‘余命女(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19〕《史记》中有关唐叔虞的身份以及分封的传说当不可信,但晋始封君为唐叔,且唐叔身份高贵则是可以肯定的。铭称虞为“叔”而不称“子”,器当作于成王时。“夨”可能就是“吴”省略“口”,是当时书写者的一种书写习惯。如果结合叔夨方鼎的出土墓葬来分析,可知鼎出土于晋侯墓地,非普通身份,于是将“叔夨”释读为唐叔虞就很好理解了。古文字“吴”字写作“夨”,与“麗”字写作“鹿”字类似,如楚王“熊麗”写成“熊鹿”,何琳仪先生在《说“麗”》一文中认为二者音近〔20〕,我们认为形体省略的可能更大些。学者在讨论单个文字时,也曾留意到这种特殊省略情况,可是没有系统总结。
我们分析某个字的字形时,往往首先依据《说文》,然而《说文》有较多不可信之处,以“匋”字为例,魏宜辉先生在《说“匋”》一文中论述了“匋”字的构形和意义。《说文·缶部》:“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读与缶同。”对于“匋”字构形,《说文》以为“匋”字从缶、包省声,大徐本所注反切为“徒刀切”。魏宜辉先生认为考之古音,“匋”为定母幽部字。然《说文》以为“匋”从包省声,且引“《史篇》读与缶同”,“包”“缶”古音皆为帮母幽部字。“匋”与“包”“缶”虽然韵部相同,但定母和帮母两声纽远隔,从音韵上看它们似乎不应该有互谐或通假的关系。“匋”字的构形本作“”,从宀从缶,表现置于窑灶中烧制的陶器。《说文》“匋”字所从之“”并非“包之省”,而是“宀”的变体,故“匋从包省声”是不可信的。古文字中存在“缶”读作“匋(陶)”的情况,这里的“缶”其实是由“(匋)”字省简所致〔21〕。陶文中陶工刻字为了通俗简化,往往用“缶”表示“陶”,当是省简形体所致。今天的陶工在刻字的时候,仍然没有一定的书写规范。字形省略之例另如辛鼎(《集成》2660)铭有“辛万年唯人”,《集成》修订增补本读“人”为“仁”,吴镇烽先生《铭图》1318从之。读为“仁”当不可取,“仁”表示“仁义”这一抽象观念产生较晚,在西周应还没有表示“仁义”的意思,与西周金文时代不符。而且读“人”为“仁”这样的通假也显得突兀,存在猜想的成分。田炜先生认为“人”为“亟”的错字,读为“极”〔16〕,但没有说明原因。我们认为田炜先生将“人”和“亟”相联系、读为“极”可从。田炜先生可能是依据伯梁其盨(《集成》4446)铭中之“万年唯亟”对读而得出“人”为“亟”之错字。金文“人”与“亟”字形有相似之处,金文“亟”有作(《集成》4341),如果在书写过程中省略上下形体,即为金文“人”。和田炜先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这也可看作是特殊省略之例。
三、结语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一些字的用例,发现在古文字中形声字可以完全省略声旁、表意字省略部分形体,从而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字。这些现象并不是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写错的,可看作是书写者的一种书写习惯,目的在于求简。如同今天有些人将餐厅的“餐”写成“歺”,而“歺”和“餐”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这些字形简写后,当时人是可以看懂的。在汉字从象形转变为亚象形的时代,各种简省的情况皆有可能,这与汉字发展的趋势当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今天我们分析某个古文字时,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构形理论,而应当结合具体内容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