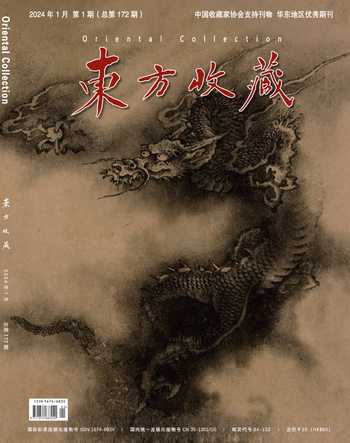从“亲子图像”看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变
摘要:家庭自古以来都是社会组成中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男性和女性组成家庭共同养育后代、抵抗风险。由此,一个个小家庭成为庞大社会的构成之基,与之相对的,不同时代的社会共识和文化思想也会反作用于每一个小家庭。这种关于家庭结构、性别分工以及家庭成员情感的微妙改变是社会变迁和生产力发展的缩影,透过不同时代关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图像作品,探索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发生转变的家庭观念,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现代社会和民众思想较千百年前的巨大转变。
关键词:亲子图像;家庭观念;女性身份
中国古人拥有独特的天地观和生死观,在数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社会中,运行着一套由观念衍生而出的无形规则。先民们在社会秩序的规训下休养生息、繁衍子嗣,谱写出一段段或波澜壮阔、或平凡淡然的人生。作为承载这些无形规则的有形图像,绘画向我们无声地彰显着那些埋藏在时间中的观念变迁,使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与先辈们心灵相通。
通过一幅幅描绘不同时期爱情、家庭、亲子的绘画,我们能够从图像的变化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国人的家庭观念是怎样悄然转变的。
一、汉画像中的恋爱观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所刻画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耕种制造、弋射收割、舞蹈庆典等场景,是对汉代人民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在众多的画像砖、画像石中,偶有一种特殊的图像,通常绘有男女亲密交合的场景,动作设计大胆奔放,人物刻画生动传神,大致有“野合图”“接吻图”“秘戏图”几类。
如四川荥经县石棺图像(图1),一对男女正相向对坐,应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彼此的双手正于胸前紧紧相握。视线再向上移动,两人亲密依偎的脸庞便出现在观者的视野中。仔细观察他们的脸部,可以发现画匠特意描绘了二人的双唇,将“亲吻”这一举动刻画得十分精细。与该图有着相似图式的还有四川彭山崖墓的“接吻图”、徐州汉画像石“接吻图”、四川乐山麻浩大地灣崖墓的“接吻图”等,这些图像的出现无疑与汉代人对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一些学者将人物的交合行为与原始时代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相联系,认为这种描绘、暗示两性交合的图像创作是出于祈求多子多福、作物丰产的目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此类图像的出现与汉代兴盛的房中术以及道教修炼成仙的神仙思想有关。[1]然而,无论这些图像产生的目的和作用究竟为何,我们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汉代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开放和包容。在家庭或是夫妻关系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共同存在的,且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密切,他们通过自然的繁衍来获得家庭的延续——具有相同血脉的子嗣,三个角色的互相作用成为组成家庭的基础。
二、婴戏图中的子女观
唐宋时期逐渐出现一种表现亲子、家庭的绘画,被称为“婴戏图”或“戏婴图”。这种以婴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绘画是中国传统题材中较为常见的门类,《中国传统婴戏图起源问题探究》一文将其归纳为:“以表现孩童在世俗生活中嬉戏玩耍为主要内容,以展现孩童纯真快乐的天性为基本主旨,多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赋予象征意义融于画面的创作。”[2]婴戏图既展现了人们对天真活泼孩童的喜爱与关怀,又表现出人们对于家庭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在婴戏图中,画家们把人类观念中生命的延续——孩童作为创作的中心,试图传达出一种充满美好愿景的家庭图式,在营造出轻松美好氛围的同时,兼具着祈福的吉祥寓意。
早期的婴戏图像以装饰的形式出现在三国时期的漆器用品之中,到魏晋时期则形成了绘画形式的婴戏图。发展至两宋时期,婴戏图逐渐形成典型范式,为大众所喜爱,在宫廷与民间绘画中常有出现。[3]至元明清时期,婴戏图除了继承自宋代的传统图示,还发展出了符合时代的全新形象。
在依赖农业的古代社会,孩子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要的存在,更多的子嗣代表了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在以农耕野采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多子”就代表“多产”,代表着更为安逸富裕的未来生活。这种对子孙后代的期盼和重视早在远古时期就已产生,例如石器时代出现的夸张了女性胸臀部位的小型石人像,便直观地彰显出了人们对生育子嗣的重视和需求。故而在年代较早的众多婴戏图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幅作品中出现众多孩童形象的图式,这些孩童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孩,还有4至6岁之间的男童、女童。《毛诗注疏》载:“皇甫谧云,武王五男二女。”[4]《后汉书》中亦有“畅有五男二女”[5]的记述。“五男二女”的生育比例常出现于文字典籍中,被认为是一个家庭中拥有孩子的最好范式,如莫高窟112号《唐群童采花图》(图2)中出现的五个男童形象和两个女童形象,可作为上述观念的图像印证。宋画中的婴戏图同样是家庭与美好生活的象征,可以在宋人绘制的婴戏图中看到打扮各异的男孩、女孩在自由玩耍。例如宋代佚名所作的《秋庭婴戏图》描绘了三个年幼的孩童嬉戏打闹的场景,画面的最中心,一名女童正在跟兄弟抢夺玩具(图3)。
然而,在宋代之后绘制的婴戏图中可以发现,有女童形象的作品明显变少了。笔者在传世作品中搜集到宋代婴戏图45幅(包括仇英等明人临摹的宋婴戏图6幅),其中有女童形象者20幅;若剔除明人临摹,则宋婴戏图为39幅,其中有女童形象的为17幅。无论是否计入明摹画,有女童形象者皆占宋婴戏图总数的40%左右。收集到元明婴戏图26幅,有女童形象者3幅,约占10%。现存清代婴戏图最多,宋与清进行比较更有意义。目前收集到清婴戏图63幅(册),画册有多页,如焦秉贞《百子团圆图》有16开,将所见婴戏图册按页合计113幅,其中有女童形象的画作10幅,约占总数的9%。[6]女童形象在画面中的减少,代表着古人家庭观念的巨大转变。在唐宋时期,男孩和女孩同样是家庭后代成员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而在元明清时期,女性后代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降低,甚至从家庭观念中隐身。
三、婴戏图中的养育观
在历代婴戏图的创作中,除了对于后代中男女性别期待的子女观转变,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即其中所显现出的家庭养育观。图像中除了出现玩耍的孩童之外,一些成年人的形象也会出现在画面中。这些成年人为孩童们的养育者,或是监护者,其与家庭中的孩子有着更加强烈和深刻的情感联系,而这些养育者基本全部以女性的形象出现。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珍藏的宋代《仿周昉戏婴图》(图4)中出现在婴孩身边的五名监护者,皆为体态健壮的成年女性形象。她们蹲坐在地上,或环抱孩童轻轻安抚、或抬手逗弄婴孩嬉戏,地上散落着几件玩具,画面右上角还有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正是一片祥和欢乐的育儿图景。在宋代佚名扇面《荷亭婴戏图》(图5)中,右侧的院子里有几个玩耍的孩童,而在左边的亭子中坐着的同样是一主一仆的两名女性。中间的女性似乎是孩童们的母亲或长辈,正慈爱地一手抚摸趴在亭子中的婴孩,一手伸向院子中玩闹的一群较为年长的孩童,眼神关切。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送子得魁图》是清代画家任淇的作品,表现了希望家庭后代能够得到功名、获得成功的殷切期盼。在这张或許并不是描绘现实景象的作品中,送别孩子的依然是一位衣着华丽的女性形象。
在这些同时绘有孩童与养育者形象的作品中,有男童、女童,也有侍女、母亲等女性长辈,却没有出现成年男性的形象。纵观中国古代众多绘画作品,我们很难看到男性家长与子女共同出现的图像,更别说如戏婴图中描绘的女性形象一样与孩子进行亲密的玩耍、抚慰。几乎所有出现在画面中的男性都局限于强调个人所拥有的自然属性,如强壮、俊朗、瘦弱等,或是他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心情思想,而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家庭属性,即便这位男性拥有三妻四妾、子嗣成群。与此相反,大部分出现在画面中的女性角色,要么作为男性凝视下的观赏对象,如同花草奇石一般供人品评赏玩;要么作为类似于“慈母”这一被高度化的形象出现。与男性相比,图像中的女性身份建构显得更加单一、扁平,失去了自身的多样性与独立性。
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深入家庭,在后代子嗣的成长过程中,男性长辈在画面中消失了。从图像中可以感受到古人家庭观中男性长辈的身份和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隔离于家庭之外的,他们或许被当作是家庭中不应与孩童交互的那部分,因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女性的束缚,同样也是对男性的束缚,因为有些父亲或许希望能够与孩子有更紧密的连接,而社会的凝视却可能迫使他失去这项权利。
四、《大家庭》中的家庭观
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创作的一系列关于家庭题材的画作,恰好从侧面反映出当代国人在家庭观念方面的转变。张晓刚自 1993 年起开始精心构思创作《大家庭》 系列油画,这组油画一面市便立刻引起了画坛的强烈关注。画面基本取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相馆纪念照,一家人或坐、或站立,高低错落地聚集在一起,集体目视镜头,表情严肃。
在这些关于家庭的画面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家庭中三个不同的身份,即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三个身份的连接代表着新社会中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同时也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家庭模式。在《大家庭》系列中出现的人物形象中,有父亲、母亲与孩子的组合,也有父亲一人与孩子的组合,更有子女组合。在其中我们发现了女孩身影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形象重回家庭的概念之中,甚至出现父亲独自与子女组合的形象(图6)。这代表了新的家庭观念中的多元组合倾向,母亲不再只是作为家庭中丈夫的依附者和孩子的养育者身份出现,她坐在父亲的身边,获得了与家庭中男性长辈相等的地位;父亲也更多地参与到与孩子、妻子中间。
这种家庭观念的转变,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男女长辈身份的僵化定势,为家庭的组合以及孩子的养育带来了更为多元化和包容的选择。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地位和经济实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这种提升在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随着时代观念的进一步变迁,如今社会中对于家庭的观念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父亲与母亲的角色或许不会再被男女性别所限制。而艺术家对于家庭关系的认知和观念也与张晓刚创作《大家庭》时的观念截然不同,创作的图像自然会彰显出独属于此的不同面貌。
参考文献:
[1]卫恒先.汉画像石交合图研究[J].中国美术,2019(03):70-77.
[2]陈维艳,刘忠国.中国传统婴戏图起源问题探究——由三国朱然墓《童子对棍图》谈起[J].美术大观,2020(01):96-97.
[3]陈维艳.由装饰图案到独立成画——传统婴戏图发展路径探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1(22):15-17+21.
[4]蒋鹏翔.阮刻毛诗注疏[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5][晋]袁宏. 后汉纪校注[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6]程郁.尚见女孩的时代——由婴戏图看宋元之间生育观念的变化[J].形象史学,2021(02):121-154.
作者简介:
康紫馨(1996—),女,河南淮阳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李明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