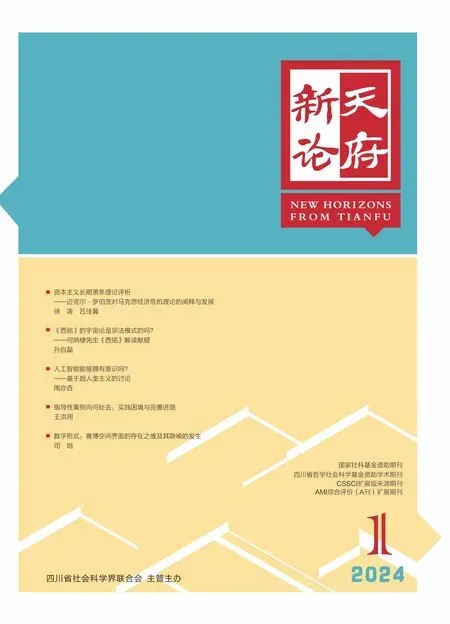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约翰·霍洛威激进批判理论阐释及反思
邝光耀
对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型后革命可能性问题的关注与回答,是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建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绕不开的核心议题。近年来,著名的“开放马克思主义者”、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教授约翰·霍洛威(1)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社会学教授,其著作《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无需夺权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被译为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因个人“三部曲”之终章《无望时代的希望》(2)John Holloway,Hope in Hopeless Time,London:Pluto Press,2022.一书的出版而再度受到国外左翼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在21世纪初,霍洛威就因《无需夺权改变世界》(3)John Holloway,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10.和《裂解资本主义》(4)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两部作品问世而名声大噪,此番更因其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革命主体理论而在左翼学者中激起讨论。左翼学术界中如齐泽克、卡利尼科斯和奈格里等人对其所主张“停止制造资本主义”观点的评价至今仍褒贬不一。霍洛威的激进批判主张缘起于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沉溺于资本逻辑及再生产体系的同一性批判,继而遗忘了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重要意义。阿多诺(又译为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强调“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5)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页。。霍洛威认为,这种非同一性打破了黑格尔同一性辩证法造成的综合性封闭趋势,也打破了所有承诺“幸福结局”的必然性结论。他通过吸收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对商品交换的同一性批判和反黑格尔综合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思想,指出,正是我们自身通过不断从事抽象劳动“制造”了资本主义。而由于“劳动和资本是同一方的”(6)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156.,因此我们不能把阶级斗争直接看作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与之相反,只有“我们”打破自身被定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身份,才能不断“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最终达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性、非同一性阶级革命。相较于当代激进左翼醉心于资本逻辑批判,霍洛威所提出的“停止制造资本主义” 并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叙事的激进主张,毫无疑问是一种难得的理论贡献。
一、从“封闭”到“开放”:黑格尔式辩证法的错误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出场
在霍洛威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但自第二国际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却把它歪曲、矮化成了有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黑格尔辩证法“正题—反题—综合”体系导致的斗争封闭和矛盾的同一化,致使各类革命党领导的斗争实践最终都被融入新的资本主义整合体系之中(如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地基的“先锋队”式阶级斗争理论使得各种各样的斗争都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概念,将“差异”单一化为“矛盾”,进而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综合要素”的否定扩大到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否定,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7)John Holloway,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10,p.44.。霍洛威认为,必须借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尤其是蕴藏其中的非同一性思想来弥补“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不足:需要拒绝的不是辩证法本身,而是对辩证法的综合性认识。换言之,应当坚持的是一种作为否定运动和非同一性的辩证法。霍洛威通过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他看来,非同一性意味着否定和创造,只有将其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革命”理论中,阶级斗争才能重新具有反抗和超越资本的潜力。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谱系中,阿多诺更多的是以文化批判理论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乃至音乐评论家的形象出现,其一生代表性论著的主题也主要集中在以上几个领域。但霍洛威认为阿多诺事实上从来没有轻视或放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遗产,对商品交换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是其走向非同一性主张的重要理论资源。早在1937年9月,阿多诺就告诉本雅明,“对《资本论》的系统研究”是他现在的首要任务之一。到了美国后,阿多诺仍然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至于阶级理论开始在他的思想中占据显著地位。正是经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等价交换原则的拜物教成因的揭示,阿多诺逐渐认识到,商品并不只是区分现代和前现代的社会关系差异性的哲学工具,事实上,普遍的商品世界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以界定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殊性的重要范畴之一,而且这一概念只适用于资本主义。
第一,阿多诺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等价交换形式的同一性原则走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关注。阿多诺指出,历史的发展本身被构造成一个包含因果交换的庞大过程,“似乎交换原则不仅是构成人类生活的无数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历史的宏观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禁欲精神必然同时伴随着索取行为”(8)Theodor Adorno,History and Freedo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93,p.50,p.51.。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揭示出启蒙理性和社会统治之间结构性关系的实质是同一性交换原则基础上的权力支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多诺认为“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9)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梁敬渠、蔡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历史永远不会摆脱神话的束缚。此外,阿多诺更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普遍的商品交换同一性特征。一方面,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的抽象同一性原则,即一种将社会无意识地综合为一个客观整体的中介原则。通过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它实际上把社会中所有参与生产关系的人都联系在一起。因此,阿多诺把交换的抽象视为一种先于个人的认知抽象的客观抽象。另一方面,在阿多诺看来,身处商品世界的主体不仅是被动的交换对象,而且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环节。真正抽象的商品交换形式不仅构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也影响了价值观念的思想生成形式。阿多诺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称为“同一性思维”,这种思维是指通过概念预言来表征现实的一种认知方式。阿多诺认为同一性思维是工具化和支配性的,因为它总是倾向于将“特殊性”简化为共性的存在。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通之处就在于,意识形态的因素隐含在交换关系之中——它是从人与商品之间的特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对这一交换过程的抽象形成了虚假的意识。虚假意识把单纯的概念假设反映为事物的本质。没有这一关键因素,普遍的交换机制就无法持存。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外在的虚假意识,而是维持整个机制的“真实意识”。
第二,阿多诺对“同一性”进行批判的目标是开显出等价交换原则掩盖的人类苦难和非同一性意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确保了交换原则的永恒同一性不断得到加强并继续在整个生产领域盛行,而生命过程本身在“同一性”的表现中显得“凝固”了。阿多诺在其《否定的辩证法》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整体“不仅仅是在冲突中生存,而是因为冲突而生存”(10)Theodor Adorno,History and Freedo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93,p.50,p.51.。这一辩证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一切个人生活都受到交换原则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利益竞争,使每个人都必须设法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产品。由于这种对抗性关系和利益冲突的存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实际上成功地维持了自身。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进行的使用价值生产,而是为了价值增殖进行的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第一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那些控制着生产资料的阶级获得利润,并且人的生命也只有经过这个服务于价值增殖的过程才能得到再生产。阿多诺指出,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利益冲突和阶级对立关系,因为“实际上生产是为了利润,人们从一开始就被计划为消费者”(11)Theodor Adorno,History and Freedo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93,p.50,p.51.。相应地,事物非同一性是指被压抑的事物与注定是同一性的普遍统治之间的对立。对阿多诺来说,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既无助于减轻非同一性的自由意识的丧失,也无法阻止同一性支配下主体对自由愿望的日益冷漠,即使是最自由的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表现也会阻碍这种自由意识的产生。霍洛威从阿多诺这里得到的启示是,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应当着眼于微观的、非主流的、个体的、身体的、部分非概念性的和未理论化的事物,着眼于非同一性事物所具有的客观真实价值及伦理和实践意义。
霍洛威引入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反对黑格尔的同一性辩证法,并不代表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辩证法因素,他所反对的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再度黑格尔化,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封闭体系所带来的对革命未来幸福结局的必然承诺。在他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辩证法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实际上却是实证主义的——最终变成了一种封闭性理论,成为苏联借以合法化国家机器的理论工具。这种封闭化的辩证法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化运动,并且重视实现肯定性的综合,即承诺矛盾终将得到积极解决。霍洛威的“开放马克思主义”(12)“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是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中形成较早、影响甚广的一派,其倡导建构一种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试图走出“封闭”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方式。其代表人物有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和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等人。立场展现了辩证法不是关于客观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而是专门关注人类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互动的理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成了霍洛威借以重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性的最佳理论资源。霍洛威指出,革命的希望就在于社会关系的非同一性“流动”,在于打破固定身份。霍洛威明确辩证法是否定的而不是综合的,是非同一性的而不是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正是“一致的非同一性”的辩证法,“它既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又是革命性的”(13)John Holloway,Fernando Matamoros and Sergio Tischler,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London:Pluto Press,2009,p.13,pp.15-16.,而要在危机中实现辩证法的革命性,前提是我们“要理解阶级斗争作为非同一性的运动”(14)John Holloway,Fernando Matamoros and Sergio Tischler,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London:Pluto Press,2009,p.13,pp.15-16.。
二、从“摧毁”资本主义到“停止制造”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重塑
霍洛威在2013年接受英国学者采访时,就曾透露其理论建构的下一步重心是“如何理解危机和革命之间的关系”(15)John Holloway,Simon Susen,“Change the World by Cracking Capitalism?A Critical Encounter between John Holloway and Simon Susen,”SSRN Electronic Journal,Vol.7,No.1,2013.。阶级斗争理论毫无疑问是联结其危机批判理论与非同一性革命方案之间最重要的“桥梁”。霍洛威在2019年出版的《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对自己危机批判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观念作出了系统的解释与说明。首先,由于阶级关系建立在剥削和对抗的基础之上,因此,任何阶级关系的结构体系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其次,要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就必须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解放劳动的“实践”——对抽象劳动的反抗是阶级斗争的中心;最后,阶级的概念给予了我们共产主义的希望,“因为它表明资本依赖于我们来生存,我们是唯一的主体。”(16)John Holloway,We Are the Crisis of Capital:A John Holloway Reader,Oakland:PM Press,2019,p.214.
(一)从危机到革命:自下而上“裂解”资本主义
第一,霍洛威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观与共产主义观均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的危机性基础之上。换言之,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试图从危机中寻求支持和信仰,并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并不孤单”(17)John Holloway,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10,p.109,p.109.。然而,对于“我们并不孤单”的理解有两种方式。一种理解方式是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必然表现,进而将物质利益、历史进步论、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等神化为无产阶级的“救星”,即认为危机必然催生革命,从而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但这种理解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将革命视为夺取权力而非反权力的手段,即“摧毁”资本主义并重建新的权力秩序。这极易导致革命胜利后不平等的支配权力关系再次重生。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危机视为我们反对资本的行动结果,即没有所谓的“客观矛盾”,只有我们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我们是唯一的创造者,唯一可能的救世主,也是唯一有罪的人”(18)John Holloway,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10,p.109,p.109.。因此,我们需要将革命视为反权力的手段,而非夺权的胜利。“开放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这种“停止制造资本主义”批判范式将危机看作我们自身力量的表现,而非资本主义矛盾的客观发展,以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
第二,霍洛威主张,革命主体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本质是拒绝接受资本逻辑的复制与再生产。“停止制造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凝聚力的断裂,更是其社会关系再生产整体性的破裂。这一论断揭示了“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骄傲”,暗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政治宣言。霍洛威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是,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在于建立“先锋队”式革命政党,期盼资本主义有朝一日由于危机自动崩溃,由革命党夺取国家权力、并打破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是不现实的,而应承认、创造、扩张、倍增并最终汇集所有反对资本逻辑的“裂缝”,不断放大所有反对资本逻辑的主体行动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持续“裂解资本主义”。基于此,革命主体要改变斗争方向:不应再把斗争看作反对既定统治制度的斗争。与之相反,应当把行动的主体理解为不服从资本逻辑和生产命令的革命主体,把“我们”作为攻击资本主义的对象以及实现共产主义的主体。“如果我们把资本及其存在形式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那么我们就把对抗而不是支配放在它的中心位置。”(19)John Holloway,We Are the Crisis of Capital:A John Holloway Reader,Oakland:PM Press,2019,p.20.资本逻辑绝不仅仅是支配的逻辑,“我们”作为革命主体对其本质的理解乃是对抗性。
总之,霍洛威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应该被简单化为经济危机,其危机的本质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崩溃,它本身是“我们力量的表现”,无产阶级应对危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以“行动”否定权力而非夺取权力。因此,一方面,霍洛威强调“我们制造了资本主义” “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霍洛威也认为只有“我们”能够“停止制造资本主义”。而“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统治普遍性的关注扭转到对危机来临时革命可能性的关注上来,进而将阶级斗争视作自下而上不断“裂解”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
(二)“我们”而非“他们”:以具体行动反对抽象劳动
霍洛威指出,必须始终牢记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他认为,劳动二重性理论实际上告诉我们主体行动的两个方面之间存在非同一性、不相宜性(unfit)和对抗性关系,即抽象劳动和具体行动之间存在持续发生、时刻进行着的对抗。因此,从危机到革命,重要的是要从我们的创造性行动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及打破危机的潜力,而不仅仅是从抽象劳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价值、货币、资本等)视角去理解资本如何滋生了对劳动的剥削,这是其“无需夺权改变世界”主张的核心论点。霍洛威强调,抽象劳动和具体行动之间对抗性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主体反抗抽象劳动的个体经验,以及主体对劳动形式和内容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在这种“对抗性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反对并超越资本主义抽象劳动的行动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个体反对资本逻辑、拒绝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共谋的日常行动和经验之中。正是在这种超越抽象劳动的行动中,有可能诞生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世界”。
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反对资本,更重要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抽象劳动。霍洛威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不应局限于工厂内传统的劳工斗争,革命主体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反对抽象劳动的斗争,是“恢复人类自身行动自决权的运动”(21)John Holloway,Grubacic Andrej,In,Against,and Beyond Capitalism,Oakland:PM Press,2016,p.34,p.46.。霍洛威的观点源于过去20年新社会斗争运动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形式出现的新变化。他指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革命斗争运动中,一种关于“使用价值政治学” (politics of use value)的理念开始盛行,即从实用性而不是盈利性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正确的观点应当是:“不,我们的力量在价值层面上是看不见的;我们的力量是在劳动层面上可见的,在抽象劳动的矛盾性层面上也是可见的。”(22)John Holloway,Grubacic Andrej,In,Against,and Beyond Capitalism,Oakland:PM Press,2016,p.34,p.46.霍洛威认为,“价值”并不是孤立、静止、不变的物,而是一场将我们推向参与某种行动的斗争;同样地,资本也不是物,它推动着每个个体作为行动者采取不同形式“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行动。他还指出,资本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主体的对抗性行动将推动着我们从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名词性理解”中解放出来,继而把身处其中的世界看作一个“动词”意义上的、不断发生和改变着的动态世界。一旦我们作为革命主体开始把世界“动词化”,我们就已经开拓了新的革命时刻与革命空间。
另一方面,霍洛威把反对抽象劳动的“行动”定义为“活的流动”(23)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255,p.116,p.117,p.9.(living flowing)的社会性行动。“活的流动”的行动没有明确的个体行为分界线,一个人的行动必然流入另一个人的行动中,没有其他人一起的行动是无法想象的。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中,劳动的抽象化将这种“活的流动”的部分集体行动转化为孤立行动,从而打破了行动的社会流动,使革命主体碎片化为孤立的个体,最后贴上不同的身份标签让“我们”陷入相互竞争、互相反对的境地。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为了不断实现商品交换,破坏了集体行动的社会合作系统,将其重建为个体抽象劳动的商品交换系统,进而缔造出生产这些商品的带有不同身份标签的个体。在霍洛威看来,个体的概念本身就是商品交换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出个体,还削弱了“我们”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限制了社会性行动的“活的流动”。社会性行动最终变成了一个静止不变且具有永恒性外观的名词:社会(society)。实际上,社会是由许多“支离破碎的个体”组成的整体,这些个体的身份标签都是有限的——仅仅是根据他们的抽象劳动而被定义的。
三、“尊严的抵抗政治学”:非夺权式裂解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
在重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危机与革命的关系后,霍洛威进一步提出问题:“在一个人们都只是其社会再生产功能化身的世界里,我们怎样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呢?如果我们都被资本主义产生的角色身份所束缚,我们怎样能打破由这些身份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24)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255,p.116,p.117,p.9.这一问题尤其关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工人直接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如何构成革命阶级并反过来成为推翻劳动抽象化的阶级?霍洛威认为唯一的方法是“质疑身份化的力量,尝试将身份的面具从佩戴者脸上撬开,看看面具背后是否有什么”(25)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255,p.116,p.117,p.9.。只有当无产阶级不仅作为自身而存在,而且与自身身份相对立,成功地以“行动”摆脱和超越了自己的身份面具,并与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存在的事实做斗争时,方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性的阶级。从“裂缝”形成的否定和“溢出”的不相宜去重新思考世界,方可揭示出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和弱点,这才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并超越危机的革命希望所在。
(一)裂缝(cracks)与溢出(overflows):危机带来革命的希望
如果把资本主义体系看作“一堵墙”(the wall),资本主义危机便是这堵墙上可能出现的“裂缝”(the cracks)。霍洛威在《裂解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当面对资本主义体系这堵“墙”时,不同人的选择亦各不相同。有些人选择拒绝正视现实,逃避且沉溺于资本所制造出的“迪斯尼幻境”,固守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有些人则谴责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残酷压迫,选择建立激进的政党组织,期待有一天这堵“墙”自动消失后迎来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霍洛威和其他“开放马克思主义者”则与上述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选择在这堵“墙”上寻找既有的“裂缝”,推动创造出新的“裂缝”,力图揭示并放大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否性矛盾和弱点。霍洛威认为,寻找并识别裂缝的活动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活动:通过寻找裂缝,推动主体不断认识资本主义表层坚硬“墙壁”背后的裂缝或断层,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中的裂解在此过程中相辅相成。寻找并打开墙壁裂缝的活动就是反对资本同一性和资本主义封闭体系的行动方式:通过对这些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抽象劳动所否认和禁锢的行为(done)的重新“开放”,批判并突破社会表层的资本逻辑,从人类行动(doing)的力量来重新理解社会和社会关系。“这是一种辩证法,但不是通过齐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综合体系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否定辩证法,一种不相宜的辩证法。”(26)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255,p.116,p.117,p.9.思考革命的希望不是寻找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来拯救我们,而是“寻找一种内在的否定,一种溢出自身而内在的否定性力量”(27)John Holloway,Hope in Hopeless Time,London:Pluto Press,2022,p.36.。
革命的希望何以可能是内在“溢出的”(overflows)。霍洛威援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掘墓人”的比喻力图证明这一点: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即资本主义制度既形塑了无产阶级,又造就了无产阶级反对并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一种存在于未被定义的无产阶级身上的内在否定力量。这是具体行动对抽象劳动的反抗和超越,对资本逻辑束缚的不相宜和打破,革命必须作为“动词”来消解其“名词”形式的限制。如果我们仍然将阶级视作从商品、价值、抽象劳动等范畴中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它必定与这些范畴一样继续以同一性的方式禁锢着我们。如果无产阶级依旧被理解为商品化的劳动力群体,或抽象劳动者(或雇佣劳动者)群体,那么它的确只是“资本的附属品”。霍洛威认为,“阶级”的本质是一个对我们进行身份定义和分类的形式化过程。然而,我们既存在于阶级之中,也存在于阶级之外——正如我们存在于商品世界之中,也可能存在于商品世界之外。资本主义对我们进行身份定义和分类的过程不是虚幻的而是非常真实的,正如它将我们的具体行动抽象为从属于资本主义整体的抽象劳动,以及将财富表现为商品堆积一样真实。革命希望的运动应当是一场反对抽象化、反对身份化和反对分类的运动。革命的希望首先在于将无产阶级视为反劳工主义和反阶级身份的,即视为格格不入的、溢出的、不受资本控制和征服的行动式个体。
(二)反资本主义的新语言:“尊严的抵抗政治学”
霍洛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行动以抽象劳动的方式存在,但两者的关系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和包容性关系。恰好相反,具体行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同一性、对立、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具体行动不是,也不可能完全从属于抽象劳动,它们之间“存在盈余、溢出和不同的推动方向”(29)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173.。抽象劳动的驱动力是金钱,即通过货币增殖来获得社会认可;具体行动的驱动力是行动的自我实现,即实现自主、自决。因此,不能把阶级斗争看作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因为劳动与资本是同一方的,抽象劳动生产资本。陷于抽象劳动拜物教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失败并不是彻底的失败,而是向更深层次的阶级斗争的转变。
霍洛威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墨西哥“萨帕塔起义”运动(30)“萨帕塔起义”(Zapatistas Movement):指从1994年起,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爆发的反新自由主义,并受到全球声援的原住民起义运动。“萨帕塔运动”被认为是第一场后现代意义上的自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霍洛威用以构建反资本主义革命策略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及其自治主义主张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哈特、奈格里和其他支持自治主义运动的学者们停留于理论层面寻找新的革命主体时,霍洛威坚持认为,新革命主体的可能性是由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土著农民缔造的,因为“萨帕塔主义者”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传统信条。无论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式夺权理念,还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主张,都不受他们的欢迎。事实上萨帕塔运动提出了一种“对话政治”的新原则:一种组织形式(军队组织)和“不服从运动”(无明确领导核心的组织)之间的张力。这种组织上的军事结构与土著社区的自治主义生活模式之间的差异对比尤其明显。萨帕塔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是一个在构成上几乎完全是土著人的运动,但我们不仅仅是一种土著人运动。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土著人的权利而斗争,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人类尊严而斗争的运动。”(31)John Holloway,Grubacic Andrej,In,Against,and Beyond Capitalism,Oakland:PM Press,2016,p.13.萨帕塔人至今仍居住在一块由他们自己开垦、完全自主治理的领土上。在恰帕斯州的萨帕蒂斯塔地区随意路过的某一块路标,上面甚至都会告诉你:“这里是人民统治,坏政府不要进来。”(32)John Holloway,Grubacic Andrej,In,Against,and Beyond Capitalism,Oakland:PM Press,2016,p.14.这便形成了一个空间“裂缝”——一种与国家权力统治逻辑完全不同的复杂社会组织形式。由此,霍洛威认为革命的作用不是用一个权力总体取代另一个权力总体。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打破资本权力的统治逻辑,在统治结构中制造裂缝。
如何将这些反资本主义的“裂缝”进一步扩大、倍增并融合?霍洛威判定,阶级斗争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因为劳动者仍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一个追求价值无限增殖的社会。我们的行动基础是不断与使人类行动服从于价值生产的要求所进行的斗争。阶级斗争虽然依旧是中心问题,但它已经发生变化,并在持续变化,再把它看作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已经远远不够了。霍洛威提出:“理解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对抗的重点不仅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而且在于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固有的和持续的对抗。”(33)John Holloway,Crack Capitalism,London:Pluto Press,2010,p.190.生活本身就是具体行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将具体行动(或具体劳动)视为抽象劳动的危机,就是将推动变革视为危机的核心。危机不是简单的崩溃,而是“潜在的突破”。霍洛威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裂缝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反资本主义的种种行动、空间和过程如同冬天湖水冰面上的一道道裂缝,当这些裂缝不断在冰面上产生并联结时,缝隙将越来越多并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冰面”轰然破碎。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危机视作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观念,使得主体革命时常同虚无缥缈的资本主义绝望时刻相联系。只有当我们将危机视为突破资本逻辑的空间与时刻,即视为主体反对并超越抽象劳动的行动时,我们才能走向新的世界。
据此,霍洛威提出,我们有必要学习“反资本主义的新语言”,即“尊严的抵抗政治学” (against politics of dignity)。阶级斗争的中心依然是矛盾,但绝不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是有尊严的行动与抽象劳动之间更深层次的(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冲突。在阶级斗争中,主体行动的力量是反同一性的:它抵制同一化的过程,无论是一个具有激进观点的小团体同一化,还是抽象劳动的总体同一化。拒绝同一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停留在特定的层面上。相反,非同一性意味着不断地推挤、不断地反对资本——反对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并挫败我们行动的所有同一化、僵化和拜物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体行动的阶级斗争给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其裂缝的移动,而不仅仅是群体自治的移动。因为体制的改变不能仅仅通过增加个体的叛乱来实现,而只能通过社会性行动的流动、主体行动的汇合,通过不断裂解资本主义而实现。例如,当我们面临气候变化和核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目前存在的全球性协调形式(无论是国际性组织还是区域性组织)均与资本追求利润的动机密切相关,几乎不可能产生解决全球性危机的任何希望。与此相反,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只能来自我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绝不会来自某个国家或某个世界机构,而只能来自对抽象劳动的拒绝、来自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责任担当。
四、结 语
从论证存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裂缝”,到提供以具体行动对抗抽象劳动的“尊严的抵抗政治学”革命方案,霍洛威所谓“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主张,都有效地拒绝了基于一般劳动解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主义立场。他有意识地将马克思在写作《巴黎手稿》时期所使用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概念和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具体劳动”概念关联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联合团结的“具体行动”反对抽象劳动统治,继而“裂解”资本主义的自治主义行动方案。其理论尝试既反对人本主义超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劳动的观点,也是对人为制造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认识论断裂”的纠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新特征、新趋势,以及反资本主义斗争运动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下,霍洛威仍然致力于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革命理论何以继续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由无数的反抗和逃逸构成的动态网络,社会发展是一个由资本主义支配到反资本主义逻辑的革命过程,社会的危机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体系性矛盾导致的。他主张通过主体行动的反抗和逃逸来实现社会革命和新世界的创造,从而实现危机到解放的转变。对于如何实现革命,他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但他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解答对于问题本身的探索,继续寻找前进的方向,进而寻求如何彻底摆脱资本主义这一条必然通向全球性人类灾难的道路。
一方面,这种理论尝试为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形态,以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逻辑问题提供了可供参鉴的理论资源。霍洛威基于反资本主义运动客观形势变化所提出的从“摧毁资本主义”到“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重要洞见,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即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更不可能“摧毁”资本,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透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进行当代审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霍洛威基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提出所谓以“具体行动”取代“抽象劳动”的尝试,没有真正理解、领会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劳动”这一范畴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是把劳动作为工具理性活动这一知性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劳动,而是从历史存在论的意义上把劳动“实践化”。所谓劳动的“实践化”,即马克思赋予劳动以建构社会关系的感性活动实质——实践化的劳动是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达致对过往一切旧哲学和理性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批判,正在于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化了的劳动作为其立论的根基和出发点。劳动作为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乃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增强”(35)夏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新探》,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页。。生产力变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物质财富的丰富和增长,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的是实现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识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劳动出发,揭示了人的劳动不仅生产出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物质财富,还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由于忽略了劳动“实践化”的存在论意义,因而,霍洛威在其斗争策略的建构中,严重地消解乃至“遗忘”了革命的现实物质基础以及斗争的首要目标——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的当代启示恰恰在于:国家必然是“阶级国家”,而“阶级”是一个历史概念,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是“阶级消亡”而非“阶级平等”。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