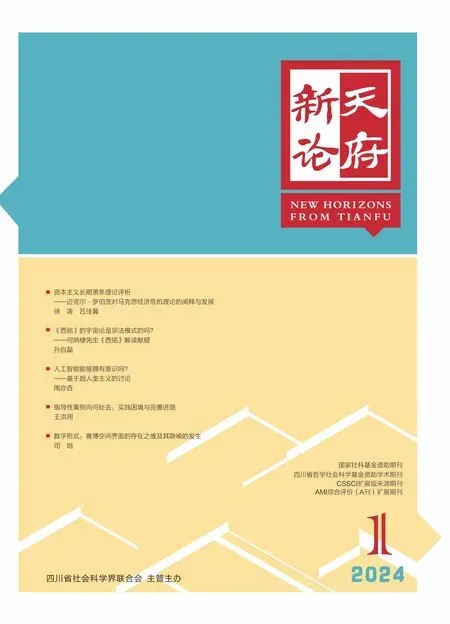数字形式:赛博空间界面的存在之维及其隐喻的发生
司 培
赛博空间是一个计算机网络与虚拟现实相融合的信息化与数字化世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界面,也多在赛博空间语境中进行。界面英译为interface。其中,inter意为相互,face则为脸或物体表面。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界面被解释为“物体与物体间的接触面”(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83页。。由此看来,界面是一个临界的表面,它蕴含了一种交互式的关系。在赛博空间中,界面的这种交互一般表现为信息流之间的交互。迈克尔·海姆就将界面定义为“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交汇之处”(2)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8页,第80页。。他认为,界面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和显示屏”;“二是指通过显示屏与数据相连的人的活动”。(3)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8页,第80页。这表明了界面具有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特质,也就是说它既可以以屏幕的物质性方式呈现出来,同时还能够在VR、AR等系统中作为数字化的虚拟形式存在;这还意味着界面是一个信息与信息以及信息与人的连接与交互之所。
马诺维奇就曾直接将界面称为“交互界面”。他对“人-计算机-文化交互界面”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这是计算机呈现文化数据的方式,也是计算机允许用户用文化数据进行互动的方式”(4)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1页。。这种观点直接指明了界面以数字信息的流动完成其“跨界”交互。这一信息交互,实质上是在一个数字形式的表面中完成的。波斯特与基特勒等学者就对界面之“面”作出了解释。波斯特直接指出“新技术安装了‘界面’,即面面之间的‘面’”(5)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基特勒认为,“信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体差别”,“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界面”。(6)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按照基特勒的观点,数字形式统一了界面中的诸种媒介,并将其与信息共同融合为一种“表面效果”。
也就是说,界面不仅显示信息世界,同时也囊括信息世界。它既是一个连接媒介或者一种形式,同时还压缩着内容与信息;不仅能以平面的形态呈现,同时还具有一个开阔的内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界面可以被认为是数字时代信息与意义呈现的重要形式。它在质料、时间、空间等存在维度上具有与传统媒介迥然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它对其所显现世界的构建逻辑,并促发了一种由技术语言构筑的文化隐喻,体现出信息技术时代的独特文化表征形式。
一、质料之维:界面的半透明化显现方式
界面的质料即它的质地与用料,亦是令其显现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是“事物由所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的那东西”(7)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0页,第49页。,它是一种显现方式,与事物的“聚形”和“终态”先行关联(8)李章印:《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重新解读》,《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亚氏还指出,“在技术产物里,人以功能为目的制作质料”(9)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0页,第49页。。也就是说,质料关涉物在生成时的功能性倾向影响其存在的性质。“从物质意义上来讲,界面实质上是一种显示屏。”(10)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6页。屏幕交互界面是最为普遍的界面显现方式,一般而言,它表现为一个矩形的平面,其表面材质往往是经由特殊处理过的玻璃。玻璃这种材料原本是用来隔风透光的,尤其是透明玻璃,光可以从这一介质中自由通过,将其在物理上所阻隔的世界放入人的视觉系统之内。玻璃也由之呈现出一个在它之外的世界。但屏幕上的玻璃并非完全透明,它不呈现或者说不照搬一个现实存在的世界。屏幕的表面是一个具有显示特质的窗口。它的内部则是诸如控制板、背光灯板、液晶层等物理材料的技术装置的压缩。它的显示原理是基于技术对光的控制,其所呈现的乃是一个经由技术再处理的世界,是一种数字图景。在这种技术组装中,屏幕更新了人对世界的表现方式,以其具有显示功能之表面与深邃的数字技术世界共同纠缠出了一个半透明之域。
一方面,从屏幕交互界面的世界呈现方式或者说构造原理上来讲,它是不透明的,它以物理性的表面与复杂的技术原理创造了一个具备一定隔绝性的空间。一直以来,人类都在试图以某种物质性的表面来呈现或者容纳一个世界。譬如书法或绘画通常就是借助某个表面来展开一个世界。当然,在民间艺术中也有一种与屏幕极为相似的表面,那就是皮影人物前的那一层幕布。如果说皮影前的矩形幕布可以被视作闪烁的屏幕,那么皮影背后活动的皮质人偶就有些类似于屏幕所呈现的可视化世界。不过,皮影幕布后的人偶是由人的肢体活动所控制的,其在运动上基本是可见的,作为表面的幕布只是依靠光源将人物的剪影投射出来,并不对其背后之物进行其他复杂的加工。这实质上是一种十分传统的世界表征方式,物质性的表面在此担任的主要是一个传递的角色,它将自己背后的那个世界“递”给了观者,所以无论从运作原理或者说运动方式来讲皆是近乎透明的。屏幕则与之十分不同,其在质料的构造上具有深度的不可见性,并不面向一般观者敞开。我们不能像观察皮影人物的剪影那样去观察屏幕图像的生成过程。屏幕的内在乃是一个幽深的数字技术宇宙,它囊括了物理现实与数字虚拟这两重物的存在维度,是一种具有复杂性与多维性的介质。故而屏幕不会直接呈现其背后的世界,它还需依照技术逻辑对其所要表现的世界进行转化,这一转化的过程通常是不透明的。也就是说,屏幕在表现世界时具有一定的隔绝特性。按照波斯特的观点来讲,“界面介于人类与机器之间,是一种膜,使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相连”(11)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第62页。。作为“膜”而存在的屏幕首先是一个物理性屏障,其以自身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和致密的技术系统把现实存在的物阻隔在外,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封闭性质的系统。这也就隐藏了屏幕在表现世界时的技术加工手法,从而使其以不透明的方式来呈现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屏幕与现实世界之间完全分离,屏幕的隔绝性与不透明性实质上是在为虚拟的世界设立出存在的位置,它还有另一重可见的物质属性,这一物性促成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
另一方面,从屏幕交互界面的显示与连接层面上来讲,界面又具备一定的透明性,颇有些类似于一个将人接入数字世界的通道。马诺维奇曾梳理出了一个屏幕的谱系,他认为屏幕的发展经历了经典屏幕、动态屏幕与实时屏幕三个阶段。经典屏幕是一个“矩形的平面,供人们从正面观看”(12)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5页,第96页,第101页。,由画框圈住的绘画作品便是此中典型;动态屏幕“显示的图像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电影、电视录像的屏幕(银幕)皆是如此。在这两种屏幕中,“单一的图像充满了画面”,观众需要“聚焦于窗口内的再现性场景,同时忽略窗口之外的现实空间”。(13)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5页,第96页,第101页。在这种观看关系中,屏幕通常只是呈现“现实图像的一种手段”(14)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5页,第96页,第101页。,它并不直接作用于现实,它存在的一般性使命是将人带入由屏幕所显现的世界之中。因此,从参与程度上来讲,它是完全不透明的,人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被加工好的世界。在实时屏幕中,“图像可以持续性地进行实时更新”,它甚至可以及时地与观者发生交互,信息在屏幕与其使用者之间流动与更替。这种交互性的实时屏幕也就是早期的计算机屏幕,亦即赛博空间的屏幕交互界面。界面于此承担了一个显示与连接的角色,它不仅呈现了一个由数字代码编织的虚拟世界,同时还有一个面向人所活动的世界并与之发生交互的平面。屏幕交互界面在显示层面上面向它的观者敞开,并且能够将观者活动纳入其内容创作体系之中,对信息进行实时更新与反馈。在波斯特看来,“因特网的界面必须显示出某种程度的‘透明度’,也就是说要显示为不是一种界面,不是一种介于两个相异生物之间的东西,而同时还要显得令人迷恋,界面在宣示其新异性的同时,还要鼓励人们去探索机器世界的差异性”(15)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第62页。。就此而言,屏幕交互界面将观者所处的世界与数字化的世界联系了起来,制造了人机之间信息联动的场域,促使虚拟数字世界在显示层面显现出一定的透明性。
马诺维奇总结的这个屏幕的谱系,显现了屏幕在显示与连接层面不断透明化的趋势。然而,与这种透明化相伴随的却是屏幕在技术构造上的越发不透明。马氏所提到的经典屏幕实质上是一种在构造上高度可见的屏幕,但到了实时屏幕这里,一切复杂的技术都被压缩为一个数字化的平面,洞悉其背后的技术构造变得极为困难。屏幕可见的现实世界背后所掩盖的其实是一个幽深的数字技术宇宙。齐泽克曾经指出过这种矛盾,他认为界面的屏幕“掩盖了机器的运作”,“屏幕后面的数码机械蜕变为彻底难以穿透,甚至无法看见之物”,“用户放弃了掌握计算机运作的努力”,“在与赛博空间的交流中,他被抛进一个非透明的环境”(16)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正是由于屏幕交互界面这种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性,最终催生出一个半透明化的数字虚拟世界。
这意味着界面的质料属性对其所显现的世界造成了影响。在这里,由屏幕所显现的这个数字虚拟世界既不展示它背后的机器运作系统,也不还原界面所关联的现实世界。占据人视野的实质上是屏幕本身,我们的关注焦点被放置在了一个闪烁着数字信号的平面上,对“屏幕后面”的探求也因此而显得毫无意义,人甚至于要“根据事物的界面价值理解它们”(17)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也就是说,由于屏幕交互界面的不透明性,它所显现的数字虚拟世界只能以颇为断裂的方式被悬置在一个表面上,我们既难以了解这背后的技术运作逻辑,也无法直接在屏幕上触摸实在的世界。这导致数字虚拟世界从界面这里开始,就与我们产生了一定距离,并不面向人完全敞开。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数字虚拟世界完全透明化,它就摒弃了自身,成为一块任由光所穿透的透明玻璃,人们会透过玻璃看向它背后的实景而非玻璃本身。也正是因为屏幕以一道玻璃似的屏障将物理意义上存在的世界拦截在外,才划定出了赛博空间的入口位置,为虚拟带来了一个区隔于物理现实的繁衍之地。所以数字虚拟世界的构造逻辑是一种与物理现实的世界产生间距的逻辑,而非促使实在的世界面向我们完全透明化的逻辑,即便屏幕消失,界面完全以虚拟化形态存在,该逻辑依然有可能延续。故而对于借由界面进入赛博空间的参与者而言,数字虚拟世界实质上是半透明化的。这种半透明化意味着它与物理现实之间既具联系又有隔阂的暧昧关系。很显然,数字虚拟世界并非对现实的完全复刻,在界面这个中间域里,它获得了将现实进行再表现的空间。一个象征形式的世界也于人们眼前逐步展开,无尽的想象与隐喻亦由之衍生。
二、空间之维:界面的均质化与离散化状态
空间是界面存在的基本维度之一。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工具,是一种中间物”。(1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24页。界面也具有这样的“中间物”特质,它不仅仅是一个显现数字虚拟世界的表面,同时还“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的边界区域”(19)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从界面的外延来讲,它占据着空间,并以物理形态包围出了一个颇具稳定性的信息交往场域。从界面的内涵来讲,它包含着空间,在虚拟化的数字世界中可以有无数个既分散又叠合的空间。所以界面在空间维度上基本处于一种均质与离散相结合的状态,既具同一性与整体性,也兼有裂变的可能。
从均质化的状态来讲,界面保留了它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将处在多个现实空间的信息流统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之内。在传统的物理认知中,空间往往被视作一个“事件发生在其中的固定舞台”(20)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 (第3版),徐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34页。。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空间被认为像容器之类的东西,因为容器是可移动的空间,而不是内容物的部分或状况”(2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6页。。牛顿也将空间看作“它们自己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处所”,所有事物置于空间之中,方能得以“排出位置”。(22)伊萨克·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王克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也可以认为界面在空间维度上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它既通过事物而显现其存在,也是一个衡量事物的尺度。
就具体的角度而言,界面以物理实体的空间形态为虚拟数字世界提供一个相对封闭与稳定的处所。无论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手机屏幕还是电脑屏幕,都可以被视为“容器”意义上的空间,因为它能够将无数流动的信息装载进一个具有物理边界与明确位置的封闭空间之内,从而确保了界面在空间构造上的同一性。就抽象角度而言,界面以一套统一的逻辑组织了多个空间,具备一个具有整一性的空间规则系统。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空间的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2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页。。但是“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 (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了出来”,对空间的描述不必再受场所之限,并且“不同的空间单元相互替换也成为可能”。(2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7页,第17页。界面实质上就构建了一个跨越不同地点的组合型空间。在界面所划定的范围内,多个与地点脱离了的空间按照统一的逻辑被组合为一个彼此相互联动的场域。这些空间在界面中完成了两重蜕变:第一,它们从原本地点与情境中分离出来,演化为信息与数字形式;第二,它们被界面以数字世界的规则统合为一个具有整一性的空间。为了解释这种空间的“缺场”与再组合,吉登斯使用了世界地图作为例证。他认为地图使得“空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点和地区”(2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7页,第17页。。在一定程度上,界面空间便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与地图相类似的抽象空间。正如地图以固定的方位以及比例尺等规则将多个空间在形式上统一化为一般,界面也依靠相应的操作与显示系统令无数零散的空间在赛博空间的技术逻辑中运行。界面之所以能够将处在不同地域的空间显现在同一平面上,正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均质化特质的衡量空间而存在。
从离散化的状态来讲,界面在空间维度上又显现出鲜明的裂变特质。界面所内含的是一个流动的数字世界,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变化性。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固定的“舞台”,同时还可以被视作一个关系与概念系统,在内在的空间关系层面上,呈现出分裂与变化的特质。列斐伏尔就曾指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26)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布尔迪厄则将空间直接视为一个弥漫着“关系网络”(27)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的场域。也就是说,空间还意味着一种关系上的相互作用,在界面中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信息关系。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空间存在着“既是相连接的,又是相分离的,既是被分解了的,又是维持着原状”(2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页。的状态。由此看来,当我们从关系视野考虑界面存在的空间维度之时,所要关注的还有它在统一之外的分裂性与变化性。
界面的内在空间通常是要通过分裂进行延展的,我们的手机与电脑桌面上的多个图标,以及在网页上打开的多个窗口就是这一分裂性延展的直接例证。在这些窗口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个数字化的空间,所以说正是界面在空间上这种离散的状态才打开了通往数字世界内部多元空间的通道。手机和电脑界面存在的重要意义也是要将使用者引入多个图标之后的世界,否则它可能就只是一张平面化与抽象化的地图,以纯粹符号的形式而存在。赛博空间界面的独特品质或许也正在于它于信息的流动与分裂中变化出了多个数字空间,囊括了气象万千的世界。并且这些分裂出的空间并不像文学或艺术作品中那样需要依赖阅读与想象来激活,而是在与使用者的交互中以数字化的表象系统来呈现,开拓出如神话般变幻莫测的多重显示空间。界面上的每一个图标都如同一个数字化表象空间的入口,由于这些图标通常是随机组合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连续的,它们往往具有不同的功能偏向与空间表现形式,以离散的状态构筑了界面在内在空间分裂上的丰富性与变化性。
三、时间之维:界面的“无时”与瞬时性
作为一个虚拟化的数字与信息流动空间,界面在时间维度上显现出与现实物理世界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现代生活中所使用的是一种“单向线性时间”(29)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概念,典型如钟表时间就属于一种抽象的线性时间,它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刻度不断地向前推移,对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流逝情况加以标记。在这一参照体系中,时间似乎不仅具有方向,还具有顺序,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线的串联之下逐步发生。经典物理学就认为“事物置于时间中以排出顺序”(30)伊萨克·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王克迪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时间于此也更像是“一个先定的而且不再更动的框架”(3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这种时间的顺序显然在界面中被打破了,卡斯特就曾指出“在网络社会里,这种线性、不可逆、可以度量、可以预测的时间正遭到挫折”(3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第564页,第563页,第530页,第543页。。界面在时间之维上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多样化状态。在其所显现的虚拟数字世界里,时间似乎并不完全依照单向线性流逝,不同的时序之间甚至能够发生并置与组合。现实世界的时间在这里遭到了数字信息系统的重构,一个流动的“无时”之境逐步展开,瞬时性的时之叠套与拼装构筑了界面的基本时间特质。
“无时”亦即“无时间之时间”,这一理论概念来自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看来,“无时间之时间”通常产生于“信息化范式和网络社会”,“在该脉络里运作之现象的序列秩序发生系统性扰乱之时”,这种序列的消除创造了“未分化的时间”,“而这形同永恒”。(3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第564页,第563页,第530页,第543页。未分化的时间实质上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混沌,永恒则进一步指出了时间的凝固,时间在此处于一种未经处理的待开发状态。在界面中,由于稳固序列的打破,时间成了可以操纵的对象。卡斯特就明确提到,“对时间的操纵乃是新文化表现里一再复现的主题”(3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第564页,第563页,第530页,第543页。。由此看来,赛博空间界面的“无时间之时间”至少具有两重意涵。
第一,它意味着“时间序列与时间本身的消失”(3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第564页,第563页,第530页,第543页。。这种消失造成了界面在时间维度上的两种断裂:一是与具有参照地位的线性时间的断裂;二是“与社会之节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观念”(3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0页,第564页,第563页,第530页,第543页。的断裂。经由这两种断裂,界面制造了一个时间上的虚空或者说永恒之地,并将自身封存为一个时间装置与存储器。在这个世界里,流逝的时间被凝固为一种永恒发生的状态。一切已发生的事件一旦上传到界面系统就有可能被反复地调取与观看,它们不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在时间的链条上继替发生,而是被摒弃了时间,定格为一个数字化标本。
第二,它意味着时间的多维并置。在界面未分化的时间状态中,时间有可能是混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有关时间的再创造,从而促成了多维时间的生发。界面所显示的数字虚拟世界是一个时间能够被调配的世界,各种时态的时间有可能在多个维度上并置,呈现出实时、延时与共时共在的状况。我们在界面中也往往能将多个时序的时间于同一语境中进行调用,譬如分屏播放的模式其实就是界面多种时间序列并置的典型代表。再如我们与界面交互时所产生的线上与线下的时间差也是一例。不仅如此,界面甚至还可以借由影像或游戏构造出一个虚拟化的多维时间世界,充分延展时间的存在维度。
与界面这种“无时间之时间”相伴随的,是一种瞬时性的时间。“现在”是瞬时性时间中的普遍性存在时刻。一般而言,我们认为现在与过去和未来之间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延续性关系。胡塞尔就曾以意识的统一性建构了一种连续性时间,他提出了“滞留-原印象-前摄”的时间结构。“原印象”在狭义上指当下、现在与此刻,它区分了过去和将来。“滞留”是流入过去的现在,它如同逐渐变弱的声音一般向消逝的方向延展。(37)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2页。“前摄”则是现在对未来的敞开与预期,“它是可确定的将来意象”(38)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7—1918)》,肖德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页。。在这一结构中,过去与未来都被统摄于现在之中,形成了一种意识时间的连续性。但是利奥塔基于电子信息世界的特质,对这一时间结构提出了反驳。他认为,电子信息世界中的“现在”摒弃了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绽出的瞬间。在他看来,在信息化语境中时间意识的连续性是很难达成的,因为它“无法揽括各种时刻,而且每次必然将这些时刻现时化”(39)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夏小燕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7页。。他甚至据此指出:
“当下不是可把握的:它还没有或者它已经不在场了。要把握呈现本身并且呈现它,总是要么太早,要么太晚。”(40)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夏小燕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6页。所以,界面中的“现在”是一个充满着偶在性与不确定性的瞬间,正是通过这些流动着的“现在”,界面的瞬时性特质才得以显现。
这种瞬时性往往凝结于时间的交织与叠套之中。界面不仅是一个信息显示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数字存储系统,可以被视作人类记忆的装载装置,界面的瞬时性凝结也往往发生于此类数字记忆的交织之中、在其综合之时。这些流动中的过往种种信息,充斥着时间的碎片,有着对混沌记忆的重组,与意识流小说所表现的情形颇有些相似。乔治·普莱曾在对普鲁斯特的作品进行考察时指出:“人的存在并不是由他所经历的时日那表面的连续性构成的;它是由一定数量的经历、在远距离中互相体验的经历、被遗忘的大碎片分割的经历构成的,不过这些经历间却十分相似,因此组成了重复出现的主题。”(41)乔治·普莱:《普鲁斯特的空间》,张新木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而“重复并不是同样完全相同事物的回归,并不是上述相同内容的回归”,“乃是过去事物之可能性的回归”。(42)吉奥乔·阿甘本:《宁芙》,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也就是说,界面中那些被认为是不断复现的碎片化记忆与时间,也有可能在交织与叠套中绽发出新的可能性。譬如视频剪辑活动就能够打破既定的时间线索,对多个时间线上或重复的或断离的视频源进行编辑与组合,进而凝结出一个新的“现在”,构造出一种新的充满隐喻特质的时间文化表现方式。
四、界面的时空压缩及其隐喻之基的构建
界面,从其显现形式来讲,可以被看作一个压缩的平面。这种压缩是信息急速流动社会中的一种典型性文化表现形式。在技术理性的推促下,物理上的时空于界面中坍缩为一种数字形式,并通过闪烁的符码来呈现其自身。界面也由之成为一个隐喻系统,“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4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第18页。,在数字化的世界中重新描述现实。波兹曼认为,“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4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第18页。。从这一点来讲,界面隐喻意味着一种赛博空间数字文化表征方式的生成。
时空压缩是界面的世界表现方式。按照哈维的观点,时空压缩可以被概括为“地理现实无可避免地趋向融合与混乱,一切地方都可以互相交换,可见的(静态)参照点消失不见,成为恒常变换的表面影像”(45)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1页。。由此看来,界面的时空压缩主要具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它意味着物理与现实意义上时空的收缩,以及信息世界中时空的挤压与高度浓缩。维利里奥就曾明确指出,“运输工具和各种推进载体的发展本身引起了世界和我们的直接环境的一个觉察不到的大地收缩”(46)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第35页。,带来了一个“全世界都在远程在场的社会”(47)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第35页。,时空逐渐从物理环境中抽离出来,表现在界面中。哈维也曾援引麦克卢汉有关“地球村”的论述,对这种由信息高速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压缩现象作出解释。他认为,在远程通信的影响下,时空逐渐收缩成为一个“地球村”。界面就是这种物理意义上时空收缩的产物,它所表征的是一个被压缩的世界。从空间维度来讲,界面的均质化特质正是为了将收缩后的物理时空在统一的技术逻辑下进行重组而产生的。从时间维度来讲,界面的“无时”之特性则为这种物理性时空在信息世界收缩之后的再构提供了条件。也正是通过对现实的物理世界的信息化压缩,界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意义集聚的隐喻系统。
第二,它意味着界面时空的混融、拼贴乃至凝结。哈维认为,时空压缩的文化表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透视与叙事的连贯性”,导致“非常不同的世界的空间相互向对方倒塌”,“全世界一切不同的空间都在一夜之间集中为电视屏幕上的各种形象的拼贴”。(48)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78页。他甚至以立体主义的艺术作品为例来形容这种时空的混融与拼贴。这进一步证明了,在界面时空的压缩、扭曲与重组中,一个新的隐喻系统将有可能被创造出来。此外,哈维与维利里奥等人也十分关注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加速,因为时空压缩中的混融与拼贴往往是在高速的流动中发生的。由加速所带来的时空内聚促成了界面内多维时空的坍塌与凝结,从而于瞬时中形成了一幕幕“表面影像”。
在时空压缩的作用下,界面成了一个形式化的表面。维利里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电光学的和听觉的新环境的速度变成了最后的真空,这个真空不再依赖于地点间的、事物间的间隔,也就是世界的伸展本身,而是依赖于一种对遥远表象即时传播的界面。”(49)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对物理时空的抽离与数字时空的压缩,促使界面成为一个诸多表象的呈现之所,发挥出意义关联的功能,促发一种新的世界隐喻。进一步而言,是界面的时空压缩构筑了其隐喻之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时空压缩带来一种对世界的新的表现形式,促发了一种由技术语言构筑的隐喻。由于原本处于具体物理场所之中的时空被投射到界面,时空的显现方式发生了转化,它从现实的语境进入数字技术的语境,界面承担起了重构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关联之责,隐喻就是界面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在界面时空压缩的作用下,世界浓缩为一个数字化的表面,充斥其中的流动符号为隐喻的生长创造了条件。由于时空压缩只是将时空的表象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而非直接传递时空本身,所以它造成了界面与现实时空之间的某种断离。这种断离为界面虚拟时空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一个数字形式与符码表意世界的生成,界面隐喻的世界表征逻辑也由之显现。
五、界面隐喻的发生逻辑及文化意涵
界面隐喻是数字世界的文化表征方式,是一种由技术语言构筑的修辞格,蕴含了新技术语境中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表现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中,隐喻被认为是“以一事物的名称指称另一事物”。利科将之解释为“名词的转换”(50)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6页。。这种观点表明隐喻是一种词语之间替换的现象,它牵涉到两个不同的事物。界面的隐喻也是基于一种物与物之间的转换而发生的,作为一个信息交汇的中间域,界面本身就承担着对物的转化功能,是它将现实意义上的物转化为数字虚拟物,这种转化同时也包含了信息与意义的传递。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等人认为:“隐喻存在很多可能的身体和社会基础”,“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51)乔治·莱考夫、马克· 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第3页。也就是说,隐喻不单单是一个词与词或者物与物转化的管道,就像界面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传递媒介,它同时也是一种意义的生产方式。从隐喻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出发,莱考夫还指出了“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事物”(52)乔治·莱考夫、马克· 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第3页。。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5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页。有所不同,虽然都牵涉到两个事物,但是莱考夫想要着重强调的是隐喻中蕴含着人的感知与精神系统。这就与界面隐喻的逻辑颇有些相似,因为我们也会借由界面所呈现的这个数字虚拟世界来感知和体验一个遥在的现实世界。所以界面的隐喻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表现形式的转化,它还牵涉到一种文化意义生产方式的转化。界面隐喻的生成及其文化生产往往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以数字形式实现对现实世界之物的替换,将虚拟的世界与物理上实存的世界共同关联于界面符号系统之中。隐喻不仅是指词语之间的替代现象,同时也涉及事物或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要促使界面的隐喻发生,不仅需要实现一种事物或概念之间的替换,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种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映射关系。这种隐喻方式与符号学家皮尔斯所提出的符号“三元组合”具有相当的吻合性。按照皮尔斯的观点,符号由三种元素即Sign、Object和Interpretant构成。国内较早讨论相关理论的学者将之译为“符号媒介”、 “指称对象”和“符号意义”。(54)丁尔苏:《论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Charles Sanders Peirce,中文又常译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指称对象”通过“符号媒介”来显现,这一显现过程蕴含了与之相关的解释项,也就是“符号意义”。
如果我们依照这一符号学视域来考察界面隐喻的生成逻辑,就会发现在界面隐喻的发生之初,存在两重基本关系:第一是作为“符号媒介”的界面与其所要指称的对象——物理现实之间的关系。由于界面是一个由数字代码所构筑的世界,它在显现现实的过程中也采用代码的语言,所以这一显现过程在意义上讲几乎是空洞的,其意义的生产主要发生在第二重关系中。这也就是被数字形式替换了的界面指称对象与其关联着的现实意义以及促生这一意义的文化思维之间的关系。这两重关系并非割裂,而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完整意涵的隐喻符号系统,进而促发了界面的隐喻。
其次,在实现对物理现实的数字形式替换与符号编码之后,以技术语言对新的符号进行再组装,开拓出更为多元的意义空间。亚里士多德曾将谜语与隐喻进行类比。他认为,谜语的本质是“把词按离奇的搭配连接起来,使其得以表示它的实际所指”,“一般词类的连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用隐喻词却可能做到这一点”。(55)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6页。也就是说,隐喻词的搭配可以造成源始的单向度意义的扭曲,构造复杂的多义性空间。从这一点来讲,界面也需要经历这一重组装,才能促发更具多义性的隐喻空间。如果界面仅仅是进行以数字形式替换物理性现实这一步骤,那么它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对现实的显示系统,机械地将远距离的时空景象投射出来。然而,界面所做的不止于此,它还创造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系统,并以虚拟现实编织了新的意义世界。
抽象概念系统的典型性表现是时空压缩之后的界面窗口图标,它制造了一种概念的隐喻。按照莱考夫的观点,“隐喻建构了我们日常的概念系统”(56)乔治·莱考夫、马克· 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何文忠译,2015年,第57页。,这是一种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界面的隐喻实质上也是在制造一种概念之间的意义关联。所以它把抽象了的物理性现实在数字系统中进行了重组并构造出了新的意义生产逻辑。譬如我们在网页上所见的按照一定类目排列的图形符号,就是由一个信息高度浓缩的概念系统所组成,并且它们在同一页面的语境下生发出了一种新的意义关联。
除了以抽象的概念逻辑对现实进行隐喻,界面还可以在象征性的数字表象系统编织中创造生动可视的虚拟形象,实现对现实的隐喻。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世界被再度组织并还原成数字化形象,这些具体的形象通常不是对物理性现实的1∶1复制,而是对现实概念要素重新编织后的影像化再造。这是一种类神话叙事的数字虚拟化虚构,一般性的符号系统映射关系在这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界面将多元符号进行拆解与拼贴式的再构,为其连接了一个新的意指世界。如同神话的时空重组与故事的离奇设定一般,界面也能够借由时空压缩与影像化的拼贴再构出一个迥异于现实,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技术神话世界。
最后,在交互中实现对界面隐喻系统的延展与文化意义再生产。在隐喻研究的诸多理论中,还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隐喻观”。在这一观点中,隐喻被认为是“内容拓展”,它由以下成分构成:“(1)一个首要的主题P;(2)一个从属的主题S;(3)一组与S相关的含义I;(4)依据我们通过S透镜观察P时,P所要求的一组属性。”(57)迈克尔·布雷德:《科学中的模型与隐喻:隐喻性的转向》,王善博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譬如“人(P)是狼(S)”这一隐喻,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或类比,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的新视野。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意识到隐喻中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意义生产的促发作用。在界面中,尽管虚拟的数字世界替换了物理上实在的现实世界,却并不意味着这二者之间彻底地断绝了关系。相反,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交互对界面隐喻的延展具有重要作用,界面的意义需要在交互中方能实现持续性的再生产。此时的界面更像是一个意义的触发域,我们通过敲击键盘、触摸屏幕与之实现最基本的互动,从而将现实卷入到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之中,不断延展虚拟的意涵,促发其意义的生长,构筑出虚实相生的文化表征形式。
六、结语:界面与数字时代的文化表征形式
界面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既关联现实又超出现实的数字文化空间,它提供了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表现逻辑。从质料层面来讲,它以半透明化的质地确定了数字世界的入口,并为虚拟与想象留下了余地。从空间层面来讲,它既以统一的逻辑将跨越了诸多地点的空间纳入其中,又以离散的逻辑创造了数字世界的空间分裂,构筑了极具变化性的界面空间系统。从时间层面来讲,界面所创造的是一种“无时间之时间”,与传统的线性时间之间产生了断裂,促进了多维时间的衍生,瞬时性的凝结成为混沌与流动时间中的常态,从而促发时空的坍缩。界面成了一个信息浓缩的表面,隐喻成了它关联物理性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界面隐喻的发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正在以数字形式显现其自身,它诞生出了一种由数字技术语言构筑的世界表征逻辑与文化生产方式,一种能够生产幻象的文化表现方式,将人类主体置入了更为复杂的存在维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