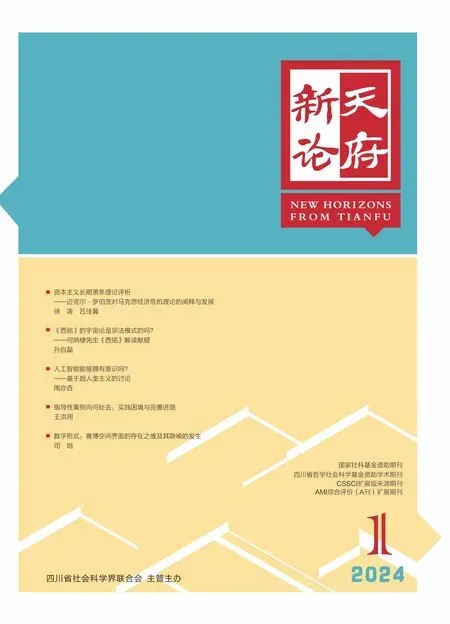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解释
涂 藤
一、问题之所在
没有人会否认,著作权的历史是“一部扩张史”(1)易健雄:《技术发展与版权扩张》,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直至近年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广播权定义的重构、从“电影作品+类电作品”到“视听作品”的统合,以及从“作品类型封闭”到“作品类型开放”的转换等重要改正点,仍在不断反映著作权的扩张趋势。然而,由于著作权法的规制范围广泛延及文化领域,限制公众的行动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著作权扩张被广泛认为有害于著作权的核心目标和经济理性”(2)Neil W. Netanel,“Why has Copyright Expanded?Analysis and Critique,” in Fiona Macmillan, New Directions in Copyright Law,Volume 6,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8,p.3.。在此种共识和危机面前,若要对著作权的扩张展开任何形式的回应,都必须对著作权扩张的历史成因提出问题。
由此,在著作权扩张的诸多可能的解释中,浪漫主义作者观(romantic authorship)逐渐成为一个被反复提起和批判的众矢之的。在美国版权法学界,学者们与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幽灵缠斗了数十年之久,这或许是受到了在美国影响深远的解构主义传统的波及。(3)Erlend Lavik,“Romantic Authorship in Copyright Law and the Uses of Aesthetics,” in Mireille van Eechoud,The Work of Authorship,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4,pp.88-89.20世纪末,玛莎·伍德曼西(Martha Woodmansee)和皮特·贾西(Peter Jaszi)就将整个版权法“自其诞生的三百年多以来,保护期限越来越长,规制越来越多种未经授权的使用,涵盖越来越多所谓的‘作品’类型”的扩张趋势归因于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建构。(4)Martha Woodmansee &Peter Jaszi,“The Law of Texts:Copyright in the Academy,” College English,No.7,1995,pp.772-773.马克·罗斯(Mark Rose)将浪漫主义作者观与18世纪后半叶英国发生的文学财产大论战,即英国书商谋求普通法永久权利保护的“书商之战”(battle of the booksellers)联系在一起:
当德国的浪漫主义观被柯勒律治引入英国思想中时,关于版权的长期论战已经为这些思想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对原创性、艺术作品的有机形式,以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独特个性的表达等概念的浪漫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版权论战期间发生的法律和经济变革的必要的完成。为什么作者应该对其作品拥有财产权?该作品包括哪些内容?文学作品与机械发明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理论所解决的,正是版权论战所提出的理论问题。(5)Mark Rose,“The Author as Proprietor:Donaldson v. Becket an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Authorship,” Representations,No.23,1988,p.76.
詹姆斯·波义耳(James Boyle)总结道,我们被驱使着将信息财产权赋予那些最接近浪漫主义作者形象的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这带来了过多的知识产权,使权利被赋予错误的人,并且极大地低估了商品化信息的来源和受众的利益。(6)James Boyle,Shamans,Software,and Spleens: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x-xi.此外,也有学者使用“作者中心主义”(author-centrism)概括作者权体系中作者独揽大权的境况。简·金斯伯格(Jane C. Ginsburg)用该术语指称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作者权理念,这种依据作者智力创作而授予财产权的理念与英美版权体系的“社会取向”(society-oriented)形成对立,后者认为公共利益与作者利益至少是平起平坐的。(7)Jane C. Ginsburg,“A Tale of Two Copyrights:Literary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merica,” Tulane Law Review,No.5,1990,p.993.
同样,在我国著作权法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几乎所有人都将浪漫主义作者观视作著作权法的拱顶石。在理论层面,批判著作权扩张的文献接受了作者中心主义的母题,将浪漫主义作为著作权法的哲学基础之一。(8)林秀芹、刘文献:《作者中心主义及其合法性危机——基于作者权体系的哲学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在实践层面,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被视为对著作权法的解构,这将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问题提供新的思考。(9)丁晓东:《著作权的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作品法律保护的法理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5期。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亦认为,排斥独创性的“类型化”网文创作与著作权法背后的浪漫主义作者观产生了严重的龃龉。(10)郑熙青:《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和著作权问题》,《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因此,在援引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11)Roland Barthes,“Death of the Author,” in Stephen Heath,Image Music Text,California:Fontana Press,1977,p.148.理论,以及福柯对作者身份的社会建构性和“作者功能”(12)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 in Josue V. Harari,Textual Strategies: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148.的探问之后,主流观点希望借此填补著作权法与文化理论之间的鸿沟,期求以浪漫主义为立法根基的著作权法能够跟随1960年以来哲学和文学理论中出现的后现代作者观的潮流。(13)刘文献:《从创造作者到功能作者:主体范式视角下著作权作者中心主义的兴与衰》,《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二十八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0页;郑熙青:《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和著作权问题》,《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诚然,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能够为我国的著作权法研究带来深刻的教益。第一,近代以降,我国在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律》和1990年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时两次选择了来自欧洲大陆的作者权体系,而没有选择英美的版权体系,作者权体系的运行逻辑深刻地根植在我国现行的著作权制度中。(14)李明德:《两大法系背景下的作品保护制度》,《知识产权》2020年第7期。因而,在实践层面,在人工智能创作不断冲击著作权法“人类作者”的基本预设的境况下,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作者观将作为一个回溯著作权主体理论的楔子,为人工智能创作等新问题带来最为直接的启示。第二,在理论层面,如果波义耳所言不假,那么被浪漫主义作者观所笼罩的著作权法演化进程将呈现为一条直线,一条沿时间轴不断扩张的单行道,在这条道路的尽头,“资源、受众和未来的创造者们都将走入失败的境地”(15)James Boyle,Shamans,Software,and Spleens: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42.。因此,如果浪漫主义作者观正是著作权扩张的病灶,那么通过清除当下著作权法中残存的浪漫主义作者观的余绪,便可能扭转著作权的单向度扩张,缓解产权过多、资源利用不足的“反公地悲剧”现象。最后,法不能无视社会现实,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16)李琛:《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5页。因而,在学科层面,规制文化领域的著作权法理应与人文学科中的相应理论展开积极的对话。
然而,本文承认浪漫主义作者观对著作权法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但不赞成牵强附会地在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做法。本文的核心主张是,认为浪漫主义作者观招致了著作权扩张、应该用后现代作者观取代浪漫主义作者观并将之作为著作权法的基本信念的主流观点不能成立。浪漫主义作者观既与著作权扩张的历史和现状有诸多龃龉,也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本质,著作权法的发展更不需要亦步亦趋地追随文化理论的步调。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历史文本描述浪漫主义作者观的诸核心命题;第二部分向主流观点提出商榷,通过著作权法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背离、浪漫主义作者观本身的含混性,以及主流观点主张的“后现代著作权法”的不合理性等三个面向,解构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的因果关系,阐述无法借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缘由;在揭示并批判“后现代著作权法”所预设的错误前提之后,本文的第三部分将理论视角提升到一个更为宏观的向度:不是列举浪漫主义作者观以外的著作权扩张成因,而是提出一个解释著作权扩张一般规律的替代性理论;在结论中,陈述历史批判对当下的意义与价值。
二、观念的缘起:作为著作权扩张成因的浪漫主义作者观
(一)作者观念的流变
在反思借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思潮之前,必须首先代入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的视角,描述浪漫主义作者观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将如何影响著作权的扩张和著作权制度的形式。从古希腊到现代作者形象流变的历史叙事中,可以窥见浪漫主义作者观的诞生时刻,以及浪漫主义作者观与其他作者观念范式的差异。
在古希腊人眼中,艺术家只是在模仿工匠制造的物品,是对理念之再现的再现,“处在事物本质的第三外围”(17)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61页。。诗人吟诵的诗歌也不是其天才的独创性使然,而是诗人被文艺女神缪斯凭附、支配的产物:“毋庸置疑,那些优美的诗句不是属人的,也非人之创作,而是属神的,得自于神,人不过是神的传译者而已,诗人被神凭附”(18)柏拉图:《伊翁》,王双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此后,在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的手抄书时代,懂得希腊文的“抄书家”获得了最优渥的待遇和酬劳,(19)雅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花亦芬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42页。而读者对书籍的真正作者并无兴趣。在中世纪一个著名的四分法中,圣文德(St Bonaventure)区分了“制造一本书的四种方法”:抄写者(scribe)只是抄下别人的文字,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改;编写者(compiler)把并非出自他手的段落放在一起;评论者(commentator)同时书写别人的和自己的文字,但他将别人的文字放在首要位置,他自己的文字只是为了澄清意义而添加的;作者(author)也同时书写别人的和自己的文字,但他自己的文字占据首要位置,别人的文字只是为了确证而添加的。(20)J. A. Burrow,Mediev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1100—15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1.显然,圣文德所说的第四种造书方式,即“作者”,是最为接近如今著作权法中的作者形象的,但他并未赋予“作者”任何优先地位。中世纪的“作者”与“抄写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作者”只是位于从简单复制到原创写作的光谱上,虽然这两种功能在我们看来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对这一时期的读者而言,同时代的写作者丝毫不比抄写者更为重要,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权威,而只是故事或信息的传递者。(21)Andrew Bennett,The Author,Oxford:Routledge,2004,pp.39-41.真正享有权威地位的是那些写下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的古代作者,但这种权威的来源不是现代人所崇尚的独创性写作,而是紧紧依附于此前的文化传统和遗产。(22)Donald E. Pease,“Author,” in 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105.
在18—19世纪,即英国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时期”,作者观念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在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作者诞生了。一份浪漫主义作者的代表性宣言,即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在1759年发表的《试论独创性作品》(ConjecturesonOriginalComposition)受到了著作权法学界的关注。在这篇文本中,扬格开创性地区分了“独创性作者”和“模仿者”:独创性作者开拓了文学的疆土,而模仿前人的模仿者们只是提供了已有的卓越作品的副本,徒然增加了一些不足道的书籍,而使书籍可贵的知识和天才却未见增长。(23)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第26页。此外,扬格还提出了类似于“作品所有权归属于独创性作者”的论调,使法律与现实的话语相辅相成:只有尊重自己头脑中的产品,摒弃最华贵的舶来品的独创者才拥有作品的唯一所有权,而所有权又将“作者”这个崇高的称号赋予他,即他是一个思想者和创作者,而不仅仅是读者和写者。(24)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第26页。扬格的独创性理论与此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天才的论述相得益彰:天才是一种产生出超脱确定规则之外的东西的才能,独创性是天才的第一特性,天才与模仿的精神完全对立。(25)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8—349页。《判断力批判》影响了歌德、席勒、赫尔德、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等一众浪漫主义作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将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Ballads)1800年版《序言》中的著名论断“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6)William Wordsworth &Samuel Taylor Coleridge,Lyrical Ballads:1798 and 180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98.作为英国浪漫主义文论或“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ies)取代此前的作者观念范式的标志。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作者自发的情感取代了对事物的技术性模仿,作者作为权威主体的崇高地位开始显现,创作和批评理论的重心也随之转向了作者,“艺术家本身成了生产艺术品和艺术评判标准的主要因素”(27)M. H. 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22.。总之,浪漫主义的旗手们编织了一张涵盖个性、情感、独创、天才、所有权等主题的网,使18—19世纪的作者观念呈现出与此前的“模仿论” “书写者”和“古典传统”截然不同的面貌。
(二)“法的稳定性”之预设
在主流观点看来,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者观为何能够持续对当下的著作权法产生影响?为什么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能够不由分说地断定,“18世纪初在遥远英国确立的基本原则,仍一如既往凝视着网络上的作者、作品和读者,试图为经验世界提供一个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制度结构”(28)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9页。?
若要在浪漫主义作者观和著作权扩张的现状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批判者必须假设,在第一性的文学理论中存有诸多不同的作者观念,而第二性的著作权法在其成形时期吸收的是浪漫主义作者观或表现说。(29)陈杰:《论著作权法视野下的作品观》,《知识产权》2012年第6期。在著作权法此后的历史中,这个吸收而来的内核恰恰一成不变、持续至今,作为著作权法的根本信念和意识形态,继续对当下的现实起着调整的作用,(30)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4页。而对文学理论在浪漫主义作者观之后的发展充耳不闻。此即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预设的“法的稳定性”之前提。
三、批判与商榷:因果关系的解构
然而,著作权法真的吸收了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内核,且这个内核一直保留至今了吗?本节将会证明,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并未射中著作权扩张问题的靶心,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的扩张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一)著作权法对浪漫主义作者观的背离
通过历史回溯,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描绘了著作权法诞生前后和成形时期的作者观念范式与社会图景。然而,如果希望通过清除过时的浪漫主义作者观来批判著作权的扩张,则首先必须把目光转回著作权法的实证研究,在当下的著作权实践中辨认这些古老观念的藏身之所。事实上,浪漫主义的诸命题在著作权扩张中早已生发出特殊的含义,这使得浪漫主义作者观招致了著作权扩张的断言与著作权法的现状显得貌合神离。
1.著作权法的独创性理论
无论是在著作权法理论中还是在浪漫主义文论中,独创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在上文援引的《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扬格未曾打算探究严格意义上的独创性定义,而是直接将独创性视为一个定量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
我不打算作好奇的探究,谈谈什么是、什么不是严格意义的独创,而是满足于大家必须承认的事实,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地添上一个新省区。(31)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第19—20页。
浪漫主义作者观认为作品的价值与其独创性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种独创性观念甚至与今日专利法所要求的“新颖性”只有一纸之隔:激励技术创新的专利法预设了人类的技术水平沿时间轴不断线性进步的图景,这要求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必须“不属于现有技术”(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防止已被公开的、能够为公众自由利用的技术被重复授予专利权,阻碍产业的发展。不满于18世纪英国独创性作品日渐式微的文学境况的扬格正是如此比较文化和技术领域的:在机械工艺中,人们总是力图超越前人,使技术永远得到进步和发展;在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中,人们追随前人,使文化不断倒退和衰落。(33)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第19—20页。然而,著作权法已然生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独创性理论,在拒斥浪漫主义独创性话语的同时,削弱了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的因果关系。
诚然,在一些涉及美术作品和视听作品独创性判断的案例中,法院对独创性的解释时常闪现着浪漫主义的色调。在“乐高公司诉广东小白龙动漫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独创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加以判断的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实际上,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其独创性要求体现作者在美学领域的独特创造力和观念。”(3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358号。此后,在“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讼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案”,即“新浪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案”二审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并通过体系解释将独创性的判断细分为“角度”和“高度”两个面向,“不同类型作品独创性判断的角度及高度要求不尽相同”(3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这些隐含浪漫主义底色,促使著作权法积极介入审美判断的观点可以称为“独创性高低说”。相反,在“新浪诉凤凰网体育赛事转播案”的再审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立场可以称为“独创性有无说”:著作权法仅仅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作品的独创性只能定性为有无,无法定量为高低。(36)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再128号。
在本质上,“独创性高低说”和“独创性有无说”的争议体现了浪漫主义思维和著作权法思维之间的张力和矛盾。然而,用浪漫主义作者观主张的独创性高低来解释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这陷入了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
第一,独创性高低说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文义。《著作权法》只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3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并未对作品的创作高度提出任何要求。虽然美术作品和建筑作品的定义要求这两种作品具备“审美意义”(38)《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款第(八)(九)项。,但定性的“审美意义”与定量的“创作高度”并非等同,“审美意义”要件并未使这两种作品的独创性判定独立于其他作品类型。由此,作品的作者无须进行某种高度的智力创作,作者仅仅是“实际创作作品的人,也即将一个思想转化为具有受版权保护资格的固定、有形表达的人”(39)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v. Reid,490 U.S. 730,737 (U.S.Dist.Col.,1989).。
第二,奠定著作权法独创性理论基础的判例并未采用独创性高低说。在1879年的Bakerv.Selde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独创性,但排除了版权法对作品新颖性的要求:“如非从其他作品盗版,书籍便将受到版权保护,与其主题是否缺乏新颖性无关。”(40)Baker v. Selden,101 U.S. 99,102 (U.S.,1879).在Feist Publications,Inc.v.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案之后,人们更加认识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不是扬格描绘的那条由低到高无限延展的光谱,而只是一道极低的门槛:“‘独创’一词,作为版权术语使用时,仅仅意味着该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而非从其他作品复制),并且具有至少一定程度的创作性。无疑,所需的创作性水平非常低,即使微小的量也已足够。”(41)Feist Publications,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Inc.,499 U.S. 340,345 (U.S.Kan.,1991).在这段时常被援引的论述中,美国最高法院虽然使用了“微小的量”(a slight amount)这样看似为独创性高低说背书的用语,但法院对作品创作性的判断是客观的,不是评价创作性的美学价值或质量,而只是评价创作性的存在或不存在(presence or absence)。(42)Willam F. Patry,Patry on Copyright,Eagan:Thomson West,2007,c.3,s.36.直至近年,这个标准也未曾改变。在Star Athletica,L. L. C.v.Varsity Brands,Inc.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实用艺术品仅仅需要考量“产品和其特征是如何被理解的,而非它们是如何设计的,或为什么被设计出来”(43)Star Athletica,L. L. C. v. Varsity Brands,Inc.,580 U.S. 405,423 (U.S.,2017).。换言之,著作权法不考虑实用艺术品创作者的主观创作方法、创作目的和理由,只考虑实用艺术品中是否存在客观可辨认的美感要素。
第三,在这些奠基性判例中,法官往往会主动划定专属于著作权法的独创性问题域,增强独创性有无说的强度。在Feist案判决主旨的首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将独创性严格限定为一个“版权术语”,排除了浪漫主义的独创性概念,建构了独创性在著作权法领域中的特殊语义。在此前的Alfred Bell &Co. Ltd.v.Catalda Fine Arts Inc.案中,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曾如此区分文学和著作权法领域中的独创性含义:“被告的主张显然源于‘独创’一词的多义性。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惊人的、新颖的、非同寻常的、与过去显著不同的……在谈论版权作品的独创性时,‘独创’是指该特定作品源自作者,不需要很大程度的新颖性。”(44)Alfred Bell &Co. Ltd. v. Catalda Fine Arts Inc.,191 F.2d 99,102 (2d Cir. 1951).
第四,历史解释也否定了独创性高低说。在1976年《美国版权法》的修订过程中,美国版权办公室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作品“创作性”(creativity)的提案,要求作品为作者独立创作的同时“必须表现出可观的创作性”,并认为这个要求“通常被版权专家认可”(45)Copyright Law Revision: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on the General Revision of the U.S. Copyright Law,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9.。这项提案此后被否定的原因不是作品不需要创作性,而是担忧法院将所谓的“创作性”解释为需要具有可证明的艺术价值。(46)Copyright Law Revision Part 3:Preliminary Draft for a Revised U.S. Copyright Law and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on the Draft 42 (Finkelstein),45-46 (Schiffer)(1964). Cited in Willam F. Patry,Patry on Copyright,Eagan:Thomson West,2007,c.3,s.36.因此,最终1976年《美国版权法》中仅仅使用了“作者的独创性作品”(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的表述,并保留了对独创性的进一步解释。(47)17 U.S.C.A. § 102.不过,审美判断在立法报告中被直接否定:“该标准不包括对新颖性、创意或美学价值方面的要求,并且不存在提高版权保护标准来要求它们的意图。”(48)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No.1476,94th Congress,2nd Session,1976,p.51.据此,在一定程度上,1991年的Feist案判决并未提出任何新的独创性标准,而只是对这些历史解释的某种确认。
第五,对法官审美判断职能的最直接否定,无疑是霍姆斯在Bleisteinv.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案中提出的“非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如果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在最狭窄和最明显的限度之外,对绘画插图的价值作出最终评判,这将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在一个极端,一些天才的作品肯定会失去赞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吸引了教育程度低于法官的公众的图片,它们的可版权性也会被拒绝。(49)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188 U.S. 239,251 (U.S. 1903).
究其根本而言,这项原则的背后是一种在市场和法律之间划分职能的法政策学理念。浪漫主义作者观所主张的独创性对应一种市场定价标准,而著作权法的独创性对应着权利的存否。换言之,作为一种权威介入的手段,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只能判断作者法定权利的有无,而不能决定作品市场价值的高低。作品的价值只能交由市场决定,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资源分配优势无法简单地被著作权法取代。(50)田村善之:《知財の理論》,有斐阁,2019年,第11—15页。无论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估价与法官有何种差异,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对此都不予考虑,“一名法官自身的审美判断在版权分析中不得起任何作用”(51)Silvertop Assocs. Inc. v. Kangaroo Mfg. Inc.,931 F.3d 215,221 (3d Cir. 2019).。由此,著作权法不会涉足评判作品市场价值的浪漫主义领地,作品的独创性判定过程拒斥了文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判断。
以上论述均是对著作权法独创性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事实判断,而非对独创性高低说和独创性有无说之优劣或合理性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意在通过著作权法对独创性高低说的拒斥,证明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牢不可破。显然,主流观点无法解释著作权法何以在独创性这一文学和著作权理论共有的核心命题上走向了追求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范围更加宽泛的独创性有无说,而没有选择充满浪漫主义色调的、保护范围更加狭窄的独创性高低说。如果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内核在如今的著作权法中得以存续,换言之,如果著作权法仅仅保护少数天才作者的高度独创性作品,那么获得著作权保护对大多数作者而言将成为一个奢望。然而,事实却与此截然相反,无论多么拙劣的绘画,抑或是幼儿稚嫩的画作,都有资格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作品。(52)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有斐阁,2010年,第422页。从这个角度看,浪漫主义作者观不仅不可能推动著作权的扩张,反而只可能限缩著作权的保护范围。
2.著作权法的经济属性
扬格对独创性和财产权关系的论述提示我们,在辨认著作权法在独创性层面的浪漫主义余绪之后,应该将目光转向权利的归属问题。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的一大区别便是“主体不再被表述为整个有机社会的一分子,而是投身于一项漫长的,有时是无穷无尽的追寻的孤独个体”(53)M. H. Abrams &Geoffrey Galt Harpham,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11th ed.),Connecticut:Cengage Learning,2015,p.240.。伍德曼西同样认为,我们的知识产权法根植于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创作过程概念的重构,而华兹华斯的孤独、个体化的浪漫主义宣言正是创作过程理论的高峰。(54)Martha Woodmansee,“On the Author Effect:Recovering Collectivity,” in Martha Woodmansee &Peter Jaszi,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p.27.有时,作者的创作过程也被描述为一种无需依赖任何外部资源的神迹:作者“凭借他的天才和特殊的知识,无中生有(ex nihilo)地创造了作品”(55)James Boyle,“The Search for an Author:Shakespeare and the Framer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No.3,1988,p.629,p.629.。总之,这些原子式的个体观念将作者和作品从社会、历史和传统的语境中抽离出来,而它在著作权制度中的化身便是作者中心主义的宣言:作者对作品享有的不是私权利,而是某种王权,作者是作品的暴君。(56)林秀芹、刘文献:《作者中心主义及其合法性危机——基于作者权体系的哲学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自作品完成时开始,著作权法便会自动赋予作者严丝合缝的著作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使作者得以全面排除他人对作品的使用,“根据这种主宰权,作品就是他的了”(57)M. 雷炳德:《著作权法》(第13版),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74页。。由此,一旦出现立法时尚未出现、立法者未曾想见的作品和使用方式,著作权法便会受到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感召,通过扩张客体范围和权能,或是援引一般条款的方式维持作者对作品及其衍生市场的全面控制。
然而,主流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著作权法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削弱了作者对作品的控制。浪漫主义遗世独立的个人英雄作者观念决定了它必须拒斥作者和作品的商业面向,如果一本书具有商业价值,它便缺乏美学价值。(58)Andrew Bennett,The Author,Oxford:Routledge,2004,p.52.“在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愿景中,艺术(特别是作者身份)和商业利益是无法相容的。写作者不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他对作品的完满性以外的东西都没有兴趣。”(59)James Boyle,“The Search for an Author:Shakespeare and the Framer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No.3,1988,p.629,p.629.但是,著作权法从未怀有过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相反,它自始便具有强烈的贸易法属性,这使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所谓的“作者主宰权”成为一个虚构的幻象。
第一,从著作权史上看,在1710年的《安妮女王法令》颁布之前的游说活动中,为了维持市场垄断利益,图书销售商借助作为财产权人的作者,以及与之相关的父权、不动产、鼓励学习等修辞工具,论证作者可以合法地将权利和身份转让给他们。(60)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0—54页。《安妮女王法令》显然体现了出版商的利益,根据该法第2部分的规定,作者的版权从首次出版之日起算,有效期为14年。(61)8 Anne,c. 19 (1710),s.Ⅱ.换言之,由于版权保护始于作品的出版,作者一开始就必须依靠出版商来获得版权保护。(62)Molly Van Houweling,“Authors versus Owners,” Houston Law Review,No.2,2016,p.374.因此,一个常见的对《安妮女王法令》的批判便是该法“只不过是不合时宜地将既有的书籍贸易实践编纂成法律罢了”(63)John Feather,“From Rights in Copies to Copyright:The Recognition of Authors′ Rights in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in Martha Woodmansee &Peter Jaszi,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08-209.。也有人认为英国议会察觉到了书商的垄断诡计,转而利用作者创设了一个作为贸易规则的版权。据此,《安妮女王法令》是作为一部防止英国书商垄断市场的贸易规则法来设定的,证明这一属性的特征包括版权的有限保护期、任何人均可获得版权保护,以及价格控制规定。(64)莱曼·雷·帕特森、斯坦利·W. 林德伯格:《版权的本质:保护使用者权利的法律》,郑重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5页。无论如何解释,《安妮女王法令》的商业属性都压倒了现代人有意或无意附会在该法中的浪漫主义叙事。归根结底,《安妮女王法令》的颁布早于扬格1759年先驱性的浪漫主义宣言《试论独创性作品》数十年,遑论华兹华斯在1800年对浪漫主义时期的正式揭幕。将18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法中的作者等量齐观,这显然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65)Lionel Bently,“Introduction to Part I:The History of Copyright,” in Lionel Bently,Uma Suthersanen &Paul Torremans,Global Copyright:Thre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Statute of Anne,from 1709 to Cyberspac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0,p.10.
因此,与其说浪漫主义作者观经由法律的稳定性而被保留至今,毋宁说被保留下来的是著作权法的经济旨趣。如今的著作权法毫不掩饰其浓厚的商业属性,在实践中演化出独占使用许可、排他使用许可、普通使用许可、(66)李扬:《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第288—290页,第297页。质押(6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8条。等经济利用形式。曾经的书商在著作权法中被称为“图书出版者”——一个独立的邻接权主体。虽然作者现在在作品创作完成时即可获得著作权保护,(68)《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这些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无须履行任何手续,并与作品的来源国给予的保护无关。”《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指南》,刘波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但《出版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这使得作者若要通过图书等有形形式发行其作品,便必须授予出版单位独占复制以及发行权,即专有出版权。(69)李扬:《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第288—290页,第297页。质押(7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8条。作者非但没有实现全面宰制作品的浪漫主义理想,反而不得不受到出版者的制约。
第二,现代著作权法生成了一种带有明显市场倾向的“作者/著作权人二分法”。作者是实施创作行为的人、作品的初始来源,著作权原则上归属于作者,但唯有著作权人才是拥有并行使著作(财产)权的主体。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条例不仅允许作者转让著作财产权,而且详细列举了职务作品、合作作品、委托作品、演绎作品、汇编作品、视听作品、美术和摄影作品原件展览权、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是划定清楚而分明的权利归属关系,降低作品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雇佣作品和视听作品的场合中,著作权在初始阶段便被直接分配给雇主、制作者等并非原始作者的主体,这进一步消解了浪漫主义个人作者的权威。
第三,在软法层面,著作权法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特定地域和行业的商业惯例,并非必然将权利划归作者。例如,虽然视听作品的著作权通常归属于作为制作者的电影或电视剧公司,但日本的行业惯例是由负责影片分发、电视播放、广告代理等项目的公司缔结“组合契约”(类似于合伙合同),共同出资组建一个“制作委员会”作为行使著作权的许可窗口,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委员会的成员按份共有。(71)半田正夫、松田政行编:《著作権法コンメンタール2》,劲草书房,2015年,第128页。在“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福州市嘀哩科技有限公司、福州羁绊网络有限公司等”案(72)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0民初8708号。中,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认为“基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作品的署名方式、转让、授权链条的确定等事项因各国地域文化、法律规定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肯认了日本影视作品的特殊署名方式和制作委员会成员共有的权属。
从上文对独创性高低说和有无说的论述中,可以窥见著作权法对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独创性作品的重视,但在另一端,著作权法对所谓天才作者的报偿却是游移不定的。在作者和著作权人时常分离、由大公司掌握大量具有市场价值的作品的情况下,带有市场取向的“著作权人中心主义”显然远比带有浪漫主义底色的“作者中心主义”更能恰切地描述著作权法的现状。《安妮女王法令》的立法史表明,著作权法从未被离群索居的浪漫主义个人作者话语统治;现代著作权法对作品经济利用和特殊作品权利归属的成文法与习惯法表明,在著作权法的语境中,作品不是作者闭门沉思的天才构想,而是在市场中广泛流通的经济资产。作品的商业价值使著作权正在或是已然成为和专利权平起平坐的企业战略支柱。(73)中山信弘:《著作権法》,有斐阁,2020年,第5页。
浪漫主义作者观必须反对商业性以肯定自身。但是,通过一种古典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在将不合时宜的个人英雄作者附会到著作权法中的那个时刻,浪漫主义作者观完成了对自身的反讽:“一定程度上,美学的特征是对这种堕落的精神补偿:正是在艺术家沦为一个小商品生产者时,艺术家才会诉诸卓越的天才”(74)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Blackwell,1990,p.65.,而正是这些远离市场的天才创作使作品产生了商业价值。
3.著作人格权的市场化
20世纪前夕,欧洲大陆的作者权体系和英美版权体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权利扩张道路。1774年的Donaldsonv.Becket(75)Ronan Deazley,Commentary on Donaldson v. Becket (1774),https://www.copyrighthistory.org/cam/tools/request/showRecord.php?id=commentary_uk_1774,访问日期:2023-12-15。案宣告了英国书商普通法永久权利愿望的破产,英美版权体系的作者权利被限制在社会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内。(76)Peter Baldwin,The Copyright Wars:Three Centuries of Trans-Atlantic Batt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28,130.相反,欧洲大陆的作者权体系缓慢地将财产与“作者不可侵犯的人格表达”这一自然权利结合起来,而作品与作者的个人联系当然是浪漫主义“艺术家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作品乃是把外界材料制成为描绘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那样一种物:它完全表现作者个人的独特性”(7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86页。。由此,作者权体系相较于版权体系所多出的那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即不可转让的、具有专属性的著作人格权,似乎与著作权法的经济属性并不相符。在浪漫主义作者观看来,作品中的人格要素早已根植在公众的常识之中,正是这些常识标示了作者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深深地认为艺术和作者身份与其他市场交易有所不同,以至于很难意识到这项规定实际上有多么引人注目”(78)James Boyle,“The Search for an Author:Shakespeare and the Framer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No.3,1988,p.629.。
著作人格权与著作权扩张的连接点在于,《伯尔尼公约》是在作者权体系国家的牵头下诞生的。1878年,在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主持的巴黎国际文学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作者的法定永久权利、国民待遇和简化手续;同年,在巴黎召开的另一次国际艺术大会则是呼吁欧洲各国订立保护艺术财产权的国际公约。此后,瑞士促成了伯尔尼联盟的诞生。(79)山姆·里基森、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第二版),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页。一个世纪以后,为了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的作者精神权利规定相协调,英美版权体系国家在制定法中纷纷写入作者精神权利的相关条款。例如,英国在1988年的《版权、设计与专利法法案》(Copyright,DesignsandPatentsAct)中设置了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禁止虚假署名,以及保护特定照片和影片的隐私权;(80)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c. 48,part I,chapter IV (moral rights).美国也在1990年制定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VisualArtistsRightsAct,VARA),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81)17 U.S.C. § 106A.因此,似乎可以说,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作者观逐渐推动了著作人格权这个强力权能向英美版权体系的扩张。
然而,在如今的著作权法中,著作人格权的地位日渐式微。《伯尔尼公约》的立法过程表明,公约不是作者权体系背后的浪漫主义单方面占领版权体系的结果,而是参与者之间不断妥协的产物。浪漫主义作者观首先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伯尔尼公约》没有完全禁止著作人格权的转让或放弃,这有意或无意地为一些国家的“非自然人作者”制度留下了一道通风口。《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第(1)款虽然规定著作人格权不受著作财产权的影响,作者在转让著作财产权之后仍然可以行使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但该条只确认了著作人格权相对于著作财产权的独立性,并未明言禁止著作人格权的转让或放弃。这使一些版权体系国家得以在本国法中将非自然人视为或直接规定为雇佣作品的作者,享有包括著作人格权在内的一切著作权(除非双方另有约定)。(82)17 U.S.C. § 201(b);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c. 48,s. 11(2);Copyright Act,R.S.C.,1985,c. C-42,s. 13(3).我国和日本虽然主要遵循作者权体系的立法逻辑,将著作人格权规定在著作财产权之前,但仍然吸收了版权体系的雇佣作品制度,允许非自然人享有著作人格权。(8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法人作品)、第18条第2款(特殊职务作品);《日本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美国《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虽然仅仅将精神权利赋予“视觉艺术作品”的作者,且在“视觉艺术作品”的定义中排除了雇佣作品,(84)17 U.S.C. § 101 (work of visual art).但该法允许作者明示放弃精神权利。(85)“如果作者在一份由其签署的书面文件中明确同意放弃这些权利,则可以放弃这些权利。”17 U.S.C. § 106A(e).换言之,只要与雇员签订放弃精神权利的契约,雇主便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作品。
作者权体系的支持者们向来无法理解版权体系的某些制度,他们认为以毫无艺术品位的、愚不可及的功利主义为基石的版权话语“将文化推上了商品的祭坛”(86)Peter Baldwin,The Copyright Wars:Three Centuries of Trans-Atlantic Batt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20.。因此,将非自然人视为或规定为享有著作人格权的原始作者,以及通过各种手段使作者放弃著作人格权的做法承受了一些浪漫主义式的批判。例如,非自然人作者将削弱著作权法的道义理由,或是使著作权法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工商业投资而非文学艺术创作。(87)山姆·里基森、简·金斯伯格:《国际版权与邻接权——伯尔尼公约及公约以外的新发展》(第二版),郭寿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9页。在著作权法的客体仅仅涵盖文学、绘画、音乐等作者人格要素强烈的文艺作品的时期,浪漫主义作者观或许尚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当著作权法的客体范围逐渐扩张至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人格要素稀薄的作品,甚至由“作品类型法定”转向“作品类型开放”后,著作人格权的形象便不再局限于联系作者与作品的纽带,它产生了作为市场交易对象的属性。不得不承认,非自然人作者有着难以替代的交易成本优势,这与将电影、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授予制作者的规则(88)《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1款。有着相同的原理:“数量众多的单独交易带来的高成本,使得一体化成为一个更好的替代性选择”(89)罗伯特·P. 莫杰思:《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金海军、史兆欢、寇海侠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00页。。此外,雇主为雇员的创作提供的劳务报酬,以及著作权法在双方另有约定时的除外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雇员著作人格权的丧失。(90)田村善之:《著作権法概説》,有斐阁,2001年,第377页。
由此,浪漫主义作者观同样无法解释一些国家何以对本应扩张的著作人格权做出了方方面面的限制。例如,《日本著作权法》中规定了作品发表推定同意制度(91)《日本著作权法》第18条第3款,第19条第2、3款,第20条第2款。、对署名权在作品已有作者署名标示或是不妨害作者利益与公正惯例时的限制,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在学校教育、建筑物改建、计算机软件运行等场合的例外。这些为保证作品在市场中顺利流通而设置的规则反映了作者人格要素的式微和市场要素的兴起。一言以蔽之,即使在与浪漫主义作者观联系最为紧密的著作人格权方面,著作权法也逐渐表现出对市场的偏好,而没有全然选择浪漫主义的理想。
(二)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含混性
除去对著作权法实证研究的忽视之外,借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理论家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置性问题:浪漫主义作者观是否拥有一个(或一些)一成不变的属性?
在描述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核心命题时,主流观点采用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定义法,即认为“物体具有一些本质特征”(92)Essential vs. Accidental Properties,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20-10-26,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ssential-accidental/,访问日期:2023-09-10。的信条。例如,在与新古典主义的比较中,浪漫主义的特征被描述为“偏好创新、以诗人的个人情感为必要组成部分、以外部自然环境为主题、以诗人自身为主角、全新的开端和可能性”(93)M. H. Abrams &Geoffrey Galt Harpham,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11th ed.),Connecticut:Cengage Learning,2015,pp.238-240.。沿袭这种思路,上文也通过古希腊、中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作者观念史文献,绘制了批判者眼中的浪漫主义作者形象——一位永恒追求高度独创性写作,不谙世事的孤独天才。然而,本质主义无法避免面对诸多例外所带来的张力。观念史家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曾说:“‘浪漫’这个词已经被用来表示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它本身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94)Arthur O. Lovejoy,“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o.2,1924,p.232.不难发现,上述定义已经彰显了从不同角度界定浪漫主义作者形象时的冲突和含混。伽达默尔总结道,浪漫主义通过诉诸自然景观,“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它把某种特有的价值归给过去的时代,并且甚至能够承认过去时代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优越性”。(9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90页。然而,这些对往昔充满乡愁的追忆既然要把过去当作素材,那么它终将与无中生有式的独创性观念渐行渐远。
更具体的例证是,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旗手们时常间接或直接地表达对独创性天才的否认。在扬格那里,独创性作者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对传统的接纳:“让我们的思想从他们的思想吸收营养,他们供给最高的养料;不过让他们滋养,而不是消灭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读书时,让他们的优美点燃我们的想象;我们写作时,让我们的理智把他们关在思想的门外。”(96)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9页。诸如此类的例证直接削弱了浪漫主义作者观作为著作权扩张成因的证据价值。在任何时代,人们都能轻易找到一大批(同时)拥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是其他任何流派的某一或某些特征的作者。在创作生涯中,随着时间推移、经验积累或社会环境的变迁,作者往往也会有意地或无意中改变创作理念。在《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ASpeechfortheLiberityofUnlicensedPrinting)中,弥尔顿写道:“书籍……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97)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6页。这使弥尔顿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吗?在《失乐园》(ParadiseLost)中,弥尔顿又如荷马一样诉诸缪斯:“因此我向那儿求您助我吟成这篇大胆冒险的诗歌,追踪一段事迹……”(98)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页。这是一种向古希腊“灵感论”的倒退吗?显然,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完全符合独创、天才、无中生有、孤寂、远离市场等全部特征清单的“理想的浪漫主义作者”,而是不得不接受济慈的断言:“天才之人是伟大的,他们像某种醚制的化学物质一样,对中等智力的群氓产生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任何个性,也没有确定的特征。”(99)John Keats,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2由此,本质主义的弱点招致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后果:借助含混不清的浪漫主义作者观批判著作权扩张的正当性依据被进一步削弱。
(三)“后现代著作权法”的疑问
当批判者宣称“在主流的法律思维模式和主流的文学思维模式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100)Mark Rose,“The Author as Proprietor:Donaldson v. Becket and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Authorship,” Representations,No.23,1988,p.78.,“作者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悄然发生了变迁,从而以旧式哲学为依据而建构的作者中心主义著作权制度面临合法性拷问”(101)林秀芹、刘文献:《作者中心主义及其合法性危机——基于作者权体系的哲学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之时,他们向往的是一个摒弃了著作权法这样过时、笨重的文化管制的体系,像福柯在《什么是作者?》(WhatisanAuthor?)的结尾所说“谁在说话又有何关系”(102)Michel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 in Josue V. Harari,Textual Strategies: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160.那样的美丽新世界。(103)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60页。然而,“后现代著作权法”中暗含了以下三个可疑的前提。
1.对“法的第二性原理”的误解
“法的第二性原理”认为,法以社会现实为调整对象,社会现实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法只能选择它能够调整的事物,采用它能够调整的手段。(104)李琛:《知识产权片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5页。然而,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错把文学理论当作著作权法所要亦步亦趋地调整的现实。著作权法规制的是人的行为,它所调整的第一性的社会现实只能是人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不是文学理论。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作者观不是社会现实或人的行为本身,而是在某种视角下对人的创作行为展开的归纳和解释,它们与著作权法同样是第二性的,只有视角之差,而无层级之分。促使著作权法追随文学理论的观念缺乏充足的依据。
2.反对主体
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认为著作权法必须亦步亦趋地追随文化理论的潮流,却未曾考虑激进的“后现代著作权法”在保守的民法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后现代作者理论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巴特对“作者之死”的庆贺,还是福柯对“具有作者功能的话语”的辨认,都根植于一种反对主体性、反对人文主义的普遍理想。巴特“作者之死”的宣言“成了文本科学领域的反人文主义口号”(105)Antoine Compagnon,Literature,Theory,and Common Sense,Trans. by Carol Cosm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31.,通过将“文学”转化为一种没有固定意义的“写作”(writing),巴特拒绝了理性、科学、法律等带有固定意义的文本。(106)Roland Barthes,“Death of the Author,” in Stephen Heath,Image Music Text,California:Fontana Press,1977,p.147.而福柯对作者的怀疑更是紧紧依附于其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中提出的“人之死”结论:人是一个近期的发明,人终将消失。(107)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Oxford:Routledge,1989,pp.421-422.
显然,这些反主体理论无法与著作权法及其背后的民法一般理论相协调。著作权法将公共物品拟制为财产权客体的做法,或者说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物权式占有,反映的不是人与物的自然关系,而是人与人的法律关系:“对法律人而言,财产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指物、物质或其他东西,而是与物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或关系”(108)Jesse Dukeminier,Property (5th ed.),Los Angeles:Aspen Publishers,2002,p.40.。单纯的人与物的自然关系既无权利意味,也无法律意义,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为背景,才可能从事实状态中诞生出权利。(109)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9页。由此,即使在后现代作者观念诞生的数十年后,著作权法仍在运用各种手段维护人类的作者身份。例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曾经否认一只用相机自拍的猴子作为版权主体的资格;(110)Naruto v. Slater,888 F.3d 418,426 (9th Cir. 2018).美国版权局发布的《版权登记指南:包含由人工智能生成素材的作品》(CopyrightRegistrationGuidance:WorksContainingMaterialGeneratedbyArtificialIntelligence)再次澄清,宪法和版权法中的“作者”不包括非人类;(111)Copyright Registration Guidance:Works Containing Material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3-03-16,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3-03-16/pdf/2023-05321.pdf,访问日期:2023-08-17。《日本著作权法》更是明文规定,作品是“思想或感情的独创性表达”(112)日本《著作权法》第2条第1款。,而只有人类才可能具有思想和感情。可以想见,根植于“人之死”的“后现代著作权法”带来的将不是作者主宰权的消亡和所谓“使用者权”的兴起,而是作者、使用者,乃至整个民事主体概念的一并消失,以及一地稀碎的权利关系。
3.人文学科知识的线性进步与可证伪性
最重要的是,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假定了人文学科的理论演化必然遵循线性进步的理想。在批判者眼中,著作权法之所以必须紧紧跟随文化理论的步调,是因为后现代理论在转瞬之间便确定无疑地宣告了作者的消亡。换言之,新的理论能够直接使旧的理论成为一无是处的谬论:作者的观念史大致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浪漫主义(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而每一个新时期都是对旧时期的清算,每一个新出现的观念都彻底清除了旧观念的余绪。这种思维的背后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标准:“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113)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52页。在证伪主义者眼中,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虽然无法说一个理论成了真理,但通过批评和测试,我们能够得出当前的理论优于旧的理论,因为它能够经受住那些旧理论无法通过的测试。(114)Alan Chalmers,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4th ed.),Brisban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2013,p.64.
然而,人文学科的知识演化并不遵循线性进步的理想。在著作权法所规制的文学和艺术领域,“生产伟大作品的知识并不是那种随时间流逝而积累的,随代际继承而丰富的,能够轻易被后世所吸收的知识。”(115)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65.因而,在人文学科中往往很难找到一个旧理论被新理论完全证伪的依据。浪漫主义作者观的批判者没有说明,他们是如何得出浪漫主义作者观已经被后现代作者观证伪的。在巴特1967年发表《作者之死》(DeathoftheAuthor)的同年,赫施(E. D. Hirsch)也提出了“保卫作者”(In Defense of the Author)(116)E. D. 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1.的口号。显然,对作者主体性的捍卫,以及更早的浪漫主义作者观都不会如批判者所假定的那样,仅仅因时间的短暂流逝便被反对作者的理论彻底淘汰。
著作权法本身的发展不符合“可证伪性”标准的例证则是,虽然各国的著作权法已经明显倾向于提高市场交易的便利性,而非个人作者对作品的控制,但德国仍然坚持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的一元论:由于著作权中蕴含人格要素,作者不能通过转让或放弃著作权的方式实现财产利益。(117)《德国著作权法》,范长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39页。此外,著作权的扩张虽然早已偏离浪漫主义的理想,但浪漫主义作者观在当下著作权法中的功用仍然无法否认。主流的功利主义知识产权法通过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来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但仅凭这种“目的与手段”的思考模式很难完全推导出权利的正当性。(118)田村善之:《知財の理論》,有斐阁,2019年,第58页。因此,在另一个侧面,浪漫主义作者观的修辞能够弥补功利主义在著作权法正当性阐释方面的不足之处,因为“权利的确立需要社会认可,创造物原始地属于创造者,这是最容易被社会接受的产权起点”(119)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既然著作权法本身的理论演化,以及著作权法外部的人文学科知识均不依循新理论不断证伪旧理论的线性进步图式,那么法律思维和文学思维之间的龃龉便不是一个需要过度担忧的问题,著作权法也并无必要追随文化理论的步调。不过,在辨认并揭示批判者怀有的线性进步预设之后,本文的问题意识随之发生了一个自然转换,从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之因果关系的微观层面转向一个更为宏观的向度。在此,要问的不是著作权扩张的其他历史成因,而是修正主流观点背后的错误预设,探寻著作权扩张自身的结构。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替代线性进步与可证伪性的、解释著作权扩张一般性规律的理论呢?
四、规律的修正:著作权革命的结构
(一)功利主义的弱点与回应
对著作权扩张一般性规律的探寻始于对功利主义知识产权法的批判。在围绕知识产权法正当性依据的长期论战中,掌握话语权的是将功利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价值,以及继承功利主义传统的美国法经济学派所提倡的价值(效率、趋利避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财富最大化……)作为评价制度合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实证主义者。然而,在知识产权学界,这些价值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指责。反功利主义者牢牢抓住了功利主义自身的“实证主义把柄”:功利主义者虽然崇尚实证的经验科学,但他们恰恰未能提出能够证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有效率的证据。反对者正确地指出,目前我们并不清楚知识产权法是否对社会的整体福利带来了何种改变,无论这些改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换言之,我们无法断言知识产权法对于鼓励创作作品和激励工业创新而言是不是一个真正不可或缺的装置,也不知道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收益是否超过了创设和运作这个制度的巨大成本。(120)N. Stephan Kinsella,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Aubur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8,p.21.
在功利主义的弱点渐次显现后,为了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合法性,理论家们展开了不同的回应。其中,经济学家弗林茨·麦克卢普(Fritz Machlup)1958年为美国参议院所做的一份报告中的结论值得留意: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个作为整体的制度(与其具体的特征相对应)是好是坏,那么所能得出的风险最低的“政策结论”便是“应付过去”(muddle through),——如果已经与这个制度长期相伴,就一如既往,不要改变现状;如果尚未建立这个制度,就不要去建立它。(121)Fritz Machlup,An Economic Review of the Patent System,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p.80.
麦克卢普所谓“应付过去”的观念为著作权扩张的解释带来了什么样的教益呢?
(二)从功利主义到渐进试错
在回避功利主义的实证性缺陷的同时,麦克卢普的结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保守主义论断。在上述引文的开头,麦克卢普早已建立了“作为整体的制度”和这个制度中的“具体特征”的对子,作为对其结论的限制性条件。换言之,他并未置喙法学界对著作权法中细枝末节的具体规定进行改革和修正的努力,而是否认了法律整体的创设或取缔。在此,问题转换为“一般”与“特殊”的对立,即如何看待作为“整体”的著作权法与其内部的“具体特征”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个方面(一般),对法律整体理想和气质的追问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德沃金曾经提出一种“整全性”(integrity)的理念,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要求政府用一个声音说话,以原则的、融贯的行动对待它的全体公民,将它用于部分人的实质性正义或公平标准扩展至每个人”(122)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31—133页,第131—133页。。其中,“立法的整全性原则”要求立法者保持法律的融贯性,而“裁判的整全性原则”要求法律的解释者将法律看作具有融贯性的整体,并予以实施。(123)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31—133页,第131—133页。
第二个方面(特殊)指向了以成文法形式呈现的具体规定,但必须经由法解释,这些文本才能开口说话,这些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才能向我们言说自身的意义。法不是客观的存在物,我们无法被客观地引向其所命令之处,也不能以世界上那些物理的、自然的或是本质的存在物为参照,来判断法所处理的,或是积极创造出的现实是否正确。相反,我们应该将法理解为一种在其根本的不确定性之中创造客观性的系统,制造人工现实的“拟制”之手法才是法解释活动的真正意义。所谓的法解释不是一种为了在世界的某处找出某个与行为无关的“正解”的方法,而是“我们创造法律现实的行为本身”(124)大屋雄裕:《法解釈の言語哲学―クリプキから根元的規約主義へ》,劲草书房,2006年,第iii页。。
由此,根据法的“一般”和“特殊”两个面向,田村善之将麦克卢普所谓“应付过去”的态度解释为一种对现行的制度整体进行“渐进试错”的策略。渐进试错的方法论必须依赖法律中的隐喻,如著作权法中的“作者” “著作权人” “作品” “复制” “广播”等极为抽象的概念。(125)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学の課題~旅の途中~》,《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8年第2期。《荀子·正名》有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质言之,事物的命名没有本质意义,只有约定而成的意义。命名看似一成不变,但由约定所赋予的意义却紧随现实的需要而流变不居。当最初作品的约定意义尚且仅限于文学写作时,现实中出现了将音乐作为作品保护的需求,作品的约定意义便随之发生了扩张,将以乐谱形式记录下来的音符涵盖在内。(126)孙远钊:《版权拾轶: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扩展、限缩与平衡》,2022-08-15,https://mp.weixin.qq.com/s/C_kLDkzlyhUYOM pmm6lOhQ,访问日期:2023-08-13。当“视听作品”的约定意义尚且只能涵盖电影和电视剧、纪录片等类似电影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时,现实中出现了将电子游戏画面作为作品保护的需求,视听作品的意义便随之发生了转变,将电子游戏画面容纳其中。
对法律隐喻之约定意义的改变带来了著作权法的渐进式扩张。著作权法与其规制的行为之间必然有诸多龃龉,但凭借法官和法学家对法律隐喻之约定意义的转用、改变甚至重构,著作权法悬置了现实中表现得千差万别的利害关系,将诸种差异之物统摄在看似静止不动的制度中,由此生产出只是在“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假象,使渐进式的变化成为可能。(127)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学の課題~旅の途中~》,《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18年第2期。
(三)渐进试错、常规科学、科学革命
既然著作权的扩张是一种缓和的渐进式变化,那么其背后的结构便不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而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提出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在常规科学阶段,理论研究“牢固地建基于一个或多个过去的科学成就”(128)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8页,第131页。之上,科学共同体习以为常地运用既有的理论与概念,以共同的范式作为他们的研究基础,信守相同的规则和标准来从事科学。当反常出现之时,科学家不会因为这些现象而放弃、拒斥他们曾经仰赖的范式,而是“会对其理论作出大量阐述和特设性的修改,以消除任何明显的冲突”(12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8页,第131页。。换言之,既有范式的合法性不会立即被反常和例外证伪或革除,通过调整自身,范式将会对这些反常做出有力的抵御和反抗。常规科学阶段的基本工作便是在既定范式的框架内处理理论与反常之间的参差。
在常规阶段,著作权法以法解释的方法应对、化解、容纳了现实中的诸多例外状况。例如,当音乐喷泉的可版性问题出现时,法院通过对美术作品的解释,维持了著作权法“作品类型法定”的结构,以及鼓励创作的功利主义理念;(130)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等诉北京中科水景科技有限公司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1 404号。当人工智能创作对著作权法的常规形成挑战时,法院否定了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的可能性,认定对提示词进行独创性选择和安排的使用者为作者,坚持了人类的作者身份和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131)李某某诉刘某某案,北京市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京0491民初11 279号。在将著作权法的守备范围扩张至新出现的表达形式的同时,这些渐进式的解释构成了常规科学阶段的“解迷题”活动:不是开辟新的领域,不是旨在生产新奇的概念和现象,而是被法解释的规则和信念“限制可接受的解的性质以及求解的步骤”。(13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8页,第146页,第136—138页,第144页。
但是,仅凭常规科学阶段的渐进式变化,显然无法解释著作权扩张史中发生的诸多重大变革。对此,库恩对常规科学的下一个阶段,即“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观察提供了有益的洞见。当“科学共同体中一个狭小的部门逐渐感到,现有的范式不再能有效地用于它曾经引领的对自然的某一方面的探究”(13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8页,第146页,第136—138页,第144页。之时,理论研究便逐渐从常规科学转向科学革命。在此,反常的严重性已经超越常规阶段所能应对的程度,理论研究不得不面对危机和非常规的科学。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开始承认这种危机,并将其作为这门学科的根本要务。最终,随着危机中的学科范式重塑自身并转换为一个新的范式,危机也随之得到解决。(13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8页,第146页,第136—138页,第144页。
库恩强调了个人先驱者在新范式诞生过程中的作用,(13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8页,第146页,第136—138页,第144页。而著作权法在危机之后的范式转换起初也总是由发起游说的个人,或是创设先例的法院率先促成的。例如,在18世纪作者权利的合法性尚无太多头绪之时,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用父权和不动产的修辞推动了《安妮女王法令》的颁布;(136)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4—56页。在西学东渐时期,传教士林乐知曾经促成了清末著作权法制的建立和完善;(137)李祯:《林乐知的版权观念对清代著作权法制的影响》,《中国版权》2022年第2期。20世纪初,欧洲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代理人威廉·普拉格(Wilhelm Plage)对日本的海量侵权发起警告、收费、起诉和缔约交涉,直接迫使日本建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138)半田正夫、松田政行编:《著作権法コンメンタール3》(第2版),劲草书房,2015年,第864页。在Bleistein案中,霍姆斯仍在使用“复制件是个体对自然的个人反应,人格总是带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139)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188 U.S. 239,250 (U.S. 1903).这样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述,这种张力使该案很难成为美国版权法独创性的奠基案例,而Feist案则标志着新的独创性范式的正式确立。
五、余论:历史批判的意义与价值
对浪漫主义作者观与著作权扩张因果关系的解构,对后现代作者观背后预设的批判,以及对著作权扩张结构的洞见,至少将对著作权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如下三个影响:
第一,这些批判将会清除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与著作权法之间虚假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恢复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的生机。在网络文学研究中,每每有人认为,根植于浪漫主义作者观的著作权法早已无法回应反对高度独创性的“类型化”网文创作模式。然而,恰恰相反,著作权法非但没有怀揣浪漫主义的独创性天才理想,而且不会在“类型化”生产机制面前失去回应能力。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浪漫主义作者观与作者的私有财产权等量齐观,因为这种附会过度强调作者对作品的宰制,却遮蔽了著作权法对作者权利的诸多限制。网络文学语境中的“类型”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genre),而是指玄幻、仙侠、都市、悬疑、言情、穿越等由某些作品催生并固定、对其他后来者的创作方向产生限制的网络文学主题。这些“类型”显然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抽象思想,而非具体表达。即使隶属于同一“类型”之下的两部作品中的情节、设定等元素(如穿越小说中的主角总是会逆袭、修仙小说中的主角往往有一个法力高强的师傅)有相似性,只要使用的不是著作权人的独创性表达(如几乎相同的角色台词),就不会侵犯著作权。在判例法中,“类型”属于“在处理特定主题时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至少是标准的事件、人物或背景”(140)Atari,Inc. v. N. Am. Phillips Consumer Elecs. Corp.,672 F.2d 607,616 (7th Cir. 1982).,对既存“类型”的使用因思想/表达二分法中的“必要场景”(scènes à faire)原则而不构成侵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没有直接规定“必要场景”原则,但该原则仍是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应有之义。
第二,这些反思能够抵抗“使用者权”等激进的新兴权利立法论。使用者权试图将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上升为具有可诉性的主观权利,(141)刘银良:《著作权法中的公众使用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它将反对作者主体性的后现代作者观作为提升数字时代作品使用者地位的理论资源。(142)林秀芹:《使用者是版权制度重要的建设者》,2022-05-07,https://mp.weixin.qq.com/s/0X3HRVpkKYsMqR19eyrJwQ,访问日期:2023-09-20。在反思后现代作者观与著作权法的龃龉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使用者权只是一种将作者中心主义转换为使用者中心主义的尝试。如果合理使用等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被升格为主观权利,它将招致诸如“如果使用者因合理使用目的请求著作权人提供作品,著作权人必须无偿提供,否则将侵犯使用者权”的不合理结论。依托后现代作者观的使用者权不仅无法解决著作权法中固有的不平等性,还将建立更多的不平等性。
第三,这些重构将会使著作权扩张的解释从浪漫主义作者观的单行道转向多元主义。浪漫主义作者观不是对著作权扩张成因的唯一解释,后现代作者观也不是扭转著作权扩张趋势的合适方案,而只是著作权法的解构者牵强附会在著作权法身上的先入之见。在哲学、文学、技术和法律等范式的竞逐和争斗中,著作权扩张的历史早已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真相、一个现成的事实,而是一个蕴含着多重意义的图式。相应地,对这些意义的创造和诠释,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方案不是朝向某个被预先设定好的目标(如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作者观)的目的论演化,而将是“以阐述得越来越清楚和越来越专业化为标志”(14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张卜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