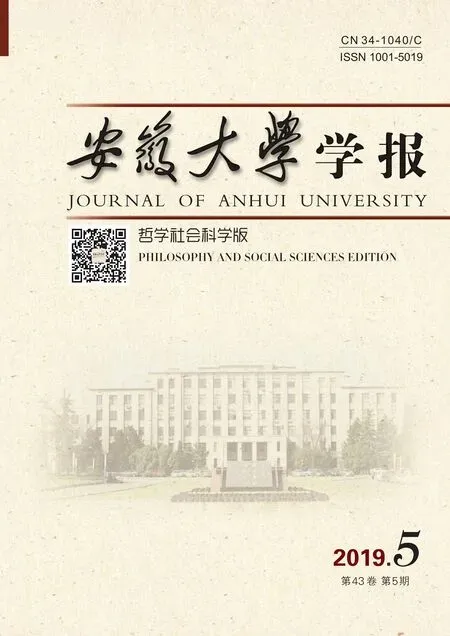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司法审查
周佑勇
裁量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做出一定的判断选择,但这种判断选择并非完全“自由”,否则构成一种裁量权的滥用。裁量基准作为控制这种“自由”滥用的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制,在规范裁量权行使的同时,也有可能因过分依赖于严格的规则而导致适用上的机械、僵化。这样的裁量基准之治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又怎能实现裁量的个案正义?因此,如何有效确认与审查构成符合个案正义的个别情况,或者说是识别脱逸裁量基准的正当理由,便成了裁量基准适用及其司法审查的关键。对此,本文拟作些初步探讨。
一、裁量基准法律属性的认知争议及其司法审查逻辑的分歧
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是否会对行政执法人员产生一种应予适用的法定义务,理论与实务界对此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备受关注的“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1)参见云南省文山县人民法院(2007)文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书;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8)文行终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陈娟:《驾车超速该罚多少?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惹争议》,《人民日报》2008年4月2日,第15版。中,原告周文明以实速90公里/小时在限速70公里/小时的省道上行使,被文山县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作出200元顶格罚款并扣3分的行政处罚(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周文明不服,认为根据作为裁量基准的《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标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处罚标准暂行规定》)第9条关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未到50%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之规定,被告按照法律规定所作出的200元顶格罚款显失公正,应予变更。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周文明的主张,认定《处罚标准暂行规定》对被告具有应予以适用的法律效力。但二审法院对此予以了否决,认为《处罚标准暂行规定》仅属省公安厅内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低于法律、法规,原审法院适用该规范性文件变更上诉人文山县交警适用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罚于法无据。那么,面对裁量基准的法律地位,两审法院为何会表现出如此截然对立的审查姿态呢?在此有必要考察其背后的认知争议及其逻辑分歧。
(一)认知争议:裁量基准法源论抑或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
实际上,周文明案中两审法院都将《处罚标准暂行规定》认定为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规范性文件。虽然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为规范性文件位阶的裁量基准并非法院直接的裁判依据,但根据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补充,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裁量基准,在满足合法要件的情况下,同样具有“可以乃至应当被认定”的拘束力(3)对于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49条则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然而,二审法院为何会在未判定裁量基准违法的情形下,仍然脱逸该司法解释的约束而直接否定裁量基准的适用效力呢?究其背后的缘由,唯有此处的“合法”依然存在“文义合法性”与“适用合法性”的区分(4)参见朱芒《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要件——首例附带性司法审查判决书评析》,《法学》2016年第11期。。前者意味着,法院对裁量基准单独审查后,如未确认违法就应该认定裁量基准的依据地位,合法的裁量基准具备司法审查的法源资格。但后者则与之相反,其表明裁量基准并无适用的拘束力,行政机关必须履行进一步的个别情况考量义务。
很明显,二审法院潜在地采纳了被告的抗辩主张(5)交警在上诉状中提出,近年来,文山县所发的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文山县2006 年因交通事故死亡57人,其中省道210 线上就死亡了25人。鉴于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法律赋予了交警自由裁量权。因此,文山县交警一直对超速行驶实施上限处罚。如果对同样违法处罚偏差过大,就是显失公平。,认为针对事发路段的特殊情况应该给予有别于裁量基准的处罚效果。因此,在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论者眼中,文山交警不仅可以而且应当甚至必须逸脱“处罚标准”作出本案处罚,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对于文山交警而言既是一种“权力”(裁量权)也是一种义务(个别情况考虑义务)(6)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周文明诉文山交警不按“红头文件”处罚案评析》,《交大法学》2011年第2卷。。在他们看来,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根本目的,在于行政机关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个案的裁量实现行政正义,因为“证成裁量正义的理由通常是个别化正义的需要”(7)[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一项初步的研究》,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页。,而“绝对规则的主要危险在于,即使一致适用也可能导致恣意的结果”(8)Abraham D. Sofaer, Judicial Control of Informal Discretionary Adjudication and Enforcemen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72, 1972, p.1327.。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普遍性意味着,“在逻辑上归结为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一般性否定”(9)王万华:《司法实践中的裁量基准》,《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由此可见,裁量基准对行政执法人员并无拘束力,行政机关仍应视情节行使裁量权,以补裁量基准的不足,否则,便有可能构成裁量怠惰;行政机关不得盲目引据裁量基准,而应留意裁量基准的内容是否已经适度地考量相关案件的情节轻重,以“善尽合义务裁量之本分”(10)参见林三钦《裁量基准与裁量瑕疵——兼评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3月份第2次庭长法官联席会决议》,《法令月刊》2016年第1期。。
但从一审法院审查的结论来看,法院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原告提出的关于裁量基准控权价值的主张(11)原告周文明提出的理由为: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不能等同于上限处罚,要根据具体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定。这个暂行规定,正是对交警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可以遏制交警乱罚款。。在法源论者看来,其一,从裁量基准设定的逻辑与目的上看,裁量基准是以规范行政裁量的行使为内容的建章立制,设定者往往通过将基层公务人员的执法经验,规整为程式化的、结构性的、相对统一的规则形式,表现为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系列具体的、细化的、操作性的约束性规则,其本质是试图对自由裁量权在给定幅度内进行“规则化”,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明细化的实体性操作标准(12)参见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而正是基于行政裁量的此种自我拘束原则之约束,文山交警应该按照裁量基准的处罚效果进行处罚,否则,把裁量基准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便违背了设立裁量基准制度的初衷(13)参见高秦伟《论行政裁量的自我拘束》,《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其二,从裁量基准设定的内容与过程来看,裁量基准一般通过限定行政裁量的真实目的、列举相关考虑的因素,以及对行政裁量的显失公正进行权衡等,因其内容正确性所具有的说服力,不仅为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酿造了客观化的操作(参照或依据)标准(14)参见熊樟林《裁量基准在行政诉讼中的客观化功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明,裁量基准本身就代表了行政机关对应当如何行使裁量权的规范表达,是对立法意图与立法目的进一步解释与阐明的具体化裁量过程。而且,即便裁量基准的原初可能只是来自几个一线执法人员的口头商谈,但其制定过程却也不乏公众参与、民主协商以及集体决策等正当立法程序的加持(15)譬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1条规定:“裁量权基准的制定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办理。裁量权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而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该《规定》第48条明确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并经制定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审议决定。”,同样具备制度性权威。从这个意义上看,裁量基准更像是为了贯彻执行法律而实施的“二次立法”(16)参见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二)逻辑分歧:裁量二元审查论与判断过程一元审查论
裁量基准法源论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认知上的分化,不仅导致了裁量基准效力有无的分歧,也进一步区隔了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逻辑进路。在法源论者看来,裁量基准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立法权,“不是法定标准的具体化,而是创设必要的决定标准”(17)[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95页。。因此,对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承认意味着司法介入行政裁量的排斥,其对应的是裁量问题的戒惧审查与法律问题的完全审查二元严格区分。当周文明的超速行为符合裁量基准的处罚规定,一审法院在确认裁量基准未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而具备合法性之后(法律问题/文义合法性),便直接认可了裁量基准的适用效力,屏蔽了对执法人员裁量权具体行使合法/合理的进一步审查。二元论所具有的特点便是针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往往采取独立心证式的严格审查,“在法律适用领域,行政和司法原则上不存在协调,只存在隶属关系;法院的法律观点居于行政机构的观点之上”(18)[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曼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1~342页。。
与之相反,在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者看来,裁量基准只是“法的具体化”。“法的具体化”意味着,对行政执法机关有拘束力的实际上是行政法律规范本身,而非裁量基准,上级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定。违反裁量基准并不必然导致该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即便周文明的违章行为切合裁量基准的规定,但二审法院并未放弃对执法人员裁量权行使过程的进一步审查,在确认行政机关具备其他合理考量因素(判断过程审查)而脱逸裁量基准的约束,给予周文明顶格数额的罚款之后,法院认可了文山交警裁量决定的合法性(适用合法性)。很明显,遵循判断过程式审查逻辑的法院降低了审查强度,“如别无其他违法情形,皆属合法,行政法院自不得取代行政机关,以自己之合目的判断另为裁量决定”(19)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209~210页。。因此,在二审法院看来,裁量问题也属于应受法院审查的法律问题,只是法院的审查应予以尊重而尽量避免判断代置。由于设定裁量基准的条件、依据、范围都与行政机关所执行的特定行政法律规范相关,而非行政机关自治的结果,那么在逻辑上,裁量基准与“裁量一元论”有着血缘关系(20)参见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当然,从“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的最终结果来看,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否定,意味着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论获得了确证,而一直被认为是自由法治主义以及概念法学遗迹的裁量二元论似乎已经走下神坛(21)参见王天华《从裁量二元论到裁量一元论》,《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裁量基准不应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针对行政裁量以及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应该放弃主张裁量与法律问题两分的裁量二元论,进而依照裁量一元论的逻辑进行判断过程的审查”(22)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但纵观我国整个司法审查实践,情形则并非如此简单。面对裁量基准的法律地位及其审查进路,我们既看到了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裁判依据”案例的大量存在(23)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也有在理论上基于裁量基准的规范特性,尝试建构符合实务具体特征的区分式审查技术方面的努力(24)参见周佑勇、熊樟林《裁量基准司法审查区分的技术》,《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即便是针对那些具有明显违背裁量合理性而被认为应以违法论处的完全限缩了裁量空间的裁量基准(25)参见熊鹰、李桂红《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溯源与模式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司法实践也是争执两端。譬如,在“王某某诉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案”中(26)参见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3)津法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书。,原告对被告以“超速50%以下一律处200元罚款”的裁量基准作出处罚表示不服,但法院以该限制性基准属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范畴,不予以审查。再如,在“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沈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沈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行政处罚案”中(27)参见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判决书。,原告认为被告适用的裁量基准中大量使用“50%、1倍、2倍”等限制裁量权的处罚基准,属违法创设处罚幅度,但该主张未获法院的支持,法院在确认裁量基准未违法的情形下,仍然认可了裁量基准的依据效力。而在“何庆友诉香洲交警案”中(28)参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城(行政)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交警则因使用“全省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进行罚款而被认定为裁量怠惰。事实上,观察域外情形,也可得出类似结论。譬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3号解释就曾针对《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罚锾标准》第5条,作出“仅以当事人接到违规举发通知书后之‘到案时间与否’,为设定裁决罚锾数额下限之唯一准据”,“纵其罚锾之上限并未逾越法律明定的裁罚之额度……与法律保留原则亦属有违”的解释决议。但面对类似的限制性裁量基准,台湾大法官会议释字第511号解释则作出相反的解释结论(29)该号解释阐明:“至上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行为人逾指定应到案日期后到案,另同细则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为人未依规定自动缴纳罚锾,或未依规定到案听候裁决者,应罚机关即一律依标准规定之金额处以罚锾,此属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就裁罚事宜所订定之裁量基准,其罚锾以额度并未逾越法律规定之上限,且寓有避免各行政机关于相同时间恣意为不同裁罚之功能,亦非法所不许。”。在美国,即使面对推崇备至的“谢弗朗原则”,最高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方面也还没有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和勤勉,有时赋予其较强的效力,有时又忽略该原则,有时则以奇怪而又矛盾的方式对待谢弗朗标准(30)参见[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5版),苏苗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如果从“实证”的角度观察,司法审判实务的复杂性似乎向人们宣示,裁量基准本身就包含了法源资格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的双重属性,只要各个法院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并无违法违规操作的情形,法源论以及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视域下的司法判决都可具备合法性。但如果从“法理”的角度观察,裁量基准内含的这种双重属性就始终存在着难以消解的逻辑矛盾,即如果承认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意味着对个别裁量正义的忽视,与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裁量的立法目的明显不符,此时行政立法还有取代议会立法的违宪嫌疑;而如果承认裁量基准的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意味着行政机关会受到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等基本原则的责难,同样难以获得合法性上的确证,且裁量基准的实际功能与现实意义将会付之东流。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之间(包括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逻辑),究竟谁具备法律上的规范性和正当性?抑或如果承认裁量基准的双重属性,那么又该如何防止陷入相对主义?
二、裁量基准审查过程中存在的悖论及其解决进路
裁量基准法律地位与司法审查的逻辑分歧及其司法实践存在的不同形态,表明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过程中存在着不同价值的衡量与取舍,而争议背后的复杂性,实际还潜藏着两种不同法律风格——规则取向与概念化的规范主义和功能取向与进化式变迁的功能主义——的角逐。而只有从规范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视角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量之间存在的悖论,使裁量基准获得规范正当性,个别情况考量也由此在双重偶联性结构中得以自我确证。
(一)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过程中存在的悖论及其规范主义解决进路
从“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的两审过程来看,文山交警的处罚决定并没有明显违反上位法律的规定,实际属于行政行为合理性判断的范畴。在这里,相比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本及其概念的解释,起作用的反而是各方主张的事实理由及其所具备的法律价值。但问题在于,并没有现成确定的可对两方价值谁高于谁进行对比衡量的“元”标准存在。即便基于法律解释规则进行认定,但“因为这些规则本身就是指导我们使用语言的一般化规则,而其所利用之一般化语言本身也有解释的必要,它们和其他规则一样,并不能够提供对它们自己的解释”(31)[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因此,面对实际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法官的决断就容易产生“一、二审法院对《暂行规定》效力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32)姜明安:《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批判性立场。
事实上,从法律论证二阶观察的角度来说,裁量基准司法审查过程中两审法院所支持的理由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悖论。二阶观察即为对观察(者)的观察。具体言之,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分别属于一审、二审审查结论证成的逻辑前提,但争议的消解往往还需要对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这两个前提是否正确做进一步论证,这就是前述两方分别列举的关于支持法源论和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的各种理由,且这种对理由的证立还可以(甚至必须)一直延续下去,即理由的理由的理由……。法院在对这些理由进行辨别的时候,总是以好的理由/不太好的理由这一区分形式进行筛选,但问题在于,当循环追问“好的理由/不太好的理由”本身是好的还是不太好的时候(二阶观察),悖论便出现了。如果这一区分是好的,那么只是同义反复;但如果这一区分是不太好的时候,就出现了好的理由是不太好的悖论。其实,裁量基准本身也存在着悖论,即只要追问裁量基准“有拘束力(法源论)/无拘束力(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论)”这一区分时,悖论就会产生。
在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世界里,自我指涉或者循环论证所形成的悖论一直都被看成是危险的,应被禁止的。严格的规则主义就认为,法律是由一套内容一致且无逻辑矛盾的规则所组成的规范体系。很明显,裁量基准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之间的矛盾对立,无法在规则主义那里被同时承认。而为隐藏此种悖论,学理和实务都在努力挖掘裁量基准应然的“本质面貌”,试图通过指涉到本体论的方式获取确定甚至唯一的答案。这种绝对主义的消解进路往往把希望寄托于某一个阿基米德支点——“那种在(法律)制度框架内似乎与一种规范且理性的人类利益秩序相符合的东西,也因此是一种无需作进一步证明的东西”(3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所有的答案都从该支点演绎出来,由此产生的结论就是客观的、绝对的。绝对主义要么将矛头指向更高等级秩序以避免自我指涉,要么借助某种程序达成的共识以避免循环论证,防止迷失在“明希豪森三重困境”(34)“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即每一个认识论者必然面对的三大难题,其一是无限倒推;其二是循环论证;其三是武断地终止论证。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代译序第1~2页。之中。对于前者,在凯尔森那里,通过“寻求法律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逻辑结构”(35)王轶:《法律规范类型区分理论的比较与评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我们看到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规范体系——“基础规范即诸规范之共同渊源,而构成某秩序之众多规范的统一性在于斯;而某种规范所以归属某秩序,亦因其可回溯至此秩序之基础规范”(36)[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81页。。而对于后者,在哈巴马斯那里,我们则看到了法律商谈——确定一个判断的有效性,“只能以商谈的方式,确切地说通过以论辩的方式而实施的论辩过程”(3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78页。。前者属于将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涵摄于“较高等”之下,最后大量的法律素材可归结到少数“最高”概念上的等级规范体系。这样,虽然保持了最大可能的体系概观性,同时亦可保障法的安定性,但它同样也有其缺陷,即只要在此等体系界限内,适切评价的问题将为适当涵摄的问题所排斥(3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17页。。其实,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也只是一种预设而已,它虽保证了法律体系内部逻辑的“无矛盾性”,但却不能满足形式逻辑的“完全性”(39)参见宾凯《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卢曼的悖论解决方案为考察框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同样,哈巴马斯的法律商谈也不过是将“不在场者理想化”,它只关注于社会维度,却忽视了时间维度,由于理想商谈情境并不是一种能够一直保持不变的状态,而这种变动性也就使得商谈并不总是能够获得理想的结果(40)参见杜健荣《法律合法性理论的现代走向——以卢曼/哈贝马斯之争为线索》,《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5期。。进一步而言,一旦对商谈规则进行自我指涉,理想商谈依然无法消解悖论。
可见,为了避免自我指涉所产生的悖论,试图通过向系统外寻找一个评价论证理由/标准的高级实体,以便在裁量基准的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的义务论之间作出一个非你即我的选择的努力,最终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无法实现的“理想化”境地,因为二者都存在着难以取舍的规范价值。这种将秩序类型、国家形式与法律概念之间进行二元对立的法律风格可归结为一种规范主义风格,在规范主义那里,“应然”被过分理论化了,显然无法与实践结合起来(41)参见[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0页。。
(二)裁量基准个别情况考量的双重偶联性及其功能主义解决进路
规范主义借由某种外在实体来消解裁量基准自身存在的悖论。如果说其解决进路的失败,意味着悖论本身并不是法律运行的禁忌或死穴,那么悖论反而是法律从其他社会子系统中分化出来并不断自我复杂化的动力机制(42)参见宾凯《法律悖论及其生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理论出发》,《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事实上,随着社会形态从身份到契约再到功能的转变(43)功能主义的转变,不仅影响到人们对法律自身性质的认知,也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产生了影响。参见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特别化的沟通循环已经从一般的社会沟通循环中独立出来,成为自创生的次级社会系统——再生产自己的要素、结构、过程以及边界(44)陈雨薇:《论反思性的法社会学的现实价值》,《东方法学》2018年第2期。,法律以其独有的合法/非法二值符码封闭地运行而成为一个自创生系统。所谓自创生系统,简单地说就是法律决定法律,“需要法律通过法律沟通使事情合法并以有关这些事情的沟通把它们包括进法律本身,这种法律沟通与早先的法律沟通相连并传达到将来的法律沟通”(45)[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相比于把静态的“规则”或意识化的“行为”视为法律系统基本单位的规范主义而言,自创生法律系统基于法律事件的沟通而让自己产生了时间维度,因此,“法律统一性不再意味着下级规则来源于上级规则的演绎,而是表明系统回溯既有法律沟通,制造新的法律沟通,在递回的网络中自我再生产”(46)参见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法学: 一种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
随着法律事件沟通的不断进行,法律系统逐渐产生了冗余和信息。其中信息是由于提供了有限或无限数量的其他可能性而具有意想不到的价值,也即差异或者多样性;而冗余则是产生于在自我生成的系统的运作中对信息的需要,一种运作减少了其他运作的选择价值,也即化简信息(47)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具体言之,面对行政裁量,法律系统同样总是以合法/非法二值符码不断地产生冗余和信息,裁量基准就属于冗余的范畴,个别情况则属于信息。在法律系统中,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二者彼此将对方看成另一个自我,而把主我看成异我,互相参照,交互作用,组成了一个“双重偶联性”的社会结构(48)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3页。。即只要开端一旦产生,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产生化约复杂性的效果。也就是说,虽然接下来的每一步,互动双方都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但此种选择必然受制于先前所做出的选择,而马上做出的选择,又会对未来的选择形成某种化约的关系——无论此种选择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如此一来,每一步选择都具有化约复杂性、重构交互结构的作用和效果(49)参见泮伟江《双重偶联性问题与法律系统的生成——卢曼法社会学的问题结构及其启示》,《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很明显,冗余/信息这个区分相互排斥但又相互设定,缺少了任何一方,另一方就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照的黑匣子中,无法作出任何观察(50)参见宾凯《社会系统论对法律论证的二阶观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就此而言,没有裁量基准,就没有个别情况,因为个别情况须从裁量基准中识别,“个案必须在其他决定之脉络中定位,‘以防止系统被去整合化为纯粹一定数量的个别决定’”(51)[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没有个别情况,也就没有裁量基准,因为裁量基准同样产生于处理个别情况的过程中。
由此观之,裁量基准其实同时具备了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的双重属性。作为冗余的裁量基准,维系的是法律系统当中的“同等情况同等处理”,因此,裁量基准对行政裁量的复杂性进行化简,从而提供了稳定的规范预期与融贯裁量决定的功能。其实,从功能主义观之,规范有效性的基础根本就在于期望领域的复杂性和偶在性,而其功能就在于对此进行化简(52)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页。。所谓“效力”,“涉及的是在系统中流通的、使运作互相联系的标志,这种标志使人们回忆起可以循环重复使用的运作的结果”(53)[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裁量基准因保持了裁量决定之间的融贯性/一致性便具有规范有效性。如此而言,尽管合法的裁量基准因不具备议会立法的授权而无法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其对行政裁量复杂性的化简,从而提供稳定的规范预期,将同样在法律系统中产生规范效力。当然,“同等情况同等处理”的言下之意即“不同情况应作不同处理”。但此时,作为个案裁量正义的实现缘由,并非个别情况考量义务论下的权利/义务“实体”,而是一种寻找理由和价值的偶联性程序“公式”(54)参见宾凯《卢曼系统论法学:对“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二分的超越》,《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从对于给付之“或多或少”的衡量,推移到在系统当中那个对于诸多决定之再生产的循环性网络里,什么事情应该被视为相等,什么事情应该被视为不相等(55)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社会中的法》,“国立”编译馆主译、李君韬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58页。。因此,行政裁量并非一味地体现为个别情况考量,裁量基准也非因消除了个别情况(违反区别对待)而不可产生规范效力,而是意味着,在行政裁量系统统一性的基础之上,基于一种有别于裁量基准的外在刺激,在具备否定裁量基准具体要件的条件下,方才构成个别情况。但此时,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的否定并非裁量基准效力的一般性否定,而只是表现为基于正当理由脱逸裁量基准适用的例外情形。换言之,“有无裁量的判断,并不能按照传统上的由概念法学所倡导的以特定的概念和法条来确定,而是需要根据行政机关的任务范围、行为性质以及具体的场合,一个个地得出结论”(56)参见[日]田村悦一《自由裁量及其界限》,李哲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由此可见,法律系统会不断产生悖论,但又不断通过否定非我而展开悖论、消解悖论,合法是对非法的否定而成为合法,同样,个别情况也是对裁量基准的否定而成为个别情况。这种不断否定、不断产生沟通的系统论既超越了绝对主义的先验性困境,同时又避免陷入“怎么样都行”的相对主义。相比于在规范与事实之间二元严格对立的规范主义,系统论功能主义显然让裁量基准产生了规范与事实的双重维度,它关注的是行政裁量以及裁量基准“如何变得可能”,而不是基于某种纯粹的概念或本体论上的“是什么”进行探讨。因此,尽管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因不具备原始立法权而无法获得规范意义上的直接法律效力,但在系统功能主义那里,只要裁量决定(包括行政立法)与司法审查一直沟通下去,裁量基准就具备正当性。只是因需要考量裁量正义的实现,在满足特定条件下裁量基准可脱逸适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相对性的法律效力(57)参见周佑勇、周乐军《论裁量基准效力的相对性及其选择适用》,《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由此而言,在“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中,一审法院并不是因为承认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而违法,除非裁量基准明显超越上位法律的规定或者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而是因为缺少了对个别情况进一步考量的实际过程,造成了对个案正义实现可能性的忽略;同样,二审法院也并非因为履行了判断过程式审查就没有瑕疵,因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院并未阐明对个别情况考量而脱逸适用裁量基准的具体理由(或者本身还不构成判断过程合理式审查),造成了说服力上的不足。因此,在“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中,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的否定性,也即何为相对于裁量基准的个别情况。
三、相对于裁量基准的个别情况考量及其审查规则
当法院对应否适用的裁量基准进行文义审查确定合法性之后,裁量基准便获得了一种“应当适用”的约束力,如果没有个别情况或者个别情况构成的理由不足,对裁量基准的脱逸适用便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如何有效识别相对于裁量基准的个别情况,直接决定着司法审查的强度及相关规则。
(一)个别情况构成的识别标准
在内外各种复杂的因素之间,如何有效识别出个别情况?根据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否定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事实要件的否定与效果要件的否定。事实要件的否定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正确、不全面、裁量决定证据不足,导致适用了错误的裁量基准或者错误地适用了裁量基准。其中,一方面表现为行政机关未全面认清事实,应该适用A基准却适用了B基准或者其他法律规定。譬如,在“韩某诉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案”(58)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琼行终字第45号行政判决书。中,被告行政机关查明原告韩某销售假电线产品,属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认定韩某违反《产品质量法》第39条关于“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规定,并按照《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试行)》之规定,将韩某的违法行为认定为该基准规定的最严重违法情形而处以顶格3倍罚款。但法院基于韩某涉案的413卷电线尚未售出,认为韩某的行为仅构成裁量基准所规定的较重违法情形,处以3倍罚款显失公正,遂按照基准中较重违法情形判决变更。很明显,“涉案的413卷电线尚未售出”这一事实构成了脱逸严重违法基准的个别情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行政机关未履行调查案件事实、客观评价相对人行为的职责,径直适用了裁量基准,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定义务,导致适用裁量基准错误。在“韩迎春不服淄博市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59)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3行终6号行政裁定书。,当被告直接根据《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9条关于“强拿硬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300元以上的”属于“情节较重”之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法院则查明,被告并未委托周村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被损财物进行财产损失鉴定,直接适用裁量基准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违法决定。显然,在这里,“行政处罚应基于对财产损失进行鉴定的基础上”之职责事实,构成了否定裁量基准适用的个别情况。
当然,即使行政机关正确地查清了案件事实,但如未全面考虑裁量情节,同样可能会产生违法的法律效果。在“周文明诉文山交警案”中,虽然原告周文明的超速行为无可争议,但事发路段的特殊性是否构成顶格罚款的裁量情节则是案件争议的关键。裁量情节其实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以裁量情节是否具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60)参见周佑勇《论行政裁量的情节与适用》,《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法定情节对行政机关而言是一项必须考量的法律义务,行政机关未履行将会直接产生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法律效果。因此,个案中如果出现的法定情节未被裁量基准所包容,就属于个别情况,行政机关必须脱逸裁量基准的约束而另为裁量决定。法定情节虽可通过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或原则性条款进行综合推断,但多来源于法律具体条款的明确规定。例如,在“胡向青与惠民县公安局胡集派出所行政处罚案”(61)参见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滨中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胡向青与第三人赵延星因纠纷殴打造成原告轻微伤,被告认定第三人属于情节较轻之情形,根据《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3条给予第三人500元罚款。但法院查明,第三人赵延星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此时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35条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五)刑罚执行完毕、劳动教养解除三年内,或者在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认定被告直接适用裁量基准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案中的“再犯”情形就属于行政机关必须予以考量的法定情节,构成了相对于裁量基准的个别情况。
不过,相比于法定情节个别情况的构成主要基于法律适用技术进行认定而言,酌定情节虽然同样属于行政机关应该考量的义务,但该情节是否构成个别情况而可脱逸裁量基准的约束,则需要考量该情节对裁量结果影响的程度进行认定。这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事件起因、违法情节、性质、后果、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相对人违法后的态度和表现及社会影响大小等因素。因此,法律原则的均衡技术尤其是借助比例原则便成为酌定情节认定的主要方法。譬如,在“唐中华与邵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62)参见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5行终93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唐中华遂与戴某发生口角,先后用本地脏话两次谩骂戴某,被告邵阳县公安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项的规定,作出对唐中华行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但法院认为,唐中华谩骂他人系在其与他人发生言语冲突的过程中因激愤而为,在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时明确表示愿意向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认错态度较好,在唐中华的违法情形依法可选择处以罚款或者处以行政拘留的情况下,考虑唐中华作出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认错态度,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处罚过重,以对唐中华予以罚款处罚为宜,作出了变更判决。
(二)个别情况考量的审查强度
在上述四种个别情况认定的标准当中,除了针对酌定情节法院往往给予行政机关较大幅度的裁量空间之外,其他三种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或者事实认定范畴。因此,法院一般以“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作为判决理由,往往具有相当严格的审查强度。其实,这源于对酌定情节的审查主要从裁量结果的公正性(63)参见余凌云《论对行政裁量相关考虑的审查》,《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而非法律适用或事实认定的角度进行判断。因为并非任何酌定情节的相关因素均可构成个别情况,如果行政行为考虑了某种因素和不考虑某种因素对其结果无任何影响,那么,这些相关考虑就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因素即使存在也是无任何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酌定情节的相关考虑必须是一个在行政行为作出时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行政行为过程的影响上,更为重要的是对行政行为结果的影响上(64)参见张淑芳《行政行为中相关考虑的价值及基本范畴》,《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除非法院认定那些相关的因素对裁量结果的公正性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它们,将会导致裁量决定极为不合理、不公正,此时相关因素才构成个别情况(65)G. D. S. TayLor:Judicial Review of Improper Purposes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35, 1976, p.291.。因此,法院一般以“显失公平”作为判决理由。而显失公平行政行为的逻辑前提,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自由裁量权(66)参见关保英《显失公平的行政行为研究》,《法学论坛》2017年第2期。。如果不能调查到证明裁量滥用的重要证据,就应当推定裁量权的行使正当,除非有明显的自利或他利倾向(67)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拖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0页。。这意味着,酌定情节个别情况考量的审查强度一般低于其他三种认定标准。
由此可见,不同的判断标准因适用的方法、技术不同,法院审查的强度往往就不同。但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裁量基准规定的内容与个别情况之间的包容性,或者个别情况对裁量基准的否定性,影响法院审查强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法院不仅需要考虑法律条文中法律概念的明确程度,也要综合考虑立法目的、权利保障甚至社会影响等。此外,司法审查中有时还会充斥着国家政策、常识等因素的刺激。因此,真正决定司法审查强度的,并不完全取决于效果要件与事实要件的规范位置,而是对各种影响因素与理由的综合权衡。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公正并不能通过司法自身予以证明,司法公正必须要考虑社会认同这个基础方面(68)参见李瑜青《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价值、内涵和标准》,《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其实,裁量权的赋予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运用,不在于使用不同的表述就可以把规制内容的空白或是置于构成要件部分或是置于法律后果部分的可能性,而是在于待适用规范的同种性和其适用的模式一致性:基于各种实际状况对原则性主导思想进行关联化的具体化(69)参见[德]卡尔-埃博哈特·海因《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判断余地——一个教义学问题的法理思考》,曾韬译,《财经法学》2017年第1期。。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往往也总是存在着主观评价的余地。因此,在“华源公司诉商标局案”(70)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177号行政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2345号行政判决书。中,面对争议的“同一天”是否可以按“30日”处理,法院并没有因行政机关在其制定的过渡期间具有诸多合理的考量因素(71)本案中,被告国家商标局主张的合理判断理由有“为了顾及服务商标使用的现状,给商标注册申请人以必要的准备时间”“一贯的做法”“撤销过渡期的规定,将会影响相关申请的后续处理,严重损害相关申请人的信赖利益”等等。而予以尊重,而是继续坚持了“同一个自然日”的独立判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合理判断并不能径直取代上位法律已有的明确规定,在民众的合理预期、权利保障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效果等与行政机关的合理判断之间,法院做了相应的权衡。而“施某诉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罚案”(72)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6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中,对于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赌博违法案件的量罚指导意见》将“在个人赌资无法确定时,按照参赌款物价值总额除以参赌人数的平均值计算,认定人均赌资”的做法,则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法院通过综合考量2005年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内容与精神,以及人们对赌博日常经验知识的了解,获得了目的上、体系上与常理上的合法性判准(73)参见殷勤《对赌资较大、情节严重行政裁量基准之司法审查》,《人民司法》2017年第2期。行政机关对类似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解释获得法院尊重的案件,还有“赵忠述案”中对《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参与“地下六合彩”“赌球”“扳砣子”“斗牛”“三跟”“推牌九”等方式的赌博,单注金额二十元以下或者全场输赢二千元以下的情形认定为赌博的“一般违法行为”,参见湖南省冷水江市人民法院(2017)湘1381行初61号行政判决书;“杨世锟案”中对《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将(一)以个人赌资200元至500元为起点;(二)个人单次(局)赌博输赢额20元以上的情形认定为“赌资较大”,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行终391号行政判决书。。可见,法院对裁量基准内容的尊重与适用,意味着实践中对具体个别情况的否定。
四、结 语
随着公法风格由规范主义向功能主义的转变,行政裁量的治理也由规则治理走向原则治理。裁量基准作为控制裁量权滥用方式的一种,在限制与规范裁量权行使的同时,也一并产生了阻滞个别裁量正义实现的可能性。在系统功能主义那里,裁量基准存在着法源地位与个别情况考量义务的双重属性,二者相互映照,彼此否定,共同促进裁量基准的不断生成与发展。面对裁量基准的双重属性,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由此也应具备一种双重视角:对裁量基准法源地位的承认,必然是对个别情况构成的否定,抑或是相反。否定的过程,其实质是各种理由的对比与权衡的过程。从系统论角度而言,理由在认知意义上的开放性决定了裁量基准的开放性,但其内部各种因素运作的统一性又决定了裁量基准在规范意义上的封闭性。正因为裁量基准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特征,形成了司法实践形态各异的审查结论与论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