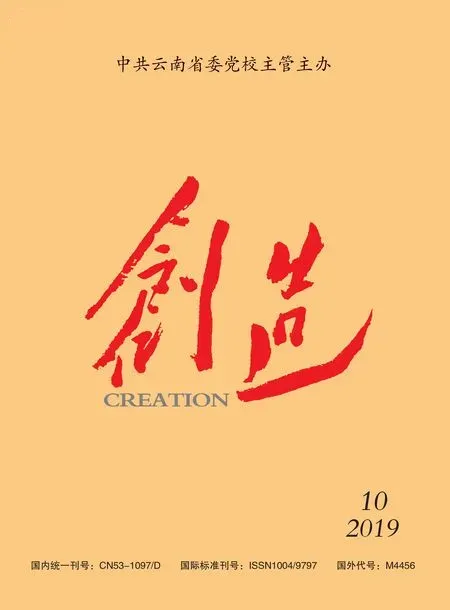关于“暹罗”改称“泰国”历史问题的一点思考
——从人类和语言学角度
2018年11月《读书》 杂志刊发了葛兆光先生《当“暹罗”改名“泰国”——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1]一文,其中关于“暹罗”改称“泰国”诸问题,正好是笔者平时关注的,遂行之于文,不揣谫陋,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泰人的起源
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关于泰人的起源和泰国早期历史的描述,常常停留在神话传说和中国保留的零星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因此很难确定泰人是泰国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按照泰族的一支老挝老族的传说,祖先坤博隆骑着白象,带着王者的仪仗,来到奠边府附近的孟天。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条瓜藤上挂着两个大南瓜,当南瓜被劈开时,立即有男人、女人和各种动物、植物和器具出现,因此繁殖了这个世界。坤博隆有七个孩子,他把他管辖的地区分封给他的七个儿子,逐渐建立了老泰民族的国家。
泰国历史学家姆·耳·马尼奇·琼赛认为坤博隆即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皮罗阁,泰人正是从中国南诏逐渐移居到今中南半岛地区的[2]。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基本是反对的,南诏是中国云南彝族、白族建立的政权,不论从人种还是语言上都跟老泰民族有较大差异。但中国学者和泰国学者基本认同泰老民族早期曾经在中国南方同其他民族有过较长时间的混居期。
笔者曾经在老泰地区生活过较长时期,据笔者观察,老挝农村的一些生活习俗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有类似之处。比如,我国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有用芦管或细竹管插入土法酿造的坛子酒中聚众饮酒的习俗。1930年庄学本在岷江上游拍摄到当地戎人(即羌族)饮酒的场景:“戎人饮酒,并不用菜肴,也不用酒杯,坛中的糟粕也不去掉,将空心竹子插入糟粕里,每人衔着一枝,慢慢的抽吸。不到半点钟酒吸进了,将锅子中预备的开水冲下去,酒味当然淡一点,然而还很芬芳,他们在高歌一曲之后,再来咂酒。”[3]
这种习俗在今天的老挝农村还十分常见,也是他们待客聚众娱乐的一种方式。坛子酒是用糯米酿制的,饮用时打开封泥,插入许多竹管,一人或数人围坛吸吮,边喝边谈,并不断地向酒坛中加清水。喝醉了还会又跳又唱,直到酒干尽兴而归。
我国历史书籍中有对这种习俗的描写,称为“鼻饮”。如, 《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4]李延寿《北史》:“僚者(即老挝老族的前身,笔者注),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其口嚼食并鼻饮”[5]。陆游《老学庵笔记》 对这一民俗记载则更为细致:辰、沅、靖州蛮……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6]。
笔者认为:鼻饮之说未必可信,众人聚集在一个小罐子周围饮酒,由于手握竹管,可能会挡住口鼻,让人产生用鼻子饮酒的错觉,汉族观察记录者可能缺乏“了解之同情”,不免大惊小怪,而以一种猎奇的心理记录下来。但这一历史记录,也为我们证明老泰民族曾经在中国境内混居提供证据,要不然今天看起来距离相隔较远的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的老挝怎么会有如此类似的生活方式。
大约在八世纪左右老泰民族开始移民和定居今天中南半岛的时候,这里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孟高棉人的统治下。历史上老泰民族应该是并非情愿地生活在孟高棉霸主的统治下,而是因为太过弱小而不能有所作为,直到十三、十四世纪,老泰民族才逐渐摆脱孟高棉霸主的统治,成为今天老泰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主人。1238年坤斯里因塔腊提在泰国素可泰建立素可泰王国,1283年孟莱王在泰国清迈建立兰纳泰王国,1373年,法昂王在老挝琅勃拉邦建立澜沧王国。1296年,素可泰王国第三代王兰甘亨大帝创造了现代泰文和老挝文的字体,老泰民族才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
传说澜沧王国的法昂王是坤博隆的第二十三代孙,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曾和父亲一起被放逐到高棉的吴哥王朝,在那里娶了一位高棉公主,并从那里引进了小乘佛教。坤博隆的传说是十四世纪时老族人统一了大半个中南半岛,建立了强大的澜沧王国时才产生的。所以其可信度还存疑,但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泰老民族是从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渗透至中南半岛今天的老挝、泰国地区的。在我国西南、两广地区,还有很多原始壮侗语族(泰语、老挝语属其下语支)的底层残留,这也是语言学家已经证实的事实。
在今天的老泰地区,远古时代就曾经存在着多个城邦国家,记载在中国的文献中,如林阳、盘盘、金陈(金邻)、赤土等,但这些城邦是否是老泰民族所建立的,由于语焉不详,仍然存疑。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国文献中存在的“掸国”,关于这个“掸国”,很多历史学家把它看作是一个以泰老民族建立的早期城邦国家,如,葛兆光:“如果追溯早期历史,他们(指泰族) 就是生活在这一带的。”[1]但也有很多研究东南亚的学者认为这个“掸国”并不是泰老民族建立的国家,其地理位置不在缅甸,也不在老挝,与泰国和越南更没有关系。如,江应樑《傣族史料及东汉掸国的商榷》[7],何平《一个涉及中国和中南半岛诸国多民族历史的讹误—关于“掸国”的最新研究与结论》[8],范宏贵《关于掸国的问题》[9]等已有详细论述,资不赘述。笔者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多年,对于“掸国”是泰老民族建立的早期国家一说也颇存疑。我国早期文献中关于“掸国”的记载,兹录如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10]
这里明确指出使者自言为海西人,范晔接着解释“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正是范晔的这个解释让后人对“海西”和“掸国”产生了迷惑,“掸国”和“海西”是什么关系?范晔记载了表演者自称海西人,可能是实录。但“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显然不是表演者的自述内容,而是范晔对海西和掸国地理关系的解释,是范晔根据史料或当时的地理知识做出的判断,而“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的时候“海西”和“掸国”的关系,我们并不得知。
按常理推断,使臣出访带去的应该是本国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一是展示本国的艺术特点和水平,二是表示亲善友好,就是艺术水平一般的国家也会这样,不会招募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去充门面,这样做有失体面。所以笔者认为这个代表掸国去表演的海西人可能是加入了掸国国籍,或是海西统治下“掸国”人,即当时“掸国”隶属于“海西”, 《后汉书·西域传》 记载:“大秦国一名犁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10]由此笔者推断“掸国”和“海西”不会相距太过遥远,文化艺术应该比较相近,要不然这个“海西人”也不会代表掸国去表演。
另外关于这次朝贺《后汉书·陈禅传》 亦有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日:‘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日:‘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日:‘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 云:以《雅》 以《南》,《株》 《任》 《朱离》’。 今掸国越流沙, 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10]
当时,汉安帝率群臣观看演出,谏议大夫陈禅认为不妥。尚书陈忠说,这些人“越流沙,逾悬度”,不远万里而来,理应受到欢迎。按照《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的解释,流沙(今我国西北沙漠地带)和县度(今印度)都在西域,与现在的老挝泰国所在地相距甚远。而且就使者团表演的内容来说:“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跳丸,数乃至千”,在现有老泰民族的艺术形态中也难寻踪迹,反倒类似于早期欧洲或阿拉伯国家的艺术形态。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汉代史籍中记载的这个“掸国”可能不是老泰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不能简单地将它和现在缅甸的“掸邦”(老泰民族的一支)对等起来。中国古代对外国地名的记录常采用音译的方式,早期“掸国”和现在“掸邦”采用同一个汉字记录,可能仅仅是偶然,而由此推定“掸国”是老泰民族早期建立的国家一说值得商榷。
二、关于暹罗的来源
暹罗是中国人对古代泰国的称呼,暹罗是暹和罗斛两国的合称。罗斛国在我国宋代至元代初期典籍中有所记载,是建都于今泰国华富里的孟人国家,暹国指十三到十四世纪初在泰国境内的素可泰王国[11]。1296年,周达观作为中国元朝使团的一员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写了《真腊风土记》 一书,书中把真腊西边的邻邦素可泰王国称为“暹罗”。这是中国史籍中首次用“暹罗”来称呼泰国地区的国家。但伯希和认为这是元末明初删订本书者误改“暹”为“暹罗”,因为周达观所在时代,罗斛还没有并入暹国,同书中还有“暹人”“暹妇”“暹中”等称呼[12]。1349年,南方的“罗斛国”(即建都阿瑜陀耶的大城王国) 征服了“暹国” (即素可泰王国),由于两国已合并,中国遂以“暹罗斛”来称之。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阿瑜陀耶国王为“暹罗国王”,于是“暹罗”这一名称正式固定下来,成为中文语境下对泰国的称呼,汉字文化圈其他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也采用“暹罗”之称。
但泰人似乎并不称呼自己为“暹” (Siam),“暹”最早见于十一世纪一块占婆碑铭中,其中提到暹人奴隶。12世纪柬埔寨吴哥窟石刻中也提到了暹人士兵[2]。暹粒是今天柬埔寨的一座城市,十三世纪时数遭暹军袭击,故其城名在柬埔寨语中意为“战胜暹人”。可见“暹”是外界对泰人的称呼,可能还带有贬义色彩,一说系梵语,有两种意思:黑色或黝黑皮肤,黄金或金黄色。泰国学者姆·耳·马尼奇·琼赛则认为:暹是孟高棉人对当地被征服的泰族的他称,意思是皮肤黝黑的土人,这种称呼后来又被由孟高棉人征服的马来人带给了欧洲人。因为在东南亚大陆的居民中,欧洲人首先跟马来人接触[2]。
笔者认为琼赛所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在现今老泰语言中,称被老泰民族征服的原著少数民族为“卡”,“卡”即老泰语中“奴隶”的意思,这跟缅甸人称其境内的泰人为“掸人”一样,“卡”和“掸”都非自称。
笔者认为“暹”可能是“掸”的同名异音,“掸” (Shan) 在缅甸语中的发音近似“暹”(Siam),是孟高棉民族对老泰民族的他称,将缅甸的“掸邦”和上文提到的中国古史中的“掸国”联系起来,证据不足。“掸” (Shan) 的出现年代不明,可能远晚于《后汉书》记载的时代。
泰老民族一般以族名自称,如老挝人自称“昆老”,泰人自称“昆泰”,“昆”即泰老语“人”的意思。又一般以都城来称呼本国,如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等。1855年泰国与英国正式开放通商的《鲍林条约》中,曼谷王朝以“勐泰”自称,“勐”即泰老语中“城邦”的意思,1292年泰国兰甘亨大帝石碑上就曾写到“勐泰的人民是博学、勇敢和坚强的人民。”但1856年批准《鲍林条约》 时,曼谷王朝出于适应国际习惯的目的,采用外界的称呼“暹”(Siam),这才成为正式国号。在泰老印度化过程中,还引用梵语“巴特(国家)”一词自称,泰国称“巴特泰”,老挝称“巴特寮”。
泰人自称“泰”也非自古就有,西方学者认为“泰”有自由的意思,是泰人摆脱孟高棉统治后的族称。在我国宋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泰”这个自称,只有泰人的一支老挝人,“哀牢”“僚”这类族称。泰人独立后,自称“勐泰”,在泰语中“勐泰”意味着“勐伊沙拉”,即自由泰国之意。老挝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时期,也有“伊沙拉”组织,即自由老挝组织。
有趣的是,在今泰国有很多以Buli(汉语写作武里)结尾的地名,Buli是梵语词,是地名后缀,表示城市,如碧武里府、叻武里府、巴真武里府、北碧府、春武里府、素攀武里府、占塔武里府、暖武里府、华富里府(Lopburi)、信武里府、吞武里府。老挝万象附近也有沙耶武里、占塔武里。泰老本民族表示地名的词语,主要是“勐”,如老挝的勐赛、勐蓬洪,“万”,如老挝的万象、万荣,“清”,如泰国的清迈、清盛、清莱、清孔。
以Buli结尾的地名多集中在泰国中部,在老挝和泰国东北部却很少见。由湄公河孕育的泥沙平原为泰国中部提供了国内最肥沃的土壤,是盛产稻米的主要区域,这里原属罗斛国,这正合我国历史典籍的记载:“暹与罗斛,古之扶南国也。暹国北与云南徼外八百媳妇接壤,东界安南,西北距缅国。罗斛,在暹之南,滨大海。暹土瘠,不宜稼穑。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人仰给焉。”[13]罗斛是孟族人建立的国家,孟人是早于泰老民族先印度化的,但泰人逐渐在这片土地上战胜了统治者孟人,成为罗斛的主人。但地名并没有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改变,仍然保留在语言中。
三、关于泛泰主义和暹罗改名
20世纪30年代以来,暹罗掀起泛泰主义思潮,暹罗军人銮披汶·颂堪在1938年成为总理。华人后裔銮威集极力鼓吹以族名“泰”来取代“暹罗”(Siam或Sayam)国名,强调泰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之一,为了联合他们和集中全体泰人的意志,国家应该改名。1939年5月23日,暹罗政府通过决议,拟改国号为“泰国”,当局的解释是:“暹罗”(Siam或Sayam)是由外国语音译而来,并非泰人自称,泰人自称为“勐泰” (即泰国);“Siam”容易让人误以为有一个名叫暹罗的民族。1939年6月24日,銮披汶政府在立宪革命中将Siam变成Thailand,就中文而言,则是从“暹罗”变成“泰国”。泛泰主义和同时期德国、日本的种族主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泰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亲日政策,当日本渐落下风时,銮披汶政府于1944年倒台,泰国又投向反法西斯阵营。由于“泰国”国号是泛泰主义的产物,在1945年2月又恢复了“暹罗”的旧称。1948年,銮披汶·颂堪再次登上首相宝座,1949年5月11日第二次改国号为“泰国”,此后再也没有变动,延续至今。
泰国从来就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内政外交的国家。拉玛五世及之后的统治者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使得泰国免遭殖民命运。与其像中国和缅甸一样被炮火打开国门,不如主动向列强示好,1855年暹罗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随后又拉拢法国对抗英国,1893年的《法暹条约》 让泰国付出了湄公河以东的大片领土,即今天的老挝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成为英法两国利益的缓冲地,一直保持着国家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泰国又重演游弋在大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先是利用日本抗衡英法,随着日本败局已定,泰国军政府倒台,左翼领袖比里帕侬荣领导自由泰运动,迅速示好英美,避免了泰国被作为战败国处理。
泛泰主义的提出是其民族主义高涨的反映,但提出者似乎忘记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界限和边境是完全重合的这样的简单道理。当泛泰主义者把中国境内的壮傣等民族纳入其大泰圈内,“暹罗”改名为“泰国”时,中国正处于中日战争的深渊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有所警惕而做出各种反应。民族主义的高涨或低潮从来都是跟其特定时代背景相联系的,当我们跳出那个时代的背景,历史研究或许能还原其真相。
“暹罗”改名为泰,看起来只是字词的互换,但语言从来都不是如此单纯。在中国的语言学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台语”,这个台语,不是什么台湾话,而是指我国境内的傣族,以及境外的泰国、老挝等语言共同构成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泰语支”。为什么中国不用“泰”这个字眼,或许就是特意规避“泰国”的“泰”。当语言被政治和时势染指的时候,语言也就有了特殊的含义,而变得十分有趣了,“暹罗”改名为“泰”如此,“台语”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