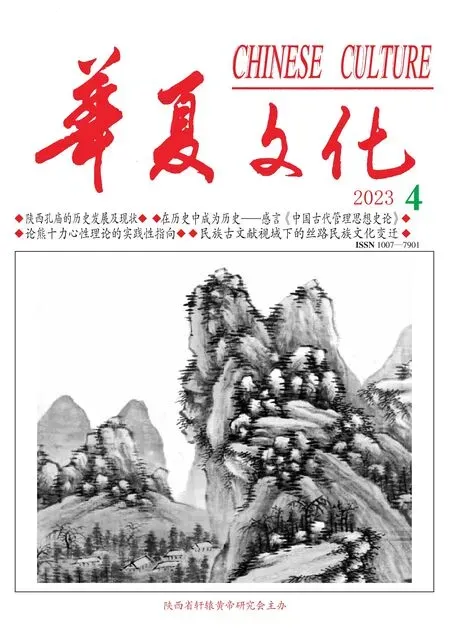郭象“逍遥”思想探析
□王 涛
郭象的《庄子注》是建立在庄子的内、外、杂篇的基础上,进行的注释和理解。钱穆认为,庄子的外、杂篇并非庄子本人所作(钱穆:《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55页)。庄子内篇不谈论“性”的问题,而郭象的《庄子注》是在以内、外、杂篇为整体的思想上,将外、杂篇中的“性”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郭象通过“六经注我”的诠释来发展自身的哲学思想,通过“独化”的思想使得万事万物都达到“适性”逍遥的境界。本文欲通过探究“独化”“自生”的思想来分析郭象“逍遥”思想的哲学基础,以及“适性”逍遥思想的具体内容。
一、郭象“自生”思想的起点
冯友兰提出魏晋玄学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贵无论,第二阶段是裴頠的崇有论,第三阶段是郭象的无无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42页)。汤用彤也通过正、反、合的思想解释魏晋玄学的发展,王弼注《老》而阐贵无之学。向、郭释《庄》而有崇有之论。皆就中华固有学术而加以发明,故影响甚广(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2页)。通过正、反、合的思想阐发魏晋玄学的思想脉络是否得当?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视作对王弼、何晏“贵无论”思想的对立,而将郭象的思想视为否定之否定,这种解读方式难免会落入惯性的思维习惯,尤其是将裴頠的“崇有论”看作“贵无论”的反题。裴頠的“崇有论”并不只是专门反对某一家的思想,而是对整个玄学风气的批判。因此,郭象的思想也不能简单看作对王弼“贵无论”的反动,实际上郭象的哲学思想是以王弼的“贵无论”为起点,并进一步阐发王弼思想中不彻底的一面的。
魏晋玄学自王弼始,就不断思索“黜天道而究本体”的问题,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完成了从汉代宇宙论到本体论的思想转化。在王弼看来,本体性的“无”已经没有汉代宇宙创生性的含义,他提出“崇本息末”的概念,这也是对“以无为本”的深入阐发。所谓的“崇本息末”就是从本体与现象、主宰者与被主宰者的角度去看问题。在这里,王弼并不是将本体与现象所割裂,而是认为本体比现象更为重要,不能重末轻本。王弼认为“无”是构成和支配万物的根源,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17页),这里的“无”就有统归万物的作用,是形而上的本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道”。如果“道”的运行都落实到具体的存在物上,就不足以为“道”,所以在王弼的思想中,“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但在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万物只依据自身的本性而发展。因此,在郭象看来,王弼思想中有不彻底的一面,既然万物都可以依据自身,那“无”就是多余的概念。郭象以王弼的“无”作为自身哲学的出发点,去解决王弼思想中的弊端。郭象的本体论目的是为了解决“有生于无”的宇宙论思想,他反对从无到有的创生思想。郭象认为,万物不是由实体性的“无”产生的,一切都是“块然而自生”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无”并不是万有背后的主宰者和支配者。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自己运行的结果,他说:“然则无事而推行是者,谁乎哉?各自行耳”(郭象 注、成玄英 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287页),万物不依赖于任何的主宰者,所以就不假外求,万物只需依自身的内在而各反其宗,所有的是非与纷争就会泯灭。
二、“独化于玄冥之境”
在郭象的思想中,万物都是自生的,“自生”本身有什么含义?郭象说:“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南华真经注疏》,第26页)由此引出自生、我生和自然,这里的“自生”和“我生”有较大差异,通常的“自”是指“我”的意思,但在这里“自生”是指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这种不知其所然而然的变化,在郭象的哲学中可以用“命”来解释。而与之相对的,“我生”指的是由自身可掌控的,也就是说,万物的生生与变化都来自不可预测的“命”,这种“自生”非“我”所能把握和掌控。在这里,由不可预知的外在变化之“命”与主体性的“我”形成对立,对于“我”而言,所谓的“命”或“自然”都是自身无法掌控的,但“自然”本身却是具有客观性的。冯友兰认为:“郭象所讲的自然,那是从‘独化’这方面讲的,也就是从‘性’这一方面讲的。从这方面讲,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自然’),好象是很自由自在。但是,从‘命’这一方面讲,郭象所讲的自然,也是对事物的一种决定,一种限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47页)就“命”而言,万物都有其自身的不得不然,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就“性”而言,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身的本质倾向,这种主体性的倾向来源于必然性的“自然”,一切事物只要不超出自身的本性,在“自然”规定的限界内去发展,就可以自得其分。郭象认为,“自然”规定了独立的具体之“我”的存在,所谓的“自生”并不是指万物自身能够自我产生或自我决定,而是强调一种必然性。万物面对这种必然性都是无法掌控的,每一独立的个体都要认清自身的界限,在“自然”或“命”的限定中完成自身的本分,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完成必然和自由的统一。
汤一介认为,“如果说‘有’是郭象哲学体系中最普遍的概念,那么‘独化’则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郭象的“独化”才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所谓的“独化”实际上就是“自生”的另一层表达,郭象说:“无所资借而独生,即无所待而独化也。惟其独生独化,乃始谓之自然。自者,超彼我而为自。然者,兼生化而成然。”(参见《庄老通辨》,第371页)郭象认为独生和独化就是没有依据和“无所待”,万事万物都是来源于绝对性、无条件的“自然”。“待”的概念成为独化的核心,郭象在《庄子注》中解释罔两与影中提到:
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南华真经注疏》,第57页)
“待”的问题在《庄子》中表示的是罔两、影和形三者相互依赖的关系,庄子所强调的是“形之所待”本身就是超越于“形”的存在,所以“形之所待”就是无形的存在,这里就引出了庄子所面对的无知之境。郭象将“待”的问题解释为“独化”生成的问题,罔两、影和形都是从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玄冥之境”而化生的,三者本身看似是“有所待”的存在,实际上都是万物“自生”的表现。罔两、影和形之间看似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实际上是自身所尽本性的结果呈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某种契合,即使像罔两这样没有主体性的存在,也是由不可预测的境域生成的。因此,才会有所谓的“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既复玄合而非待也”,其中“相因”的解释是理解“独化”的关键。在郭象的眼中,万事万物的“独化”都是一种自我生成,每一种事物都依存自身的本性而自我发展,没有依赖和依靠其他事物。事物在独化的过程中,可能会无意地与他者形成某种契合,但这种契合并不是有意的为之,而是在自我发展中偶然的达成。就像身体的五官,原本就各自有自身的职责,当彼此完成自身的职责,实际上也是助力于其他器官,但这种助力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产生的附加效果而已。冯友兰说:“任何物,都是自己为它自己而存在,就这一方面,事物各有各的方向,各自向着自己方向走,有的往东,有的往西。这是‘独化’。但是在各各自为的时候,有不期然而然的配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41页)冯友兰认为,郭象的独化都是彼此有各自的方向,在各个自为的过程中,都不期而然地彼此互相配合,也就是在自为中,也彼此相为。
郭象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本性”,每一个具体的存在者都有其自身的固有分限,如果超出自身的本性,就会产生混乱。郭象说:“举其性内,则虽负万钧而不觉其重也;外物寄之,虽重不盈锱铢,有不胜任者矣!”(《南华真经注疏》,第99页)只要在自身的本性范围内,就算是万斤之物也不以为重,如果是在本性范围之外,即使斤两之物仍以为重。这里的本性也指内在的本质倾向,亦是一种潜在的能力,郭象认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南华真经注疏》,第342页)即使是后天造成的“落马首,穿牛鼻”,也是因为牛马先天有此种本质倾向,所以这种后天的行为并没有超出“性分”的范围。郭象否定普遍性的人性之论,而主张个体的“性分”,每一个具体存在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总是将大多数人的特征视为普遍性的存在,而不知此种观念是人自身所设定的相对标准,就像骈拇的存在,人总是以五指为标准,而视骈拇为异类,这种思想就是违背万物自身的本性。如果以一种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万物的存在,那就意味着人、物皆有高低贵贱之分,最终会造成人、物之用不能各尽其分。所谓的“性分”就是指万物生成以后,各自所受的本性分限,这种本性的分限也是不由自身所决定的,与“自然”有共同之意。
三、“适性”逍遥
“独化”所达到的目的是要实现各自的“逍遥”,那逍遥本身有何意义?在庄子那里,“逍遥”就有消除成见和是非的意思,王夫之解释逍遥时说:“消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这里的“消”指的是一过即忘的思想,不停滞的状态,“遥”则通过极远的视野来摆脱有限的心知。庄子通过大鹏扶摇而上九万里的过程,来呈现某种距离感所带来的“其远而无所至极”的视野,鹏就有摆脱和消除有限的认知和是非的主动性,达到了真正的逍遥。在庄子的眼中,逍遥就有消除和脱离的意思,想要摆脱有限的认知就需要极大的主动性,通过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来消除否定性的认知与是非,从而实现真正的逍遥。庄子通过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来摆脱现实的限制,所以才有“游于四海之外”的心境。
郭象的逍遥思想是建立在各自“性分”的基础上,通过各安其分的方式接受现实的各种境遇。庄子在《逍遥游》中曾以小大之辨来区分大鹏与蜩、鸠的差别,以此彰显大鹏高于二虫之逍遥境界。郭象释曰:“二虫,谓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南华真经注疏》,第4页)首先,这里的“逍遥”没有人为的因素在里边,万物之分限皆自然而然。另外,郭象将鹏蜩称为二虫,也就是将鹏与蜩拉到同一层次,大鹏境界并没有高于蜩、鸠的意味。郭象又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郭庆潘:《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郭象通过齐物自得的思想解释逍遥,小鸟和大鹏都有自身的生存之境,大鹏没法体会蜩、鸠“枪榆枋”之乐,蜩、鸠亦无法企及“九万里”之视野,万物只要依靠自身的本性生存、发展就是逍遥。在庄子看来,逍遥是一种最高的境界,通过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安命作为始端,并经过齐物的方式才可抵达,庄子将逍遥和齐物分为不同的层次,只有同时拥有圣人之道和圣人之才的人,才可以摆脱一切束缚,达到“逍遥”的境界。
对郭象而言,庄子之逍遥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自觉,与大多数人无关。郭象想要将逍遥建立在齐物的基础上,只要在自性的范围内,逍遥就是万物任性而自为。齐物的思想在庄子那里是达到逍遥的途径。在这里,郭象将逍遥与齐物的思想放在同一层次上,逍遥不只是个别的或少数人的偶然性境界,而是万事万物所达到的普遍性能力,将逍遥境界普遍化也是郭象的目的。在庄子那里,齐物是为了达到逍遥的方法,根据郭象的理解,齐物和逍遥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二者的具体内容都是相同的。通过齐物之大小更能显示出“逍遥”的意义,郭象在解释《齐物论》中提到:
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未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 《南华真经注疏》,第43页)
郭象从“性分”的方面来看待事物之差异,如果秋毫本性自足,那天下没有大于秋毫之物,则秋毫可称为大;太山如果没有自足其性,则其形虽大仍可称为小。在这里,郭象并非以事物形体来衡量其大小,而是以事物自身的本性来衡量。事物如果真能各足其性,都实现自身的内在本质,那就无所谓大小,最终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齐物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齐是非”,郭象说:“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南华真经注疏》,第36页)每一个“我”都有自身的认知,但具体的个体认知是有限的,并将自身以外的“彼”之他者看作“非”,如果不能以超出是非的观念去衡量彼此的观念,只能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的对立之上,那将永远停留在争论之中。郭象提出“反覆相喻”的方法,要站在他者之立场去看待事物,将在“此”之“是”与在“彼”之“非”反复进行衡量,以超越是非的视野去看待是非本身,这样就会通达无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身的立场,所以就有不同的是非产生,也正是是非之争造成了视野的蒙蔽,所谓的逍遥就是要超越彼此的是非,真正地消除所有的成见。在某种意义上,逍遥和齐物是互相成就,只要自足其性,事物都在各自的“性分”之内发展,则万物逍遥一也,不会再有差异。
庄子的“逍遥”是建立在追求天之“无待”而形成的境界,这里的逍遥不是可普遍化的,就像鲲可化而为鹏,举翼南飞,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但是蜩与学鸠就没有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所谓“待”的问题,上文提到,郭象将罔两、影和形的依赖关系转化为独化问题,另一面,郭象将“有待”和“无待”进行概念的使用。刘笑敢认为,把“有待”“无待”当作哲学范畴的不是庄子,而是注《庄子》的郭象。(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所谓的“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都是从属于“适性逍遥”的范畴,但二者有不同的层次。一般而言,“有待”经常被理解为有条件的涵义,但在郭象这里,万物都是来自不可知的玄冥之境,都有自身的“本性”分限,依据自身的本性而行,也谈不上依赖他者。事物只要依自身的本性而行事,不去追求性分之外的事就可以达到逍遥的境界。另外,“有待逍遥”主要是指普通个体的逍遥,因为万物虽然在自身的性分内实现足性逍遥,但只是满足自身的自我通达,仍然是有所对待的。所谓的“无待逍遥”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和区分,不只是通达自我,而且不囿于万物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实现万物之逍遥,也只有真正的圣人才可达到。郭象的“有待逍遥”是有其政治指向的,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南华真经注疏》,第12页)圣人虽身处现实的生活,但其心没有受环境的影响,圣人与常人一样也有情的产生,但圣人有情但不滞于情。因此,圣人可以达到“无待逍遥”的境界,也就是说,“有待”和“无待”只是层次上的差异。郭象将超越性的理想追求拉回到现实,如果只讲圣人无情,那常人便失去追求的机会。郭象一方面讲圣人有情,给常人追求向上的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面,区分了圣人与常人的差异,在“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之间划分了层次。圣人之逍遥是能够通达万物的“无待逍遥”,常人之逍遥是自足其性的“有待逍遥”,虽然二者的层次不同,但仍都属于“适性逍遥”的范畴。
四、总结
综上所述,郭象站在王弼“以无为本”的基础上,通过解决王弼思想中的弊端来发展其“自生”的思想。郭象认为,所谓的“无”并不是万物背后的主宰者,他提出“万物块然而自生”的观念。他认为,“自生”不是自己决定自己,而是由不可掌控的“自然”所决定的,具体的存在物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产生,所以万事万物都“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依自身的内在“本性”发展并达到某种契合,实际上相为的契合不过是万物自为的结果呈现。郭象认为,只要在自身的分限内去发展,就可以实现自我的“逍遥”,这里的逍遥并不像庄子所说,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达到。郭象将齐物与逍遥放在同一层次上,他提出“有待”和“无待”两种逍遥,但这两种逍遥都是“适性”逍遥的范畴,只不过在“独化”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差异,造成了不同的逍遥。“有待”逍遥是普通个体之逍遥,而“无待”逍遥是指圣人之逍遥。总之,郭象的逍遥是通过“六经注我”的诠释方法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时代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