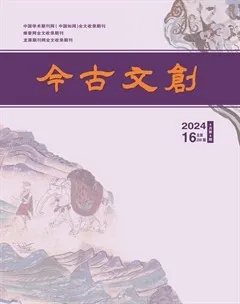多模态隐喻视角下中日死亡美学对比探究
孙泽钰
【摘要】电影是一种典型的利用不同感官通道的多模态叙事文本,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表达,具有更为丰富全面的隐喻系统,可以创造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验。本文以《一一》(中国台湾电影)和《步履不停》(日本电影)为代表,在多模态隐喻视角下,通过分析影片中的叙事手法、人物刻画、意象符号以及镜头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对中日两国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的死亡美学进行对比探究,旨在探讨两国文化在对待死亡主题上的异同。研究发现:中日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的死亡美学多悲情色彩浓厚,隐喻性表达含蓄克制,且具有去戏剧性的写实特点。受中日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国电影中,死亡往往被赋予深厚的社会和人文意义,强调生命的坚韧与对生的珍视,尚未形成约定俗成的审美性的死亡意象;而在日本电影中,则具有独特的民族化死亡符号,更侧重于个体心理与情感的表达,探究死亡本身的意义。
【关键词】多模态隐喻;死亡美学;生死观;《步履不停》;《一一》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6-009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28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批评隐喻分析视角下的日本政治语篇研究——以岸田文雄施政演讲中的外交话语为例”(项目编号:SZKY2023043)资助。
一、理论背景
(一)多模态隐喻
Lakoff和Johnson(1980)指出,隐喻作为人类普遍的认知和思维方式,通常以语言和文字来表达。而作为人类社会符号的表现形式之一,完全依赖语言和文字的隐喻研究势必是不全面的。对此,Forceville(1996)所提出的多模态隐喻则扩展了传统隐喻的概念,通过结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模式来传达隐喻性信息,构成文字-图像源域(喻体)向目标域(本体)映射的多模态隐喻过程(赵秀凤,2011)。
电影是典型的多种符号和感官建构的多模态叙事文本,包含语言和非语言两大系统。电影隐喻是影像-语言的多模态映射模式。电影多模态隐喻的符号系统和模态资源的丰富性决定了其并非是简单的意义堆砌,而是具有复杂隐喻结构和丰富隐喻形式的交叉互动隐喻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中的隐喻往往只呈现源域,而把目标域的联想与阐释空间留给观众,由此实现电影与现实、源域与目标域连接的映射结构(苗瑞,2021)。
(二)死亡美学
死亡,折射着人们的精神思想,也表征着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死亡美学,突破了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等对死亡的认知,即在艺术作品的“死亡”中发现“美”和意义。根据颜翔林(2014)的解释,在艺术作品中,死亡意象与符号的价值有三个方面,即伦理价值、宗教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价值并非是单孑独立的,彼此往往相辅相成。但是,在这些价值之中,审美价值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
电影作为一种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艺术形式,对死亡的表现受到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反映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观念。而现实主义家庭电影更是社会中人间百态的缩影,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即真实性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生死往往是其不可或缺的母题。因此,东方情境、纪实主义与文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中日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独特的死亡美学。
二、中国电影中死亡美学的多模态隐喻探究
(一)人物与情节设定
家庭电影往往有着比较标准的人物结构:子女、父母、祖父母三代人,根据故事情节不同或有人物的缺失。这样的缺失往往以代表青春年少的子女一代和雪鬓年老的祖父母一代为主要对象,且通常为电影中的“死亡”情节埋下伏笔。而与此相对,观众则以正值壮年的主人公为视角,对“死亡”带给人物的困顿进行体会和思考。
电影《一一》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较为优秀的一部,在全世界都享有极高声誉。影片是比较完整的三代人的人物结构,代表老年的祖母中风昏迷是故事的开端和电影叙事的基点。同时通过“家人每天轮流和祖母讲话帮助其恢复”这一情节,也成为其他角色情感表达和宣泄的窗口,是代表性的多层次人物形象建构。
(二)符号意象
贯穿影片《一一》的一个最明显的意象就是洋洋的相机。虽然看似与“死亡”并无直接联系,但它却拥有着最深刻的哲学意义。洋洋用相机可以拍摄别人看不到的背面,正如人們无法完全了解自身,相机便成为记载拍摄对象视觉盲点及重构自我认知的媒介。电影中阿弟自杀和胖子情杀就与人物内心的迷茫脱不开干系,在自视之后,“生死”正是哲学所追求的终极问题。
此外,电影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祖母这一被符号化的多重意象。祖母一开始就中风昏迷,处于死亡边缘游走的状态。在此之后,从影片的角色对话角度来看,祖母不再有任何一句台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简家人与祖母交谈时,祖母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各类人物内心的迷茫,其情绪符号的作用极致发挥,贯穿影片始终。
(三)镜头语言
电影是一种影像艺术,镜头语言是与视觉观看直接相关的电影手段。杨德昌作为新台湾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新德国电影观念,追求以现实世界的外部真实和内心真实作为电影取材的基本依据,探索电影剪辑方法的真实效果,完善以长镜头为核心的电影再现美学在表现人生、反映社会心理中的巨大作用(潘天强,2003)。长镜头具有写实主义电影美学特征,在审美上保持时空的一致性,从而促使观众使之与客观世界相连接。在电影《一一》中,近景和特写往往被导演有意舍弃。比如电影的结尾祖母去世时,没有一个镜头是对准祖母的,而是通过一个固定的长镜头,尽可能地向观众呈现其他人物的真实反应,并以此来间接交代祖母的死亡。此外,电影中的长镜头还大量地以玻璃等隐喻性空间为对象。玻璃作为一种反射的镜像载体,不仅可以反映都市空间的样态,还将影像人物对内对外的情感同样呈现出来(卢文超,2017)。
三、日本电影中死亡美学的多模态隐喻探究
(一)人物与情节设定
日本的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也有着与中国相似的人物和情节设定。是枝裕和作为日本当代生活流电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享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小偷家族》等众多闻名海内外的现实主义家庭题材电影。《步履不停》正是讲述了一家人因大哥纯平的忌日团聚在一起的故事,是比较标准的子女、父母、祖父母三代人物结构。其中,《海街日记》则讲述了三姐妹在父亲去世后接纳同父异母的妹妹共同生活的故事。虽然《海街日记》与《步履不停》都是以“死亡”为故事的开端,但前者以四姐妹青年一代为主角,且三场葬礼场景的出现连接全片,分别是父亲的葬礼、外婆的周年祭和饭店老板娘的葬礼,对应着中年和老年一代的“死亡”,显然在人物和情节结构上做出了创新。此外,2018年获得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小偷家族》中更是给出了一个奇特的家庭乌托邦景观:所有成员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但却组成了一个“上有老, 下有小”的结构非常稳定平衡的六口之家。由此可见,是枝裕和在突破传统家庭电影的叙事结构上越走越远,逐渐建构出一个非血缘性的“流动”家庭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侯孝贤与杨德昌对是枝裕和的电影风格影响很大,他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即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份经历成为塑造其纪实性电影气质的重要契机,推动是枝裕和逐渐跻身日本,乃至亚洲家庭电影的标志性导演行列。
(二)符号意象
在《步履不停》中,母亲认为在夜里飞进客厅的蝴蝶是死去的长子纯平。屋中飞舞的蝴蝶与逝去的年轻生命形成了类比。蝴蝶落在纯平遗像上的细节,则在视觉上更加明确地将蝴蝶与逝者联系起来,成为影片中家人哀思涌动的情感开关。
作为最日常的象征符号,食物的意象也常在日本的家庭电影中出现,厨房更是不可忽视的叙事空间。影片一开始便是厨房做菜的画外音,整部电影也由一家人的几顿饭串起而成,厨房与餐桌自然成为情绪宣泄的窗口。炸玉米天妇罗就是特别的情感切口,这是已去世的长子纯平最爱的食物,母亲每次都会做天妇罗就是在表达对已经去世的淳平的爱和怀念,这样借食物的隐性表达更显日式内敛。如此相似的意象也曾多次出现在是枝裕和的其他电影中。
(三)镜头语言
是枝裕和偏爱用景深长镜头层层递进地展现人物间的羁绊。在《步履不停》的尾声部分,良多一家人纪念逝去的父母,是枝裕和将他们下山的路完整地拍摄出来,并与之前一家人去祭拜长子的画面相呼应。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暗示着母亲的“死亡”和新生命的诞生。将影片的主题隐喻于眼前之景,羁绊与情感不会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是会不断绵延下去的永恒存在。
作为导演侯孝贤的忠实拥趸,是枝裕和电影的镜头语言颇具侯氏风格,兼有对自然风物及光影变化的偏爱展现出其独具日本“幽玄”“物哀”的美学特色(戴小清,2020)。例如其对空镜头的运用使画面产生了一种留白之美。《步履不停》中多次出现台阶和道路的空镜头。影片末尾,父母目送良多一家离开后,又出现了夫妇二人一起上阶梯的画面。随后出现良多的画外音:“三年后父亲死了,最后和父亲约定的球赛也没有办成。”两人的身影逐渐在荧幕中消失,画面停留在阶梯的空镜头上许久。在这里,对于人生的生离死别,是枝裕和没有进行丝毫的渲染,仅仅只是用平淡的画外音结束,空镜头的停留,将影片的余韵延长。
四、中日死亡美学隐喻的对比分析
(一)相同点
中日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的死亡美学多悲情色彩浓厚,且生与死往往紧密相连。电影《一一》中的气氛因为婆婆的昏迷不醒而充斥了悲戚的因子。《步履不停》中人物的情感关系更是一直笼罩在哥哥忌日的氛围中,特别是良多和父母三人在面对遗像与蝴蝶时静默的悲伤,是全片最为动人的时刻之一。
但电影中的“死亡”往往并不孤立,反而常常与“生”息息相关。《步履不停》结尾重复的长镜头暗示着母亲的死亡和新生命的诞生。电影《一一》的开头与结尾,分别是隐喻新生和生命旅程终结的两场宴席——婚礼与葬礼。这种巧妙的设置给观众传导一种生与死之间的联系,生命也如这般循环往复。
其次,受东方美学的影响,中日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的死亡美学表达含蓄、克制而隐忍。是枝裕和(2013)曾写道:电影也应尽量用不直接说出悲伤或寂寞的方式,表现悲伤或寂寞。我想创作的,就是有效利用类似文章里的“行间”(留白),让观众自己以想象力补足的电影。《步履不停》中虽然没有刻意刻画一家人对于失去长子的悲伤,但是却通过一件件小事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强烈的情绪冲击。《一一》中对“死亡”的表达与感悟更是借小孩子洋洋的口说出,巧妙而富有深意。
最后,中日现实主义家庭电影具有去戏剧化的写实特点,对死亡美学的呈现也倾向于真实细腻。为了防止观众情感的过度参与而失去理性的思考, 在电影《一一》中,杨德昌导演尽可能减少近景镜头的使用,且基本不用特写, 从而削弱了影片的有意煽情效果。而是枝裕和也不刻意追求情节上的跌宕起伏,而是通过生活化细节直抵人心。《步履不停》中,导演为了讲述这一家因哥哥的离世带来的缺憾,用了多个片段化情节:例如缺了一个抽屉的柜子、拍全家福时爷爷不情愿再到始终没有修好的厕所瓷砖。
(二)不同点
首先,整体来说,中国电影缺少以死亡为主要主题的影片。死亡总是与其他主题混合在一起,成为烘托其他主题的陪衬,如死亡与灾难、死亡与爱情、死亡与战争等等。而家庭电影中对死亡意识的忽视更甚,自然对死亡探究的意义不够深刻。日本的家庭电影则更为成熟,在东亚乃至世界首屈一指。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电影审美,近年来尤以是枝裕和的家庭电影为代表,《无人知晓》《小偷家族》等享誉国内外,在意义上追求“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现实。
其次,在关于死亡的影像表达上,相较于具有较强死亡美学追求的日本影片,中国電影对死亡的审美表现较为随意,大多为导演个人风格所致,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审美性的死亡意象,如日本影片中的樱花、蝴蝶等。小谷瑛辅(2018)指出,日本文化中蝴蝶的死亡象征也是以蝴蝶的生态特点加上日本固有的神灵信仰为认识本源的。蝴蝶美好易碎的“无常感”符合日本民族的泛灵信仰和多神崇拜的审美文化心理。因此,是枝裕和在电影中以蝴蝶为符号来表现生者对死者的哀思。这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流露出的民族文化心理使然。而中国电影的死亡意象还较为随意零散,缺乏一种艺术化、民族化的美感。
最后,中日两国的死亡美学主题有所差别。日本电影中死亡美学的核心是“向死而生”,追求“为何而死”的死亡意义。如日本武士电影中“成就而死”的现象极为常见。在家庭电影《步履不停》中,大哥纯平也是为救落水的孩子而死。而中国则往往是“向生而死”,“死亡”会对活着的人造成影响,成为故事的转折或人物成长的契机,因果关系强烈。如《一一》中,婷婷和洋洋都在外婆死后获得了成长。
五、结语
电影作为内涵与形式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常常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而与其他电影类型相比,现实主义家庭电影中的“死亡”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是经常被忽视的领域。中日导演有意识地对死亡主题的创造,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体验。笔者以期通过多模态隐喻视角下的对比研究,提供关于两国电影文化之间死亡美学差异的新维度,也为理解中日文化中对生命和死亡的独特态度提供洞见。
参考文献:
[1]Lakoff,George&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Forceville,C.1996.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M].London:Routledge.
[3]趙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Forceville&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外语研究,2011,(01):1-10+112.
[4]苗瑞.当代电影隐喻的多模态认知建构[J].当代电影,2021,(03):41-47.
[5]颜翔林.死亡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4.
[6]潘天强.西方简明电影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卢文超.杨德昌《一一》:都市漫游下的生存之惑[J].电影文学,2017,(14):93-94.
[8]戴小清.《步履不停》:家庭伦理电影的叙事风格及画面艺术[J].电影文学,2020,(03):141-143.
[9]是枝裕和.歩くような速さで[M].ポプラ社,2013.
[10]小谷瑛輔.蝶になりたい小泉八雲:芥川龍之介「或自警団員の言葉」を視座として[J].ヘルン研究150-59,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