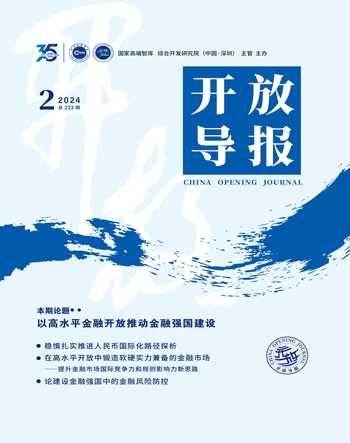在高水平开放中锻造软硬实力兼备的金融市场
黄新飞 李嘉杰



[摘要] 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实施金融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参与程度虽不断提升,但依然受限于金融市场软实力和硬实力不足,导致竞争力和影响力较弱。面对国际支付清算能力不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较少以及金融监管引领不够等挑战,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境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科技应用,赋能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提高风险防范精准度,保障金融稳定,从而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关键词] 金融市场 国际竞争力 规则影响力 金融高水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 F83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4)02-0019-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IFDI与OFDI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16ZDA042)。
[作者简介] 黄新飞,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和国家金融学;李嘉杰,中山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金融学。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这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金融强国目标建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外部环境看,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国际贸易局势紧张、金融监管体系趋严等,不仅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资本流动的极端波动,而且增加了国家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营运成本,给中国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带来严峻的外部挑战。从内部环境看,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持续推进,金融科技赋能步伐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在确保中国金融市场安全和稳定、吸引和助推资本流动的同时,也为中国金融的深度国际参与提供了机遇。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我国还存在“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等问题。以深化金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既是维系我国经济社会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抓住发展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在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下,如何通过深化金融高水平开放,加强国际金融参与度,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不仅关系到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也是关乎我国能否提升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议题。
一、金融高水平开放是提升金融市场
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提高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前提是要深度参与国际金融、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优势,而扩大金融开放,则是实现上述两个前提的必由之路。2018年4月至2023年底,我国相继推出金融对外开放措施50余项,内容包括取消银行保险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减少金融业外资数量型准入门槛、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方式和渠道等,具体涉及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降低了包括银行业、债券市场、保险市场开放等多个方面的要求,全面放开了境外金融机构参与养老金管理、参与货币经纪活动以及理财公司控股要求的限制等;2020年6月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全面清零;2023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取消了QFII和RQFII办理资金登记的行政许可要求等限制,境内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开。我国扩大金融开放不仅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同时积极助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如中国银行伊斯兰堡分行等海外分行相继成立、中国平安收购英国家庭保险公司、复星国际收购葡萄牙保险公司等都体现了中资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决心和能力。
1. 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增强金融科技优势
金融科技已经成为现代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竞争、维持市场地位、拓展盈利空间的重要手段。金融科技颠覆了传统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涉及支付、借贷、资产管理、保险、区块链、数字货币等多个方面,旨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取性、效率和安全性。金融高水平开放可通过两方面提升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水平:第一,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利于整个社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从而助推金融机构实现技术升级。科技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蕴含的高风险决定了其资金融通的困难,因此减少创新投资需求与金融供给之间的摩擦,对实现创新驱动型发展至关重要。如图1所示,随着国内金融机构境内贷款总额的增长,金融供给不断增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也呈现迅猛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1.5%。高水平金融开放可通过丰富金融资源供给和减少金融市场摩擦两条渠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通过与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效应,增加了国内金融要素投入,在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下,压低了金融资源和服务的供给价格(吴晓求,2010)。而较低的金融资源和服务价格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高风险的研发活动面临的较高融资约束(Allie and Mensah,2019)。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直接丰富了国内金融要素供给,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成本,从而提升创新能力(谈俊,2019)。第二,金融高水平开放可以为拥有先进金融科技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金融科技通过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善用户界面和服务流程,促进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个性化,显著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处理速度(李青原和章尹赛楠,2021)。与此同时,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和用户的服务成本,使得金融服务更加普惠。此外,应用最新的安全技术(如区块链、生物识别技术)还增强了金融交易和数据存储的安全性。这些更成熟的“软信息”技术依赖特征有助于塑造金融机构竞争优势(黄益平,2021),从而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2. 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金融参与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有序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开放力度不断增强。自1979年我国首次批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至2023年底,我国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数达888家,资产总额约3.86万亿元;与此同时,中国资本账户项下40个子项目中,包含部分可兑换在内的可兑换项目占比高达90%。扩大制度型开放,体现了中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决心。积极主动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金融参与度。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金融系统透明度的缺乏,会增加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Mudd,2013),而且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还会面临经济转型风险以及经济转型期间政策不确定性风险(Demir,2009;罗长远 等,2023)。此外,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系统的不透明还会增加金融机构的征收风险(Bernanke and Gertler,1989)。基于此,金融制度型开放一方面通过确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则和制度,减轻了开放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通过优化金融监管框架,强化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质量,主动对外释放规则意识、发布规则制度安排、做出政府承诺,降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风险。从2016—2023年期间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情况(图2)可知,中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具有“渐进式”的典型特征,即从样本期间内的最低值到峰值用了5年时间,其中2021年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中国债券与股票余额分别达到4.1万亿元和3.9万亿元的顶峰。无论是持有股票还是债券,境外投资者对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不断上升。这说明,一方面,我国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切实加深了国际金融参与度,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吸纳和承接大量的资本流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3. 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金融市场要想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一个高效的国内金融系统是必要条件,而评判金融系统是否高效的标准,在于该系统对资源的配置是否充分。而高水平开放作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关键一环,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条件。由普惠金融—小微指数(图3)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和质量不断上升,同时小微企业的融资效率大幅提高,融资价格和风险逐年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也获得了全面改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金融强国目标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局面:全面的工业体系、雄厚的市场潜力以及庞大的人力资源为新时期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黄群慧,2021),而金融机构垄断、金融资源分化以及金融业务单一也为新时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在此背景下,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助推高质量发展。首先,金融机构的垄断会导致信贷配给的低效,从而导致金融机构效益的损失,进而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Guzman,2000)。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垄断势力会形成固定的关系借贷,导致金融机构丧失信息甄别能力,增加了借贷中的道德风险(Rajan and Zingales,2001)。其次,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分化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降低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倾向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给关系客户或大型企业(Chen et al.,2013),这就导致了容纳就业市场绝大多数劳动力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企业发展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而金融高水平开放带来的数字金融普及以及金融资源供给扩张有利于普惠金融的深化,为中小微企业发展赋能(李建军和李俊成,2020)。再次,金融高水平开放也有助于丰富国内金融市场业务类型,为国内企业融资、投资以及保险等提供丰富的可选择业务。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通过加速国内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丰富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种类,加速了一国金融市场的成熟,而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也增加了企业的多重金融业务需求,从而倒逼金融市场的完善,进而更好服务国内企业实体(黄益平和黄卓,2018)。总之,在深化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金融系统配置资源能力可以得到大幅提升,金融市场实力增强,参与国际金融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4. 金融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货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不仅是其经济实力和金融稳定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货币的国际地位受到经济规模、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与开放性、政治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升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已成为许多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举措就是高水平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活力,还能够加强国际投资者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从而促进货币的国际使用和储备(裴长洪和刘斌,2020)。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增长,降低外贸企业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海外金融支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等需求被提上日程,而人民币的国际化正是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最佳方案。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频率和地位,减少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中依赖第三方货币(如美元)的需求,降低汇率风险,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包括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设立离岸人民币市场、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商品交易、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等。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启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程,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此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全球贸易人民币融资比例位居全球第二,超过80个国外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篮子中。如图4所示,自2016年以来,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储备比重不断增加,在2021年达到2.8%的峰值。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普及不仅有助于形成货币依赖,同时也会通过进入锚货币篮子而被他国汇率对冲行为自动维持货币币值稳定、降低货币危机发生概率(Ilzetzki et al.,2019)。金融高水平开放带来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效应,再加上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优势,进一步放大了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助推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确立。以人民币债券市场为例,截至2024年1月底,人民币债券市场连续4个月净流入,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债券规模约5000亿元。与此同时,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债券投融资潜力巨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对世界范围内各国央行的三年期调查数据(图5),离岸人民币日均交易额不断增长,离岸人民币交易的前四大市场中,美英市场增长迅速,反映了海外市场对人民币的强烈需求。强大的金融市场规模优势往往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Arslanalp et al.,2022)。除此之外,積极参与经贸合作、扩大进出口市场规模、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等措施也可通过规制融合效应、市场规模优势效应以及价值链攀升效应等渠道增加本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王一鸣,2020)。
二、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
和规则影响力面临的挑战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金融系统的强大是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及规则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实力直接影响到其经济的稳定性、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以及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金融系统的强大能够为国家提供稳健的金融环境,吸引国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自身金融系统实力的强大需要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体现。硬实力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规模、深度以及效率,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备性,以及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和国际化程度。而软实力则涵盖金融监管体系的成熟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创新能力,以及金融人才和金融文化等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只有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色,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增强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然而,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定欠缺,这成为提升自身金融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挑战。硬实力方面,尽管我国的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但市场深度和效率相比发达国家仍有差距,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亟待提高。软实力方面,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虽然不断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和最佳實践的接轨仍有空间,金融开放程度、金融创新能力以及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1. 国际支付清算能力不足
国际支付清算能力的典型表现是拥有一个本国构建、控制和维护的,承担全球支付清算功能的基础设施。拥有一个成熟的可承担全球支付清算功能的基础设施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极为重要,它不仅是该国参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关键,也是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成熟的支付清算系统能够为国际交易提供高效、安全的支付解决方案,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增强交易的便利性和可靠性。此外,这样的系统还能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提高国家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因此,构建并维护一个高效的全球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显得尤为重要。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包括关闭SWIFT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这一事件突出体现了全球支付清算系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SWIFT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信息传输网络,几乎所有国际银行交易都通过这一系统进行。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断开SWIFT系统的举措直接限制了这些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措施不仅凸显了控制全球金融信息流通渠道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国际金融系统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争斗工具的潜力,其安全和独立性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我国于2012年4月12日开始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虽然CIPS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CIPS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是覆盖范围和参与机构有限。CIPS的国际覆盖范围和参与机构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与长期建立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相比,其覆盖的地理范围和参与的国际银行数量仍然有限。首批直接参与的19家银行中仅有8家外资银行,仅覆盖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外地区。此外,CIPS的参与方式进行了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的区分,直接参与者可在CIPS开立账户,通过CIPS直接发送和接收业务,而间接参与者则需要通过寻找直接参与者的代理来获得CIPS提供的服务,因此直接参与者的数量反映了CIPS系统的覆盖规模。从图6可知,间接参与是CIPS系统的主要参与方式,这极大地限制了CIPS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和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便利性。二是交易时间的限制。CIPS(一期)的业务受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北京时间上午九时至晚上八时,这就导致了CIPS系统运行时间与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营运时间重合度有限,其服务时间可能不完全适应全球市场,特别是与欧洲和美洲市场的交易时间差异可能影响跨时区的支付效率和便捷性。三是系统功能和服务水平不够完善。虽然CIPS在支付和清算服务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与成熟的国际支付系统相比,CIPS在一些高级功能、定制化服务以及风险管理工具方面仍有待完善和提升。从系统功能来看,2021年SWIFT系统的日均业务处理量达到4200万笔,日均处理金额高达5万亿美元,而CIPS系统在2022年日均处理金额才刚刚达到3880亿元人民币,日均业务处理量仅1.77万笔,交易规模远远落后。从服务水平来看,SWIFT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消息类型,覆盖了支付、证券交易、贸易融资、外汇和衍生品交易等多个领域。CIPS系统不会直接进行资金转换,而会送出支付指令,并必须由各机构所持有的往来账户处理,其本身不直接支持金融资产的交易活动。SWIFT系统还提供全球支付创新(GPI,Global Payment Innovation)服务,大大提升了支付处理的速度,绝大多数支付能够在几分钟内完成,甚至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到账,这对于以往可能需要数日才能完成的跨境支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GPI服务,银行和企业客户可以实时追踪其支付的状态,从发起支付到接收方确认收款,每笔GPI支付都有一个唯一的端到端交易参考号(UETR),使得参与各方都能实时监控支付流程,而且GPI还提供了费用透明度,确保发送方在发起支付时就能清楚地了解到支付过程中会涉及的银行费用和汇率,避免了费用不明确的问题。而CIPS系统虽然实现了实时全额结算,但并未对直接参与者提供定制化服务,且对于汇款订单的追踪仅通过CIPS内的唯一行号标识码来定位汇款路径,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支付流程信息,且费用透明性等方面还有所欠缺。
2. 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较少
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的数量在评价一个国家金融国际地位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些机构被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认定为对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重大影响的机构。它们因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和跨境经营广泛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关键位置。一个国家拥有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量,直接反映了该国金融行业的实力、影响力以及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截至2023年底,中国仅有5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而美国则有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且不仅限于传统商业银行,还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公司。图7展示了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评估标准确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布,根据所需额外资本缓冲的程度(1.0%—3.5%)不同分为了5档,档次越高表示该金融机构规模越大、重要性越大,第5档没有金融机构入选。从图7可知,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且档次从高到低大体呈现金字塔结构,分布较为合理。而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仅种类单一,仅为传统商业银行,且分布极为不合理。我国2023年入选的5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有4家归属于第2档,仅有1家归属于第1档,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形状。这表明我国的金融机构相当集中,金融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缺乏市场活力。同时,金融机构过分集中容易造成风险的集聚,一旦风险爆发,缺少能够分散、缓冲和托底的其他金融机构支撑,会造成风险的迅速蔓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冲击。再者,我国的头部金融机构缺失,第3和第4档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量为0。这意味着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地位较低,在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缺少能够代表本国金融行业利益的大型金融机构,无法推动国际金融规则朝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方向演进。此外,头部金融机构的缺失还会影响我国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通常通过跨境业务推广本币使用,增加本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流通和认可度,从而提升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而头部金融机构的缺失使得我国丧失了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利用自身金融机构地位助推人民币交易结算和人民币金融资产买卖的机会。此外,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是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柱,更是一国金融实力的最直接体现。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缺失,不仅影响国内经济的融资能力,也会影响本国金融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从而导致本国企业发展受限以及资本流动、货物进出口自主调节能力的损失。
3. 金融监管引领不够
金融监管在评价一个国家金融国际地位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能够保障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还能够提升国家金融体系的国际声誉和吸引力,进而增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然而,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速度不仅落后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且在改革的基本框架结构上存在趋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监管经历了一个严格到放松再到收紧的缓慢过程。该历史过程的鲜明特点集中于三个方面:统一监管机构、分化监管措施以及完善应急方案。首先,就统一监管机构而言,2010年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决定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作为统一监管机构,与之类似,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以及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合并升级成欧洲金融监管当局。其次,美欧发达经济体也针对统一监管框架下的不同金融机构,根据其自身系统重要性量身定制了监管要求。例如,美国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产规模划分标准下调,使得更多大中型银行进入了资本充足率的严格要求范围之内。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法和适用对象进行了优化,一方面根据金融监管收紧趋势提出了更加稳健且严格的评级方法,另一方面优化了压力测试的模型,提高了所使用金融机构数据的透明度。再次,针对金融机构风险爆发后的应急方案设置进行了规定。例如,美国发布了《机构间融资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声明》,主要目的是帮助金融机构制定风险爆发后的处置方案。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行动较慢,落后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统一监管上,我国于2017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23年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同时下设新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证券业之外金融业的统一监管。在分化监管措施上,我国于2023年相继出台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评估办法》等不同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在完善应急方案上,我国目前主要采取的是事前防控的思路,即通过完善的配套制度文件从金融活动的发生时期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产生,缺乏针对不同金融机构风险爆发后的应急处置指导性方针政策。
除此之外,我国也未能通过利用金融创新赋能金融监管的方式来塑造本国金融监管特色,形成金融监管引领。金融创新在金融监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推动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激发金融市场的活跃度,还能够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有效性,帮助一个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建立起竞争优势。我国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金融科技领域,已经成为全球的领先者之一。然而,相对于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金融创新技术应用于金融监管领域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框架和技术手段来全面监测和管理金融科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等领域出现的风险暴露问题。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在采集、处理和分析这些大数据方面,尚未充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导致在实时监测市场动态和风险预警方面存在不足。除此之外,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跨界融合,如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但这也带来了监管的新挑战。监管框架和技术手段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这种跨界融合带来的复杂性和新型风险,但在实践中,如何有效监管这些跨界金融活动仍然是一个挑战。
三、在金融高水平开放中提升我国金融
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
不论金融开放到何种程度、金融改革到何种深度,打造“软硬兼备”的金融市场才是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根本。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着重强调了完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的重要性,其中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为此,我们亟须从增强自身金融市场硬实力和软实力角度,寻找能够有效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新思路。
(一)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我国已经拥有CIPS系统进行国际支付清算工作,截至2023年末,CIPS的参与者达1492家,覆盖了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业务稳步发展。然而,CIPS系统还存在境内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占比较高、业务类型单一、结算功能受限等问题,这对于提升CIPS系统的国际交易结算参与程度、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不小的阻力。破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CIPS系统中境外参与者的参与深度,可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是扩充业务类型。目前的CIPS系统仅可进行跨境人民币的支付结算,无法与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具体的金融产品交易绑定,如果参与者需要交易上述金融产品,仅参与和了解CIPS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额外了解交易对象的具体交易规定,无形中增加了CIPS系统参与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境内外机构很少有仅因为持有人民币现金而加入CIPS系统的情况,大部分CIPS系统参与者的目的是交易金融资产。因此,拓展CIPS系统业务类型,有助于吸引更多除银行外的其他专业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同时,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参与者推出定制化服务,如考虑将绑定金融产品的相关业务仅对直接参与者开放,吸引更多間接参与者转变为直接参与者,提高CIPS系统与参与者的关联程度。二是减少交易限制。制约CIPS系统发展的交易限制措施主要集中于交易时间限制和订单追踪限制。CIPS系统的交易时间无法完全覆盖欧美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且CIPS系统无法做到全年无休,这就导致了欧美参与者使用CIPS系统存在时差以及在人民币跨境支付需求最旺盛的节假日期间,CIPS系统无法实时运行的问题。鉴于此,可考虑前期暂时性调整CIPS系统交易时间,使之可覆盖欧美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同时可根据以往的交易需求量,选择在交易需求旺盛的某些节假日延长营运时间,在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参与者数量和参与程度都大幅增长后,可逐步实现全年全天实时交易结算。
此外,在持续扩大资本双向流动的趋势下,离岸人民币交易需求压力将陡增,我国可借此机遇加快建设完备的离岸金融市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是离岸金融中心模式的选择问题。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成熟、开放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健全,内外分离型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金融开放的需求,应根据我国金融发展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内外混合型的特点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并账操作,资金出入境不受限制。由于这种模式是在同一账户上同时运作本国或本地区居民和非居民的金融业务,蕴含极大风险;避税港是没有实际的离岸资金交易,只是办理其他市场交易的记账业务而形成的一种离岸金融市场,容易滋生非法经营行为。因此,我国应当选择以分离为基础的渗透型模式,实现从内外分离型逐步向渗透型模式转变,有条件地允许居民参与离岸金融交易和融资,有条件地允许资金流入境内。该模式可使离岸资金直接为国内使用,为国内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以提升离岸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离岸金融中心的业务设置问题。借助离岸金融中心,可以逐步扩大人民币离岸业务范围,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人民币离岸交易结算中,可为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设置一个专门的结算中心,以确保结算的高效性和可靠性,同时按照国际结算惯例,可提供T+0或T+1的快速结算服务,以尽快完成交易结算;在人民币离岸投资中,设立一个专门的人民币离岸投资业务部门,负责处理离岸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提供包括股票、债券、基金、期货等全方位的服务;在人民币离岸保险中,提供包括寿险、财产险、意外险等,以满足不同离岸客户的需求。
(二)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境内金融机构
能否入围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是评价一家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一国拥有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数量,是衡量该国金融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不仅体现了该国金融行业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是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这些机构的全球影响力意味着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通常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够代表本国金融行业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金融规则朝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方向演进。因此,拥有较多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具有较强的规则制定能力和影响力。然而,国内金融行业较高的进入壁垒和较低的海外业务联系,使得我国的金融机构出现了整体实力不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机构分布不合理等问题。
因此,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两个方向、四个方面着手进行。一个核心是竞争,竞争在提升金融机构实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推动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的关键驱动力,也是加強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两个方向包括降低国内金融行业进入壁垒和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较低的国内金融行业进入壁垒将吸引大量新的市场参与者,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充分竞争。而在竞争充分的环境中,现有的境内金融机构会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速度会加快,境内金融机构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和需求的能力也会逐步增强。同时,密切的海外业务联系一方面可以充分释放境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市场活力,有利于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境内金融机构与国际市场接轨、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规则、参与国际金融创新和技术交流的机会,从而使得境内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可采取以下四方面措施来加强境内金融机构竞争:一是全面清零金融服务业对外负面清单。目前,《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关于金融业的相关限制措施已经完全清零,为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全资子公司进入方面还存在较高的限制,如货币金融服务的负面清单主要针对非银行业,且跨境金融服务面临较多事前审批流程;资本市场服务的负面清单最长,尤其对基金行业的开放程度有限,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必须为中国基金管理公司或证监会核准的其他机构。二是统一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管辖权。不同自贸试验区之间的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覆盖范围重叠,但彼此事权分隔,在仅增强了当地金融开放程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跨区域经营成本,整体上降低了境内金融机构面临的竞争程度。三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国际经贸合作。境内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机制举办的会议和活动,为国际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献声,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发挥影响力。境内金融机构也可在我国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合作中寻找拓展海外业务的机会。可依托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海外业务拓展的步伐。四是提高“走出去”境内金融机构多元化程度。我国目前“走出去”的境内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业,开展的海外业务类型集中于传统的银行借贷,因此,无论是机构类型和业务种类都呈现单一化的特征。未来要鼓励除银行业外的境内金融机构与海外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合资、战略联盟、互认基金等形式。这些合作能够帮助本土金融机构借助合作伙伴的品牌、网络、客户基础和当地市场知识,快速进入新的市场。
(三)加强金融科技应用,赋能金融产品和制度创新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已成为推动一国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提升的关键力量。通过引入创新技术,金融科技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可达性,还为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促进金融产品和制度的创新,从而在全球金融舞台上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金融产品创新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满足市场和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创新型金融产品,如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数字货币、P2P网络借贷、众筹平台等,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透明度。这些创新产品通过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增强了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提升了国家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地位。同样,新型高效的金融市场制度对于提升一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至关重要。制度创新,如监管沙盒、电子支付法规、数据保护政策等,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框架和政策支持。这些制度不仅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消费者权益,还鼓励了创新和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市场更加灵活和开放。通过制度创新,一国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监管形象,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参与,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从金融科技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的视角来看,金融科技的应用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个性化和便捷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风险评估、财富管理和投资咨询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增强金融产品的吸引力。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深入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精准识别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这使得金融机构能够设计更为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如基于消费者信用行为的信贷产品、个性化的投资和储蓄方案等,满足市场的细分需求。AI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如智能投顾、自动化资产管理等,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新思路。通过AI算法,金融机构可以提供基于复杂模型和算法的投资策略,为客户带来更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体验。区块链技术以其独特的去中心化、透明、不可篡改的特性,在金融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创新潜力。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开发出新型的支付系统、数字货币、智能合约等金融产品,能够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此外,金融科技促进了金融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如金融与电商、金融与健康护理等领域的结合,促成了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的诞生。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也为金融服务的场景化和细分化提供了可能。
金融科技作为金融行业的一场创新革命,不仅推动了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变革,还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金融科技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使得金融监管、市场运作和服务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金融制度的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引入新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监管机制或政策框架,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需求、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金融服务功能的一系列创新活动。金融科技的发展不断拓展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外延,使得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内涵不断丰富。另一类是制度集成创新,即通过整合、优化现有制度安排来促进技术、产品、服务等方面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涉及单一制度的改革或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制度整合,形成更为高效、协同的制度体系,从而激发整体创新活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金融科技的高效和便捷的特点,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共享和信息流通,因此,在单一制度革新的同时,往往也要适时关注各项制度之间的配套和协调,确保制度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能够相互支持,形成合力。除此之外,金融科技还可以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遵守国际规则、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技术支持,增强国家金融市场的规则影响力(盛斌和黎峰,2022)。
(四)提高风险防范精准度,保障金融稳定
金融稳定是一国金融市场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基石。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不仅能够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还能提升国家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声誉和影响力。金融稳定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操作环境,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利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发展,从而增强国家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采取过于严厉的监管和准入限制并非明智之举。过度的监管可能抑制金融创新,限制金融市场的活力和效率,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过严的准入限制也可能阻碍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减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国际交流。因此,平衡金融稳定与市场开放和创新是提高国家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精准度成为了一种理想的选择。未来可从三个方面着手,构建风险防范体系:一是在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全面覆盖监管科技。监管科技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帮助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实现对市场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通过部署智能监控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市场异常行为,帮助监管机构及时采取措施,减少金融风险。同时,监管科技也为金融机構提供合规服务,帮助它们更有效地遵守监管要求。二是面向市场主体加快数字身份认证。利用区块链和生物识别技术,可以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身份认证系统,提高客户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这对于打击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鼓励金融交易的开放透明和可追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能够在满足预设条件时自动执行合约条款,这为金融交易和合同执行带来了高效和透明的新模式。利用这一技术,可以简化和优化贷款、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的流程,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和欺诈行为,促进金融市场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同时,风险爆发后的事后应急处置措施尤为重要。事后处置措施对于恢复市场信心、稳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处置措施不仅要求迅速有效地缓解危机影响,还要对未来的风险防范进行布局,确保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信心是事后处置措施的首要目标。这包括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保证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以及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轻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同时,保护投资者和储户的利益,避免群众恐慌性提款,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清理和重组金融机构也是推动金融市场恢复的重要措施。对于因危机而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需要根据其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实施资产剥离、注资、合并重组等措施,清理不良资产,恢复其正常运营能力。加强金融监管和完善法律法规是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关键。事后处置,应总结危机经验,识别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针对监管漏洞和市场失灵,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引入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改善风险管理框架、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等措施,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此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也是事后处置的重要内容。金融危机往往暴露出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在危机后应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产业升级、鼓励科技创新和企业创业,提高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总之,风险爆发后的事后处置措施旨在通过一系列综合政策和制度安排,不仅要缓解危机带来的即时冲击,还要从根本上改善和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中国内地国际收支格局和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定位[J].开放导报,2020(3):14-21.
[2] 黄群慧.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其历史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2021(7):4-20+204.
[3] 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经济学(季刊),2018,17(4):1489-1502.
[4] 黄益平.关于中国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几个观点[J].金融论坛,2021,26(11):3-5+36.
[5] 李建军,李俊成.普惠金融与创业:“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J].金融研究,2020(1):69-87.
[6] 李青原,章尹赛楠.金融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证据 [J].中国工业经济,2021(5):95-113.
[7] 罗长远,李铮,智艳.“走出去”是否有助于抑制企业的“脱实向虛”行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3,23(6):2369-2386.
[8]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20(2):46-69+205.
[9] 盛斌,黎峰.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J].开放导报,2022(4):15-20.
[10] 谈俊.我国金融“走出去”的角色转换[J].开放导报,2019(2):40-44.
[11]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12] 吴晓求.中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探讨[J].金融研究,2010(8):199-206.
[13] Allie J N, Mensah I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Nexus: A Realistic Testimony from VECM Approach[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 7(4): 118-126.
[14] Arslanalp S, Eichengreen B, Simpson-Bell C. The Stealth Erosion of 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 138.
[15] Bernanke B S, Gertler M.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14-31.
[16] Chen Y, Liu M, Su J. Greasing the Wheels of Bank Lending: Evidence from Private Firms in China[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37(7): 2533-2545.
[17] Demir 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Choic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314-324.
[18] Guzman M G. Bank Structur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A Simple Macroeconomic Model[J]. Economic Theory, 2000, 16(2): 421-455.
[19] Ilzetzki E, Reinhart C M, Rogoff K S. Exchange Arrangements Enter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ich Anchor Will Hold?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2): 599-646.
[20] Mudd S. Bank Structure, Relationship Lending and Small Firm Access to Finance: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13, 44(2): 149-174.
[21] Rajan R G, Zingales L. Financial System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owth[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1, 17(4): 467-482.
Forging a Financial Market with both Hard and Soft Power in a High-level of Opening-up
—New Idea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gulatory Influence of Financial Markets
Huang Xinfei, Li Jiaji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gulatory influence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financial country and a fundamental assur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Despi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opening-up,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still suffer from insufficient soft and hard power, resulting in relatively weak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capabilities, fewer globally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sufficient guidance from financial regul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future to improv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gradually loosen restrictions on the access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foster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financial product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risk prevention to ensure financial stability, thus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lanning influence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gulatory Influence; High-level of Financial Openness
(收稿日期:2024-03-10 責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