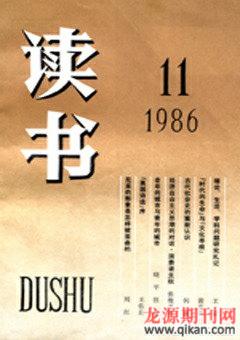人类“做的是同一个梦”
兰 明
日本。大约一个世纪前。一位年青的诗人,在留下了他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诗剧后,寂寞地化作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墓碑①。
诗人留下的这部诗剧,在它刚刚问世时,说不清到底是因其晦涩、艰深;还是因其沉重、压抑;或是因其“情节不整,不知所云”;抑或因其“正经得有些天真”,“严肃得有些逼人”,有人竟这样晒笑道:“倘若没有超凡的耐力,便不能卒读三页”。
然而,就是这部诗剧,在“二战”后的日本,却同其主人并时“名声大振”。人们似乎于一夜间突然悟到了它的价值,感受到了它所蕴含着的“震慑人心的魔力”。不仅文学家把它视为珍宝,剧作家几次把它搬上舞台,就连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家也都不吝笔墨,每每借它大发议论。
这位年青的诗人,就是被后人封为著名文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的北村透谷。这部长篇诗剧,就是八十年代又一次被搬上戏剧舞台的《蓬莱曲》。
《蓬莱曲》正式发表于一八九二年。它不仅是作者自认的“处女作”,也是日本近代戏剧史上第一部长篇诗剧。它的外部情节线索,粗粗说来应是主人公柳田素雄因厌恶污浊的尘世,拚命挣扎着逃往蓬莱,但蓬莱山也和尘世一样,到处有魔鬼横行,这使他大为失望。就在此同时,他痛切地感受着自身内部的矛盾冲突,并为此更加烦恼。在与大魔王论战后,他决意脱去躯壳以求新生,悲愤地倒在了“自古本是瑞云
对于前者,即“我”与社会的矛盾,作者把它完全凝聚到了“囚犯”与“牢狱”这一组尖锐对立的形象之中。从此设喻中透射出来的强烈的“我”与社会的冲突意识(它迫切而又清醒地要求两者统一,互为表里),本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思想标志。它在资本主义的后进国日本,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可在文学领域却率先出现如此明确而大胆的设比,自然不能不令人叹服作者的识勇。然而,作者的卓识及《蓬莱曲》的魔力,或称未来价值,我以为,主要还在于后者。即在于作者对主人公自身内部“人性”与“神性”冲突的“记录”,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人类自我认知发展情态的“典型”片断。
本来,“神性”与“人性”、精神与肉体的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人们到了近代,才较普遍、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文学家们极力要在作品中表现这一主题,也是近代的事情。
在古代,当哲学家们把目光集中于本体论的探索时,文学家们在作品中“突出强调的是职责和完成”②即外部要求与实现之间的矛盾,人的主观世界的真实情形尚未得到专门光顾。“神性”与“人性”,精神与肉体,两者处于人类童年时代相安无事的状态。到了中世纪以至整个封建社会,则是由神学(西方)和佛教(东方)统治了一切,它把灵肉对立推到了顶点,不仅承认精神有支配肉体的无上权力,而且为了抬高精神,恣意诋毁肉体,甚至“连最无辜的感官的快乐,也成了一种罪恶”③。文学和哲学一样,成为寻求获救的忏悔和劝善惩恶的教义。直到人类摆脱了这个黑暗的世纪,而向资本主义过渡并至其上升发展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才使哲学由神学变为世俗的、科学的学问。当哲学家们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提出了主客体关系问题,给予认识主体以科学的前所未有的独自地位时,文学的内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近代诗中突出强调的是意愿与完成之间的不协调”。要注意的是,到这时,行为主体自身的要求,开始获得中心位置。人们的目光由了解外部世界,相对集中转向了认知自我。
如果在文学世界里追根求源,这也许可以一直追寻到俄狄浦斯猜破斯芬克斯之谜。但更切近地说,它初始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诞生。哈姆莱特一方面认识到人类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一方面又目睹了人类的卑俗丑恶,这使他(人类)第一次体验了“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精神危机,他(人类)的面容从此蒙上了难以拂却的“忧郁”——可以说,就是这危机,这忧郁,促使人类真正开始了探寻“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历程。自从莎士比亚的“忧郁王子”出世后,人们为摆脱“忧郁”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却始终不得奏效。一直到了十八世纪末,“浮士德”从德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歌德的笔下站起④,人类的自我认知才发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把自身的矛盾性、自身的美丑,进行科学的、世俗的表现与理解。浮士德率直地向人们道出:“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
大约过了二十年,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来之前,英国诗圣拜伦推出了他的曼芙莱德⑤,与浮士德唱和:“我们,半属泥土,半属神性,/同样地不适于沉落或飞翔。/以我们这混杂的本质,/造成它那元素间的相互冲突,/呼吸着腐朽与骄傲的气息,/并为那些卑微的欲望与高尚/的意志奋斗着。”
从浮士德到曼芙莱德,这个声音,在欧洲大陆回荡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在亚洲产生了共鸣,这就是北村透谷的《蓬莱曲》主人公柳田素雄的自白——
饱受社会“大牢狱”摧残之苦的柳田素雄,在几经反复,终于大叫一声“从此后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毅然与“囚牢中的家”诀别的同时,发现自己正被一种陌生的、更为深刻的痛苦纠缠着,他对此审视再三后慨然表道:“在我的生命的内部,/一定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性情。/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这两种性情在我的内部/片刻不停地斗争。/它使我疲倦,/使我烦闷,/使我患病,/将直到熬尽我的生命。/……”
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小的时差,而恰是这个时差,形象地说明着人类自我认知、精神发展的方位走向,标志着人类不同群体及分子,在人类自我认知发展历程中的位置。从透谷对相互冲突的两性的价值取向、情绪色彩,以及最后的结局设置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自后诞生于日本的《蓬莱曲》与它的承体、先行者《浮士德》和《曼芙莱德》,在宏观上,基本分属于人类自我认知同一发展阶段的两端:近代科学理性支配人类认知自身的初始和临末。而从微观透视角度,我们也不难发现《蓬莱曲》区别于其先行者的异样因素:近代科学理性危机的露头。
透谷在《蓬莱曲》中,首先把“人性”和“神性”放在同一层次进行审度,给以共同的肯定。这与歌德和拜伦基本一致。主人公柳不仅意识到了两者的存在,而且深知两者是“共同长成”,两者间的斗争,是他生命的动力。
记得海涅在讲到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制度的革命任务时曾这样说过,“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重获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与精神和好如初”⑥。我以为,这里的为物质恢复名誉,也就是为“人性”即俗性——世俗要求恢复名誉。由此,《蓬莱曲》对于当时日本社会虚伪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的冲击,对于时代审美意识的进步作用,自该是不言而明的了。
进一步,我们看到,透谷虽然肯定了“神性”,也肯定了“人性”,但他最终的抉择是明确的:崇拜神性。他的柳田素雄面对群魔之首的威逼,可以置生死于不顾,就在于他“是堂堂义之子,与你(大魔王)不同的是‘灵魂”。为了强调“神性”,透谷有时不免流露出排斥“人性”、甚至对“人性”嫉恶如仇的情绪。在他那里,这两者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全“和好如初”。从根本上讲,曼芙莱德和浮士德也不例外。文学家到底不可能彻底超越时代历史的局限。
透谷为他的主人公找不到统一两者的途径,但又不愿亵渎“神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神性”的完好,便只有让他的柳田素雄“脱去躯壳”,而使灵魂再生于“慈航仙境”了。这个结局设置与歌德为浮士德安排的、由女神将灵魂引到天堂的归宿,很是相近。象这种以毁灭肉体来保全精神,从而解决自身矛盾的处理,在近代文学中是很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它似乎还有些宗教的味道,但其实质已根本不同。它表现着作者对人类理性的顽强追求。但是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同样是对理性的希望与追求,然而仔细分辨便可以发现,透谷远不如老者歌德那样乐观。这不仅因为他无意为柳田素雄选择一条在改造大自然的实践中实现自我的途径(象歌德为浮士德选择的那样),还因为他的柳田素雄最后倒地,不是由于看到了“美”,而是感到了“唯有生活才怪诞”,从柳田素雄身上已经明显流露出理性危机的苗头。
我们知道,后来导致理性危机蔓延成全人类的普遍情绪的直接契机,是世界大战。“是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类的支柱垮了”(卡夫卡)。在西方,以非理性主义为思想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文坛主角;在日本,由于痛感“理性教给我的,终究是理性的没有力量”(芥川龙之介),而使有名作家随步透谷后尘⑦。人类似乎对自身完全失望了。然而,我们很快明白,这种判断有所失误。因为倘若换个角度考虑,我们便会发现,理性危机也好,文明危机也罢,都是人类发展进程必然伴随的逆反现象。它并不是左右人类的决定性力量。即使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那里,透过怪诞的外装,我们不是也还可以看到,人类仍在以顽强的意志追寻着自身的奥秘,寻求驾驭、发展、实现自身的道路吗?“人类的支柱”也许有过“垮了”的瞬间,可它现在不是还在挺立着吗!
自问世到战后,《蓬莱曲》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才与其主人一道,在本土上幸遇知音。笔者以为这个“情节”很耐人寻味。它似乎可以表明,日本民族在战后已从整体意义上,接近了先驱者所达到的高点,进入了科学认知自我的阶段。而从此时荒正人于《第二青春》中提出的“从利己主义走向高层次的人道主义”口号,以及坂口安吾的“先堕落而后有新生”的宣言中,我们则可以窥知到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先行者们,对于“我是谁”的认识,已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把人从天上彻底拉回到了地上。在这一代人的眼里,利己主义(人性、俗性)和人道主义(神性),“将作为纯粹一元的东西,作为覆盖人类始终的东西,进而作为如同一日三餐一样日常的东西而被把握”。虽然我们还没有充分依据,证明这种认识的科学性及其在人类中的代表性,但我们仍无法否认这比“升天”、“成仙”,都更为踏实,更接近人自身的真实。至少,人要真正“上天”或“成仙”(仍不失人的特征),必须先经历这样一个“彻底落地还俗”的过程。
实在难以估测,人类要真正完成认知自身、实现自身,还要经过怎样漫长的世纪,但我们依据文学大家们留下的、描绘着人类自我认知发展情态的杰作,已经发现:从古至今、东天西土,人类“作的都是同一个梦”(比利时万莱贝格《夏娃之歌》)——认知和实现自身。这至少可以使我们在今后漫长而艰苦的探索道路上,时常感到慰藉。
(《蓬莱曲》,兰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0.80元)
①日本近、现代作家多自杀者,这位年轻诗人首开先河(一八九四年五月自缢)。对此自杀之因,大则可以说是学术课题,在此不宜论说。
②歌德《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③海涅《论德国》,第30页。薛华、海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版。
④《浮士德》第一部发表于一八○八年,引文出自第一部第二场《城门外》,写于一七九七年,据钱春绮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版。
⑤《曼芙莱德》发表于一八一七年,评论界多认为这是“《浮士德》之予”。引文据刘让言译本。平明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版。
⑥海涅《论德国》,第264页。
⑦芥川龙之介,日本短篇小说巨擘。一九二七年七月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