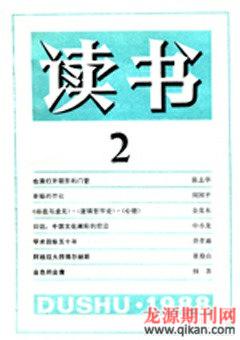也请打开朝东的门窗
陈志华 等
解放初年,有过一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高潮。拿我们建筑行业来说,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好东西。从城市规划、工业建筑、住宅和居住区设计到建筑工业和建筑管理,都面貌一新,总之一句话,我们大体上学会了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尽管有一些做法现在已经过时,确实有相当多的现在还在起作用。不过,我们也从苏联学来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比方说,彻底否定西方现代派建筑,大搞复古主义。那一套理论,到现在也还在起作用。不久前还有人旧话重提,说当初苏联人如何批判了“世界主义”,其实,苏联人自己早已把日丹诺夫搞的那场运动反掉了。
过了十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于是,苏联的建筑书籍和杂志不大看得到了,没有人再敢说借鉴苏联经验,即使想,也难办了。
先是反帝,反掉了西方建筑,后是反修,反掉了苏联建筑,政治斗争吞没了一切,把我们跟世界上所有建筑经验都隔绝开来了,于是,就只好吹嘘“干打垒”。现在,噩梦初醒,痛定思痛,大家都不赞成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再打政治棍子。不过,阴魂难散,一年多之前,还有人痛斥反对搞大屋顶的人“党性有问题”。好在大形势变了,这一棍子不得人心。
开放以来,情况好转,我们可以比较认真地评说世界建筑的成败得失,有所借鉴了。不过,朝西的门窗开得早而大,朝东的门窗开得迟而小。从西门西窗涌进来的建筑成就大开了我们的眼界,对提高我们的建筑水平确乎好处很大,这几年的进步真是小看不得。话说回来,那些建筑思潮和那些高级旅游设施之类刮起来的旋风,弄得我们有些人怕真有点儿晕乎。
晕乎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人忘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筑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建筑,毕竟还应该有所不同。他们挑战式地发问:差别何在?
差别当然是有的。
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把直接为普通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服务的建筑放在第一位,把为普通劳动者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学习、休息环境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建筑和城市,要体现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平等关系,要慎重而积极地体现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里合乎逻辑地出现和发展的新动向。建筑要参与和推动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观念的建立。我们的建筑,还要激励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样去看问题,我们就能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筑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是不大一样的,倒不是说社会主义者住进资本家的旅馆就会处处觉得不大方便。
当然,说把为普通百姓直接服务的建筑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它们的造价要最高,要占据城中心最好的地段,而是说,在宏观的考虑中,它们是最主要的;说建筑要体现人和人的平等关系,并不是说要搞绝对平均主义,而是说,至少不要搞那么特殊的长官楼、书记院,不要搞那么多
贵宾席、贵宾入口;说建筑要推动生活的发展,并不是要再搞生活公共化的公社大楼,而至少是不要麻木不仁,对生活的变化视而不见,以不变应万变,或者限制了一切变化的可能性;说建筑要激励人的创造性想象力,并不是要凭空虚构,而至少是不要再仿古复古,用传统束缚自己。
当然,还要说一个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建筑师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如果整个社会还
这就是建筑的价值观问题。只要这个价值观不变,对苏联建筑就不会有多大的兴趣。目前,这份兴趣甚至还赶不上对日本的。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得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深入,不过,也可以通过朝东的门窗涌进来的信息本身,多了解它们一分,就会对它们增加一分兴趣。吕富
就历史的价值说,苏维埃的建筑有两段应该特别重视,一段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一段是五十年代中。就实际创作的借鉴价值说,需要特别重视的是近三十年来平稳的发展时期,虽然最近对它有尖锐的批评。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这个时期,开始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思想解放,结束于个人迷信建立后的用行政手段统一思想。这是一个很富有创造精神的时期,虽然有许多荒唐幼稚的失误,更多的却是严肃的有成效的探索。苏联建筑师在这时期里不但当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先锋,而且大多自觉地把建筑创作跟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这样也就改造了建筑本身。
一九二○年十二月,塔特林的一个助手写了一篇关于“第三国际纪念塔”的文章,说“它鼓励我们在建设新世界的工作中有所创造”。两年之后,一九二二年,甘发表了宣言性的著作《构成主义》,认为在俄罗斯既然发生了激烈的政治革命,艺术观念当然也要发生激烈的变化。他写道,“站在十月革命一边的艺术家,……应该实际地从事建设并表达新的、积极的劳动阶级的有计划的目标,这就是建立未来社会的基础。”又过了两年,一九二四年,构成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金兹堡在他的《风格与时代》里提出了关于建筑创作的三个观点,第一点是:“确认建筑和人工环境对社会变化的促进作用。”
建筑要促进社会的变化,也就是促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思想太重要了,二十年代许多建筑师都明确地认识到它,并且努力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城市规划和工业建筑里全新的探索不用说了,就只说公共建筑里的剧场。老派建筑师如福明,新派建筑师如维斯宁兄弟,都尝试把观众厅做成统一的散座,没有包厢和其他的特权者的座位,维斯宁兄弟说:“那种座位失去了我们这个没有阶级的、彻底民主的社会的基本思想。”而“圆形大厅最能适合观众平等团结。”在住宅方面,有过一场很热烈的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探索,设计了许多“公社大楼”。因为把家庭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造设想得太简单了一些,有些设想过头了一些,打算消灭家庭,所以“公社大楼”没有成功。不过,这种探索并不是毫无道理,新的探索还在进行,这就是设计和建造“新生活大厦”,“为各种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的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一九六六年还由国家建设委员会和苏联建筑师协会组织过一次公开的设计竞赛。
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苏联建筑师为促进社会关系和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作的探索,生气勃勃。如果我们怀着同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我们就会对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建筑作出很高的评价,发生浓厚的兴趣。当然,也会对这个活跃的时期的结束表示惋惜,而把导致它结束的原因引为鉴戒。
五十年代中期这一段历史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结束了三十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年的复古主义和装饰主义的统治,开辟了直到现在的三十年的富有创造力的发展。
在复古主义和装饰主义统治期间,苏联建筑在一些方面停滞,在
一些方面甚至倒退了。问题不只是在形式上的复古和装饰繁琐,而是在基本观念上,直接为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的建筑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占据着主要地位的又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用辉煌的建筑来歌颂时代的伟大和光荣,也就是神化了的领袖的伟大和光荣。于是,建筑的封建传统恢复了,它被重新定义为艺术,强调它的形象的思想审美意义。一九四五年,国家建筑委员会主席莫尔德维诺夫写道:“建筑,这就是艺术,……建筑是为满足人民的审美要求服务的。”一九五三年,建筑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库洛奇金套用了一句名言的格式说:“苏维埃建筑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苏人民不断增长着的审美要求。”可是,尽管给许多城市住宅、大量性公共建筑物和工厂套上了宏伟的古典外衣,它们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担当起那个光荣的任务。因此,有些理论家干脆把它们开除出建筑之外,叫它们为“构筑物”,照建筑科学院院士马扎的说法:“决定建筑特征的因素是艺术。”
建筑的封建传统一恢复,必然导致形式的复古和烦琐装饰。于是就下功夫把现代派建筑批倒批臭,说它们是没有人性的冷冰冰的方盒子,是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对现代派建筑的诞生和发展立过功勋的苏联的构成主义被打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有一些杰出的建筑师从此靠边站。反过来,倒吹嘘作为沙皇俄国宫廷文化的古典主义建筑和帝国式建筑多么富有人民性,非继承这个传统不可。建筑师的创造性窒息了,他们没完没了地在陈旧古老的古典框框里做文章,只能靠变换装饰题材讨点儿新花样。
当然,在复古主义和装饰主义的统治下,苏联建筑也并不是全盘都坏了、错了。五十年代,我们一边倒的时候,虽然学来了那一套复古主义,毕竟也还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不过,复古和虚假装饰阻碍了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施工缓慢,功能质量很差,而造价却高得要命,人民大众的居住状况因此长期不能改善。一九四五年,布宁教授说:“为了美化城市就需要一些在功能上没有根据的建筑物,特别是圆顶和高塔。”那时候,卫国战争刚刚结束,老百姓还在废墟里栖身,说这样的话未免太超脱了。糟糕的是,这类在功能上没有根据的东西真的流行起来,连普通住宅都有扣上尖塔和圆顶的,钱花得象淌水一样
这种情况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召开了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一年之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第二次全苏建筑师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坚决地批判了复古主义、装饰主义和铺张浪费,迫切地要求迅速提高建筑工业化的水平,明确地重申了住宅和大量性建筑的首要地位,热烈地鼓励建筑师的创新精神。二十年之久的复古主义和装饰主义的统治终于结束了。
就在一九五五年,我们也批判了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复古主义。
这几年,我们很有一些人重弹五十年代初年的老调。也有人受到美国传来的文化寻根热的鼓舞,用新的理论提倡复古主义。看来,再温习一下五十年代中叶的苏联建筑史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次全苏建筑师代表大会之后,苏联建筑的发展比较平稳,有不少新的探索,成就很可观。我们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听说苏联建筑师创作出什么轰动世界的特殊作品,就以为苏联建筑没有多大意思。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一九八二年,我跟来自二十一个国家的二十三位建筑师一起生活了半年。有一天我问他们,世界上哪个城市最美。七位到过莫斯科的建筑师一致说莫斯科最美。我很吃惊。他们解释说,世界上有些城市里有伟大的建筑杰作,但是,一般居民并不见得天天都能去欣赏它们,而他们日常生活的建筑环境往往不很好。在莫斯科,平民百姓的生活、学习、工作和休息的环境很好,这是他们天天都在享受的,所以,应该说莫斯科最美。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几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倒很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筑的价值观。这大概是因为建筑师的职业本身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缘故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十日
(《苏维埃建筑》,〔苏〕A.B.PЯБyШИН,И.B.ШишКИHA合著,吕富
陈志华/鲁德涅夫/尼各拉娃/高玛洛娃/切尔尼霍夫/切尔尼霍夫/伏洛尼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