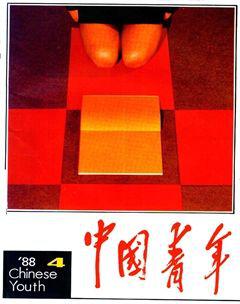心比天高
罗雪莹
笔者前记:3年前,艺谋还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无名小辈。如今,他已成为影坛瞩目的名人。他拍的《黄土地》,获金鸡最佳摄影奖;他在《老井》中饰演陈旺泉,夺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桂冠;他最近独立执导的《红高梁》,又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熊奖”。大伙儿夸他是“奇才”,戏称他是“得奖专业户”。作为朋友,我当然为他的成功而欣喜;但感触最深的,是他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艺谋出身于军人世家,大伯父解放前夕远走台湾,二伯父率部投奔延安未成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死后却一直背着罪名;父亲因毕业于黄埔军校,便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头衔在新社会当了30余年的活尸。这样的家庭背景带给艺谋的是什么,大家可想而知。用他的话说,“我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文革期间,他下乡插了3年队,在纺织厂当了7年搬运工。他爱上了摄影这桩花钱的事儿,卖血换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海鸥”并不名贵,艺谋却拿它拍出了获全国摄影一等奖的作品,并征服了爱才者的心,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26岁上破格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他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但因没有“路子”,虽家在西安,却被分配到边远的广西厂。他和一道分去的几位大学同窗剃头明志,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这一发愤之作。继之而来的《黄土地》,更使影坛对他刮目相看。他本可以驾轻就熟地当一名出类拔萃的摄影师,但强烈的主体意识却使他渴望在创作中成为一名统帅。他深知电影说到底是导演的艺术,于是便决心改行当导演。在西影厂长吴天明的信赖和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最近,笔者曾与艺谋作过一次长谈。下面披露的部分谈话内容,或许有助于青年朋友了解艺谋其人。
笔者艺谋,这几年你一直在酝酿着当导演。在众多可供拍摄的题材中,何以选中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张艺谋1986年春天,朋友把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推荐给我,一口气读完,觉得这东西挺棒。那高粱地里如火如茶的爱情,那无边无际红高粱的勃然生机,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们这回拍电影,在山东种了一百亩高粱。体验生活时,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浇水除草。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棵棵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窜。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中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梁地里的感觉一样,觉得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只是觉得一篇小说有点单薄,就把其言的另一篇小说《高粱酒》合进来,互为补充。
笔者《红高粱》正是一部题材和创作者自我达到高度融合的作品。通过一个现代神话般的传奇故事,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精神的力和美,而且看到了“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般的血液在你的血管里流动。
张艺谋应该说,《红高梁》是我的一次情感和心态的展示。人创造艺术,就是想对世界、对人生发言。如果完全采取出世的态度,那就别折腾电影这事儿,到深山拜佛打禅好了。所有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是人创造的一个精神世界。现实中得不到的,就去艺术中寻求。我这个人的性格从小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也活得很累,一点儿也不松弛。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这一情感能够在艺术中得到渲泄。人都是如此,自己所缺少的,便充满希望去汲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在我内心深处,对爱和死都是顶礼膜拜的,认为它们是生命中很神圣、很美丽的东西。现今大家都在谈关于文化的各类学问,文学和电影也在争相表现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但总的来看,理性太强,人物形象干瘪,有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不多。我想作学问的目的,还是要使人越活越精神。你把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重新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敢恨敢爱,敢生敢死。不能一肚子文化,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这几年,我深感中国人活得太累。中国人原本皮色就黄,伙食又一般,遇事又爱琢磨,待一脑门子官司走顺了,则举止圆熟、言语低回,便少了许多做人的热情,半天打不出一个屁。红高粱》小说中有段话,我非常欣赏,奠言写道:与生活在高梁地里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我觉得,造成我们民族精神萎缩的原因之一是穷,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而我偏要在影片里把人的精神气儿往高里提。咱们穷归穷,可往全世界150多个国家跟前一站,劲头儿得搁在那儿!咱们跟洋人比,只不过个头儿低点儿,穿着差点儿,可要让洋人觉得咱们人活得挺棒!气质挺有魅力!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张张扬扬、轰轰烈烈,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要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老百姓过日子,每日里长长短短,恐怕还是要争这口气。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要说这片子的现实意义,恐怕这是一层。
笔者有同志看过《红高粱》之后,认为它既不够“探索”,又不够“主流”,也不够“商业”。很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艺谋《红高梁》这部影片的确是个“杂种”,好像什么都有点,但跟哪头都够不上,属于野路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探索。我不同意把电影简单地归类为主流电影、探索电影、商业电影,这种归类法反映的还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艺无定法,技无定规,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就像我们影片中的一句歌词说的那样:“你朝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希望评论界的同志对第5代的作品不要只寄予一种期望,我们自己也不愿拘泥于一种模式。红高粱》的拍摄,实际上反映了我创作心态的不安分。我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如果一个艺术家的最高目标是完整,那么,他的创造性活力可能会受到追求完整的抑制,这样,走向完整就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我看电影时,绝不看它如何圆熟得天衣无缝,而是特别关注和推崇其中洋溢着的创造性活力。这几年,无论干摄影、当演员、做导演,我的每一次创作,都是想方设法和自己过去不一样,和其他人不一样。当然,这个“不一样”不是盲目的,而是眼界放得比较开,经过审时度势、左顾右盼之后的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比如《一个和八个》中的不完整构图和黑白灰影调所产生的雕塑般的力度感,一反过去中国电影画面的“贪花好色”,这在当时真是大逆不道。拍《黄土地》时,有感于许多影片忽略造型的剧作意义,我们又非常自觉地在画面中注入强烈的思想内涵。但是,当一大批电影铆着劲儿朝哲学层次上奔时,我就想自己能不能换个路子,拍另一种电影?这种电影既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内涵,又有比较强的观赏性,它的思想是由引人入胜的艺术形式包起来的。红高粱》是我发挥电影观赏性的一次尝试。电影是一次过的观赏性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人看一遍的电影。它没想负载很深的哲理,只希望寻求与普通人最本质的情感沟通。这种感受有文化的人可以写成长篇大论,没文化的人一句话就说完了。有个青年司机对我说,看了《红高粱》之后觉得特痛快、特来劲儿,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笔者当你的价值终于被社会认可时,你有没有一丝志得意满的情绪?
张艺谋你跟我交往这几年,什么时候见我沾沾自喜过?虽然这些年我的路走得比较顺,但从不敢忘记我是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过去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某个单位当一个摄影干事,进电影学院摄影系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我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他们都让“文革”给耽误了,现在拖儿带女,为电大文凭,为子女入托等琐事所缠扰。他们说:“艺谋,你现在出息了,真跟我们不一样了。”但我深知自己是从他们那一堆儿里出来的。今天能干电影,纯粹是出于机遇。我的许多同代人都想很好地发展自己,都在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争,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个机会。而所谓成功,实际上是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所以,我特别珍视自己现在所获得的这些条件,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兢兢业业地把每件事干好。拍《黄土地》,有一天我们在外景地坐着等天气。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黄土高原。凯歌对我说:“艺谋,在咱们82届各系153个同学中,有一点你最强烈—心比天高。”这四个字的概括不一定准确,如果让我自己说,那就是始终对自己不满足。我每拍完一部作品回头看,都觉得毛病太多,其实自己可以拍得更好,并且一定可以争取下一部拍得更好!下一部拍完后我又会觉得:我还是没有做得更好。我可能到死都对自己不满意。
这几年,找我拍电影和电视剧的人不少,但我从没有为了挣钱,去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倒不是自视清高,而是感到人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就算我能活到60岁,去掉一半睡觉的时间和15年少小不懂事的时间,再去掉各种活动和杂事,真正能干事的日子也就十几年。往顺利里说,就算一年能拍一个,我这辈子总共还能拍多少部?所以,我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我觉得我这个人活不长,也不希望自己太长寿。因为后浪推前浪,人到晚年还能始终保持对社会、对时代的创造活力,是很难的。当我最终意识到我已经才思枯竭、力不从心,只能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玩“虚”的时候,那种痛苦是不堪忍受的。
笔者在平日的交谈中,似乎没听你五体投地地崇拜过哪位艺术家,是吗?
张艺谋 我的确没有彻底地崇拜过什么人,没有由衷地拜倒在哪位大师的脚下。我的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克制,潜在的却是咄咄逼人的气势。我永远不服气,永远铆着一股劲儿,觉得自己可能比许多人做得更好。即使对世界级的大师,说心里话,心里也没有服气过。我望尘莫及的只是人家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演员条件,以及导演的权威地位。假如给我同样的条件,让我在那种开放性社会和开放性知识结构中生存,我肯定比他们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