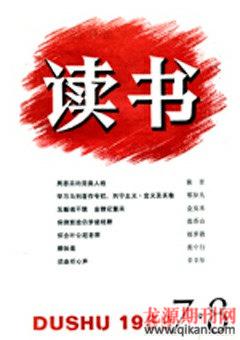周恩来的完美人格
陈晋
当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相继离开人世以后,人们发现,倒是生前不那么争邀事功,常常退让,从来没有做过名义上的一把手或跨进接班人行列的周恩来,亲切地矗立在人格境界的峰颠。这并非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好人人缘好。恰恰相反,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党内出现的分歧,周恩来都很少能置身事外。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他逝世的五十五年的艰难征途上,他竟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党或国家的核心领导。这常常使一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感到难以理解(尼克松说这是创了世界纪录),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谜。
读完金冲及同志主编的《周恩来传》(一八九八——一九四九),虽然这部洋洋六十万余言的政治传记,只写到建国前夕,但从那丰富、准确、平实的记叙中,多少可捕捉到这样一个消息:周恩来固然是靠他的才干和贡献,赢得人民的特殊尊重,由此为自己构筑起一座巍巍丰碑;还应该看到,在这丰碑的另一面,也记录着他那独具魅力的人格内容。
一
从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来看,如果说,毛泽东富于幻想并乐于用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性格,与韶山冲那片封闭的农田和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有关,那么,《周恩来传》则告诉我们,周恩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那些发挥了巨大潜能的性格,多少孕育于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四处漂泊的生涯以及温馨的母爱。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年轻守寡,从不外出,于是也不许童年的周恩来外出,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本文所引事例和文字,均出自《周恩来传》,以下不再注明。)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则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周恩来小时经常在生母跟前观看她如何处理家族事务,学得一些办事方法和能力。家庭败落后,迫使十岁左右的周恩来开始扮演“当家人”的角色。熟悉中国民俗风情,明了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在近代中国,维系一个大家庭的生存与主持国务活动似乎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至少在对“当家人”的性格素质上的要求上是这样。好面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也丝毫不可忽视。《周恩来传》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位少年把亲戚的生日、死期一一记下来,贴在墙上,到时候便去借钱送礼,磕头应酬。这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周恩来从两个已经去世的母亲那里,自然地继承下来的两种性格能力,是他能够扮演好当家人角色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政治活动家,这或许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自幼养成的,是因为压抑(由于父亲的严格管束)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环境和需要,周恩来全然没有,他自幼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一个才具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正是这种复杂而精明的性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长并丰富多采。——这句话是尼克松说的,我觉得还算准确。《周恩来传》的作者记叙传主早年的生活,不失时机地突出他的两个母亲对他的影响,不知是否也试图要说明这一点。
辗转漂泊清江、淮安、东北、天津、日本,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对其人格个性的影响,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丰富阅历,开拓胸怀。从《周恩来传》的记叙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传主这样一种心理历程:从对家族的伦理情感的渴求,走向对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探索。
十六岁终于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无疑有一种摆脱了空间和心理上的局限的轻松和亢奋,自幼漂泊的周恩来,则始终承受着浓烈痛苦的怀乡思亲之情的折磨。与怀乡思亲相伴而生的,是对和睦的群体关系的寻求。这或许是一种情感转换吧。但是,传统有志之士的激励(在东北读小学时,课余爱读《史记》、《离骚》),对山河离乱的国家命运的忧患(东北特殊的爱国气氛对他的薰染),以及自幼养成的责任心,毕竟使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观:一个人不能脱离公众“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生活”,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为朋友,为集体办事,赢得老师和同学的高度评价。《同学录》中有关他的评语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可贵的是,周恩来这种急人好公的利他行为,很少有外在的功利色彩,不是眼下人们爱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诚实地表达过这样一种心情:“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则觉得“倍有乐趣存于中”。好一个“乐趣”,他的“服役”,全然是一种品行本色,是那包裹不住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流泄。正是从重道德情感的周恩来中自自然然地走出了一个重群体义务的周恩来。这就注定了他在一生风雨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割不断自己和社会、和朋友、和事业、和使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年轻时在自己的精神几近崩溃的关头,他也会因情感和义务的召唤,从痛苦绝望中挣脱出来。这一点,我们感谢《周恩来传》的作者提供了他旅日期间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反映,由于他初到异国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加之家庭窘境的打击,还有前景未卜的入学考试,周恩来曾考虑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的思想来解脱尘世的痛苦。但是,“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象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上述出于性情本色的集体主义义务感,日后便十分自然地溶合入这位后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人格基础。在革命的队伍里,虽然都有一致的信仰,并肯为它献身,但有这种人格基础,和没有这种人格基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乏骄躁、浮华、虚荣、盲动,而周恩来却总是显得那样的真诚、平实和坚韧。而且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那种缺少人情味的干巴巴的共产党员。在后来他已经成熟和伟大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他口中听到那句本来属于宗教教义的道德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破不了“情关”,断不了“有缘”,正是他在党的事业遭遇多大挫折,也会勇往直前,在个人名誉受到多大误解,也不会拂袖而去的心理基础。
《周恩来传》告诉我们,他在南开上中学时,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绝少有令人敬而远之的领袖欲权力欲。他认为,“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不计利害;……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能涵养虚心的英雄观,不计个人利害的功名观,确实有他高雅脱俗的地方。
由此,从青少年开始,周恩来就很看不惯那些虽然不乏才干作为,但却内怀邀名之心,爱出风头的人。他也不是完全不重视个人的“名”,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他甚至把它视为“人生的第二生命”。但他心目中的“名”,更多的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名誉”,而主要不是反映个人利益的“名位”。显赫的名位,并不必然带来高尚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名誉的罪人。协调二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重名誉而不能重名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的功名利益的关系。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中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奋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如果要从人格境界上找原因的话,或许与在实践中(在理论上很少有人公开地一味强调个人私利)未能摆脱“私于个人”的困扰有关。这就在“道德”上先自降了几等,最终连自己尽力创造的某些“文章”也受到损害。周恩来能获得举世赞誉,与他青少年起就注重不私于个人的人格设计,并一生遵奉,不能没有联系。
二
撰写伟人的政治传记,特别是我国撰写当代领袖的传记,通常当传主处于政治上走向成熟以后,作者的笔墨主要倾注在他所从事的同时代背景密切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贡献方面。《周恩来传》也是如此。在第六章(全书三十七章)写到他赴欧勤工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领导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以后,除了引述其他当事人对周恩来的个性、品德、作风的印象和评价外,较少有机会空出笔来直接勾勒他的内心世界,表现他对自身人格完善的探寻。这固然是因为,描写一个正在苦苦探索的青少年的内心世界,与描写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的人格品貌,在分寸的把握上有不同难度,同时也由于材料的限制和传主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过于丰富。但即使这样,该书在写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也常常在同他的战友的比较中注意表现周恩来独有的个性作风。这也是该书作者的一个很可贵的意图。金冲及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到:如果从这本书中看不出周恩来的个性才能,《周恩来传》岂不成了一部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史了吗?换一个角度讲,只要是忠实地并且尽可能具体地记录了传主在面对种种复杂而棘手的政治事件时是怎样思考和处理的,他的人格品貌多少总会蕴于其中。至于如何体验和分析,是读者的事情。
理性与情感,是革命家较难处理的一对矛盾。只讲理性不讲情感,或者把某些本来正确的道理和原则推向极端,难免把它们变成生硬的教条,似乎革命家就应该有一副刻板的冷冰冰的面孔,这容易使革命队伍缺少一种很难用理性语言说清楚的亲和力。反过来,如果以丧失理性原则为代价,一味讲求情感的融洽,或者用情绪化的态度从事政治活动,同样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应有的品格。
从《周恩来传》的大量描写中,我体会到他有少见的理于所当理,情于所当情的分寸感。
中国人常用“刚”与“柔”来评判人物的性格。“刚”包含着勇敢果断、坚强不屈,“柔”包括着通权达变、温和忍让。至刚易折,至柔少志,这是普通的道理,对一个现代革命家来说,也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在和周恩来接触过的人的评述中,我们大量看到的是他的柔的一面:温和、谦逊、平静、忍让。如果据此认为他在是非面前缺少勇断,近乎世故,更未必公正。从总体上看,周恩来属于勇于所当勇,退于不得不退的革命家。更多的时候,是寓刚于柔,融韧于忍。这或许就是古代圣贤津津乐道的那种外圆内方的人格品性吧。这种品性在政治斗争中的意义是刚强而不固执偏激,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的确,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比较看起来他往往调和,有时妥协,做自我检讨的次数也算是比较多的一位。这与他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的政治见识有关,与他通权达变的灵活性和避虚务实的工作态度有关。从中也可体会到他的多侧面的性格,丰富的智慧和经验,还有正直、诚实和毅力。特别是他的忍让涉及到党的事业大局时,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外圆内方的人格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
对于政治家来说,意志、权力和地位是不可缺少的,完全失去这些,也就无所谓政治家。革命领袖也不能回避这一点。革命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怎样处理权力地位与集体事业的关系,权力地位靠什么方式获得,它是为某种目标理想奋斗的手段,还是目标理想本身。
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党,不可能是朝气蓬勃、进取有为的党,一个没有相应的组织纪律和不服从权威的党,则是一个涣散的缺少整体力量的党。一九二二年入党不久,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自觉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在理论上认识和宣传这个问题,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不会太困难,重要的是实践,特别是在个人意志的张扬伴随着获取和维持相应的权力地位,伴随着给其他同志乃至党的事业带来损害的时候,怎样对待。关于周恩来,我想提一下《周恩来传》记叙的他到江西苏区后同毛泽东的关系。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明显地比毛泽东高。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央局提议由周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当即两次提出:这一提议事实上让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前线无事可做,而且使自己这个中央局书记多头指挥,应该由毛任总政委。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突出地批评毛泽东的左倾倾向,再一次决定把毛召回后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再一次提出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坚持在两个办法中选一个,由周负责,毛助理,或者由毛负责,周监督。总之是要毛留在前方。如果就此解释周从这时起就相信,革命事业必须靠毛泽东来领导才会取得胜利,是难令人信服的。但从他的做法上,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政治品格: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即使由于大家折服于他的才干威望主动给他,如果有碍于党的事业,有损于他人,他也不会伸手,更不会“墙倒众人推”,从中捞取好处。事实上,从一九二八年到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做过名义上的“一把手”。这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他还有意把瞿秋白推向前台发表总结性的意见。他总是扮演用实干而不是用权力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这或许是他的个人意志和才干智慧充分发挥的最好方式。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痛苦,或因此能轻松地超脱党内经常发生的不排除权力角逐内容的斗争。相反,他经常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自觉或被迫地写检查,因为他不仅参与决策,更多的还要主持实施。有了错误,或在那些拍脑袋、唱高调的人看来有了错误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回避责任,相反还要硬着头皮去干,有时打击他的人也离不开他。就象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国际代表挖苦他的那样:“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三
从个性、才干和品德诸方面,读解了《周恩来传》记叙的周恩来这座人格丰碑上的一些文字以后,我获得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周恩来是现代中国革命家中,无论是道德品质还是政治品质都给后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影响的人格典型。这个典型说明,在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天平上流芳千古的伟人,除才干和贡献以外,还必须留下点别的“财富”,譬如怎样做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度里,似乎更不应该忽视。
不错,周恩来是一个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但他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员。他虽然不象毛泽东那样有足够的机会和明显的兴趣,乐此不疲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人格养分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途径,但是,儒家的入世、忧患,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善;道家对外在的功名利益的相对超脱和达观;墨家的勤苦和为群体的事业近乎宗教的献身精神;纵横家审时度势的机敏才智;以及法家的严谨与务实,似乎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一些影子。于是,我常常想起尼克松的一个回忆:一次有新闻记者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事实上,无论属于哪种传统的伟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周恩来同样如此。上面列举的那些传统的理想人格,既造就了他的伟大,也形成了他的局限。周恩来也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局限。《周恩来传》就谈到,他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参加整风时,曾认为自己应该从专而精入手,不要包揽许多,不要浅尝即止,要“宁务其大,不务其小”等。这类局限固然属于工作方法上的,但却来自他的难以改变的性格。又如,他遇事不走极端或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的中庸态度(毛泽东曾对此提出过批评),固然有其民主、宽容和求实这样一些积极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它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的暖昧态度有其不积极的效应。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他反冒进,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在一些重大决策上较少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他原来曾经提出过的正确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其他还有过多的自律和忍让以及不象毛泽东那样具有充分的想象力等。
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想象力是拓展新局面作出划时代的独创成就的不可忽视的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宁务其大,不务其小”的周恩来,主要以策略的灵活性和战略的原则性为特征。让自己的情感想象在决策中驰骋,能非常敏感地预测事物发展总趋势的毛泽东,则以战略的灵活性为特征。虽然这两个伟人都从传统中获益甚深,但毛泽东偏于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周恩来则偏于主体人格的构成秩序和人格的理想境界。由此使毛泽东在接受传统的同时又大胆地背叛传统,在建立革命秩序之后又往往无顾忌地打破这种秩序。这种政治品格使他具有开创时代的超凡魅力,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又使他借用这种魅力在建国后把国家当作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终于走向一个伟人的悲剧。周恩来的政治品格则主要体现在善于完善革命的秩序,实施革命的战略,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周密、可靠、信赖、稳定和协调。他不属于那种极度张扬个性意志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因此,尽管他的才干、贡献、地位和机会,都有可能使他成为“舵手”,但他始终没有,也不愿意成为“舵手”——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确实存在着那个需要超凡魅力的革命年代难以使他成为“舵手”的局限。
结果,周恩来在人格实践上获得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结局。在毛泽东晚年,他和人们的联系,大多是靠成功的经验和神圣的信仰支撑起来的。他太高、太远,他考虑的问题和做出的决策也是十分的浪漫和远大,因此人们很难用是与非、左与右的评判准则与他在同一基点上对话。一九五六年以前他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功的选择,从而使他在包括道德人格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完美无加的典型和象征(至少在一般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是这样的)。“文革”后期和结束以后,当人们发现他晚年的政治选择是把中国引向灾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情况就是另一样了。人格崇拜的重心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周恩来,尽管他也不能完全回避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某些失误中应承担的责任,但人们不愿意去计较。因为他长期主持实际工作,与人们的联系是实在的理性的,他还常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求实的工作作风,对某些极端的做法进行局部修善和抵制。更重要的是,人们理解,即使他有错误,也都不是来自某种个人的动机。人们没有理由指责一个以极大的心理负担来支撑危局的人。反过来,具有视“立功”与“立德”为一体的传统的中国人,还会自然地把周恩来塑造在人格境界的颠峰上。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包含着关于革命领袖人格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这大概就是我读完《周恩来传》以后决定拿这个题目作文章的原初想法。
(《周恩来传》〔一八九八——一九四九〕,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一版,1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