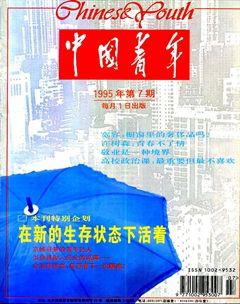京城寻梦
金油
一
北京意味着机会
时下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到了北京才知道官有多大,到了深圳才知道有钱人有多阔。不过还应该加上一句:搞文化艺术,到了北京,才体会到这块地盘儿有多重要。
北京是一座最大规模地吸收各类人才的城市,自然也包括艺术人才。这里有着最多的名人大腕儿,最多的文化机构,最齐全的高校和最好的师资,覆盖面最广的传播媒体——“到中央台磨刀,到地方上‘宰人”,这形象地比喻出平日锱铢必较的歌星影星在北京不挣钱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北京意味着机会,也是成名的跳板。古往今来,无数的艺术家、准艺术家、潜在艺术家、空想艺术家纷纷涌向北京,与他们在稿纸、舞台、银幕上演绎的故事一样,他们的事业、生活也经历着成功,失败,或喜剧,或正剧,或悲剧……
新时期以来,北京培育出各个领域里一流的艺术人才,像影视界的刘晓庆、张艺谋、巩俐、王志文,作曲界的瞿小松、谭盾、叶小钢、郭文景,歌星彭丽媛、韦唯、刘欢、毛阿敏……人们至今还能说起这样一些轶闻:张艺谋当初进京入学无奈去求助文化部长黄镇,刘晓庆在一些影片中跑龙套,中戏的老师为学习成绩一般又有颗虎牙的巩俐发出疑问,李谷一连砖头录音机都买不起,毛阿敏因漏税风波而万念俱灰……
北京就是这样造就着人,其中有一小批大获成功的艺术家,他们都成了北京人。不过,有更多的正在做着艺术梦北京梦的奋斗者。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大概有数十万文化与科技人才长期或不定期地住在北京,文化个体户近万人,其中有名气的约数百人,等着上戏“待价而沽”的演员数百人,梦想成为歌星在北京租着房子在歌厅“卖艺”的逾千人,流浪艺人聚集的村落数十处。
每当一部电视剧在北京开拍,总会有不少外地专业剧团演员和文化个体户前来应聘。北京的文化团体那么多,他们依然勇敢地参与竞争。而一些名演员深感北京的重要,干脆把家搬到北京。像在北京拍了《爱你没商量》火起来的盖丽丽在京城找到了住房,把母亲从山东接来。因《情满珠江》获1994年飞天奖的左翎近一年来始终在北京拍戏,拍完《住别墅的女人》又拍《中国空姐》。这位珠影厂的湖南籍演员说:“我爱上北京了,冬天有暖气,房间里好舒服,到哪里都是普通话,打‘面的时司机说话都好听。拍戏时有艺术氛围,在广东拍戏很久没有像在北京这样谈剧本谈人物了。”哈尔滨籍的王路遥在北京找了3套房子,他的父母和哥哥长住北京,父亲在北京写完电视剧本《周璇》,由她主演。在上海已名声大噪的李媛媛干脆投奔中央实验话剧院,搞艺术连上海都难以和北京相比。
青年歌手黄格选说,他在很多地方寻求过发展,包括广州、深圳那样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四处漂流,最后感到最理想的还是北京。歌手需要好老师指点,要有好歌曲,要新闻界宣传,而什么地方能比北京更适合呢?在日本学习通俗唱法归来的潘劲东,也一头扎到北京,他说什么地方也不像在北京,被良好的艺术氛围包围着,离开北京一长,就想赶紧回来熏陶一下,否则就该落伍了。率先在中国刮起“灵歌”风的上海青年歌手丁蕾说:我不想比较北京和上海,上海毕竟是我的故乡,不过我决心到北京来,我对北京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来自大连的作曲家徐沛东也告诉请教他的歌手们,要想取得有全国性的影响,你只有到北京来!
二
两个在京城“变法”的作家
豪华的北京五洲大酒店正准备举行长篇小说《骚土》研讨会。《骚土》那历史传奇式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的色彩及幽默精炼的语感,使它再版4次,印数达50万册!
《骚土》红了,它的作者老村红了。京城的读者在找《骚土》,京城的记者在找老村。记者们敏感地预见到,这是陕军东征又一军。但研讨会迟迟不见老村来。
直到研讨会开始,腼腆的老村从不起眼的角落站出来,人们不敢相信他是个作家。他完全是农民的装束,浑身带着黄土高原朴实的土气。问起他何以叫这么个古怪的“老村”,他说:“陕西人把死叫做‘老,假如我死,也得死在我备受磨难的小村里,故叫‘老村。不过要活,要活得有声有色,就得在北京。”
老村写《骚土》萌发于1969年,那时他才十几岁,他感受到农村的混乱、饥饿来源于农民的愚昧与文化素质的低下,他觉得哪怕写实地把村里的人与人之间的格斗表现出来,也是惊心动魄的。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想写,但连纸笔和灯油都买不起,父亲因养不活子女而几度号啕大哭。他小小的年纪就在水利工地背石头,压得他至今只有一米六的个子。他想买本书,父母骂他太不懂事。全家的确饿得吃不住劲了,他到青海当兵,其全部动机是把肚子填饱。从儿童到成年人,他剥了几层皮,只剩下一把骨头。在部队里,他写作的梦不死,前后写作的稿纸足有十几斤重,但没有人能相信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农民会写出能发表的文章。他想,如此下去,只能“老”在村落里,他要出奇制胜。他带着妻儿和仅有的几百元复员费来到北京,在远郊租下房子,一个月全家的开销只有50元。他带着稿子到各个出版社,北京的出版社太多了,这家不出找那家。北京的文学爱好者也多,左托右托总能找到一些门路。一位哲学博士看完《骚土》手稿,颇为赞赏地说:“这是又一个贾平凹式的怪才。”这位博士又推荐给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阅后当即决定出版。书一到市场,老村便由一个陕北农民变成京城的作家个体户。
老村在京城可以付得起房钱了,可以不再到大街上替人钉鞋糊口了,即使同是一个太阳,照在京城高楼大厦上的璀璨与照在贫瘠土地上的苍凉也大不一样。从文学上来讲,他心中永远留恋着老村、厮守着古老,但从观念和生活上来讲,他更希望感受现代文明,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往昔。
比老村更负盛名的是草原上盗马贼出身的名作家江浩。
江浩11岁时父母离婚,在封闭、落后的草原,这是十分见不得人的。他和一位同学吵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说:“你爹和你妈离婚,你还敢闹?”他逃离了欺侮,一头扎向草原深处,独自搭起了小棚,放马种地糊口。一个晚上,一群土匪闯进他家,抢了他的粮食又把他带走,让他当小盗马贼、盗墓贼。一次,他们凿开荣禄公主的墓,墓贼让瘦小的江浩第一个钻进阴森恐怖的墓中,江浩把公主赔葬的文物一件件扔了出来。但不久墓贼们一一落网,14岁的江浩也开始了一年半的铁窗生活。刑满后,他被遣送到科尔沁草原。在那里,他向北京的知青们学会了写字,懂得了文学,并考进了内蒙师大研究生班,毕业后到内蒙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并因创作出影片《猎场札撒》(田壮壮导演)而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力作”。从此,他不断地被邀请到北京为电影厂创作剧本,他渐渐感到,远离北京是不行的。作为内蒙厂头号编剧,厂里挽留他,给他住房等优厚条件,他还是对厂里说:“为了事业,我不得不去,但我今后会无偿为内蒙厂干事。”
他告别了草原。在北京,他的畅销书有人替他经纪包装,他的电视剧本可以由他来挑选剧组,他能对约稿人毫无愧色地说:“找我的大有人在,我按价论质,一句话,拍出你的金钱来,拿出我的智慧来。”近年江浩已完成了5部长篇,11部电影,近百集电视剧。他的《血祭黑河》以15万元高价被台湾制片商买走改编权,他的另一部作品换来了香港一家影视公司送他的一套两居室,他创作的20集电视剧《中国律师》每集片酬5000元,他给台湾制片商写的20集电视剧《把悲伤留给自己》,稿费共25万元。他刚完稿的电影剧本《红牌坊》,稿费10万元,合同上标明:“合同签字之日,甲方向乙方付酬5万元,乙方向甲方交稿之日,甲方再付5万元。款数额均为税后款。”江浩就是如此神奇。他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北京,如果我在大草原,如何来操作这些事呢?金钱的收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品位上的更新。在北京这个文化殿堂数年,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用大量有特色的生活素材堆砌,来掩盖自己哲学和美学的贫困,用带着卖弄色彩的笔者主观意识,来代替凝重的思考;那种导游似的风景画所展现的直观对象,缺少一种痉挛般的生命力。而在北京,我明白了许多,北京使我在文学上变了法,使我在心态上兼有都市和自然两种文化。
三
两个在京无窝的苦撑者
来北京的艺术人才生存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问及他们最大担忧和困惑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两个字:住房。
北京的房租可能是大城市里最高的,以至北京人在抱怨,百万外地人在北京,把饭馆价提高了,把房租也抬上去了。如今三环路内两居室月租金已达1500元,就是郊区简陋的农民房也不会低于300元。对于尚未成名的艺术青年来说,一进北京就等于每个月先背上几百元的债。艺术青年在困境中颇有相濡以沫的精神,他们合租一间房,把费用压到最低限度。他们互相打听什么剧组要人,什么歌厅缺歌手,争取早日告别拮据。
艺术青年不同于民工,他们在原籍大都家境不错,他们不是过惯了苦日子才来北京的,他们到北京后恰恰要先过上一段过去未过过的苦日子,要没有点对艺术执著的精神是很难挺过来的。山东青年歌手红霞生在军人家庭,生活很优裕,她从山东艺术学院声乐系毕业后曾获得省级歌手大赛奖,她在省级文艺团体完全可以成为台柱子,她却瞄上了北京。她进北京时只有200元钱和一把小提琴,她只能在音乐学院的宿舍里“打游击”,那些北京籍学生常回家,空下的铺位就是她暂时的栖身之处,她在前半年几乎没有睡过安稳觉。她这时才体会到家中三室一厅的住房是多么舒适和惬意,但她依然拒绝轻松而寻找压力,她辗转找到王扶林等老师,学习后感到长进不小。她又在朋友的介绍下“走穴”,虽然报酬一场才一二百元,但她更重视的是现场表演的机会。她进步很快,两年后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五洲杯”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获得通俗唱法专业组铜牌,这使她的境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机,中国广播艺术团聘她为合同制演员,她在市中心租了一间20平米的住房,她终于可以潜心钻研声乐了。度过难关,运气便来了,她的演唱专辑《让往事飞》已在今年问世,她离名歌星只有一步之遥。她庆幸自己的选择,回忆起初闯京城的日子,她感慨万端,那没着没落的日子至今仍透着辛酸。
在朝阳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对青年人,无论从外貌、气质还是神态看都与众不同,居民们都不相信这对高等艺术学府的毕业生会居住在胡同内最破旧的危房里。这间清朝年间盖的10平米小屋终日不见阳光,躺在床上能看到裂着大缝的房梁,使他们有种房屋随时都将塌下来的感觉。夏天,屋子闷得人进去就大汗淋漓;冬日用两个电热器才能使温度保持到七八度,他们不得不盖上三层被子才不致被冻醒。这对年轻人叫赵燕国和沙威,分别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他们的一些同学早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演员了,而他们还在为上演角色而奔波。其实,赵燕国家乡的话剧团准备让他当副团长,两室一厅的房子在等着他,沙威作为父母的独生女,也住惯了宽敞的房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可他们觉得,回去固然舒适安逸,却难以成气候,即使成了当地的尖子,也远不能使他们满足。在北京再苦再难,也是在向艺术的高峰冲击,冒险的追求要远胜过无为的安逸。
理想归理想,生活中住房、收入的危机始终困扰着他们。有一天他们身上只有10元钱,连两天的饭钱都难以维持,他们买了8包方便面,硬坚持了三天,一直接到父母电汇来的200元才度过危机,他们不能奢望什么高片酬,哪怕在片中有个小角色也好。他们跑了多少个电视剧组,多少次用期盼的目光等待着。但京城的竞争者太多了,无数个中央、北京的文艺团体演员在条件、关系上占有先天的优势,数不清的外地演员在北京争夺着有限的角色。为了生存,他们也不时干些与表演无关的活儿。赵燕国曾在一家广告公司搞艺术策划,老板许愿一定把他办到北京。他为公司赢了大利,半年多后他问老板何时兑现当初的许诺,交谈中他才发现老板根本没有考虑这件事。他也曾为一家电视台的节目搞过创意,当他通过一个电视上的大型晚会发现自己的创意完全被用,而署名报酬与他无关时,他才知道某些店大欺客的编导是多么无聊。他无法打官司,他甚至请不起律师一顿饭!更让小两口万般无奈的是,房主有一天通知他们,房屋马上要拆迁,限他们三天内搬家。家里的一堆东西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扔到马路上吧?一向刚强的赵燕国在夫人面前也缺少汉子气,他急得□然涕下,沙威也趴在他肩上哭起来。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的一位朋友为他们四处奔波,推荐他们到沈小萌、方青卓夫妇执导的《换个活法儿》剧组。方青卓这位获过“飞天奖”的演员见到沙威就说:“你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剧中小保姆,你会成功的。”他们的东西可以在剧组内存放几个月,他们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窝。沙威在剧中扮演一位小保姆,拍摄一段时间后导演沈小萌预言,剧播出后沙威就不必寻剧组了,剧组将会主动约她拍片了,她和赵燕国从此将有一个好的转折……
四
两位来京“文化
民工”的自述
刘殿军男35岁四川乐山人
我原来在老家开个体照相馆,对摄影特别有兴趣,一年赚个万儿八千块没问题。我想,我不能一辈子总在那里窝着,我热爱艺术,特别想拍电视剧,我干脆到北京去寻找心目中的好莱坞吧。既然北京有那么多民工,为什么就不能有文化民工呢?我告别了妻儿,他们很难过,在家乡我算高档次、高收入的人,到京城算个啥子哟?
经朋友介绍,到两个电视剧组当剧务,和北京小伙子比起来,我比他们会吃苦,什么脏活累活儿都抢着干,谁指使我我都像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我多想上个镜头啊,可我不能招人家讨厌,我要水到渠成后再提演戏的事。后来,有人介绍我去电影《冒牌皇帝》剧组,导演是刘国权,一位挺慈善的大姐,她对我为艺术而玩儿命的精神很赏识。有一次剧情需要替身钻火圈,大演员不愿钻,北京小伙儿也不玩儿这命,我自告奋勇说:“我来!”我根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我要用我的血肉之躯使人们认识我。我壮着胆子向火圈钻去,火燎焦了我的头发眼毛,我还是钻过去了,尽管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刘导演表扬了我,这比给我钱都痛快。后来剧情需要一个阴阳头,剃完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挨斗的反革命一样,谁愿出这个丑啊?我说:“我来!”只要能演戏,付出这么点代价算什么?阴阳头有什么关系,演完了剃个光头不就行了嘛!我第一次当了个大群众演员,还有特写镜头,日后我成了丑星,成了葛优,这个镜头就有纪念意义了。
现在我是片约不断,廉价的剧务、群众演员、替身兼于一身,哪个剧组都喜欢。要说日子,过得挺苦的,在老家我的客厅就有二三十平米,可在北京我和另两个也想当演员的外地青年合租一个8平米小屋,除去三张床,什么也放不下,有个人要洗脚另外两个人都得出去。至于吃的,就更别提了,北京的文化人都把吃方便面视作吃苦的象征,到我这里方便面就是佳肴了。为了当丑星,我一切代价都能付出。
头些天,我爱人发来三个急电,告诉我父亲病危直到病逝。可我在剧组里是个第七号人物,我一离开戏就耽误了。我没回去,买了几丈白布,在父亲的遗像前搞了个告别仪式,其他外地来京的艺术朋友都为我鞠躬,我大哭了一场。
我要为当丑星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今后有什么剧需要人,千万别忘了我,请帮我公布一下我的BP机,使导演能找得到我:4630127呼8275118。不同意透露姓名男32岁湖北人
我没北京户口。别看没户口,一年就赚了十几万,您未必有这实力吧?
5年前,我从湖北农村把女朋友带到北京时,觉得这座城市是那么冷漠,我们几乎到了无处栖身的地步。我们在郊区租了农民房,一个月50块的房钱都付不起。我当过建筑小工、木匠、瘫痪老人的“保姆”、垃圾战抢夺战利品的勇士、火车站前的挑夫……北京人看不起的活儿我都干过。最惨的一个月因付不起房钱被封了门,我和女友在北京站呆了一夜,第二天狠狠心卖了一次血,才算有了窝。我到北京,就是想到一个我久已向往的艺术院校进修,至于这个校名我也别说了,说出来我很容易被对上号。
我这种人最理解“穷则思变”,北京人最讲究的脸面我不在乎。衣食不足,谈得上什么荣辱?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进了一家民办的影视公司。我本来是个打杂的,我用尽一切手段巴结经理,北京的小伙儿、小姐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怕跌份儿啊!
我在影视公司的地位节节上升,后来终于在一人之下、十人之上。为了便于工作,经理说,以后你对外就算副经理吧。我掌管了一定的财权,我用尽智慧给经理提出钱来。我也小打小闹,每个月都有两三千块进项。
后来经理脑子一热,要亲自当导演拍电视剧。我终于发现,电视剧对掌管钱的人来说简直像管着一个没有手续的小银行。比如要建个摄影棚,二十万能建成,我就和对方讲二十五万。现在很多没有玩儿过导演的人都想当导演,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在艺术上是学徒工水平,在成本核算上是个傻瓜。电视剧组时常有实物赞助,那也是一笔糊涂帐,我常常拉出厂就卖一批,卖的钱当然与经理兼导演“合理分配”。
电视剧组最容易打架,哪部剧不动起手来就算奇迹。我处处、事事紧跟经理兼导演,把演员、工作人员的费用降低。有的演员骂我:“你纯粹是个跟屁虫。”很多人不会想到我曾在大桥下瑟瑟发抖,想不到我曾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我如今已是衣冠楚楚、油头粉面,还戴着价值一千多块的眼镜(这也是按剧组道具款报销的)。我有过在那所艺术院校业余旁听的经历,了解学校的概况,学到了大学生的派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大学毕业留京的文化人。
你看我多诚实,把自己的老底抖落给你。我还要说的是,一个连续剧下来我尽赚十几万,不算大款也是中款了吧?你们一看我的大哥大大概就能认可我的身分……
五
北京给他们的震荡
北京给搞文化艺术的外来人带来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缘。怀着各种憧憬到北京来的人,有成功的,有始终在苦苦追寻的。人就是这样的奇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人自身又变得难以把握。人只要往高处走,并随之得到生活的充实与愉悦,人的心理价值观念就要发生变化。那些走出国门的中青年男女,他们不少人的爱情与家庭要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那些来到北京成功或不成功的“艺术人”,他们原本海誓山盟乃至田园牧歌式的爱情,也在发生着某种嬗变。
这对年轻夫妇是一个中等城市话剧团的演员,他是剧团的台柱子,市报三天两头都要报道他的动态。无论《雷雨》还是《风雪夜归人》,他都是无可争议的男一号。她正是在对他的崇拜中,才释放出须臾不能分离的爱。婚后,他们如胶似漆,她常常呆呆地聆听他对艺术和人生的见解。每天清晨,她都要陪他跑3000米,然后到形体房练功。她在剧团里渐渐脱离了女服务员甲、女大学生乙的龙套角色,开始演剧中的三、四号人物,她觉得她唯一的导师是自己的先生。她怕失去他,他是这座城市的白马王子。哪怕他晚回来一个小时,她都心神不宁,都要站在门口久久地伫立着等待他。
他们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北京要拍一部电视连续剧,竞争女一号的已逾百人。他觉得她的文弱气质与主人公多少有点相似,劝她不妨来试一试。她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在本市剧团都不是女一号的她怎么去人才济济的北京竞争呢?他沉思了良久,以几乎是催促的口吻说:“去吧,我们还年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里。北京没有什么可怕的,刘晓庆、韦唯、张艺谋进北京时,不也像你一样默默无闻吗?再往远了和大了说,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只是个图书管理员,后来不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吗?”后面的例子尽管不恰当,却也极大地鼓舞了找不到信心和感觉的她。为了让她有底气,他亲自陪她进京,经济拮据,他们住在一家澡堂旅馆内,靠着当时只有4毛钱一包的方便面,度过了一周的艰难日子。在等待考试的几天,他们坐公共汽车玩了名胜古迹,他对她说:“这里地大,人的心胸与视野也随着大,皇帝选这块宝地太有眼光了,我们一定要冲进北京,走向全国,你这次不成功,咱们今后要接着冲。”
在试戏的前一天,他又一遍遍地帮她策划。进考场前,她又有点怵,他说:“你要再胆怯,我把你踹进去。”一句玩笑,让她轻松了许多。
几天后他们得知她成功了。她不禁泪流满面,一下扑进他的怀中。他轻轻地用手梳理着她的秀发,比她更高兴。她说她实在离不开他,她要通过这个戏在北京扎根,尽快把他接来。
在剧组里,她头几天都没有睡好,结婚后她没有一天离开过他。神情恍惚一段,她才平静下来。紧张的排戏,剧组内的欢乐,早日成名的欲望,使她心境渐渐好转。这个剧使她有机会接触各种人,沉浮的文化人,倜傥的小伙子,花钱潇洒的款爷。她感到过去的天地太小,使她太晚接触到各类优秀人才。 他来过几次北京,她的生疏感一点一点增加,奔放的热情在慢慢降温。他意识到了,内心多少有点忧虑,如果不早日来京,前景是莫测的,只是没有住房,他在北京耗不起。
电视剧上演,她成了明星。如果一年前大街上有人认出她是演员,她会感激,可如今她不得不戴上墨镜;如果过去有记者采访她,她会受宠若惊,可如今影响不大的报她会借故推掉了。
她想留在北京,她想向双栖发展,成为通俗歌星,她不愿意再回去过卿卿我我的小日子。她有了更远大的抱负,她对原先的生活不再满足。
她正在发愁落脚之处时,一家广告公司找她拍广告,她提出必须给她包一间能让她住几个月的宾馆,老板满口答应。老板也是搞表演出身后下海的,挺理解她再火下去的心理,他还是个办实事的人。老板不仅用她,还刻意包装她。她流露出要开独唱音乐会,能干的老板仅用三天便筹来10万元。她的歌只是卡拉OK歌厅的水平,但有钱开路,不仅租到了剧场,还在不少报发了消息与专访。尽管没有什么人买票,老板还是成功地策划成热闹非凡的假象。那一晚她陶醉了,她觉得自己又再度辉煌。老板把她送回宾馆,对她说:“我今天不回去了。”她没有惊愕,早在剧组,她就已经适应了这种事情。
这一切都让远方的他蒙在鼓里。直到他接到坚决离婚的信,他的幻想与愿望才彻底破灭。他在戏中演的都是大义凛然的男人,生活中的他却选择了用刀片割动脉,幸而同事发现早,才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同事写信告诉她,她说他不像个男人,都什么时代了还用这种方式殉情?
六
成功的代价
来北京的成功者是从无数苦苦追寻的人中脱颖而出的。那些腕儿级的人物当初的寒酸与苦斗,早已成为鼓舞后人的光荣奋斗史。闯京城文化圈的人,伴随的并不都是成功。人们可以看看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个村落,一些外地艺术青年租用着民工才住的简陋家舍,他们过着和民工没有什么差别的清苦生活。他们幻想当艺术家,理想的力量是神奇的,他们干得认真执著。这个剧需要他们被打得屁滚尿流,那个剧又需要他们从高处往下跳,他们都在所不辞。有的文学青年给文化掮客当“枪手”,他们的剧本只以几百元被收购,掮客再以几千元出售。舞蹈青年给晚会伴舞,唱歌青年在卡拉OK厅卖唱。这一切都是为了换来日后在京城的成功。祝晓彤和王爱妍是来自东北的年轻夫妇,祝晓彤是歌唱演员,王爱妍擅长写作。他们分别辞掉了地区歌舞团与报社的公职,租了300元一个月的农民房,日子当然清苦。他们四处托朋友,想先把王爱妍的剧本推出去。后来他们辗转认识了一个热心人,这个人说一定用自己在中央电视台的有利位置把剧本推出去,他分文不取,只是署个名字,而且在王爱妍的后面署。这条件也不算什么,夫妇二人对他感激涕零,并对这么好心的人是个瘸子深感同情。有一天夫妇俩去剧本拍卖市场,见到王爱妍的剧本被署上瘸子一个人的名字,夫妇俩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打听到这个左腿比右腿短半尺的人根本不是中央台的,而 一个无业混混,多次用各种手段行骗。祝晓彤找到这个人,说:“要不是怕给国家增加负担,我把你那条腿也打折了!”瘸子早已把原剧本撕毁,而他自己抄了一遍,他们之间又没有合同。祝晓彤也以“混”对“混”,他抓住此人的脖子就揍,直逼得瘸子当场签字承认真相才算了结。这件事也深深刺痛了祝晓彤的心,他不再托人,而是每月去医院抽一次血,以此交房钱和养王爱妍写作,他完全放弃了当歌唱家的愿望,力保王爱妍早日出道。王爱妍终于成功了,她用笔名写出两本通俗畅销小说,书稿卖给书商后,他们买下四环路边上的一个独居室。一些出版社来北京约稿请王爱妍吃饭,王爱妍总是带着先生,她总说:“他的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除了他,我不会再爱任何人。”北京有了几代移民,其中不少是文化人。最近十几年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的这些文化移民,难免盲动与无序。北京尽管给有志于搞文化艺术的人提供了最佳的地域和无数机会,但在北京成功,还要自身的条件与机会的契合。“北京是中国的好莱坞”,去那里就像下海一样,也同样会使人或沉或浮,会展现出比虚构还生动的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