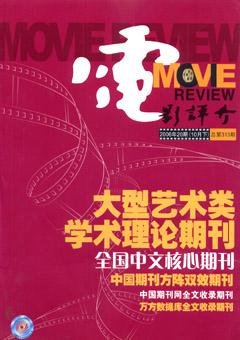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
魏红梅
[摘要]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以《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最为精绝。本文解读此词,并结合苏轼和贺铸的悼亡词作比较,体味纳兰合性德对亡妻惊心动魄、哀痛至忣的思念。[关键词]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悼亡至情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妻子卢氏的去世对纳兰性德的打击很大。在卢氏去世后,纳兰陆陆续续写了三四十首悼亡词,每首都哀痛至骨,其中以此篇《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最为精绝。
这首词开篇就是一个疑问句:“此恨何时已?”即“此恨不能已”,用问句的形式凸现感情的强烈,语气的不容置疑。然后“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的三句,表面是点明时间地点。却有多重含义:一是暗示作者思念亡人而夜深不眠,一直听着愁雨滴落空阶,于是愁雨愁人交融在一起。加重了气氛二是承接上句,意为一直滴个不停的雨也终有歇住之时,而作者思念亡妻之情却无法停止;三是“葬花”二字实指三年前妻子的殡葬之事。由上可知:纳兰为亡妻上了三年坟后,入夜不眠,而夜静之时雨打空阶的声音特别入伤心人之耳,刺伤心人的心直到更深夜寒雨停之时,词人才从思念之境回来,写下了这首词。
从词作内容看,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写于他梦醒之时,而纳兰呢,只觉得妻子去世后的这三年整个是一个大梦,而一个长达三年的人鬼相思之梦太长了,该醒来了,于是“三载悠悠魂梦杏,是梦久应醒矣”。生活在这样一个愁恨不已的世界里,当然是“料也觉、人间无味”,这样的人间,还“不及”那“尘土隔”的“夜台”,那里虽冷清,却有我亡妻在,那是我的“一片埋愁地”啊!作者哭诉道:“钗钿约,竟抛弃!”就是说,我们本有厮守一世的约定,你却早早走了,把我一个人抛弃在人世间受这死别相思之苦呢?要知道,纳兰此时并没有苏轼写《江城子》时身处密州的狼狈,年纪轻轻的他却身处显贵之位,深得皇帝之宠信,在别人眼中正是春风得意,但在他自己看来却只是无味人间。这样荣华富贵的人间在他眼中不及那冷清清的尘土相隔的坟墓。知道了这一层,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他对妻子的用情之深。
下片承接上片:“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自古悼亡之词,最为脍炙人口者除纳兰、苏轼的这两首之外,就是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了。无论苏词还是贺词,都是从自己的角度纯写自己的愁恨失意,而纳兰词则是为对方着想,他在想若九泉之下也能通信,就会知道妻子这三年来的喜怒哀乐,知道她在九泉之下与谁为伴了。显然这是一种情到深处的更高境界。而你在那边也一定想知道我过得怎样吧?我只是每个晚上都辗转难眠,也不忍听那凄凉的琴声。
“待结个、他生知己”这种情深之人的安慰之语,在深受亡妻之痛折磨的纳兰看来,这种安慰几乎是不存在的:“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要是下一辈子我们两个还是薄命呢?我们两个还是没有很好的缘分昵?我们这一辈子属于光风霁月的日子只有三年,下一辈子是不是还是大部分的时间只能剩月零风呢?这种恐惧心理的透露,让读者确信亡妻之痛对纳兰来说已经是渗透了他的灵魂,深入了他的骨髓。这样的语言说来平淡,细细深味,令人悲不能言。纳兰词在这一刻令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震撼于人间竟有如此至情之人,震撼于人间竟有如此真情,震撼于人间还有人有这样深情至极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不是情至极处,不是在至情之处徘徊许久,也就是说不是被这种至情之痛常年折磨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末尾以“清泪尽,纸灰起”作结。特别是动态的“纸灰起”,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意:这片片飞起的纸灰,连接了已亡人和未亡人,表达了未亡人对已亡人的无尽思念,也是未亡人对已亡人的承诺:你在那边先过着,不久之后,我要跟你团聚了。果然,五年之后,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就去世了。
纳兰性德的这首词虚虚实实,有梦幻有空想,看上去有些凌乱,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其实词中的每一句在感情上都有铺垫,下面的每一句都是承接上面的词句而来从感情的脉络看来,这首词写得也非常自然,感情步步深化,步步升华,达到极致之时,又以“清泪尽,纸灰起”作结,于是那种深情就随着飞扬的纸灰刻在了读者的心里。严迪昌的《清词史》评价此词“情伤肠断、语痴入骨”,是“一段痴情裹缠、血泪交溢的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语”。
若把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鹧鸪天》与纳兰的这首《金缕曲》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不少信息。
三词相似之处:苏词的“不思量,自难忘”,就是纳兰词的“此恨何时已”之意,不过苏词较为柔和,纳兰词较为激烈而已;贺词的“同来何事不同归”,就是“钗钿约,竟抛弃”之意,只是贺词更为概括,纳兰词较为直接而已;贺词有“空床卧昕南窗雨”,其实就是纳兰词“滴空阶、寒更雨歇”之意三首词都提到了坟墓,也提到了自己和妻子同居过的房间。
若论不同之处:纳兰写这首词时仅仅二十六岁,是个翩翩少年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三十九岁了,在古代,这已是标准的中年人了:贺铸词中有“头白鸳鸯失伴飞”。可见他应是老年失伴。写这首词时当然已是暮年了。另外,关于三词的写作背景:苏轼这时在密州的处境颇有些狼狈,词中“尘满面,鬓如霜”之语可以证明;贺铸也是郁郁不得志;最年轻的纳兰,身居要职。颇得皇帝宠信。
由以上两段分析,我觉得贺词苍凉深沉,没有少年人和中年人直接的感情宣泄,更多的是一种含蓄,于是他的词中没有梦和泪,可以称作老年人的睿智之作;苏词大气整齐,骨肉丰满,确实是中年人的成熟之作而纳兰词呢,完全是凭着感情凭着思绪任意而为,意到笔到,直接是少年人的任性之作,血泪之作。三者比较,虽然都给人以伤感凄凉,但贺词却令人深思感悟,苏词则令人咀嚼不已,纳兰词则直接令人惊心动魄。诗词是抒情的工具,只要那一段情高出众人,为他人所不及,就是顶尖的作品。
另外,苏轼、贺铸在落魄之时写下悼亡名作。若这两人官居高位,是不是还能写出这么凄凉之至的词来?如果能,我们怎么没看到?可是,纳兰却是在自己官场得意之时写出这些作品来的,甚至妻子的去世直接影响了他的性情,使他改变了人生观,也使他改变了词风,甚至也是促使他早逝的重要原因,这种境界,苏轼、贺铸能达到吗?